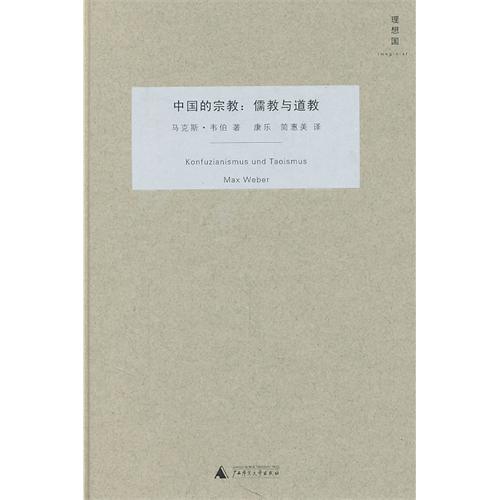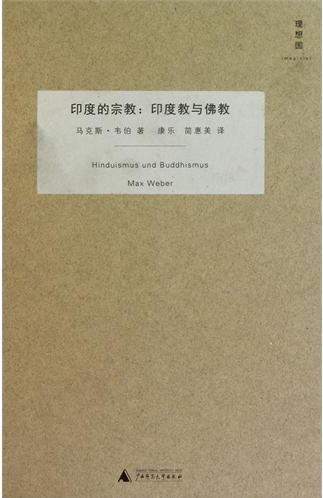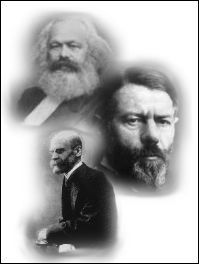個人生活 妻子:瑪麗安娜·施尼特格爾(Marianne Schnitger),韋伯一名遠親的表妹;
個人生平 1864年4月21日,馬克斯·韋伯生於
德國 圖林根的埃爾富特市,不久舉家遷至
柏林 。他的父親是出身於
威斯特伐利亞 紡織業實業家兼批發商
家庭 的一位
法學家 ,是當地知名的政治家,其父親的職業為家庭營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圍,青年時代的韋伯便在他的父母親的客廳里結識了當時知識界和政界的許多傑出人士,如
狄爾泰 、莫姆森、聚貝爾、特賴奇克和卡普等人。在1882年韋伯進入了
海德堡大學 的
法律 系就讀。和他父親一樣,韋伯選擇以法律作為主要學習領域,並且也加入了他父親讀大學時的曾經加入的社團。除了法律的學習外,年輕的韋伯也學習了
經濟學 、中世紀歷史、神學。此外他還在斯特拉斯堡加入
德國國防軍 服役了一小段時間。
1882年進入
海德堡大學 學習法律,1883年在
斯特拉斯堡 服兵役一年,1884年的秋天,韋伯回到老家以後就讀於
柏林大學 ,在接下來8年裡,除了曾至
哥廷根大學 就讀一個學期並且又服了短期的兵役外,韋伯一直都待在柏林研究深造。韋伯與雙親住在一起,除了繼續學業外,韋伯也擔任實習律師,最後則在柏林大學擔任講師。韋伯在1886年通過了律師“實習階段”(Referendar)的測驗,成為實習法官。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韋伯繼續他對歷史的研究。在1889年完成了一篇標題為“中世紀商業組織的歷史”的博士論文,取得了他的法律
博士學位 。兩年後,韋伯寫下了一本名為《羅馬的農業歷史和其對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的書,完成了他的教授資格測驗(Habilitation),韋伯也因此成為正式的大學教授。
在韋伯即將完成博士論文的那一年裡,韋伯也開始對當時的社會政策產生興趣。在1888年他加入了一個名為“社會政治聯盟”(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的團體,這個專業團體成員大多是當時隸屬
經濟歷史學派 的德國經濟學家,他們將經濟視為是解決當時廣泛社會問題的主要方法,並且對當時的德國經濟展開大規模的統計研究。在1890年,聯盟成立了一個專門的研究計畫,以檢驗當時日趨嚴重的東部移民問題(由於當時德國勞工逐漸遷往快速工業化的德國城市,大量外國勞工遷徙至
德國 東部的農村地區)。韋伯負責這次研究,並且寫下了許多調查結果。最後的報告得到良好評價,被廣泛認為是一篇傑出的觀察研究,也因此鞏固了韋伯身為農業經濟專家的地位。
在1893年韋伯與一名遠親的表妹瑪麗安娜·施尼特格爾(Marianne Schnitger)結婚,她後來也成為了一名女性主義者和作家。新婚的兩人在1894年搬家至
弗萊堡 ,韋伯在那裡獲聘為弗賴堡大學的經濟學教授。1896年韋伯也被獲聘為其母校
海德堡大學 的教授。一年後韋伯的父親去世了,在他死前兩個月父子間剛巧經歷了一場激烈的爭吵,這場沒有和解的爭吵成為韋伯畢生的遺憾。在那之後韋伯患上了
失眠症 ,個性也變的越來越神經質,使他越來越難以勝任教授的工作。他的精神狀況使他不得不減少教學量,並且在1899年的學期中途休假離開。韋伯在1900年的夏季和秋季於精神療養院休息了數個月的時間,接著在年底和妻子前往
義大利 旅遊,一直到1902年的4月才返回
海德堡 。
在1890年代初期著作頻繁的幾年後,韋伯在1898年直至1902年底都沒有再發表任何著作,最後終於在1903年秋季辭去了教授的職位。在擺脫了學校的束縛後,韋伯在那一年與他的同事維爾納·松巴特(Werner Sombart)創辦了一本名為“社會學和社會福利檔案”的社會學期刊,由韋伯擔任副編輯。在1904年,韋伯開始於這本期刊發表一些他最重要的文章,尤其是一系列名為《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的論文,這後來成為他畢生最知名的著作,並且也替他後來許多針對文化和宗教對經濟體系的影響的研究奠定根基。這篇論文是唯一一篇他在世時便已出版成書的著作。也是在那年,韋伯前往美國旅遊,並且參與了當時在聖路易斯所舉行的社會和科學大會——那也是世界博覽會相關的大會之一。儘管韋伯表現的越來越成功,他仍覺得自己無法再勝任固定的教學工作,因此繼續維持著私人學者的身份。1907年韋伯獲得一筆可觀的遺產,也使他得以繼續專心研究無須擔憂經濟問題。在1912年,韋伯試著組織一個左翼的政黨以結合
社會民主主義 者和
自由主義 者,最後並沒有成功,主要是因為當時的自由主義者仍擔憂社會民主主義的革命理念。
1914年大戰爆發後,馬克斯·韋伯參加軍隊服役,負責駐在海德堡的幾家醫院的工作直到1915年底,期間《世界性宗教的經濟倫理》的一部分(《序》和《儒教與道教》)出版。1916年多次去
布魯塞爾 、
維也納 和
布達佩斯 執行各種非正式的秘密使命,盡力勸說德國的領導人物避免擴大戰爭,同時他也斷言德國對全世界政治負有責任,並認為俄國是主要威脅。
1919年應聘去
慕尼黑大學 任教,接替
布倫塔諾 教授的工作。在1919至1920年間講授的是
普通經濟學 史,後成書,於1924年出版。韋伯支持共和國,但並不熱情。他參與慕尼黑的庫爾特·埃斯納的革命專政,是魏瑪憲法起草委員會的成員之一。
(少年時期的馬克斯·韋伯圖冊參考資料來源:)
學術成就 馬克斯·韋伯與
卡爾·馬克思 和
愛米爾·涂爾幹 被並列為現代
社會學 的三大奠基人,儘管他在當時主要被視為是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涂爾幹遵循著
孔德 的方式,以社會學的
實證主義 進行研究。而韋伯以及他的同僚維爾納·松巴特(也是德國社會學最知名的代表人物)採納的則是
反實證主義 的路線,這些著作開始了反實證主義在社會科學界的革命,強調
社會科學 與
自然科學 在本質上的差異,因為他們認為人類的社會行為過於複雜,不可能用傳統自然科學的方式加以研究。
韋伯的早期著作通常與
工業社會學 有關,但他最知名的貢獻是他後來在
宗教社會學 和
政治社會學 上的研究。韋伯在《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中開始了他的研究,文中他顯示出某些禁慾的新教教派—尤其是
加爾文教派 ,教義逐漸轉變為爭取理性的經濟獲利,以此表達他們受到上帝的祝福。韋伯主張,受到這種理性教義基礎扶助的資本主義很快便會發展的越來越龐大,並且與原先的宗教產生矛盾,到最後宗教便會無可避免的被拋棄。韋伯在後來的作品裡繼續研究這樣的現象,尤其是在他對官僚制和對於
政治權威 的分類上。在這些著作中他隱約了這種社會的理性化是無可避免的趨勢。
宗教社會學 韋伯在
宗教社會學 上的研究開始於名為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的論文,並且繼續在《
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 》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的社會學》、《
古猶太教 》里進行探索。他對於其它宗教的研究則由於他在1920年的突然去世而中斷,使他無法繼續在《古猶太教》之後的一系列研究—包括了計畫中對於詩篇、塔木德
猶太人 、以及早期
基督教 和
伊斯蘭教 的研究。他所完成的那三個主要研究都關注於宗教對於經濟活動的影響、社會階層與宗教理想間的關係、以及西方文明的獨特特徵。
在《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中,韋伯提出了一個知名的論點:“那就是
新教徒 的生活倫理思想影響了
資本主義 的發展。一般宗教的傳統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務,尤其是經濟成就上的追求,但為什麼這種觀念沒有在新教里發生呢”,韋伯在這篇論文裡解釋了這個悖論。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韋伯將“資本主義的精神”定義為一種擁護追求經濟利益的理想。韋伯指出,若是只考慮到個人對於私利的追求時,這樣的精神並非只限於西方文化,但是這樣的個人——英雄般的企業家——並不能自行建立一個新的經濟秩序(資本主義)。韋伯發現這些個人必須擁有的共同傾向還包括了試圖以最小的努力賺取最大的
利潤 ,而隱藏在這個傾向背後的觀念,便是認為工作是一種罪惡、也是一種應該避免的負擔,尤其是當工作超過正常的份量時。“為了達成這樣的生活方式而自然吸納了資本主義的特質,能夠以此支配他人”韋伯如此寫道:“這種精神必定是來自某種地方,不會是來自單獨的個人,而是來自整個團體的生活方式”。
他的目標是為了找出東西方文化發展差距的主要原因。不過與當時許多遵循
社會達爾文主義 的思想家不同的是,韋伯最初並沒有打算衡量和評斷東西方兩者的優劣;他希望專注於研究並解釋西方文化特殊之處。在他的研究分析里,韋伯指出卡爾文主義(或者更廣泛的—基督教)宗教理想的影響成為
歐洲 和美國的社會變革以及經濟體系發展的主要原因,但他也指出這並非促成發展唯一的因素。其它重要的因素還包括了
理性主義 對於
科學 的追求、加上
數學 的科學統計、法律學、以及對於政府行政理性的系統化、和經濟上的企業。最後,依據韋伯的看法,
宗教社會學 的研究只不過是探索一個階段的變革,亦即那些讓西方文明突出於其它文明之外的重要特徵。
《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是韋伯在
宗教社會學 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韋伯專注於探索
中國 社會裡那些和
西歐 不同的地方—尤其是與清教徒的對照,他並且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資本主義沒有在中國發展呢?”韋伯專注於早期的
中國歷史 ,尤其是
諸子百家 和
戰國 ,在這個時期主要的中國思想學派(
儒教 與
道教 )開始突顯而出。
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
韋伯指出儒教對於許多民間教派的信仰展現相當寬容的態度,而從沒有試著將他們統一為單獨的宗教教義。與一般形上學的宗教教義不同的是,儒教教導人們要順著這個世界進行調整和修正。“高等”的人們(
知識分子 )應該避免追求財富(雖然沒有貶低財富本身),也因此,中國變成了一個擔任公務員比商人擁有更高社會地位和更高利益的國家。
韋伯主張,雖然有一些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有利的因素存在(長期的和平、運河的改善、人口增長、取得土地的自由、遷徙至出生地以外的自由、以及選擇執業的自由),然而這些有利因素都無法抵銷其它因素的負面影響(大多數來自宗教):
① 技術的改革在宗教的基礎上被反對,因為那可能會擾亂對於祖先的崇敬、進而招致壞運氣,而調整自身適應這個世界的現狀則被視為是更好的選擇。
②對於土地的賣出經常被禁止、或者被限制的相當困難
③擴張的親戚關係(根基於對家庭關係和祖先崇敬的宗教信仰上)保護家庭成員免受經濟的困境,也因此阻撓了借債、工作紀律、以及工作過程的理性化。
④那些親戚關係也妨礙了城市特殊階級的發展,並且阻撓了朝向完善法律制度、法規、和律師階級崛起的發展。
依據
韋伯 的說法,儒教和新教代表了兩種廣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兩者都試著依據某種終極的宗教信仰設計人類生活。兩者都鼓勵節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與財富的累積相併存。然而,儒教的目標是取得並保存“一種文化的地位”並且以之作為手段來適應這個世界,強調教育、自我完善、禮貌、以及家庭倫理。相反的,新教則以那些手段來創造一個“上帝的工具”,創造一個能夠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這樣強烈的信仰和熱情的行動則被儒教的
美學 價值觀念所排斥。因此,韋伯主張這種在精神上的差異便是導致資本主義在西方文明發展繁榮、卻遲遲沒有在中國出現的原因。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的社會學》是韋伯在
宗教社會學 上的第三本主要著作。在這本書中他檢驗了
印度 社會的架構,對照了正統的印度教教義與非正統的佛教教義,以及其它民間信仰的影響,最後並研究這些宗教思想對於印度社會在現世上的道德觀的影響。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的社會學
印度的社會體制是由
種姓制度 的概念所形塑,直接連結了宗教思想與社會上的階級分隔的關係。韋伯描述這種種姓制度是由
婆羅門 (僧侶)、
剎帝利 (戰士)、
吠舍 (商人)、
首陀羅 (勞工)所組成。接著他指出種姓制度在印度的散布是因為歷史上的征服侵略所造成,某些部落遭到了邊緣化、種族制度也因此越來越根深蒂固。
韋伯特別專注於對婆羅門階級的研究,並分析他們為何能夠占據印度社會的最高階級位置長達數個世紀。在研究了佛法概念的影響後,韋伯總結認為印度社會的道德觀多元傾向,與儒教和基督教普世而統一的道德觀不相同。如同中國一樣,他注意到種姓制度也妨礙了印度都市獨特階級的發展。
在研究的總結里,韋伯將他對於印度社會學和宗教的研究與之前對中國的研究綜合起來。他注意到這些宗教都將人類生命的意義解釋為超脫世俗的或是神秘性的經驗,這些社會的知識分子通常傾向於厭惡政治,而社會架構往往被區分為受過教育與否的兩種階級,那些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作為先知或智者的榜樣,而未受教育的大眾則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庸俗里並且相信迷信的民間巫術。在
亞洲 社會,如同基督教彌賽亞一般、能夠不分受過教育與否皆給予救贖和指引的救世主並不存在。韋伯主張,正是因為彌賽亞救世主起源於
近東 國家,使得他們與亞洲大陸的主要宗教產生差異,西方國家也因此免於陷入中國和印度的道路。韋伯在他下一本著作《
古猶太教 》進一步證實了這個論點。
《古猶太教》 是韋伯對於
宗教社會學 的第四本著作,韋伯試著解釋“各種情況的結合”導致了早期東方和西方文明的差距。尤其是將
西方基督教 的世俗禁慾主義與印度發展出的神秘冥思信仰相對照時,這種差異顯得特別明顯。韋伯注意到一些基督教的觀點帶有征服和改變世界的理想,而不加以逃避之。這種基督教的基本特徵(當與遠東的宗教相對照時)則是源於古代猶太人的先知。當韋伯述及他研究古猶太教的原因時,他寫道任何在現代歐洲文明傳統下成長的人都會自然的以一連串的假設來解決遇到的歷史問題,這對他而言是不可避免而且也相當合理的。這些問題將可以找出在各種情況的結合下,西方文化的獨特之處、以及其普遍的獨特文化涵義。
古猶太教
韋伯分析了中東
貝都因人 、城邦、牧人和農夫、和他們之間的互動和衝突,以及
以色列 聯合王國的興起和衰落。聯合王國的時期就彷佛歷史中的一個插曲,將《出埃及記》以來的聯邦時期與以色列人在
迦南 的殖民時期一分為二。這種時期的區分和宗教的歷史有極大關係,由於猶太教的基本教義是在以色列聯邦時期形成的,它們在聯合王朝衰敗後成為了先知概念的基礎,並在後來對西方文明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韋伯討論了早期以色列的聯邦架構、以色列人與耶和華的獨特關係、外國宗教的影響、宗教狂熱的形式、以及猶太教祭司們對抗宗教狂熱和偶像崇拜的鬥爭。他接著描述了王國的分裂、聖經的先知們在社會方面的態度、蠱 惑人心的政客、宗教迷信和政治,以及先知們的道德觀。韋伯注意到
猶太教 不只是
基督教 和
伊斯蘭教 的始祖,同時也是現代西方世界崛起的關鍵因素,因為它影響了
古希臘 和古羅馬的文化。
政治社會學 在政治和政府的社會學上,韋伯最重要的貢獻之一便是一篇名為《政治作為一種職業》(Politik als Beruf)的論文。在這篇論文裡韋伯提出了對
國家 的定義:亦即國家是一個“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地位”的實體,這個定義成為西方
社會科學 的重要基礎。在這篇論文裡韋伯主張,政治應該被視為是任何會影響到控制暴力的權力分配的活動。政治也因此是純粹來自於權力。
韋伯提出了三種正式的
政治支配 和權威的形式:魅力型權威(家族和宗教)、傳統權威(
宗主 、父權、封建制度)、以及法理型權威(現代的法律和國家、官僚)。韋伯主張歷史上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關係多少包含了這樣的成分。 他認為魅力型權威的不穩定性必然導致其被迫轉變為“常規的”權威形式,也就是傳統或者官僚型支配。同樣的,他也注意到在純粹的傳統型支配里,對於支配者的抵抗到達一定程度時便會產生“傳統的革命”。因此韋伯也暗示了社會會逐漸朝向一個理性合法的權威架構發展,並且利用官僚的架構制度。儘管韋伯龐雜的著作中暗示這種社會的理性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他自己十分小心避免進化論與
目的論 的邏輯。
韋伯在三種正當支配之外,還曾經提出義大利的城市
共和 政治是一種非正當的支配,可見他的支配類型學仍有模糊之處。他對民主政治魅力型領袖與官僚鐵籠之間互動的悲觀,也對後世的民主理論,特別是
熊彼得 的精英政治學說,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韋伯對
魏瑪 民主的看法似乎預見了納粹的興起。
經濟史學 從經濟學家的觀點來看,馬克斯·韋伯代表的是德國的
經濟歷史學派 “最年輕的一代”。他對於經濟學最重要的貢獻是他的知名著作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這本書經典的對照了宗教在經濟發展上產生的影響。韋伯的研究領域也與他的同僚維爾納·松巴特相同,宋巴特則將資本主義的崛起歸功於猶太教的影響。韋伯對於經濟學的其它主要貢獻(整體上也是對於社會科學的貢獻)還包括了他在方法學上的研究:他對於解釋社會學(Verstehen;此詞來自德語,意為理解)的理論和
反實證主義 (又稱為
人文主義 社會學)。
解釋社會學的原則是社會學主要的研究範例之一,支持者和批評者都相當多。這種研究方式主張社會學、經濟學、和歷史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永遠不能徹底的歸納和記載,因為研究者必須一直有著概念上的認知才能加以探索之,韋伯將這種條件稱為“理想形式”(Ideal Type)。這種理想可以這樣子歸納:一個理想的形式是由許多現象提供的某些特徵和成分所組成,但它卻不會與任何特定的現象有著完全一樣的特徵。韋伯的理想形式成為他對社會科學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韋伯承認這種“理想形式”是一種抽象的產物,但他主張任何想要了解特定社會現象的人都必須有這種理想形式,因為與物理的現象不同的是,社會科學還牽涉到複雜萬分的人類行為,而這隻有可能以理想形式的方法來加以解釋。理想形式的概念,加上他的反實證主義的立論,可以被視為是他對“理性的經濟人”的方法論假設的辯護。
韋伯並且公式化了社會階層的三大要件理論,主張社會階級、社會地位、和團體(或政黨)在概念上是不同的要件。
1. 社會階級是以在經濟上與市場的互動所決定的(物主、承租人、員工等等)。
2. 社會地位是以非經濟的成分如榮譽、聲望和宗教構成。
3. 政黨則指一個人與政治界的聯繫。
而這三種要件都會影響到韋伯稱為“生涯機會”的結果。
韋伯對經濟學還有其它一些貢獻:包括了經過認真研究的
羅馬 農業歷史,和他在《經濟和社會》一書里述及的
唯心主義 及唯物主義兩者對於資本主義歷史的影響,韋伯也在書中呈現了對於
馬克思主義 的一些批評。最後,他在《經濟與歷史》(Wirtschaftsgeschichte)中的仔細研究則可以被視為是經濟歷史學派最傑出的作品之一。
主要作品 社會總評 馬克斯·韋伯被譽為“組織理論之父”。
馬克斯·韋伯關於基督
新教倫理 決定經濟發展的觀點和歐洲的發展本身相矛盾。
義大利 北部地方、
巴伐利亞 、
萊茵河 地區、西班牙和法國等地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經常被看作資本主義發展單一因素決定論的反例,包括地理的、政治的或者其它單一因素的決定論,也包括新教倫理理論。一般認為歷史上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力在於財產權的加強、交易成本的降低、封建主義的衰落和瓦解等。
韋伯、馬克思與迪爾凱姆(涂爾幹)。
在現當代,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台灣、新加坡、日本等地在經濟上取得了繁榮,而這些地區是具有儒家價值觀的社會。東亞地區的成功,也和基督教沒有關係。因此,表面看來馬克斯·韋伯關於基督新教倫理和經濟發展的理論似乎與事實相悖。但是,馬克斯·韋伯在他的研究中僅僅試圖揭示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精神形成初期的所扮演的“火車扳道工”角色,此後的
資本主義 風尚(ethos)在時空的推移中獲得了新的非宗教性能量和執著物慾的理由,人類歷史也就此走上了新的軌道。
韋伯的主要著作圍繞於社會學的
宗教 和政治研究領域上,但他也對
政治 、
經濟學 領域作出極大的貢獻。他的知名著作《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是他對
宗教社會學 最初的研究。韋伯將國家定義為一個“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地位”的實體,這個定義對於西方現代政治學的發展影響極大。他在各種學術上的重要貢獻通常被通稱為“
韋伯命題 ”。
韋伯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他的成就開創了
比較社會學 、
理解社會學 的基本研究方法,指出了理性對於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潛移默化的影響,系統的闡釋了東西方宗教倫理差異對於社會現代性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他和
迪爾凱姆 被認為是宗教社會學最早的開創者,也是
巨觀社會學 的集大成者。其學術成就之宏大精深,影響之深遠,在社會學界乃至整個世界社會科學理論體系上都是空前絕後的,他的思想體現了一個博大的智慧之神。
名人點評 美國社會學家
科瑟 對韋伯的學術淵源和成就讚譽說:“韋伯的頭腦容量大得驚人,影響他思想的因素多種多樣。他不是
哲學家 ,但在大學讀書時就熟悉大多數古典哲學體系。他不是神學家,但他的著作表明他廣泛閱讀過神學書籍。作為經濟
史學家 ,他幾乎讀遍了這個領域以及經濟理論的一切著作。他具有第一流的法律頭腦,對法律的歷史和原理了如指掌。他對古代史、
近代史 以及東方社會的歷史具有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當然,他專心研讀過當時所有重要的社會學論著,就連那時還鮮為人知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也為他所熟悉。韋伯是最後一批博學者中的一個。”
1917年時代韋伯
著名經濟學家
熊彼特 用一句話讚揚韋伯:“歷來登上學術舞台的角色中最有影響的一個。”
英國 傳記作家D·G
麥克雷 說:“我相信,韋伯對我們來說的確就是一座迷宮。”
英國社會學家、哲學家
弗蘭克·帕金 的評價:“韋伯就像幾乎和他同時代的
迪爾凱姆 一樣,在任何一套論及重要社會學家的叢書中,都應占有一席之地。不論在哪裡講授社會學,他的名字總是跟迪爾凱姆和
馬克思 結合在一起,被奉為社會學的三位現世神明”。
美國社會學家根瑟·羅思認為:“韋伯是惟一能同
卡爾·馬克思 相提並論的思想家”。
美國學者萊因哈特·本迪克斯認為:“韋伯有一種特殊的能力,即把判斷與比較歷史的方法對其確定性進行核對的能力。”
德國著名哲學家
卡爾·雅斯貝爾斯 認為,馬克斯·韋伯是一個集政治家、科學家、
哲學 家於一身的人物。“儘管由於命運和環境的作弄,他沒有在政治方面享有顯赫的地位,但卻毫不減損他傑出政治家的本色,他的偉大就像一個沒有手的
拉斐爾 ,沒有功績但卻有無限的潛力。”
德國著名的韋伯研究學者莫姆森(Wolfgang J.Mommsen)強調了韋伯對
官僚 組織之外的民選領袖的認識,指出:“韋伯將偉大
政治領袖 的產生作為議會民主的最重要的功能,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其合法性的最重要的源泉。”
英國學者戴維·比瑟姆則突出韋伯的民族主義和
愛國主義 特色,指出:“韋伯在政治上的民族(國家)主義價值立場,正是以對民族文化價值的優越性的堅定信念為核心的。”
哈佛大學 的歷史學教授休斯曾經指出:“韋伯的腦袋是一個能夠容納多種矛盾思想的神經系統。總的看來,韋伯既是一個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又是一個學術上的民主主義者;既是一個不受傳統宗教觀念束縛的自由學者,又是一個對宗教傳統抱有濃厚興趣的社會學家;既是一個批判社會主義的理論家,又是一個十分敬重
馬克思 及其學說的思想家。”
英國學者
麥克雷 認為:“從某個觀點來說,韋伯是個
歷史 主義者,韋伯開始的著眼點是把社會學視為史學,對他而言,所有人類的實相都可以在時間的向度里及史家的方法論中被理解”。
當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法蘭克福學派 的
哈貝馬斯 指出:“在韋伯的合理化理論中,法律發展既具有突出的地位,也具有雙重意義的地位。法律合理化的雙重意義在於,法律合理化同時表現為目的合理經濟行動和行政管理行動的機制化,以及目的合理行動的下屬體系可以——或者似乎可以擺脫它們道德實踐的基礎。”
“韋伯之問” “
韋伯之問 ”即韋伯在《
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 》等著作中反覆提出的:為何中國、印度這樣的東方社會,沒能在政治、經濟、
科學 乃至藝術領域走上獨立於西方之外的理性化道路?在國際範圍內看中國研究的許多重要命題,都能感受到韋伯思路的影響。“韋伯之問”是“
中國學 ”的核心課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