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最讓李文俊先生感到不枉此生的事,就是
翻譯介紹了美國重要作家福克納。在
西方現代文學中,福克納的作品以艱深著稱,而李文俊以令人欽佩的勇氣和毅力啃下了這塊硬骨頭,翻譯了福克納最艱深的作品。
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福克納文集》7部作品中,李文俊譯了4部重要作品,有《喧譁與騷動》 、《押沙龍,押沙龍!》、《
我彌留之際》、《
去吧,摩西》。
李文俊在他65歲到68歲即1995年到1998年這三年間翻譯了這部福克納最難譯的作品,完成了此生最大的心愿,他因此把自己累垮了,發作了心肌梗塞。而他對此無怨無悔,他除了翻譯福克納作品,還寫了福克納評傳和畫傳,編譯了《
福克納評論集》,在譯《福克納隨筆全編》,覺得對得起福克納這位大師了。做成了自己最想做的事,快樂莫大於此,即使付出代價也在所不惜。
除了譯介福克納,他還參與撰寫了《
美國文學簡史》、《大百科全書英美卷》,獲過“中美文學交流獎”等獎項。
學術風格
有句老話,叫做“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李先生的散文集本來就不多,也唯讀過這一本《縱浪大化集》,但單單從這本集子就可以看得出,他的散文功夫也十分了得。創作與翻譯不同,不需要“帶著鐐銬跳舞”,散文創作更是如此,只有拋開前人束縛,“我手寫我口”,讓情感自然地在筆端流淌,才有可能寫出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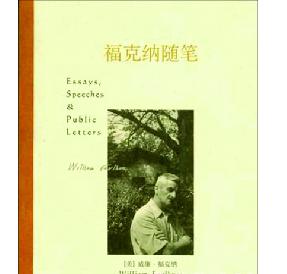 李文俊作品
李文俊作品李先生的散文,也多是這般“信筆”而作,在冷靜中抒情,在灑脫中執著,在嚴肅中幽默,情真意切,毫不矯飾——長此以往,很多職業散文家的飯碗恐怕難保了。在《縱浪大化集》中,感情最真切的一篇是《負疚感》。其中,有這樣一個
情節:小時候,他天天與妹妹一起上學,兩人各帶幾塊餅乾,邊走邊吃。哥哥吃得塊,妹妹卻捨不得一下子吃光,只是“像蠶寶寶吃桑葉那樣沿著邊緣一點點啃”。於是,哥哥便以不帶她過馬路作威脅,想要騙取妹妹的餅乾,結果:“她從不肯,到猶豫,到作出決定,必然有一番思想鬥爭——每天如此!但最後總是不得不忍痛割愛。單從一兩片餅乾看,事情不值得一提,但就兒童心靈所受的折磨來說,則是與一個無辜者受冤獄相差無幾。”
魯迅先生的名篇《風箏》 ,這兩篇散文的情感有相通的地方。寫人最妙的,是《我所知道的蕭乾》這一篇。作者僅僅通過幾件小事,便把
蕭乾先生寫得活靈活現,好像正置身於讀者眼前。更妙的是,對
冰心、
沙博理等人,文中雖只寫了幾筆,卻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文中曾講了這樣一件事:一次,作者與蕭乾先生一同去已加入中國籍的美國人沙博理家作客。談話中,作者發現沙博理的京腔比自己還地道,便用英文跟他對話。可是,在談到“書評”一詞時,作者使用了一個不常用的單詞“criticism”:“蕭乾一聽,怕引起不良國際影響,趕緊解釋說李先生的意思是‘review’,亦即書評的意思。
華籍美人沙博理不愧是大紐約市律師出身,他不動聲色地給我打圓場,以母語使用者的權威身份說,在英語中,criticism也有評論的意思,甚至包括好評。”
看,作者用這么短的一段,就寫出了
蕭乾先生的政治敏感,還有
沙博理的寬容性格。(其中的“華籍美人”一詞,甚為幽默。) 在《毅力可佩》一文中,作者又換了一種筆法,只是“老老實實”地敘述
羅新璋先生為學習翻譯所下的“死功夫”。當我從中讀到,羅新璋先生“曾將好幾部
傅雷的譯文,逐字逐句抄在法語原作的字裡行間,用這個方法來學習翻譯”,“單是《約翰·克里斯朵夫》就抄了120萬漢字”時,不由得也對羅新璋先生產生了敬意。
此外,《同夥記趣》、《家璧先生與福克納的初版本》這兩篇寫人的文章也很有意趣。前者生動地敘述了錢锺書夫婦批點原版《
大衛·科波菲爾》的情形,後者則表現了一位愛書人的敦厚長者之風。在《從未出過那么多汗》一文中,有這樣一句話:“我沒有寫出宏篇巨構,更沒有富起來,但這不要緊。我的工作就是娛樂。”李先生的灑脫和執著,由此可見。在《也談文學翻譯批評》一文中:李先生又說:“若是真的受到批評,而且言之鑿鑿,確有道理,老譯家亦不妨豁達超脫一些。不必弄得心煩意亂,摧殘自己的健康。……倘若評文作者有借評名家以自重的不純動機,對其無理糾纏處,不妨加以教訓,好讓後生小子們知道廉頗雖老,卻尚善飯,手中有真理的老者也是不好欺負的。這樣一來,譯壇有連台本戲好看,攻守雙方大腦皮層也會活躍起來。退一步說,受批評也總比全然漠視滋味好受一些。”
 李文俊作品
李文俊作品這樣豁達的胸襟,也不是一般的譯者所能具有的。於李先生的嚴肅與幽默,在他的散文中幾乎處處都有,這裡抄幾處精彩的:“(聖經)裡面的神在詛咒不義之人時所用的語言,與我們今天的市井小民的罵罵咧咧,竟無多大差別:‘你的妻子必在城中作妓女,你的女兒必死在刀下,……’”(《公諸同好——推薦我讀過的幾本書》)“一位朱諾般威風凜凜的女士就曾問我:‘老實說,你讀翻譯作品嗎?’我原是在翻譯書堆里混大的,但是對著離我鼻子不遠的那根手指,我也只能囁嚅支吾了。”(《譯人自語》)“偶爾在書攤上發現某篇舊譯給收入集子,寫信去乞討,多少能蒙賞給幾文。”(《譯人自語》)“記得蕭乾當時選譯了
捷克小說《
好兵帥克》的片段給《譯文》發表。別以為我會在這裡吹捧譯文之精妙,那是不符合要求的。我想說的是在發表《帥克》的同時,刊物上登了捷克名畫家約·拉達所作的一幅哈謝克速寫像。”(《我所知道的蕭乾》)
這些句子,讀來都引入發笑,但在笑過之後,仔細品味一下,就知道其中含有嚴肅的,令人深思的成分,並非那種林語堂式的為幽默而幽默。
單是《縱浪大化集》這個書名,已經給李先生泄了密,書中那篇精彩的長文《非是“思君若汶水”,未曾“三夜頻夢君”——海明威與福克納眼中的對方》更顯露了他的舊學根底。“思君若汶水”,出自李白的《
沙丘城下寄杜甫》;“三夜頻夢君”,出自杜甫的《夢李白二首》之二。用李白和杜甫來比喻
海明威與福克納,極妙;加上兩句詩前面的否定詞,則表露了作者對海明威與
福克納不能像
李杜那樣成為知交而遺憾的心情,亦妙。
人物愛好
翻開《縱浪大化集》,會立刻發現,李先生有喜歡收藏的習慣。他不但珍藏著寫有
陶潛詩句“縱浪大化中”的稿紙(
朱光潛先生題),英國女作家默多克來華時開列的書單,還把一張畫在“土紙上的道士符咒”,“隆重地供在鏡框裡”。有時,他也買些價錢不太貴的古董,就算“家裡人都說是假古董”,他也毫不在乎,認為“就當它是真的豈不更為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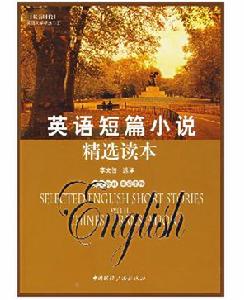 李文俊作品
李文俊作品除名人書信、手跡、舊書之外,對中外文學作品的插圖及相關的文字資料,李先生大概也蒐集了不少,不然,他為《外國文學名著圖典》所寫的那篇提為《精美如繡 五彩具備》的序文怎能那樣洋洋灑灑,下筆千言?
對肯特的美術作品,不知李先生是否有專門的收藏。不過,他在《我所知道的蕭乾》一文中曾說,他曾為《人民日報》
副刊撰寫過一篇介紹肯特的短文。既然他對這位世界級的版畫大師關注得這么早,說不定早就收藏了一套美國精印的《
白鯨》插圖呢。
對兒童畫,
李先生也很關注。比如,他在《可愛的小鹿》一文中專門介紹了畫家
韓美林先生為中國少兒社1980年版的《小鹿斑貝》所繪的82幅水墨插圖,對它們大加讚賞。
李文俊著作
(包括由其編選的著作)
1.《婦女畫廊》(散文集),×年於重慶印行
2.《縱浪大化集》(散文集),譯人視界叢書之一,
九州圖書出版社1997年初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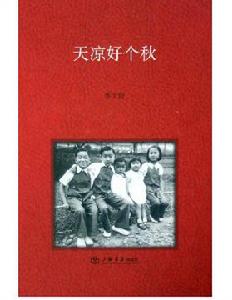 李文俊作品
李文俊作品3.《尋找與尋見》(散文集),譯家文叢之一,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初版
7.《
美國文學簡史》(修訂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初版【該書第四章《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二、七節“詩歌創作1”與“福克納與南方小說”乃李文俊撰寫】
以下為單篇文章:
1.《五十周年瑣憶》 ,《
世界文學》2003年第4期
2.《埃士拉·龐德的漂流歷程》(評論),《世界文學》1981年第1期
3.《<世界文學>40年佳作選:中短篇小說》序言,《世界文學》1991年第4期
5.《聖經故事》的啟示(書評),2004年10月20日《
中華讀書報》
6.《奧斯丁:寫鄉野的幾戶人家》(《
愛瑪》譯序),李文俊、
蔡慧,2004年10月《博覽群書》
7.《先知們的話語》,×年《博覽群書》
9.《挽弓當挽強》,×年《中華讀書報》
李文俊譯作
1.《變形記》,卡夫卡著【最初“內部發表”於1965年,發表刊物不詳】
①《
世界文學》1979年第1期,P191頁【據該雜誌注,譯文曾請
張佩芬女士據德文校訂】
③《變形記》,佳作叢書第二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初版【內收三篇小說,其一為《變形記》】
④《變形記》(插圖本),
灕江出版社1994年初版內收《變形記》、《致科學院的報告》(書名不同於人文版),譯文又作了一些修改,序文後收入《縱浪大化集》
2.《
在路上》,
凱魯亞克作,與
施鹹榮等4人合譯署的是化名,“文革”期間“內部出版”,出版時間及出版社不詳
4.《喧譁與騷動》,福克納著
①《外國現代派文學作品選》第二冊,
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初版【收入《喧譁與騷動》第二章】
②《喧譁與騷動》(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初版 ★
③《喧譁與騷動——福克納作品集》(外國文學名著精品),
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初版【譯文據1987年美國
諾頓公司出版的“修訂本”修訂】
④《喧譁與騷動》(
威廉·福克納文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初版★
5. 《我彌留之際》 ,福克納著
①《
世界文學》1988年第5期(附:《他們在苦熬》)
6.《道格拉斯自述》,
道格拉斯著,李文俊譯,三聯書店1988年初版
8.《比眼淚更美——加拿大現代詩選》,
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初版【此書是李文俊所譯還是由其編選,尚不清楚,姑列於此】
10.《押沙龍,押沙龍!》(威廉·福克納文集),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初版
11.《我愛你,羅尼》(
隆納·雷根致
南希·里根的信),[美]南希·里根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初版
15.《小公主》,[美]伯內特著,譯林出版社2004年初版
17.《福克納隨筆全編》(未譯完)
單篇譯文
1.《根子》(選譯),阿歷克斯·哈萊著,
施鹹榮、李文俊譯,《
世界文學》1977年第2期
4.《大衛·坎貝爾詩五首》, 《世界文學》1996年第6期
5.《一千謝克爾一篇》(短篇小說),[奧]卡斯特爾·布魯姆作,《
世界文學》1999年第2期
6.《男人之間的無言友誼》(散文),[美] 羅傑·羅森布拉特作,《譯林》2000年第1期
7.《調換位置》(小說),福克納作,收入《世界文學》2000年第5期;後又被
陶潔編譯林版《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福克納短篇小說集》所收。
8.《福克納書信選·致馬爾科姆·考利書》,《世界文學》2003年第4期
人物評價
李文俊以翻譯福克納為人熟知,以至給讀者造成一種印象:但凡一提到福克納,馬上就會想到李文俊,福克納某種意義上成了他的標籤。不過,鮮為人知的是:他和
施鹹榮等四人合譯了
凱魯亞克的《
在路上》,在“文革”期間作為內部書出版;他還是卡夫卡《變形記》最早的中文譯者,更少有人知道他還翻譯過
海明威。“‘文革’結束後不久,
上海譯文出版社找我翻譯《
喪鐘為誰而鳴》,譯了幾萬字後才知道已經有人翻譯,且被某領導推薦給了出版社,自己的譯稿只好就此‘擱淺’。”然而,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卻讓他陰差陽錯與福克納結下了不解之緣。李文俊用“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詞句,來形容自己當初選擇福克納的“壯舉”,因為他深知自己面臨的將是一項極其艱難的工作。而且1979年前後,國內知道福克納名字的人可謂“寥若晨星”,更談不上有人在從事這方面的譯介工作。
從 1980年2月開譯《喧譁與騷動》,李文俊一直到1982年6月才將全書譯出。“大概總有兩年,這本書日日夜夜糾纏著我,像一個夢——有時是美夢,有時卻又是噩夢。”被普遍認為最難譯的《押沙龍,押沙龍!》,對他則是一個更大的“噩夢”。他說:法國福克納專家
莫里斯庫·安德魯譯過多部福克納作品,惟獨未譯《押沙龍,押沙龍!》。晚年,李文俊揀起此書。花了三年時間,68歲的他終於翻譯完這部作品,也因此累垮,心肌梗塞發作住進醫院。
翻譯福克納的艱辛,也讓李文俊對翻譯有了更深切的體悟。在他看來,翻譯外國文學的最大難題是:跨越兩種文化的間隔,要以崇尚簡潔、清晰的漢語形態出現時,仍能原汁原味地保持文本的美學價值。一個真正的譯者必須要有“手段”,把散見各處、或埋伏較深的“脈絡”、“微血管”、各種“神經”一一理清,把握好它們的來龍去脈,才能還原出一幅完美的原圖。
身體康復後的李文俊依然筆耕不輟,翻譯一些偏於輕鬆的東西,如塞林格的《
九故事》、兒童小說《小公主》、《
小爵爺》等,譯得最過癮的是和已故翻譯家
蔡慧合譯的《
愛瑪》,還學會了用電腦寫文章。引用一位美國詩人的詩句“行人寥落的小徑”,李文俊說:在一個分叉的路口,選擇一條路走下去,不管是否還有更便捷的路,他都選擇堅守在翻譯第一線,最終抵達一生極力追求的人生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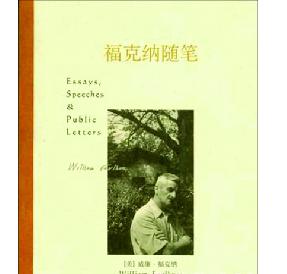 李文俊作品
李文俊作品 李文俊作品
李文俊作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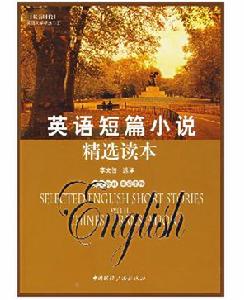 李文俊作品
李文俊作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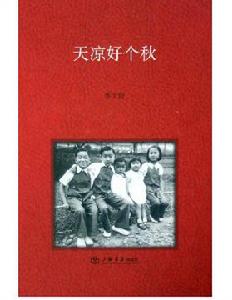 李文俊作品
李文俊作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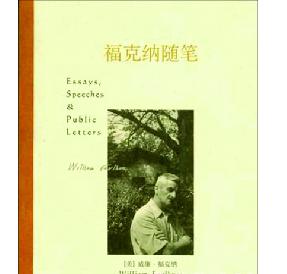 李文俊作品
李文俊作品 李文俊作品
李文俊作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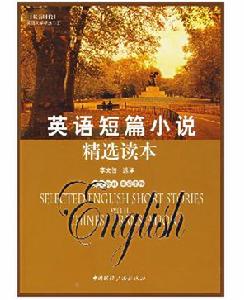 李文俊作品
李文俊作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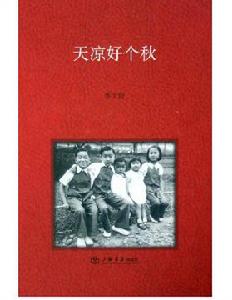 李文俊作品
李文俊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