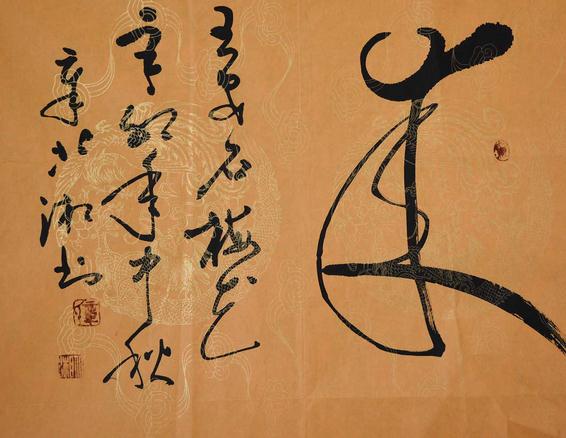產生淵源
名家的產生,最早可以追溯到與上古
禮官。成文法公布之後,社會上出現了類似
律師一類人,他們根據法律條文進行辯護,由於這些學者專門從事名詞概念的探討,因此稱他們為“辯者”。
漢代學者司馬談《
論六家要旨》,則他們稱為“名家”。
春秋後期鄭國的
鄧析,就是這類人物的代表。春秋末期以來的名辯思潮,發展到
戰國中期,由於激烈的社會變革,使舊有的概念不能反映新事物的內容,而新出現的概念還需要社會的公認。
這種名實不符的現象,在當時的社會上十分普遍,急需解決。適應這種社會需要,後來逐漸出現了一批以人的認識本身為研究對象的思想家,他們致力於論辯中邏輯問題的研究,形成了名家學派。
政治主張
在政治上,
惠子提出"去尊",但是具體內容並沒有留傳下來,應該是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這種"去尊"的平等觀在中國思想史上是極為罕見的。惠子和
公孫龍還提出了"偃兵",反對用暴力統一天下。
派別
契約異派
這一派注意到事物的普遍聯繫和不斷發展,認為事物的差別只是相對於一定的時間、地點和條件而言,主張一切現實差異都只有相對的意義,提出人們在認識中應該否定差異的界限,直至承認一切對立都為無條件的同一,“畢異”的本是“畢同”的。他們用來論證自己觀點的主要命題有10個,《莊子·天下》篇中記載了這些命題。其中第一個命題說,萬物都由一種叫做“小一”的東西構成,因而彼此在本質上並無差異;由萬物組成的宇宙,又是一個唯一的“大一”,此外別無他物。第五個命題說,一般常識認為,事物之間有“大同”與“小同”的差別,但從本質上說,可以認為萬物是“畢異”的,也可以認為萬物是“畢同”的。第十個命題說,歸根結柢,“畢異”的本是“畢同”的,因而應該不分物我,“泛愛萬物”,天地雖然上下懸隔,其實猶如一人之身,也不必要分彼此。
離堅白派
這一派注意到事物和名稱的差異、獨立和穩定,強調不同名實的不同質的規定性和發展的中斷性。他們認為,萬物都是各自獨立、互不相同的,甚至一物之中的各種屬性也是互不相關的,因而否定了事物和概念之間的相互聯繫。這一派的著名論題為“
白馬非馬”和“堅白石二”。他們認為“馬”是“命形”的,“白”是“命色”的,“命色者非命形也”,所以說“白馬非馬”。他們又說,眼看不見石之堅,而只能看見石之白,因此“無堅”;手摸不著石之白,而只能觸及石之堅,因而“無白”,由此斷言“堅”和“白”是互相分離、各自獨立存在的。
總結
上述兩派各自的側重點不同,並且各持一端。契約異派誇大事物的普遍聯繫和變動不居的特性,認為一切都是同一;離堅白派則誇大事物的相對獨立和相對靜止的特性,認為一切都是差異。契約異派合異為同;離堅白派離同為異。前者犯了相對主義的錯誤,後者則犯了絕對主義的錯誤。
契約異派和離堅白派在認識上所犯的各持一端的片面性錯誤,到戰國末期經其他哲學家的努力而有所糾正。後期墨家提出了“
堅白相盈”的命題,
荀況,強調“
制名以指實”的原則,這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古代
邏輯學和
認識論的發展。秦統一六國以後,各辯思潮隨之消匿。到清代,西方形式邏輯傳入中國,有人將其譯為“
名學”,但它同中國先秦時期的名學實有很大區別。
白馬非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
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
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
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
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
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
曰:“以有白馬為有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是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指物論
《
指物論》乃公孫龍子的認識論,篇中討論了認識的特點以及認識與事物之間的關係。其為文以同一詞兼表不同概念,判斷中常省略主詞,推理中又常省略前提、隱藏結論;其結構則為提出論題、自我辯駁、自我答辯。由於其辭曲折,其論詭譎,致使全篇晦澀難懂,遂成千古之謎。
原文: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代表人物
鄧析
名家第一人是鄧析
(《漢書。藝文志》)。其生卒年月約公元前560年至前501年,是春秋末年鄭國人。由於鄧析從事的製作刑法活動是晉國法治文化的流韻所及,並且鄭國在戰國時代併入韓國版圖,所以,鄧析的思想與三晉文化思想具有深刻的淵源關係,學者多認為中國邏輯史的開創者是鄧析而不是孔子。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鄧析著有《
鄧析子》兩篇,但經考證系後人偽托。不過,我們認為《鄧析子》還是保留了鄧析思想的原意。
公孫龍
戰國末年趙國人,是名家在戰國末年的代表人物。作為一位善於論辯的游士、謀士,公孫龍常年活躍於政治舞台上,曾在趙國
平原君家中當了幾十年門客。在政治觀點上,公孫龍同惠施一樣,也是主張“偃兵”的和平主義者,他曾數次力勸諸侯國君停止相互之間無謂的戰爭
在學術思想上,公孫龍專注於對“名”的研究,是名家著名人物之一,“離堅白”派的領袖,“白馬”、“堅白”之辯等,是他名垂史冊的主要辯題。就連公孫龍也曾自詡:“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
尹文
齊國人,戰國時代著名的哲學家。「宋尹」學派始祖,生平不詳,大致活動在
齊宣王、愍王之際,與
宋鈃齊名,屬
稷下道家學派。他們的思想特徵以道家為主,兼
儒墨合於自身道法,廣收並納各派學說,這正是稷下黃老學風。對後期儒家思想有深刻影響。尹文於齊宣王時居住在稷下,為
稷下學派的代表人物。他與宋鈃、
彭蒙、
田駢同時,都是當時有名的學者,並且同學於
公孫龍。公孫龍是當時有名的名家,能言善辯,“
白馬非馬”為代表性的論點,以詭辯著稱。尹文的學說,當時很受公孫龍的稱讚。流傳於世者唯《
尹文子》一書,先秦論法術和形名的專著。
惠施
即
惠子,戰國中期宋國
(今河南商丘)人,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辯客和
哲學家,是名家思想中“契約異”的主要代表人物。在《
莊子·天下篇》中,
惠施學派還提出了"雞三足"、"火不熱"、"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白狗黑"等二十一個命題。學者認為按照先秦名家的發展如果沒有被打斷,中國是可以發展出邏輯學的。惠施有些命題是和後期墨家爭論的。後期
墨家運用數學和物理學的常識,對物體的外表形式及其測算方式作了分析,下了定義。《
墨子·經上》曾說:“厚,有所大。”認為有“厚”才能有體積,才能有物體的“大”。而惠施反駁說:“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認為物質粒子(“小一”)不累積成厚度,就沒有體積;但是物質粒子所構成平面的面積,是可以無限大的。後期墨家曾經嚴格區分空間的“有窮”和“無窮”,《墨子·經說下》說:“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認為個別區域前不容一線之地,這是“有窮”;與此相反,空間無邊無際,這是“無窮”。而惠施反駁說,“南方無窮而有窮”,就是說南方儘管是無窮的,但是最後還是有終極的地方。後期墨家認為“中”(中心點)到相對的兩邊的終點是“同長”的。《墨子·經上》說:“中,同長也。”而惠施反駁說:“我知天下之中央,燕(當時最北的諸侯國)之北,越(當時最南的諸侯國)之南是也。”因為空間無邊無際,無限大,到處都可以成為中心。後期墨家認為同樣高度叫做“平”,《墨子·經上》說:“平,同高也。”而惠施反駁說:“天與地卑(“卑”是接近的意思),山與澤平。”因為測量的人站的位置不同,所看到的高低就不一樣。站在遠處看,天和地幾乎是接近的;站在山頂上的湖泊邊沿看,山和澤是平的。
惠施把一切事物看作處於變動之中,例如說:“日方中方睨(“睨”是側斜的意思),物方生方死。”太陽剛升到正中,同時就開始西斜了;一件東西剛生下來,同時又走向死亡了。這種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認識了事物矛盾運動的辯證過程。但是他無條件地承認“亦彼亦此”,只講轉化而不講轉化的條件,這樣就否定了事物的質的相對穩定性,不免陷入到相對主義的泥坑中去。
衰落
先秦名學到了秦始皇滅亡六國就難以發展,其原因可以分為以下幾項:
第一項:秦朝使中國統一以後,為了加強
中央集權的統治,
秦始皇禁止
私學,只能以吏為師;到了
漢代,又有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中央政府的強勢領導下,名辯之學難以發展,名家也隨之衰落。
第二項:名辯之學與秦漢以來的中國主流文化精神不一致。中國古代文化重人文,輕自然,名辯之學窮極事理,卻招致諸多批評;而
儒家成為
顯學之後,
士大夫皆關注於社會倫理,強調經世致用,名辯之學被視為以爭勝為目的的無用之學。此外,名辯之學所採取的分析方法,接近純粹的語言分析,然而主流的儒、道之學皆對此方法有所批評,甚至根本否定。在主流文人的排擠之下,名家之學無立足之地。
第三項:就名家內在的發展而言,名辯之學本身相當艱澀難懂,也影響了其發展。首先是一字多義的情況嚴重,致使後學眾說紛紜,難以詁訓;其次,由於名家時常以違反常識的語言敘述命題,常人難以接受而失去研究興趣。在後學難以為繼的情況之下,難免走向絕路。
先秦諸子論名家
先秦諸子與名家或迭有爭辯、或有所批評,錄於其作中。
儒家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學說當中也吸取了名家與
墨家的認知心和邏輯方法,但是他卻用這些方法,對名家與墨家都展開批評。荀子評名家:“不法先王,不是禮儀,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
有些研究指出,荀子認為學術必須為政治、道德服務,而對於名家熱烈研究“堅白”、“同異”、“有厚無厚”等自然科學問題,荀子認為這是以人的認知能力,是不可能求盡的。所以他批評名家是“愚者、妄人”,認為君子不應該去追求這類知識,而要由“格物致知”轉向“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之道。
也有學者指出,由於荀子學說中的“名實”與公孫龍的“名實”有別:
“實”方面:荀子指的是時空中的個體物與其統類;公孫龍指的是物體的性質。
“名”方面:荀子是用以命謂一個個體或統類;公孫龍則用以命謂一個體物的各項性質。
名實對應方面:荀子認為名應該與對應物的個體或統類相應;公孫龍則認為應該與個體物的各項性質相應。
在“名實”觀點不同之下,荀子便以自己的名實觀批評公孫龍的“以實正名”是“以名亂實”。
另外,也有人認為荀子在批評名家時是站在政治的立場,以統治者而非哲學家的觀點討論名家問題。荀子認為制名是統治者的重要任務,而名家的詭論會威脅到這個系統,統治者對其學說不必研究,應該予以壓制。對於名家哲學,荀子不但反對,甚至主張以政治勢力和
刑法禁止。
道家
名家強調純粹的語言邏輯,因此,道家中
莊子一系對於語言採取懷疑而蔑視的態度。就像《莊子‧秋水》篇認為能用語言來論說的,都是“物之粗也”。在追尋道的過程,語言也只是一項工具而非目的。對於將語言當成思想的名家,自然不是道家所追求的。所以,即使名家中惠施對知識語言的看法與莊子頗為接近,但是莊子仍然批評他是“逐物而不返,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
墨家
《
墨子》一書中,有〈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六篇,通常合稱為《
墨經》,是後期墨家通過邏輯的方式,反駁名家辯論的著作。
對於
惠施的“
契約異”之說,墨者認為這其中的“同”字必須分別為“重、體、合、類”四種,而“類同”為真的命題,不能據以推論出“
體同”的命題也為真。惠施的謬誤,是出自於文字的歧義。
而對公孫龍的“堅白石”之說,墨者以現實世界的堅白石為據,認為堅、白同時存在於石中,不會互相排斥,反對公孫龍的論點。
文獻
《成公生》五篇。與黃公等同時。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
《黃公》四篇。名疵,為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
《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譥者為之,則苟鉤鈲鋠析亂而已。
名家流傳下的代表著作《鄧析子》,《尹文子》,《
惠子》,《
公孫龍子》等,今僅存《公孫龍子》、《
鄧析子》、《尹文子》。《
莊子》一書曾有許多惠子和莊子的對話。
歷史地位
名家之地位在秦朝以後退出政治舞台,名家的後世傳人的影響均不及
儒、墨、道、釋、易、兵、
法家等諸家影響面廣,名家在不同程度的被融入到諸家文化的精髓中。名家在戰國中期卻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學派,標誌著中國古代人思想學與邏輯學大融合也是達到了相當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