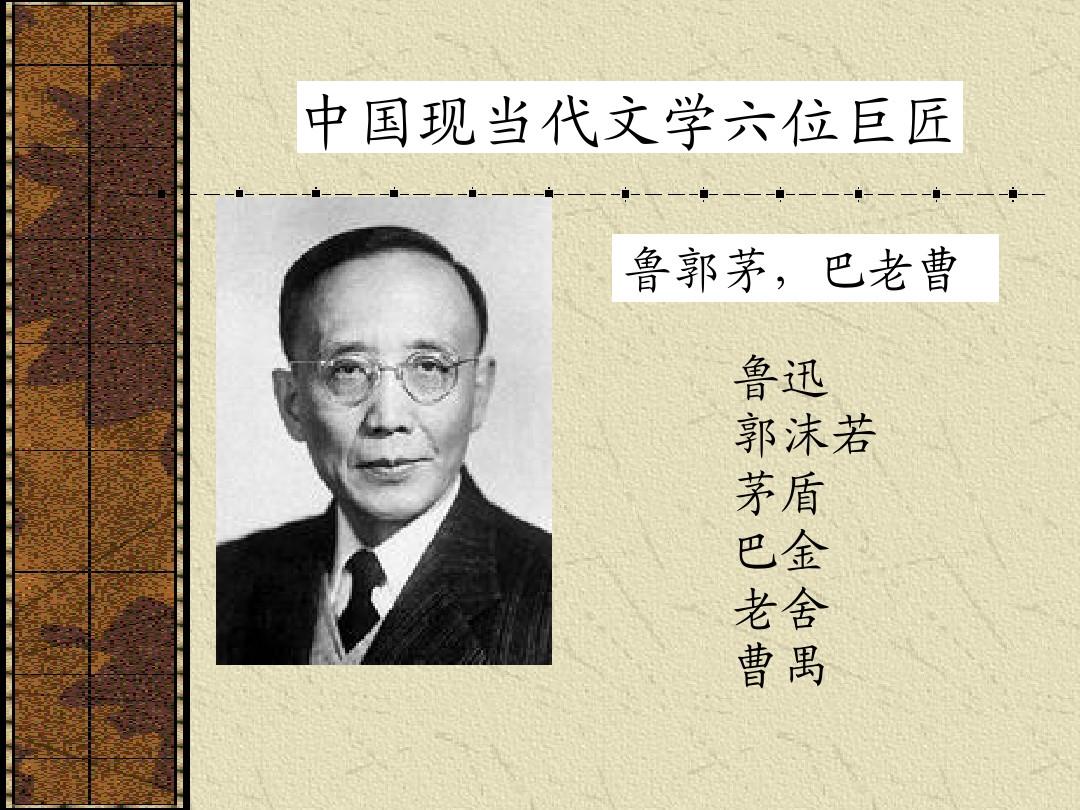產生緣由
1936年秋,魯迅的突然辭世,凸顯了這根擎天之柱坍塌後中國左翼文壇的懸空狀態。孫伏園一句話概括了人們當時的驚慌失措:“像散沙一般,正要團結起來;像癱病一般,將要恢復過來;全民族被外力壓迫得剛想振作,而我們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奮進的大將忽然撒手去了。”(
孫伏園:《哭魯迅》)
在時間無盡的長河中,魯迅之死是一個非常偶然的事件,但在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心理中,卻包含和預示著必然性的內容:命名。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來,在國民黨政權的連續血腥鎮壓和瘋狂迫害下,中國共產黨一直處於十分不利的邊緣。國民黨政府試圖從文化和軍事兩個方面剝奪和取消中國共產黨存在的合法性,但一向批判國民黨思想政策的魯迅,則無疑是蔣統區內實施上述文化企圖的極大屏障。因為,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魯迅不獨是左翼文壇的領袖,還是廣大進步青年心目中的“聖人”,是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的去世當然就不只是中國左翼文壇的巨大損失,也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的巨大損失。所以,剛剛得知他辭世的訊息,毛澤東就通過馮雪峰把自己列入治喪委員會的名單,延安等地舉行了一系列的紀念活動。魯迅周年忌日,延安又發起隆重的紀念大會,毛澤東親自到場講話,這個講話,後來以《毛澤東論魯迅》為題發表在1938年3月1日出版的《七月》雜誌。(林志浩:《魯迅傳》)這一系列行動反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命名的熱情和渴望,當然也反映了無名可“命”的焦慮。
1938:武漢提名始末
就在這個歷史空檔,郭沫若出現了。
1937年7月27日,闊別10年的他,從日本橫濱乘“皇后號”客輪迴到已陷入戰火的中國。作為北伐戰爭以來的風雲人物,郭沫若當年的流亡和今天的歸來一樣都不可能是個人行為,而要受制於國共兩黨力量的制衡。也正因為如此,他的“歸來”才成為上海、南京、武漢和廣州等重鎮的“號外”新聞。
雖然在《洪波曲》中,郭沫若曾把他流亡生活的結束很瀟灑地概括為“歸去來”三個字,但事實上,自打他重新登上30年代中國的政治舞台,他的行動已經成為一個極富政治文化含意的象徵性符號,包括他的去從,都由不得他自己了。
國共兩黨都深深懂得這時借重郭沫若的重要性。1937年春,張群、何應欽忽然想起他與日本政界元老西園寺公望的關係可以利用,便敦促蔣介石取消對郭的“通緝令”。隨後,由福建省主席陳公洽托郁達夫轉告郭沫若,口氣頗為急切,謂:“委員長有所借重,乞速歸”,“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對兄有所表示,萬望即日整裝。”不僅如此。1937年7月27日下午,當郭沫若乘坐的船剛剛停靠上海公和祥碼頭,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何廉即受命前往迎接。雖然他當時藉機“逃脫”,但隨後的時日,即陷入與國民黨上層“迎來送往”的“車輪大戰”中:8月,赴崑山叩訪陳誠、馮玉祥、薛岳和黃琪翔諸將領;9月下旬,在南京受到蔣介石的接見,“希望我留在南京,希望我多多做些文章,要給我一個相當的職務”;見張群,並由他出面約見孫科、汪精衛、邵力子、陳銘樞等人……
在國民黨方面緊鑼密鼓地拉攏郭沫若的同時,共產黨方面也在積極與他接洽並做有關安排。潘漢年是在郭歸國3天后才得知訊息的,但他的動作卻不算慢。據夏衍回憶,“沫若回到上海大約10天后”,潘漢年向“我傳達了恩來同志的口信,由於當時已經考慮到《新華日報》不可能很快出版,所以明確地決定,由上海‘文救’出一張報紙”,由郭沫若擔當社長。另外,“我和阿英輪值,幾乎每天都去看他一次,並把他的情況隨時告訴漢年。”(
夏衍:《
懶尋舊夢錄》)
《郭沫若傳》和《郭沫若自傳》等書也為我們留下了郭由廣州北遷武漢後與共產黨要人之間頻繁往來的非常翔實的記錄,現抄錄如下:1938年1月9日晚,剛到武漢就參加了周恩來、葉挺、王明、葉劍英、博古、鄧穎超等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舉行的歡迎會;29日,收到周恩來“一起過年”的邀請函(《周恩來書信選》);郭因不滿國民黨在第三廳安插特務,一甩手去了長沙。又是周恩來派正與他處於熱戀之中的於立群前去接駕,郭在《郭沫若自傳》中寫道:“我禁不住心子急跳,同時我也看見立群的臉忽然漲得通紅,把頭埋下去了”;周恩來甚至還想到,“我在這兩天將各事運用好後,再請你來就職,免使你來此重蹈難境。”不可謂不細心周到,關懷備至了。
圍繞郭沫若,國共雙方之間進行的與其說是一場“禮遇之戰”,還不如說是一場對“命名權”的爭奪,而在這方面,後者似乎永遠都更勝前者一籌。1938年夏,就在國民黨非常笨拙地給了郭沫若一個偏低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職位的同時,共產黨在內部突然宣布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訊息:“黨中央根據周恩來同志的建議,作出黨內決定:以郭沫若同志為魯迅的繼承者,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並由全國各地組織向黨內外傳達,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領袖的地位。”(吳奚如:《郭沫若同志和黨的關係》)一開局,共產黨人周恩來就明顯占了蔣介石的上風。因為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廳長”只是一個官僚意義上的職務,任何人都可以乾,不妨說還有“不乾淨”之嫌;而文化界“領袖”則無疑是社會道義的擔當者也即道統的化身,它很大程度只能在公認的少數幾個比較“乾淨”的知識精英中間產生。因此,“領袖”往往比“廳長”更容易獲得人民大眾的尊敬,在社會倫理和心靈的層面上得到普遍認同。
3年後,在重慶舉行的郭沫若50壽辰的慶典上,周恩來更是巧妙地發揮了他對文化領袖的想像,把魯迅這箇中斷的中國式的政治敘事與郭沫若這後一個政治敘事銜接了起來,他在《我要說的話》一文中說:“郭沫若創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二十五年。魯迅自稱是‘革命軍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闢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嚮導。魯迅先生已不在人世了,他的遺範尚存,我們會感覺到在新文化戰線上,郭先生帶著我們一道奮鬥的親切,而且我們也永遠祝福他帶著我們奮鬥到底的。”
毛澤東評價魯迅
認真考辯起來,
毛澤東可能是在井岡山時期開始注意魯迅的。1933年1月,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解除了毛澤東紅軍總政委的職務,只保留了政治局委員這個實際沒有決定權的空銜。賦閒狀態的毛澤東在瑞金山窪中聽左翼文藝家馮雪峰大談“魯迅經”。大概是個人“遭遇”觸動了毛澤東的心弦罷,魯迅引起了他情感上很深的共鳴。對魯迅的鬥爭、寫作、身體狀況、結交的友人以及生活習慣,毛澤東都非常關心,反覆詢問。毛澤東與魯迅從未見過面,也不曾有直接的個人接觸,但兩人的心似乎是相通的。毛澤東對馮雪峰等給魯迅出題目寫文章感到驚訝,但當聽到馮雪峰說,“有一個日本人,說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時,沉悶已久的毛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陳早春、萬家驥:《馮雪峰評傳》)
但毛澤東對魯迅書面上的正式評價,卻是1937年底在延安風沙瀰漫的操場上做出的。毛在這篇由大漠記錄、後來刊發在《七月》雜誌第四集第二期上題為《毛澤東論魯迅》的講話中指出,魯迅“並不是共產黨的組織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化的”。
1940年,毛澤東在他著名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中進一步明確提出:“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縱觀毛澤東已公之於世的所有著作,對一位中國現代作家,包括其他歷史人物,一口氣連用了9個“最”的措辭,並冠之以“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3個頭銜的現象,是絕無僅有和令人吃驚的。
周揚的作用
1949年以後,
周揚實際成為新文藝界的“文化班頭”,他的一言一行比被稱為文化班頭的郭沫若更能準確地反映中共上層的意圖、願望和信息。周揚1949年7月2日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的報告《新的人民的文藝》,是他代表中共所作的首次正式評論。他說,五四以來,以魯迅為首的一切進步的革命的文藝工作者,為文藝與政治結合、與廣大民眾結合,曾作了不少苦心的探索和努力。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藝運動,始終把“大眾化”作為文藝運動的中心,在解決文學與人民民眾的關係上作了不懈的嘗試。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當時革命文學的根本問題---為什麼人服務和怎樣服務的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廣大文藝工作者同工農兵還沒有很好結合。而在解放區,由於有了1942年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由於有了毛澤東文藝方針的具體指導,由於有了人民的軍隊和人民的政權,“先驅者們的理想開始實現了”。
在五四先驅如陳獨秀、胡適等從建國後政治文化政策的調整中紛紛“落馬”的大背景中,這種評論顯然“保護”了魯迅。如果說毛澤東、周恩來是想通過魯迅、郭沫若等左翼文學界頭領在國民黨的統治心臟建立另一條“文化戰線”,凸顯出聲東擊西的政治和軍事上的策略性目的的話,周揚則是將前者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理想具體落實到對文化界的“改造”、“利用”的環節之上。當時成功實踐了《講話》精神的作家僅有趙樹理等寥寥數人,建國初年的文藝界一時“大腕”稀少,門庭冷落,魯、郭、茅、巴、老、曹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白----他們在廣大文學藝術家中的號召力是自不待言的;周揚是新文學陣營中人,他的闡釋和評論對完成文學大師在新、舊社會之間的“轉型”,有著政治家們無法發揮的作用。
我們注意到,周揚50、60年代有關這一領域的報告和發言不僅不單調、空洞,相反卻十分飽滿、充實和自信,通過他的闡發,上述各位大家的思想和創作與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論說產生了必然和內在的歷史聯繫,不少作品成了《講話》精神的生動反映。
周揚指出:“魯迅就是偉大的革命的現實主義者,在他後來的創造活動中更成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偉大的先驅者和代表者。我們傑出的作家郭沫若和茅盾,都是三十幾年來新文藝運動戰線上的老戰士。”(《周揚文集》第二卷)
他還認為,老舍是改造自己並很快實現“轉型”的一個典型。老舍解放後在創作上顯示出的積極和主動,都說明他確實適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了。為此,周揚親自撰文《從〈龍鬚溝〉學習什麼?》,他興奮地說:“老舍先生所擅長的寫實手法和獨具的幽默才能,與他對新社會的高度政治熱情結合起來,使他在藝術創作上邁進了新的境地。”
但周揚不是華而不實的演說家,而是一個腳踏實地的實幹家,對實施“文學大師”工程,他是真抓實幹而且一抓到底的,首先是他對大學文科教材建設工作的領導。
編選文科教材的任務是1960年9、10月間在中央書記處的一次會議上確定的。會後,書記處書記彭真受總書記鄧小平委託向周揚下達了這一任務,並要他立下軍令狀,限期解決教材問題。1961年4月,周揚主持北京高等學校文科和藝術院校教材編選計畫會議,並作了長篇講話。事後,對教材的編寫他都是親自過問,具體指導,大到確定國內第一流的學者專家作為主編人選,敲定文科7種專業和藝術7類專業,小到為個別教授舊作的修改和重版“開綠燈”,周揚都抓得很細、很到位。
據“文革”中一篇“揭批”周揚的文章稱:“在‘文科教材會議’上,周揚又決定將馮友蘭解放前出版的《中國哲學史》重新出版。這本書在國民黨時代已出版過八版,至今仍大量充塞於舊書市場,周揚唯恐不能引起人們的注意,竟利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出版機構,來繼續國民黨的工作。馮友蘭還因此得了一筆一萬多元稿費的意外之財。工人、農民所創造的財富,就這樣通過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之手,‘孝敬’了資產階級‘權威’。”(郭羅基:《清算周揚毒化大學文科的罪行》)但它卻從“反面”描畫了周揚當時殫精竭慮和忙碌的身影。
據說,從文科教材編選計畫會議到1965年6月底,已出版新編選教材68種165本,已完稿和已付印的有24種33本,加上正在編選的教材共156種367本,約占計畫編選教材總數的一半。
另外,他在各種場合的報告中,也比較注意強調文學創作與文學遺產繼承關係,對形成尊重文學大師的風氣、建立穩定的文學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他在1959年的宣傳工作會議上說:“什麼叫做文化高潮,也得和外國和古代比較,沒有大作家、大科學家很難叫做文化高潮。”沿著這一思路,周揚一直深信文學大師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能夠起到精神和文化意義上的“示範”作用。50年代,他就曾借評論趙樹理的機會,稱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是“語言大師”。1978年,郭沫若病重時,周揚到病房與之長談,稱讚他:“您是歌德,但您是社會主義時代的新中國的歌德。”這種極高的評價雖然令郭沫若不免汗顏、不知所措,但確實說明了周揚真實的思想態度。
王瑤的貢獻
1949至1951年,是現代學術發展中的一個“沉寂期”,卻是以解放區作家為主體的新文藝創作的一個“爆發期”。學界的寂寞與創作界的熱鬧形成鮮明的比照。清華眾學者好像還未從聞一多、
朱自清非正常死亡的余痛中擺脫出來,新時代的軌道一時也令他們難以適應。這時,喜歡嘴銜菸斗、家住清華北院的王瑤恰好36歲,處在人生的本命年,也是一生中思想最為成熟、精力最為旺盛的時候。
王瑤早年參加過左翼文藝運動,頭腦不僵化,雖然是朱自清的親傳弟子,但絕無他們那一輩人的孤傲和迂腐,“彎”自然會轉得較快。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隆隆禮炮還未在天安門廣場轟響,“1949年暑假以後”他便已經率先在清華園開出“中國新文學史”這門課,“年終便基本完成了《中國新文學史稿》的上卷,1952年初又完成了下卷。從蒐集資料到完稿,這部首創的近60萬字的巨著,才用了兩年多一點的時間。”(何善周:《懷念昭深》)
《中國新文學史稿》被學術界公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開山之作”。第一,是它首先運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理論來探討中國現代文學的外部發展和內在規律,對其作出了符合這一理論的整體性概括。第二,“魯、郭、茅、巴、老、曹”的專章模式及敘述方法儘管當時還未浮出歷史地表,但關於他們的評價卻不能不說是“新民主主義式”的。細讀《中國新文學史稿》與魯、郭、茅、巴、老、曹密切相關的章節,將會給讀者很多的啟示。例如在第三章,他認為魯迅《吶喊》、《彷徨》的意義在於,它們“不但使讀者增高了文學革命的信心,而且更重要的,使革命的知識分子擴大了他們的視野,注視到在農村生活的老中國的兒女。這裡有麻木狀態的負著生活重擔的農民閏土,也有浮浪的農村無產者阿Q。這正是那時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生活,他們負著幾千年因襲的重擔,麻木無知地活著,而魯迅,正是抱著‘毀壞這鐵屋的希望’,力圖喚起這些昏睡的人的。因之,即使在那個啟蒙時期,他的思想和作品必然也是清醒的現實主義的。”這種典型的“人民性”的眼光,也被用於對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創作的觀察與定位當中。一個證明是,對曹禺的力作《雷雨》、《日出》表現出一種少見的挑剔和指責。他說:“《雷雨》的題材本來是極富於現實意義的”,作品人物的悲劇命運本來是“社會制度的殘酷”造成的,但作者卻把這一根本原因歸咎於“宇宙里鬥爭的殘忍與冷酷”,而採取一種“悲天憫人”的態度,這樣就使得他對題材的把握“不能深入”,勢必減弱了思想的力量;在《日出》結尾,“沒有組織的工人社會運動而只有辛苦地為資本家蓋洋樓的工人也就很難具象地代表光明”,作品的“愛憎的強度”也會受到削弱。
文學大師的研究,顯然不僅是一般的文學史,而是在確立一種文學史秩序,也即幫助確立建國後的思想文化秩序。新民主主義理論通過王瑤的文學史撰寫,成功地運用到了學術研究當中,它無疑對更多學人起到一種“示範”與“規範”的作用。
其它幾本現代文學史的表現
1951至1957年,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豐收年”。繼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之後,1952年蔡儀的《中國新文學史講話》出版,1955年
張畢來的《新文學史綱》付印,緊跟著是1956年
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1957年
孫中田、何善周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與讀者見面。如果時間稍往後順延一下,還有幾本大學師生集體編寫的文學史著作面世,它們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59)、北京大學中文系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60,初稿)、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講義》(1961,初稿)等。1956年以前出版的主要是個人撰寫的文學史,較多雜糅了“個人”眼光和氣質,所以,我們將考察工作確定在這一範圍。
張畢來和丁易是兩位謹小慎微的師範大學教師。張任教於東北師大(由東北大學併入),丁任教於北京師大。張畢來的《新文學史綱》可能還早於王瑤的文學史,據說他1949年就在“東北大學講新文藝運動史”(《張畢來:《文章與友誼》),因為偏居長春,處於學界的邊緣,《新文學史綱》(第一卷)羞澀地放在抽屜中而沒有像王瑤那樣公之於世。原籍安徽桐城的丁易,30年代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時,參加過“一二·九”運動。1945年在四川三台東北大學任教,因支持學運被解聘。1947年後,先後在解放區的北方大學、華北大學擔任教授,解放後沒有去宣傳部門或中國作家協會,“等級”明顯低了一截,自然難免“氣短”。所以,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只是幾經修改的“未定稿”,直到1954年客死莫斯科大學任上,仍未最後“定稿”。兩位學者的謹慎使其文學史遠沒有王瑤的書在學術界影響大,但這並不等於他們平庸,沒有尖銳的個性。
值得注意的是,張、丁因在1951年以後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受到過“驚嚇”,在文學觀上表現得比王瑤更為“急進”。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學史綱》(第一卷),在不少方面與王瑤本有不小差異。在王瑤本中,除魯迅一人,其他文學大師的名字沒有列於各個章節的“目錄”,處於“無名”狀態;張畢來本則頻繁列入,大師的“命名”開始浮出時間的地表。丁易更進了一步,把張畢來的“專節”提升到“專章”,對魯迅等人做了更完整的歷史命名。譬如,第五、第六章作者均以“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旗手---魯迅(上、下)”,第七章以“郭沫若和‘五四’前後的作家”、第九章以“茅盾和‘左聯’時期的革命文學作家”等名之,老舍、巴金和曹禺也被列入專節的“進步作家”中。不要小看這一“變動”,因為其中不僅敏感地反映了建國初期政治文化政策某種調整的跡象,更主要的是迎合了主流文化對確立新的文學秩序的急切願望。所以,後來的文學史家傾向於把張、丁的工作看作是王瑤和蔡儀工作的進展,是進一步的“政治化”。
和王瑤的平易、張畢來的舒展、
丁易的嚴謹比較起來,劉綬松的文學史用字簡潔、眼光到位,顯示了他長期研究《文心雕龍》的心境和功底。前面幾位學者在運用新時代特殊詞語時的猶豫不決,在對中國現代文學及其作家做政治性判斷時的“底氣不足”,在劉本中似乎變成了“過眼煙雲”,所有“問題”都不再成為問題。僅僅從文學史的目錄看,
文學大師雖然基本沒有“露面”,但它的分析與判斷應該說是與解放後形成的流行的閱讀習慣最為合拍。與前面幾位把魯迅看做處於“轉變”中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代表的觀點有所不同的是,劉綬松的文學史開門見山地將其確定為“戰士”,魯迅變成了一個拿著筆衝鋒陷陣的戰士,魯迅不再呆在風花雪月的文學史中,他只有在中國社會學史中才更出彩。
習近平講話
我國就更多了,從老子、
孔子、莊子、孟子、
屈原、王羲之、
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關漢卿、
曹雪芹,到“魯郭茅巴老曹”(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到
聶耳、冼星海、梅蘭芳、
齊白石、徐悲鴻,從詩經、楚辭到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以及明清小說,從《格薩爾王傳》、《瑪納斯》到《江格爾》史詩,從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的今天,產生了燦若星辰的文藝大師,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藝精品,不僅為中華民族提供了豐厚滋養,而且為世界文明貢獻了華彩篇章。
——摘自《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