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張炳熹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河南南陽
- 出生日期:1919年6月12日
- 職業: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副主席
-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
- 主要成就:地質礦產資源勘探
- 性別:男
求學歷程,教書育人,管理工作,規劃謀略,
求學歷程
張炳熹,河南南陽人,1919年6月12日生於北京, 幼年時,父親在詹天佑設計建造的京綏鐵路任職,常年在野外奔波,承擔鐵路沿線徵購土地和測繪工作。他隨父母多次乘火車往返北平—張家口一線,在他幼小的心靈里從此種下了熱愛山野的種子。當他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讀書時,上學的往返途中,沿著一段鐵路行走,枕木下的各種卵石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從此他對地質學發生了興趣。恰巧那時附中有礦物學和地質學的選修課,教科書上的許多內容,如岩石的種類及結構,以及卵石在河流搬運過程中磨蝕出來的形態等等,在這些卵石中屢屢能見到,從而認識到地質學中講的東西很多是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因此,他就打定主意學地質。1936年夏考上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滿足了張炳熹的志願。他當時是班上最年輕的學生,只有17歲。他學習很認真,很勤奮,這就為他終生為祖國的地質事業奮鬥不息並取得優異成績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張炳熹在北京大學剛剛讀完一年級的時候,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全國全面的抗日戰爭從此開始。7月29日北平陷落,天津也隨即淪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隨即遷往湖南長沙,組成臨時大學。張炳熹在不願做亡國奴和繼續學習地質的心情驅使下,離家前往長沙,在長沙臨時大學地質地理氣象學系繼續學習。1937年底,南京陷落,武漢告急,學校於1938年1月決定遷往雲南省昆明市。1938年2月開始搬遷,人員分兩路赴滇,一路乘坐交通工具,一路步行。學校組織了一個“湘黔滇旅行團”,根據自填志願,檢查體格,核准步行者244名,地質地理氣象學系有15人參加步行,張炳熹先生是其中之一。2月20日出發,4月28日抵達昆明,歷時68天,全程1671公里。除車船代步、旅途休整外,實際步行40天,步行1300公里,平均每天走三十多公里,最多時達50公里。沿途還作社會調查、觀察地質現象、採集標本。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壯舉,對參加步行者來說,也是意志、心理、勇氣、身體等多方面的磨練。張炳熹參加了這次不平凡的旅行,是很有紀念意義的。張炳熹自己還認為,從學地質的角度來看,這也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抗日戰爭期間,昆明西南聯大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辦學。新建的教室及宿舍1939年夏開始使用,那是一些低矮的土牆泥地草頂(部分是鐵皮頂)的平房。設備差,儀器少,開始只能借雲南大學礦冶系的實驗室進行礦物岩石實習。經過補充,略有改善,但顯微鏡仍不敷套用。圖書也少,學生們不得不在圖書館前排隊等候借書。圖書館坐位少,有的學生不得不到街市的茶館中看書。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張炳熹不僅對地質學方面的課程有濃厚的興趣,還選修了不少數理化方面的課程,並且充分利用雲南的條件,多次出野外作地質考察。畢業前,他與同班的董申保先生一起,填繪了200多平方公里1∶5萬的地質圖,共同寫成了《雲南嵩明楊林一帶之地質》的畢業論文。張炳熹於1940年夏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並留校任教。
張炳熹在西南聯合大學是北京大學學籍的學生,所以既是北京大學的畢業生,也是西南聯大的畢業生。他得到兩份聘書,一份是北京大學的聘書,一份是西南聯大的聘書。張炳熹先任助教,後任研究助教。任教期間,主要擔任光性礦物學和岩石學實習課的教學任務。當時圖書資料有限,也沒有岩石學辭典,為了教好學生,他蒐集資料,將岩石命名的沿革、出處等查找出來。當時沒有卡片,便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寫在一頁一頁的紙上。後來他出國學習,便將這部分資料留給董申保先生。董先生至今仍保留著的就有二三百張。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是多么珍貴的歷史資料,僅從這一側面就可反映出張炳熹的敬業精神、嚴謹的治學態度。
張炳熹特別重視野外地質調查,在當時系主任孫雲鑄教授的安排下,多次出野外考察。1940年寒假,隨新到校的德國人米士(Misch)教授去滇西考察,從大理出發,經永平,沿瀾滄江北行至喇雞井,折東經蘭坪、劍川,返回大理,歷時6周。1941年暑期,隨王恆升、王嘉蔭教授在滇緬鐵路沿線彌渡至順寧間作地質調查。1941年寒假,與蘇良赫、池際尚二先生一起,在易門、安寧一帶考察鐵礦,並且找到了王家灘鐵礦一條主要礦脈,成為雲南鐵礦的一個基地。1942年,西南聯大地質地理氣象學系與雲南建設廳合作,成立雲南地質礦產調查委員會,孫雲鑄教授兼任主任委員。暑假期間,張炳熹與鄧海泉先生一起,去玉溪、峨山、河西三縣作地質礦產調查。1943年秋,參加大理至麗江的驛運路線調查,從麗江經永北、永仁回昆明,歷時3個月。1944年暑期,與司徒穗卿先生一起,隨袁復禮教授赴武定、羅次一帶調查鐵礦。1945年暑期,在孫雲鑄教授率領下,與董申保、池際尚二位先生同去箇舊錫礦。大量的野外地質礦產調查,不僅為雲南的地質工作和建設作出了貢獻,而且也為張炳熹深入了解雲南的地質礦產情況和日後的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地質實踐和理論基礎。 雲南考察
雲南考察
 雲南考察
雲南考察1943年夏,張炳熹參加清華大學第六屆留美公費生“物理礦物學”名額的考試,1944年他被錄取。與學物理的人一起參加考試並被錄取是很不容易的。這說明,張炳熹不僅地質學基礎好,而且數理基礎也好。1946年5月,張炳熹離開昆明赴美國哈佛大學學習。在學習期間,他廣泛涉獵礦物、岩石、礦床、構造地質等領域的課程,在一個變質岩地區做博士論文,學習成績優異,曾獲“金鑰匙獎”。他先後獲碩士、博士學位。在哈佛大學學習時,張炳熹結識一位讀礦物學研究生的美國同學,叫ArtharMontgomery,這位先生對中國人民很友好,經張炳熹聯繫,他贈送給北京大學地質學系一支研究礦物的X光管,張炳熹請途經美國的王鴻禎先生帶回系裡,安裝在原有的X光機上,這支X光管有4個視窗,當時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同時還配有一台最新式的一台粉末X光照相機。
教書育人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身在美國的張炳熹先生早就期盼著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於1950年夏回國,應聘為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副教授,他講授礦床學,在講課中,介紹成礦作用、礦床成因、分類及各種礦床實例。張炳熹講課條理清楚,非常注意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中國的實際材料比較多,很受學生歡迎。張炳熹很注重實際,他講的一些實際內容對學生以後的工作很有用。
馮鐘燕先生回憶說,他在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畢業後,曾在銅官山銅礦工作,關於該礦儲量有多少,有人認為計算少了。馮先生就用張炳熹先生講過的“最近地區法”仔細地計算儲量,很有說服力。當時北京大學沒有專門的礦相課,在礦床課中看光片,但礦相顯微鏡很少,只能供研究用,因此,為了給學生創造學習的條件,張炳熹自己設計,將淘汰的10台岩礦顯微鏡加以改造,在鏡筒上鑽一個眼,強光能射進去,裝一塊45°的反射蓋玻璃片,前面加一塊藍色濾光玻璃片,這樣,學生就能看光片了。學生們不僅感謝張炳熹為改善他們的學習條件所付出的辛勞,也深受張炳熹自力更生精神所感動。時任礦床學助教的邵克忠先生在1952年翻譯的M.M.Short所著《金屬礦物鑑定》一書中,譯者附了一節《一種簡便的反光顯微鏡照明器》,介紹了張炳熹設計的簡便照明器及普通顯微鏡改裝的方法,以及使用一年來的經驗。張炳熹在講課中還將在舊中國從事地質調查時的見聞告訴同學們。例如,箇舊錫礦的工人們如何在惡劣的條件下工作,土豪劣紳如何稱王稱霸、魚肉百姓等等,這些對同學們了解新舊中國的對比很有啟發。
1950年抗美援朝,開展了捐獻運動,為抗美援朝出力。地質學系的師生們想出一個辦法,請剛回國不久的張炳熹先生推薦一批書籍進行翻譯,以所得款項捐獻。張炳熹主持、組織部分師生翻譯的M.P.畢令斯的《構造地質學》(譯者張炳熹等)就是其中的一本,由於種種原因,該書於1959年5月才出版,受到讀者的歡迎。張炳熹地質知識廣博,解決地質問題的能力很強。
1951年夏,張炳熹帶學生去黑龍江省雞西鶴崗煤礦實習,當時礦上有個棘手的問題,由於斷層的原因,煤層找不到了,在礦上的前蘇聯採礦工程師也沒有辦法。張炳熹用構造作圖法解決了這個問題,大家都很佩服。張炳熹對青年教師也很關心,解放初期,由於學生人數激增,每年都有青年教師留校工作,雖然那時政治運動較多,但系裡還是為青年教師組織了一個學習班,每星期三晚上上課,張炳熹為大家講礦床專題,持續了半年之久,對青年教師幫助很大。
管理工作
1952年夏,張炳熹在高等院校調整過程中由北京大學地質學系調到新組建的北京地質學院。他當時擔任地質礦產系副主任、建校委員會(後為校務委員會)委員和岩礦教研室主任。1954年11月任科研處副主任(尹贊勛先生為主任)。1955年院學術委員會成立,張炳熹任常委,1957年任礦產地質勘探系主任,直到1960年調地質部任職。張炳熹在北京地質學院工作了8年,他全力以赴、認真負責、言傳身教、辛勤耕耘,為學校的教學和科研建設,為勘探系和礦床教研室的建立和發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大家一起培養了一大批新中國建國初期急需的地質礦產人才。
教研室是學校的教學基層單位,是辦好學校、保證教學質量的關鍵環節。建校初期,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張炳熹花了很大精力,帶領剛參加工作的幾位年輕教師,一步步把礦床教研室建立起來。當時是大批學生上課。缺少礦相顯微鏡,他以他淵博的知識和很強的動手能力,提出設計方案,和青年教師一起將十數台舊式顯微鏡,加上自製的簡易照明器,改裝為反光顯微鏡,及時地保證了礦相課的教學。上礦床學課缺少掛圖和標本,他和青年教師一起畫教學掛圖,關於岩漿礦床礦石組構圖就是張炳熹親手繪的。他還參加挑選礦石岩石標本,配齊了一些主要礦區(如大冶鐵山、銅陵銅官山等)的實習用成套標本,使同學們能感性地具體地認識礦床地質特徵。幾百人同時上課,缺少教材是突出的困難,張炳熹就抓緊翻譯英文和俄文礦床學資料,給大家做參考。他還編寫了簡明的《礦床成因講義》,發給學生人手一冊,由於內容豐富、論述透徹、重點突出、文字簡練,深受學生和教師的歡迎,不僅滿足了當時教學的需要,也是後來礦床教研室主編礦床學教材的藍本。
張炳熹不僅在教學上關心大家,還幫助每個人明確專業方向,制定進修提高計畫,創造多種條件讓大家很快成長。包括對兄弟院校派來進修礦床學的教師,他都給以熱情指導和具體幫助。張炳熹十分重視對研究生的培養,花了很多心血,一個個地作具體指導。林新多的研究方向是礦田構造,為了提高構造地質知識,張炳熹對他一人講過“構造地質學”。石準立研究海城偉晶岩礦床,當時不會鑑定其中的稀有金屬礦物,張炳熹就找來法文寫的關於馬達加斯加的偉晶岩論文,口譯給他,使他掌握了礦物鑑定方法,很好地完成了研究生論文。
張炳熹在教學上、學術上既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又善於吸收別人的長處,兼收並蓄,作風民主,善於團結,和他在一起工作感到踏實,進步也快。第二,他主持創建了礦產地質及勘探系和專業,帶領全系教職工培養了一大批國家建設急需的礦產勘探人才。張炳熹自1952年起擔任系領導工作,當時是按照前蘇聯的高等教育模式,以培養地質勘探工程師為目標,將學習時間由5年壓縮為4年,但各個教學環節仍舊保留,這對於一支以地質理科專業人員為主組建起來的教師隊伍來說,任務十分艱巨。要反覆修訂教學計畫,組織各類課程教學,安排教學實習和生產實習,組織畢業論文和設計,還要規劃和建設教師隊伍、建立和健全教學管理規章制度等,每一項工作張炳熹都要親自過問和主持,他認真負責、一絲不苟,工作十分繁忙。當時的政治運動、時事學習也多,他經常工作到深夜,兢兢業業、苦幹實幹、以身作則,為全系樹立了榜樣。他既熟悉美國的地質教育情況,又注意分析研究前蘇聯地質教育特點,結合中國國情,逐步地摸索總結自己的經驗,一環扣一環地組織好每一項教學工作。他特別重視野外教學,曾親自帶隊到龐家堡等礦山實習,兩次在江西主持勘探系的生產實習現場會議,多次到實習基地具體指導工作。礦床地質及勘探系廣大師生能有較強的野外地質工作能力,與他的大力倡導和具體幫助是分不開的。建校初期,數理化等基礎課教師對如何與地質教學結合,如何充分發揮作用不很明確。張炳熹就請他們來座談,他以親身經歷說明地質學與數理化各學科間的關係,以及地質類學生學習數理化知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家聽後很受啟發,這不僅對提高基礎課教學質量有利,也為後來一批基礎課教師參加地礦類課題的合作研究打下了思想基礎。
張炳熹組織領導學校的科研工作,並親自主持勘探系兩個重大研究項目,獲得重要進展。1954年12月,學校為加強科研工作,新組建了科研處,張炳熹任副主任兼科研科長,具體組織全校科研工作,包括撰寫科研規劃,組織研究力量,建設重點研究室,組織學術交流等。1956年他作為地質學家代表參加了國家12年科技遠景規劃工作,張炳熹從多個方面給予有關研究項目以具體的指導。例如,著名的結晶學和礦物學家彭志忠教授在開始研究晶體結構時,張炳熹曾幫助他掌握測角的方法。北京地質學院建校初期,不僅教學工作抓得緊,科研工作也有重點地紮實開展,獲得了一批優秀研究成果,也湧現出一批富有才華的年輕學者,這與科研處和張炳熹的努力工作是分不開的。
除了全校的科研組織與管理工作外,張炳熹還親自主持和領導勘探系廣大師生,按教學、生產、科研相結合的原則,進行了兩項意義深遠的研究工作。
中國華南、東南地區,地質結構複雜,礦產資源豐富,張炳熹領導大家綜合研究湘、贛、閩、浙四省地質特徵及成礦規律,他提出用不同構造層來分析地質條件與成礦的關係,從研究區地史演化特點來認識成礦規律性等指導思想,經過師生們三年的努力,撰寫了《湘贛閩浙四省內生金屬成礦規律及對太平洋成礦帶的新認識》一書(1960,內部發行),書中提出一些重要學術觀點,如:中國中生代燕山運動形成的構造岩漿成礦帶具有截穿中生代前不同大地構造單元的特徵。還針對前蘇聯學者強調太平洋成礦帶以鎢錫礦為主而銅鐵礦貧乏的說法,指出銅鐵也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並對太平洋成礦帶的組成和結構提出了新認識。這些都引起中國地質學界的重視,被認為是60年代中中國開始研究太平洋成礦帶的先導性代表成果。此外,他主持編著的《中國礦床學》(1961,內部發行,共75萬字)一書,學習運用唯物辯證法和新的成礦理論,對新中國成立12年來礦產地質勘查的新成果,做了初步的整理和綜合研究,對中國的主要礦種、礦床類型進行了實例解剖,分析了時空分布規律,提出遠景評價和找礦方向,劃分了綜合成礦區,進行了綜合成礦預測。這類理論聯繫實際的大型成礦學專著在60年代是很少見的,為以後的礦床學教學和科研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被認為是“中國區域成礦學研究的代表作”。
1958年北京市委責成北京地質學院負責組建了北京地質局,張炳熹兼任總工程師,為北京地區開展基礎地質工作及普查找礦、為北京地質學院實行教學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一有機會就帶領師生到野外、到礦山作地質考察,指導生產實踐,不斷吸取新知識。
規劃謀略
1960年以後,張炳熹教授一直在地質礦產部領導部門從事地質勘查、科技工作的計畫和業務指導工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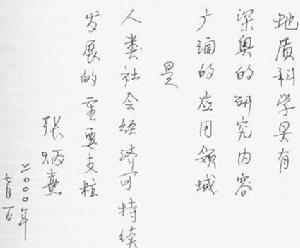 張炳熹題詞
張炳熹題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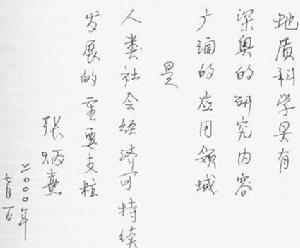 張炳熹題詞
張炳熹題詞為適應中國發展現代尖端工業的需要,加強稀有金屬鋰、鈹、鈮、鉭,放射性鈾、釷以及特種非金屬等礦種的勘查工作,1960年地質部決定成立第二地礦司,張炳熹任總工程師。當時,正值前蘇聯撤走專家,這方面的勘查工作過去又缺少經驗,他力挑重任,使工作及時得以發展。例如,粵北仁化長江鈾礦的工作,他深入基層指導,指出要注意對原生、後生構造的研究,要對礦床的成因、特點認真分析等,對705功勳地質隊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秦嶺東部、阜幕山區與偉晶岩有關的鈹、鋰礦,廣東風化殼型的鈮鉭礦床,白雲鄂博稀土稀有金屬礦的評價,安徽金紅石的工作,以及特種非金屬,諸如硼、壓電水晶、金剛石、藍石棉等工作,他都不辭辛勞,親臨現場指導,並結合專業會議,一再介紹上述礦產和國外情況,參照國內具體條件,認真對比,進行技術指導。可惜這些礦種當時定的保密級別很高,他講述的很多資料當時不能公開出版,現已很難蒐集。
1965年,地質部第一、二地礦司合併後,張炳熹仍留在地礦司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國家機構進行了調整。1969年他被下放幹校。1970年調回當時的國家計委地質局工作。1972—1975年間,他先後4次以中國代表團顧問身份參加了在紐約和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和平利用國家管轄範圍以外海底委員會會議;1975年,又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代表之一出席了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第三期會議,並參加審議“建立國家管轄範圍以外海底、洋底及其底土區域和資源的公平國際制度”等檔案。1980—1982年,他被推選擔任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理事會自然資源司司長,出色的工作受到一致好評。1987年7月,張炳熹被聘任為聯合國國際海底管理局籌委會審查先驅投資者申請的專家小組成員。多年來,他以其廣博的知識,在為維護中國海洋礦產資源權益,為國內研究解決國際海域劃界爭端的辦法,制訂東海大陸架立法的原則等方面,從地質依據角度,提出了有充分說服力的見解,作出了有重要意義的貢獻。
70年代後期,張炳熹教授曾寫有《有關長江中下游中生代晚期火山岩系中鐵礦的若干問題》(1983年在《礦床地質》上發表),對中國矽卡岩和火山岩型鐵礦的關係作了深入的探討。在1980年全國第二次礦床會議上,張炳熹寫有《礦床學研究問題》一文,深為各方所關注和重視。
張炳熹教授在制訂中國地質科技發展規劃中,常以自己卓越的見識,豐富的實踐經驗發揮了重要作用。50年代,他就參與了國家科委編制的中國十二年(1956—1967)科技發展規劃。近幾年,主持了中國地質學會“2000年的中國地質”研究工作,主編出版有《當代地質科技動向》、《2000年的中國地質》、《中國地質工作發展戰略》、《依靠科技進步,推動地質工作發展》等多種專著。他又是《國土資源遙感》刊物的主編,先後撰寫了多篇有關地質科技工作的建議,並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起草的初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