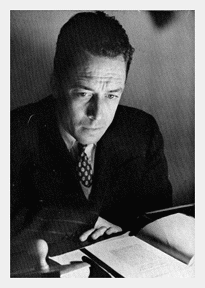人物經歷
1913年11月7日,阿爾貝·加繆生於
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Mondovi)。加繆父親在1914年大戰時陣亡後,他隨母親移居阿爾及爾貧民區外祖母家,生活極為艱難。阿爾貝由做傭人的母親撫養長大,從小就在阿爾及利亞的貝爾庫(Belcourt)的貧民區嘗盡了生活艱辛。1923到1924年在鄉村國小里,一位名叫路易·熱爾曼(加繆對他的知遇之恩一直念念不忘,在他的諾貝爾獎答謝辭中提到了這位老師)的教師發現了加繆的天分,極力勸說加繆的家人讓他繼續上學。於是,加繆參加了助學金考試,並得以於1924年進入阿爾及爾的Bugeaud中學。

阿爾貝·加繆
1930年加繆進入哲學班學習。首次得肺結核,生病的經歷讓他感受到生命對於人類的不公。1931年結識哲學教授Jean Grenier。加繆年少時是阿爾及利亞競技大學隊的門將,可惜1931年因為肺病終結了足球生涯。加繆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只有通過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靈魂”。1932年,他在《南方》(Sud)雜誌上第一次發表隨筆作品。1933年,他進入阿爾及爾大學攻讀哲學和古典文學。
1934年6月,與Simone Hié結婚,一年後離婚。加繆1935年開始從事戲劇活動,曾創辦過劇團,寫過劇本,當過演員。戲劇在他一生的創作中占有重要地位。1935年秋天他加入了法國共產黨阿爾及爾支部。但由於他與穆斯林作家和伊斯蘭宗教領袖來往,對黨在阿爾及利亞的政策有不同看法,因而於1937年11月被開除出黨。1936年畢業,論文題為《新柏拉圖主義和基督教思想》,但因肺病而未能參加大學任教資格考試。

阿爾貝·加繆
1936至1939年,一開始在勞動劇院(Theatrê du travail),然後在團隊劇院改編並參演眾多劇目,如
馬爾羅的《蔑視的時代》(Letemps dumépris)等。
1937年,加繆就出版了隨筆集《反與正》,第一次表現出自己思想的鋒芒。他的隨筆涉及到了人在被異化的世界裡的孤獨感、人面對自身的罪惡和死亡威脅時應該如何做出選擇等等。1940年,阿爾貝·加繆來到法國首都巴黎,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先在《巴黎晚報》從事編輯工作。這一年的6月14日,希特勒軍隊的鐵蹄就踏進了巴黎市區,很快,由納粹扶植起來的法國傀儡政權維希政府開始運作。這年的冬天,加繆帶著妻子離開淪陷的巴黎,來到了阿爾及利亞的
奧蘭城教書,在這裡一共住了18個月,正是這一段生活,使他醞釀出《
鼠疫》。
1942年,加繆離開阿爾及利亞前往巴黎,開始為《巴黎晚報》工作,然後在伽里馬出版社做編輯,秘密地活躍於抵抗運動中,主編地下刊物《
戰鬥報》。
加繆因小說《
局外人》成名,書中他形象地提出了存在主義關於“荒謬”的觀念。隨後,他開始寫作哲學隨筆《西西弗的神話》。
1943年4月,加繆結識了薩特(讓-保羅·薩特)和波伏娃,在哲學和戲劇等方面的共同愛好使他們成了非常親密的朋友。然而薩特傾向於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而加繆則對蘇聯社會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1944年法國解放,加繆出任《戰鬥報》主編,寫了不少著名的論文。

1957年的加繆
1945戲劇《卡里古拉》首次演出。1947年的長篇小說《鼠疫》曾獲法國批評獎,它進一步確立了他在西方當代文學中的重要地位,1949年12月,戲劇《正義者》(Justes)首次演出。
1951年加繆發表了哲學論文《
反抗者》之後,遭到了左派知識分子陣營的攻擊,並引起一場與薩特等人長達一年之久的論戰,最後與薩特決裂。這時人們才發現,加繆是荒誕哲學及其文學的代表人物。
1954年春天,《夏天》出版。10月4、5、6三天,他前往荷蘭作短暫旅行。這是加繆唯一一次訪問這個成為他的小說《
墮落》(La chute)發生地的國家。加繆在
阿姆斯特丹停留了兩天。在
海牙,他參觀了Mauritshuis博物館,對倫勃朗的作品讚不絕口。11月1日,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線開始襲擊阿拉伯和法國平民,隨後
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
1955年3月,《一件有趣的案件》(Uncas intéressant)上演,改編自Dino Buzzati的作品。4月,訪問希臘。5月到轉年2月,為《快報》(L‘express)寫專欄文章,評論阿爾及利亞危機,所有文章以後,以“ActuellesIII”為題結集出版。
1956年,阿爾貝·加繆發表了中篇小說《
墮落》,還出版了包括6個短篇小說的集子《流放與王國》。這個時候,他的思想多少已經開始轉向基督教倫理的探討,對過於世俗化的道德和存在的命題,已經不那么感興趣了。中篇小說《墮落》的發表,實際上是對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知識分子的一種質疑。最終,歷史證明了阿爾貝·加繆更加正確,而薩特在當時似乎正確,但是後來則並不正確了。

阿爾貝·加繆
1957年10月,
瑞典文學院宣布,44歲的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獲得了該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阿爾貝·加繆因此成為了這個獎項歷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之一。這一年的12月,他在瑞典的一所大學做了一場題為《藝術家及其時代》的演講,他說道:“面對時代,藝術家既不能棄之不顧也不能迷失其中。如果他棄之不顧,他就要說空話。但是,反過來說,在他把時代當作客體的情況下,他就作為主體肯定了自身的存在,並且不能完全服從它。換句話說,藝術家正是在選擇分享普通人的命運的時候肯定了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藝術的目的不在立法和統治,而首先在於理解。”
1958年《瑞典演講》出版。在Lourmarin買了一幢房子。

加繆之墓
1959年《鬼怪附身的人》上演。同時,加繆千方百計想實現一個渴望了許久的夢想:成立自己的劇團。
1960年1月4日,加繆搭朋友的順風車從
普羅旺斯去巴黎,途中發生車禍,加繆當場死亡,年僅47歲。在他隨身攜帶的提包里,還有一部沒有完成的長篇小說手稿《
第一個人》。
主要作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 Renégat ou un esprit confus | |
| | |
| | |
| Jonas ou l'artiste au travai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創作特點
荒誕
在阿爾貝·加繆的全部文學作品和哲學隨筆當中,“荒誕”是他強調的最重要的一個概念。“荒誕”這個概念也是20世紀文學和哲學中非常重要的關鍵字之一。但是,對“荒誕”的解釋則大為不同,各人有各人的表述。加繆是這么說的:“這個世界是不合理的,這是人們可以明確說出的表述。但是,
荒誕是這一不合理性與人的心靈深處所呼喚的對理性的強烈要求的對立。”聽上去,他的這句解釋特別的拗口和費解,其實,他理解的人生荒誕感,是人對世界的主觀感受。加繆認為,人在面對艱難而機械的現實生存的時候,每天都要按照一個節奏和生活模式來生存,必然要產生出我為什麼要這么生活,我為什麼不能以其它方式生活的荒誕感,可是,偏偏人就不能以其它方式生活,人還必須要以人現在的方式生活。於是,這就產生了荒誕感。

阿爾貝·加繆
風格
加繆的創作特色是用
白描手法,極其客觀地表現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筆簡潔、明快、樸實,保持傳統的優雅筆調和純正風格。他的“小說從來都是形象的哲學”,蘊含著哲學家對人生的嚴肅思考和藝術家的強烈激情。在短暫的創作生涯中,他贏得了遠遠超過前輩的榮譽。他的哲學及其文學作品,對後期的
荒誕派戲劇和新小說影響很大。評論家認為,加繆的作品體現了適應
工業時代要求的新人道主義精神。薩特說他在一個把
現實主義當作金牛膜拜的時代里,肯定了
精神世界的存在。
人物評價
“加繆的作品始終與追求正義緊密相連。”——法國作家文化部長
馬爾羅“加繆在20世紀頂住了歷史潮流,獨自繼承著源遠流長的醒世文學,他懷著頑強、嚴格、純潔、肅穆、熱情的人道主義,向當今時代的種種粗俗醜陋發起了勝負難卜的宣戰”。——法國作家、哲學家薩特
“他(加繆)作為一個藝術家和道德家,通過一個存在主義者對世界荒誕性的透視,形象地體現了現代人的道德良知,戲劇性地表現了
自由、
正義和
死亡等有關人類存在的最基本的問題。”——
瑞典文學院授予加繆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辭
“加繆的作品是從戰後混亂中冒出來的少有的文學之聲,充滿既和諧又有分寸的人道主義聲音。”——《
紐約時報》
“加繆有著一顆不停地探求和思索的靈魂。”——美國作家
福克納“
加繆以外,我想不起還有其他現代作家能喚起愛。他死於1960年,他的死讓整個文學界感到是一種個人損失。”在她看來,加繆是20世紀文學具有“理想丈夫”般形象的作家,同樣描繪自殺、冷漠、罪咎、絕對的恐怖這些現代文學主題,“卻帶著一種如此理智、適度、自如、和藹而不失冷靜的氣質,使他與其他人迥然有別。”——(
蘇珊·桑塔格《反對闡釋》)
加繆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他留給人們的遺產不僅有《西西弗的神話》、《
局外人》對人的荒誕處境的揭示,更重要的也許是人們該如何應對荒誕。加繆發現了有一種跟“情慾的罪惡”表現形態不同的罪惡——邏輯的罪惡——大行其道,荒誕理性以喬裝打扮的樣式鼓譟著,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德國的
法西斯主義,邏輯性殺人成了人類尊嚴和良知的最大敵人。他追根溯源,對理性暴力的傳統和哲學基礎進行了梳理,他提出了以
古希臘的均衡思想為基礎的南方思想,亦即太陽思想、地中海思想,並把二者的關係比喻為“永恆的青春過分行為與成年人的力量之間”的關係。顯然,加繆的“太陽”思想與《局外人》中的“陽光”是根本對立的。他所真正熱愛的,是給人帶來溫暖的真實、美好、自然、均衡的“陽光”。——《文匯報》
後世紀念
2013年,巴黎十多家公共圖書館聯合推出了貫穿9、10兩個月的紀念活動,他們以加繆著作中的“荒謬”和“反叛”為主題詞策劃活動。這些活動包括了作品朗誦會、圓桌討論會、電影放映會、配樂朗誦等等。
在倫敦的加繆協會(由英國的加繆愛好者們於2007年成立)也舉行了討論會。美國的加繆協會沒有忘記在他們的官網上對這次活動進行導覽。來自英美等國的很多專家會參與這次活動,他們討論的主題包括了“加繆和陌生人”、“加繆和荒謬”、“加繆和薩特”等許多方面。而美國方面許多不同的大學內有著各種各樣的活動,包括了展覽和配樂朗誦等等。
主要思想
人道主義思想
加繆的思想,其核心就是
人道主義,人的尊嚴問題,一直是纏繞著他的創作、生活和政治鬥爭的根本問題。《西西弗的神話》和《
局外人》構成了加繆文學創作的母題,包含著加繆未來作品的核心問題。書中,西西弗的幸福假設的提出,其本質動機,不在荒誕,荒誕既不能告訴我們幸福,也不能告訴我們不幸。之所以加繆假設西西弗是幸福的,是因為他認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嚴,被責為永罰,卻
幸福,這是一種反抗,也是在這種條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體現
尊嚴。加繆在假設西西弗幸福的時候,充分運用了想像和獨斷,其潛台詞,卻是人類尊嚴的需要。由
荒誕的出發點,薩特走向焦慮和不安,而加繆走向幸福,薩特是思辨後的結論,加繆卻是激情洋溢的獨斷。

阿爾貝·加繆
二元對立
加繆的創作存在大量的
二元對立的主題,其中有一些直接作為書名如反與正,流放和王國等,荒誕和理性,生與死,墮落和拯救,陽光和陰影,有罪和無辜。這些二元對立的主題經常成對出現,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輔相成的意思,這是他的一大特點和魅力之所在。加繆在他的隨筆中數次使用這樣的修辭方式:用一片黑暗來形容明亮的陽光。隨筆中也許不過是一種修辭,但這種修辭代表的思維方式卻貫穿了加繆幾乎全部的創作,成為他的重要特色。

阿爾貝·加繆
無論是他的小說還是戲劇,或是哲理
隨筆,都看不到邏輯的一貫性,到處都隱含著矛盾,這在別的作家那裡,這可能是個致命的弱點,可從加繆的作品中體現的卻是複雜的深刻。
丹麥物理學家
玻爾說過:"和小真理相對的當然是謬誤,可是和偉大的真理相對的仍然是偉大的真理。"正是在這樣對矛盾的正視當中反映了人類思維的局限及其與世界的斷裂。二元對立的兩極互相為對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強大的張力,悖論和歧義性、多義性在此叢生,這也成為加繆難以被定義的地方,其間人道主義一以貫之,然而人道主義本來就是意義含混的詞。
二元對立其實是西方的傳統思維習慣,傳統的二元對立主要是主客關係,善與惡,美與醜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加繆那兒,這些傳統的理念被拋棄了,善惡美醜問題被諸如流放和王國,陽光和陰影這樣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講述一樁殺人案的《
局外人》中,傳統的罪與無辜的問題竟消解於無形之中,只是作為一個背景存在。加繆的這些悖論性的理念沒有給他找到理論上的出路,卻使他的小說和戲劇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義性,成為意義之源。在美學的意義上,則是用簡單,毫不修飾的語言產生讓人困惑的效果,這在《局外人》和《墮落》中最為明顯。
存在主義
阿爾貝·加繆並不是一個純思辨型的哲學家,他從來都沒有像薩特那樣寫過磚頭一樣厚的哲學著作。他是以自身經歷、以文學創作中的人物形象和人的行為,來推導出時代的哲學命題的帶有哲學思想的小說家。
加繆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
存在主義者,儘管他自己多次否認。以《鼠疫》為例,《鼠疫》是存在主義作家加繆的代表作,被認為是加繆最有影響力和社會意義的作品。加繆的存在主義哲學不像
讓-保羅·薩特和
海德格爾的那般艱深,至少在這篇小說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加繆認為世間的混亂和荒謬是必然的,人作為一種存在,是沒有他的必然的意義與目的的。在故事中,加繆描寫了一個神甫的兩次布道,從而否定了宗教可以帶來的意義。他通過主人公的態度表明了一個人面對虛無的人生的態度,就是以愛情、
友誼和最重要的——
同情心來充實內心。存在主義本身就否定了“意義”,把人放逐到了荒蕪的沙漠。可是和這種哲學相反,存在主義哲學家往往都是“良心”的虔誠追隨者。
阿爾貝·加繆是存在主義哲學家中對荒誕論述得最為全面、最深刻,並使之具有新意的人之一,這也是他的哲學的最大特色,因而被人們稱之為“
荒誕哲學” 。荒誕哲學是資產階級文明遭到嚴重衝擊的哲學表現。隨著西方
資本主義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出它的痼疾,和由此帶來的災難性、毀壞性後果,諸如劇烈的
階級鬥爭和社會震盪,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兩次
世界大戰,
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它對人的
滅絕人性的迫害,“使得人們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所滋長蔓延起來的對
理性和科學的頌揚,對社會進步的樂觀幻想,迅速被一種所謂‘存在的不可理解’,‘人的存在的走投無路的悲劇性’的感覺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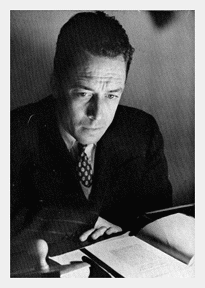
阿爾貝·加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們更感到前途渺茫,苦悶彷徨,人的生存面臨嚴重威脅,人失去了安全感,人被絕望、孤獨和無家可歸的情緒所籠罩,這時
理性主義、
科學主義和樂觀主義逐步被荒誕哲學所取代。人們普遍感受到這個世界的荒誕性,人存在的荒誕性,於是荒誕哲學應運而生。存在主義哲學對於“荒誕”的解釋是:由於人和世界的分離,世界對於人來說是荒誕的、毫無意義的,而人對荒誕的世界無能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對一切事物都無動於衷。在
存在主義文學中,加繆無疑是將這種狀態表現得最惟妙惟肖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