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陀
- 別名:孟克勤
- 國籍:中國
- 民族:達斡爾族
- 出生地:內蒙古莫力達瓦旗人
- 出生日期:1939年
- 職業:作家、文藝批評家
- 畢業院校:北京第101中學
- 主要成就:首屆優秀短篇小說獎,優秀電影獎
- 代表作品:《李四光》,《沙鷗》,《七十年代》,《視界》
簡介,人物生平,個人作品,個人榮譽,傳奇身世,批評家,文學批評觀,人物評價,
簡介
人物生平

童年隨父母遷移各地,後來定居在北京讀國小,中學,從中學時代起就練習寫詩歌,小說和散文。1958年北京一零一中學高中畢業後到第二通用機械廠工作,當過熱處理工、加熱工、鉗工,1979年加入中國作協,文化大革命期間參加編輯《北京工人》報。1980年調作協北京分會從事創作,後為《北京文學》副主編。
1982年前後停止小說寫作並轉向文學和電影批評。停筆30年後,開始創作長篇小說《無名指》,並回歸作家行列。
1982年以前他以小說創作為主,他的小說《願你聽到這支歌》曾獲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另外,《自由落體》、《餘光》等短篇小說以其對人物獨特的心理意識活動的捕捉和呈現而別具一格,也引起不同評論。
另外,他還加入創作了《李四光》、《沙鷗》等電影劇本。
《李四光》將傳記故事的真實性與情節的曲折性和生動性較好地融匯在一起,展示了李四光的優秀品格和科學成就,獲文化部1979年優秀影片獎。
《沙鷗》追求表現人物的意志幻覺,情緒等方面的形象語言,在表達一種時代性的主題這方面有很大成績。
1982年以後,他較多地從事理論批評,與張暖忻合寫的《談電影語言的現代化》,強調了以電影語言的研究,提出在電影語言的迅速,持續更新的前提下,現代電影藝術應對電影語言開始新的探索,洋為中用,加快我國電影語言現代化的步伐。在理論方面,他思路敏捷,有獨到見解,對於具有探索傾向的作家作品尤有興趣,但有時顯得熱情有餘,理論準備不足。
個人作品
1987年—1991年與黃子平合作編選《中國小說》年選(共4冊),香港三聯出版。1988年—1991年主編《中國尋根小說選》、《中國實驗小說選》、《中國新寫實小說選》分別在香港和台灣出版。2000年主編《大眾文化研究譯叢》及《當代大眾文化批評叢書》。
2000年—2004年與陳燕谷主編理論刊物《視界(1-10輯)》,《中國前衛藝術》。
2000年與北島合作主編《七十年代》;主編《昨天的故事:關於重寫文學史》等。
個人榮譽
傳奇身世
早年李陀隨同母親流落北京,青少年時期就讀於北京貴族學校101中學。
少數民族的血緣,不僅給了李陀聰明才智,而且還給了他一副相貌堂堂的儀表。不說讓女人們人見人愛,至少不太會受到女人的冷落。李陀能讓才貌雙全的電影才女導演斷然下嫁。他也能讓主人家的公主,對他好感永存。那位回憶錄作者在書中說起李陀時的聲調,真是甜得不能再甜。一聲小哥哥,叫得就像大觀園裡的哪個小女孩在呼喚著賈寶玉似的。由此也可以想見,作為謎語的李陀,有著如何不凡的個人魅力。
李陀不僅讓女人對他著迷,也讓男性朋友覺得他非常哥們。李陀待人熱情起來,有著不顧一切的豪情滿懷,從不讓人懷疑他具有兩脅插刀的俠氣。可能也是基於這樣的義氣,李陀推薦起文學新人和小說新作來,同樣的不遺餘力。
批評家
1978年,39歲的“產業工人”李陀正在貴陽修改關於李四光的劇本,電話傳來,他的短篇小說《願你聽到這支歌》獲得了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之後,李陀從北京石景山的一家重型機械廠調到中國作家協會北京分會,成了一名“駐會作家”。

駐會作家”李陀看了很多外國作品後,開始覺得自己這么寫作不行,1982年他決定暫時放下小說,先做積累,結果“小說就一直放下,最後就變成搞文學批評的了”。
1989年6月2日,應芝加哥大學之邀,訪問學者李陀前往美國。一訪就是5年,1994年李陀才第一次回國,此後他又陸續在伯克利大學、杜克大學、北卡羅來納、密西根等大學當訪問學者,教中國現當代文學,直到現在。1980年代,至少都認真,能爭吵
1980年代,各個編輯部還都把“為他人做嫁衣裳”當作編輯的天職。當時文學的繁榮局面,得益於思想啟蒙、思想解放運動,而且編輯大都是有文學理想的人,那種文學理想,跟“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期刊史有著密切的關聯。
當時編輯一旦發現好作品,就會把作者請來,住下改稿,成熟了就發表。發表後還會請作者來開會。其他刊物的編輯看到新作者的出現,也都會馬上約稿。編輯部內部氣氛也很活躍。一篇文章來了,年老的說不能發,年輕的說一定得發。類似衝突是各個編輯部的常態。
1980年代的批評也是有權威性的。即使是在官方政策制約下的批評家(以下簡稱為“官方批評家”),也是有權威性的。“傷痕文學”,就是在官方批評家的提倡、鼓勵、刺激下發展起來的。
1985年以後形成的新批評家群體,他們的權威性來自文學發展的創新訴求。在打破文化專制主義的問題上,官方批評家總是顧慮重重。而新批評家想的就是文學本身。可以說,“純文學”潮流並不是作家創造的,而是新批評家創造的,至少是批評家和作家共同創造的。當時的情況,首先是作家走在前面,而批評家則把大旗樹起來。
1980年代初,官方批評家,如馮牧、雷達都是傷痕文學的支持者、宣傳者,可我們都很懷疑,覺得傷痕文學不是我們期待的文學。然而我們的期待也很模糊。汪曾祺的《受戒》之後,何立偉、阿城陸續出了一些探索性的作品,但他們沒有構成潮流。從今天的角度,可以把他們看成“尋根文學”的先頭部隊。
如何看待虛構的歷史?如何看待跟社會主義革命無關的小說?官方批評家有點亂了,不少人甚至一下子就喪失了批評能力。這時候,年輕一代批評家站出來了。比如季紅真,對阿城作品的詮釋是“文明與愚昧的衝突”。今天看來,那種詮釋很成問題,但當時震動很大,因為她根本不提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大家都覺得非常新鮮。年輕批評家,像吳亮、蔡翔、程德培,黃子平等人,立刻得到了廣泛認同,堪稱一夜成名。
1987年,余華、蘇童、北村、格非、孫甘露、殘雪這批作家出來了。但包括新潮批評家在內,大家都沒注意。批評界還有人說1987年前後沒有好作品,“文學陷入了低谷”。新潮批評群體的成員,一般來說,跟作協、文聯繫統的關係都很疏遠。最典型的是蔡翔,他原來是工人,寫了很好的批評文章之後,被調到《上海文學》編輯部。在編《上海文學》理論版時,他仍然堅持撰寫獨立的批評文章。當然,新潮批評群體中的很多人都成了作協會員,但一開始都不是。當時發表批評文章的文學刊物很多,最多的是《上海文學》、《文學評論》、《文藝報》、《鐘山》、《花城》、《中國作家》等刊物。

1980年代,由於精神生活長期匱乏,所以全民都熱愛文學。因此,即使是很小的刊物,只要是關於文學批評的,也會很快就被注意。比如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崛起》,發在一個“很偏遠”的雜誌上,但當時很轟動,官方批評家都圍剿他。全世界都一樣,作家一般都假裝不在乎批評。1980年代,有作家甚至說,文學批評只不過是長在文學這棵樹上的蘑菇。但作家都偷偷看批評;不但看,批評還能對他們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1990年代,惟一的作用就是促銷.1990年代,新潮批評家群體很快就消失了。年輕的職業批評家,要么到學院去了,要么改行做別的。進入大學的那部分批評家,成了學術機制里的一部分。文學批評應該面對普通讀者,學術研究應該面向學術界,完全是兩回事。
張頤武等學者,習慣於把學術名詞搬到報紙上,搞得誰也看不懂,而一些人卻覺得很深奧。1990年代初,此風盛極一時。
文學批評領域率先實現“市場化”的群體,是1980年代的一些官方批評家。他們的批評與出版、銷售合成一體,很快就被“收編”進了商家宣傳這個炒作體制當中。
商業大潮中,期刊也沒法不“濕鞋”。大概只有《讀書》至今還沒有拿錢買版面的事情。
1990年代,記者、編輯中誕生了一個很大的批評群體,這個群體也很快就與商業機制融為一體了。那種批評無所謂方法,沒任何節制,毫無標準地吹捧作品。這樣一來,像以前那樣對文學創作起著關注、監督、反省作用的批評家隊伍就不復存在了。
1990年代以後,“70後”、“80後”、“個人寫作”,看似火爆。不過在我看來,那不過是一些批評家濫用命名權而已。濫用命名權,也是1990年代以後批評家權威性喪失的一個註解。所以,在1990年代,文學批評沒什麼作用,惟一的作用就是促銷。
作為文學批評家,李陀算得上成就斐然,與此同時,也招來了不少的質疑和反對的聲音。對於這一點,他並沒有太過激烈的反應。他提出的“小人時代的文學”在網上招致罵聲一片,他仍然告訴記者,至今還是有著同樣的觀點。
他說,他很歡迎大家對他的觀點提出質疑,和他進行討論,只要提出了問題,就能夠通過探討取得收穫。
李陀在《讀書》上號召廣大作家,為工農寫作,替民眾代言。他說:“那些沒有筆桿子的下崗工人、民工、還在窮困中掙扎的農民,他們怎么辦?他們的感情、思考、喜怒哀樂、他們的‘顯意識’和‘潛意識’,怎么來表達?”他認為,如今的文學可以稱作“小人時代的文學”,特徵之一是“文學的內容越來越瑣碎”,很少有作家再去關注底層的生存狀態和需求。
針對網上不少人支持的“小人時代的文學正說明了每個人都能發出自己的聲音,沒有人需要代言,是一種文學的進步”這種觀點,李陀認為,持這種意見的人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而沒有考慮到真正的最底層的人的需求。
“他們說,網路發達了,每個人都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倒要問問,那些沒錢買電腦的人呢?那些沒錢上網咖的人呢?人們怎么傾聽得到他們的聲音?”李陀堅持認為,作家不能太過“小資”,要有社會責任感。或許,這就是他長期堅持的“知識分子要用‘文學的方式’參與社會生活”這種觀點的表現吧。
不久前,李陀的台灣同行南方朔告訴記者,寫評論是他的謀生手段而非興趣所在。記者把這個問題拋在李陀面前的時候,李陀的表情顯得有些凝重。他說,自己不是個聰明人,不可能同時做很多事情——“今後,我就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搞文學批評。”
文學批評觀
李陀在《上海文學》1999年第四期上發表《移動的地平線》一文,他指出,文學的進化論批評在九十年代初的所謂“後新時期文學”的言說中已經露了頭,九十年代中期之後越演越烈,至近一兩年,關於“晚生代”的大量評論又把這種批評推向了一個高潮。他認為,不能說當前的文學批評完全沒有批判。但令人驚訝的是,無論目前正在深入發展的關於“現代性”的討論,還是文化研究領域對當代資本主義所做的分析和批判,似乎都沒有得到進化論批評的注意,進化論批評不僅一般地肯定市場經濟對“個人”的解放,認為正是這種“解放”才使“真正的文學”,也就是“個人化的文學”得以出現,而且往往用生命體驗、生存處境或惡的欲望這些具有哲學或心理學意味的概念做依據,來為“個人化寫作”辯護,為商品形式“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並按照自己的形象來改造這些方面”這一歷史過程辯護,我們不難發現這些論說與八十年代新啟蒙話語之間的內在聯繫。但是如何評價新啟蒙運動已經成了中國知識界熱烈爭論的一個焦點,面對這樣一場爭論,文學批評如何對待自己與新啟蒙的關係首先就是個問題。當然,這究竟是不是一個問題,前提仍然是批評家要作一個選擇:我們到底需要不需要批判的文學批評?

人物評價
在80 年代北京文學圈裡,甚至在整箇中國文壇上,找不出一個比李陀更活躍比李陀更知名比李陀更悲劇的人物來。每每說到甚至想到李陀,總讓人哀其境遇,怒其功利心。說他是文學那五,他卻沒有那五那樣的舊貴背景;說他很有文學的責任感使命感,他有時候像個文學玩票者。說他從來不把文學當回事,他卻對文學熱愛到了一生都沒有離開過文學。說他是個文學青年,他絕對是個文壇領袖,號稱陀爺。但要說他是文學大家,卻還沒有寫出一部經典大作。他有時跟人說話親切隨和,謙虛謹慎;有時突然變得高高在上,向所有他所見到或者沒有見到的人們指手畫腳。

陳建功:當時不管是一個地區也好,一個國家也好,有一兩個核心的批評家真是太重要了。在我們這個文化圈子中主要有李陀、鄭萬隆、阿城、張承志、還有後來的李歐梵、聶華苓等人形成了一個很好的文學氛圍。李陀讀書多,視野開闊,對文學理解時有創見。當時因為李陀的存在,很多作家都到他家聚會,也因為他的存在,聯繫了內地作家和海外作家。因為李陀,我認識了李歐梵,聶華苓等。李陀經常提出一些創作上的見解,對於我們的創作很有啟發,比如他提出關於各式各樣的小說的觀點,肯定了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他的許多發現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比如說阿城的《棋王》就是在我們的飯桌上講述的故事,後來催促他寫出來的。鄭萬隆的《老棒子酒館》當時也是引起我們廣泛的討論。還有張承志從西北帶回來的幻燈片,也就是從那個時候他開始醞釀《心靈史》。還有那個時候我寫《前科》,經常從劉家窯跑到東四那邊鄭萬隆的家,連夜給他講我的構思,然後騎車回來接著寫。談到半夜很興奮的時候,我和鄭萬隆、李陀三個人到天安門廣場溜達,坐在馬路邊上談文學,有時候餓了就到旁邊的西瓜攤買西瓜來吃。當時就是這樣一種狀態。因為李陀的存在,後來和李歐梵、聶華苓、蔣熏等人也經常交流文學創作體會。在我們的交流中,經常會有一些激烈的話題,比如李陀經常會訓斥一些作家文體上缺乏自覺等等,李陀是性情中人,憤怒露於言表。李陀會敏銳地發現作家中產生新的因素,在他的推薦下,成就了很多作家。李陀的言論同時也給予我們很多的幫助,提高了我們的境界和思想。李陀的視野不僅僅局限於文學方面,他在影視方面也多有創見,支持過不少藝術家的文藝活動。在李陀的影響下,我們也接觸到各種藝術門類,這些藝術門類的相互融合,大大拓寬了我們的視野,提高了我們的藝術鑑賞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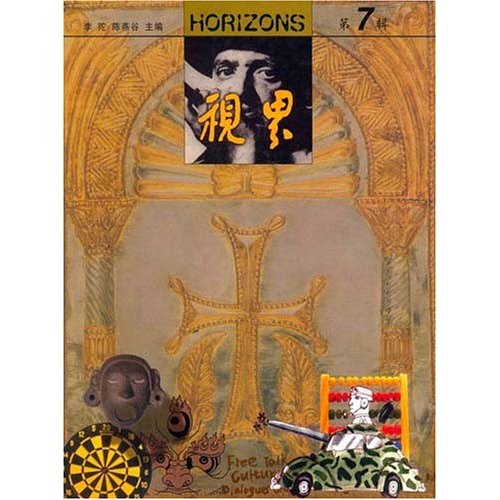
 李陀
李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