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背景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末的
民權運動 ,在美國全國範圍內喚起對於種族問題的重視,與此平行的女性主義運動,也通過大量的
街頭運動 、政治論述與文化創作,來喚起社會對於工作場所和
公共領域 中女性所受歧視的重視。1969年“
石牆事件 ”爆發,標誌著之前還較為零散和地下的同性戀權益運動,也正式進入公眾政治舞台,成為積極爭取權益、呼籲社會意識的政治力量。
19世紀50年代,一小群女同性戀者在戴爾·馬丁(Del Martin) 和菲利斯·萊昂 (PhyuisLyon) 的領導下,建立了一個女同性戀組織,取名為“比利蒂斯的女兒”(Daughter of Bilitis),這個名字來源於由古希臘著名女同性戀詩人
薩福 (古希臘文:Σαπφώ;拉丁化:Sappho,約前630或者612~約前592或者560) 一首詩改寫的色情詩。在美國約有600個同性戀者的組織,有大量的出版物。她們經常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活躍在各類傳媒上;選舉能代表同性戀利益的地方議員和行政長官;爭取法律上對同性戀婚姻的認可。80年代,在美軍中,
女兵 將近15萬人,有大量的女同性戀者無意中在那裡得以聚集,她們當中的許多人在平民生活中是難以相遇的。無怪乎有人說,曾經不敢道出自己姓名的愛已經變得滔滔不絕了。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組織“復仇女神” 定義 女同性戀理論伴隨著20世紀70年代激進女性主義之發展而崛起,到20世紀90年代卓然成家,歷經不同歷史時段與種族、階級、文化差異之衝擊,與婦女運動和同性戀運動相互合縱連橫,以凸顯
性傾向 (sexuality)與性別(gender)、
異性戀 機制與
父權 結構之勾連。
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 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認為:“所有女人皆為女同性戀”;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認為:“女同性戀不是女人”;有人認為女同性戀乃膚血乳骨的信誓承諾;有人則以為“女同性戀”乃相當晚近的歷史建構,並不指涉任何文化變異和歷史決定論架構之外唯一永恆存在的女同性戀本質。各家說法紛紜,莫衷一是。
在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的概念中,女同性戀並不完全是一個性傾向的問題,而是每一個想要認同女性、從而終結男性優勢的女性都必須做出的一個政治上的選擇,因此又被稱為政治女同性戀者(political lesbian)。
沿革 女同性戀分離主義(Lesbian Separatism)是這種複雜關係的一個極具想像力和北美特色的產物。
1961年之前,美國的每個州的法律里都將肛交規定為違法;1973年,美國心理學會才將
同性戀 從精神疾病中移除;此前,心理醫生們普遍認為同性戀是可以治療並且應當被治療的。與這樣的壓抑的環境對比,1969年的石牆運動使得同性戀權益運動成為無法忽視的強音,也讓大部分同性戀者開始敢於對生活和社群進行各種天馬行空的想像。
女同性戀者不久後就開始熱情擁抱女性主義,但是她們一方面將女權主義對於女性獨立的訴求推至極端,一方面又對女性主義為爭取權益而不斷與社會主流協商感到不滿,既希望能夠建立毫不依靠男性、完全實踐平等自由原則的女性身份,又希望能夠擺脫與立法和輿論進行的令人失望的關於
同工同酬 、家務平分、生育休假等的持久戰,於是女同性戀者開始嘗試建立自己獨立的社區——一個個只有女人的、經濟和文化自給自足的“
烏托邦 ”在美國各地紛紛興起,在1970年代末期的高峰期,約數有幾千人居住在這樣的社區里。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精神領袖:薩福繪畫 在北美,宗教社區選擇過獨立、隔絕、自給自足的生活,有幾百年的歷史,在歐洲大陸受到宗教迫害的阿米什人(Amish)就至今在美國各地分散居住,維持著兩百年前的生活習慣、社區結構和宗教儀式。因此,女同性戀分離主義者建立堅持自己信仰、維持自己生活的小社區的構想並不是空穴來風。
事實上,由於她們堅持女性獨立的訴求非常有吸引力,一度說服了很多對女性並無多少
情慾 的女權主義者,從而造成了美國女權主義歷史中的一個頗有趣的現象:“政治女同性戀者”(political lesbian),意即為擺脫無處不在的男權文化而選擇與女性建立親密關係的女性。女權主義理論家
蘇珊·布朗米勒 (Susan Brownmiller)就提到過:“一夜之間就有許多人轉變為女同性戀者,我認識的許多運動家都忽然改變了取向。”
最有影響力的女同性戀分離主義團體之一,“復仇女神”(The Furies)在她們同名刊物的創刊號上寫道:“(女同性戀)並不完全是一個性傾向的問題,而是每一個想要認同為女性、從而終結男性優勢的女性都必須做出的一個政治上的選擇。” 不同的團體政策不同:有的團體拒絕與男性接觸,有的團體拒絕與異性戀女性接觸,但她們都或多或少認為,依舊在主流男權社會中謀求女性平等權利的女性主義運動過於妥協。
這樣的運動理念,帶著當 時美國社會運動(反對越戰、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年輕人對於主流社會的普遍失望與憤怒)深深的印記,雖然隨著美國社會整體的代際轉變,而慢慢從行動中退回到紙面上,但也給之後的思考者與實踐者留下了豐富的借鑑和反思資源。
理論 主要內容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日趨公開、活躍,
女同性戀分離主義 (lesbian separationism) 也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她們提出“
多元 ”(diversity) 口號作為對“
變態 ”(perversity) 這一指責的回應。她們說,“我們已經超越了要求隱私權的階段,甚至超越了開辦女同性戀酒吧、實業和項目的階段,達到了要求開展廣泛的公開討論的階段。”
有的女同性戀者認為她們的文化被女性主義重新解釋了。她們說,“女同性戀是實踐而女性主義是理論”的口號不失為一個好的動員令,但它卻歪曲了我們的歷史。她們批評保守派,認為她們反對和壓制了一切有關性、性別、種族和階級的嚴肅討論。她們認為,性別主義是一切壓迫的根源,而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是對男性霸權的威脅,女同性戀者必須組織起自己的運動以反對男性霸權。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猛烈抨擊男性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和
攻擊性 性行為。她們還認為,
母性 是女性的優點,而不是女性的弱點。她們反對異性戀霸權,即那種以為只有異性戀才屬正常範疇的偏見。
未及宣告的女同性戀+女權主義者瑪麗蓮夢露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可以分為選擇性的與“天生”的,當然關於同性戀傾向到底是先天形成還是後天形成的至今尚無定論。此處所說的選擇性同性戀是指將同性戀生活方式作為一種政治選擇來實踐的女性。關於女同性戀形成原因的理論可以被分為:
生理決定論 ,
社會建構論 和社會政治選擇論。所謂社會政治選擇論這一成因專指那種以選擇女同性戀生活方式作為擺脫異性戀壓迫制度的行為。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有一大批女性確實做出了這樣的選擇。這些政治導向的女同性戀者選擇將自己的生命、愛和精力交付給另一個女人,而不浪費時間經營同男人的關係。認為異性戀女性是與敵共眠。從女同性戀中的三種成分可以看出,
性傾向 的差異是自然的、文化的,有時又是政治的。
核心信念 激進的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認為,之前的女性主義僅停留在理論,而她們是對女性主義理論的實踐。她們認為女性受壓迫的根源是性別主義,認為其她女性主義流派更多的是從理論上尋求女性獲得平等、脫離被壓迫可能,而她們是在踐行,將對男性霸權構成威脅。她們認同婚姻的存在,但反對異性戀霸權,認為女性在婚姻上只有與男性分開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與平等。換言之,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的婚姻思想是,主張婚姻存在,但只是女性之間的婚姻,反對傳統的異性戀形式的婚姻。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將女性的被壓迫狀況歸之於異性戀的
婚姻制度 。她們認為,正是男女間的異性戀導致女人對男人的依附與服從。很顯然,她們分享了
後現代主義 的反二元論劃分的理論資源,認為把性別劃分開來是一種統治關係的根源,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認為真正能夠打破二元劃分的
男權制 的方式是混淆嚴格的性別身份,因此,女同性戀並非如社會上所公認的那樣是一種“異類的病態反常的身份”,而是一種“
被女人自己認同的女人 ”。而且,她們認為,只有建立一種女性間的認同關係才能擺脫男性價值觀對女性的約束,因為,只有女同性戀者才是強大而獨立的,不依附於任何男性的女人。這就是說,只有女同性戀才由內到外都擺脫了男性的控制,她們的創造力能夠得到極大地解放,而不被局限在重複性很強且非常枯燥的家務勞動之中。因此,女同性戀者反對異性婚姻制度,反對異性婚姻制度對女性生活的“設計”,女同性戀主義者夏洛特·本奇(Charlotte Bunch)認為異性愛是“男性霸權的基石”。
在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的影響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產生了著名的“
酷兒理論 ”。“酷兒理論”反對傳統的異性戀婚姻形式,質疑婚姻的必要性。“酷兒理論”不相信傳統的一夫一妻制是人類婚姻狀況的應然秩序,提出創立新型人際關係和新的生活的方式的可能性,從而提出了很多嚴重衝擊傳統婚姻秩序的顛覆性的觀點。她們質問:“為什麼一個社會必須實行一夫一妻制?為什麼不可以有情人?為什麼不可以不結婚?為什麼人只能和一個人發生性關係?為什麼不可以有開放的性關係?為什麼不可以有開放的人際關係?為什麼非要孩子不可?等等。”不僅如此,“酷兒理論”的提法並非只是停留在理論的宣講的層而之上,它還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很多青年亞文化運動所踐行的實際行為的總結。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突出了女同性戀這一女性
亞文化 在女性中的特殊之點,其關注點是女性主義運動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有注意到的問題。而且,通過對女同性戀自身特點的強調尋找到一種沒有壓迫的性別關係作為對男權制
家長制 的替代。
運動 各個政治運動和理論之間既有交叉又有衝突,而女性主義和同性戀運動內部也充滿了
多元 性、爭議與矛盾;女同性戀及其研究、運動和理論,與這些紛繁複雜的理論和運動,從1970年代至今,一直在不斷的結盟、借鑑、批判中,形成了複雜而充滿活力的關係。
面對著社會各個領域對於女性的壓迫與歧視,女性主義不僅僅追求和堅持女性的平等權利,更是一種批判的立場和視角。批判,並非簡單的拒斥,而是一種尋求理解和判斷的理論態度;女性主義批判,試圖理解社會各個領域的傳統、習慣、規定、法律、語言、社會角色等各方面可能蘊含的基於性別的壓迫、歧視、刻板印象等,並在此理解的過程中,發現它們所依賴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從而尋求可能的改進方向。
從這個角度來說,女性主義的立場幾乎內在的包括了女同性戀作為政治群體的訴求:對於社會“主流價值”的追問與懷疑,對於性別身份的關注和對於女性體驗的探討,對於壓迫和邊緣化的敏感和反對等等。女同性戀理論學者戴納·海勒(Dana Heller)就此寫道:“女性主義給了我審視‘傳統’的理論工具。女性主義向我揭示了西方思維傳統中的抽象論述對於女性、酷兒、少數群體的忽視,以及對此傳統的抵抗。女性主義教會我讚賞矛盾性和與矛盾性共存的必要。”
分裂 女同性戀與女性主義這樣自然的親近關係,使得“比利提斯的女兒”(Daughters of Bilitis,美國早期重要的女同性戀組織)的創始人之一戴爾·馬丁(Del Martin) ,在1970年撰文聲明與同性戀運動分道揚鑣,而擁抱與女性主義理論和運動的結盟。
馬丁指責當時的同性戀平權運動由男性及男性的“兄弟情誼”(brotherhood)為主導,十五年來都在忽視和排斥女性的訴求,而她們在同性戀運動社群中找不到的“接受、平等、
愛 與
友誼 ”,正可以在女性主義運動中找到。(Martin 1970) 馬丁的聲明代表了一群在同性戀運動中發現自己被忽視和噤聲的失望的女同性戀者,她們在女權主義中找到了同盟,因為女性主義恰恰強調女性在整個
社會環境 中的被忽視和噤聲的地位;在女性主義陣營里,不同性傾向的女性可以共同反對對於女性的壓迫,尋求女性的獨立自主與政治聲音。
不僅女同性戀者可以從女性主義理論和運動中汲取力量、借鑑資源和尋求同盟,後者也從前者獲益良多。女同性戀者在西方歷史上的
邊緣化 和沉默,成為了她們最有力的理論創新的來源;女同性戀理論研究的興起,為女權主義理論帶來了更加豐富的視角和批判。
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是
女同性戀 作家、詩人
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 對於“強制性異性戀”(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的批判。里奇認為,在當代社會中,女性的社會化不可避免地基於異性戀的模式,即女性所受的教育和社會影響告訴她們,她們的性別身份(例如女性意味著美麗的外表和溫柔的態度等),和
社會角色 (妻子、母親、
情人 等),都是基於與男性的異性戀關係,而這樣的模式使得女性既背離了真實的自我,又與其他女性形成競爭關係。為了使女性能夠自由發展自己的人格與才能,免於受到壓迫性的社會要求,與其他女性相互認同,而不是爭奪男性的認可,女性應該致力於創造以女性為主的空間和文化。異性戀本身並不一定對於女性構成問題,但是從社會層面上來說,異性戀的絕對主導地位和“所有人都是異性戀”的預設、以及異性戀者因符合社會要求而享受到的特權,不僅會使得同性戀女性被邊緣化和從社會圖景中被抹去,更會促進對於性別形象和角色的
刻板印象 ,從而使所有女性的自由發展受到限制。(Rich 1980)
與里奇一樣,越來越多的女性主義理論寫作強調作者的女同性戀視角,通過對於異性戀模式、
性別角色 、
社會規範 、
性表達 和
性行為 模式的梳理、懷疑、反思和批判,使得女性主義理論和運動的層次更加豐富,角度更加多樣,批判更加深入。
解構 然而,這個極具活力的結盟卻不是一個簡單的玫瑰色圖景;相反,自從1970年代中期女同性戀研究和論述大量興起和融入女性主義寫作之時,相關的爭議就從未間斷。 女同性戀力量被一些人擁贊為女性主義運動的先鋒,又被另一些人認為是運動最大的可疑力量;一部分女性主義者為克服社會文化中普遍的“女性主義者都是同性戀”的偏見,而疏遠女同性戀的力量;一部分女性主義者因為反對女性在男權文化中被
物化 、僅僅被視為性對象,而反對色情製品,尤其是具有
虐戀 、
戀物 或控制幻想的色情製品,而這又引起了一部分主張女性情慾、尤其是女性之間情慾的自由表達的女同性戀者的不滿;一些女同性戀者對於“男性氣質”的戲仿、重視或追求,對於“
女性氣質 ”的不屑、遠離甚或壓制,使得一些女性主義者(尤其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指責女同性戀亞文化強調
本質主義 (在
社會性別 和性表達問題上,強調先天與內在因素,常被認為與強調建構、選擇和可能性的建構論相對立)與二元對立(陽剛氣質與陰柔氣質,同性戀與異性戀等非此即彼的範疇)。
這裡所舉的例子只是一些相對持久和激烈的爭議,而女同性戀和女性主義之間關係的複雜性已在此可見一斑。總而言之,正是因為女同性戀和女性主義的社群、運動及理論都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各自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訴求,充滿了多元性與矛盾,又在連結中因為各個處境和議題的特殊性而充滿交叉、重合與碰撞,因此她們的結盟不會一帆風順,卻也可能因此更具創造性和生命力。
一個瑞典研究小組經對志願者測試發現,同性戀女性的大腦對
性激素 的反應與異性戀女性不同。據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2006年5月9日報導,這個研究小組對3組女性志願者進行了測試。研究人員在給這些志願者嗅雌性和雄性激素以及4種普通氣味後,對她們的大腦進行了掃描。掃描結果發現,這些志願者在嗅了普通氣味後,大腦的嗅覺區域都產生了相同的反應。但女同性戀者和正常女性大腦對性激素的反應卻不相同。
輿論 著作 一般認為,女同性戀比男同性戀更寬泛模糊,更不易捉摸、不願言說。1928年,英國女作家拉德克利芙·霍爾發表了表現女同性戀生活的小說《孤獨的井》,“企圖表現關於婦女對婦女的愛的真相”,引起軒然大波,被認為是本世紀最早呈示女同性戀的婦女文學。但將女同性戀作為一種文學批評的
主要內容 或
價值尺度 來張揚,則是女性主義運動催生的。它首先產生於美國,與勃興於60年代初的“新
女權運動 ”同步,這個運動號召婦女直接在
核心家庭 的堡壘內與男人對抗,堅持認為婦女是自己身體的絕對權威,有權對是否生育等問題作出選擇。
在美國,50年代末便萌生了女同性戀文學批評,如珍妮特·福斯特的《不同性愛的婦女》(1956)及吉恩·戴蒙等人的《文學中的女同性戀:一個目錄》(1967),都表現出明顯的女同性戀意識。可直到70年代末,
女權主義批評 的重要刊物《符號》和《邊陲》上才出現以女同性戀為中心的論文。
這些文章指出,女性主義批評早期的許多重要論著,如埃倫·莫里斯的《文學婦女》、帕·斯帕克斯的《女性想像力》、伊·肖瓦爾特的《
她們自己的文學 》以及吉爾伯特和格巴的《閣樓里的瘋女人》等,都沒有提到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批評,因而與
男性中心主義 一樣,是一種
極權主義 。從1974年起,芝加哥現代語言協會和女同性戀作家聯合會便每年舉行專題討論會,建立了女同性戀批評家、教師和學者的網路,一些女同性戀批評家還公布了通訊錄,建立了諮詢站,搞得好不熱鬧。1975年,珍妮·魯爾在《女同性戀形象》一書中較早地勾勒了一個女同性戀文學傳統,將許多女作家都納入了女同性戀文學範疇。1976年,著名詩人艾德里安娜·里奇發表了女同性戀詩作《二十一首愛情詩》和女同性戀論文《這便是我們的女同性戀》,產生了廣泛影響。
為了將女同性戀主義與同性戀或男同性戀(male homosexu-ality)區別開來,一些批評家作了耐心的闡發。她們宣稱,女同性戀不同於男同性戀,像男同性戀中的匿名性行為的盛行、對男性戀者
雞姦 的辯護、男同性戀中性吸引標準對老年人的排斥等,在女同性戀中是絕少見的,女同性戀是反抗男性中心主義的一種行為,不僅僅是一種“
性選擇 ”或“另一種生活方式”,它還是一種對傳統秩序的根本批判,是婦女的一種
組織原則 ,一種試圖創造一個分享共同思想環境的表現,是女性在同類中尋找中心的嘗試。有人求助於失落了的
母權制 黃金時代,有人大談女同性戀始祖薩福,有人在
愛米莉·狄金森 的詩作中尋找女同性戀意象,有人在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 、多羅茜·理查森、
維吉尼亞·伍爾芙 的傳記及作品中尋找女同性戀傾向,以此證明女同性戀文學的恢弘傳統。
宣言 70年代末,一群生活在利茲的女同性戀者,即我們所知道的女性主義解放者(簡稱PFs),發起了一項爭議極大的運動,這在我和很多其它女性中引發了很大的反響。她們呼籲所有的女性主義者包容女同,號召他們的異性戀姐妹把男人“從自己的床上和思想中”驅趕出去。”她們發起辯論,在最高潮的時期——1981年,出版了一本臭名昭著的小冊子《愛你的敵人?——異性戀女性主義和政治女同性戀之爭》 (簡稱LYE) 。在這本書中,PRs寫到:“所有的女性主義者可以而且應當是女同。我們對政治女同的定義是,一個不和男人上床的自我女性身份得到確定的女人。這並不意味著你必須要和女人發生性關係。”
LYE所傳達的信息很快激起了強烈反應,而這其中多有的是負面回應。儘管有一些激進的女性主義者贊同她們的理論,但大多數人從中得知和男人上床“有違革命意志”,而且對女性解放運動不利,她們都幾乎要抓狂了。LYE的主要作者希拉·傑弗里斯(Sheila Jeffreys) 說道,這本冊子所引發的迴響,即便是在女同群體中,都是十分強烈的。很多人對此大為光火。她們感到這本冊子讓自己站在了異性戀女性主義者的對立面。
這本冊子引發如此之多的爭議,本是意料中的事情。“我們認為嚴肅的女性主義者除了放棄自己的異性戀立場外別無選擇,” 書中寫道。“壓迫者只有在男性至上的體制中才能夠進攻並且奴役受壓迫者的身心。”它還強調,“男性的插入動作不僅僅是一個符號,它的功能和效果就是懲罰、控制女性。”
RFs成員蒂娜·克羅克特(Tina Crockett) 和其他人一起在約克郡的度假村里創作了這本冊子。她說,書中除了關於異性戀女性能夠選擇成為女同性戀這一觀點引發了廣泛爭議,另一個把男性當做敵人看待的觀點也十分顯眼。“我們試著推翻異性戀女性主義者和‘Niger、John’們同居的藉口。” 她說,“她們覺得,‘噢,但是我的男人還可以,’這樣就不用去審視為什麼有些男人確實仇恨女人這個問題。”
艾莉森·蓋斯維特(Alison Garthwaite) 是作者之一,她支持這一原創性的概念。
“ 性取向 並不是由基因決定的,這不是生來就確定了的,” 她說到。
“它可以隨著時間發生變化,決定因素包括環境,另外還有你自身做出的抉擇。” 但Garthwaite迫切希望異性戀女性主義者能夠理解,她們在女性主義陣營中的角色並不是可有可無或者被排斥的。
“也許書中暗示過異性戀女性主義者作用不大,她們並不被需求。但我的觀點不是這樣的。” Crockett和Garthwaite兩個人都知道LYE引發不滿的原因。“LYE所爭論的問題好比是將一枚炸彈,”Crockett說到,“投入到傳統女性主義中——即異性戀女性主義決不能因為她們選擇了異性而非同性受到指責。”
LYE的發行首次將性取向作為可選擇的概念置於英國女性運動的公共領域。很多女性主義者認為性取向只是一個純粹的私人問題,而將同性戀提高到政治決策的高度是一個非常“殘酷”的問題。“人們覺得性取向和性偏好不是個人所能左右的,而是個體是受控的,”Jeffreys說到。“人們可以接受或者與之抗爭,但卻不能操控它們。”
女性主義作家Bea Campbell是LYE的另一位作者,她認為比起讓整個女性群體放棄希望,挑戰男性的行為顯得更加重要。“政治女同性戀這個概念太瘋狂了,”她說到。“它抹殺了需求,因此可以說這並不是出於對女性的熱愛,而是因為畏懼異性。”學者Lynne Segal是一位支持異性戀的女性主義評論家。“對我個人而言,在70初加入到女性主義運動時,‘政治女同性戀’只是一小部分前衛女性所持有的立場,”她說到。“這是一種悲劇立場,因為答案是否定的,並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敵人。”她還提到LYE曾為媒體利用,在大眾中對女性主義進行貶低。“這無疑讓我們感到十分地難堪,不管是當時還是那以後的歲月里。”
儘管有很多人對此表現了不滿,但還是有一些女性認真地對待LYE所討論的問題。當70年代的女性仍然被貶低、被排斥的時候(恰巧在昨天,小報《太陽報》還用“蕾絲邊”蔑稱愛爾蘭當選的過渡政府總理),這本冊子用了十分光彩的篇章描敘了女同性戀,這的確顯得與眾不同。一些女性記錄如下的言論後便將她們的男朋友和老公甩到一邊去了:“異性戀女性主義者就好比,有這樣一些人,在抵抗攻占歐洲的納粹時白天炸橋,到晚上又去修橋。”
而另外一些人,包括我在內,認為LYE的言論直接命中了我們發展中的一些認知。反對政治女同性戀的人相信驅動“真正的”女同性戀者的因素是她們對女性的渴望,而不是出於對異性和異性戀的牴觸。但是於我而言,我的女同性戀傾向是在女性主義政治以及參與抵抗性別暴力的運動中發展起來的。
當我在達林頓的房舍里成長的時候,我所預見的是某日和住在這裡的某個男孩結婚安家生子。說實話,這種想法令我感到恐懼。我的身邊全部都是男人——他們是我的爸爸和兩個兄弟,在幼年時我就從社區的傳聞中聽到了關於家庭暴力和虐待兒童等林林總總的不愉快的話題。另外讓我感到不安的是女人要做各種各樣的家務。當男人在外面花天酒地,計畫著釣魚出遊,享受自己的自由時,女人卻要忙著給他們做飯,洗衣服,圍著孩子團團轉。對女人來說,異性關係是個天大的謊言。
我曾經不那么當回事地談過一個男朋友,接著15歲時,我變成了一個女同。三年後,我去了利茲,為了尋找傳說中十分了不起的女同性主義者們,並且加入了一個反色情的組織,最終,我遇到了RFs。她們在聚會時邀請我加入異性關係的討論,她們譴責這一主流的性別文化,我覺得這十分在理——最起碼我還沒有遇到過一個從中獲益的女人。RFs告訴我,對這些女人而言同性戀是一個選擇,而同性戀並不是我們應當在出生時所必備的“條件”。“所有的女人都有成為同性戀的可能”,這就是她們的箴言。我喜歡這種感覺,我自己選擇了我的性取向,和那些因此而感到羞恥或者內疚的女人相比,我能夠感到驕傲,並且認為這是一種特權。
許多在七八十年代參與了政治女同性戀運動的人直到今天仍然堅守她們的信念。對Jeffreys而言,30年前LYE中曾經探討過的問題直到今天仍然有它們的實際效用。“我們身為女同性戀者,就要為我們所熱愛的女性群體而奮鬥,這是我們生活的中心,對我來說它仍然是。如果我終生都在為解放女性而奮鬥,到最後卻要回到一個男人的家中去,這將令一切變得毫無意義。”Crockett表示她支持這本書的主旨,但同時希望她們不要只強調異性關係的消極面。“我們應當這樣說,‘來吧,水溫正合適,’因為身為一個同性戀的確是充滿了樂趣。”
對我來說,政治女同性戀主義仍將繼續成為一種內在的動力,它加強了這樣一種觀點——即性取向是一種選擇,我們的命運不應該被染色體所左右。而我也懷疑,你白天去反抗男性暴力只為了晚上能和男人睡一張床——這是很難成功的一件事。另外還有一個事實是,和女性一起為了某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這會使你們彼此建立起穩固的情感聯繫——可為什麼又有一些女性主義者卻排斥和她們的政治姊妹們建立性關係,轉而在夜幕下投入了男人的懷抱,這一點我實在不能理解。
我認為我們應當重新開始探討異性關係,並且包容政治女同性戀思想。我們所生活的環境中,每天都上演著女性被強姦卻受到指責,就好比是異性關係中無法改變的一個特徵。家庭暴力仍是許多和男人一起生活的女性所長期面臨的問題。女人被告知,我們必須愛壓迫我們的男人;然而女性主義者卻在奮鬥,為終止他們自認為是上天賦予的欺侮權。姐妹們,你們知道這是言之有理的論證。請停止你們的錯誤看法,將女同看作是一個排外的團體,請加入到我們的運動中來。
代表人物 阿德里安·里奇 (Adrienne Rich):女同性戀連續體。1980年文章《強迫性異性戀與女同性戀的存在》(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為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的重要經典。其重要主張“女同性戀連續體”:包含所有認同女人的女人,其認同方式從情感、性慾到政治無所不包,對里奇而言,所有的女人都可以是女同性戀。
奧德瑞·洛德(Audre Lorde): 情慾小黃球。慣以“圈外姊妹”(sister outside)自居,以凸顯其身具女人、黑人、女同性戀的多重邊緣身份位置。重要主張“情慾小黃球”。洛德對女性主義之貢獻,不僅在於凸顯差異政治之迫在眉睫,更在於以己身女同性戀的性愛經驗為出發所倡導的情慾革命觀。在《情慾的利用:情慾及力量》(Uses of the Erotic: the erotic as power)一文中,他企圖區分女人自主的“情慾”(the erotic)與男人定義下的色情之不同,前者涵蘊性愛、生理、情感、心靈與智識的內在生命能量與創造力,後者則是將一切化約為性交與感官刺激而無情感與力量可言。因此洛德視情慾為女人的能量、欲望與創造力的原動力,並將其比喻為小黃球。
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 異性戀思維與性範疇。為當代法國女同性戀小說創作者與理論家,他的小說充滿文體與性慾的實驗,常被喻為“陰性書寫”的代表。他的理論文字則是在後結構論述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將女同性戀標舉為打破異性戀機制中男女二元對立的主要動力。重要發表,1980年《異性戀思維》(The Straight Mind),主要主張“異性戀思維與性範疇”。認為唯有全面摧毀獨裁宰制的“性範疇”,才能開放自由思考的空間。
蓋爾.盧賓(Gayle Rubin): 女同性戀S╱M與性階級。為美國女性主義文化人類學者與女同性戀理論家,1975年以《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經濟學初探》(The Traffic in Women—Not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of Sex)一文聞名,提出“性、性別系統”的概念,指呈文化以男女生理之別以區隔掌控社會之別,而後更以1984年的《論性:性慾取向政治的基進理論筆記》(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直接切入80年代初女性主義陣營中的“性論戰”。提出“情慾少數”的口號,企圖囊括所有被異性戀婚姻、一夫一妻、陽具掛帥,生殖中心排拒在外的各種性慾樣態,如同性戀、易服者、變性人,S╱M等。
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lter): T與婆的性別嘲諷。1990年著作
《 性別麻煩 》(Gender Trouble) ,標示了同性戀研究的一個新里程碑,該書成功的顛覆了傳統女性主義“生理性別、社會性別”的劃分。巴特勒特別提出《
性別表演 》(gender performativity)的概念,強調性別不是可揮灑自如的角色轉換,也非可脫下換上的服裝表演,而是異性戀機制下
“強制而又強迫的重覆” 。巴特勒的理論不僅強調性別本身的社會建構,也同時凸顯任何身份認同的不穩定性。
影響發展 地位影響 在其發展初期,
同性戀文化 從女性主義汲取了大量的理論養分。例如,女同性戀者利用女性主義的“反
本質論 ”(anti-essen tialism)揭示異性戀為確立並維護他們的統治地位如何構造性正常/性變態的
二元對立 。正是基於此,
在一段時間內同性戀文化被冠以“女同性戀女性主義” (lesbian feminism)之名,而且“在女性主義者發掘和發展女性文化的活動中,大部分積極分子是女同性戀者”。成為女同性戀,完全擺脫父權社會,因為“對於很多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來說,脫離父權社會是最終的政治行為”。雖然最終女同性戀者與女性主義者分道揚鑣,但前者與後者在文化和理論上的淵源關係仍然清晰可見。
前景藍圖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的婚姻思想對婚姻思想以及
婚姻形式 產生的影響。如果說婚姻權利是人類自由的一項選擇權,那么婚姻的必要與否和婚姻形式對個體來講是可以多方而選擇的。婚姻的存在與否、以及婚姻形式、
婚姻制度 的變化在不斷爭辯中得以加強或是了有力反駁。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認為異性戀婚姻是對女性的壓迫,這對於婚姻中女性如何才能全而獲得與男性平等的權利與地位、人類婚姻形式是否只能是異性戀婚姻等問題均給出了另一個視角。隨著這些問題的深入,婚姻制度與婚姻形式都發生了變化。同性戀,包括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從隱秘逐步被社會所知。甚至在西方一些國家,法律允許同性戀結婚,同性戀合法化。
這可以視為女同性戀女性主義對傳統婚姻主體與形式顛覆性的結果 。世界是多樣性的共同存在,婚姻與愛情到底天生就是男女之間關係,還是人與人間的一種關係。這個問題的答案的多樣性,勢必造成婚姻思想及形式的多樣化。
積極作用 1988年,美國通過了新的地方政府法案,其中第28條款竟然還有這樣的規定:禁止“提倡同性戀和假家庭關係”,禁止“在學校接受同性戀的教育”。這是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所面臨的社會現實,證明同性戀權利運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世紀90年代,酷兒理論橫空出世,它是一種全新的性話語。而酷兒政治可被追溯到60年代和70年代。酷兒不是一種固定的身份,而是一種身份批判的過程。在酷兒理論中,身份形成和身份政治是中心論題。酷兒一詞被用來指稱這樣幾種人:第一,同性戀;第二,對某人有感情;第三,拒絕接受傳統的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分類的人,挑戰的欲望超越了異性戀規則。
女同性戀研究擺脫了男同性戀研究發展為酷兒理論研究和女性主義的研究。酷兒的視線一反70年代和80年代求人接納的正面描述同性戀的姿態,故意去探索變態,觀照性慾的“下腹部”,探察同性戀關係中的
暴力 、
嫉妒 、
不平等關係 、
占有 與
背叛 。在90年代做一個酷兒,就是“對你自己的性和你的政治保持熱情”,而採取一種“現身”的策略或生活方式,對主流的趣味和敏感採取不屑一顧的不讓步的態度,將快樂視為真正自我的一種表達。
爭論焦點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所關注的爭論焦點包括:
性活動:是任何形式都可以還是應當反對性活動中的權力關係,如虐戀關係。
傾向的選擇:是天生的還是選擇的,要做一個女性主義者是否一定要先做一個女同性戀者。
恐懼症:許多女同性戀被診斷為“內化她們的同性戀恐懼症”,把社會歧視說成心理疾病。
結婚與否:異性戀占有性、愛、婚姻、家庭之權利,女同性戀應當爭取同性婚姻。
雙體制還是單體制:異性戀與男權制是一個體制的兩面,還是各自獨立存在的兩種制度。
女同性戀母親:撫養孩子的家庭環境缺乏刻板的性別示範問題。
女同性戀的不可見性:無論在異性戀霸權的社會還是在同性戀世界中,女同性戀都面臨邊緣化的問題。
女同性戀被視為女性男性化:異性戀的男女兩分思維以及異性戀與同性戀的兩分思維總要將女同性戀關係中的角色比附於異性戀關係中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不能夠接受性別模糊或混淆的狀態。因此,女同性戀往往被視為女性的男性化,而不被當作正常女性看待。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組織“復仇女神”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組織“復仇女神” 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
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精神領袖:薩福繪畫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精神領袖:薩福繪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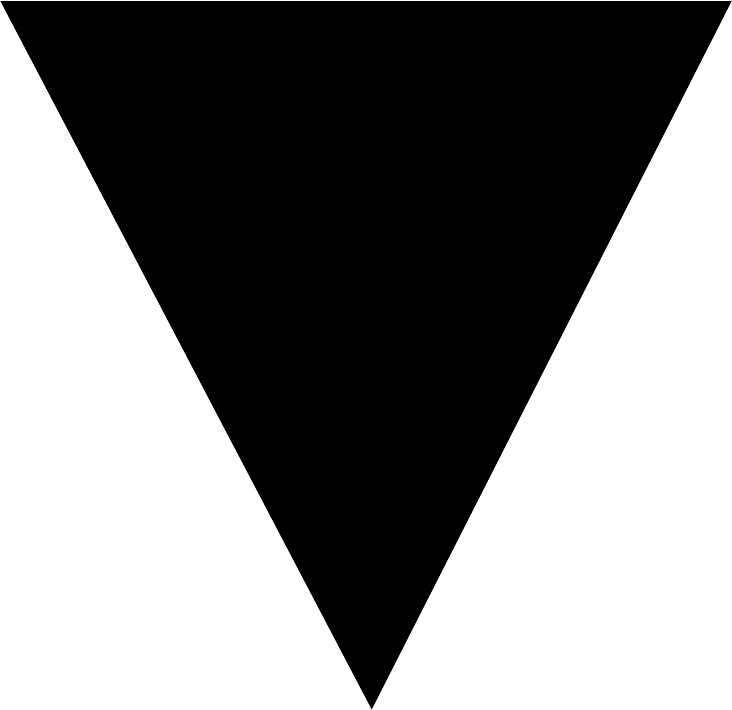
 未及宣告的女同性戀+女權主義者瑪麗蓮夢露
未及宣告的女同性戀+女權主義者瑪麗蓮夢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