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劉述先,江西吉安人,1934年生於上海。其父劉靜窗畢業於西南聯大,與
熊十力相熟。劉述先求學期間受
方東美,以及熊十力弟子
唐君毅、
牟宗三、
徐復觀等
新儒家影響頗深。他先後獲得台灣大學哲學系文學士、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哲學博士等學位。研究領域為儒家哲學,特別是宋明理學、文化哲學、比較哲學,曾任教於
台灣東海大學、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哲學系、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台灣“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特聘講座(1999年-)
 劉述先教授
劉述先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1996年-1999年)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至1993年止〕(1981年-1999年)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哲學系正教授(1974年-1981年)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哲學系副教授(1970年-1974年)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助教授(1966年-1970年)
2016年6月6日晨,當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劉述先逝世,享年82歲。
獲獎記錄
Phi Kappa Phi Honors Society, inducted in 1966.
《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台北學生書局,
金鼎獎,1982。
Honorary Member, The club of Budapest, inducted in 1998.
人物著作
《文學欣賞的靈魂》、《語意學與真理》、《新時代哲學的信念與方法》、《文化哲學的試探》、《生命情調的抉擇》、《中國哲學與現代化》、《馬爾勞與中國》、《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文化與哲學的探索》、《黃宗羲心學的定位》、《中西哲學論文集》、《大陸與海外—傳統的反省與轉化》、《儒家思想與現代化》,編有《熊十力與劉靜窗論學書簡》、《
儒家倫理研討會論文集》等書。 譯作:有卡西勒《論人》等現代西方哲學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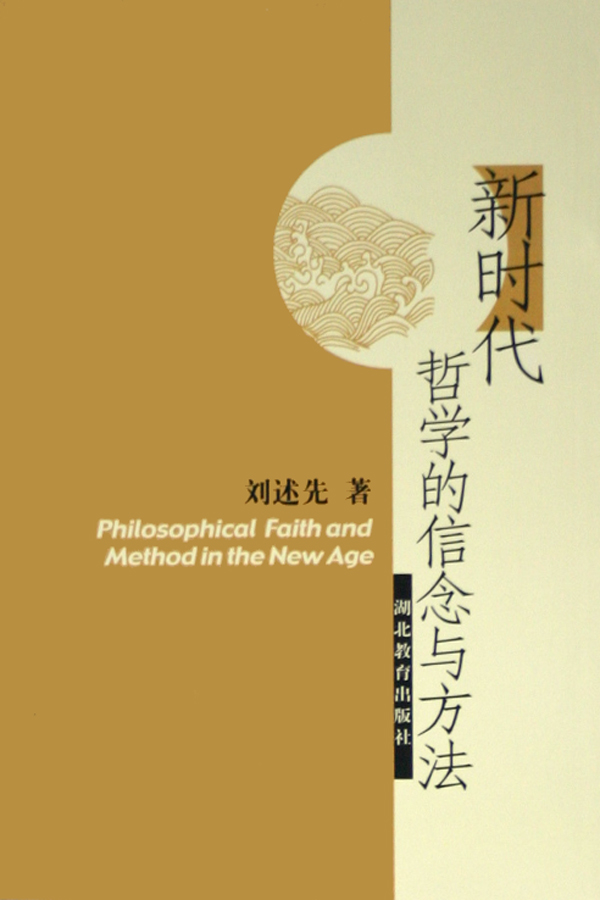 著作
著作學術貢獻
綜述
劉述先先生是學貫中西的學者、著名
哲學家與哲學史家,是在國際哲學界頗有影響與活力的開放型的當代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專長是西方文化哲學、宗教哲學與中國儒學,尤其是宋明理學,以及中西比較哲學、比較宗教學。他有著深厚的中西哲學的底蘊與修養,以發掘儒家思想的現代意涵為職責,努力促進傳統中國哲學的創造性轉化。劉先生主要是一位講堂教授與書齋學者,做純學術研究,但他也以極大的熱誠反省現代化與“全球化”帶來的諸多問題,積極參與並推動全球倫理的建設與世界各宗教間的對話,在反思、參與和對話中代表中國人與中國文化,貢獻出
華夏民族獨特的智慧、理念與精神。劉先生是一位極有涵養的忠厚長者,寬容、儒雅,但他偶爾也因不得已與人辯論,打筆仗,所辯均關乎儒學思想資源的理解與闡發。劉先生不迴避理論爭鳴與當代新儒家所面臨的挑戰。
推進並豐富了“內在——超越”學說
劉先生的創見和貢獻尤多,以我的膚淺理解,最重要的是,他推進並豐富了“內在——超越”學說,創造性地詮釋“理一分殊”,積極倡導“兩行之理”,發揮發展了儒學“仁”、“生生”與“理”之旨。劉先生的精神成果對儒家學說乃至中國傳統精神的世界化、現代化作出了貢獻。
 劉述先
劉述先現代
神學家與宗教學家認為,上帝可以死亡,但宗教意義的問題不會死亡。對於“他世”的祈向並不是宗教的必要條件,對於“超越”的祈向乃是任何真實宗教不可缺少的要素,對現世精神的注重未必一定違反宗教超越的祈向。劉述先先生從這一視域出發,判定孔子並不缺乏深刻的宗教情懷,中國傳統對於“超越”的祈向有它自己的獨特的方式。由孔子反對流俗宗教向鬼神祈福的態度,並不能夠推出孔子主張一種寡頭的人文主義的思想。孔子保留了傳統人格神信仰的遺蹟,對超越的天始終存有極高的敬意。孔子思想中“聖”與“天”的密切關聯及孔子對祭祀的虔誠態度,表明孔子從未懷疑過超越的天的存在,從未把人事隔絕於天。但孔子強調天道之默運,實現天道有賴於人的努力,人事與天道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這與當代西方神學思想所謂上帝(天道)與人之間的夥伴關係相類似。人自覺承擔起弘道的責任,在天人之際扮演了一個樞紐性的角色。但這與西方無神論不同,沒有與
宗教信仰完全決裂。孔子所提倡的儒家思想兼顧天人的一貫之道,一方面把聖王之道往下去套用,另一方面反身向上去探求超越的根源。
劉先生認為,進入現代,面臨科技與商業文明的挑戰,儒耶兩大傳統所面臨的共同危機是“超越”的失墜與意義的失落。新時代的宗教需要尋找新的方式來傳達“超越”的信息。就現代神學思潮企圖消解神化,採用象徵語言進路,重視經驗與過程,並日益“俗世化”,由他世性格轉變為現世性格來說,儒耶二者的距離明顯縮短。儒家本來就缺少神化的傳統,至聖先師孔子始終只有人格,不具備神格,
陰陽五行一類的宇宙觀是漢儒後來附益上去的,比較容易解構。中國
語言對於道體的表述本就是使用象徵語言的手法。中國從來缺少超世與現世的二元分裂,儒家自古就是現世品格。儒家有一個更注重實踐與實存的體證的傳統。面對現代化挑戰,在現代多元文化架構下,宗教傳統必須與時推移作出相應的變化,才能打動現代人的心弦,解決現代人的問題,既落實在人間,又保住超越的層面,使人們保持內心的宗教信仰與終極關懷。在這些方面,儒教比
基督教反有著一定的優勢,有豐富的睿智與資源可以運用。
提出“超越內在兩行兼顧”的理論
劉先生髮展“超越內在”說,充分重視二者的張力,提出“超越內在兩行兼顧”的理論。他詳細梳理了儒、釋、道三家關於“超越”與“內在”及其關係的理論。關於儒家,他指出,儒家有超越的一面,“天”是孔子的超越嚮往,《論語》所展示的是一種既內在而又超越的形態。劉先生指出,
孟子從不否認人在現實上為惡,孟子只認定人為善是有心性的根據,而根本的超越根源則在天。我們能夠知天,也正因為我們發揮了心性稟賦的良知和良能。孟子雖傾向在“內在”一方面,但孟子論道德、政事同樣有一個不可磨滅的“超越”的背景,由此發展出一套超越的性論。只不過儒家把握超越的方式與基督教完全不同:基督教一定要把宗教的活動與俗世的活動分開,儒家卻認為俗世的活動就充滿了神聖性;基督教要仰仗對於基督的信仰、通過他力才能夠得到救贖,儒家的聖人則只是以身教來形成一種啟發,令人通過自力就可以找到自我的實現。既然民之秉彝有法有則,自然不難理解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的境界;而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中庸》講人與天地參,與孟子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劉先生認為,孟子與孔子一樣清楚地了解人的有限性,接受“命”的觀念,但強調人必須把握自己的“正命”。如此一方面我們盡心、知性、知天,對於天並不是完全缺乏了解;另一方面,天意仍不可測,士君子雖有所擔負,仍不能不心存謙卑,只有盡我們的努力,等候命運的降臨。
劉先生指出,由孟子始,儒家認為仁心的擴充是無封限的,這一點與蒂利希之肯定人的生命有一不斷自我超越的構造若合符節。儒家這一路的思想到王陽明的《大學問》,發揮得淋漓盡致。大人的終極關懷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不能局限在形骸之私和家、國等有限的東西上。在陽明那裡,人對於無限的祈向實根植於吾人的本心本性,良知的發用與《中庸》所謂“
天命之謂性”的本質性的關連是不可以互相割裂的。儒家沒有在現世與他世之間劃下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所體現的是一既內在又超越之旨。由這一條線索追溯下去,乃可以通過既尊重內在又尊重超越的兩行之理的體證,而找到安身立命之道。劉先生肯定“仁”是既超越又內在的道,同時強調即使是在孟子至陽明的思想中,天與人之間也是有差距的,並非過分著重講天人的感通。孟子既說形色天性,又說盡心、知性、知天,可見通過踐行、知性一類的途徑,就可以上達於天。這是典型的中國式的內在的超越的思想,無須離開日用常行去找宗教信仰的安慰。但有限之通於無限不可以滑轉成為了取消有限無限之間的差距。儒家思想中‘“命”’的觀念正是凸出了生命的有限性,具體的生命之中常常有太多的無奈不是人力可以轉移的。人的生命的終極來源是來自天,但既生而為人就有了氣質的限定而有了命限,然而人還是可以就自己的秉賦發揮自己的創造性,自覺以天為楷模,即所謂“正命”、“立命”。天道是一“生生不已”之道,這一生道之內在於人即為人道。儒家“生生”之說體現的是個體與天地的融合。劉先生認為,自中國的傳統看,宇宙間的創造乃是一個辯證的歷程。創造要落實則必具形,有形就有限制。宋儒分疏“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
後者講的是創造過程落實到具體人的結果,說明人的創造受到形器的、個體生命的、外在條件的制約。但“氣質之性”只有返回到創造的根源,才能夠體現到“天地之性”的存在。只有體證到性分內的“生生之仁”,才能由有限通於無限。儒家強調,吾人接受與生俱來的種種現實上的限制,但又不委之於命,不把眼光局限在現實利害上,努力發揮自己的創造性,不計成敗,知其不可而為之,支撐的力量來自自我對於道的終極託付。如此,超越與內在、無限與有限、天與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道與器,都是有差別有張力的,兩者的統一不是絕對的同一。劉先生認為,只顧超越而不顧內在,未免有體而無用。而超越的理想要具體落實,就不能不經歷一個“坎陷”的歷程,由無限的嚮往回歸到當下的肯定。而良知的坎陷乃不能不與見聞發生本質性的關連。超越與內在的兩行兼顧,使我有雙重的認同:我既認同於超越的道,也認同於當下的我。我是有限的,道是無限的。道的創造結穴於我,而我的創造使我復歸於道的無窮。是在超越到內在、內在到超越的迴環之中,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
重新解釋“理一分殊”
再次,劉先生強調超越理境的具體落實,重新解釋“理一分殊”,以示儒家宗教
哲學的現代性與開放性。他認為,超越境界是無限,是“理一”,然其具體實現必通過致曲的過程。後者即是有限,是“內在”,是“分殊”。“理一”與“分殊”不可以直接打上等號,不可以偏愛一方,而是必須兼顧“兩行”。兼顧“理一”與“分殊”兩行,才合乎道的流行的妙諦。
劉先生重新詮釋“理一分殊”有三方面的意義:第一,避免執著於具體時空條件下的分殊,陷入教條僵化。他指出,超越的理雖有一個指向,但不可聽任其僵化固著。例如當代人沒有理由放棄他們對於“仁”、“生”、“理”的終極關懷,但必須放棄傳統天人感應的思想模式、中世紀的宇宙觀、儒家價值在漢代被形式化的“三綱”及專制、父權、男權等。把有限的分殊無限上綱就會產生僵固的效果,以至於徒具形式,失去精神,甚至墮落成為違反人性的吃人禮教。如果能夠貫徹理一分殊的精神,就會明白一元與多元並不必然矛盾衝突。到了現代,我們有必要放棄傳統一元化的架構。今天我們不可能像傳統那樣講由天地君親師一貫而下的道統;終極的關懷變成了個人的宗教信仰的實存的選擇。這有助於批判傳統的限制,揚棄傳統的負面,打破傳統的窠臼。第二,鼓勵超越理想的落實,接通傳統與現代。
劉先生指出,今日我們所面臨的時勢已完全不同於孔孟所面臨的時勢,同時我們也了解,理想與事實之間有巨大的差距。我們要在現時代找到生命發展的多重可能性,採取間接曲折的方式,擴大生命的領域,容許乃至鼓勵人們去追求對於生、仁、理的間接曲折的表現方式,這樣才能更進一步使得生生不已的天道實現於人間。如此,以更新穎、更豐富的現代方式體現傳統的理念。超越境界(理一),好比“廓然而大公”、“寂然不動”、“至誠無息”;具體實現的過程(分殊),好比“物來而順應”、“感而遂通”、“致曲”(形、著、明、動、變、化)。生生不已的天道要表現它的創造的力量,就必須具現在特殊的材質以內而有它的局限性。未來的創造自必須超越這樣的局限性,但當下的創造性卻必須通過當下的時空條件來表現。這樣,有限(內在)與無限(超越)有著一種互相對立而又統一的辯證關係。我們的責任就是要通過現代的特殊的條件去表現無窮不可測的天道。這樣,當我們賦予“理一分殊”以一全新的解釋,就可以找到一條接通
傳統與
現代的道路。第三,肯定儒家傳統智慧、中心理念與未來世界的相干性。劉先生通過對朱熹的深入研究指出,“仁”、“生”、“理”的三位一體是朱子秉承儒家傳統所把握的中心理念,這些理念並不因朱子的宇宙觀的過時而在現時代完全失去意義。
朱子吸納他的時代的宇宙論以及科學的成就,對於他所把握的儒家的中心理念(理一),給予了適合於他的時代的闡釋(分殊),獲致了獨特的成就。今天,我們完全可以打開一個全新的境界,以適合於現代的情勢。劉先生把儒家的本質概括為孔孟的仁心以及宋儒進一步發揮出來的生生不已的精神,倡導選擇此作為我們的終極關懷,並以之為規約理想的原則,同時對傳統與現代均有所批判。他認為:儒家思想的內容不斷在變化之中,其仁心與生生的規約原則,在每一個時代的表現都有它的局限性,所謂“理一而分殊”,這並不妨害他們在精神上有互相貫通之處。每一時代的表現,都是有血有肉的。儒家的本質原來就富有一種開放的精神,當然可以作出新的解釋,開創出前人無法想像的新局面。這當然只是適合於這個時代的有局限性的表征而已,不能視為唯一或最終的表現。後人可以去追求更新的、超越現代的仁心與生生的後現代的表現。
劉先生指出,培養
哈貝瑪斯(J.Habermas)所說的交往理性,求同存異,嚮往一個真正全球性的社團,同時要反對相對主義,肯定無形的理一是指導我們行為的超越規約原則。我們所要成就的不是一種實質的統一性,而是
卡西勒(E.Cassirer)所謂的“功能的統一性”。通過現代的詮釋,對於超越“理一”的終極託付並無須造成抹煞“分殊”的不良後果。但是對於“分殊”的肯定也並不會使我們必然墮入相對主義的陷阱。這是因為我們並不是為了“分殊”而“分殊”,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理性的具體落實與表現,雖然這樣的表現是有限的,不能不排斥了其它的可能性,然而彼此的精神是可以互相呼應的。宋儒“月印萬川”之喻很可以充分表現出這樣的理想境界的情致。
總之,劉述先沿著
牟宗三、
方東美等人的思路,從存有論和宗教哲學的角度闡明儒學的核心,強調儒家仁心與生生精神可以作為現代人的宗教信念與終極關懷,通過對傳統與現代的多維批判,肯定儒家思想的宗教意涵有著極高的價值與現代的意義。他著力論證、開拓並辯護了“超越內在”說,並通過“兩行之理”、“理一分殊”的新釋,注入了新的信息,使之更有現代性和現實性,肯定超越與內在、理想與現實的有張力的統一。
社會評價
多年來,劉述先教授盡心盡力,無論在教學、研究、行政上均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文學院、新亞書院及大學貢獻良多。劉教授在香港桃李滿門,大部分博士學生現任職香港各間大學;他對香港的高等教育,可謂竭盡樹人之責。在研究方面,劉教授著作等身,望重學林,多年來致力於重建儒學,被譽為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評)
劉述先一生著述不斷,在儒學研究方面不僅造詣甚為深厚,而且不斷結合歐美的新的哲學、宗教的發展,據本開新,在理論上開出新的局面,為當代儒學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清華大學國學院院長陳來評)
 劉述先教授
劉述先教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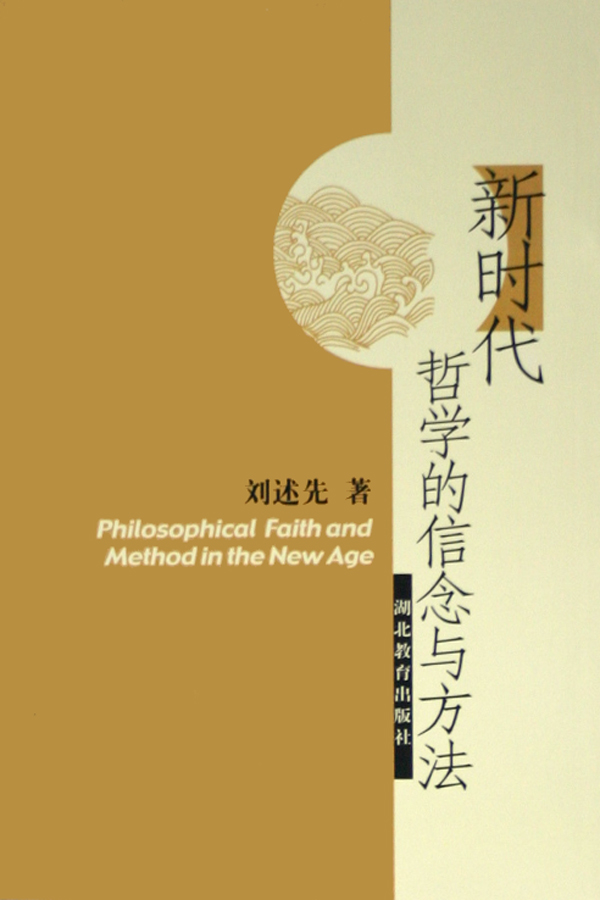 著作
著作 劉述先
劉述先
 劉述先教授
劉述先教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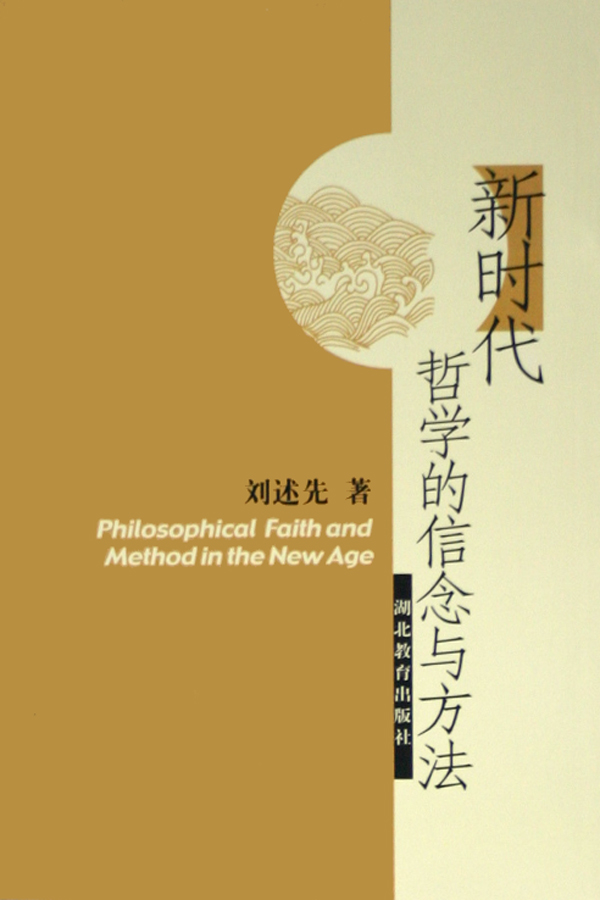 著作
著作 劉述先
劉述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