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在
西漢中期,戰亂頻仍的諸侯王國割據局面基本結束,生產得到恢復與發展,中央集權得到鞏固與加強,出現了經濟繁榮和政治大一統的局面。為適應統一的中央集權的需要,董仲舒的神學唯心哲學思想便應運而生。他的哲學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春秋繁露》中。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據《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董仲舒說《
春秋》事得失,作《聞舉》、《玉杯》、《蕃露》等數十篇。《蕃露》是他講《春秋》諸篇中的一篇。“蕃”與“繁”古字相通。《史記》說“蕃露”原是冠冕的一種裝飾,綴玉而下垂。賈公彥在《周禮·春官大司樂》中作疏說:“前漢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為《春秋》作義,潤益處多”,認為《春秋繁露》是對《春秋》大義的引申和發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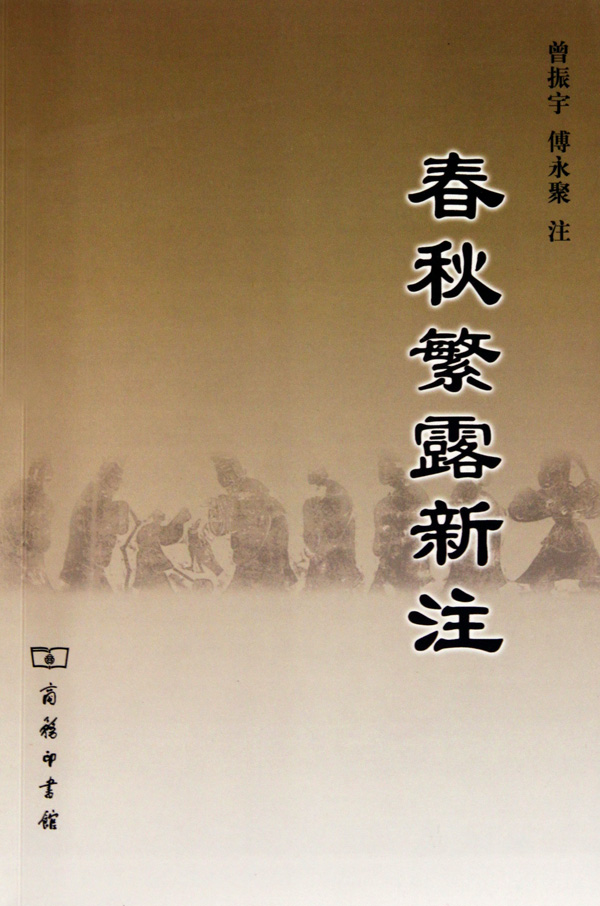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現存《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於書中篇名和《
漢書·藝文志》及本傳所載不盡相同,後人疑其不盡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系後人輯錄董仲舒遺文而成書,書名為輯錄者所加,隋唐以後才有此書名出現。
中國現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
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計台刻本,現藏於北京圖書館。注本很多,最詳盡的是蘇輿的《
春秋繁露義證》。其版本有《
永樂大典》所載《宋本》,明代蘭雪堂活字本,清代盧文弨抱經堂校刊本。注釋本有清代
凌曙的《
春秋繁露注》和蘇輿的《春秋繁露義證》等。
主要內容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一公元前104年)撰。仲舒,廣川(今河北棗強)人,西漢哲學家,
今文經學大師,專治《春秋公羊傳》;曾任博士、
江都相和膠西王相,漢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他對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為武帝所採納,開此後兩乾餘年封建社會以儒學為正統的先聲;除此書外,尚有《董子文集》。此編為作者闡釋儒家經典《春秋》之書,書名為“繁露”,《
四庫全書總目》云: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為說也。此書篇名與《
漢書·藝文志》及《漢書·董仲舒傳》的記載不盡相同;《漢書·藝文志》只言《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漢書·董仲舒傳》所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皆為所著書名,數十篇,十餘萬言;今存《玉杯》、《竹林》則為《春秋繁露》中之篇名,因此,後人疑其不盡出董仲舒一人之手,宋儒
程大昌攻之尤力,但《四庫全書總目》卻認為,書雖未必全出仲舒,但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
董仲舒在書中極力推崇《公羊傳》的見解,闡發“
春秋大一統”之旨,把封建統一說成是天經地義而不可改變。他認為自然界的天就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並且建立起了一套神學目的論學說,把人世間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權的統治都說成是上天有目的安排,將天上
神權與地上王權溝通起來,為“王權神授”製造了理論根據。同時,又以
陰陽五行學說將自然界和社會人事神秘化,理論化,作出各種牽強比附,建立“天人感應”論的唯心主義形上學的神學體系。如仲舒創造的“
人副天數”說,將人身的骨節、五臟、四肢等等,比附為一年的日數、月數,以至五行、四時之數,人身五臟與五行符、外有四肢與四時符,從而得出“為人者,天也”的理論,認為人類自身的一切都由天所給予。用天有陰陽來比附人性,謂“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意即天道兼備著陰陽兩種作用,人身也兼備著貪仁兩種本性等等。概括而言,仲舒的神學體系包括“三綱”、“五常”、“三統”、“
三正”、“性三品”諸說。在《基義》篇里,謂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之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
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綜合前論,即是所謂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並把“仁、義、禮、智、信”五種封建道德倫理規範,與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相比附,則為“五常”。“三統”與“三正”實際上是仲舒的歷史觀。
秦漢以前古書記載有夏、商、周三代,董仲舒遂認為夏是黑統,商是白統,周是赤統,改朝換代只不過是“三統”的依次循環,只是“改正朔,易服色”,在曆法和禮儀上作形式上的改換。夏以寅月為正月,商以丑月為正月,周以子月為正月,三代的正月在曆法上規定不同,故被其稱作“三正”,在仲舒看來,一個新王朝出現,無非在曆法上有所改變,衣服旗號有所變化,此即為“新王必改制”,表示一新個王朝重新享有天命。
從“
三統”、“三正”論中不難看出,仲舒否認歷史的發展,王朝的更迭只是形式上的改變,實質上卻是絕對不變的。所謂的“性三品”,即是聖人生來性善,小人生來性惡,中人之性,則可善可惡,性善聖人則是天生的統治者,中人之性則可以教化,逐漸變善,至於小人則是“斗筲之性”,只能接受聖人的統治。總之,此書內容反映了作者的整個哲學思想體系,這種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學說的思想體系,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作用與影響。傳本很多,主要有清《四庫全中》本,光緒五年(1879年)
定州王氏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附張駒賢《校正》十七卷,又有《
四部備要》本及1975年
中華書局鉛印本。 蘇輿撰《
春秋繁露義證》點校本收入到中華書局《
新編諸子集成》裏面
創作背景
秦政成功的經驗為漢政所繼承,秦政失敗的教訓為漢政所吸取。漢初對外和親避戰,對內平定外姓藩王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文景之時刑罰大省,用賢納諫,輕徭薄賦,在此基礎上,武帝強化中央集權頒行推恩令建立中朝、地方設立刺史制度,使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在思想文化方面,武帝時期相對寬鬆,廣開獻書之路,使大批因秦始皇焚書坑儒而隱藏起來的典籍得以再現;大批隱退於民間的學者得以重新回到學術領域,出現了繁榮局面。
《
春秋公羊傳》的作者是戰國齊人,在公羊傳的傳受過程中,正是稷下
黃老之學形成和發展之時。公羊春秋大一統思想,與齊國大一統思想有著密切關係。齊威王、宣王時期,國力強大,“諸侯東面朝齊。”(《史記·孟荀列傳》)當時遊學齊國的孟子,就認為齊國有希望統一中國。他說:“諸侯之三寶:土地、人民、政事。”(《孟子·盡心》)齊國已據有二,“夏後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民不改聚也。”只有在“政事”上“行仁者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孫丑上》)因為當時“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孟荀列傳》)齊國統治者勵精圖治,懷有統一天下的強烈願望,廣招學士,優厚待遇,使之講習議論,著書立說,言治亂之事。稷下學士,盛極一時,各家雖異說,但對全國統一,成為共識。孟子主仁政而王,認為“以齊王,由反手也。”(《公孫丑上》)《黃帝四經》說:“唯餘一人,兼有天下。”(《十六經·成法》),“抱道執度,天下可一也。”(《道原》)《文子》說:“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王者以道蒞天下,執一無為,“君必執一而後能群矣。”(《道德》)《管子》對統一大局,描繪了種種藍圖。如《霸言》中對霸業和王業的構想,《君臣》中提出“天子出令於天下……書同名,車同軌”的大一統思想。《荀子》“四海之內若一家”的構想(《儒效》),以及向齊閔王相田文獻策,“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強國》)。齊統治者從而獲得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和理論武器,這就是以道為本,因循為用,仁義禮法為具的黃老之學。
以道家思想為基礎,兼采儒墨名法陰陽,構成綱紀道德,經緯人事的理論,打著黃帝旗號,一方面把自己說成是黃帝之胄,黃帝戰勝炎帝的傳說,成為田氏代替姜氏(炎帝之胄)的理由;另一方面,黃帝又成為其稱雄天下,繼承黃帝統一天下偉業的旗幟。帝統和學統組合黃老之學,是齊國的特有思想。
公羊春秋大一統思想,是通過實行統一曆法來標誌的。《漢書·王吉傳》載王陽上疏中說春秋大一統政治含義很明確,“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契約風,九州共貫也。”董仲舒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書·董仲舒傳》)大一統在這裡,成了天經地義的古今常道。它不僅表現 在“改正朔”的曆法一統天下,而且包括各個方面。顏師古對此作注說:“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系統天子,不得自專也。”師古之注,本於董仲舒。董仲舒說:“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漢書》本傳)“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元者為萬物之本也。”所以,“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系之元也。”(《春秋繁露·重政》,以下只具篇名)一是數之始,物之極,“謂一元者,大始也。”(《玉英》)春秋為什麼貴乎元而言之呢?“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道》)這裡的“一”,“元”和“天者萬物之祖”的“天”,(《順命》)實際上就是道家的“道”或“一”和“玄”。可見董仲舒大一統思想受黃老之學的影響,這是確實無疑的。
董仲舒思想與黃老之學
董仲舒思想以儒家為主,融合名法陰陽道,對先秦儒學加工改造,重新創造一個新的儒學體系,奠定了長期封建統治的理論基礎。
黃老之學由老子發展而來,然而它與老子有一個顯著的不同,黃老學者把超凡的“道”引向社會人事,道,不僅是物之所道,也是人之所由。《文子》說:“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故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董仲舒援道入儒,以陰陽五行為骨架,將天道與人事組合在一起,構成其天人理論體系。“察天人之分,觀道命之異……人道者,人之所由。”(《
天地陰陽》)在這個體系中,“天”是最高的主宰,它是萬物之祖,“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效義》)“天”是由天地人陰陽五行十因素構成,“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官制象天》)十端組合成四時、五行的運動體系,“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制為四時,列為五行。”(《五行相生》)天通過五行生剋的次序,顯示其運動的功能,這就是天道。而五行的次序與人間的倫常政治和社會制度相配合,四時有四政,木火土金水五行有仁義禮智信五行。“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四時之副》)天人相通、聖人法天而立道,故董仲舒說:“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本傳)道是適於治的必由之路,故為人主者,法天之行。“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離合根》)人主法天之行,是“其法取象於天,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為仁。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為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為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天地之行》)法天之行,也就是人主“以無為為道,以不私為寶,立無為之位,而乘備具之官,”實行無為之治道。人主“內深藏”,“外博觀”,而不自勞於事,做到“足不自動”,“口不自言”,“心不自慮”而“群臣效當”,故“莫見其為之,而功成矣。”(《離合根》)這種主逸臣勞,就是黃老之學的君道無為,臣道有為的思想。
黃老之學與老子另一個顯著的不同,是對“無為”作了新的解釋。《文子》說:“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卷握而不散;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掛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自然》)無不是不作為,而是不以主觀成見和好惡而害道,而是循理而舉事,因資立功,推自然之勢,“所謂無為者,不先物動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道原》)文子認為,無為而治的“王道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自然》)董仲舒的“為人君者,居無位之位,行不言之教,”即本於此。他認為,人君無為,不是不理朝政,放任臣下,而是人君執一處靜,無需每事親躬,是以君臣分職而治,各敬其事。不同的一點是“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保位權》)“行不言之教”,也不是不講話,不號令,而是“以臣言為聲,以臣事為形”,因為“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人君“虛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影,以行賞罰。”這種聲響相應,形影隨合,“■名考質,以參其實,賞不空行,罰不虛出”的“自然致力之術”,(《保位權》)也就是黃老之學的“循名責實”的“王術”。《文子》說:“無為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並應無窮。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不遠也。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君不自勞,使臣下“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為之功。”(《下德》)“循名責實,使自有司……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上仁》)此亦董仲舒所謂“建治之術”也。
天下變道也不變與不變故易常
人們常認為,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也不變”是形上學,是為腐朽的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這種斷章取義的評論,對董仲舒是很不公正的。董仲舒此話是在回答漢武帝冊問:“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董仲舒認為,“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三代聖王,因循繼統,從容中道,王道條貴,故不言其所損益,因此說“天不變,道也不變”。三代之後,情況不同,夏桀殷紂,逆天暴物,殷之繼夏,周之繼殷,是繼亂世而治,天命改變了,王道也要變化。他對上述兩種不同情況的結論:“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三代所守道一,故天不變道也不變,聖王繼亂世,則“掃除其跡而悉去之”,今漢繼秦後,“如朽木糞牆”,必解而更張之,必變而更化之。
董仲舒認為,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 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並徵引“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要漢武帝“退而更化”,其更化方案是“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以上見本傳)“更化”是董仲舒獨特的思想,不變之道只有通過更化“變”取得,這與黃老之學變中求不變是一致的。《黃帝四經》說:“夫天地之道,寒熱燥濕,不能並立;剛柔陰陽,固不兩行。兩相養,時相成……若夫人事則無常,過極失當,變故易常,德則無有,措刑不當。”(《姓爭》)人事是變化不定的,在處理其事務時,擅自改變一貫的制度和政策,德教就無收穫,刑罰也會不當,因此要不變故易常。
《
文子》則從另一方面說:“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
下德》)“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精誠》)董仲舒引臨淵羨魚,退而織網時,稱“古人有言”,這個古人,就是文子。可見董仲舒熟知黃老之學。他稱引文子,要漢武帝更化,以求三代相受而守一道的不變之道,“復修教化而崇起之”,這也是他不同於黃老之學,而尊儒之所以。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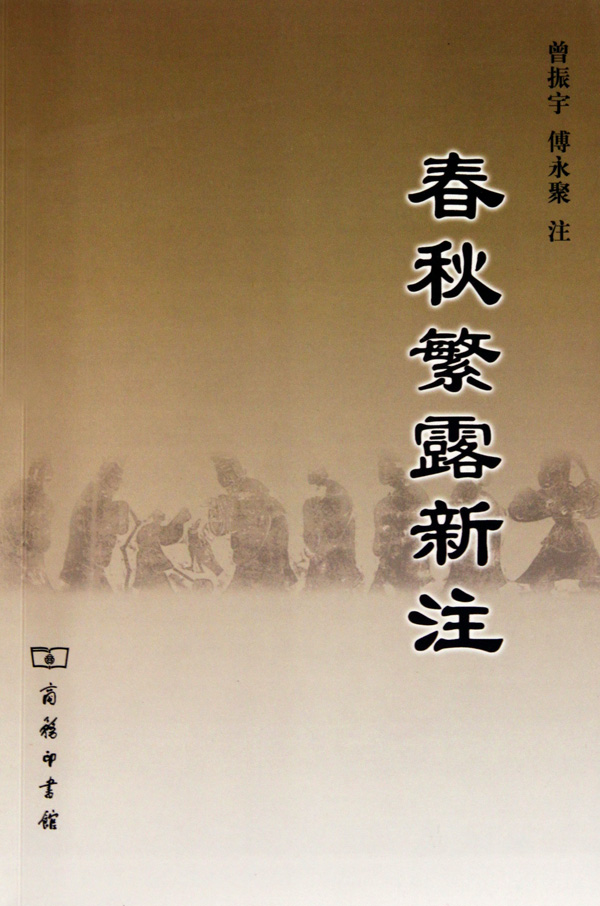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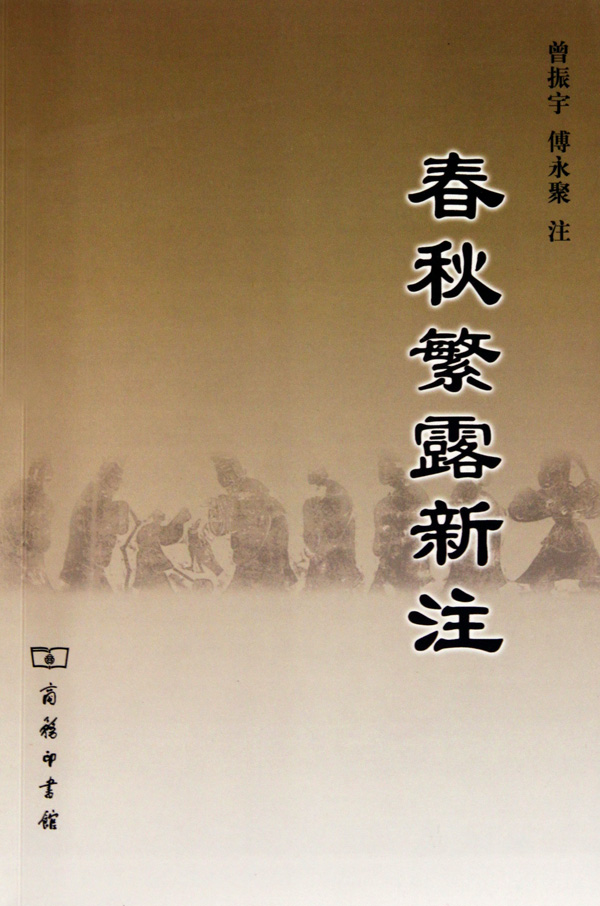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