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德十年》是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季羨林。該書記錄了季羨林先生1935年至1945年在德國留學的經歷。
基本介紹
- 書名:《留德十年》
- 作者:季羨林
- ISBN:9787500844051
- 類別:傳記
- 頁數:211
- 出版社:中國工人出版社
內容簡介
對於這些夢有沒有留戀之感呢?應該說是有的。人到了老年,往往喜愛回憶往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當然也不能成為例外。英國人常說什麼"往日的可愛的時光",實有會於我心。往日的時光,回憶起來,確實感到美妙可愛。"當時只道是尋常",然而一經回憶,卻往往覺得美妙無比,回味無窮。我經常陷入往事的回憶中。
但是,我從來也沒有想到,把這些輕夢或者噩夢從回憶中移到紙上來。我從來沒有感到,有這樣的需要。我只是一個人在夜深人靜時,伏在枕上,讓逝去的生命一幕一幕地斷斷續續地在我眼前重演一遍,自己仿佛成了一個旁觀者,顧而樂之。逝去的生命不能復歸,也用不著復歸。但是,回憶這樣的生命,意識到自己是這樣活過來的,陽關大道、獨木小橋,都走過來了,風風雨雨都經過了,一直到今天,自己還能活在世上,還能回憶往事,這難道還不能算是莫大的幸福嗎?
只是到了最近一兩年,比我年輕的一些朋友,多次向我建議寫一點自傳之類的東西。今天年輕的知識分子,甚至許多中年知識分子,大都不能體會。有時候同他們談一點過去的情況,他們往往瞪大了眼睛,像是在聽"天方夜譚"。因此,他們的意見是,我應當把這些經歷寫出來,不要過於"自私自利",只留在自己腦海中,供自己品味玩賞。這應該說是我這一輩人的責任,不容推卸。
我考慮他們的意見,覺得是正確的。就我個人來說,我生於辛亥革命那一年的夏秋之交,距離10月10日,只有一個月多一點。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當過大清皇帝的臣民,大概也算是一個"遺少"吧。我在極小的時候,就聽到"朝廷"這個詞兒,意思是大清皇帝。在我的幻想中,"朝廷"是一個非人非神非龍非蛇,然而又是人是神是龍是蛇的東西。最後一個"朝廷"一退位,立刻來了袁世凱,緊跟著是軍閥混戰。赤縣神州,群魔亂舞。我三歲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我對此毫無所知。對於五四運動,所知也不多,只對文言改白話覺得新鮮而已。在國小和國中時期,跟著大孩子遊行示威,焚燒日貨和英貨,情緒如瘋如狂。高中時期,國民黨統治開始,是另一種群魔亂舞,是國民黨內部的群魔。大學時期,日本軍國主義者蠢蠢欲動。"九一八事變"以後,我曾隨清華同學臥軌絕食,赴南京請願。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蔣介石。留學時期,"七七事變"發生,半壁河山,淪於外寇鐵蹄之下。我的家鄉更是早為外寇占領,讓我無法回國。"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休向耳邊啼"。我漂泊異鄉,無從聽到杜鵑鳴聲,我聽到的是天空中轟炸機的鳴聲,伴隨著肚中的飢腸轆轆聲。有時候聽到廣播中希特勒瘋狗似的狂吠聲。如此度過了八年。"烽火連八歲,家書抵億金"。抵億金的家書一封也沒能收到。大戰終於結束。我在瑞士待了將近半年,費了千辛萬苦,經法國、越南回到祖國。在狂歡之餘,災星未退,又在通貨瘋狂膨脹中度過了三年,終於迎來了解放。在更大的狂歡之餘,知道道路並不是總有玫瑰花鋪地,有時難免也有狂風惡浪。就這樣,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一直活到了今天,垂垂老矣。
如此豐富複雜的經歷,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有的。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這些經歷也是十分可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從中都可以吸取,對人對己都會有點好處的。我自己如果秘而不宣,確有"自私自利"之嫌。因此,我決心聽從別人的建議,改變以前的想法,把自己一生的經歷實事求是地寫出來。我特彆強調"實事求是"四字,因為寫自傳不是搞文學創作,讓自己的幻想縱橫馳騁。我寫自傳,只寫事實。這是否也能寫成文學作品,我在這裡存而不論。古今中外頗有大文學家把自傳寫成文學創作的。德國最偉大的詩人歌德就是其中之一。他的DichtungundWahrheit(《詩與真》)可以為證。我個人認為,大文學家可以,我則不可。我這裡只有Wahrheit,而無Dichtung。
但是,如此複雜的工作決不能畢其功於一役。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沒有太多的餘閒,我只能分段解決。我把我七十多年的生命分成八個階段:
一、故鄉時期
二、在濟南上中學時期
三、清華大學、中學教員時期
四、留德十年
五、解放前夕
六、五六十年代
七、牛棚雜憶
八、1978年以後
在1988年,我斷斷續續寫成了四和七兩部草稿。現在先把四"留德十年"整理出來,讓它帶著我的祝福走向世界吧!扯雪芹作一絕:
毫無荒唐言
半把辛酸淚
作者並不痴
人解其中味以上算是楔子。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仔細分析其中原因,有的同今天差不多,有的則完全不同。相同的原因我在這裡不談了。不同的原因,其根柢是社會制度不同。那時候有兩句名言:"畢業即失業";"要努力搶一隻飯碗"。一個大學畢業生,如果沒有後門,照樣找不到工作,也就是照樣搶不到一隻飯碗。如果一個人能出國一趟,當時稱之為"鍍金",一回國身價百倍,金光閃爍,好多地方會搶著要他,成了"搶手貨"。
當時要想出國,無非走兩條路:一條是私費,一條是官費,前者只有富商、大賈、高官、顯宦的子女才能辦到。後者又有兩種:一種是全國性質的官費,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類;一種是各省舉辦的。二者都要經過考試。這兩種官費人數都極端少,只有一兩個。在芸芸學子中,走這條路,比駱駝鑽針眼還要困難。是否有走後門的?我不敢說絕對沒有。但是根據我個人的觀察,一般是比較公道的,錄取的學員中頗多英俊之材。這種官費錢相當多,可以在國外過十分舒適的生活,往往令人羨煞。
我當然也患了留學熱,而且其嚴重程度決不下於別人。可惜我投胎找錯了地方,我的家庭在鄉下是貧農,在城裡是公務員,連個小官都算不上。平常日子,勉強餬口。我於1934年大學畢業時,叔父正失業,家庭經濟實際上已經破了產,其貧窘之狀可想而知。私費留學,我想都沒有想過,我這個癩蛤蟆壓根兒不想吃天鵝肉,我還沒有糊塗到那個程度。官費留學呢,當時只送理工科學生,社會科學受到歧視。今天歧視社會科學,源遠流長,我們社會科學者運交華蓋,只好怨我們命苦了。
總而言之,我大學一畢業,立刻就倒了霉,留學無望,飯碗難搶;臨淵羨魚,有網難結;窮途痛哭,無地自容。母校(省立濟南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要我回母校當國文教員,好像絕處逢生。但是我學的是西洋文學,滿腦袋歌德、莎士比亞,一旦換為屈原、杜甫,我換得過來嗎?當時中學生頗有"駕"教員的風氣。所謂"駕",就是趕走。我自己"駕"人的經驗是有一點的,被"駕"的經驗卻無論如何也不想沾邊。我考慮再三,到了暑假離開清華園時,我才咬了咬牙:"你敢請我,我就敢去!"大有破釜沉舟之概了。
省立濟南高中是當時全山東惟一的一所高級中學。國文教員,待遇優渥,每月一百六十塊大洋,是大學助教的一倍,折合今天人民幣,至少可以等於三千二百元。這是頗有一些吸引力的。為什麼這樣一隻"肥"飯碗竟無端落到我手中了呢?原因是有一點的。我雖然讀西洋文學,但從小喜歡舞筆弄墨,發表了幾篇散文,於是就被認為是作家,而在當時作家都是被認為能教國文的,於是我就成了國文教員。但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我深知自己能吃幾碗乾飯,心虛在所難免。我真是如履薄冰似的走上了講台。
但是,宋校長真正聘我的原因,還不就這樣簡單。當時山東中學界搶奪飯碗的搏鬥是異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換校長,一大批教員也就被撤換。一個校長身邊都有一個行政班子,教務長,總務長,訓育主任,會計,等等,一應俱全,好像是一個內閣。在外圍還有一個教員隊伍。這些人都是與校長共進退的。這時山東中學教育界有兩大派系:北大派與師大派,兩者勾心鬥角,爭奪地盤。宋校長是北大派的頭領,與當時的教育廳廳長何思源,是菏澤六中和北京大學的同學,私交頗深。有人說,如果宋校長再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與何在國外也是同學,則他的地位會更上一層樓,不只是校長,而是教育廳的科長了。
總之,宋校長率領著北大派浩蕩大軍,同師大派兩軍對壘。他需要支持,需要一支客軍。於是一眼就看上了我這個超然於兩派之外的清華大學畢業生,兼高中第一級的畢業生。他就請我當了國文教員,授意我組織高中畢業同學會,以壯他的聲勢。我雖涉世未深,但他這一點苦心,我還是能夠體會的。可惜我天生不是幹這種事的料,我不會吹牛拍馬,不願陪什麼人的太太打麻將。結果同學會沒有組成,我感到抱歉,但是無能為力。宋校長對別人說:"羨林很安靜!"宋校長不愧是北大國文系畢業生,深通國故,有很高的古典文學造詣,他使用了"安靜"二字,借用王國維的說法,一著此二字,則境界全出,勝似別人的千言萬語。不幸的是,我也並非白痴,多少還懂點世故,聆聽之下,心領神會;然而握在手中的那一隻飯碗,則搖搖欲飛矣。
因此,我必須想法離開這裡。
離開這裡,到哪裡去呢?"抬眼望盡天涯路",我只看到人海茫茫,沒有一個歸宿。按理說,我當時的生活和處境是相當好的。我同學生相處得很好。我只有二十三歲,不懂什麼叫架子。學生大部分同我年齡差不多,有的比我還要大幾歲,我覺得他們是夥伴。我在一家大報上主編一個文學副刊,可以刊登學生的文章,這對學生是極有吸引力的。同教員同事關係也很融洽,幾乎每周都同幾個志同道合者出去吃小館,反正工資優厚,物價又低,誰也不會吝嗇,感情更易加深。從外表看來,真似神仙生活。
然而我情緒低沉,我必須想法離開這裡。
離開這裡,至高無上的夢就是出國鍍金。我常常面對屋前的枝葉繁茂花朵鮮艷的木槿花,面對小花園裡的亭台假山,做著出國的夢。同時,在燈紅酒綠中,又會驀地感到手中的飯碗在動搖。二十剛出頭的年齡,卻心懷百歲之憂。我的精神無論如何也振作不起來。我有時候想:就這樣混下去吧,反正自己毫無辦法,空想也白搭。俗話說:"車到山前必有路"。我這輛車還沒駛到山前,等到了山前再說吧。
然而不行。別人出國留學鍍金的訊息,不時傳入自己耳中。一聽到這種訊息,就像我看別人一樣,我也是渾身發抖。我遙望歐山美水,看那些出國者如神仙中人。而自己則像人間凡夫,"更隔蓬山千萬重"了。
我就這樣度過了一整年。
然而,對我來說,這卻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非抓住不行了。我在清華名義上主修德文,成績四年全優(這其實是名不副實的),我一報名,立即通過。但是,我的困難也是明擺著的:家庭經濟瀕於破產,而且親老子幼。我一走,全家生活靠什麼來維持呢?我面對的都是切切實實的現實困難,在狂喜之餘,不由得又心憂如焚了。
我走到了一個歧路口上:一條路是桃花,一條是雪。開滿了桃花的路上,雲蒸霞蔚,前程似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堆滿了雪的路上,則是暗淡無光,擺在我眼前是終生青衾,老死學宮,天天為飯碗而搏鬥,時時引"安靜"為鑑戒。究竟何去何從?我逢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擇。
出我意料之外,我得到了我叔父和全家的支持。他們對我說:我們咬咬牙,過上兩年緊日子;只要餓不死,就能迎來勝利的曙光,為祖宗門楣增輝。這種思想根源,我是清清楚楚的。當時封建科舉的思想,仍然在社會上流行。人們把國小畢業看作秀才,高中畢業看作舉人,大學畢業看作進士,而留洋鍍金則是翰林一流。在人們眼中,我已經中了進士。古人說:沒有場外的舉人;現在則是場外的進士。我眼看就要入場,焉能懸崖勒馬呢?
認為我很"安靜"的那一位宋還吾校長,也對我完全刮目相看,表現出異常的殷勤,親自帶我去找教育廳長,希望能得到點資助。但是,我不成材,我的"安靜"又害了我,結果空手而歸,再一次讓校長失望。但是,他熱情不減,又是勉勵,又是設宴歡送,相期學成歸國之日再共同工作,令我十分感動。
我高中的同事們,有的原來就是我的老師,有的是我的同輩,但年齡都比我大很多。他們對我也是刮目相看。年輕一點的教員,無不患上了留學熱。也都是望穿秋水,欲進無門,誰也沒有辦法。我忽然撈到了鍍金的機會,洋翰林指日可得,宛如蟄龍升天,他年回國,決不會再待在濟南高中了。他們羨慕的心情溢於言表。我忽然感覺到,我簡直成了《儒林外史》中的范進,雖然還缺一個老泰山胡屠戶和一個張鄉紳,然而在眾人心目中,我忽然成了特殊人物,覺得非常可笑。我雖然還沒有春風得意之感,但是內心深處是頗為高興的。
但是,我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除了前面說到的家庭經濟困難之外,還有制裝費和旅費。因為知道,到了德國以後,不可能有餘錢買衣服,在國內制裝必須周到齊全。這都需要很多錢。在過去一年內,我從工資中節餘了一點錢,數量不大,向朋友借了點錢,七拼八湊,勉強做了幾身衣服,裝了兩大皮箱。長途萬里的旅行準備算是完成了。此時,我心裡不知道是什麼滋味,酸、甜、苦、辣,攪和在一起,但是決沒有像調和雞尾酒那樣美妙。我充滿了渴望,而又忐忑不安,有時候想得很美,有時候又憂心忡忡,在各種思想矛盾中,迎接我生平第一次大抉擇、大冒險。
臨離家時,我思緒萬端。叔父、嬸母、德華(妻子),女兒婉如牽著德華的手,才出生幾個月的延宗酣睡在母親懷中,都送我到大門口。嬌女、幼子,還不知道什麼叫離別,也許還覺得好玩。雙親和德華是完全理解的。我眼裡含著淚,硬把大量的眼淚壓在肚子裡,沒有敢再看他們一眼——我相信,他們眼裡也一定噙著淚珠——扭頭上了洋車,只有大門樓上殘磚敗瓦的影子在我眼前一閃。
我先乘火車到北平。辦理出國手續,只有北平有可能,濟南是不行的。到北平以後,我先到沙灘找了一家公寓,賃了一間房子,存放那兩隻大皮箱。立即趕赴清華園,在工字廳招待所找到了一個床位,同屋的是一位比我高几級的清華老畢業生,他是什麼地方保險公司的總經理。夜半聯床,娓娓對談。他再三勸我,到德國後學保險。將來回國,飯碗決不成問題,也許還是一隻金飯碗。這當然很有誘惑力。但卻同我的願望完全相違。我雖向無大志,可是對作官、經商,卻決無興趣,對發財也無追求。對這位老學長的盛意,我只有心領了。
此時正值暑假,學生幾乎都離校回家了。偌大一個清華園,靜悄悄的。但是風光卻更加旖旎,高樹蔽天,濃陰匝地,花開綠叢,蟬鳴高枝;荷塘里的荷花正迎風怒放,西山的紫氣依舊幻奇。風光雖美,但是我心中卻感到無邊的寂寞。僅僅在一年前,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那眾多的小夥伴都還聚在一起,或臨風朗讀,或月下抒懷。黃昏時漫步荒郊,回校後餘興尚濃,有時候沿荷塘步月,領略荷塘月色的情趣,其樂融融,樂不可支。然而曾幾何時,今天卻只剩下我一個人又回到水木清華,睹物思人,對月興嘆,人去樓空,宇宙似乎也變得空蕩蕩的,令人無法忍受了。
我住的工字廳是清華的中心。我的老師吳宓先生的"藤影荷聲之館"就在這裡。他已離校,我只能透過玻璃窗子看室中的陳設,不由憶起當年在這裡高談闊論時的情景,心中黯然。離開這裡不遠就是那一間臨湖大廳,"水木清華"四個大字的匾就掛在後面。這個廳很大,裡面擺滿了紅木家具,氣象高雅華貴。平常很少有人來,因此幽靜得很。幾年前,我有時候同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等幾個好友,到這裡來閒談。我們都還年輕,有點不知道天高地厚,說話海闊天空,旁若無人。我們不是糞土當年萬戶侯,而是揮斥當代文學家。記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時,我們幾個人在這裡碰頭,議論此書。當時意見截然分成兩派:一派完全肯定,一派基本否定。大家爭吵了個不亦樂乎。我們這種侃大山,一向沒有結論,也不需要有結論。各自把自己的話儘量誇大其詞地說完,然後再談別的問題,覺得其樂無窮。今天我一個人來到這間大廳里,睹物思人,又不禁有點傷感了。
在這期間,我有的是空閒。我曾拜見了幾位老師。首先是馮友蘭先生,據說同德國方面簽定契約,就是由於他的斡旋。其次是蔣廷黻先生,據說他在簽定契約中也出了力。他懇切勸我說,德國是法西斯國家,在那裡一定要謹言慎行,免得惹起麻煩。我感謝師長的叮囑。我也拜見了聞一多先生。這是我同他第一次見面;不幸的是,也是最後一次見面。等到十一年後我回國時,他早已被國民黨反動派暗殺了。他是一位我異常景仰的詩人和學者。當時談話的內容我已經完全忘記,但是他的形象卻永遠留在我心中。
有一個晚上,吃過晚飯,孤身無聊,信步走出工字廳,到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中所描寫的荷塘邊上去散步。於時新月當空,萬籟無聲。明月倒影荷塘中,比天上那一個似乎更加圓明皎潔。在月光下,荷葉和荷花都失去了色彩,變成了灰濛濛的一個顏色。但是縷縷荷香直逼鼻管,使我仿佛能看到翠綠的荷葉和紅艷的荷花。荷葉叢中閃熠著點點的火花,是早出的螢火蟲。小小的火點動盪不定,忽隱忽現,仿佛要同天上和水中的那個大火點,爭光比輝。此時,宇宙間仿佛只剩下了我一個人。前面的鵬程萬里,異鄉漂泊;後面的親老子幼的家庭,都離開我遠遠的,遠遠的,陷入一層薄霧中,望之如蓬萊仙山了。〖JP〗
但是,我到北平來是想辦事兒的,不是來做夢的。當時的北平沒有外國領館,辦理出國護照的簽證,必須到天津去。於是我同喬冠華就聯袂乘火車赴天津,到俄、德兩個領館去請求籤證。手續決沒有現在這樣複雜,領館的俄、德籍的工作人員,只簡簡單單地問了幾句話,含笑握手,並祝我們一路順風。我們的出國手續就全部辦完,只等出發了。〖JP〗
回到北平以後,幾個朋友在北海公園為我餞行,記得有林庚、李長之、王錦弟、張露薇等。我們租了兩隻小船,蕩舟於荷花叢中。接天蓮葉,映日荷花,在太陽的照射下,紅是紅,綠是綠,各極其妙。同那天清華園的荷塘月色,完全不同了。我們每個人都興高采烈,臧否人物,指點時政,意氣風發,所向無前,"語不驚人死不休",我們真仿佛成了主宰沉浮的英雄。玩了整整一天,盡歡而散。
千里涼棚,沒有不散的筵席。終於到了應該啟程的日子。8月31日,朋友們把我們送到火車站,就是現在的前門老車站。當然又有一番祝福,一番叮囑。在登上火車的一剎那,我腦海里忽然浮現出一句舊詩:"萬里投荒第二人"。
作品目錄
創作背景
作品鑑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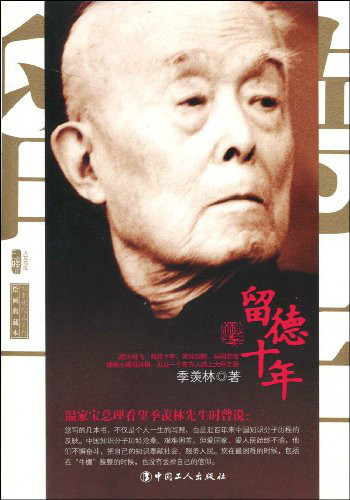 留德十年
留德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