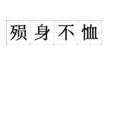殞身不恤,讀音yǔn shēn bú xù,犧牲生命也不顧惜。出自魯迅先生《華蓋集續篇》中《記念劉和珍君》一文
基本介紹
- 名稱:殞身不恤
- 拼音:yǔn shēn bú xù
- 釋義:犧牲生命也不顧惜
- 結構:聯合式
- 用法:定語
- 詞性:褒義
- 出處:魯迅《記念劉和珍君》
解釋,出處,詞語辨析,相關資料,魯迅,劉和珍,《記念劉和珍君》,
解釋
【釋義】殞:犧牲;恤:顧惜。犧牲生命也不顧惜。
出處
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詭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魯迅《記念劉和珍君》)

詞語辨析
發音:yǔn shēn bú xù
近義詞:慷慨捐生、慷慨赴義、 視死如歸
反義詞:貪生怕死
易錯字:殞(隕身不恤)
語法:複句式;作定語;含褒義
相關資料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祖籍河南省正陽縣),是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的精神被稱為中華民族魂,並且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父親周伯宜、母親魯瑞。在這一生中他寫了小說,散文,雜文,對中國現代文學貢獻巨大。
魯迅出身於沒落的士大夫家庭。1898年到南京求學,先入江南水師學堂,次年考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其間接觸了西方資產階級的“科學”與“民主”。青年時代受進化論、尼采超人哲學和托爾斯泰博愛思想的影響。1902年去日本留學,原在仙台醫學院學醫,後從事文藝工作,希望用以改變國民精神。1905—1907年,參加革命黨人的活動,發表了《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論文。1909年,與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譯《域外小說集》,介紹外國文學。同年回國,先後在杭州、紹興任教。辛亥革命後,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員、僉事等職,兼在北京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等校授課。1918年5月,首次用“魯迅”的筆名,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五四運動前後,參加《新青年》雜誌工作,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劉和珍
劉和珍,(1904一1926)女,江西南昌人。
劉和珍出生於貧民,自小養成吃苦耐勞,好學上進的品德。1918年秋以優異成績考入南昌女子師範學校。時值五四運動前夕,她受到革命思潮影響,經常閱讀《新青年》等進步書刊,認識到新的女性,肩負著改造舊中國、舊制度的責任,積極投身於反帝、反封建的實踐之中。五四運動爆發以後,如不顧學校當局的阻撓,起而奔走呼號組織同學走上街頭講演,抵制日貨,開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當時,南昌女師校規森嚴,她與進步同學一起同南昌學生聯合會聯繫,成立了女師學生自治會,學校被迫取消了不合理的校規,而帶頭人之一的劉和珍,則受到了 “記大過”處分。1921年,劉和珍繼續帶領同學們向封建勢力公開宣戰,在江西首倡女子剪髮。女師很快掀起剪髮高潮,三兩天內剪髮者不下百人,學校當局認為她"首倡剪髮,有傷風化”,被勒令退學。同年冬,劉和珍等人在南昌發起組織了進步團體“覺社”,並主編《時代文化》月刊和《女師周刊》。
女師大的校長楊蔭榆由於極力維護封建禮教而引起進步師生的不滿,於1924年11月爆發了驅楊運動,這就是我國婦女運動史上著名的女師大風潮。劉和珍作為女師大學生自治會主席,是這次風潮的主要組織者和參加者。她受同學們的委託起草驅楊宣言,撰文揭露反動文人陳西瀅的無恥抵賴,有理、有力、有節。在教育總長章士釗的唆使下,劉百昭竟然率領軍警闖進學校,僱傭女流氓打手百餘人毆傷學生,斷電、斷水、斷炊逼迫學生離校。8月10日,教育部頒發了停辦女師大的命令。
女師大“停辦”以後,在魯迅等著名教授的支持下,於西城宗帽胡同繼續開課,劉和珍等二十餘人,聯名呈文,向京師地方檢察廳公訴章士釗等人。北方革命運動不斷緊張,段祺瑞政府要員紛紛逃離北京,章士釗也逃往天津,經過艱苦鬥爭,女師大仍回師駙馬大街舊址復校,學生們整隊從宗帽胡同回校,同年12月11日正式開課,在劉和珍主持下,三百餘人召開大會慶祝鬥爭的勝利。
1926年3月12日,日本軍艦駛人我大沽口挑釁,繼而糾集列強各國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進行無理要挾。北京各界無比憤慨,劉和珍說:“外抗強權,內除國賊,非有槍不可”;“軍閥不倒,教育事業就搞不好,打倒軍閥後,我再當教師不遲。”
3月18日上午8時許,林語堂教授接到劉和珍的電話,以學生自治會的名義請準停課一日。這天,劉和珍正患病,時時嘔吐,她不顧病痛,進行動員和組織工作。她把標語小旗分發給同學們,發表了簡短而激昂的演說,然後高擎校旗,帶隊出發。女師大的同學來到天安門,國民大會尚未召開,主席台上懸掛著前一日請願被刺傷代表的血衣。會後,正午12時,兩千多民眾開始示威遊行,劉和珍擔任女師大隊伍的指揮。
鐵獅子胡同段祺瑞執政府門前的衛隊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幾個士兵對手擎校旗的劉和珍指指點點。把罪惡的槍口瞄準了劉和珍。槍聲響了,一場預謀的大屠殺開始了。頃刻間,劉和珍身中數彈,臥於血泊之中。同去的張靜淑、楊德群急撲過去救助,她說:“你們快走吧,我不行了,不要管我了。”依然是那樣溫和地關切著同學。一排槍彈射過來,張靜淑、楊德群倒在她的身邊。兇殘的士兵衝過來,復用木棒猛擊劉和珍……
劉和珍烈士犧牲時年僅22歲。
《記念劉和珍君》
魯迅先生在參加了劉和珍的追悼會之後,親作《記念劉和珍君》一文。追憶這位“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學生;痛悼“為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歌頌“雖隕身不恤”的“中國女子的勇毅”。劉和珍烈士是中華民族的好女兒,是北京師範大學人的驕傲!
原文摘錄如下
一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為十八日在段祺瑞執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群兩君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獨在禮堂外徘徊,遇見程君,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麼沒有?”我說“沒有”。她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一點罷;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
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編輯的期刊,大概是因為往往有始無終之故罷,銷行一向就甚為寥落,然而在這樣的生活艱難中,毅然預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於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卻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夠相信真有所謂“在天之靈”,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現在,卻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裡還能有什麼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它們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
二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我們還在這樣的世上活著;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離三月十八日也已有兩星期,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餘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雲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卻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為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出校之後了,才有人指著一個學生告訴我,說:這就是劉和珍。其時我才能將姓名和實體聯合起來,心中卻暗自詫異。我平素想,能夠不為勢利所屈,反抗一廣有羽翼的校長的學生,無論如何,總該是有些桀驁鋒利的,但她卻常常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偏安於宗帽胡同,賃屋授課之後,她才始來聽我的講義,於是見面的回數就較多了,也還是始終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學校恢復舊觀,往日的教職員以為責任已盡,準備陸續引退的時候,我才見她慮及母校前途,黯然至於泣下。此後似乎就不相見。總之,在我的記憶上,那一次就是永別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民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為懷疑。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還有一具,是楊德群君的。而且又證明著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著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五
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沉勇而友愛的楊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只有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還在醫院裡呻吟。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
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著血污……
六
時間永是流逝,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閒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只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陶潛說過,“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倘能如此,這也就夠了。
七
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兇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