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生平,早年生涯,學術活動,政治活動,思想,理氣觀,斥洋論,對清觀,著作,評價,
生平
早年生涯
 李恆老故居
李恆老故居李恆老(朝鮮語:이항로,1792年—1868年),朝鮮王朝後期著名的思想家、儒學家,朝鮮近代史上“衛正斥邪”思想的代表人物。初名光老,字而述,號華西,本貫碧珍。1792年(朝鮮正祖十六年壬子)二月十三日出生於朝鮮京畿道楊根郡櫱溪里,因此人稱櫱溪先生。
李恆老從3歲開始就習讀《千字文》,此後熟讀四書五經,很年輕就名噪一時。1808年(朝鮮純祖八年),李恆老入漢城(今首爾)參加科舉考試,一位宰相派人給他捎話說:“只要與我兒子交遊,你今年就可以及第。”被李恆老拒絕。李恆老雖然考中了泮試(一種別試),但因目睹了官場和科場的腐敗,認為“此非士子涉跡之地”,所以不再應舉,回到家鄉,專心鑽研學問。
學術活動
李恆老到40歲左右時,已是“學德明尊”。朝鮮政府曾在1840年(朝鮮憲宗六年)徵召李恆老為參奉,但他沒有接受,立志傳道,於是“廣開門庭,士赴若渴”,從而形成了在朝鮮王朝末期有巨大影響力的“華西學派”。李恆老篤信程朱理學,學宗宋時烈,因此他的學說也一脈相承了宋時烈所倡導的尊周大義和北伐論。1836年(憲宗二年),李恆老前往忠清道清州參拜宋時烈墓,併入華陽洞瞻仰萬東廟,他當時“坐泣弓岩,涕簌簌下”,又有詩云:“天造皇明享帝山,陪臣壁立死生間。一線殘陽猶在此,春光何日遍區寰”。1863年(朝鮮哲宗十四年),李恆老題壁述志:“承羲黃堯舜禹湯文武孔顏孟朱宋之統緒,緒立五常五倫天地人物之本體,死生不足以動其心,貴賤不足以易其守,古今不足以限其至”,明確表達了他繼宋時烈之後、以儒家道統自任的志向。 李恆老畫像
李恆老畫像
 李恆老畫像
李恆老畫像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李恆老開始率領其門人進行一些著述活動。李恆老作詩將其目標概括為“朱書擬輯東儒說,青史行刪北帝編”,所謂“朱書擬輯東儒說”說的是李恆老收集朝鮮儒者對朱熹著作的註解達20餘家,欲整理成書但又精力不支,遂於1846年(憲宗十二年)將此項任務交給自己的長子李埈,最後編成《朱子大全集札》20冊。而“青史行刪北帝編”則是指1852年(哲宗三年),李恆老命弟子柳重教編《宋元華東史合編綱目》,該書刪除了明朝商輅《續資治通鑑綱目》中元朝的正統地位,以彰顯尊周大義;同時又將高麗歷史寫入其中,表現“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春秋之意”。
政治活動
1862年(哲宗十三年)發生李夏銓之獄,李恆老被誣告入獄,後又被釋放。這是李恆老初次涉入政治,其後則漸漸頻繁。朝鮮高宗即位後,左議政趙斗淳於1864年(高宗元年)推薦李恆老入仕,稱讚他“早從事於性理之學,開門受徒,到老靡倦”,朝廷乃除授其掌苑別提的官位,後又授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掌令,李恆老均上疏辭退。
1866年(高宗三年),法國侵略朝鮮,史稱“丙寅洋擾”,左議政金炳學於此時推薦李恆老,朝廷乃拜李恆老為同副承旨,提供快馬,令其火速來漢城就任。起用李恆老的目的是利用他的衛正斥邪思想來為當時攝政者興宣大院君李昰應的抗法斥和政策宣傳造勢,但李恆老對於當時大院君大興土木重建景福宮、苛捐雜稅搜刮民脂民膏、裁撤書院關閉萬東廟等做法極其不滿,因而他雖應召進京,卻呈上一道《辭同副承旨兼陳所懷疏》,他在該奏疏中極力主戰,稱:“謂洋賊可攻者,國邊人之說也;謂洋賊可和者,賊邊人之說也。由此則邦內保衣裳之舊,由彼則人類陷禽獸之域,此則大分也”,同時又以高句麗擊退隋煬帝和唐太宗、高麗擊退紅巾軍的事例來強調凝聚人心的重要性,暗喻當前大院君的政策已失去人心,因此呼籲“停土木之役,禁斂民之政,去侈大之習……表里一致,孚信旁達,則民力大紓”,並警告道:“苟為不然,上失君子之心,下結小民之怨,日往月來,不知所以反之。則雖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前知預計之士日效其能,無救於土崩瓦解矣”。這道奏疏並非空談愛國,而是強調“內修”才能“外攘”,洋洋灑灑一千七百餘字,傳誦朝野,“時稱百年以來第一名疏”。同年九月十三日,李恆老在昌德宮重熙堂接受高宗召見,再次表達辭職的願望,並希望高宗堅持斥和主戰的政策。李恆老雖在上疏中婉轉批評大院君的政策,但大院君對上疏中斥和主戰的主張非常滿意,於是擢升李恆老為工曹參判,並讓他參與政府事務。李恆老連上四疏,請求辭職,同時申明“內修外攘”的道理。十月,李恆老的弟子梁憲洙打敗法軍,法國撤退,丙寅洋擾結束,李恆老失去利用價值,大院君也就批准了他的辭職請求,於是李恆老重返鄉間。在最後一次上疏中,李恆老強烈要求恢復祭祀明朝皇帝的萬東廟,但自然不可能得到大院君的同意。此次丙寅洋擾中的經歷也成為李恆老一生中唯一一次正式出面的政治活動,而影響卻頗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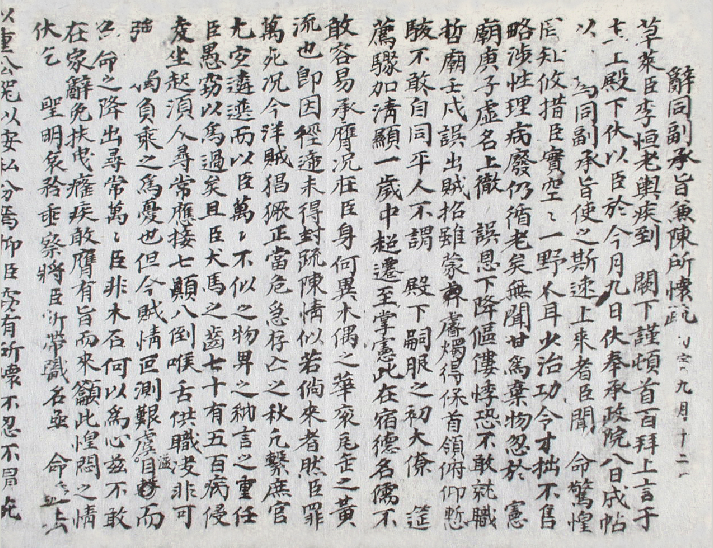 李恆老名疏《辭同副承旨兼陳所懷疏》
李恆老名疏《辭同副承旨兼陳所懷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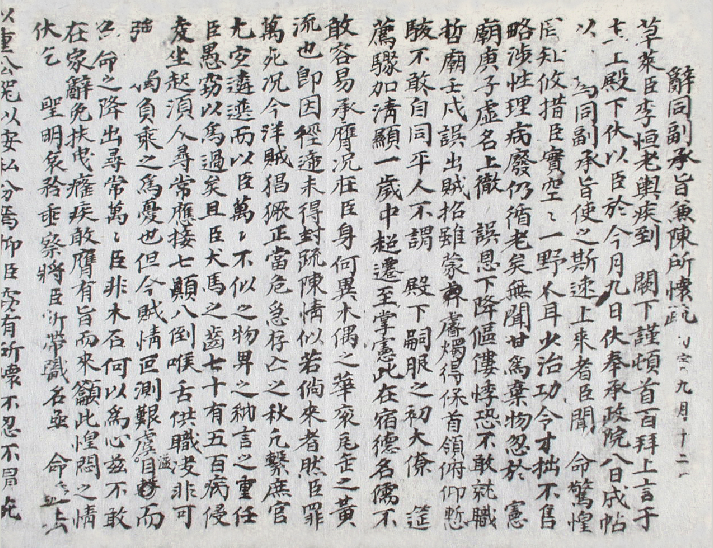 李恆老名疏《辭同副承旨兼陳所懷疏》
李恆老名疏《辭同副承旨兼陳所懷疏》思想
理氣觀
正如前文所述,李恆老信奉程朱理學,學宗宋時烈,以儒學道統自居,因此沿襲了理學思想及宋時烈所倡導的尊周大義和北伐論,帶有濃厚的小中華思想。同時又在朝鮮王朝末期的特殊背景下加入了新的內容。在理氣問題上,他提出“理氣二元論”,認為理氣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指出:“理外無氣,氣外無理”“天下無有理無氣之物,無有氣無理之物”。但是,他又認為理和氣不能等量齊觀,歸根到底還是堅持朱子學的“主理說”,認為“理為至善至中之準則,而氣為偏倚過不及之緣由,此則不可雜之說”,並強調“理為主,氣為役,理為公,氣為私之等,則本分已判,更不容移動”,因而提出了“理主氣客”、“理主氣役”的觀點。李恆老認為,如果“理”為主而“氣”為客的話,萬事皆可被駕馭,天下安樂;萬一“氣”為主而“理”為客,則萬事擾攘、天下大亂。他認為自己所處的是一個“氣”蔓延的時代。因此,他以“主理論”武裝自己的精神,希望解決時代的危機。
斥洋論
李恆老的理氣觀是其“衛正斥邪”、“尊華攘夷”思想的哲學基礎,而“衛正斥邪”、“尊華攘夷”(簡稱“衛斥尊攘”)又是李恆老及其華西學派思想的核心。李恆老強調:“尊中華,攘夷狄,窮天地之大經;黜己私,奉帝衷,有聖賢之要法”,此句話被華西學派奉為圭臬。李恆老的思想雖與朱熹、宋時烈一脈相承,但時代背景不同,具體內容也就不同。朱熹所斥的是金國,宋時烈所斥的是滿清,而李恆老所斥的則是西洋。當時天主教已傳入朝鮮,早在1836年(憲宗二年),李恆老就針對洋教之禍專門論述。李恆老認為朝鮮是中華,滿清是夷狄,西洋是禽獸,並將天主教定性為窮凶極惡的“邪教”,痛斥“充塞仁義、惑世誣民之說,何代無之?亦未有如西洋之慘!”因此要“衛正斥邪”。李恆老反對西洋的依據就在於他的理氣觀,他指出:“吾儒之所事者,上帝也;西洋之所事者,天主也。……吾所謂上帝者,指太極之道也。”而“西洋則不然,不問天所以命我者是何事,只以拜天祈福為事天。此無他焉,吾儒所謂事天之天,專以道理言也;洋人所謂事天之天,專以形氣情慾言也。二者之不同,實分於此。”也就是說,李恆老認為儒家所崇拜的天是指“理”(太極之道),而西洋所崇拜的天使指“氣”(形氣情慾),這是兩者的根本差別,因此他認為西洋紊亂人倫,與之誓不兩立。李恆老疾呼:“西洋亂道最可憂,天地間一脈陽氣在吾東,若並此被壞,天心豈忍如此?吾人正當為天地立心,以明此道,汲汲如救焚,國之存亡猶是第二事。”也就是說,李恆老認為保全“天地間一脈陽氣”(即明亡後由朝鮮所繼承的中華文化)比朝鮮國家的存亡還重要。
那么,如何抵禦西洋呢?李恆老並未提出軍事上的主張,而是強調“內修外攘”,特別是禁用洋物。他認為“禁絕洋物為內修之機要”,指出“夫洋物之來,其目甚多,要皆奇技淫巧之物,而於民生日用不惟無益,為禍滋大者也。……且況彼之為物也,生於手而日計有餘;我之為物也,產於地而歲計不足。以不足交有餘,我胡以不困?以日計接歲計,彼胡以不贍?”因此他建議國王“一有洋物介於其間,則悉行搜出,聚之闕庭而燒之”,並將使用洋物者處以重刑。他說“身修家齊而國正,則洋物無所用之,而交易之事絕矣;交易之事絕,則彼之奇技淫巧不得售矣;奇技淫巧不得售,則彼必無所為而不來矣。此與誅捕征伐本末相資,表里相因,不可不加之意也。”他自己也身體力行,“平生身不著洋織,家不用洋物”。後來他的弟子崔益鉉在反對同日本簽訂《江華條約》的上疏中也重申了洋物的危害。“衛正斥邪”是當時朝鮮儒林的共識,只是李恆老的華西學派最為突出罷了。
對清觀
李恆老雖然反對西洋,但並不代表他放棄了對滿清的敵視。李恆老仍秉持宋時烈所倡導的尊周大義和北伐論,主張時機成熟後北伐中原,驅除韃虜,恢復大明。他為華西學派所制定的規矩中其中一條就是:“北虜毀裂衣冠,西鬼蠱惑心術,當挺身立腳,明心張目,不墜聖賢之教、父祖之業,是儒者徹上徹下法門。”也就是說,“北虜”(滿清)和“西鬼”(西洋)是他“尊華攘夷”的共同鬥爭對象,只是在他所處的時代下西洋上升為主要矛盾而已。然而當時朝鮮大部分人已默認滿清為中華正統,李恆老對此感到非常憂慮。有人勸李恆老用清朝年號,被他嚴拒。李恆老認為朝鮮之所以不能北伐,就是因為不講尊華攘夷之義,“倘使我國之士民家家而講尊攘之義,人人而講尊攘之義,則夷狄無所容身,而孝廟(朝鮮孝宗)之志伸矣;孝廟之志伸矣,則華夏之運啟矣”。當時太平天國反清的訊息傳入朝鮮,有人認為不應該在此時背棄清朝,這種觀點被李恆老斥為“為北虜守節”,他說:“使斯人(洪秀全)掃清夷狄,君長天下,則我國當用圃隱(鄭夢周,高麗末年親明派)之義,背北胡而向真主可也;彼或復拾崔瑩(高麗末年親北元派)之餘論者,天地之罪人也!”與此同時,李恆老具有濃厚的小中華思想,他與歷來的朝鮮儒者一樣,認為“至若我東,素以禮義之邦稱‘小中華’,自崇禎以後,周禮實在東魯”,即明亡以後朝鮮才是中華文化的傳承者。 宋元華東史合編綱目(簡稱華東合編)
宋元華東史合編綱目(簡稱華東合編)
 宋元華東史合編綱目(簡稱華東合編)
宋元華東史合編綱目(簡稱華東合編)基於以上觀點,李恆老組織門人編輯了《宋元華東史合編綱目》,一方面將元朝攆出中國正統,另一方面將高麗歷史(即“東史”)編入中國史中。前者是為了彰顯尊周大義,而後者則引起爭議,李恆老對此解釋道:“我東,中國之屬國也。自高麗時,駸駸然知尊周之義,有變夷之實,而至我朝則純如也。又自圃隱先生倡程朱之學於麗季,以至我朝一二先覺,擴大推明,以承統緒,則古所謂進於中國者,莫如我東。而其在神州陸沉、西洋昏墊之時,正如重陰之底,陽德來復也。又當表章於始,昭布百代,示法四裔也。”也就是說,他這么做是為了表彰高麗的“用夏變夷”、“進於中國”,符合春秋大義。李恆老編《宋元華東史合編綱目》無疑是想以蒙元和高麗來影射滿清非正統而朝鮮又是中國文化的繼承者,體現出他的文化優越感。但李恆老並不因此盲目地自我感覺良好,儘管他在《宋元華東史合編綱目》中削去了元朝的正統地位,卻並未將高麗列為正統,而將這段時間作“無統”處理,說明他仍不敢僭越。同時他又指出:“清俗雖腥膻,享國長久,亦有規模故也。我國上自朝廷,下至閭里,只是無規模,所以不可為國。”可見李恆老並非如某些小中華思想膨脹的朝鮮人那樣夜郎自大,仍清楚地認識到朝鮮不如滿清的現實。
著作
李恆老的遺著有《華西集》(原集32卷、附錄9卷,合22冊)、《華西雅言》12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