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年表
1、1901年11月9日生在
湖北黃梅,家境殷實自幼多病,童年受傳統私塾教育,13歲入學黃梅八角亭初級師範學校。
 廢名
廢名2、1917年考入國立湖北第一師範學校,接觸
新文學,被新詩迷住,立志“想把畢生的精力放在文學事業上面”。畢業後留在武昌一所國小任教,期間開始與
周作人交往。
3、1922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英文班,開始發表詩和小說。在北大讀書期間,廣泛接觸新文學人物,參加“
淺草社”,投稿《
語絲》。
4、1925年10月,廢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
竹林的故事》。
5、1927年,
張作霖下令解散北大,改組京師大學堂,廢名憤而退學,卜居西山,後任教成達中學。
6、1929年,廢名在重新改組的北平大學北大學院英國文學系畢業,受聘於
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任講師。次年和
馮至等創辦《
駱駝草》文學周刊並主持編務,共出刊26期。此後教書,寫作,研究學問,抗日戰爭期間回
黃梅縣教國小,寫就《阿賴耶識論》。
7、1946年由
俞平伯推薦受聘北大國文系副教授。
 俞平伯
俞平伯8、1949年任北大國文系教授。
9、1952年調往長春東北
人民大學(後更名為吉林大學)中文系任教授。
10、1956年任中文系主任,先後被選為吉林省文聯副主席,吉林第四屆
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吉林省政協常委。
11、1967年10月7日,因癌症病逝於長春。
傾心佛禪
廢名與禪的因緣大致可以從兩個方面去探尋。
 廢名
廢名廢名1901年出生於湖北省黃梅縣城,黃梅自隋唐以降,便成為佛教興盛之地,有關
四祖道信、
五祖弘忍、
六祖惠能的故事,在黃梅家喻戶曉,甚至弘忍大師本人就是黃梅當地人,中國禪宗正是在這裡通過這些大師們的付法傳衣而 最終走向成熟。縣城附近,東山寺、
五祖寺、東禪寺這些佛教對地仍香火不絕。由於出生在這樣一個濃厚的禪宗文化氛圍之中並整整生活了17年(1917年廢名才離開黃梅到武昌求學),廢名從小對黃梅的禪宗聖地嚮往之至:“五祖寺是我小時候所想去的地方,在大人從四祖、五祖帶了喇叭、
木魚給我們的時候,幼稚的心靈,
四祖寺、五祖寺真是心嚮往之。”(註:《馮文炳選集·五祖寺》,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在事隔近40年以後,廢名在他的《
五祖寺》一文中仍能清楚地記得他第一次被外祖母帶著上五祖寺進香還願時的情景。他還經常到寺廟裡去觀傳戒禮,這種對禪宗文化的生動的感性認識與鮮活的情感,為以後廢名禪宗思想的自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像所有同時代的青年一樣,基於對新文化的嚮往與憧憬,1922年秋廢名考入
北京大學預科英文班。在北大他結識了當時大名鼎鼎的
胡適、
周作人等人。胡適其時正在撰寫
中國禪宗史,對來自禪宗聖地的黃梅人廢名自是十分感興趣,他經常邀廢名到家裡去喝茶聊天,談禪論道。據
郭濟訪《夢的真實與美——廢名》記載:有一次,胡適突然問廢名:“你們黃梅五祖到底是在馮茂山,還是馮墓山?我在
法國圖書館看敦煌石窟發現的唐人寫經作馮墓山。”廢名根據自己兒時的有關記憶作了回答,引起了胡適的高度注意。正是這樣的一些交談,使廢名大開眼界,他開始認識到了家鄉黃梅在歷史文化史上的重要價值,可以說正是帶著這樣的一種自豪感,廢名開始了對於佛禪之學的自覺的認識與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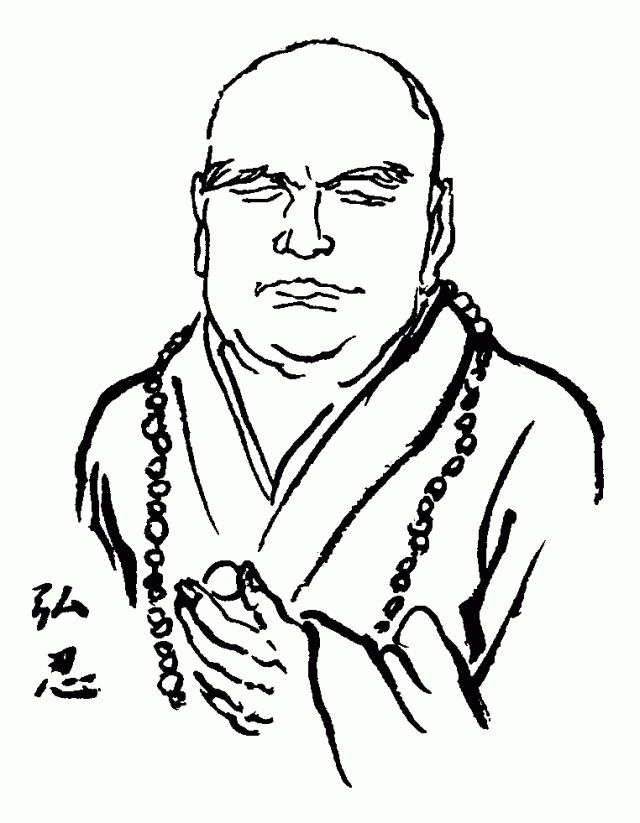 禪宗大師弘忍
禪宗大師弘忍也幾乎是在同時,廢名與
周作人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此時的周作人思想上正發生著重大轉變,逐漸地由“流氓鬼”向“紳士鬼”過渡,追求沖淡平和的佛道一路,正如沈從文所評價的那樣,周作人這種“用平靜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動靜,從為平常眼睛所疏忽處看出動靜的美”的紳士作風實在是有些“僧侶模樣”(註:
沈從文:《論馮文炳》)。事實上周作人已開始研讀大量的佛教經典,他甚至在北大國文系講授“佛教文化”課程,並常自詡為在家和尚。後來,他曾給廢名寫信說:“一月三十日夢中得一詩云,‘偃息禪堂中,沐浴禪堂外,動止雖有殊,心閒故無礙’。家中傳說不佞前身系一老僧,今觀此詩其信然耶,可發一笑。”眾所周知,廢名與
周作人之關係非他人所能比擬,周作人包寫廢名小說集所有的序言即可為證。周作人對於佛禪的興趣,不能不啟發並促進廢名對於禪學的進一步的自覺。
到這時,在
胡適、
周作人等人的啟發下,廢名從小潛在著的家鄉的禪文化影響被充分地激活了,廢名與禪的因緣更加密切而牢固。
佛學研究
廢名對於佛學有相當的研究,著有《阿賴耶識論》,專門探討佛學中的唯識論。不過,他的
哲學研究並沒有受到注意。周作人說“隨後他又談《
論語》、《
莊子》,以及《
佛經》,特別是佩服《
涅槃經》,不過講到這裡,我是不懂玄學的,所以就覺得不大能懂。”廢名寄
哲學論文給周作人,沒能得到回應,令他很失望。
 卞之琳
卞之琳詩人
卞之琳說“1949年我從國外回來,他把一部好像詮釋什麼佛經的稿子拿給我看,津津樂道,自以為正合
馬克思主義真諦。我是凡胎俗骨,一直不大相信他那些‘頓悟’,……無暇也無心借去讀,只覺得他熱情感人。”語氣略帶諷刺,這是對佛學缺乏興趣的人的話。
學者
張中行也研究佛學,他說廢名“同熊十力先生爭論,說自己無誤,舉證是自己代表佛,所以反駁他就是謗佛。這由我這少信的人看來是頗為可笑的,可是看到他那種認真至於虔誠的樣子,也就只好以沉默和微笑了之。”
態度也和卞之琳類似。
只有
熊十力,雖然和廢名觀點全然不同,但願意和他激烈辯論,甚至打架。
思想形成
廢名禪學思想在其形成發展過程中經歷了比較明顯的兩個階段。
從20年代中期受胡適影響開始接觸禪宗到30年代初可以視作第一階段。廢名的好友兼同鄉程鶴西在回憶他1928 年北大退學後在成達——
孔德中學任教的情景時說:“在成達時我記得他曾請馮至同志把
施耐庵的《水滸傳》序寫成一個橫幅掛起,這也是我喜歡《水滸傳》序的開始,後來讀庾信的詩賦和維摩詰經也是受他的影響”(註:鶴西:《懷廢名》。)。從這裡至少可以見出,其時廢名是很喜歡《維摩詰經》的。《維摩詰經》是由漢魏時期高僧
支謙翻譯的一部佛教經典,它對於大乘禪學特別是中國
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曾起過很重要的作用,它與《楞伽經》、《圓覺經》一起有“禪門三經”之稱。《維摩詰經》強調,要達到解脫,關鍵在於主觀修養,淨化心地。後來另一位高僧鳩摩
羅會重譯此經將其思想表述得更其明白:“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廢名對《維摩詰經》的喜愛,恐怕是被其“淨心”一論所傾倒。前面提到的《水滸傳·序》中“虛名薄利不關愁,裁冰剪雪,談笑看吳鉤”以及庾信的“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均與“淨心”論交相輝映,怪不得為廢名所鐘愛了。
作為黃梅之子,在接近禪學之初廢名不可能不接觸四祖、五祖之禪學思想,特別是對於廢名來說,是先有四祖、五祖才有禪宗的(儘管六祖在黃梅承衣受法,但他旋即到南方講學,加上六祖系廣東人,因此,在黃梅一帶,人們更多地是談論四祖尤其是五祖)。廢名曾在許多文章中提到五祖、五祖寺,而五祖弘忍依《楞伽經》發揮而成的《最上乘論》正是強調“守本真心”、“守心住境”、“息妄修心”,這一思想與前述《維摩詰經》“淨心”思想是一致的。後來被弘忍大師視為教授並引為上座的弟子神秀所作一偈可視作是對四祖、五祖等楞伽禪觀的形象性概括,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總之,此一階段廢名的禪意主要表現為對觀心看淨,超越世俗的虛靜境界的凝視與憧憬。
30年代起一直到整個40年代,可以視作廢名禪宗思想發展的第二個階段。事實上廢名思想上的轉變在30年代前的二三年早就已開始。1927年冬
張作霖解散北大,
周作人被辭退,作為學生的廢名忿然退學。這一選擇使他頓時成為了流浪漢,經常是吃了中飯,晚飯尚無著落。他被迫卜居西山。這時的廢名一面繼續看書,一面卻不得不從“觀心看淨”的夢中醒來直面現實人生,夢破以後又將在何處找尋自己的心靈歸宿?
正是帶著這樣一種思想上的痛苦與“凌亂”,廢名於1929年結束了學生生涯,做了北京大學國文系講師。生活的挫折,對社會的了解的加深,特別是出於講課的需要,他開始重新大量地閱讀
中國古典文學(大學階段廢名學的是英文),《論語》、《孟子》、《老子》、《莊子》都成為他尋找思想擴大認識的依據,再加上這一時期他更加潛心學佛,“轉入神秘不可解的一路去了”,這一切,促使了廢名思想上的新的變化。廢名曾經在他的
自傳體小說《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談到莫須有先生的思想:他的道理只要一句話夠了,一句話無所不包。這個能“一言以盡之”的道理是什麼呢?他說:“心如一棵樹,果便是樹上結出來的道理,道理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了”。“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是六祖惠能那首著名的偈中的後兩句,原偈前面還有兩句為“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從這裡可以見出,作為廢名自己化身的莫須有先生對於惠能是心有所會了。周作人《〈談新詩〉序》曾提到廢名道法的高超並提及其讀書的情況:“隨後他又讀《論語》、《莊子》,以及佛經,特別是佩服《涅槃經》。”而據《曹溪大師別傳》與
王維《六祖能禪師碑銘》載,惠能在
弘忍之前曾有過一段學佛的經歷,特別是曾聽無盡藏尼誦《涅槃經》並為之釋之,由此而初步形成了自己對佛性問題的見解。惠能在論《涅槃經》時引入了莊子無物無情無待與忘物忘己忘適的接近般若中道的思想,他把莊子的思想注入自己的血液,化成禪學的有機體而形成了自己融般若與涅槃為一體的非有非無的南宗禪思想體系。廢名喜讀《莊子》又佩服《涅槃經》不正可以視作與惠能禪接近的極好旁證?
個人作品
上海開明書店1931年版,廢名: 《棗》
 《廢名集》
《廢名集》上海開明書店1932年版,廢名: 《橋》
上海開明書店1932年版,廢名: 《莫須有先生傳》
北京新民印書館1944年版,廢名、開元:《水邊》
漢口大楚報社1945年版,廢名著、開元編:《招隱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廢名著、開元編:《廢名小說選》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馮文炳:《馮文炳選集》
中國華僑出版社2010年版,廢名著,黎娜編《菱盪》
作品特點
一是散文化傾向。廢名的詩往往是興筆所致,揮灑自如,行乎當行,止乎當止。同時廢名又是運用經濟的文字,廢名說:“我過去寫的新詩,比起隨地吐痰來,是惜墨如金哩!”(廢名:《談談新詩》)廢名將古文言字詞運用到新詩的語句當中並活用典故,即是極大的嘗試和探索。如“我學一個摘花高處賭身輕”,將
吳梅村的詩句直接引入,嫁接得多么自然,毫不費力氣。
 張作霖
張作霖二是以禪寫詩。1922年廢名懷著一顆極大的嚮往之心來到北京,不久卻是面臨新文學陣營分裂、論爭之時,於是 陷入極度苦悶之中。隨後1927年
張作霖率軍進入北京,北平文人紛紛南下,北方文壇顯得格外冷清寂寞,廢名不能“直面慘澹的人生”,心理由苦悶趨於封閉,性格更內向,思維方式側重於內省,在急劇變化的時代洪流中廢名找不到可辯清方向的思想作指導,於是躲進西山參禪悟道。
汪曾祺、
卞之琳都曾以此時的廢名為原型刻畫一個“深山隱者”形象。此時廢名思想藝術的變化很明顯表現在他的小說《橋》和《莫須有先生傳》上,以至他的朋友
溫源寧教授懷疑他受英國的
詹姆斯·喬伊斯、
維吉尼亞·伍爾芙等小說大家的影響,然而不單是小說,這一變化也表現在這一時期的詩歌上。至此廢名詩風大變,內容頗費讀者猜詳。廢名以禪寫詩,讀者應該以禪讀詩。
蘇軾說:“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
嚴羽在《滄浪詩話》中也說:“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廢名的許多詩句看似半通不通,無邏輯可言,其實他的詩像
李詩溫詞一樣,表面不能完全文從字順,但骨子裡的境界卻是
高華的,“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像”,像“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誰又能只通過字面而不藉助想像和領悟去理解呢?廢名大約是最早將禪引入新詩的詩人,1947年
黃伯思在《關於廢名》中指出:“我感興趣的還是廢名在
中國新詩上的功績,他開闢了一條新路……這是中國新詩近於禪的一路。”廢名的這些詩大多成於一時,“來得非常之容易”,有的是吟成的遊戲之作,不可與之較真,亦不可輕易放過,因為裡面“實在有深厚的力量引得它來,其力量可以說是雷聲而淵默”。如“我倚著白晝思索夜/我想畫一幅畫/此畫久未著筆/於是蜜蜂兒嚶嚶地催人入睡了/芍藥欄上不關人的夢/閒花自在葉/深紅間淺紅”。廢名的詩像晚唐詩詞一樣有“擔當(寂寞)的精神”和“超脫美麗”(廢名:《關於自己的一章》)。
三是美與澀的交織。廢名的詩美是天然的,詩情是古典的,往往令讀者有一種丈二和尚摸不找頭腦的美麗,有仿佛得之的感覺。這是廢名的詩晦澀的表現。廢名的詩融儒釋道為一體,並有現代主義之風,使得廢名的詩成為一個獨特的存在。廢名就曾以《掐花》為例說它是“新詩容納得下幾樣文化的例證”(廢名:《〈小園集〉序》)。廢名有的詩確實難懂,如“黃昏街頭的楊柳/是空中的鏡子/對面小鋪子的電燈/是寂寞的塵封/晚風將要向我說一句話/是說遠天的星么”。真是詩人將要囈語,是說一首詩么?
抗日戰爭勝利後,廢名再一次經歷思想大變,這一時期儘管只有四首小詩,卻不可小覷。廢名經歷九年跑反、避難,開始同情於“人類的災難”,痛恨於“人類的殘忍”,呼籲和平,詛咒戰爭,追求真理。
作品思想
廢名禪學思想由“觀心看淨”到“無相無念無住”的轉變,導致其創作由空靈靜寂轉向自由灑脫,呈現出不同的風格特徵。
《竹林的故事》、《桃園》、《棗》、《橋》是第一階段的代表作。這一時期的小說從整體上看是遠離現實人生和當代社會問題的,即使有,卻也何其微弱,尤其是越到後來,我們幾乎找不到半點當時甚為時尚的作家主觀的對於現實人生的哀愁或者抗議。《菱盪》所描繪的完全是一幅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
世外桃源。小說《橋》更是廢名精心營造的通向寧靜禪境的美麗橋樑。作品中的史家莊,處處是“
東方朔日暖,
柳下惠風和”式的平和寧靜,人們男耕女織、知足常樂,人性淳美,古風習習。小林、
琴子、細竹無論是兒時還是長大後均天真、純樸,他們和睦相處,一反一般小說中所描寫的那種三角戀愛的生活模式,絲毫沒有情人與情敵之間的種種猜測、懷疑與色心斗角。廢名只為我們提供了一幅幅靜美的中國畫,卻並不引導人們去著力思考社會現實問題。
靜寂意境的營造是這個時期小說的另一個美學特徵。《菱盪》中的
陶家村一年四季總是那樣的寧靜,它深藏在茂密的樹林之中,一道河水,一個水洲使它遠離縣城的喧囂與熱鬧,偶爾聽得見深林中斧頭砍樹的聲響,水的唧唧聲以及聾子、張大嫂們那些似斷非斷的三兩聲打趣,給人一種“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的感覺,一切最終還是消融在無垠的靜謐之中。廢名筆下的人物大多是老人、孩子及天真少女,即使是青壯年卻也是半聾半啞,如《菱盪》中的陳聾子,《橋》中的三啞等,他們的單純、質樸、少受塵世污染,更具自然本性,他們沒有如簧的巧舌去製造那些令人作嘔的噪音,他們精神豐富而形式卻簡單寧靜。陳聾子便具有極強的象徵意義,因為耳聾,他的世界永遠是寧靜的,塵世的噪音唯他能充耳不聞,也不見他輕易說話,唯其如此,他才能真正地守自己的本真心,才能自由地去體認世界萬物的真如本相。在靜中瀰漫著一股孤獨、清冷的氛圍,透露出一種孤寂之感,是廢名意境的重要特點。在廢名作品中,他大量使用墳、送路燈、
落日、簫、孤雁、廟檐上的風鈴、碑、樹蔭等意象符號,以造成一種神秘、清幽、孤獨的氣氛。《橋·習字》寫小林看雁陣,也引發出一種孤獨之感:“遠遠兩排雁飛來,寫著很大的‘一人’在天上,深秋的天氣,沒有太陽,也沒有濃重的雲,淡淡的兩手撫著母親的發,儘儘的望。”仿佛那天底下便只有這“一人”了。小林一開始認字便是這“一人”二字,在廢名也許是頗有深意的。
 《廢名選集》
《廢名選集》廢名這一時期的創作消解現實意義,隱逸了情感傾向,突出的是靜寂的詩的意境,而構成這靜寂意境“境眼”的便是作品中所表達的對於自然、人生的直覺與頓悟。廢名小說可以說是直覺的
大串聯,《菱盪》中這樣寫菱盪的水:“如果是熟客,繞到進口的地方進去玩,一眼要上下閃,天與水。停了腳,水裡唧唧響,——水仿佛是這一個一個的聲音填的!”在廢名小說里,我們隨處都可以看到通感與聯覺的運用,如“草是那么吞著陽光綠,疑心它在那裡慢慢的閃跳,或者數也數不清的唧咕”,由視覺而聽覺,二者融為一體,這種通感,聯沉正是直覺思維的一個重要特徵。
廢名的語言是跳躍式的,簡潔而空靈,因其空靈,如果沒有充分的聯想、想像,句與句,段與段之間就會產生一種“隔”的感覺,令讀者如墜雲裡霧裡。比如寫花
紅山,“沒有風,花似動,——
花山是火山!白日青天增了火之焰。”如果說前一個比喻“花山是火山”還不是很出格的話,後一個比喻卻如同飛來巨石,一不留意便會砸得暈頭轉向。廢名這樣的一種語言的獨特性與他強調主體的感覺、頓悟直接相關。要傳達出獨特的感覺必須需要獨特的語言。因此,在廢名那裡,獨特的語言與獨特的感覺是那么渾然地融為一體。
第二階段的主要作品是小說《莫須有先生傳》、《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兩個未完成的長篇以及部分詩作與散文。現實性加強是此一時期創作的一個重要變化。在前期他儘量迴避、淡化甚至消解作品中的現實功利意義,儘量為自己營造一個寧靜的“夢”境,但之後我們從廢名作品中又重新可以看到社會與時代的影子,又重新可以感到社會現實所賦予作者的喜怒哀樂,正如莫須有先生所說:“世上沒有一個東西不乾我事,靜極卻嫌流水鬧,閒多翻笑白雲忙。”《莫須有先生傳》儘管在創作時間上與《橋》相去不遠,但即使是在寫《橋》的時候,廢名的思想也已開始顯得“凌亂”,一方面,他留戀於“拂塵即淨”的“夢”,那便是《橋》,另一面卻又顯示著對現實實有世界的莫大興趣,預示著其思想上將朝著新的一路發展,《莫須有先生傳》便是這種思想的產物。《莫》是一部在風格上 與《橋》截然不同的作品。廢名曾稱他的《莫須有先生傳》是學習莎士比亞和《堂·吉訶德》的結果,他在與鶴西的一封通信中說:“我是想到了
莎士比亞與西萬提斯他們兩位。他們似乎不象Flaubert那樣專心致志做文章了,只是要碗飯吃。他們真是‘頂會作文章的人’!他們的文字並不是做得不多不少,你不可以增減一字,他好象就並不在乎,而我們在這裡看得見一個‘完全’的人了。頂會作文章的人大概就是一個生活的能手,乘風破浪,含辛茹苦,隨處可以實驗他的生存的本領,他大概是一個‘遊民’,逐水草而居了。……
屠格涅夫說西萬提斯的《吉訶德先生》是代表一個理想派,……我的意思則適得其反,他是——他是一個‘經驗派’,耍了一個猴戲給我們看。”在廢名看來,頂會作文章的人是不避現實生活的,亦非
不食人間煙火,他應該是“逐水草而居”,應該是“經驗派”。《莫》是以作者西山卜居這一段現實生活為藍本的
自傳體作品,是現實的,卞之琳評價說“是寫他自己的‘狂人日記’,他對當時的所謂‘世道人心’笑罵由之,嘲人嘲己……自有他的‘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註:卞之琳:《馮文炳選集·序》,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廢名的“逐水草而居”很使我們想起禪師們的“飢來則食,困來即眼”的生活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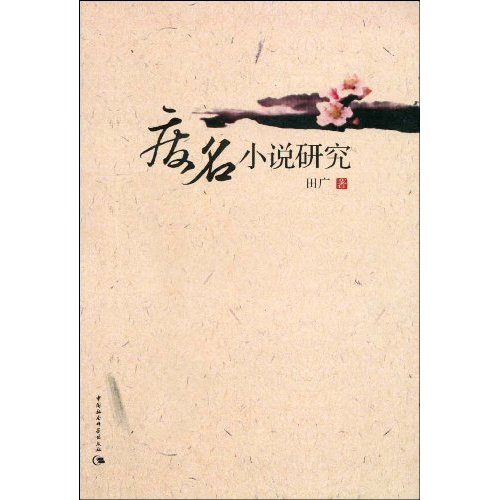 《廢名小說研究》
《廢名小說研究》對真實性的自覺追求是這一時期廢名創作的另一重要特徵。此一時期,作為整體性的“菱盪”、“橋”式的仙一般的意境在已蕩然無存。他的創作是真實的、隨意的。《莫須有先生傳》和《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除了“莫須有”的名字以外,其他都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實記錄,是自傳式的小說。如果說廢名前期的小說多寫自然之景並在其中流露出作者的體驗、感覺與直觀頓悟的話,那么,此一時期作者更多的注重敘事,並在這些自傳式的事件中滲透自己的理性思考,因而也就顯得更加真實。
廢名這一時期對於散文的鐘情亦可見他在創作上的傾向實有自然之境。因為照他的理解,散文是寫實的,非想像非虛構的,他說,“我現在只喜歡事實,不喜歡想像。如果要我寫文章,我只能寫散文,決不會再寫小說”(註:《馮文炳選集·散文》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後來他曾把他的先期的一些小說如《浣衣母》、《河上柳》等還原為散文,其目的便在於欲擺脫前期小說的虛影而使其所敘人事更原始、更真實、更具生命本相。
此一時期,語言的無所顧忌與先期簡潔、晦澀形成鮮明對照。廢名表現出來一種強烈的表現欲,他不再苦行僧式地收斂自己的情思了。其情感思辨常常毫無顧忌,毫無遮攔地傾泄出來。如果說在前期作者的情思只偶爾有些零星式的點綴的話,在《莫須有先生傳》、《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則是大段大段地抒發了。如前所述,這一時期他把更多的精力用於散文創作,理由之一正是出於一種欲更好更充分地表現自己的考慮。他把《浣衣母》《河上柳》還原成散文,也正是在這篇題為《散文》的文章中,我們看到了作者在表達自己情感思想上與小說的不同而顯得更為直接。這一時期,廢名語言的句式越來越符合常用的語法規範,語句較長,較緩,不再如先前那般短促、跳宕,用詞也力避奇僻生辣。
文學風格
廢名被認為是
周作人的弟子,在文學史上被視為
京派代表作家。代表作有《
竹林的故事》、《
橋》、《
莫須有先生傳》、《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等。廢名的小說以“散文化”聞名,其獨特的創作風格人稱“廢名風”,對
沈從文、
汪曾祺以及後來的
賈平凹等文學大師產生過影響。廢名名氣雖大,但因為晦澀難懂,讀者卻少。在文學上,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兩個著名知音。
周作人在為廢名和
俞平伯的“澀”作解釋時說“本來晦澀的原因普通有兩種,即是思想之深奧或混亂,但也可以由於文體之簡潔或奇僻生辣,我想現今所說的便是屬於這一方面。”
 莫須有先生傳
莫須有先生傳在《廢名小說選·序》中,廢名對於自己的風格有如此評論:“就表現的手法說,我分明地受了中國詩詞的影響,我寫小說同唐人寫絕句一樣,絕句二十個字,或二十八個字,成功一首詩,我的一篇小說,篇幅當然長得多,實在用寫絕句的方法寫的,不肯浪費語言。這有沒有可取的地方呢?我認為有。運用語言不是輕易的勞動,我當時付的勞動實在是頑強。讀者看我的《浣衣母》,那是最早期寫的,一支筆簡直就拿不動,吃力的痕跡可以看得出來了。到了《桃園》,就寫得熟些了。到了《菱盪》,真有唐人絕句的特點,雖然它是五四以後的小說。 ”
 俞平伯
俞平伯 廢名
廢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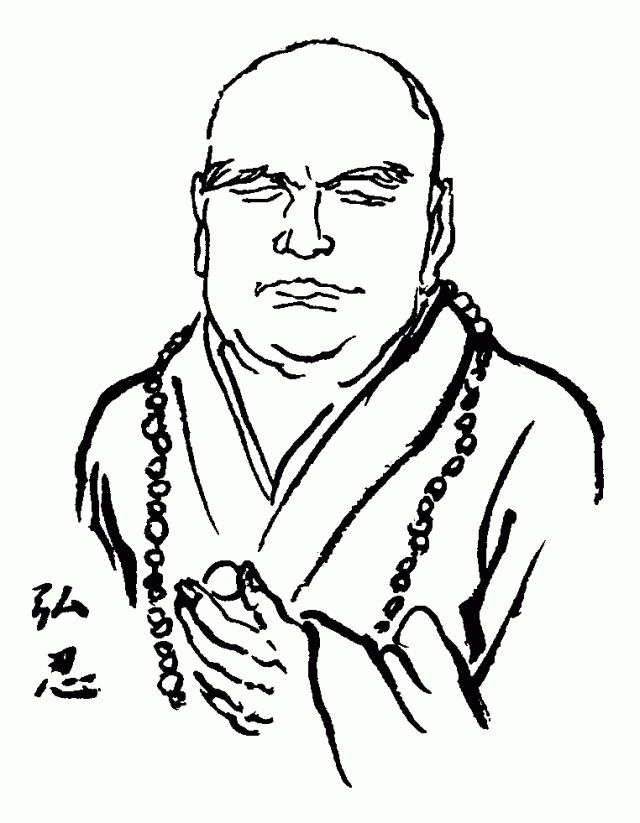 禪宗大師弘忍
禪宗大師弘忍 卞之琳
卞之琳 《廢名集》
《廢名集》 張作霖
張作霖 《廢名選集》
《廢名選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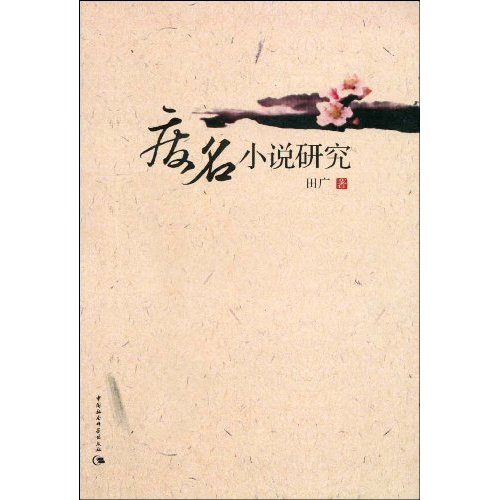 《廢名小說研究》
《廢名小說研究》 莫須有先生傳
莫須有先生傳
 俞平伯
俞平伯 廢名
廢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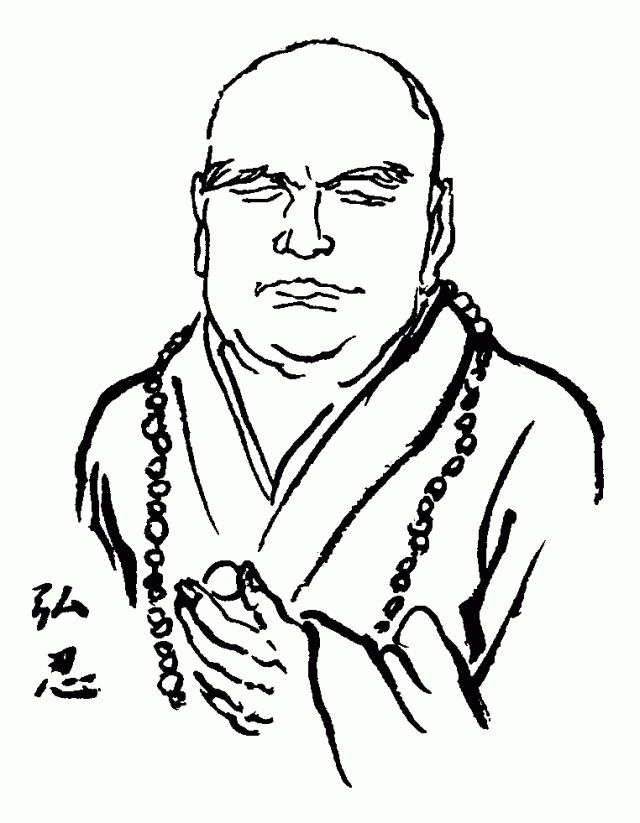 禪宗大師弘忍
禪宗大師弘忍 卞之琳
卞之琳 《廢名集》
《廢名集》 張作霖
張作霖 《廢名選集》
《廢名選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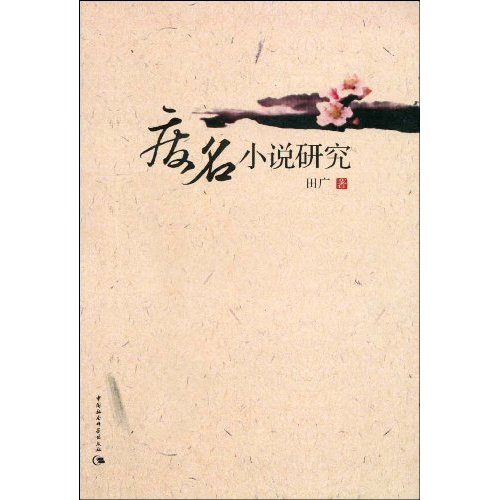 《廢名小說研究》
《廢名小說研究》 莫須有先生傳
莫須有先生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