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尋金者》是勒克萊齊奧創作的第一部帶有家族自傳性質的小說。小說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殖民統治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為背景,講述了一個發生在印度洋模里西斯的探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我”——8歲的阿力克西和家人生活在美麗而神秘的模里西斯島嶼深處,朝夕相伴於“智慧樹”、甘蔗田、星星和大海。只是好景不長,因颶風的侵襲,還有甘蔗大種植園主的吞噬,使得父親的生意破產,童年的田園生活也隨之結束。
為了重新找回昔日的幸福,阿力克西根據父親生前留下的尋寶資料,搭乘“澤塔”號輪船,踏上了前往羅德里格斯島的漫漫“尋金”路。
阿力克西飄搖於未知的大海,途經一座座傳奇的島嶼,終於抵達羅德里格斯島的英國灣。然後翻山越嶺,風吹日曬,年復一年地尋找。一次又一次,從夢想落入現實,由希望墜落於失望。有一天,他偶遇山中少女烏瑪,這位有古銅色的面龐,熔岩的顏色,閃耀著鹽的女孩讓他體驗到愛情之豐美,教他如何與自然和諧相處。“尋金”一度由於主人公奔赴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而中斷。阿力克西親眼目睹了戰爭對自然和人性的摧殘,他僥倖逃生後,又重返故地尋寶。可烏瑪卻在一場流星雨的徵兆下離開了,然而主人公依然尋金不得。主人公則獨自乘舟遠行,最後面對浩瀚的星空幡然醒悟,毅然返回了童年的故鄉。
創作背景
模里西斯
地理背景
模里西斯面積為2040平方公里,是印度洋西南部的一個島國,由模里西斯本島以及羅德里格島、聖布蘭群島、阿加萊加群島、查戈斯群島(現由英國管轄)和特羅姆蘭島(現由法國管轄)等屬島組成。海岸線長217公里。沿海多狹窄平原,中部為高原山地。亞熱帶海洋性氣候,終年濕熱。
經濟背景
製糖業是模里西斯島的主要經濟支柱之一,自18世紀以來,甘蔗一直是其主要農作物,其種植面積占年耕土地的90%左右,在模里西斯島到處可以看到青翠的甘蔗田。
一戰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年6月28日(塞爾維亞國慶),奧匈帝國皇儲費迪南大公夫婦(左圖)在塞拉耶佛視察時,被塞爾維亞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槍殺。
奧匈帝國以此為藉口,在得到德國的支援後,於1914年7月28日向塞爾維亞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戰爭主要在由德國和奧匈帝國組成的同盟國(Central Powers),和英國、法國、俄羅斯帝國和塞爾維亞組成的協約國(Allied Powers)之間進行。
作品背景
《尋金者》的故事經歷了四次地域的轉換:模里西斯本島、羅德里格島、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主人公征戰歸來的模里西斯本島。
印度洋海島的旖旎風光、一戰戰場的血腥場面、殖民地勞工辛勤勞作的場景像、地理環境的描寫構成《尋金者》小說的一大特色。
《尋金者》的社會空間主要建構在模里西斯島的甘蔗種植園上。甘蔗種植是資本主義前殖民時期剝削掠奪海外殖民地的主要實現方式。
作者的創作意圖即:把原始蠻荒的模里西斯和淪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的歐洲作為故事的物理空間進行並置與對照。作者用大海等自然意象隱喻回家的路;以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與鬥爭體現爭奪“被剝削壓迫空間——甘蔗園”的生活家園;通過對故事主人公的現代原始人形象、性格特徵、心理空間的建構與成長環境的心理映射,闡釋並隱喻終極“尋金”——其實是回歸人類的精神家園。
主要人物
阿力克西——“我”
主人公“我”——敘述者。“我”是一個成年男性。“我”的父親在“我”幼小時即去世。“我”的妹妹蘿爾、母親以及“我”在羅德里格島尋金時所遇到土著少女烏瑪。在童年的懵懂狀態里,母親對於“我”有著獨特的意義。蘿爾和“我”沒有上學,而是由母親親自教授所有課程:“‘我’已經無法說清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教育。”在與世隔絕的平靜生活里,有著母親溫柔而年輕的聲音。“我”的童年之所以幸福,並非因為物質條件富足。實際上,“我”童年時家裡過著困苦的生活,父親瀕臨破產的邊緣。
烏瑪
烏瑪是土著少女。她“父親”死後,烏瑪回到了羅德里格島。
小說中的黑人女孩烏瑪被刻畫成了具有“自然天性的夏娃”的形象。在主人公阿力克西的眼中,烏瑪渾身上下透著自然的氣息,充滿原始野性的美麗。烏瑪和其他馬納弗人一起生活在羅德里格斯島上的深山中,逃避著現代文明的影響,靠牧羊為生,過著親近自然的神秘生活。
“母親”
母親是父親從印度娶回的妻子。母親是傳統的賢妻良母一類的女性形象,專心教子,表現出溫良淑德的一面。母親始終無怨無悔,對丈夫沒有埋怨。
“父親”
“父親”是印度洋上莫里斯島(Maurice)的居民。“父親”無望地策劃著名各種注定失敗的事業,妄圖逃脫破產的命運。在一次航程中,父親病逝。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持續的生態危機,使人與自然漸行漸遠,“尋金者”在物質的誘惑中迷失了精神的家園。作家用“尋金”的小說表象,來表達對現代文明和物質主義的批判,對人的身份追尋和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思考。
《尋金者》主題思想之一:
面對西方現代文明和物質主義價值觀,通過“尋金”生態寓意和哲理,喚醒人們對永恆精神家園的追尋。
“尋金”的雙重隱喻:在“尋金”表象之下,蘊涵著豐富的自然空間意象和更為深刻的生態隱喻。人類的追求分為兩個維度:對物質富足的追求和對精神富足的追求。工業革命以前的人類傳統文明主張壓抑人的物慾,輕物質追求而重精神上的充實和滿足,追求人與自我、人與自然的和諧平衡。然而自現代文明以來,在工具理性和科技至上思維的驅使下,人類在從自然攫取更多財富的過程中,物慾變得愈加膨脹。人的精神世界也因此在物慾的消弭下變得更加空虛,被物質主義的思想侵蝕得支離破碎。於是人類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遠方的異域文明,去尋找靈魂的寄託和內心失去的幸福家園。
作為生態作家,勒克萊齊奧在《尋金者》中講述的就是一個關於迷失於物慾、找尋並回歸人與自然的和諧、回歸人的精神家園的故事。小說的主人公阿力克西在家庭遭遇了一系列重大變故後,帶著重建幸福家園的美好夢想,踏上了前往羅德里格斯島的尋金之旅。在英國灣——海盜可能的藏寶之地,他要尋找的“金”,首先當然是物質的“金”,是傳說中“不為人知的海盜科賽爾的寶藏”,是能讓阿力克西家人擺脫窘困的希望。因此,阿力克西幻想著有朝一日回來的時候“裝著父親資料的旅行箱裡,將填滿海盜科賽爾的金子和珠寶”。
作為小說中反覆出現的主題,“金”是一種意象,是“物質財富和西方的象徵”。主人公不懈地尋金之旅寓意著人類對物質追求的無盡欲望。而戰爭是人類物慾無限膨脹的極端形態。在島上4年尋寶而不得後,阿力克西參加了遠在歐洲戰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爆發在幾個西方殖民大國之間的殘酷戰爭,對自然生態和人類文明造成了巨大災難。究其起因,正是由於殖民列強在現代工業文明的驅動下“對殖民地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的爭奪”。在小說中,作者借一位生活在羅德里格斯島上山林中的馬納弗族少女烏瑪之口,表達了他對現代西方文明中扭曲的物質主義的批判:“你們其他人,上流社會,你們認為金子是最強大、最令人嚮往的東西,因此你們發起戰爭。為了擁有金子,人們四處死亡。”烏瑪用她植根於原始自然的感覺告訴人們,過度占有物質財富的欲望是導致戰爭和死亡的根源。作家借烏瑪之口,一針見血地對西方物質主義的價值觀進行了批評。這是對“金”意象黑暗一面的批判。同時,“金”也有陽光的一面,寓意人們對幸福的追求。主人公童年的幸福家園——布康傍晚金色的陽光,童年聽到的《聖經故事》封面上金色的太陽,英國灣金色的長莢果,大海上金色的波光,還有散發著“原始的美”的黑人女孩烏瑪閃耀著金屬光澤的皮膚,所有這些“金”意象的化身,代表了阿力克西心中對幸福的美好嚮往。
“金”作為物質和幸福生活的原型,在《尋金者》中無疑具有神諭和魔怪形象的雙重隱喻。物質的欲望容易遮蔽人的視野、迷惑人的心智、掏空人的內心、搗毀人的精神世界,從而呈現出魔怪的邪惡形象。
自然之美的生態隱喻:作者通過對自然元素和空間的詩意描繪,揭示了親近自然、感受自然的原始和諧之美才是尋找的真諦,是擺脫物質主義遮蔽、回歸人的自然天性的重要途徑。在《尋金者》中,與“金”意象體現的物質對人的精神遮蔽相對的,是自然元素和空間意象中呈現出來的原生態之美,是這種美的感受帶給人的心靈的平靜和人內心對幸福和諧的自然原初生活的憧憬。
在文本中,大海、島嶼和花園是反覆出現的自然形象,是小說情節展開的空間依託,是作家將目光投向自然、憧憬世界原初狀態下人與自然和諧交融的意象原型。主人公阿力克西是一位親近自然的人。大自然,尤其是大海,對他有著幾乎神奇的吸引力,是小說中無處不在、反覆出現的自然意象。小說開篇就是從大海開始:“在‘我’記憶最遙遠的地方,‘我’聽見了大海的聲音。”作為童年的家園,布康的大海帶給了主人公無盡的歡樂,讓他感到自由,充滿著對美好幸福的嚮往。在阿力克西的眼中,布康的大海“輕盈”“美麗而溫柔”,“大海的聲音猶如一首樂曲般優美”。他和大海的親密接觸,是一種水乳交融的體驗,仿佛“一切都不復存在,什麼都沒有流逝”。童年的大海代表著自由、幸福,讓阿力克西難以忘懷,留存在他記憶的最深處。即使在尋“金”的旅途中,在漂泊的大海上,在最殘酷的歐洲戰場,主人公也時常想起故鄉的大海,對海的記憶帶給他夢幻般的感覺和溫暖的撫慰。
主人公苦苦追尋的寶藏,不是代表物質財富的金銀,而是浩瀚星空、茫茫大海,是遠離人煙的海島和埋藏於記憶深處的兒時家園,是非西方價值取向的異域文明,以及它們所體現出來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融的關係。而這正是被西方文明丟棄已久、被人類遺忘在內心深處的寶藏和精神家園。
《尋金者》主題思想之二:
借用女權意識來反抗一切不平等的壓迫現象。
《尋金者》里的母親是傳統的賢妻良母一類的女性形象,專心教子,表現出溫良淑德的一面。而父親則無望地策劃著名各種注定失敗的事業,妄圖逃脫破產的命運。母親始終無怨無悔,對丈夫沒有埋怨。她當然談不上是受到男權壓迫的女性形象,她只是沒有顯現自己的欲望和獨立存在的個性,一直遵從丈夫和家庭的需要。最後她臥病在床,“不再說話,不再走動,幾乎不再進食”,成為一個象徵性的存在。
在“我”通過回憶所美化的童年裡,母親和大海之間產生了一種神秘的關聯。母親的主要功能在於成為自然的化身,揭示著“我”與大海之間的親密關係。而在原住民少女烏瑪與“我”的相處中,烏瑪似乎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她獨立地在大自然中謀生,“我”作為男性,卻在她自如的跳躍動作前顯得十分笨拙。對烏瑪的敘述倒是反映了勒克萊奇奧的女權思想,只不過在這裡女性並不具有自己獨立的敘述聲音或爭取個性解放的獨立意識。借用女權意識來反抗一切不平等的壓迫現象,這才是勒克萊奇奧最為珍視的主題。
烏瑪的形象代表了一個群體。“我”對烏瑪的敘事更多地是在控訴殖民者的罪惡和種族歧視現象,而烏瑪的堅強和自主不是在反抗男權,而是在反抗白人對原住民的剝削、對大自然的破壞:“你們以為黃金是最強大和最令人艷羨的東西?你們正是為了黃金而打仗。到處都有人為了爭奪黃金而死去。”“我”在整個文本里不斷暗示著大海和女性身體的內在聯繫,控訴殖民者對自然、有色人種的征服和掠奪的發展邏輯。勒克萊奇奧的生態觀因此不僅僅是通常意義上對自然環境的重視和保護,更主要地是反映為對人的關注。敘事者將保護自然與反殖民話語等同起來,而且與反殖民話語等同的不僅是生態,還有女性的敘述聲音,例如烏瑪對殖民者的譴責。
作者對女性的敘事策略,從文本所呈現的兩條理路來看更具有揭示性:其一是妹妹蘿爾所選擇的人道主義事業,再有是烏瑪所代表的對人類存在本初狀態的回溯。“我”雖然對蘿爾的離去表示理解,但最終選擇的無疑是土著少女的原生狀態。
最終,“烏瑪和‘我’又在一起了,‘我’感受到她身體的溫暖、她的氣息,‘我’聽到了她的心跳” 。和烏瑪相比,蘿爾無疑更具現代女權意識,和“我”有著近似亂倫的愛戀關係,但是始終保持著精神獨立。如果說“我”拒絕成長,是一個一直幻想回到母體的兒童,蘿爾卻選擇了成長和積極面對複雜的世界。
當“我”離開衰弱的母親前往尋找虛幻的黃金時,是蘿爾留下來照顧母親。她雖然不願意看到“我”離去,但是沒有哀求和崩潰,在給“我”的來信中還用幽默的語調調侃自己和母親所面臨的艱難困境。最後當“我”要蘿爾與自己一起離開時,蘿爾嘲諷地加以拒絕:“三個人一起?和楊格·卡特拉(蘿爾對烏瑪的稱呼)?”她選擇了人道主義事業,義無反顧地離去更是女權自主的典型風格:“她將母親的圍巾纏上自己美麗的黑髮,轉身離開,沒有回頭,只帶著小箱子和大大的雨傘,步伐高傲筆直,自此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改變她的道路。”另一方面,“我”對烏瑪的選擇最終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勒克萊奇奧的女權思想,表現了勒克萊奇奧對女性具有獨立的視角。雖然作者力圖尊重女性,但女權思想是附屬於作者本人男性話語的意識形態部分的。
勒克萊齊奧無疑屬於精英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綜觀當今法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大學和文學藝術界,以左派居多,他們擁有文化領導權,掌控主流言論。他們傳承了五月風暴的反叛和思辨精神,一如既往地從文化領域發起對社會體制領域的不斷攻擊。於是,在法國社會可以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主流知識分子對資產階級社會主流政治的批評。這種批評在各個時代有著不同的變種:性解放、女權主義、流產合法化、對烏托邦嚮往,等等。而在當今,則集中一體化打包式地表現為反全球化和對西方殖民史的原罪敘述,包括生態主義,例如左派知識分子對非法移民權益的關注和對薩科奇政府有選擇性移民政策的質疑等。
勒克萊齊奧的思想應該說沒有超越這個框架。遠離法國本土,位於文明世界的邊緣,長期在亞馬遜、非洲和加勒比海遊歷的作家以文明世界的醒世者自居,但他實際上秉持主流精英知識分子的話語,呼籲環保,警示全球化對文化多樣性的威脅,控訴各種形式的殖民壓迫。這種自詡為先知先覺的知識精英意識仍屬於男性話語的範疇。此處男性話語的意義,不在於所謂男權意識對女性敘述聲音的壓制或是扭曲,而是說,性別問題本身並非勒克萊奇奧始終關心的主題。男性話語下的女權主義並不包含女性性別的獨特內涵,其所標榜的女權主義並不聚焦於女性自身的價值,或解剖男權對女性的壓迫。因此,在《尋金者》里,蘿爾所代表的女性解放的私人性一面被忽略,而烏瑪所承載的與主流意識形態相關的截面則被凸顯和放大。女性形象的寓意游離於女性本身之外,在女性形象的迷霧之下涌動的是男性精英知識分子思想的暗流。
藝術特色
空間敘事
1、物理空間
《尋金者》小說的物理空間是指作為物質存在的人的生存環境。《尋金者》的背景經過了四個地域的轉換:模里西斯島——羅德里格島——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的歐洲——戰後的模里西斯島,其中,模里西斯島和羅德里格島蠻荒的自然環境與歐洲的戰場環境形成鮮明反差,作為兩種極端的物理空間以對立的形式凸顯出來。小說以豐富的環境描寫為特色,淡化了時間敘事,凸顯了空間的敘事,以語言的畫筆勾勒出敘事的圖畫效果:印度洋海島的旖旎風光、一戰戰場的血腥場面、殖民地勞工辛勤勞作的場景像畫卷般栩栩如生地展開。地理環境描寫和多重空間建構構成小說一大特色,為《尋金者》思想內容的解讀提供了一扇視窗。
在自然空間中,大自然以原初的方式存在著,保持著天然的風貌。作者在緩緩展開的這幅自然畫卷中力圖表現的是大自然的多姿多彩。例如這一段對海灘的描寫表現了原始自然界物種的豐富:“潮汐退去後的海灘留下深深淺淺的水潭,有的顏色很深、晦暗不明,有的卻清澈晶瑩、明亮生輝。往深處看,可以看見海參蜷成紫色的球,海葵綻開血紅的花冠,真尾蛇慢慢地抖動著毛茸茸的觸角。”又如小說多處對天空和大海顏色的精確觀察體現了未被工業污染的空氣和水源本真的色彩:“‘我’注視著深藍的海水,那是一種讓人頭暈目眩的藍色。慢慢地,船頭前面的海面顏色漸行漸淡。金色的浮雲在海面上泛綠的倒影。”自在的自然神奇而多變,正如這一段對安的列斯群島特有的海中礁石的描繪:“海中的小山在海面上拔地而起,好似一座熔岩鑄就的巨石,光禿禿的沒有植被。在它周圍展開了明亮的淺色沙灘,傾瀉著礁湖的流水。‘我’感覺像是來到了世界的盡頭。”在這些描寫中,作者刻意表現了自然的原初、蠻荒之美,這種美不是一種帶著人工的痕跡的田園式的溫馨,而是一種自然的廣袤與粗糲。
與之截然相反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戰場上,亞歷克西斯不是在陰暗污濁的戰壕里備戰,就是在血肉橫飛的戰鬥中拼搏,周邊總是隆隆的槍炮聲、致命的毒氣和被炮火點燃的廢墟。戰爭留下的是自然的毀滅與生靈的塗炭,亞歷克西斯描述道:“透過步槍的瞄準儀,‘我’只能看見一片燒焦的樹木和混亂的土地。炮火炸得到處坑坑窪窪,毀掉了樹林和村莊,每天都見證著死亡,見證著戰友被機關槍擊倒,像被無形的力折成兩段,被炮彈開膛破肚或炸得頭顱迸裂。”
作者把原始蠻荒的模里西斯和淪為戰場的歐洲作為兩組實在的物理空間進行並置與對照:一邊是未經工業文明染指的原初自然,一邊是文明發展到登峰時期的物極必反;進而對人類兩種生存空間的存在形式以及造成這種差異的根源進行了反思。自然空間的野性魅力與戰爭空間的觸目驚心顯然有力地否定了上述假設,說明人類社會並不是像現代性精神的線性發展觀所宣揚的那樣,能夠通過工業發展直線地走向繁榮、文明和進步。相反,工業文明的片面發展導致了戰爭,而借力於工業文明的戰爭產生了不可想像的破壞力,把人類的生存環境置於一種遠不如蒙昧、蠻荒的境地。作者藉此批判了不惜以損害生態環境、自然資源為代價片面發展工業文明的現代性精神及其所鼓吹的線性發展觀。
如果說小說中兩組物理空間的對照直白地表現了對線性發展觀的否定這一主題,那么小說中潛伏著的兩組空間隱喻深化和拓展了這一主題。
首先,大海的意象隱喻自然。《尋金者》以大海開篇,以大海收尾,大海是主人公人生經歷的一條主線,主人公對自然的眷戀最先也是從海開始的。大海的意象被描寫為遼闊、深邃、多變與神秘,大海在作品裡和天空、大地一樣是自然空間的典型表征。大海(la mer)這個詞語在法語裡和母親(la mère)同音,象徵著孕育與新生。通過這種聯繫,作者賦予自然一種母親般的情感嫁接,暗示自然空間有一種子宮般的安撫、給予和孕育的使命。
與之相對的是暴風雨的意象,暴風雨隱喻戰爭。暴風雨在《尋金者》的敘事中反覆出現,每次都帶來大規模的破壞(摧毀了亞歷克西斯童年的家園和父親的產業,洗刷了亞歷克西斯尋找寶藏的山谷,覆滅了亞歷克西斯摯友布拉德墨船長的航船)。童年時亞歷克西斯第一次見證摧毀他家的房子和產業的熱帶風暴時,他想起了聖經里的大洪水,並認為上帝這樣懲罰地球是因為人們冷酷無情地剝削種植園裡的貧窮勞工。借主人公之口,作者將暴風雨比喻為聖經里滅世的大洪水,象徵著毀滅與懲戒,隱喻著同樣具有強大破壞力並席捲一切的人類戰爭。自然母親的隱喻反駁了現代性精神中認為原初的自然低等落後、有待人類征服改造的理念;戰爭風暴的隱喻印證了工業化發展的非線性特徵,預示了盲目過度的工業化發展會招致人類的災難與懲戒。因此,兩組空間隱喻與物理空間的對立彼此形成反映參照,進一步深化了現代性批判的主題。
2、社會空間
《尋金者》的社會空間主要建構在模里西斯島的甘蔗種植園上。甘蔗種植是資本主義前殖民時期剝削掠奪海外殖民地的主要實現方式,在種植園這個實際存在的自然環境中小說建構了英國殖民者與黑人勞工壓迫與對抗的社會空間。小說中涉及的模里西斯島正處在英國殖民者管轄時期,此時奴隸制已被廢除,種植園裡的勞工主要是解放的黑人奴隸和英國從印度招買來從事墾殖的大量移民。勞工與種植園主的關係是農業工人和資本家的關係。甘蔗種植園不是農業經濟下的農作物種植,而是殖民主義工廠式的、高效集中的生產經營基地。
殖民者對勞工的殘酷剝削與壓迫集中體現在甘蔗園的空間特徵上,即環境的擁擠與簡陋。在甘蔗成熟的季節,種植園裡人聲嘈雜,擠滿了忙著收割的勞工,牛車在極其狹窄的過道里來來回回搬運,到處塵土飛揚、蚊蠅飛舞,空氣里夾雜著一股混著汗臭、粉塵和甘蔗汁的刺鼻氣味。環境的簡陋和擁擠以勞工的利益為代價,節約了資本家的土地成本,實現了生產的高效。殖民者的剝削壓迫進而表現為遍布甘蔗園的英國監工對權力秩序的維護:當成捆的甘蔗未及時被裝上推車時,監工們就用棍子抽打勞工。“成千上萬的勞工在種植園裡耕種著永遠也不屬於他們的土地,一天到晚,從早到黑,只有在需要磨鐮刀的時候才能停下,直到手磨出血,直到腿被繩索勒破,直到毒辣的太陽曬得他們噁心頭痛。”
殖民主義以犧牲勞動者為代價,堅持效率優先的原則,以種植園的簡陋和對種植園滴水不漏的監管來實現最大化的榨取和殘酷的壓迫。
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與鬥爭則體現在對作為剝削壓迫發生空間的甘蔗園的爭奪。小說通過亞歷克西斯的視角描寫了勞工在種植園暴動的場景:“‘我’在夜裡看到著火的甘蔗園冒著赤紅色的濃煙,染得天空也變成一種奇怪的咄咄逼人的紅色,讓人眼睛乾澀、喉頭緊鎖,暴動的嘈雜聲如疾風驟雨一般從四面八方同時傳來,迴蕩在山隘關口。到處是叫喊聲、咆哮聲、槍擊聲。”
殖民者以空間的密集與擁擠為基礎,殘酷地剝削和壓迫殖民地人民。而被壓迫者用以泄憤的對象首先就是作為殖民者奴役和剝削髮生空間的甘蔗園。因此,甘蔗園不僅被構想為政治、衝突與鬥爭的場所,而且也成為了被爭奪的對象。同時,暴動的勞工將鬥爭矛頭指向了維護甘蔗園權力秩序的監工,意圖打破殖民者對甘蔗園的控制。飛奔到甘蔗園的亞歷克西斯,見證了憤怒的人群一邊高喊口號一邊步步緊逼三個騎馬的白人監工,一直將他們推出甘蔗園,趕到甘蔗園邊上的煉糖廠里,並把其中一個最冷酷的監工投進了甘蔗冶煉爐。
當代語境下的空間不再是一個靜止不變的“容器”,而是一個無限開放的、充滿了矛盾的過程,是各種力量構成對抗的場所。小說中的甘蔗園也不再是一個簡單的空間存在,而是社會力量實現相互抗衡、較量、壓迫與對抗的手段和對象,是一種打上殖民主義烙印的社會存在。這種社會空間的建構反思了現代性進程中的殖民關係:它表明現代性的過程與資本主義進程相促相生,資本主義秩序又滋養了殖民主義;同時,它澄清了西方物質文明現代化的實現不僅是科技、理性的結果,更多的是仰賴於對弱小民族的殖民掠奪與剝削所創造的原始資本。
3、心理空間
《尋金者》通過主人公心理空間的建構,塑造了一個現代原始人的形象,這一形象戲仿並顛覆了在文學史上作為理性與進步的西方殖民者典型代表的魯濱遜·克魯索,從而批判了作為現代性精神支柱的啟蒙理性思想。
心理空間與現代原始人的形象塑造:亞歷克西斯是一個生活在現代卻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現代原始人。小說中成年後的亞歷克西斯在經年累月離群索居的生活後,長期以野人形象出現:他眼睛發紅,臉膛黝黑,頭髮垂到肩上,滿臉大鬍子,由於經常挨餓而身形瘦削,成了一個生活在現代的野人。這個野人形象和他的家庭出身是不相符合的:亞歷克西斯是歐洲白人移民的後裔,從小從媽媽那裡受過很好的西方文明的教育,會說法文、英文,熟悉聖經以及文學名著里的典故。他的家人都在殖民地從事白領工作,叔叔是模里西斯聲名顯赫的富商。但是他成年後無法融入殖民地的白人社會,完成他所隸屬的社會賦予他的使命。他兩度迫於生計接手父親生前的會計工作,又兩次不堪忍受悶熱陰暗的辦公室里那成堆的票據、灰塵的氣味、潮濕的熱氣和百葉窗里傳來的街上的喧譁聲而離職。他自願地選擇了居無定所的尋寶旅程,以追求自己的遠行和冒險的夢想,帶著家傳的藏寶圖隻身到孤島尋金,投入了自然的懷抱。孤島上自然生活的艱苦和嚴峻讓他飽嘗艱辛,可一旦看到天邊山崗上淡粉色的天空和翡翠般閃耀的大海,他又不禁感嘆道:“‘我’怎么能忘了這種美?現在‘我’明白了‘我’來這裡真正尋找的東西,一種‘我’自己不能掌控的力,一種在‘我’出生前就存在的記憶。”
亞歷克西斯在荒野與城市的兩種空間形態中作出了選擇,寧願在開闊自由的自然界出生入死,忍飢挨餓,也不願去適應狹窄禁錮的辦公室的舒適生活。可以說,亞歷克西斯自願地選擇成為一個摩登時代的野人,並對這種“野人”生活樂此不疲。
亞歷克西斯的性格特徵是成長環境在其心理空間的映射,是在模里西斯島粗糲的野生自然環境的長期作用下形成的。他的性格中呈現出一種難以馴服、不受拘束、崇尚冒險的特徵。小說一開篇,亞歷克西斯就述說了他對海的痴迷和嚮往,“大海的聲音像搖籃曲一樣安撫著我的整個童年”。他在模里西斯島的童年生活充滿了到處野遊、探險的經歷,他和黑人小夥伴德尼常常一起穿過甘蔗園、蘆薈園、荒地、森林、山巒、峽谷、溪流、泉水,經過克里奧人居住過的的斷壁殘垣,一直到達海灘邊觀賞潮汐。德尼在他的自然教育中給予了巨大幫助,他認為和德尼一起上的課程是最美好的。德尼帶他到森林的最深處,教他識別各種野生樹種、藥材;德尼帶他乘上獨木舟,進行了人生第一次海上航行。大自然的廣闊培養了他自由的秉性;大自然的多變鑄就他冒險的精神;大自然的瑰麗和多彩賦予他浪漫的情懷。這樣成長起來的亞歷克西斯,熱愛自然空間的自由與廣闊,難以融入城市空間的束縛與禁閉。
人物心理空間的建構以及對啟蒙理性精神的批判:為了表現亞歷克西斯這個人物心理空間的獨特性,作者實際上在亞力克西斯身上對笛福筆下的魯濱遜進行了戲仿。兩個人物的相似性使他們具有很強的可比性:都是荒島漂泊,都是隻身奮鬥,都是西方人與蠻荒自然的故事。然而兩個人物心理空間的迥異卻揭示出作者對啟蒙理性的批判。
亞歷克西斯的心理空間在自然空間的作用下發展成一種自由、隨性、粗獷的秉性,進而表現為他對自然空間的熱愛、尊重和依賴。亞歷克西斯在荒島上努力適應自然,沒有屋頂,就在樹蔭下乘涼,沒有床鋪,就在石頭的縫隙里將就;餓了采些野果子吃,渴了就喝河裡的水;從沒有刻意去計算時間,總覺得自己在島上呆得恍若隔世。
他把自然界的草草木木都視為平等的存在,他和給自己遮風擋雨的一棵羅望子樹結下了情誼,他了解樹的每一個細節——從多節的樹根到盤錯的枝幹,他認為樹才是山谷的主人。他看到鳥兒時會想像用鳥的視角去俯視山谷,並且認為只有鳥兒才懂得他來荒島真正尋求的東西。亞歷克西斯的心理空間反映了後現代的生態審美觀,即作為審美者的人與自然建立的是互動性的關係,而不是主體和客體的關係。
亞歷克西斯眷戀自然的審美個性和熱愛自然的生活理念植根於其心理空間的建構,因此,通過對人物心理空間的建構,作家間接地表達了希望剝去西方理性思想桎梏,回歸自然的願望。
生態隱喻
在《尋金者》中,與“金”意象體現的物質對人的精神遮蔽相對的,是自然萬物呈現出來的原生態之美,是這種美的感受帶給人的心靈的平靜和人內心對幸福和諧的自然原初生活的憧憬。
在勒·克萊齊奧筆下,大海、島嶼和花園是反覆出現的自然形象,是該小說情節展開的空間依託,是作家將目光投向自然、憧憬世界原初狀態下人與自然和諧交融的意象原型。
小說的主人公阿力克西是一位親近自然的人。主人公童年時期在家鄉布康的花園,同樣具有厚重的神話原型色彩和深刻的批判意義。它就像聖經故事中的伊甸園,經過作家的重構變形,成了阿力克西兒時的樂園。阿力克西都不由自主地想起童年的布康,想起與大海和五椏果樹相伴的幸福時光。布康寄託了作家對聖經中人類社會創始之初人與自然和諧天成的伊甸園純淨世界的想像。象徵著人類回歸人與自然原初和諧的夢想。布康、大海和其他自然形象一道,才是主人公真正要尋找的寶藏,是存在於現代人記憶深處而又苦尋不到的精神家園。
由此,“尋金”引起的內心虛空和回歸自然帶來的精神充實,戰爭如地獄般恐怖的氣氛和花園如天堂般的幸福感覺形成了鮮明對照。而這一切,則源自於內心深處對自然之愛的本能感受。
作品評論
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詩意敘事,其標題與敘事內容對應了貫穿作家創作靈感的烏托邦與懷舊主題。
烏瑪的形象代表了一個群體。“我”對烏瑪的敘事更多地是在控訴殖民者的罪惡和種族歧視現象,而烏瑪的堅強和自主不是在反抗男權,而是在反抗白人對原住民的剝削、對大自然的破壞。
《尋金者》小說,通過文本結構上的對稱,循環往復地歌詠美妙而壯麗的大自然,在描述人類宿命一般的尋金不得的痛苦時,暗示人類的幸福或許就在原點:自然界中的風、河流、大海、樹木、星星。該書帶有家族自傳敘述的意味。
——搜狐網
作者簡介
勒·克萊齊奧(Jean Marie Gustave Le Clézio),法國著名文學家,出生於1940年,是20世紀後半期法國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之一,也是現今法國文壇的領軍人物之一,200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品有《
訴訟筆錄》、《尋金者》、《羅德里格島遊記》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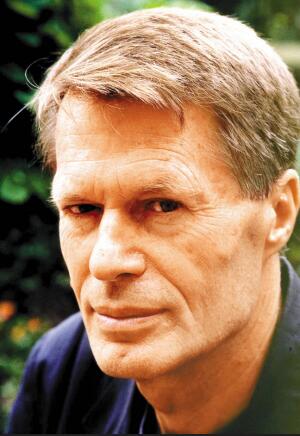 勒·克萊齊奧
勒·克萊齊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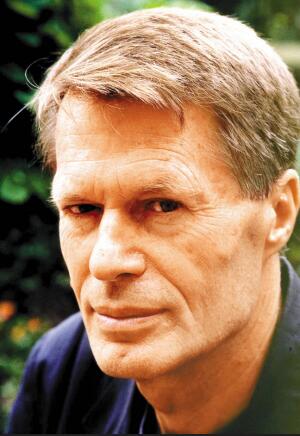 勒·克萊齊奧
勒·克萊齊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