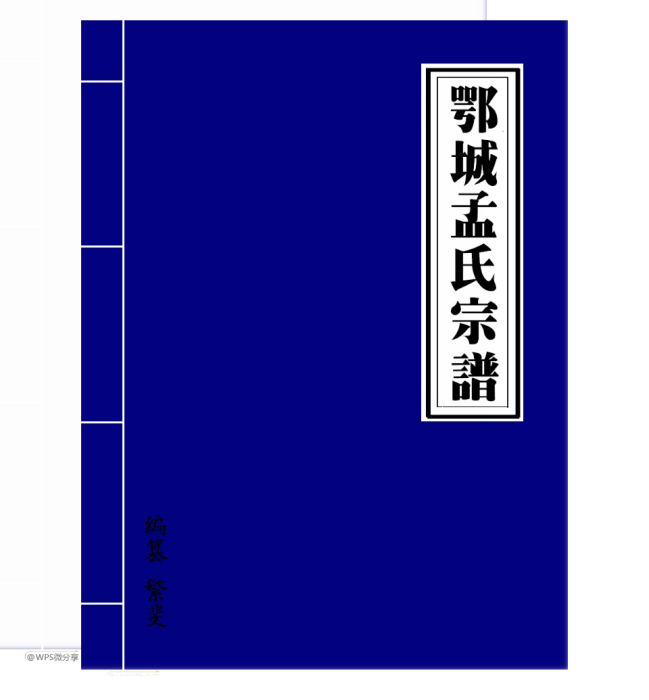孟丹溪(1886-1945),孟子第七十世後裔,孟傳綸孫,孟繼旦侄,湖北鄂城城關人,譜名孟廣溎,冊名晉,一號端溪。武昌府師範學堂(今武漢大學前身)優等畢業,蒙湖廣總督張之洞選送日本留學,畢業於日本大學專門部法律科,應學部試驗,獎給法科舉人(載《湖北通志》),民國七年(公元1918年),應第一次知事試驗及格,分發直隸。民國十年任直隸肅寧縣知事;十七年(公元1928年)任山東沂水縣法院院長;二十年(公元1931年)兼理沂水縣縣長;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督修《鄂城孟氏宗譜》;三十年(公元1941年)任鄂城縣財務委員、鄂城縣縣長。生前著有《西洋歷史教科書》三卷、《自治模範》、《言文一致》、《國文典》,《詩詞》五十七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孟丹溪
- 別名:孟廣溎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日期:1886年11月20日戌時
- 逝世日期:1945年5月
- 畢業院校:武昌師範學堂
- 代表作品:民國二十五年《鄂城孟氏宗譜》
- 職務:縣長
- 出生地:湖北鄂州
- 信仰:儒教
- 主要成就:愛國愛民
孟端溪自述,代表作品,
孟端溪自述
中華民國廿六年(公元1937年)丁丑十一月
我既無裨於斯世,終與草木同腐,奚用身後名為?我既溷跡於斯世,究當雪泥留印,何妄自菲薄為?由前之說是文,非與世道人心有關者,不作可耳;由後之說,則我非離群迕俗者,作之何妨?此次董修《家譜》將告竣,族人鹹請留行誼於《世德譜》內藉,以昭示來茲。曰:“不過庸庸者流,有何行誼可述?必多此一舉,以災棗栗乎。”族人要之再三,無已,僅自述天所待庸庸者之厚,而庸庸自處者之適耳,要亦不敢自離人群之意而已。
母周太夫人,為嗣王母袁太夫人外甥女(外祖明仲公為先曾祖景山公長婿,先母為繼妣胡孺人出)袁太夫人兩子身故,生未彌月,先羅田公暨先父雪樵公主持,以兼祧為嗣。祖母吾母,愛護備至,至於成立,此終身未敢忘罔極恩也。束髮後,就家塾先雲谷三伯、齊卿八伯授《句讀》,稍長,延洪鄉邵琴仙先生於家,同學者均城中親友,雖外傳猶家塾也。九歲時隨先羅田公之任所,前後計十年。此十年中,於舊學稍置其礎,未窺其奧,時,科舉未停,遇小試輒返里應之。清光緒甲辰(公元1904年)仲夏,應府試後,以祖母、父母鹹在南昌,遂留省候院試,適同城塗筱舫、石雲衢兩先生,投考武昌府師範學堂。時,學堂初創,隨往參觀,亦得一卷,入場與試,揭曉後有名與覆,覆亦附名,遂得入學堂矣,學章為一年畢業。南皮張文襄公,以此次省道府三師範畢業者多青年,驟為人師,殊非所宜,乃就三堂抽選百人往日本留學,亦與選。時,室人張來歸,甫數月,年廿,遂離家遠遊矣。在日本荏苒數載,從名法家游,方冀學成歸來。祖母、父母得以過去之艱辛,易將來之安享也。不意先母忽於清·光緒丁未(公元1907年)去世,由日匍匐歸,歸已蓋棺多日矣,此又終身遺憾也。以清·宣統庚戌(公元1910年)夏末,畢業於日本大學法科,以學部試在即,乃遵陸由朝鮮奉天入京。時,朝鮮國尚獨立,經過後十日乃日韓合邦矣。南滿路亦未竣功,乘者為日俄戰爭時之軍用鐵道。所過山川雄偉,風俗樸厚,今已為日(本)強占以去,回思之誠,令人太息不置。入京後,未能一索而得,至次年即為遜清末年辛亥(公元1911年)秋,乃中學部式,得法政科舉人。時,以民軍起義風甚盛,不敢久留京師,幞被以歸,歸後數日,武昌即揭義旗入民國矣。
民國紀元(公元1912年),初,就軍政府編輯部職,先父隨住省城,不幸適於是年二月病逝省寓,初,膺家務,且為客居,衣棺殯葬之屬,俱極潦草,幸得歸葬於縣西九曲亭之側。此實痛心疾首,抱恨終天者也。嗣即揭眷居省垣,與三師範同學創辦江漢學校,兼為校監,及講學於省各法政學校,併兼充律師。民三,應內務部第一屆知事試驗及格。民四,分發直隸任用,聽鼓折津,苦無依傍,(公元1914年)歷膺差委,僅可棲身,而於高堂之奉養,家事之維持,悉張孺人代之,而轉自慰曰,無內顧憂也。民六(公元1917年),權易縣篆,曾以板輿奉祖母往北一游,卒以時局不寧,北地寒苦,為時甚暫,只得於次年春仍歸故里,而遂隻身作客矣。民九,以調查吏治差,往長城以北之蔚縣。蔚與山西靈寶接壤,為多年之礦務糾葛,激起民變。適於是日行抵該縣城,聲勢洶洶,不可理喻。乃從旁極力勸解,始稍稍就範,以是見知於省長曹公銳,得督辦畿輔賑糶處差。一年來於赤地千里中,飛芻挽栗,頗無遺誤,以績得肅寧縣篆。肅寧地近京津,盜風甚熾,號稱難治,御以至誠,矯其游惰,雖未克上臻治理,亦頗近於安靜之吏也。十一年(公元1922年)冬調署元氏,已得委矣,忽為有力者櫻之以去,以知宦場險惡,極願脫離,益以多年來塋墓失修,定省久缺,乃以返里掃墓省親為請,於是,南旋度歲家人團聚矣。十二年(公元1923年)有游閩之舉,閩省地居海濱,全省遨遊幾遍,則見夫山海雄奇,物產豐富,文章科名之士,隨在皆有,復多遊覽之區,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卒以政局變動,匆匆賦歸與矣。後曾一度游汴,被兵荒阻於信陽,幸遇同城周戚,作貿於此,乃得避亂其家。適歲莫,彈聲隆隆,等於爆竹;敗兵叩門,有如賀歲。至乙丑(公元1925年)元旦始,出險返鄂,然已驚悸萬狀,衣物被劫無餘,嗣即養晦家居,遂多歲月,蓋以飽經憂患之身,不欲爭一時之聞達也。
十五年(公元1926年),革命軍入鄂,適家居,目睹一番新氣象也。十七年春,游贛游皖,夏初,觀光新都,隨軍至徐州,晤戰地委員會蔣雨岩委員長。蓋廿年前曾在日京一晤也,承委以山東沂水縣法院院長。沂為匪區,計在沂四年,與地方人士頗歡洽,遇有官紳爭執,輒就商於,其事遂解。建法院,修監獄,辦監獄工場,得地方佽助者極多,而乃煞費經營矣。法院與縣府毗連,舊有廢棄之山石多尊,與工竣後之殘餘材料,乃捐俸津貼羈押人犯。築諸樂園於法院隙地,取佛經但得諸樂而無眾苦之義,有山、有池、有亭,亭名“澹然。”為亡叔佛心所題,蓋勉以澹於功利之意耳。沂地訟簡多,餘暇,暇輒獨酌其中,復得地方詞章、秀逸之士相唱和,而題詠幾盈尺矣,生平最適意事當推此時。十九年(公元1930年)秋,以駐軍失敗,縣長潛逃,曾一度兼理縣長三月,地方幸不糜亂,而平安度去矣。廿年(公元1931年)春,祖母以八十有八之年,患重病旋即仙逝,以在官未獲親視含殮,衷心耿耿,無時或釋,請假數次始邀準回籍治喪,事畢,乃返任所。廿一年(公元1932年),駐軍展書堂師長,堅邀入幕,遂離沂水隨軍矣,賓主相得,執禮甚恭,至廿三年(公元1934年)夏,以該師與沂水民眾為難,殺戮過多,力勸之不獲,即辭職返里矣。
近數年來,家居之日多,檢點藏書,料理家務,訓誨子女,固終日皇皇,無片刻暇也。去年,寓居省城,旅省諸宗親,有續修《宗譜》之議,以夙存此願,公推董理其事,遂屏棄一切,從事修譜生活矣。今幸《譜牒》漸次以竣,其經過之煩難,經濟之困頓,及遭遇不明事理者之阻撓,蓋又終修譜之歲月,而無時安靖也,所敢自信者,秉大公無一曲筆,有如史官,任勞怨無絲毫苟且;有如家臣,持以毅力,俾底於成,有如現在抗戰之當局者耳。
自述既竣,因自為結論。論曰:生五十有二矣,正祖逖擊楫渡江之歲,亦東坡召對便殿之年,功名事業,學問文章,原非庸庸者所可期,但綜半生經歷,既與以貧仍與以健,不席其豐,卻食其德,蓋得天獨厚,得於祖宗餘蔭者亦不薄,何哉?以疏野直率之性情,而廁於士夫之列,則幸也。以險阻艱難之迭見,而卒化險為夷,則數也。以一末秩,而足跡幾遍天下,則又未嘗不引以自豪也。且囊無餘錢,室家累重,旁觀者為擔憂,而予則守分安命,順時聽天而無怨也,固曰:庸庸者流,天待庸庸之厚,而庸庸自處之適也。
代表作品
國文典
孟廣溎 撰 孟繼旦 作序 清光緒丁未(公元1907年),七月朔
廿世紀之國家,毅然獨立於地球,能制人而不制於人者,僉曰:海陸軍之強也,商工業之優也,政治家之靈敏而無遺算也,而不知實基礎於教育普及,何則?六合交通以來,國與國競為終極,必人與人競為起點。以個人論,識字愈多者,執業愈貴,而所得益豐,無形之中階級判焉。以國家論,識字之民愈多者,文明愈進,而攸住鹹宜,交涉之間,權利勝焉。然則教育一端,使人之智愚生死於是判,國之強弱存亡於是分,雖曰優勝劣敗,天演公理,毋亦人事之有盡有未盡也。鄂督南皮中堂有鑒於此,特於湖北普興教育,為各行省倡,故吾省習師範科者,海內外近數千人矣。甲辰歲(公元1904年),居鄂垣武昌道師範學堂,端溪侄亦肄業武昌師範學堂,比鄰而居,各孰其業,余余在該校時,聆教員日本稻(早稻田大學),並辛吉等之緒論,謂日本教育,以百人比例,識字者逾九十焉,蓋使人人有世界思想,合全國之人,與世界競爭,猶懼弗勝,而不足支持於廿世紀之天下,中國適為反比例,此所以不能爭衡於兩半球也。余初聆之,與吾侄端趨相談,端雲府學堂教員,並引諭英、德之教育,凌駕日本,余皆未之信。是年冬東渡,從事警察法政之學,並參加各學校之教法,及征之社會之間,則見賤役小廝,女僕車子,靡不能讀報通信,嗚呼!教育普及,信有徵矣。乙巳秋,端侄師範卒業後,亦由本省資送來東,專研師範科。余以所見聞者告之,端侄亦思所以謀普及之法於祖國也。雖然,論教育於中國,即求普及,有數難焉:一曰國家保舊慣,守四千年秦皇愚民之術,安之若素?以為人民識字之多寡,無關國家之損益,鎖港時代,信不誣也。而處今日競爭之世界,則不能不幡然改圖,故朝廷置興學專官,疆吏示教育規則,而地方官仍具文視之,此普及之一難也;二曰愚民無遠識,子弟就學,乃消費事業,非生產事產,鄉黨自好者,非欲子弟就科名,亦不願求學,此欲普及之二難也;三曰界乎國家與小民之間之紳耆無責任,學校之事,與地方最有關係者,莫如紳耆。而一則畏難而不能圖始;一則藉名而力求漁利,縻欵廢時,子弟無進化,遂不免以教育為多事矣,此普及之三難也。然此,皆形式上之難,有實心任事者出易,如奏功,而更有一最難者,則實質上之言文分離也。考西洋之ABC,東洋之イロハ,與吾國文字並駕齊驅,而其實則不過言語符號,故司教者教以文字,即教以語言,其新學者,即其舊有者,其練習者,即其必用者,故卒業於尋常高等國小之生徒,已足供終身生計界之套用矣。中國自秦漢而後,文字與語言,日離日遠。至於今,遂不可以道里計,故有讀書十年而不能執筆者,尤有八股驚人,而不克通一信札者,嗚呼!中國教育退化,其此也興。今歲暑假,端侄以其暇也,取所學之《日本文典》及《英文典》,與日本人所著各種之《漢文典》,再《馬氏文通》、《中日文通》等書,或仿其體例,或擷其精英,輯為《國文典》一書,就正於余,余於此道不聞問者三年於茲,亦未暇商其可否。然其宗旨在言文一致,雖未能博綜典要,有慚簡略,而善教者,能因此以投其俗尚,引伸以窮其變化,使學者識一字獲一字之益,以能言擅能文之稱,則是編縱不能為通國進化之嚆矢,使海陸軍人高其資格,商工事業多新發明,政治上更能得整飭內外之結果,而或者稍除教育界之障礙,即於教育界中,不無小補云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