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麥秸垛》十二部分內容集中寫了幾個女人的故事:知青楊青與沈小鳳的故事,端村小池媳婦花兒的故事,大芝娘的故事。花兒從四川逃荒過來。原來有丈夫,來到端村又嫁給了小池,她的丈夫找到她並把她帶回了四川,而此時的花兒留下了與前夫的孩子,卻是懷著小池的孩子離開端村的。
楊青是一個城府較深的女孩,雖然陸野明對她表示好感,但是她很了解此時此地不能回應他的愛情,如果背離傳統道德及政治上正確的路線,她將會惹一身麻煩。沈小鳳則相反,狠狠地纏著陸野明。終於一天晚上,學生和村民一同看完一場並非有意的煽情電影后,陸野明和沈小鳳不知不覺地同時放慢了腳步,離開眾人,在月夜裡的麥秸垛旁發生了關係。
農婦大芝娘,這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從太陽那裡吸收的熱量好像格外充足,吸收了又釋放著。她身材粗壯,胸脯分外地豐碩,斜大襟褂子兜住口袋似的一雙肥奶。每逢貓腰幹活兒,胸前便亂顫起來,但活計利索。大芝娘年輕時嫁給了一位解放軍。結婚的第四天,丈夫就出去打仗了。當丈夫勝利回鄉時,立刻要求離婚,理由是他愛上了一個護士。大芝娘不懂什麼叫做愛情,但她覺得自己應該順應時代,就答應了離婚。當他們辦完離婚手續的第二天,大芝娘卻又到前夫城裡的單位找他,要和他再睡一夜。她解釋,她不能白做一回媳婦,她得生個孩子。丈夫想躲避,只是說不,但年輕的大芝娘產生了一種衝動的力量,她拉住“丈夫”的手腕,將飽滿、堅挺,像要迸裂的胸脯擠壓到“丈夫”的身上。大芝娘發動攻勢並非為了性慾,而是為了要生一個孩子。
創作背景
創作靈感
《麥秸垛》的取材故事都發生在河北鄉村,作者把表現女性的人性本原及女性的命運放在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經濟和文化的大範疇中去加以考察。
鐵凝在孩童時,其保姆奶奶對她無私的愛一直影響到鐵凝的成年,從而形成作者對聖母形象終生的迷戀,例如《麥秸垛》中的大芝娘就是這樣的形象。
人物介紹
楊青
楊青端莊、穩重,富有心計,以一種守望者的姿態默默愛著、控制著陸野明。以她的穩重和有分寸能煽起陸野明的愛火,又能夠順利地平息它,決不會讓愛沖昏頭腦,作出越軌的事。她的愛含蓄節制,與陸野明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距離。正是她表面的雍容大度和得體內斂使她贏得了人們的信任和認可,即使在她佯裝糊塗出賣了沈小鳳時,也沒有遭到任何的指責,也正是她的得體大度,進一步促成了陸野明和沈小鳳在麥秸垛的交融,使陸野明 永遠遠離了沈小鳳。更是她的寬容大度再一次牢牢控制住了“失足”後的陸野明。
沈小鳳
沈小鳳愛哭、愛笑、敢愛、敢恨,有著鮮活的生命力。她主動向陸野明展開愛的進攻,毫不掩飾自己的愛欲渴求。“麥秸垛”事件後,她想到的是開脫、保護陸野明,而將責任攬到自己頭上。她是真誠的,同時又是透明的。沈小鳳的方式是以自 己作為女性的魅力和愛的無遮攔表露吸引著陸野明,不斷升溫的愛火終於燃燒了起來,她的種種舉動都是講究女性應該含蓄節制感情的傳統道德所不允許的。
沈小鳳帶著對愛情的體驗、對愛欲的渴望與陸野明偷嘗了禁果。她要生孩子,是因為愛陸野明,在孩子身上延續對陸野明的情愛,當然最重要的也是她僅僅能抓住的把陸野明留在身邊的救命稻草。孩子並不是她想要的結果,只是負載愛情的工具而已。沈小鳳的主動大膽、敢於衝破常規的戀愛方式是知青和端村人所不能接受的。沈小鳳則是不顧廉恥的欲望的化身。沈小鳳是輕浮、媚惑男性的“狐狸精”。
大芝娘
大芝娘四十多歲,她身材粗壯,胸脯分外地豐碩,斜大襟褂子兜住口袋似的一雙肥奶。 每逢貓腰幹活,胸前便亂顫起來,但活計利索。大芝娘有寬宏大度、忍讓、以德報怨的性格特徵,在她身上有種種傳統的美德。她像大地一樣豐滿、結實、富有生命力。她本以為可以嫁夫隨夫,但丈夫在部隊提乾後以“包辦婚姻,沒有感情”為由向大芝娘提出離婚。離婚後的大芝娘要求前夫給她“留”下一個孩子。本來母女倆可以有滋有味地生活,但不幸卻再一次降臨到她的身上。在 女兒離她而去的日子裡,大芝娘以自然母性的胸懷接納了五星、沈小鳳。甚至在經濟困難時,把前夫的一家大小接到農村,大芝娘的純樸厚道和寬廣胸懷得到了端村人的敬重。大芝娘是善良母性的象徵。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麥秸垛”豐滿結實,散發著原野的馨香
在《麥秸垛》里,女性有一種身體被懸置的狀態。“麥秸垛”在某種意義上幾乎成為性的禁忌的象徵。“麥秸垛”這個意象,它是性的暗喻的同時,又在文本里充當了禁忌的角色。而禁忌之下,必有欲望。也就是說,“麥秸垛”是作為一個矛盾體存在的,是身體與性是否能夠打破禁忌而獲得實現,實現後又當怎樣的隱喻。女性在走出身體解放這一步後,到底能獲得什麼?沈小鳳這個形象給出了一個答案,她積極主動的性姿態,最後是失敗的。她的失敗,是女性爭取身體自由的失敗;她的失蹤,成為一個懸疑,或者意味著女性身體的最終懸置,它的主動姿態沒有獲得外界環境的認同。
儘管她獲得了一次性,但這個獲得比起楊青的自我束縛更具悲劇性。它成了“在”而“不在”的“在場”,這種“在”是被剝奪的“在”,是實實在在的被缺席。而楊青更多的是在大芝娘那裡獲得一些女性的體認。大芝娘豐碩的胸脯能讓她腿上生出許多勁來,這看起來有點荒唐的表述實際卻是在那個無名時代,個體獲得的一個外界參照物。知青是沒有性別的,楊青對於大芝娘胸脯特殊的感覺,正是因為她從中有了一種身體的實在感。這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楊青身體的被懸置,她對沈小鳳的報復,也證實了她對沈小鳳獲得性的嫉妒。乳房,是女性的第二性徵,是哺育的象徵,隨著文明的發展,它又摻進了性的成分。豐碩的乳房,無論是作為哺育還是作為性觀看的對象,它都是具有不容置疑的成熟性的。而《麥秸垛》,作者把它們放置在一個寂寞的視角里,觀照著女性的身體,而僅僅是放置,並沒有讓它們獲得實實在在的歸宿,也即懸置。
一個人,如果擁有認同感,就相當於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中的存在獲得了依據,他的一切思想、 言行都有了一個完整的“內在參照性”,對自我的需求、身份、所處環境都有一個明確的界定。因此,他的行動是富有指導性和目的性的。所以,一旦一個人失去了承諾和自我的確認,他就會感到不知所措,無法判斷事物對他的意義。
就像《麥秸垛》里的沈小鳳,她也會像大芝娘那樣要求生一個孩子,這與其說是對大芝娘的認同,不如說是沈小鳳存在著認同的危機,她在她自己的事件里處於一種無力的狀態,並對事件缺乏判斷的能力。她的消失是作為一種女性主體性的消失。無法獲得的孩子,似乎隱喻了女性無法獲得的自我認同感。
在《麥秸垛》中,作者通過大芝娘這一形象,書寫了原始母性的震撼力以及女性在傳統母性重負下女性生命意識的殘缺與生存的窘境。作者把傳統母性置於廣闊的社會現實和女性的生命旅程中進行理性思考,揭示出女性生命在母性光環遮蔽下被壓抑、遭損害的可悲現實。大芝娘似乎是個已經生活了一兩千年的人物,她有著健壯、豐盈、瓷實的身體,“黑褲子裡包住的臀部撅得挺高”,“胸脯分外地豐碩”,這些生理特徵表現出女性旺盛的生命力,但卻僅成為她生殖能力與母性價值的證明。她結婚三天丈夫就離開了她,苦等幾年,等來的是丈夫對她的拋棄。但是,她並沒有表示出對男人的怨恨,反而在與男人離婚後又追到城裡,要求跟男人生個孩子。對她來說,能有一個孩子就不算“白做了一回媳婦”,就有了活著的希望和信心。
果然,當女兒大芝出生後,大芝娘一顆心“徹底踏實了”,她不要男人分文,沒命地勞作,一手將孩子拉扯大。可不幸的是大芝死於非命。在此後的日子裡,她又以博大、寬厚的母性情懷接納了本村孤兒五星、知青沈小鳳,給她們以母愛的滋養、安撫。她的純樸厚道和地母般的情懷得到了全村人的敬重。然而,贏得了“母親”的地位,並不能掩埋她作為女人的真實需求。從一而終的貞操觀使她失去了追求正常婚姻生活的勇氣,卻使她養成整夜不停地紡線和親近一個在被窩裡被磨得發亮的布枕頭的習慣。大芝娘對生命欲望決然拒斥的生活方式,極度地抑制了她自己正常的生命欲望,她只能通過非正常的渠道尋找慰藉。顯然這是人的本性的異化,是一種極為殘忍而非人道的異化。這暗示了大芝娘在母性光環下被迫以勞作和物戀替代、發泄自身生命欲望的畸變人生。
大芝娘就像原野上挺立的“麥秸垛”一樣,豐滿、結實,富有生命力,散發著原野的馨香,包容著大地的苦難,表現出自然母性的震撼力。父權社會中的婦女,也僅僅是在母親的意義上,才能得到家庭的認可和社會尊重。
對於大芝娘這類傳統母親來說,丈夫是她們從一而終的依靠,生兒育女是她們全部的人生意義。當這依靠失去,能夠使她們堅韌地活下去的動力就只剩下無私、崇高的母性了,而在“母親”這一光環束縛下,她卻常常無法抵達通向妻性的幸福和自我身份確認的道路。大芝娘人生的殘缺,體現出傳統神聖化的母性是對女性自然生命的背離,其中隱藏著對女性殘酷訓練的文化布置,傳播的是一種扭曲的、畸形的母性意識。因而,鐵凝沒有賦予大芝娘真實的姓名,暗示她看似有名,實則處於“無名”的生存狀態,表達出對傳統母親不合理生活方式的否定態度。
作者以《麥秸垛》呼喚自然母性的回歸,張揚健康的、美好的母性意識和母性情懷,從而顯露出重建母性的希冀,以捍衛人類的精神健康和心靈高貴。
在父權制社會裡,女性無論是身體還是思想,都處於一種被放逐狀態,是被由男性創造的男性體制所強迫放逐的。女性是作為“物”而存在,是去思想化,去主體化的。在傳統的男女兩性分化中,女人只不過是男人的一種隱喻手段;只有男人才有性別特徵,女人永遠只是男人的一種比喻化的替身。 因此,這种放逐充滿了壓抑的質地,一旦這種壓抑到達了一定的限度,女性便開始具備了反抗的願望。在意識到這種壓抑之後,女性開始思考自身的存在,並努力尋找存在的意義和存在的合理依據。
藝術特色
鏡像敘事
《麥秸垛》在敘事過程中,一方面讓那些“舊事”和“新事”轉換成一種形象化的存在,通過形象之間映照、折射來表現意義;另一方面,由於有了映照和折射,“舊事”和“新事”就都被納入統一的敘述空間,加以戲劇化的對比和流轉性的觀照,從而推動了敘事節奏不斷向前發展。
《麥秸垛》主要寫一男二女的愛情故事,這是該小說敘述的現在時態。《麥秸垛》還講述了在麥秸垛旁發生的過去的事情,栓子大爹和老效媳婦、老效的故事,這是《麥秸垛》呈現的舊事。舊事和新事處於同一敘事空間中,致使該文本呈現兩組同比性鏡像關係:一組是沈小鳳與大芝娘之間的關係,一組是小花、小花丈夫、小池與栓子、老效媳婦與老效之間的關係。在“昨天”,大芝娘結婚三天,丈夫就離家參戰,最後盼來的是與她離婚,並要生養個孩子;在“今天”,沈小鳳為留住陸野明的愛想跟他生個孩子。在“昨天”,老效為換皮鞋不惜將自己的妻子作為籌碼,女人只是男人的被捆綁的工具;在“今天”,四川姑娘小花為躲避貧窮與挨打,懷著孕來到端村與小池結婚,後又挺著肚子被四川丈夫帶走。
雖然時代在不斷向前發展,人們的思想還是沒有變化。如果說栓子大爹、大芝娘一代被作為舊事,沈小鳳等接受過現代文明教育的一代是新事的話,舊事和新事並沒有本質的不同,女人永遠只是男人思想的附庸,永遠是作為物而存在。如果作者不敘述大芝娘離婚後的舉動,僅僅寫到沈小鳳為留住陸野明的愛而想生個孩子這一層,雖然也能看出沈小鳳身上潛藏的傳統奴性,卻無法將女性整體的命運深入地揭示出來。正是因為有了關於大芝娘的敘事,舊事和新事之間相互映照,從而揭示了兩代女人悲慘命運的永恆輪迴,產生了敘事張力,這種鏡像關係的內涵,才變得更豐富了。另外,大芝娘在離婚後仍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即使在大芝死後,她把自己關在屋裡調整好心緒之後又出來做事,從此渾身仍然洋溢著生命的光彩,而沈小鳳在尋愛而不得後就消失了,二人在存在相同命運的同時,又因不同的性格特點和文化因襲而選擇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作者把大芝娘作為民族生命力的象徵,在批判她保守的同時給予了更多的尊重與理解。作者借大芝娘這一母親形象,傳達了對女性內在精神匱乏和對傳統文化的雙重質疑。而大芝娘這一母性形象,也以 其獨特的性格魅力豐富了新時期文學史的畫廊。
詞語意象
1、麥秸垛:“麥秸垛”具有濃厚的象徵意蘊,它既是歷史的見證者,又是悲劇的衍生地,它記載著過去、現在和未來。“麥秸垛”作為一個無所不在的存在物,實際上無形中已成了端村人心目中的“圖騰”,只不過在種族無意識的“遺傳”過程中已變相移植。它和原始圖騰的人類學涵義的區別在於外觀形式的變化:端村人並不象原始人那樣虔誠地在它面前舉行最莊嚴、神聖的儀式,載歌載舞,以祭祀祖先不朽的在天之靈,祈禱上蒼對子民的慷慨恩賜,以此來獲得一種虛假的力徽和安慰,在祖先魂靈的庇佐下確保部落的安寧。可它和遠古的圖騰崇拜另一類涵義卻是不謀而合——對生命本能、生命之力的迷狂和崇拜。雖然該小說中活動著的當事人並沒有任何一個直接在觀念意識中確認“麥秸垛”的“圖騰價值,可在無意識中“麥秸垛”已幻化為端村人種族記憶、生命綿延的見證及“神”。在“麥秸垛”這位無形之神的保護與遮蔽下,種種撩人心魄的“故事”就在這裡發生了——所有的瘋狂和痛苦、所有的喜悅和絕望以及種種坎坷,種種辛酸,種種令人恐懼的生命之輪迴。
2、太陽:在《麥秸垛》中,該文本四次提到“白得發黑”的太陽,作者賦予太陽以象徵的意義,象徵那遙不可及、那神聖、耀眼、絢爛的愛情,人們為了追求愛情,上演了一幕幕愛情悲劇,使絢爛的愛情罩上了暗淡的色彩。在蒼天之下,厚土之上,愛情無處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作品評價
《麥桔垛》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悲劇作品。
《麥秸垛》有尋根文學的文化語境的折射。
——王寧寧(北京廣播電視大學文法部副教授)
作者簡介
鐵凝,中國當代作家,1957年9月生於北京。祖籍河北趙縣。1975—1979年,在河北省博野縣張岳大隊插隊。1979—1980年,河北省保定地區文化局創作組創作人員。1980—1983年,在河北省保定地區文聯《花山》編輯部編輯工作。1983—1986年,成為河北省文聯創作室專業作家。1986—1992年,任河北省文聯副主席、省作協副主席。1992—1996年,任河北省文聯副主席,省作協主席。1996—2001年,任中國作協第五屆副主席,河北省作協主席,省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協第六屆副主席。2006年1月,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第七屆主席。作品有《
鐵凝日記》、《
大浴女》等。
 鐵凝
鐵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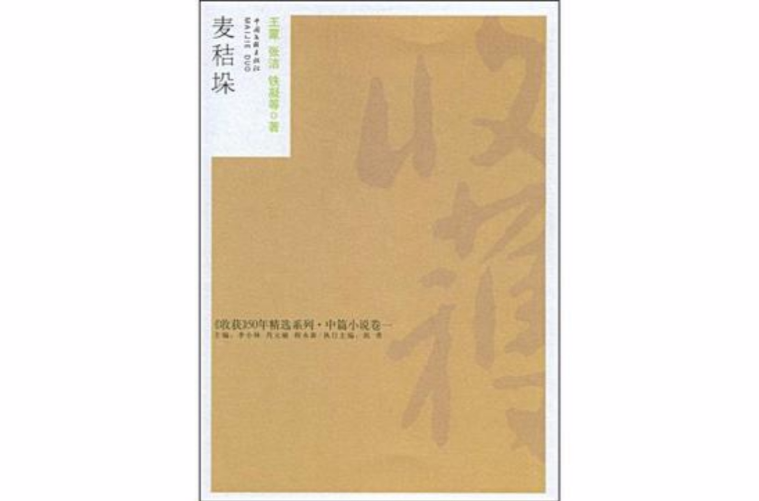
 鐵凝
鐵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