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家,中國戰國末至漢初的哲學學派。以博採各家之說見長。以“兼儒墨,合名法”為特點,“於百家之道無不貫通”。《漢書·藝文志》將其列為“九流”之一。雜家的出現是統一的封建國家建立過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結果。雜家著作以戰國《尸子》、秦代《呂氏春秋》、西漢《淮南子》為代表,分別為戰國時期商鞅門客尸佼秦相呂不韋和漢淮南王劉安招集門客所集,對諸子百家兼收並蓄,但略顯龐雜。又因雜家著作皆以道家思想為主,故有人認為雜家實為新道家學派。“雜家”並不是一門有意識、有傳承的學派,所以他也並不自命為“雜家”的流派。紀昀在《雜家類敘》中則認為「雜之廣義,無所不包」。胡適先生在其《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中指出:“雜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雜家的新名。漢以前的道家可叫做雜家,秦以後的雜家應叫做道家。研究先秦漢之間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認清這一件重要事實。”雜家的代表人物,一是淮南王劉安(《淮南子》),另一是編撰《呂氏春秋》的呂不韋。雜家在歷史上並未如何顯赫,雖然號稱“兼儒墨、合名法”,“於百家之道無不貫綜”,實際上流傳下來的思想不多,在思想史上也沒有多少痕跡。 現代科學越來越細化,“雜家”這稱號,現在基本上說的就是此人沒有專業本事,什麼都知道一點,但什麼都不精通的意思。
基本介紹
主張
著作
呂氏春秋
淮南子
 《淮南子》&amp
《淮南子》&amp尸子
 尸子
尸子代表人物
尸佼
 尸佼頭像
尸佼頭像呂不韋
劉安
 雜家淮南王劉安雕塑
雜家淮南王劉安雕塑先秦雜家學派
從《呂氏春秋》看秦道家思想特點
在道家重生、尊生的共同點上,秦道家提出人如何對待情慾的問題。呂氏春秋學派作《情慾》篇劈頭便說:“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認為面對情慾,不必迴避;也不同意“寡慾”的主張,而強調“六欲皆得其宜”(《貴生》)。這主張不同於原始儒、道對情慾之一味採取克制的態度,頗有助於個性的發展。
在治身與治國的兩大課題上,秦道家主要目的雖在治國取天下,但卻強調治身為先、為本,故《呂》書《十二紀》開卷便列示《本生》、《重己》、《貴生》、《情慾》、《先己》諸篇,言治身之道,強調“凡事之本,必先治身”。
秦道家繼承莊子之重視個體生命而提出“貴生”之說。“貴生”、“重己”要在形神之養,這是道家各派的共通點。故而秦道家也談到養生之道,必使飲食得宜,精氣流動,“精神安形”,得以延年益壽(《盡數》)。人活在世間,“莫不欲長生久視”。而“長生久視”之道,要“神和”(《本生》)、“安性”(《重己》)。這也是道家各派的相同處,但“安性”就必先“順性”,順性則需順導情慾,在這一人性基點上,就突顯出秦道家的特點了。
首先,秦道家肯定情慾是與生俱來的,並認定“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12章)。以此老子要人“寡慾”,這主張影響到莊、孟①。但秦道家卻認為耳目之欲五聲、五色,乃人情之常;無論聖與凡,七情六慾乃人之所同然。秦道家生動地舉例說明情慾順與逆的不同效果:“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木卷,而牛恣所以之,順也。”(《重己》,下引同)這生動的例子,曉諭人不當逆欲而行。“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以此,秦道家首要提示吾人當正視情慾的正當性,並由順欲而提出“適欲”的主張。
在《貴生》篇,秦道家進一步明快地提出“六欲得宜”的主張:他們引子華子之言:“全生為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為下。”並對子華子的話給予新的詮釋:“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故曰迫生不若死。”這些話都說到人的心坎里,比起原始儒家以無欲克己,板起臉孔說聖人之教,要更為合情合理。人有欲,欲要有所順②,但秦道家並沒有走向縱慾的路子,他們一方面提示吾人當正視欲的需求及其正當性,同時由順欲而提出“適欲”的主張。
“欲有情,情有節”,《情慾》篇認為情慾之動,必自貴生出,“由貴生動則得其情”,“得情”之說,與莊子後學任情、達情(“任性命之情”、“達性命之情”)相通。我們讀歷代道書與儒書,寡慾、無情或惡情,甚而以性禁情之聲,不絕於耳,頗有壓抑個性的沉鬱感,而秦道家適欲得情的主張,頗有助於個性的張揚。
——————————————————————————————————
①孟子也強調“寡慾”(見《孟子·盡心》),可能直接源於老子或間接源於稷下黃老。
②《呂》書《為欲》篇說:“善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但還警惕著:“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
認為得欲的確當方法,要“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就是說要審慎地依順人的本性去滿足欲望。
秦道家思想的第二個特點是強調生命之動出。
主虛靜是為道家的重要標誌之一,但秦道家則於動靜相養中提出主動說。
老子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如有無相生、虛實相涵、動靜相養。“動”、“靜”作為哲學一對範疇,和“有”、“無”一樣,成為整箇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概念。一般人都知道老子主靜(如謂“靜為躁君”),但忽略他是以動靜相養為前提。如《老子》15章說:“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這句名言意謂動極宜靜、靜極宜動,這是動靜相養的最佳說明。而老子重視“動”的一面,常為人所忽視,如他認為道體是恆動的(“反者道之動”、“周行而不殆”),他說天地之間是“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這都說明“動”的重要性。然而,無論如何,老子之主靜,已深入人心,而且對後世的影響也以主靜為最①。
秦道家以其朝氣蓬勃之勢,在老子動靜相養而主靜的思維中,提出主動說。他們從精氣之流動與會聚作論證。精氣是一切生命的本原,精氣之流動與會聚使一切生命煥發光輝,《盡數》篇說:“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集於走獸與為流行,集於珠玉與為精朗,集於樹木與為茂長,集於聖人與為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這裡繼承《內業》的精氣說,但跨過稷下黃老靜心以集氣的主靜觀,而由氣體之恆動以論證生命之動出:“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盡數》)秦道家由客觀事物之“動而愈出”,說到生命需在動中維繫其動力,在動中發揮其創造機能。
《達郁》則由人體生命的運行暢通,申論國政民意之宜流傳暢達。精氣鬱結則惡疾滋生,自然界現象亦然,所謂“水郁則為污,樹郁則為蠹,草郁則為蕢。”國政亦有鬱結:“民欲不達,此國之郁也。”為政的決郁之道,在於廣開言路,要人民“敢直言而決鬱塞”。這是秦道家主動說延伸到現實政治層面的義涵。
在禮樂文化領域裡,秦道家突破了原始道家的局限,開闢了寬廣的園地。
老莊對於禮樂是採取潛移默化的“不言之教”;老子論樂有其辯證觀點,一方面直陳其流弊,另方面隱說其深義。但論者多隻注視前者而罔顧後者。
老子說:“五音令人耳聾”。這話廣為人所引述,但他另外所說“大音希聲”一類的話,卻罕為人所論及。而秦道家則從老子論樂的正面義涵,加以擴充、提升。如老子謂:“音聲相和”(2章)又說:“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35章)。秦道家遂從老子“希聲”之“大音”與“聽之不足聞”的“樂”,提升而為道家的樂論,並將老子“音聲相和”引入樂的教化作用。秦道家論樂,有《大樂》、《侈樂》、《適音》、《古樂》、《音律》、《音初》、《制樂》等篇②,而《大樂》為其代表作。
一般學者多以《大樂》等論樂之作屬儒家作品。陳奇猷先生卻認為這些樂論是“樂家者流之言”,而非儒家之作。因為“儒家重樂,在於樂之實用”而不在樂論③。事實上,我們只要閱覽一遍原文,就可一目了然,《大樂》之作,在內容上全屬道家思想。
————————————————————————————————————
①如《管子》四篇中的《內業》,一直到宋明理學家的主靜,都在老子的影響下。
②《大樂》在內容上全屬道家思想,其樂理自老子道論引出,申說道家“公”、“平”、“和適”之意趣。此外,其他論樂各篇要旨:《侈樂》謂“亻叔詭殊瑰”的樂隊,不用度量,紛繁雜亂,失樂之情。篇旨申論統治者侈樂,必招民怨,如桀、紂侈樂而亡,宋、齊、楚侈樂而衰,此為史鑑。本篇內容亦合儒家旨趣。《古樂》論述三皇五帝至殷周樂舞之由來,本篇作歷史的追溯與繼承並賦予陰陽之總義。《音初》論述古代東西南北各音調之成因。上述各篇為秦道家對樂文化之史的探義。而《音律》,言音律相生之理,乃屬秦道家吸收樂家理論之作。
③見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大樂》注(一)。奇猷先生認為《音律》等篇屬於樂家之言,而非儒家之作,這看法較可取。但他又認為它們屬於“陰陽家治樂者”,奇猷先生在《呂》書中分篇認定其學派屬性時,常將道家作品劃歸陰陽家,這就如同牟锺鑒所批評的:“陳先生把陰陽家泛化了”(《〈呂氏春秋〉道家說之論證》)。
《大樂》意為太一之樂,即道之樂。《大樂》與《適音》是秦道家樂論的兩篇代表作,一著重體,一申說用。《適音》要在宣說“音樂通乎政”,樂之用於治身,則使心和行適,心適則理勝,理勝則利於治國。“先王必托於音樂以論其教”,樂以論教之說,也正是秦道家使儒、道會通之處。
————————————————————————————————
①天道環周思想源於《老子》,如謂:“反者道之動”、“周行而不殆”,郭店簡本《老子》更有“天道員員”之語(相當於通行本十六章)。天道環周論至戰國道家而熾盛,如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雲:“天稽環周”(《十大經·姓爭》)、“周遷動作,天為之稽。天道不遠,入與處,出與及”(《經法·四度》)、“極而反者,天之性也。”(《經法·論》)等,而《呂氏春秋》此處及其《圜道》謂天地車輪之義,亦皆屬道家天道環周論。
②學者多不明道家之託天道以明人事,其著意在人道。一般學者論述儒道之別時,往往以為儒家重人事而道家偏天道;割裂道家之天人關係,並誤以為道家不重人道。
在道家各流派中,秦道家思想獨具開創性,他們不僅在哲學思想上開創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而且在語言風格及其所突顯的人格風範上也是獨樹一幟的。黃老道家在思想內涵上顯然不及老莊的開創性,他們和孔孟一樣,述而有作,無論齊道家或秦道家,其祖述老子卻能掌握時代精神而援禮法以入道,如此為老學開闢了廣大的倫理空間與法制領域。他們的特長乃在於具有寬厚的涵容性。黃老道家之述而有作,即在“述”中採擷百家之長,此即今人所謂“創造性的轉化”,同時也在“述”中表現了他們難能可貴的歷史文化感,這方面的特點在秦道家的著作中尤為顯見。
齊道家已有倡導詩、禮、樂的言論,如《管子·內業》說:“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但從現存的文獻中未見其體現的具體情況。在呂不韋的特殊地位與眼光所支持下編撰的《呂氏春秋》中,體現出秦道家不僅具有試圖統一政局分裂的歷史感,更且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意識。
老莊行文立意,不依傍古人,不攀援詩書,確與儒者論說習慣不同,但論者莫不以為道家無讀經傳統,亦不盡然;學者多以經學傳統的傳承與發展為儒者所獨專,實屬偏見。事實上,《詩》、《書》、《易》等古經為先秦諸子之公共文化資產,墨子、莊周無不熟讀經書。漢武之後,官方獨尊儒術,實行文化專制主義,經學思想生命遭儒生長期禁錮窒息,幸賴魏晉新道家(如王弼之以老莊思想注《易》等)賦予經學以新生命,而《呂氏春秋》、《文子》與《淮南子》則為其先行者。《呂氏舂秋》之援引《詩》、《書》、《易》以為助證,開道家與經學關係之先河,這在道家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故而詳引例證如下:
(一)《貴公》闡發治道尚公,謂“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引《老子》“大匠不”之意,謂“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本文另一名言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篇中將孔子和老子並舉,認為老子的心胸能包容天地,評價高於孔子,而稱讚“老聃至公”,並引《老子》二章“成而弗有”句,以示“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本篇除了引老子言論外,篇首便引《尚書·洪範》:“無偏無黨,……無偏無頗……。”此引《尚書》文意以加強秦道家尚公的主張。
(二)《先己》謂欲治國家當先治身,本篇二次引《詩經》以為助說。一次引自《曹風·屍鳥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再次引《簡兮》(亦見《大叔于田》),謂“《詩》曰:‘執轡如組’……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並引孔子與子華子之言為說。本篇強調治身要在蓄養精氣,並謂如行無為之治,則“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萬民已利矣。”這都是黃老的言論,故本篇作者屬秦道家黃老派。
(三)《務本》論先公後私,與《貴公》、《去私》篇旨相同。本篇徵引《詩》、《書》、《易》以申說公而後私意旨,其引《詩·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以論“三王之佑,皆能以公及私矣”。復引《詩經》:“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大雅·大明》),以言為臣無二心,當“知本”。本篇謂“本在於民”,引《易經》:“復自道,何其咎,吉。”(《小畜·初九》),以言本在民,固本而動,則吉。
(四)《諭大》即從事於大義。引稷下道家季子言論謂:“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以言士人當從事於大義。本篇二引《尚書》以為助證,一引《夏書》:“天子之德廣運……乃武乃文。”(《尚書·大禹謨》)“廣運”,以喻事大。再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此為逸《書》)以申論“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眾多長久”。
(五)《慎人》闡明遇時、遇人且須謹於人事之意。本篇與《首時》、《遇合》等篇同屬黃老尚時之作,篇中引《小雅·北山》以言遇時而慎於人事。
(六)《慎大》闡明“於安思危,於達思窮,於得思喪”之義。篇中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再引《周易·履卦》:“履虎尾,朔心朔心,終吉。”曉喻戒懼從事,以化險為夷。本篇繼承《易》、《書》審惕之志而提示“於得思喪”之旨,這方面亦為儒道相合之處。
(七)《君守》論述君上宜守清靜無為之道。篇中引《尚書·鴻範》謂:“《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陰騭下民”即蔭庇安定下民,此處引《鴻範》之文以證《老子》守靜而能發揮其動出的效果;“不出於戶”、“不窺於牖”是陰覆安定,“知天下”、“知天道”則是“所以發之”。
(八)《適威》意謂君主立威宜適度,不足專恃。用民當依人之情性,並以仁義、愛利、忠信待民。文中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仇也。”此引《周書》說明君主宜善待百姓,百姓就會親和君主;否則就會視君主如仇敵。
(九)《知分》意謂“達乎死生之分”。本篇闡發“知分”之士,當據義行事,豁達處之。本篇論述晏子能安然果敢而行義,並引《詩》以明志。(引文見《大雅·旱麓》:“莫莫葛,延於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
(十)《行論》篇旨言時勢不利,則事仇以求存,等待事便時成而舉事,則功可成。文中一引《詩經》,述文王審慎事上以圖存(引《大雅·大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再引《詩經》論齊泯王驕橫而致敗(引逸《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這詩句與《老子》第三十六章義同)。
以上實例,足證《呂氏春秋》知識群對古典文化的喜好與探研,他們習於徵引古代經學,以助其伸張經世立意而為說,這同時也反映了秦道家具有深沉的歷史文化意識。
先秦諸子多屬“士”的階層,故而莫不以士的立場發願。至老子始標示“善為士者”的理想人格,或以“君子”、“大丈夫”期許①,自後孔、墨繼之,並對士人有諸多寄望。重士之風,乃春秋戰國時代智識階層湧現之時勢使然;重士言論,並非儒者獨有現象,道、儒、名、墨各家皆然,唯各家所標示的人格型態互有差異,乃屬同中之異。即或莊子言士,與老子也有差別。莊子那種“恣縱而不儻”(《莊子·天下》)的風格,所謂“乎其未可制”(《大宗師》),這種高邁昂視的性格,為後學發展而為“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讓王》)的高士,這種型態為孔儒所不苟同。而秦道家則接受《莊子》所倡言的耿介之士,轉而要求統治者接受這群抗頡朝政、不拘於俗的異議分子,《士節》便倡言“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這裡所說的士人,前段顯然融合了墨、孟士人的性格,而“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則是《莊子·讓王》所倡導的。接著《士節》說:“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這裡呼籲賢主要禮賢下士,吸納體制外的異議分子到體制中來。這樣的賢主,是黃老學者理想中的君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正是黃老派的重要主張。《謹聽》也要求當今治者“禮士”,包括尋求這類體制外的異議人士。其言曰:“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侮之內,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報更》也同樣認為“士其難知,唯博之則可,博則無所遁矣”,並要求世主對待高士(“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秦道家的這類言論,與黃老帛書《黃帝四經》正相吻合②。
——————————————————————————————
①“君子”之稱見《老子》31章;大丈夫之稱見《老子》38章。
②帛書《黃帝四經》呼籲國君當尊有道者為國師,謂:“重士有師有道”、“王天下者,輕縣國而重士……賤財有貴有知。”(見《經法·六分》)又曰:“帝者臣,名臣,實師也;王者臣,名臣,其實友也”、“不受祿者,天子弗臣也;祿泊(薄)者,弗與犯難”(《稱》)。
春秋戰國之動盪不安,禍根來自統治階級。由於製造問題與解決問題端賴上層,故諸子多目光朝上提出諍諫、建言。在諍諫、建言中出現民本思想。而諸子中墨派立場較關注“農與工肆之人”(《尚賢》)。老子已強調施政要“以百姓心為心”(49章),並說“高以下為基”(39章),這就是要以百姓的願望為願望,以百姓的意見為意見。秦道家一方面上承老子“高以下為基”的思想,同時採納莊子物各有所長的觀點①,並直接繼承齊道家田駢“用眾”的主張②。
《用眾》篇表達了秦道家難能可貴的貴眾說。其貴眾說有以下幾項特點:
一是取長補短之意。《用眾》謂:“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這些話正反映了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所說的黃老道家采眾說之善的特長。《用眾》還譬喻說:“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這種掇取“眾白”以成裘的方式,也正是《呂氏春秋》作者那種涵容並包的風範的表現。《不二》篇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它論述了老聃、孔子、墨翟、列子、田駢等十家學說的精華,就是從諸子的長處著眼,從而主張“齊萬不同”③,以匡正百家爭鳴時“以是其所非,以非其所是”的缺點。
二是提出“眾知無畏乎堯舜”的特殊看法。《用眾》說:“以眾勇無畏乎孟賁矣,以眾力無畏乎烏獲矣,以眾視無畏乎離婁矣,以眾知無畏乎堯舜矣。”秦道家強調眾勇、眾力、眾視、眾知所匯聚的力量之強大作用,這主張在道家或諸子中是極為特別的。借用今日的話說,諸子不免都有“優異分子”的傾向,例如主張教化成德的孔子就認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眾人(小人)只像是隨風吹動的小草。到了孟子,這個觀點更上一層樓,他對人治誇大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梁惠王》),認為聖王一出現,一切問題都可得到解決。孟子對於堯、舜、文、武一類“聖王”的個人作用之無限上綱,和《用眾》“眾知無畏乎堯舜”的主張,成了鮮明的對比,也糾正了儒家神化統治者個人功能的誇張性。同時,秦道家的貴眾說也彌補了老莊思想中濃厚的個體意識。
貴眾說的第三個特點是提出“君之立出乎眾”的逾時代意義主張。在古代,王位的取得及君權的來源等問題,總要染上天意授受一類的神話,即使在孔、孟思想中都不免透露出這痕跡。宗法世襲制行之已久,弊害顯見,墨子對儒家主張的宗親血緣政治做出猛烈的批評,如謂“骨肉之親,無故富貴”(《尚賢下》),僅僅緣於“骨肉之親”,連白痴都肆居高位而享特權,因而禪讓說的提出實已是對世襲制的一種挑戰。戰國黃老對王權的更替原來就有相當新穎而具突破性的主張,例如慎子便曾說出政權可以更易,國君可以改換的話④;再如稷下道家作品《白心》篇出現以武王伐紂媲美政權篡奪的言論⑤。在稷下黃老的這種思想空氣下,即使連孟子也曾說過這類出格的話⑥。這些言論在當時都是富有“革命性”的意見。秦道家則進一步對君位來源及君民關係提出如此言簡意賅的觀點,《用眾》說:“凡君之所以立,出乎眾也。立己定而舍其眾,是得其末而失其本。”這裡,提出兩個十分根本性的主張,一是君位出於民眾的說法;另一是民為本君為末的觀念。後者比孟子民貴君輕之說更跨進一步,而君民為“本末”關係之說,這觀念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顯然,《呂氏春秋》這種逾時代的主張和秦始皇的理念根本截然對立,這類主張便足以使呂不韋招致殺身之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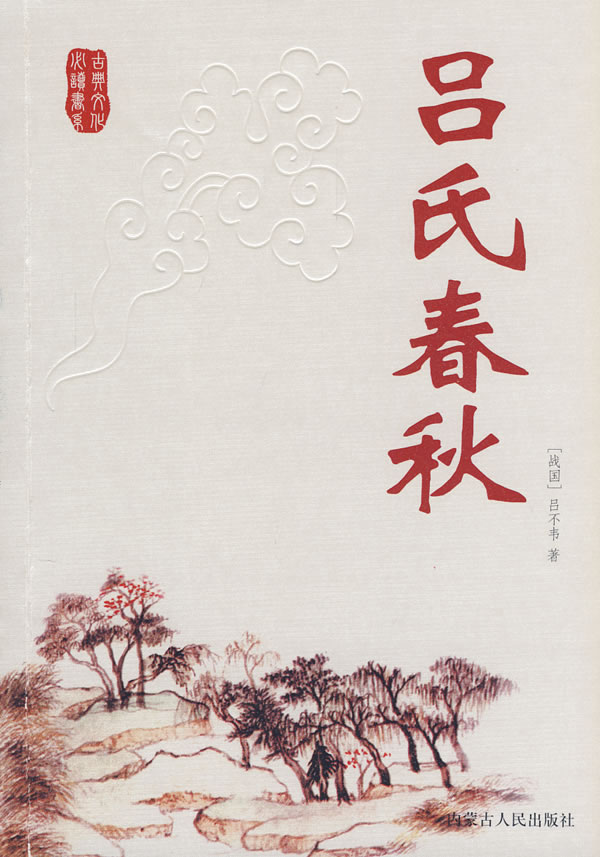 《呂氏春秋》圖書
《呂氏春秋》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