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劇情
蘇夢枕孤高寒傲,智計天縱,膽色過人,雖自小身罹重疾,卻因體質羸弱之故,反把他生命的潛力逼發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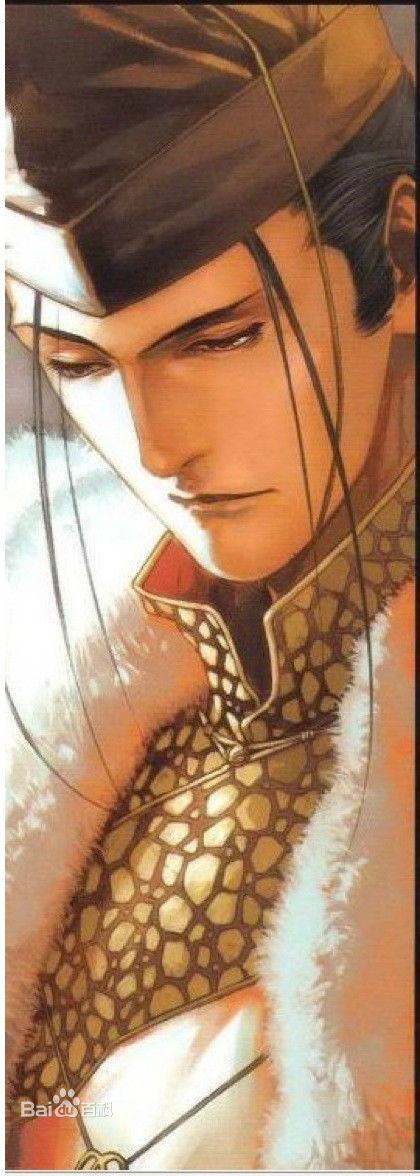 蘇夢枕
蘇夢枕他的「黃昏細雨紅袖刀法」自成一家,在刀法上已不在其師紅袖神尼的「紅袖刀法」之下。
蘇夢枕武功高,權位顯,仍畢生以國家興亡為己任,主張拋頭顱、灑熱血,共赴國難,退逐外敵。
更難得他重情重義,恩以待人,對兄弟部屬決不懷疑。
然而,也正因為這「決不疑」,故雖有
王小石的忠心不二,也有
白愁飛的引狼入室,而自己兄弟令人心寒的背叛,在很大程度上間接地促成了他的死亡。
蘇夢枕是狂傲的,他的狂,是輕漫的疏狂,他的傲,是侵骨的寒傲。
「一夜盛雪獨吐艷,驚風疾雨紅袖刀」,蘇夢枕是風雨樓的蘇夢枕,獨一無二的蘇夢枕,沉疴在身卻不減其英風銳氣,朝不保夕仍無人能挫其鋒,閱盡金古梁溫四家書便只此一人。
他的生命儘管短暫,然其間的沉浮起落、雪雨風霜,莫不是動心動魄,可感可嘆,宜泣宜歌。
縱觀其一生,果真當得起他自己所說,「我活過,大多數人只是生存!」蘇夢枕雖逝,但他的事業,一定還有人繼續,他的精神,一定還深深留在每一位金風細雨樓子弟的心中,留在故事外讀者們的心中。
能力設定
【姓名】:蘇夢枕
 金風細雨樓樓主—蘇夢枕
金風細雨樓樓主—蘇夢枕【外號】:「夢枕紅袖第一刀」
【事業】:為抗外敵,廣結豪傑,同赴危艱,兼以主持正義,扶弱鋤強
【夢想】:驅除韃虜,收復失地,恢復中原
【門派】:「小寒山派」
【師承】:紅袖神尼
【武功】:「黃昏細雨紅袖刀法」,刀法淒艷詭譎,快而凌厲;輕功不詳,推想應為「
瞬息千里」身法,與小師妹溫柔相同;內功不詳
【兵器】:「
紅袖刀」,刀略短,刀身緋紅,刀鋒透明,與
王小石的「
挽留劍」、
方應看的「血河劍」及
雷損的「不應刀」並稱為「血河紅袖,不應挽留」
【出場】:《溫柔一刀》第一章「雨中
廢墟里的人」,第十節「人·魚」,現於苦水鋪雨中廢墟(
六分半堂勢力範圍)
【死亡】:《傷心小箭》第四篇「
狄飛驚的驚」,第六章「一路拔劍」,第二節「我活過,他們只是存在!」,歿於金風細雨樓
人物關係
【父】:蘇遮幕,金風細雨樓創建人
【未婚妻】:
雷純,本與蘇有婚姻之約,後終因殺父之仇而反目
【結拜兄弟】:
二弟:白愁飛,個性傲岸自負,擅“
驚神指”,傾心於
雷純。曾與王小石齊心力助蘇剿殺雷損,後背叛,意圖弒兄篡位。蘇因毒傷沉疾在身不敵,受到重創,乃隱忍不發,託身於六分半堂,最後反撲成功,殺白復仇
三弟:
王小石,個性隨和豁達,擅刀劍,傾心於溫柔,因力誅當朝奸相傅宗書逃亡在外三年,致蘇為白所趁,後回歸京師,問罪於白,欲為大哥討回公道,參與圍殺白愁飛之役,蘇死後接任金風細雨樓樓主
【同門】:
溫柔,為蘇夢枕小師妹,容貌極美,喜著紅衣,個性天真活潑,大小姐脾氣,常惹禍生事,使“星星”刀法,刀法稀鬆,輕功“瞬息千里”身法卻是一流
溫夢豹,為蘇夢枕二師弟,人稱“溫坑王”,六扇門兵工廠廠主。濃眉大眼,脾氣不好,辦事直接有效,使“黑雲翻墨刀”。對蘇夢枕甚為崇敬。
【盟友】:
諸葛正我(諸葛小花)及其座下四大弟子“御賜四大名捕”——成(盛)崖余(
無情)、
鐵游夏(
鐵手)、
崔略商(
追命)、
冷凌棄(
冷血),他們代表了朝廷主戰派的官方勢力,與金風細雨樓所代表的江湖白道勢力互為奧援,以維護京城內朝野各種勢力力量的動態平衡
【主要屬下】:
“五大神煞”——上官中神上官悠雲(死於六分半堂二堂主雷動天)、郭東神雷媚(臥底六分半堂,為堂中大將,殺雷損者)、莫
北神(“無發無天”領導者,六分半堂臥底)、薛西神(化名“趙鐵冷”臥底於六分半堂)、刀南神(“潑皮風”部隊領導者,手握京師軍隊二成實力)
“無邪無愧,無錯無語”——楊無邪(風雨樓總管,
白樓資料掌管者)、師無愧(蘇忠心護衛)、花無錯(六分半堂臥底奸細)、余無語(與花無錯同為六分半堂奸細);茶花、沃夫子(在苦水鋪一役中因護主而死)
【主要對手】:
雷損,六分半堂總堂主,為人陰梟,
老謀深算,擅“密宗快慢九字訣”,與蘇乃是一山難容二虎。雷先與蘇合力剷除“迷天七聖”盟勢力,逐走盟主關七,始放手與蘇一較高下,後終因棋差一著,死於蘇部屬郭東神劍下
關木旦(
關七),“迷天七聖”盟七聖主(即
盟主),人雖半瘋然武功極高,於圍困關七之役中被蘇斬斷一臂,又遭雷擊後傷重,在“有橋集團”人員暗助下遁走逃逸,迷天盟就此
瓦解狄飛驚,六分半堂大堂主,為人低調,
城府極深,對主極忠,武功深藏不露,擅“大棄子”擒拿手法,乃雷損一手栽培,為其心腹得力助手。狄一直韜晦潛藏,與風雨樓
最後一戰遵雷損之令未曾參與,故得以保全,在雷損死後仍繼續與雷純共同領導六分半堂,與金風細雨樓為敵
雷純,容貌柔艷中帶殺氣,笑意里掩憂愁,“遇雪尤清,經霜更艷”,是蘇夢枕的心上人,其父死後繼任六分半堂總堂主,不會武功。雷純極工心計,心機深沉,身為一介弱女子,卻能領導六分半堂這武林一大黑道幫會屹立不倒於
風雲詭譎的險惡江湖。白愁飛反叛後,收留蘇夢枕,助其恢復地位,實暗中下毒相害,意圖縱控,怎奈蘇寧死決不願受制於人,雷純謀劃落空。
人物經歷
蘇夢枕,疑似蘇軾後人(虛構,詳見《
江湖閒話十五·蘇夢枕的夢》),祖籍
應州,父親蘇遮幕。自小受遼人侵略
大宋所禍,家人諸多罹難,自己也在襁褓之中受了嚴重內傷,此後一生體弱,身染諸多重疾巨患。師承父親的好朋友、小寒山派掌門紅袖神尼,得其親傳紅袖刀法。更因本身是武學奇才,且其寒弱體質與淒冷性情恰與紅袖刀法的陰柔之氣相得益彰,將紅袖刀法練至更勝其師的化境。後得師父親傳紅袖刀,藝成後下山赴京城助其父創立“金風細雨樓”的基業。
後其父病故,蘇夢枕接掌風雨樓大權,短短數年間,將“金風細雨樓”由依附時為京城第一大幫派“六分半堂”生存的夾縫幫會,發展為可與“六分半堂”
分庭抗禮的一大勢力。蘇夢枕本人也在這段時間內聲名大振,成為萬人敬仰的蓋世英豪,當時武林公認在刀法上難遇敵手的“紅袖夢枕第一刀”。此後,“金風細雨樓”與“六分半堂”勢力爭鬥愈發激烈,衝突漸至
白熱化階段。
是時,蘇夢枕於京城“苦水鋪”中遭親信伏擊,偶遇來京城闖蕩的
絕世高手白愁飛、王小石二人,三人並肩作戰化解危機。蘇夢枕於此役折損兩名兄弟,自己也身受重傷。然其果決睿智,不退反進,深入敵人重兵把守之處如入
無人之境,
電光石火之間斬殺叛徒為友復仇,而後從容離去。這份膽識、武功與氣度也使得白、王二人心悅誠服,三人英雄相惜,義結金蘭。
距當時十八年前,“六分半堂”總堂主雷損曾將自己的女兒雷純許配給蘇夢枕。三人結義,兩派相爭,正是距二人婚禮不足一月之時。蘇夢枕雖與雷損大有一山不容二虎之勢,卻對雷純傾心相愛。考慮到婚禮過後兩派關係更加錯綜複雜,且朝廷及其他勢力也在插手京城局勢,最終決戰
迫在眉睫。大戰一觸即發,經過一系列明爭暗鬥,在雙方機關算盡喋血相爭之後,蘇夢枕終於棋高一著,在極其險惡的情況下以微弱優勢勝出,卻也因此舊病新傷其發,徹底挎掉了身體。雷損死前,求蘇夢枕放過雷純。蘇夢枕毫不猶豫地選擇答應。
此後,由於在“苦水鋪”一戰中曾受暗算,一條腿上沾染劇毒,萬般無奈之下只好截除。自此蘇夢枕長期臥病,樓中事務多交給二弟白愁飛處理。但白愁飛權欲過重,一心登天,很快藉故迫走三弟王小石,並在樓中培植勢力,企圖獨攬大權。蘇夢枕從不懷疑兄弟,又愛才如命,對其不但不加阻攔,還多有扶持。白愁飛的勢力膨脹到難以控制,便決定狙殺蘇夢枕,弒兄篡位。蘇夢枕傷病在身,又被白愁飛收買的親信下毒,本來已決無生還可能,卻早已未雨綢繆,預先安排好退路,
金蟬脫殼,得以脫身。白愁飛占據風雨樓,卻始終未有蘇夢枕身死的訊息。這時三弟王小石回到京城,漸漸洞悉真相,立志為大哥報仇。
風雨樓決戰之夜,本要絕情斷意剷除後患的白愁飛,卻發現了遠處六分半堂的人影。現任總堂主雷純與大堂主狄飛驚,以及一座神秘的轎子不速而來。轎中人緩緩掀起簾幕,竟是蘇夢枕!王小石喜極,兄弟二人再度聯手,白愁飛眾叛親離,終於身死。
此時的蘇夢枕,卻忽然說了一句讓全場震驚的話:“他死了,下一個就輪到我了。”
而後他開始交代後事,將風雨樓全部勢力盡歸王小石繼承,囑咐他務必行事磊落伸張正義。王小石不解問為何,蘇夢枕坦然道出實情:他脫身的暗道出口正是六分半堂,而救他的人正是對他愛恨交加的雷純。雷純為控制蘇夢枕為自己所用,給他下了擾亂心智的毒,一旦雷純開口唱歌,蘇夢枕便再無半點自主。蘇夢枕大仇已報,決不願為人所制,做那
禍國殃民的惡事,但求一死。雷純聞言大驚,立刻開口唱歌企圖控制其心,不料蘇夢枕早已安排親信,在他被控制前毫不猶豫地對他動手。“我活過,大多數人只是存在。”霎時,
金剛杵砸下,他眼中的寒焰,也緩慢地,永遠地,走向了熄滅……
原著片段
【首度出現】
王小石抹去發上的水珠,笑道:“這雨,下得真大啊!”
白愁飛伸長脖子張望天色,“這雨可得要下一陣子──”忽然看見四個人,冒雨跑了進來。
經過這廢墟前的一條小路,一旁儘是
枯竹葦塘,另一旁則是民宅破居,這小路卻有個好聽的名字,叫做“將軍胡同”,這四人便是從牆角旁閃竄出來的。
由於躲雨之故,行色匆匆,白愁飛也不覺詫異。
四人進入廢墟里,兩人留在入口處探看,兩人走了進來。
進來的兩人中,有一個甚是高大、威猛、
相貌堂堂,精光矍矍的眸子往王小石和白愁飛橫掃了一眼。
另一人忽然咳嗽了起來。
咳得很劇烈。
他用手帕捂住嘴唇,嗆咳得腰也彎了,整個人都像龜一般縮了起來,連聽到他咳聲的人都為他感到斷腸裂肺的艱苦。
那高大威猛的人想過去替他揩抹淋濕了的衣發。
咳嗽的青年搖首。
他手上的白巾已沾上觸目的一染紅,而他雙眸像餘燼里的兩朵寒焰。
這時候,那青年咳嗽聲已經停了,只是胸膛仍起伏不已,一步挨一步地走到王小石和白愁飛身邊,三人橫一字平排似的,都在茫然地看著外面交織成一片灰濛濛的雨網。
雨仍下著。
下得好大。
好大。
白愁飛望著雨絲,牽動了愁懷,喃喃自語地道:“好大的雨。”
王小石在旁不經意地搭腔道:“雨下得好大。”
那病懨懨的公子居然也湊上了一腳,凝望著在檐前掛落眼前的雨線,道:“真是場大雨。”三人都同是在說雨,不禁相視莞爾。
【正式出場】
外面儘是雨聲。一位老婆婆,衣衫襤褸,白髮滿頭,蹲在牆角,瑟瑟縮縮地大概在拾掇些別人廢棄的破罐爛壇。
一面崩敗塌落的牆垣上,經過一隻螞蟻,那高大堂皇的漢子看它足足爬了半天,被外面刮進來的風吹著了也停,被外頭卷進來的雨濺到也停,忍不住伸出食指,想把它一指捺死。
那病容滿臉的公子忽道:“茶花,你等不耐煩,也不必殺死它。它既沒犯著你,又沒擋著你,它也不過同在世間求生求活,何苦要殺它?”
那高大威猛的人立即垂下了手,道:“是,公子。”
那公子其實年紀不大,臉上卻出現一種似大人觀察小孩子時候的有趣表情,問:“你怕花無錯找不到‘古董’?”
那高大威猛的人不安地道:“我怕他會出事。”
臉有病容的公子望向被雨絲塗得一片黯灰的景物,雙目又沁出了寒火,“花無錯一向都很能幹,他不會讓我失望的。”
那瘦骨伶仃的老婆婆,可能是因為天轉寒更逢秋雨之故吧!全身咯咯地打著顫,披在身上的破毯也不住簸抖著。那公子道:“沃夫子。”
那兩名在近階前看雨的漢子中,其中一名賬房先生模樣的人即應道:“是。”
病公子道:“那婆婆也忒可憐。”
沃夫子即行過去,掏出兩錠銀子,要交給那悽慘的婆婆。老婆婆大概畢生也不曾夢想過有這樣的施捨,整個人都愣住了。
這時候,忽聽剩下的一名在檐前看雨的漢子低低喚了一聲:“公子。”
喜色在病公子臉上一閃而沒,“來了?”
這漢子轉過臉來,只見他半邊臉黝黑,半邊臉白嫩,向病公子身後的殘垣一指,“花無錯來了,他背上還背了一個人。”
王小石和白愁飛都微微吃了一驚。
原來這漢子不是“看見”有人來了,而是聽出背後有人走近。在這滂沱大雨里,來者又步伐奇輕,連白愁飛和王小石都不曾聽出有人逼近。
茶花也循這漢子指處望去,也高興地道:“花無錯背的是‘古董’,‘古董’給他擒住了。”
病公子微微地笑著。
王小石和白愁飛相覷一眼:原來“古董”不是古董,而是人。
花無錯背著一個人,在雨里像一支破雨裂網的箭,俯首就衝進廢墟來。
他一來就向病公子跪稟:“屬下花無錯,向樓主叩安。”
病公子淡淡地道:“我已經一再吩咐過,這種虛禮,誰也不要再行,你要是心裡尊重,便不必在口頭上奉承,樓子裡全以平輩相稱,更何況還在敵人重地!你難道忘了嗎?”
花無錯道:“是!公子。”
白愁飛和王小石慘駭更甚。
原來眼前這個滿臉病容、嗆咳不已、瘦骨嶙峋、神色卻森寒冷傲的人,竟然就是名動天下的“金風細雨樓”樓主:
蘇夢枕!
──沒想到卻在一個雨中廢墟里,遇上了這武林中的傳奇到了神奇的人物。
【首度出手】
同一瞬間,蘇夢枕正想動手,花無錯已經動手。
他又一低首。
他背上至少有二十五個暗器,同時射向蘇夢枕,每一暗器的尖端,都閃著汪藍,顯然是塗上奇毒的,而且全是
勁弩機關所發射的,快、準、毒,正是避無可避、閃無可閃!
蘇夢枕的心神,被“古董”的倏然出手,分了一分。而他的意志,正集中在救援茶花上──他的親信花無錯就在這一霎向他下了毒手。
蘇夢枕大叫一聲,他身上淡杏色的長袍,已在這電光石火間卸了下來,一卷一回一兜一包,卷回兜包四個動作同一瞬間完成,漫天暗器全都隱沒不見。
只有一枚,像一粒綠豆般大小,釘在蘇夢枕的腿上。
—————————————————————————————————————————————
蘇夢枕猛掀開袍子下擺。
那綠豆般的小暗器驀然就嵌在他左腿上。
他想也不想,手中就多了一柄刀。
多么美的刀。
像美麗女子的一聲輕吟,動魄動心。
刀鋒是透明的,刀身緋紅,像透明的玻璃鑲裹著緋紅色的骨脊,以至刀光漾映一片水紅。
刀略短,刀彎處如絕代佳人的纖腰,刀揮動時還帶著一種像和天籟一般的清吟,還掠起微微的香氣。
這是柄讓人一見鐘情的刀。
同時也令人一見難忘!
因為蘇夢枕第一刀就砍向自己。
他剜去了那顆“綠豆”沾上的地方和周圍的一大塊肉。
他切下自己的一塊肉,猶如在樹上摘下一粒果子──傷處鮮血迸濺、血肉淋漓,一下子濕了褲襪,他卻連眉都不皺。
他的咳嗽,也神奇地消失了。
他左手使刀,剜去自己腿上一塊肉,右手已扣住了沃夫子的背門。
那柄奇異的刀,也突然紅了起來。
他右手像彈琴似地揮、點、戳、拍、推、拿、揉、捏,每一下俱絲毫不失。
他左手刀卻封殺了“豆子婆婆”、“花無錯”、“古董”的搶攻!
而且一刀就剁下了“古董”的頭!
“豆子婆婆”和花無錯驚懼、急退。
花無錯眼見“古董”的頭顱飛了上來,還瞪著一對眼珠子,不禁撕心裂肺地狂喊:“紅袖刀!”
──紅袖刀!
蘇夢枕右手仍在救護沃夫子,左手刀已先殺了一名勁敵,退了二名大敵!
這一刀砍下一名敵人首級之後,刀色更加深烈。
──這實在不知是柄神刀,還是魔刀?
──拿刀的人,也不知是個刀神,還是刀魔!
【收白、王,赴破板門】
當兩人一出現,蘇夢枕眼裡的神色,又變得孤傲、冷傲,甚至是刺骨的寒傲。
他過去看沃夫子。
沃夫子滿身都是箭,成了箭靶子。
他再去看茶花。
茶花已經死了。
但一雙眼睛並沒有合攏,他瞪著雙眼,充滿著不甘與憤憾。
蘇夢枕俯身說了一句話:
“我會替你報仇的。”
殘瓦上忽滴落一滴雨珠,正好落在茶花眼眉下、眼眶上,茶花的眼忽然闔了起來,神態也安詳多了,就像聽了蘇夢枕這一句話,他才死得瞑目似的。
蘇夢枕緩緩站了起來。
這時候,王小石和白愁飛已穩住了大局,師無愧著了四箭,但沒有傷著要害,箭仍在肉里,他並沒有把箭拔出來。
他黑的一片臉更黑,白的一片臉更白。
蘇夢枕問他:“你為什麼不拔箭?”
師無愧仍像標槍一般地悍立著,“現在還不是療傷的時候。”
蘇夢枕道:“很好!‘古董’叛了我們,賣了五百名弟兄,我叫花無錯去逮他回來,結果,我身邊六名好兄弟,只剩下你和楊無邪了。”他雙目中又發出寒火,“沃夫子和茶花的死,是因為‘古董’和花無錯。‘古董’死了,花無錯也一樣得死。”
師無愧說:“是。”
王小石看著白愁飛。
白愁飛望望王小石。
白愁飛禁不住揚聲道:“喂,我們救了你,你也不謝我們一句?”
蘇夢枕淡淡地道:“我從來不在口頭上謝人的。”
王小石道:“那你也不問問我們的姓名?”
蘇夢枕道:“現在還不是問名道姓的時候。”
王小石奇道:“什麼時候才是時候?”
蘇夢枕一指地上躺著的沃夫子和茶花的屍首道:“待報了大仇,還有命活著回來的時候。”
白愁飛冷笑道:“報仇是你們的事。”
蘇夢枕道:“也是你們的事。”
白愁飛道:“我們跟他們兩人毫無交情。”
蘇夢枕道:“我跟你們也毫無交情。”
白愁飛道:“救你是一時興起,逢場作戲。”
蘇夢枕道:“這遊戲還沒有玩完。”
王小石詫問:“你以為我們會跟你一起去報仇?”
蘇夢枕搖頭。“不是以為,而是你們一定會去。”
王小石更是愕然。
白愁飛問:“你準備什麼時候去?”
蘇夢枕冷笑道:“什麼時候?當然是現在。”
“現在?!”
白愁飛和王小石全都嚇了一跳。他們是有眼睛的,自然看見蘇夢枕身上的傷,和身邊只剩的一名手下。
王小石忍不住道:“可是……你只剩下一個受傷的弟兄。”
“我受傷,他受傷,其餘的,都死了,”蘇夢枕笑了一笑道,“我們都不能就這樣回去,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好的時機?”
他寒電似的雙目,向王小石和白愁飛各盯了一眼,兩人仿佛都感覺到一股徹骨的寒。“‘六分半堂’的偷襲剛撤,不管他們是在慶功還是在布置,我們這一下銜尾回襲,連樓里的實力也不調派,他們決料不及,意想不到。如待日後,他們必定保護花無錯,以他為餌,誘我們來殺他,但我們現在就下手!”他臉上出現一種極度傲慢之色,“何況,戰可敗,士氣不可失,‘六分半堂’毀掉了我四個人,我也要讓他感到如失右臂!”
然後他君臨天下地道:“無愧,準備好了沒有?”
師無愧即叱應了一聲道:“準備好了!”他身中四箭,還像個
鐵將軍似的,橫刀而立,威風凜凜。
蘇夢枕道:“你說,‘六分半堂’的人,會護著花無錯退去哪裡?”
師無愧道:“破板門。”
蘇夢枕道:“幾成把握?”
師無愧道:“六成。”
蘇夢枕道:“好,有六成把握的事,便可以幹了。”
白愁飛忽然道:“你現在就走?”
蘇夢枕笑了一笑,就像臉肌抽搐了一下,道:“難道還等雨停?”
白愁飛道:“這一地的人,只是受制,你若不把他們殺了,他們便會即刻通知防範。”
蘇夢枕傲然道:“我不殺他們。第一,我從不殺
無名小卒、無力相抗的人;第二,如果我現在出發,他們再快,也快不過我的行動;第三,如果我要攻擊他們,根本就不怕他們有防備。我要攻擊的是整個‘六分半堂’,不是任何一名弓箭手。”
王小石忽然道:“不好。”
蘇夢枕倒是怔了一怔,道:“什麼不好?”
王小石道:“這樣好玩的事,我不去不好!”他說著,把裹著劍鞘的布帛扯開,丟棄。
蘇夢枕雙目中的寒焰,也似暖了起來。
白愁飛一跺足,發出一聲浩嘆:“這樣有趣的事,又怎能沒有我?”他說這話的時候,把腋下的字畫棄之於地。
蘇夢枕眼中已有了笑意。
但很快的,他的眼裡又似這陰雨天一般森寒。
他一縱身,已掠入雨中。
師無愧緊躡而上。
他們在雨中奔行,逆著風,逆著雨勢,都感覺到一股激烈的豪情。
這一股豪情,把他們四個人緊緊綰結在一起。
──人生路正漫長,但
快意恩仇幾曾可求?一個人能得一痛快的時候,何不痛快痛快,痛痛快快!
白愁飛的
心機,王小石的懶散,被蘇夢枕所激起的
傲慢,全湧起了一股戰志,連同戰神一般的師無愧,一同奔赴破板門。
【“我從來都不疑我的兄弟的!”】
“我虛設這個訊息,根本不是要訛花無錯的,我也不知道誰是‘六分半堂’派來的臥底,誰是內奸,我只是把假訊息放出去,直至赴苦水鋪之際,才告訴了同行的人,想必是花無錯為了貪功,還是要行險一試,若雷損無功而返,而他們這一組人卻取了我們的性命,豈不更見高明!”他冷笑一下,道,“其實,就算他今天能殺了我,他這種作為,雷損也不會容他的。雷損是何等人!”
雨浸濕了他一雙詭異的鬼眉,眼中的寒火卻未被淋熄,“我從來都不曾疑過花無錯……我從來都不疑我的兄弟的!”
【破板門之役】
花無錯失神地道:“他……他來了!”
雷滾深吸一口氣,連下七道告急請援令,心想:總堂主和大堂主究竟在哪裡?不然,老二、老二、老四至少也要來一來啊!
不過他隨即想到:自己將與名動天下的蘇夢枕對決時,手心都因亢奮而激出了汗!
他稍微凝聚心神,道:“好,他來了,我們這就出迎他去!”
陡聽一個聲音道:“不必了!”
聲音就響在雷滾的身前。
然後就是刀光飛起。
一片刀光,擷下了花無錯的人頭!
刀光來自那兩名側立的漢子。
雷滾大喝一聲,左重九十三斤、右重五十九斤雙流星飛襲而出,這種奇門兵器又以不同重量的
流星錘最難收放,不過一旦練成,又是最難招架的兵器,遠攻長取,殺傷力大!
流星錘打出,人已不見。
人隨著刀光。
刀光艷艷。
刀輕輕。
刀飛到了花衣和尚的光頭上。
“花衣和尚”大叫一聲,手上銅缽,飛旋打出!
他手中的一百零八顆鐵棱念珠,也呼嘯而出!
同時間,他的人也破窗而出!
他只求把蘇夢枕阻得一阻,方才有逃生的機會!
廳中的高手那么多,只要他逃得過這一刀,一定有人會擋住蘇夢枕!
窗欞飛碎。
外頭是雨。
他果然看見自己逃了出去。
可是他怎么“看見”自己“逃”了出去呢?
他馬上發現,從窗子裡飛出來的是一具無頭的軀體。
──為什麼會沒有了頭?!
──這確是自己的身體,那衣履、那身形……
──莫不是……
“花衣和尚”的意識到此陡止,沒有再想下去。
因為他已不能再想。
他失去了想的能力。
“豆子婆婆”看見蘇夢枕一刀砍下了花無錯的頭顱,就像他砍掉“古董”的人頭一樣,美麗而飄忽,還帶著些許風情。
然後第二刀便找上了“花衣和尚”。
追上了“花衣和尚”。
婉約的刀光帶著緋色,在“花衣和尚”剛要飛掠出窗外的脖上絞了一絞,“花衣和尚”這時正好撞破了窗子,所以頭先飛出窗外,身子余勢未消,也摔落窗外。
然後刀又回到了蘇夢枕手中。
蘇夢枕轉過頭來,目如寒星,望向她。
豆子婆婆在這一剎那,幾乎哭出聲來。
她還沒有哭出聲,但雷滾已發出了一聲雷吼!
雷滾不明白。
那一抹灰影掠到哪裡,他的雙流星就追到哪裡。
因為他知道灰影子就是蘇夢枕。
──蘇夢枕居然進入了他的地盤,正在格殺他的人!
這個正在發生中的事實像一柄燒紅的尖刃,刺在他的腳板上!
過激的反應使他整個人都彈跳起來,而且充滿了鬥志。
這一剎那,鬥志甚至要比生命力還旺盛!
──寧可死,但決不能不戰!
──殺死蘇夢枕,就可以在“六分半堂”獨當一面、舉足輕重!
──殺死蘇夢枕,就可以名揚天下、威風八面!
一個人一直想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既不敢叛長逆上,又不服膺已成名的人物,於是便在心中立定了一個頭號大敵,以策勵自己有一天要越過他、擊敗他,來證實自己的成功。雷滾的頭號大敵便是蘇夢枕。
尤其是當別人對他這個人嗤之以鼻,以一種螢蟲也與日月爭光的眼色對待時,更令雷滾感覺到焦灼與憤怒。
──有一天,一定要擊敗蘇夢枕。
──只有擊敗蘇夢枕,才能證實自己的存在!
所以在這一刻,他已被鬥志所燒痛。
他對蘇夢枕做出瘋狂的截擊。
但他的招式卻一點也不瘋狂。
他的雙流星,重流星錘自後追擊,輕流星錘在前回截,一前一後,只要給其中一記流星錘絆了一下,就可以把敵手打了個血肉橫飛。
他的輕流星錘明明可以從前面兜擊中蘇夢枕的身子,可是,蘇夢枕忽一晃就過去了,已到了輕流星錘之前、擊不著的地方;而重流星錘明明眼看要擊中蘇夢枕的後腦,可是不知怎的,只差半寸,蘇夢枕的後發都激揚了起來,但仍是沒有擊著。無論把鐵鏈放得再長,都是只差半寸,擊了個空。
蘇夢枕這時已二起二落,砍掉了花無錯和“花衣和尚”的人頭。
淡紅色的刀變成艷紅。
艷紅如電。
“豆子婆婆”卻連眼睛都紅了。
她突然卸下身上那件百結鶉衣。
這件千瘡百孔的破衣在她手裡一揮,就捲成了一條可軟可硬的長棒,手中棒“呼”地劃了一個大翻旋,橫掃淡紅的刀。
艷紅忽亂。
亂紅如花雨。
“豆子婆婆”手中的布棒忽然碎成了千百片,漫揚在空中,“豆子婆婆”疾閃飛退,蒼髮斷落,亂飛在空。
刀光回到蘇夢枕袖中。
蘇夢枕把手攏入袖裡。他這樣說道:“能接我一刀,已經很不容易了。你要記住,我不殺你,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你並沒有親手殺死我的兄弟。”
“誰殺死我的兄弟,誰就得死!”
他一說完,轉身就走。
他不但對堂上圍堵的四百八十六名“六分半堂”的子弟視若無睹,而且也好像根本就看不見雷滾這個人。
這一點足以把雷滾氣煞。
這比殺了他更痛苦。
至少是更侮辱。
如果雷滾不使出這一記“風雨雙煞”,他所受到的挫折,也許就不致如此的慘痛。
不過,日後的成就,也許就不會如此的大。
人生里有很多步伐、許多決定,一旦跨出去、一經動念,也許現在看來是錯的,但日後卻變成了對的;或許如今明明是對的,但到了將來卻是成了大錯。對錯往往如一刀兩面,切開因和果、緣和分。一個人如果一生得意,很可能就不會有太大的得意,反之,一個人常受挫折,未必不是好事。沒有高山,就不會有平地。
雷滾那一擊結果如何?
蘇夢枕的紅袖刀呢?淒艷的殺氣,是不是可以沛莫能御?
雷滾的雙流星,未打出去前已急劇旋轉震盪,發出去後更互相碰擊激撞,沒有人能分辨得出這一對流星錘,會從哪一個角度、以哪一種方式擊在哪一處要害上;縱連雷滾自己也不能夠分辨。
但卻可以肯定,只要經這一對流星錘碰上,骨折筋裂,準死無疑!
雷滾已騎虎難下,也開始有些自知之明。
他這雙錘縱殺不了蘇夢枕,至少也可以把他留上一留。
不料有一件事卻發生了。
而且發生得毫無徵兆。
流星錘到了蘇夢枕身前,也沒見他怎么動,那兩條精鐵鋼鏈就斷了。
流星錘舞得再好,只要鏈子一斷,流星錘就跟南瓜沒什麼分別,一枚呼溜溜地滾到廳外,把圍堵的“六分半堂”弟子驚讓出一條路,而另一枚啪地撞在一名正跟師無愧纏戰的副堂主胸口,把那人的胸膛整個打癟了下去,血吐得滿錘子都是。
蘇夢枕仍是沒有多看雷滾一眼。
甚至連一句話都不屑跟他說。
他仍在往外走,一面向把湧上來的“六分半堂”子弟截住的師無愧說了一句:“立即走。”
那滾落在地上的一對流星錘,也彷佛與他毫無關係。
師無愧馬上收刀。
他收刀如此之急,使得正跟他廝拼的一刀三劍五把槍,幾乎全要扎到他的身上。
師無愧驟然收刀,全身空門大開,反而使這幾名高手紛紛收招,以為有詐。
甚至有一人還因急著收住衝殺的勢子,竟在地上劃出了一道深深的槍痕,星花四濺。
師無愧已跟著蘇夢枕,行了出去。
沒有人敢攔住他們。
沒有人能留住他們。
蘇夢枕走到檻前,微微一頓,一抬足,腳跟回蹴,把那一枚九十三斤重的鐵流星錘,踢得直飛了起來,眾人譁然閃躲,只聞轟的一聲,流星錘撞破了那面寫著一個草書“六”字的石牆。
牆坍磚裂,塵揚灰漫,再看蘇夢枕已不見。
牆上只剩下“分半堂”三個字,還有一枚墜落的流星錘。
【“他們是我的兄弟”】
小侯爺輕撫微髯,目含笑意,“很好,很好。”目光落向白愁飛與王小石,“這兩位是‘金風細雨樓’的大將吧?”
蘇夢枕道:“他們不是我的手下。”
小侯爺眉毛一揚,笑道:“喔?他們是你的朋友?”
蘇夢枕笑道:“也不是。”他頓了一頓,一字一句地道:“他們是我的兄弟。”
這句話一出口,大吃一驚的是白愁飛與王小石,他們兩個合起來,簡直是大吃二驚!
【三結義】
王小石忽道:“我只有一個問題。”
前面有幾部馬車正候在大路旁。
蘇夢枕緩了腳步,側首看看王小石。
王小石大聲問:“你──你剛才對小侯爺說──我們是兄弟?”
蘇夢枕笑道:“你是聾子?這也算是問題?”
王小石怔了一怔,道:“可是,我們相識不過半日。”
蘇夢枕道:“但我們已同歷過生死。”
白愁飛道:“你知道我們是什麼人?”
蘇夢枕冷冷地道:“我管你們是誰!”
白愁飛道:“你連我們是誰都不知道,如何跟我們結義?”
蘇夢枕翻起白眼道:“誰規定下來,結拜要先查對過家世、族譜、六親、門戶的?”
白愁飛一愣:“你──”
王小石道:“你為什麼要與我們結拜?”
蘇夢枕仰天大笑,“結拜就是結拜,還要有理由?難道要我們情投意合、相交莫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一大堆廢話嗎?”
白愁飛道:“你究竟有幾個結拜兄弟?”
蘇夢枕道:“兩個。”
白愁飛道:“他們是誰?”
蘇夢枕用手一指白愁飛,“你,”又用手一指王小石,“還有他。”
王小石只覺心頭一股熱血往上沖。
白愁飛深吸了一口氣,忽然說出了一句很冷漠的話:“我知道。”他盯著蘇夢枕緩緩地道:“你要招攬我們進‘金風細雨樓’。”
蘇夢枕忽然笑了。
他笑起來的同時也咳了起來。
他一面咳一面笑。
“通常人們在以為自己‘知道’的時候,其實什麼都‘不知道’,這句話真是一點也不錯。”蘇夢枕說,“你們以為自己是什麼人物?我要用這種方法招攬你們作為強助?你們以為自己一進樓子就能當大任?為什麼不反過來想我在給你們機會?世間的人才多的是,我為啥偏偏要‘招攬’你們?”
他一口氣說到這裡,便冷冷地道:“你們要是不高興,現在就可以走,就算今生今世不相見,你們仍是我的兄弟。”
他咳了一聲接道:“就算你們不當我是兄弟,也無所謂,我不在乎。”
王小石一頭就磕了下去:
“大哥。”
白愁飛忽嘆了一口氣道:“你當老大?”
蘇夢枕怪眼一翻,“像我這種人,不當老大誰當老大!”
白愁飛負手仰天,久久才徐徐地呼出一口氣緩緩地道:“我有一句話要說。”
蘇夢枕斜睨著他,道:“說。”
白愁飛忽然走上前去,伸出了雙手,搭向蘇夢枕的肩膀。
師無愧握斬馬刀的手突然露出了青筋。
這雙手只要搭在蘇夢枕的肩上,便至少有七八種方法可以制住他,十七八個要穴足以致命。
何況這是白愁飛的手!
蘇夢枕卻紋風不動。
他連眼睛都不眨一下。
白愁飛的兩隻手,已搭在蘇夢枕的雙肩上。
沒有蘇夢枕的命令,誰也不敢貿然動手。
白愁飛望定蘇夢枕,清清楚楚地叫:“大哥。”
蘇夢枕笑了。
他望望王小石,又望了白愁飛,眼裡都是笑意。
他一笑的時候,寒傲全消,就像山頭的冰融化為河川,灌溉大地。
【病】
蘇夢枕陰冷的眼神,望望撐黃傘的女子,又看看莫
北神所統率的“無發無天”,又觀察了一下雨勢,自懷裡拿出一個小瓶,掏出幾顆小丸,一仰脖吞服下去。
雨水落在他臉上,似濺出了痛苦的淚。
他服藥的時候,無論是莫北神還是師無愧,誰都不敢騷擾他。
隔了好半晌,蘇夢枕一隻手輕按胸前,雙目又射出陰厲的寒芒。
蘇夢枕突然劇烈地嗆咳起來。
他掏出一條潔白的手帕,掩住嘴唇。
他咳的時候雙肩聳動,像一個磨壞了的風箱在肺里抽氣一般,吸吐之間沉重濃烈,而又像隨時都斷了氣一般。
好一會他才移開手帕。
王小石瞥見潔白的巾上,已染上一灘怵目的紅。
蘇夢枕合起了眼睛,連吸三口氣,才徐徐睜開雙眼。
蘇夢枕回過身來的時候,又劇烈地嗆咳起來,他一咳,全身每一塊肌肉都在抽搐著,每一條神經都在顫動著,每一寸筋骨都在受著煎熬。
他又掏出白手巾,掩在嘴邊。
──白巾上有沒有染血?
蘇夢枕咳完了。
很少人能夠忍心聽他咳完。
他的咳嗽病也許並不十分嚴重,可是一旦咳嗽的時候,全身每一部分都似在變形,他的聲音嘶啞得似要馬上斷裂,胃部抽搐得像被人用鐵鉗夾住,全身都弓了起來,心臟像被插得在淌血,眼球充滿了血絲,臉上幾道青筋一齊突突地在跳躍著,
太陽穴起伏著,臉肌完全扭曲,連手指都在痙攣著,咳得雙腳踮著,無法站穩,活像要把肺也咳出來一般,聽去就像他的肝臟,都在咳嗽聲中片片碎裂似的。
好不容易才等到他咳罷。
他一咳完,就把白巾小心地摺疊,塞回襟里,像收藏一疊一千萬兩的銀票一樣。
“他是真病,”狄飛驚莊嚴地道,因為他知道自己所下的這個判斷足以震動整個京城、半個武林,“他全身上下,無一不病。他至少有三四種病,到目前為止,可以算是絕症。還有五六種病,目前連名稱也未曾有。他之所以到現在還不死,只有三個可能。”
他深思熟慮地道:“一是他的功力太高,能克制住病症的迸發。可是,無論功力再怎么高,都不可能長期壓制病況的惡化。”
他的眼睛又往上睇去,雷損靜靜地等他說下去,他的臉上既無奮亢,也沒怒憤,他的表情只是專心,甚至近乎沒有表情。這是狄飛驚最“怕”的表情,因為在這“表情”里,誰也看不出對方內心裡真正想的究竟是什麼。“第二種可能是他體內七八種病症互相克制,一時發作不出來。”
“第三種可能呢?”
雷損問。
“奇蹟。”
狄飛驚答。
奇蹟。
天下間還找不出理由來解釋的事,還可以有一個解釋,那就是:奇蹟!
“按照道理,這個人的病情,早該死了三四年了,可是到今天,他仍然活著,而且還可以支持‘金風細雨樓’浩繁的重責,只能說是一個奇蹟。”
雷損默然沉思。
蘇夢枕忽然連點了自己身上幾處要穴,臉上煞白,青筋抽搐,好一會才能說話:“我真是渾身是病。”
王小石關切地道:“為什麼不好好去治?”
蘇夢枕道:“我有時間好好去治嗎?”
王小石道:“至少你應該保重。‘金風細雨樓’固然重要,但若沒有你,就沒有‘金風細雨樓’。”
蘇夢枕笑道:“你知道我現在覺得最有效的治病方法是什麼?”
蘇夢枕道:“當自己沒有病。”
然後他又笑了。苦笑。
其他
溫瑞安改編的港漫中其中兩部(《
說英雄誰是英雄》、《溫瑞安群俠傳》)出現了蘇夢枕這一人物,形象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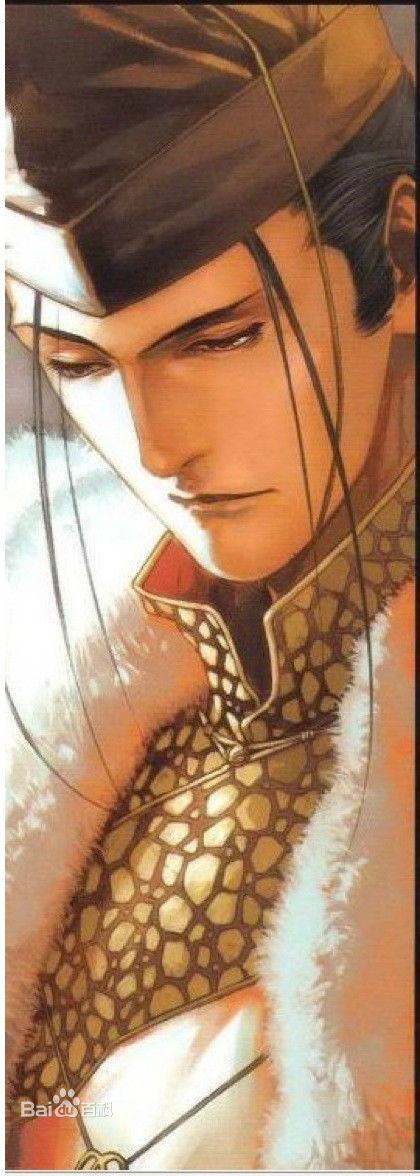 蘇夢枕
蘇夢枕 金風細雨樓樓主—蘇夢枕
金風細雨樓樓主—蘇夢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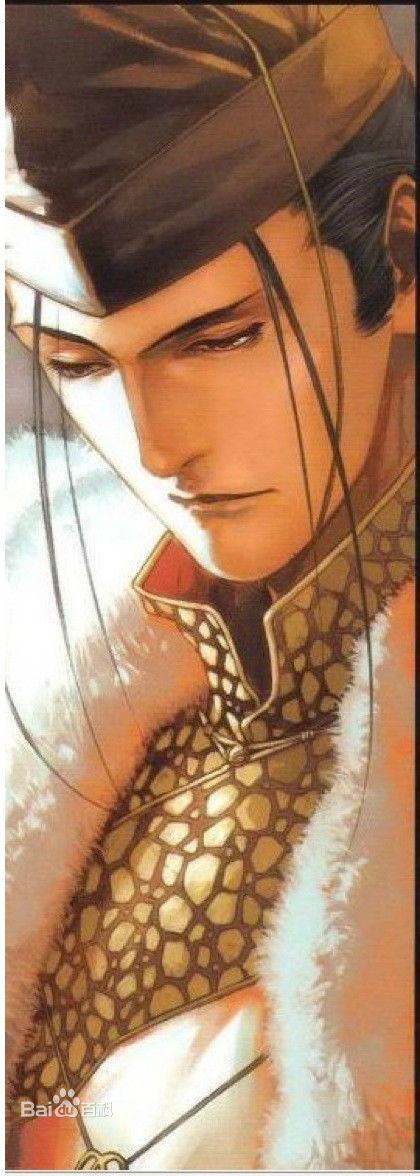 蘇夢枕
蘇夢枕 金風細雨樓樓主—蘇夢枕
金風細雨樓樓主—蘇夢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