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散文發表在省級名刊《天津文學》2023年4月期,全文借客家辭彙“尋食使”為線索,寫100年來陳家5代人、徐家3代人“賺錢謀生”的血淚史,中間還穿插了上世紀90年代末一群來自五湖四海外來青工的生存狀態,後段提及一些行業的興起及沒落對比……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百年艱難“尋食使”
- 作者:陳彥儒
- 創作年代:2023
- 作品出處:《天津文學》
- 文學體裁:散文
作品鑑賞,作者簡介,
作品鑑賞
百年艱難“尋食使”
- 一
周五下午,整理稿件之際,“尋食使”——一個客家方言辭彙,突然活生生跳了出來,在我眼前伸了伸懶腰。
在我老家廣東興寧的客家方言中,“尋”不讀“尋”,語音近似“叢”而音偏狹偏急促,“食”的發音則接近“拾”字,“尋食使”翻譯成國語就是“賺錢謀生”的意思。
地處粵東的興寧市是個小城,這個有118萬常住人口的縣級市是純客家縣。當地居民使用的客家話,屬於漢語七大方言之一。
“尋食使十分難,唔好去祿人家。”爺爺談做人的道理,最愛說的就是這句話。翻譯成國語,意思是“賺錢謀生很艱難,不能去影響別人(即不要擋別人的財路)”。
四十年前的那個暑假,爺爺砌好一壺茶,聊起了年少時北上“尋食使”的往事。那年我才7歲,聽著退休在家的爺爺跟村人聊天。
奶奶是童養媳,爺爺13歲那年,外曾祖父發跡了,開了興寧第一家牙醫診所,於是爺爺過去當學徒。當時興寧城牙科生意並不好做,外曾祖父便帶著牙醫師傅和爺爺,背著工具北上“尋食使”。爺爺一行原想一直走到北京去行醫,但到了江蘇常州後,時值“七七”事變,外曾祖父從報上獲悉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立即帶著牙醫和爺爺返回興寧老家。
1947年,興寧城改建,外曾祖父一咬牙,掏出多年積攢的積蓄,在新命名的中山西路買下一爿商鋪開診所,爺爺擔任掌柜。
從爺爺口中,我得知外曾祖父樂善好施,常布施食物給無法“尋食使”的窮困百姓。爺爺當時給外曾祖父打工,並沒有工錢,只是隔半月拎一袋糧食回家。為了“尋食使”,奶奶和曾祖母白天忙完農活,晚上還要輪流紡線;為了能掙點活錢,奶奶失眠之時,還常常搖紡線一直搖到雞鳴頭遍,才去歇息眯一會兒。
1956年公私合營,外曾祖父的牙醫診所收歸國有,爺爺留下來成為城鎮醫院的牙醫,從這時開始,爺爺才有了正式的工資收入。
而爸爸這一輩人“尋食使”則是背井離鄉。從江西萍鄉煤校畢業後,爸爸被分配在江西省安遠縣物資局工作。當他某次前往時任縣長的家中向領導匯報工作時,意外得知縣長家聘請的保姆是興寧老鄉。後來,這名熱情的保姆牽線,將剛從蕉嶺縣前往安遠林場投靠其表姐、尋找工作的媽媽介紹給爸爸。
在保姆的再三勸說下,猶豫了很長時間後,媽媽終於答應認保姆做乾媽。後來的幾十年里,我們姐弟都喊她外婆,喊得甚至比親外婆還要親。1978年,父母先後從江西安遠縣外貿局調回廣東興寧之際,外婆也因年邁返回老家。由於其含辛茹苦養大的長子和長媳不孝,晚年外婆每當受到委屈,都會跑到四望嶂煤礦,在我們家住上一個月半個月。
這位被兒時淘氣的我稱為“天上掉下的好外婆”為人很硬氣,她常常告誡我們做人要硬氣:“我在縣長家做保姆的時候,縣長家煮了什麼好的菜餚,縣長夫人總會拉我上桌一起吃飯,我從來都不去吃,我只吃自己煮的鹹菜下飯。”
外婆也常常談起自己年輕時“尋食使”的往事。她很年輕的時候,丈夫就病逝了。兩個兒子才幾歲,為了將兒子養大成人,堅持不改嫁的外婆一咬牙跟著鄉人,挑鹽擔上江西。
“一百八十多斤的鹽擔挑起來,剛開始連腳都站不穩。”外婆一邊篩著豆子,一邊回憶往事。當時的江西糧豐鹽缺,興寧至江西贛州大山橫亘,水路不通,很多客家人為養家餬口,選擇了走這條流汗流淚流血的路途,挑鹽上江西,再從江西挑米下興寧。
“講到挑擔心就酸,肩頭又痛腳又軟。”外婆很少唱山歌,講到這裡她輕輕哼著山歌,那時坐在一旁擇菜的我應該還不到十歲,看著篩箕上高高拋起的豆粒落下,外婆那哽咽的嗓聲扎進我耳中,也扎進心裡。“人人問厓擔脈介,言知擔來做三餐。”“厓”就是客家話里的自稱,“脈介”就是“什麼東西”之意。每次回想到這兩句山歌,我的眼窩便會蓄滿淚水……
粵贛兩地鹽道翻山越嶺,曲曲折折,且不提豺豹蟒蛇穿梭其間,且不提螞蟥纏身的恐怖,僅僅就是途中遇到雷電交加、暴雨山洪的險境就讓人猝不及防。鹽最怕水,避雨不及時,謀生者千辛萬苦的勞動就會血本無歸。
在那個謀食艱難的年頭,為了省下一分一毫供養兒子,外婆經常是炒好了一搪瓷杯鹹菜,就這樣拌著米飯吃上一個禮拜。
最令外婆傷心的是,很多同行的人走著走著,“咚”的一聲,一頭就栽倒在地,再也不能爬起來了……講著講著,外婆撩起衣角擦眼淚。
外婆含辛茹苦將兩個兒子撫養成人,小兒子醫藥學校畢業後分到南昌市工作。她在年邁無法勝任保姆工作之時,返回興寧刁坊鎮居住。這個時期,她的大兒媳卻對她橫挑鼻子豎挑眼,還把她安排在村人用來養豬的老屋居住。受盡委屈和虐待,外婆只有也只能趕到四望嶂煤礦,到干女兒家裡來訴苦,跟她沒有一絲血緣關係的媽媽,成了外婆晚年貼心的棉襖。
- 二
認的外婆這一生過得是那么苦,而我的親外公親外婆在那個崢嶸歲月中,也過得非常非常不容易。
外公早在12歲時就單獨下南洋尋找生父。剛到馬來西亞,得知他的生父此時已病逝。一時淪為孤兒的外公只能寄居在叔父的橡膠園裡。某天,性格倔強的外公偷偷溜了出去,流浪在大馬各地打短工為生。
當外公的叔父終於找到他的時候,時光又過去了好幾個年頭。其時,外公正在一家定居南洋的潮州母女家裡做僱工,他不願隨叔父回橡膠園。僱主家的女孩與外公年齡相仿,兩人玩得很好,女孩的寡母也非常中意外公這樣的老實人,有意將寶貝女兒託付給外公。
也許是緣分已盡,也許是命中注定,一次外公在外面闖了禍,不知是得罪了僑居的日本人還是當地的流氓……為了保住兄長唯一血脈的性命,外公的叔父在獲悉之後,重金雇了一艘大船,又安排人高薪“聘請”外公到船上幫忙卸貨。
當船開到距離陸地很遠的水域時,外公不禁滿臉疑惑。“你叔父送給你這幾個皮箱的錢物,”面對外公質疑的目光,船長這時才說了實話,“他讓我送你回去娶妻生子。”如五雷轟頂,癱坐在船頭的外公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年輕的他哀求、絕食……無效抗爭一段時間後,外公最終還是無奈地接受了這個現實。
外公回到蕉嶺過得並不舒暢。回國很久以後,他才娶了外婆。比外公小9歲的外婆是孤兒。外曾外祖父下南洋謀生曾回過一次,帶回一對金耳環給外曾外祖母戴。外曾外祖父返回南洋不久,外曾外祖母去趕墟,孤身一人經過當地山脈中一處叫做“眠床石”的地點,遭遇攔路搶劫,驚慌中她連呼“救命”,結果被歹徒劫殺。那時,可憐的外婆還不到16歲。直到新中國成立後,該起命案才告破。當地公安部門1950年在審查山匪路霸時,根據贓物線索破獲了這起劫殺案。《蕉嶺縣誌》有記載,當年曾公開槍決作惡多端的歹徒。
外婆在新中國的陽光下成長起來了,她雖然生得嬌小,但因睿智慧型乾明事理,中年後還曾被村人推舉為生產隊隊長。
外公外婆一共養了兩子六女,其中第三個女兒得白喉早逝,第七個女兒夭折。為了養活六個子女,外公靠搬運、載客、幫人治療跌打損傷為生,日子過得很拮据。有一次他騎車載物時滾下山窩,流了一大攤血,幸遇好心人救起,才撿回了一條命。1960年前後,他的叔父,不斷從馬來西亞寄回錢糧接濟,一家老小因此渡過了最困難的歲月。
我的小舅在就任蕉嶺縣某局副局長之前,曾經前往“新馬泰”走過一趟,大舅也曾積極聯絡過南洋的親屬,他們查證得知,那個潮州女子懷上了外公的崽,一直沒嫁人,在南洋苦苦等了外公一輩子。
晚年的時候,外婆跟著小舅住在蕉嶺,退伍的大舅把外公接到廣州。在蕉嶺的客家話環境中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外公,到廣州很快和附近認識的潮州人打成一片。最讓大舅驚訝的是,他居然能用潮汕話向別人反覆敘述著南洋的經歷,還不時吐出一些帶南洋口音的英文辭彙。大舅曾以為外公具有極其獨特的語言天賦,但是居住廣州這么多年,也沒發現外公學會很多常用的粵語。
——也許,幾十年來,外公心底深處一直藏著那個潮州女人。在輾轉反側的失眠之夜,他都在偷偷地回味著年少時的初戀。否則很難解釋,為何他跟賢惠的外婆一直“合不來”?為何晚年還能流利地使用少年時代只學過很短時間的語言?
到了青春期,我卻在大人們喝茶閒聊之際,悄悄羨慕著外公的艷遇:哇,一輩子兩個女人,就像張愛玲寫的“紅玫瑰”和“白玫瑰”……逐漸長大後,我果斷棄絕這樣的邪念。在一個失眠的冬夜,我聽著窗外淅淅瀝瀝敲打著芒果樹葉的雨聲,又想起外公的情事,深深體驗到他一直埋藏在心底的那份無奈、愧疚和傷痛。
- 三
我“尋食使”的遭遇,也不比祖先們“遜色”。
中技畢業後我南下珠海打工,當時工廠訂單很多,記得有一年,一個月只能休兩天,半個月才換一次班,長期要上12小時大二班,即白班早上7時上到晚上7時,晚班從晚7時上到早上7時。冬天裡早晨6點爬起來洗漱一通,就往工廠趕,騎腳踏車出門時天蒙蒙亮,到晚上7時下班回去時天又黑成一團了。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硬是在兩年時間裡啃完了大專自考課程,拿到畢業文憑。記得當時白班下班後,一些工友呼朋喚友出去滑冰、學跳舞,而我,都婉拒了,一個人待在潮濕陰暗的宿舍看書。
中年夢多,那個困窘的年月,8人擠在一間小屋子裡的情景,一幕幕,總會隔一段時間就衝進夢中。還記得那個位於一樓、過道只有一米寬的逼仄宿舍,隔段時間,就會發生下水道堵塞事件,整個樓道和房間都是濕漉漉的髒水,有時,水面還會飄著樓上衝下的髒兮兮的穢物……
宿舍門上的位置有半米寬的水泥台,我搬進時人少,立即挑了靠門邊的上鋪,在水泥台上擺上一個裝書的木箱,人站在床上,木箱箱面剛好到手肘的位置,這是一張天然的書桌。我趴在這裡完成自考學業,讀完了《百年孤獨》《簡·愛》《飄》等等名著,那時開始迷上寫詩寫散文,寫了很多稿,也投了很多稿,但大都石沉大海。
有次凌晨三點下夜班,由於白天忙著寫稿,沒有怎么睡覺,此時十分睏倦。騎腳踏車回宿舍時,軟軟的風吹在臉上,眼睛被像紗巾、像柳絲、像酒香的風兒灌得睜不開,只好眯著眼踩腳踏車。剛開始,大腦還不斷釋放紅燈信號:危險!我剎下車,狠狠地捏一下掌心,掐掐小指指甲兩邊,揉揉太陽穴解乏。但重新踩上車我還是睡過去了,只有雙腳出於慣性繼續踩著腳踏車。
在那短短的一公里直線路途上,我居然接連做了幾個短暫的夢。我夢見一位鬚髮蒼蒼的老人,穿著道袍,拎著毛筆走到我面前,在我的掌心寫下一個“艮”字;夢見游泳被水草纏住;夢見在山谷迷路……
“啪嗒!”一聲,我摔倒在地上,撞上了一位騎車夜歸的中年人。“你怎么騎車的?”他一臉的慍怒,“騎車還閉著眼睛?”
膝蓋生疼,有一種滾燙的液體流過,出血了。從地上側身爬起時,我在心底默默背誦著:“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尋食使”難,難的並不是一個、兩個“心比天高”的人,難的是一群南下的打工者。回想二十餘年前,八人擠住在一間小房間的工友們,他們何嘗不“艱難”呢?看看對面的下鋪,那裡住的是楊大哥,他在半個月才有的一天假日裡,跟著同鄉去幫人焊防盜網,賺點辛苦的血汗錢。
有一次,楊大哥在工廠扭了腰,我照顧了他半個月,說是“照顧”,其實無非是幫他按按摩,打來熱水擦身,洗洗衣裳。下班後從床底拉出煤油爐和小鍋,在狹窄的過道煮一鍋“西紅柿龍頭魚麵條”,請他一起吃。龍頭魚一直是菜市場最便宜的魚類,比蔬菜還便宜。這些再平常不過的舉手之勞,一直被楊大哥銘記心底。14年之後,舉家搬到昆明的楊大哥做義烏小商品批發生意發達了,開拓了寮國、高棉市場後,他專程請我們小兩口乘飛機到昆明玩了一周。
楊大哥上鋪睡的是小張,他住的時間不長。有一次睡夢中翻了個身,居然從一米半高的床上摔到地上,他痛得“哎喲哎喲”叫了半宿,第二天居然不捨得請假又趕去上班了。
我上鋪旁住了一年的是曾哥,當年新婚不久,他妻子在前山一家手袋廠打工,每周會過來一兩次。曾哥每到這時,就會把我們幾個逐一拉到門外,請我們到外面蹓躂兩小時。考慮到工廠工資低,酒店鐘點房貴,大夥心照不宣相約去散步,冬天時就跑到新華書店去看書。但時間久了,同室一位工友心理很不平衡,看看手錶,時間過了將近四十分鐘,他便提議回去,我和楊大哥都認為不妥,制止了兩次,卻沒能阻止大夥的行為。最後我也抑制不住好奇,跟著大夥回去。那位工友的鑰匙輕輕插在門上,警醒的小曾就高喊一聲:“誰?”然後是響亮的一聲:“別開門,等我們兩分鐘。”兩分鐘後,門打開時,穿戴整齊的曾哥臉紅紅的,大夥的臉也紅紅的。曾哥催他妻子回去,他妻子卻躺在床上扭扭捏捏,不起來,也沒吭聲,曾哥一下子就冒火了,啪地一巴掌扇了過去,在大夥多此一舉的勸解中,他的妻子氣得哭哭啼啼地離開了……回想起當年的荒唐事,真是有些後悔。又過了一個月,曾哥和妻子到工廠附近的江村租了間小房子。
那一群窘迫“尋食使”的工友們,如今都去了哪裡?他們過得怎么樣?大夥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幸福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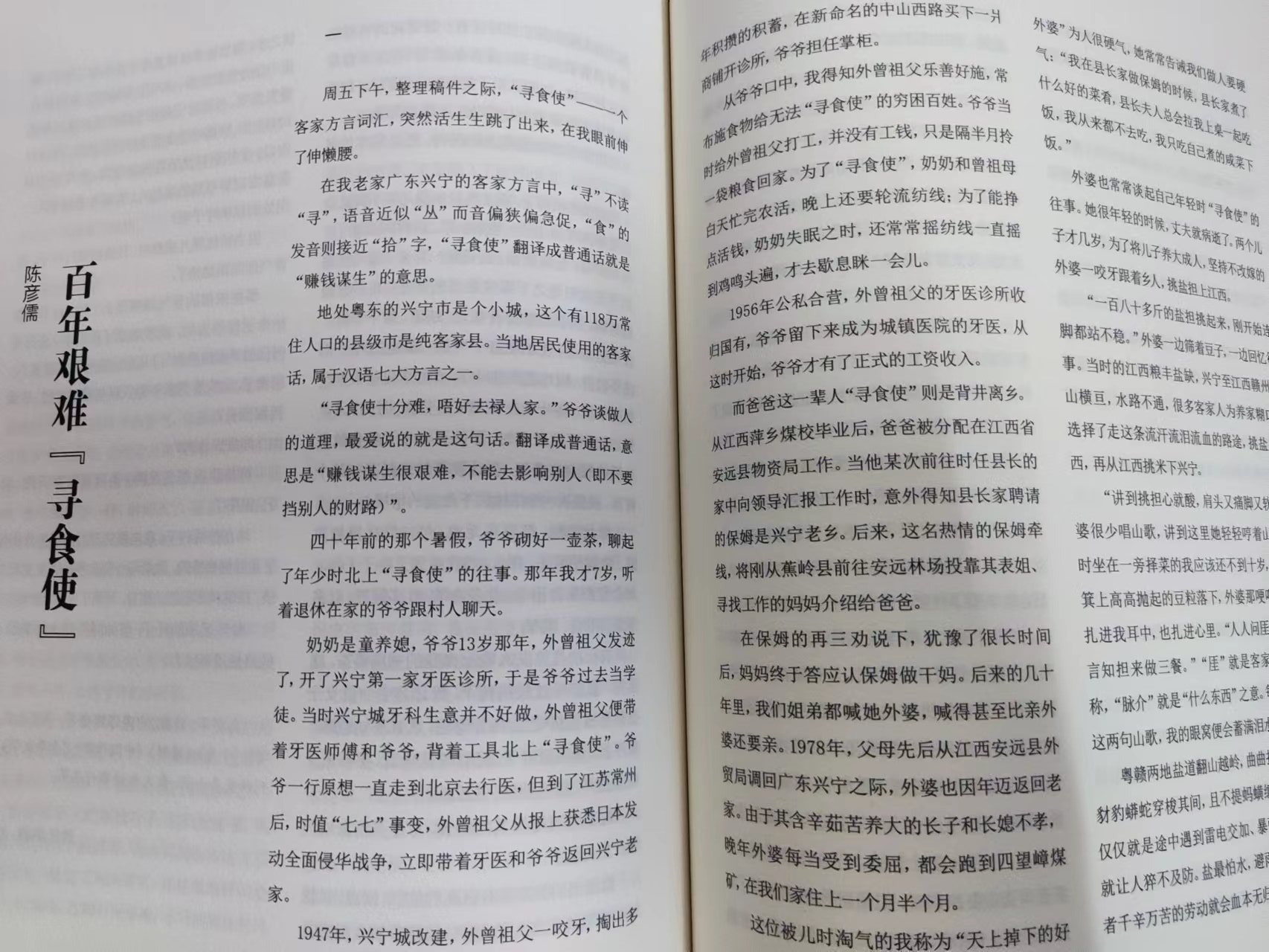
省級名刊《天津文學》2023年4月期發稿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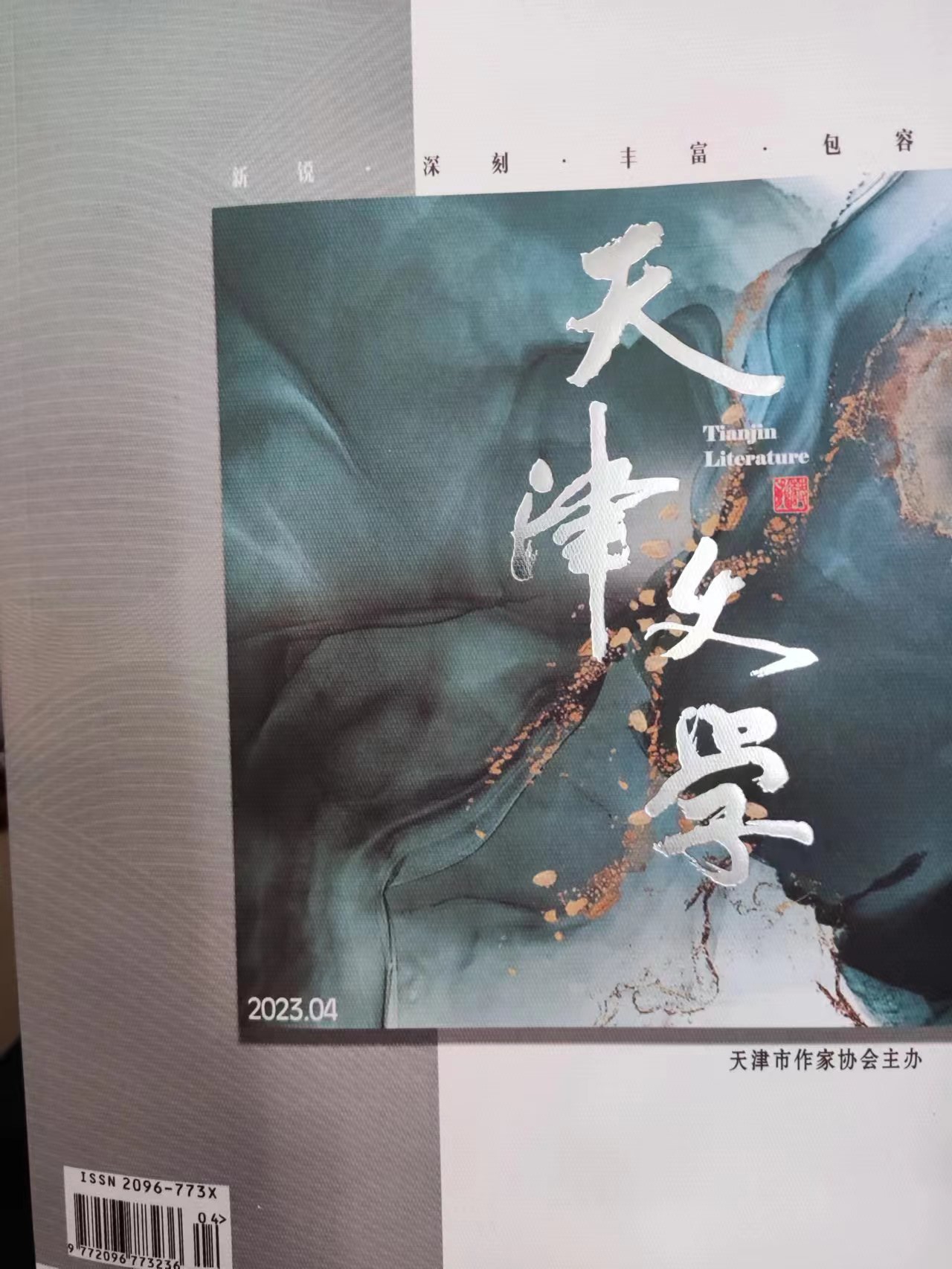
省級名刊《天津文學》2023年4月期發稿截圖
- 四
1998年下半年,我在珠海某報開了長達數月的專欄,引起市文聯一位領導的關注。他得知我的窘狀後,寫了一封蓋章推薦信給一位企業副總經理。領導本意是能寫能拍的我可以勝任工會企宣工作,沒想到副總經理上上下下打量我一會兒後,只是為我安排了一間單人宿舍,我依舊留在了繁忙的流水線工作。
這節點恰巧是我申報自考本科學業之際,當時又有一個小小的機會來了,珠海那年月有無線與有線兩個電視台,雙方圍繞收視率展開肉搏戰。略處下風的有線台在林書福主任接手後開展改革,首推“身邊事”欄目,對外招聘能拍會寫的通訊員,通訊員並無薪水,只是發稿後能拿到稿費。其時,在珠海電大教過我的一位老師剛應聘到一私立學校當校長,校門前一條爛尾多年的道路令校長痛苦不堪,於是找到我。我借來該校的攝像機,拍了雨季師生們磕磕絆絆走在泥濘的爛尾路上的畫面,又寫了條七百餘字的新聞。有線台播發這條時長兩分多鐘的“身邊事”後,立即引起珠海市市長的高度重視,專門批文指示相關部門整改。初戰告捷,我又連拍了驢友家裡養的小懶猴等幾條趣味橫生的新聞。可惜,這個節點,依舊沒人留意到我的努力,私立學校又沒有適合我的崗位,失望之極的我,依舊待在已經開設三班倒的流水線上“尋食使”。
學校的攝像機不能總扛在我身邊,後來,我又借了堂叔的攝像機玩了好幾個月。年底,我咬咬牙掏出多年積蓄,買了台攝像機拍“身邊事”。此時,自考本科剛過兩科,但我再也沒有精力去應付了。在20世紀90年代末,國內快遞行業還沒起來,每次擠公車回電視台送錄像帶、拷貝錄像帶影像要花費大量時間。這一放,本科自考就被耽擱6年之久,直到2005年我才重拾書本去考完剩餘的科目。
2001年有了一些積蓄,我不願再待在工廠浪費青春,於是跳出來做自由撰稿人。2002年參加公務員考試,我考了筆試第一,分數比第二名、第三名高出十幾分,但在面試階段卻慘遭淘汰。面試之前,曾有人打電話恭喜我,當時擔心是騙子,我沒怎么吭聲。錯失機遇後才有很多人“點撥”我,應該逮住那個電話帶來的機遇。
也許,怪自己沒經驗,也許,真是“文憎命達”……總之,磨難的陰霾,依然籠罩著我“尋食使”的人生旅程。
- 五
還記得,2016年有長達十個月時間我都是被陰雲籠罩:老爸先是摔斷股骨頸,做了更換股骨頸手術後,2008年曾治癒的鼻咽癌因實施手術,很快轉移發展成口腔癌……老人長時間住在醫院裡,當年從三月中旬至六月、八月至十月底我常常在晚上十點至早上八點,要待在醫院陪護老人,因為請的護工總是讓老爹不滿意。
臨走前一個多月,老人渾身散發著惡臭,那是一種無論用熱水和沐浴露怎樣去擦,都擦不去的味道……在這種艱難的背景之下,我白天在母親替換我守病房之後出去採訪,晚上回來陪夜,在極其難熬的背景下,每月依舊完成了采編工作,超額完成通稿、網稿任務分和海外報刊轉載落地率,在廣東各支社發稿排行中位列第一,並持續保持三年多采編地新聞“零失誤”的優良紀錄。
特別令我傷心的是,老人在奄奄一息中,只要能透出一口氣,他就會揮著手趕我去工作……老爸說的最後一句話,還是希望在生前能看到我解決編制問題……
2016年10月21日,我在休殯葬假,當天將老爸骨灰罐送到公墓後,我打開手機看到郵件有中航通飛傳來的重大通稿,於是在這個孝子人生最痛楚的時刻,在汽車逼仄的空間裡,我愣是放下一切悲痛,撥打手機採訪涉事單位負責人,將連發“黑板報”都嫌囉嗦的企業稿件,改成對海外播發的文字稿。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小時候,爺爺常常對我說起這句話,他也以身作則。還記得很小的時候,爺爺牽著我在村里村外散步,遇到熟人都會主動了解收成情況,一聽到村人講到“尋食使”難,上頓不接下頓,或孩子讀書學費都湊不齊等等,爺爺就會主動掏錢資助村人。
村人千恩萬謝離去之後,爺爺對著我質詢的目光,常常嘆氣道:“尋食使難,尋食使難!”然後他又說:“長大以後,你要記住孟子一句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其後,他又細心解釋了這句話的意思。
我雖一直“窮”而未“達”,也願意力所能及地“濟濟”天下。
我用新聞資源幫助過很多求助的人,甚至幫助挽救了一個瀕臨死亡的小女孩的生命。2014年7月,我在採訪中獲悉,一位11歲女孩和父親從湖北隨州農村趕到珠海,她患上重症造血功能障礙,其生母無法承受打擊離家出走、離婚再嫁;女孩父親花盡了身上最後的積蓄,無奈之下決定滿足女兒最後的心愿——帶她南下看海。面對攝像機,小女孩提出死後將捐獻器官——於是,我在現場採訪後一連寫下十幾篇追蹤報導。這些追蹤報導引發全國媒體的廣泛關注和熱心轉載。一時之間,全國網友紛紛捐款,小女孩的生命終於保住了……
我在這家媒體工作的八年時間裡,幾乎沒休過假,還出版了一本被清華、人民大學、中傳、復旦、上海交大、武大等眾多雙一流高校圖書館和國家、省、市、縣區圖書館購買收藏的新聞理論專著《新聞課——如何學會與讀者“拍拖”》。可是當我正在治療因多年勞累造成的疾病時,卻被炒了魷魚。
——現在我不但“兼濟”不了別人,連自己都難以“獨善”了。
實在咽不下這口氣,我與分社退休的孫老師等人不斷寫信舉報“廣東某社長私下開學校”、“辦公室主任入黨百日進黨委”等腐敗案例……
舉報有用嗎?2019年3月28日,該單位紀委人員南下調查,從下午三點到六點,一個勁就在追問我舉報的一些內容的訊息來源。
違規的不查,他們南下,難道就是為了追查內部泄露訊息的在崗知情人?
悲哀啊,我的“尋食使”經歷……

圖為作者

圖為作者的《新聞課——如何學會與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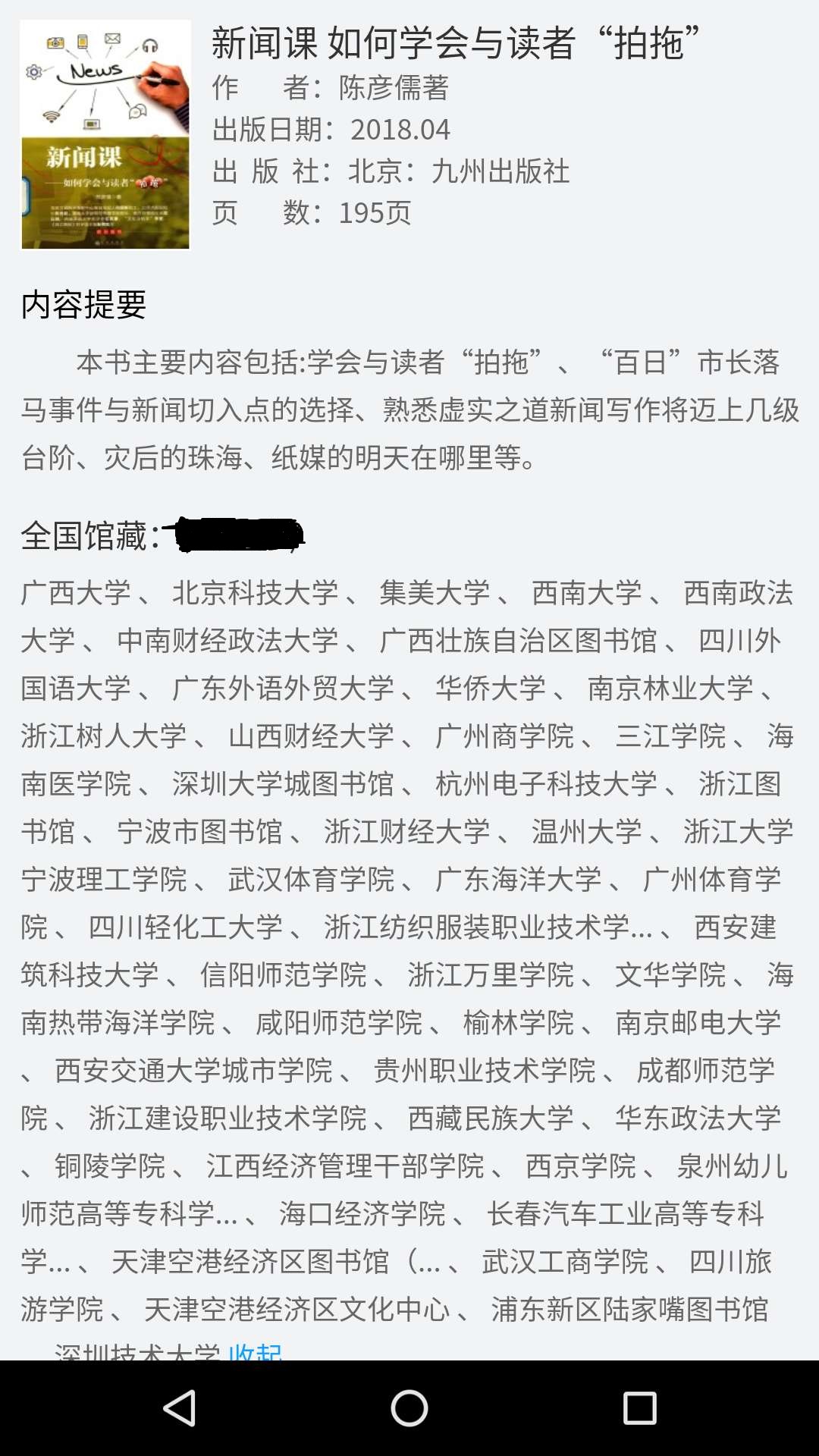
圖為眾多高校圖書館收藏購買作者圖書
- 六
爺爺剛退休那些年,每天晚上家裡都是人來人往,他喜歡講古,談年輕時北上“尋食使”的往事,但他談得最多的還是幾代人的“尋食使”經歷。據爺爺述稱,我的高祖父是晚清秀才陳獻君,第一次趕考不料適逢母親病逝,他只好返家奔喪守制。三年之後即1895年再度赴京趕考,高祖父卻又追隨康有為、梁啓超,與千名舉子、秀才一同聯名上書,呼籲清廷拒簽和約,共同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等主張。返鄉後他拋棄功名,轉身開私塾教新學。曾祖父則從事風水堪輿。一些大戶人家經常請我的曾祖父去看風水,預約時間常常排到數月之後。據說,當地廣為流傳著一個段子,我的曾祖父給人看打井,說挖幾尺的土就只能挖幾尺。當地有一個愣頭青硬是不信邪,挖到位之後又揮了一鋤,這一鋤真不簡單,井水不是緩緩冒出來而是噴出來的,鴛塘那裡於是留下一處來不及砌磚的水井。鴛塘羅氏後來出了很多人才,眾人都說是我曾祖父給看的風水。曾祖父有五個兒子,風水之學卻沒傳給子孫,因為當時風水堪輿不能發家,爺爺13歲就送到親家那裡學當牙醫。

圖為作者高祖父——曾與康梁一起發起公車上書的晚清秀才陳獻君
爺爺和四叔公都是牙醫,到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爺爺和四叔公兩兄弟成為名震粵東的知名牙醫,八十年代初連贛南、閩西等地都不斷有患者慕名來興寧城鑲牙。爺爺的牙醫技術並沒有傳下,爸爸是讀書出身,成了國家幹部,在廣東省礦山建設公司工程師崗位退休,親叔叔退伍後到了煤炭系統,他生前在坪石組建了一支建築隊南下廣州承包工程。到了我們這一代,哥哥是司機,我做了多年記者,堂弟則選擇經商。
爺爺生前常常感嘆“尋食使難”。他稱從高祖父、曾祖父到他,在他們依靠傍身之技時,都無法賺錢,只能苦苦維持生計。高祖父開私塾,當時周圍民眾都窮,只能提些糧食來讀書;曾祖父名震興寧,但在那個舉國艱難的歲月,也就謀點餬口的錢而已。到了爺爺輩,好不容易手頭寬裕點,但是,要建新房還是很難。

圖:八十年代全家福,右一為作者
現在想想,爺爺那一輩靠做牙醫謀生真是艱難,儘管名震粵東,但當時能花錢去鑲牙的人很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做一顆烤瓷牙也就三五元錢而已,我爸在礦山的月薪是七十多元,比社會各行業的綜合平均工資略高一點,做一顆烤瓷牙約占月薪的二十六分之一至十五分之一左右。如今三十多年過去了,做一顆烤瓷牙的價格大約是八千元至一萬元左右,相當於全社會各行業的綜合平均工資的兩三倍,隨著民眾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現在的牙醫診所常常是人滿為患,隨便一家牙科診所的普通醫生,從業幾年就能賺得盆滿缽盈。
“也許是家運,也許是宿命,”爺爺晚年曾跟村人抱怨稱,“家裡幾代人乾什麼行業,什麼行業就屬於同時代的沒落行業。”想想也是,別說祖父曾祖父那幾代人了,爸爸從江西安遠縣調至位於四望嶂的廣東省建一處,不過幾年,省屬單位迅速沒落;到了我從國有企業跳出來,從事媒體工作,傳統媒體這些年卻被網際網路、自媒體衝擊到犄角旮旯,記者從“無冕之王”一下子跌到“碼字民工”的可憐境地……
常常有人嘲笑我們兄弟幾個為何不跟爺爺學醫,這可怎么說呢?爺爺1989年去世,當時我哥國中畢業後不願學,我又剛讀國中,堂弟還在讀國小。爺爺在病逝前曾做好規劃,他想讓城叔(四叔公的小兒子)學醫,準備讓我未來去跟城叔學。但任何規劃都趕不上變化,城叔學會後調至珠海醫院工作,先是安排在採購崗位,牙醫技術荒廢了幾年,這個時期國家開始對執業牙醫出台了很多規定。後來,城叔離開醫院時,就乾脆改行去學開油車了。他也沒想到2005年以後,牙醫一下子就成了國內最賺錢的行業之一。
作者簡介
陳彥儒,原名陳鏡堂,廣東興寧人。2019年6月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曾歷任百年老報——香港《大公報》記者,《珠江晚報》記者、中央媒體——“中國新聞社”常駐珠海、中山記者,曾獲2012年廣東新聞獎等榮譽 。
作者2009年出版作品集《放牧星群》,2015年初出版長篇小說《白天失蹤的少女》,該部長篇小說獲得了2015年首屆報業文學獎年度長篇小說大獎 。
2016年6月出版散文集《印象興寧水墨珠海》。2018年4月出版新聞理論隨筆集《新聞課——如何學會與讀者“拍拖”》。該書獲得2020年珠海首屆文藝評論獎 。 還被清華、人民大學、復旦、武大、浙大、哈工大、廈大、華東師大、暨大等眾多高校圖書館和國家、省、市縣區圖書館購買收藏。 2021年出版散文集《浪漫珠海——我從古代來》,該書獲得第四屆蘇曼殊文學獎。
2023年,陳彥儒再度跨界,首闖兒童文學領域,出版《“好煩丫頭”的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