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歷程
創作介紹
李海鷹創作過一系列有影響的影視音樂作品。除了
電視藝術片《大地情語》的插曲《彎彎的月亮》之外,還有電視劇《外來妹》的主題歌《
我不想說》、電視劇《一路黃昏》的主題歌《走四方》、電視劇《女人天生愛做夢》的主題歌《
我的愛對你說》等等。在這些歌曲的創作中,他集作詞、作曲、編曲於一身,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才能,歌曲一經播出便大受歡迎,被廣為傳唱,流行範圍很廣。他還為電影《
鬼子來了》《黑冰》《背叛》《榮譽》——到近期風靡全國的《
亮劍》等寫歌編曲,無不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創作獎項
由於這些成就,李海鷹曾獲得五個一工程、文華音樂獎等全國、全軍、省、市以及海外音樂創作獎百餘項 ,並且還擔任了中央電視台1989 春節晚會音樂指導;擔任了1998、1999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音樂統籌。1997年,他擔任了羅馬尼亞第十屆國際金鹿流行音樂節大賽評審;1999年,他擔任了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第十屆亞洲之聲音樂節評審;他還擔任過中央電視台1988、1992、1996、1998四屆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評審,擔任過中國文化部1996、1998通俗歌手出國選拔賽評審。此外,他還擔任了
中國輕音樂學會的副秘書長、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理事、中國
電影音樂學會理事和廣東音樂家協會理事等社會職務。他還是國際藝術節組織聯合會的成員,並被入選ABI國際傑出人物名錄。
 李海鷹
李海鷹第一個里程碑
1994年11月19日,他在
北京首都體育館成功舉辦了“《彎彎的月亮》李海鷹個人作品演唱會”。這應該是他音樂生涯的一個里程碑。
醉心於音樂的李海鷹喜歡拓展新的音樂領域,成名之後,他迷上了音樂劇。音樂劇盛行於美國百老匯,以流行音樂為主體,形式輕鬆、活潑,很受觀眾喜愛。而在中國 ,由於戲劇界在“文化大革命”以後涉足音樂劇的時間還不長,所以尚未有很成功的作品。李海鷹決心要在這個領域有所作為,在1996年和1997年的
中國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上,他推出了《過河》及《地久天長》兩個音樂短劇,獲得成功。但他並不滿意,期待有一個好的劇本一試身手。當他看到四川“人藝”女編劇
李亭寫的校園音樂劇《未來組合》的劇本時非常高興,馬上全力以赴投入了創作。音樂劇《未來組合》上演後,反響很大,受到了音樂愛好者,特別是大中學生的好評。
 李海鷹
李海鷹為了迎接澳門回歸,
中國中央電視台拍攝了一部大型電視專題片《
澳門歲月》。電視片中有一首起點睛作用的主題歌,歌詞用的是詩人
聞一多先生在1925年寫的詩歌《七子之歌——澳門》。中央電視台把作曲任務給了李海鷹。
“你可知:‘Macao’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離開你的襁褓太久了,母親!/ 但是他們擄去的是我的肉體,/ 你依然保管著我內心的靈魂。/ 三百年來夢寐不忘的生母啊,/ 請叫兒一聲乳名:澳門,/ 母親!我要回來,母親!”手捧著聞一多先生寫下的充滿幽怨愁煩的詩句,李海鷹非常激動。對於澳門,他有剪不斷的情緣,因為他父親的家鄉就在離澳門僅一衣帶水之遙的南朗鄉,那裡很早以前與澳門同屬香山縣,小時候他曾回去過那裡一次,澳門的歌謠也是他兒時記憶里的童謠。四十多年在廣東的生活,更是孕育了他深沉的
南國音樂情懷,令他極易感受澳門的風土人情韻味。
聞一多在這首詩里所表現的藝術形象是一個離開母親太久了的孩童,她向母親述說著Macao不是她的真姓;她呼喚著母親叫一聲她的乳名澳門;她大聲呼喊著“母親,我要回來……”四十多個日日夜夜,李海鷹寢食不安地用心靈體會著這個藝術形象,苦苦尋找著最有表現力的
音樂語言,終於,一股壓抑不住的摯情帶著《七子之歌——澳門》的
旋律衝出他的心底……
《七子之歌——澳門》隨電視片《澳門歲月》播出之後,深深地打動了海內外億萬華人的心,立刻響遍海內外。特別是在澳門,反響尤為強烈,不但在各種慶祝回歸的大小活動中被演唱,而且經常在大街小巷響起。電視界、音樂界人士都評論說:與以往的“回歸歌曲”不同,《七子之歌——澳門》是有深度、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的作品,它將人們帶進21世紀。李海鷹感到非常欣慰,他覺得,他是用音樂的形式與聞一多這位他從小敬仰的、傑出的文化先輩進行了一次超越時空的心靈對白。這首歌曲已隨嫦娥衛星飛向太空!
 李海鷹
李海鷹李海鷹創作背景
李海鷹是珠江的兒子,他是從珠江邊走向成功的。珠江邊,曾走來過
冼星海的身影,他的一曲《
黃河大合唱》,一直都是我們這個民族品嘗不盡的精神儀式;珠江邊,也走來過
馬思聰的身影,他的一曲《思鄉曲》,直到現在,都一直是全球華人的歸家的路;今天,珠江邊又走來了李海鷹。
乘著歌聲的翅膀,他仿佛又看見了先人偉岸的背影。他想追逐那個背影,用他堅定的腳步;他想祭奠那個背影,用他一生的追求!
改革開放至今,內地流行音樂走過30年的歷程,這30年來歌壇過無數經典名曲和無數紅極一時的歌星,但是在幕後領域,卻一直鮮有具備大眾知名度的大師級人物。縱觀整個樂壇,無論從資歷、作品的影響力還是在對流行音樂的貢獻方面,李海鷹都是最具備這一資格的音樂人。他的創作總是能夠緊貼時代的脈搏,在當時都能造成深遠的影響。他抓住了流行音樂的精髓並且成功的與古典、民族元素進行嫁接,在當代音樂界有突出的貢獻。
在
民樂方面,李海鷹也作出了很大貢獻,他所創做的葫蘆絲曲《
竹樓情歌》也是廣為流傳,成為葫蘆絲樂曲裡面的標誌性作品。
2008年7月6日,李海鷹在廣州舉行了《李海鷹作品音樂會2008》,當時有
劉歡、韓磊、孫浩、
韓雪、毛寧、
孫楠、孫儷、
潘長江等眾多大腕明星將同台獻唱。
主要作品
1. 我不想說 (電視劇《外來妹》主題歌,
楊鈺瑩演唱);
2. 彎彎的月亮 (電視藝術片《大地情語》插曲,劉歡演唱)
3. 牧野情歌(
李玲玉演唱);

7.
走四方 (電視劇《一路黃昏》主題歌,韓磊演唱);
9. 我的愛對你說(電視劇《女人天生愛做夢》主題歌,
葉倩文演唱);
12.蔓延(譚晶演唱);
14.我們的孫中山(中山紀念中學學生合唱);
18.紅黃藍白紫(劉小鈺);
19.山情(羅琪);
個人音樂會
李海鷹作品音樂會 用音樂講述他的故事
2008北京奧運會,是中國人的驕傲,是世界的焦點,她終於來到我們身邊。李海鷹又一次揮筆寫下《祝福北京》這首由
韓紅演唱的歌曲。她包含了人們對北京2008的深深祝福,更道出了每一個華夏兒女的熱切心聲!祝福北京,為祖國歌唱。
以祝福北京奧運為核心主題,以“
跨界音樂”獨有的文化品牌為基點,該音樂會將全新演繹李海鷹創作的經典作品,並通過流行時尚的國際化音樂語言,激情呈獻一台穿越南北時空的“跨界音樂與現代電視特技”完美結合的視聽饕餮盛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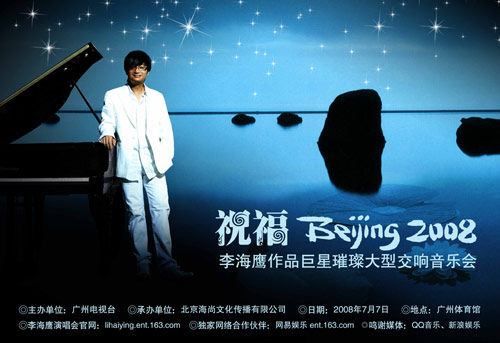 音樂會海報
音樂會海報李海鷹用音樂講述他的故事——用一生的創作、一線的演員、一流的交響樂團及合唱團、電聲樂隊、一流的現場燈光、舞台效果等眾多台前幕後國內頂陣容的加盟,共同打造出具有真正文化品牌意義的「2008祝福北京」——李海鷹作品巨星璀璨大型交響音樂會。2008年7月7日將在廣州萬人體育館激情奏響。屆時廣州電視台、
廣東電台將現場直播,中央電視台3套及4套黃金時間向全國及北美地區進行轉播。
「2008祝福北京」——李海鷹作品巨星璀璨大型交響音樂會著重體現“當代中國現代音樂”特色,音樂會擬定以80年代、90年代、21世紀為樂章劃分,充分展示改革開放以來音樂發展的輝煌歷史,彰顯作曲家獨具的人文精神和他所出生成長的城市風貌,通過大型情景歌舞和舞美特效等藝術手段的運用,達到舞台設計與周邊環境的融合、藝術表演與電視晚會的統一,在璀璨的交響音畫中將音樂會推向高潮。本次音樂會不僅具有豐富的社會內涵,而且具有濃郁的
藝術特色。該音樂會的欣賞性、藝術性遠遠高於單一的演唱會表現形態,和一些晚會形式大於內容的不足。通過音樂會傳播奧運精神、彰顯奧運文化,達到對奧運文化、當代中國現代音樂藝術的匯聚和共融!
「2008祝福北京」——李海鷹作品巨星璀璨大型交響音樂會,是一台全新概念的原創音樂會,他融合了交響、流行、民族等的跨界音樂元素,以及現代電視舞美的前衛包裝元素。由李海鷹親任指揮,聯手
廣州交響樂團、廣州工人合唱團、小雲雀童聲合唱團及中國頂級的電聲樂隊與眾多中國頂級歌唱家、當紅明星
劉歡、
韓紅、
孫楠、
譚晶、
韓磊、
毛寧、
孫儷、
韓雪、
呂薇等。
廣東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中國近現代革命策源地、中國改革開放前沿陣地,有著悠久的人文傳統和豐富的
文化資源。特別是在中國近代更是誕生過冼星海、馬思聰等偉大的音樂家。70年代末廣州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曾經誕生了一批在國內外極具影響的音樂大家及其代表作品,以強烈的時代感、現實性、平民色彩,成就了中國流行音樂的半壁江山。作曲家李海鷹正是這個時代的開創者之一,他的作品無不充滿了這塊熱土的象徵和時代記憶,他的音樂正是從這裡開始走向全國,並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流行音樂的發展,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現代音樂藝術的寶庫。
讓我們共同期待這場音樂盛會,期待李海鷹用音樂講述他的故事。
記者訪談
第一個十年
從“扒別人的”到“被別人扒”
早期給很多香港歌曲配曲,其實就是扒人家的歌,把歌詞換一下,然後根據記憶自己配上樂器和曲子,然後再拿出去賣。老實說這種事情的確侵犯了人家的著作權,但在那時候,大家都還沒有著作權的概念。不光是廣東,全中國的流行音樂,都經歷過這個階段。
 李海鷹
李海鷹記者:我查到的所有資料都顯示,您是在1983年進入流行樂壇的,為什麼是在這一年?在我印象中,在那之前就已經開始流行了
鄧麗君,在那年之後,
張明敏1984年進央視春晚,香港流行音樂才正式開始登入內地。但您進入流行樂壇的時間,似乎剛好在二者之間。
李海鷹:資料上記錄的年份,其實是我正式進入太平洋影音公司作配曲時的年份。其實在那之前,我是從部隊出來的。如果說最早接觸音樂,已經說不清楚是在什麼時候,但我記得自己15歲時,有人送了我一把
秦琴,也就是類似於
二胡的一種樂器,我在樓道里用撥片撥,嘴裡哼著胡謅的廣東小調。結果住在樓上的一個上海工程師下樓來,看了一眼我撥弦,對“這琴不高級,小提琴才高級。”然後把秦琴放到了我肩上,拿了把木尺遞給我,“在琴弦上來回鋸,用不著撥。”這算是我小提琴的啟蒙吧。但也就是因為這個,一年之後,我作為全校惟一會五線譜和略懂小提琴的人考進了廣州粵劇團,然後又進入廣州星海音樂學院作曲進修班學習了一年半。
1983年時,開始有唱片公司找我來做配曲,這種工作解釋起來有點費勁,應該是相當於出版社的約稿。也就是從那時開始,我變成了自由音樂人。所以,一般跟人說起來,我都說自己1983年進入流行樂壇。我個人應該說,那時就受鄧麗君的影響更大。
記者:粵劇團也算是個有編制的文藝單位吧,如今似乎大家不太看重這個了,但在80年代初,似乎很難想像有人甘願放棄體制內的生活,跑出來單幹的。當時,您就沒有過顧慮?
李海鷹:好像……我還真沒有過什麼顧慮。因為我記得在80年代初期時,廣州這裡的流行音樂行業就已經比較先進,幾乎是領先全國了,當時廣州的太平洋,新時代,中唱,白天鵝,簡直就是整箇中國流行音樂的
四大天王啊,所以從粵劇團出來的時候,我沒有任何猶豫,家裡也沒有特別反對,因為當時是唱片公司覺得我配器比較有潛力,水平也不錯,所以才請我過來的,我算是憑本事吃飯吧,有本事在,不怕沒單位。在早期,其實我配了不少
中國民歌+架子鼓這樣的東西,有時也有一些弦樂,這種形式的磁帶,當時真的很好賣,街上那些拎著四個喇叭雙卡
錄音機的,大部分裡面都放這些呢,還有舞廳里,因為架子鼓節奏感比較好,所以很多跳舞的也都在用。
早期那段時間,還給很多香港歌曲配曲,其實就是扒人家的歌,把歌詞換一下,然後根據記憶,自己配上樂器和曲子,然後再拿出去賣。雖然老實說這種事情的確侵犯了人家的著作權,但在那時候,改革開放剛開始,大家都還沒有什麼著作權的概念,出現這種事情也很正常。不光是廣東,全中國的流行音樂,都經歷過這個階段。
記者:80年代初,大家對於“流行音樂”的概念還不夠明確,而對於
流行文化和廣東,更有很多誤解,比如我記得小時候學校里的老師還在教育我們,說廣東那邊受港台影響深,年輕人都是喇叭褲、漢奸頭,手裡拎著錄音機,放出來的都是靡靡之音。您這樣的,應該就算是靡靡之音的作者了吧?後來覺得,廣東流行音樂的興起,應該不僅是受影響的問題吧,畢竟廣東人也不是沒有原則和主見,不管在早期還是什麼時候,廣東音樂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您覺得呢?

李海鷹:關於廣東流行音樂和北方流行樂的興起,的確有點不同。北方,比如北京,歷來都是文化中心,在那裡呆一陣你就知道,那裡有一種感覺,就是各種思想、各種潮流都能匯聚在那裡,你可以在北京談論
先鋒藝術,也可以在那裡聽京劇,這些東西還很好地融合在同一座城市之中。但這個文化中心同時也決定了,它對於任何新鮮事物,不是屬於它本身
文化衍生出來的事物,都會有一種排斥感,因為它是中心嘛,因此一改革開放,在北京好多事情都需要很激烈地爭論之後,才有可能被人們所接受。說白了就是說完了才做,很浪費時間。
而廣東則不同,廣東人在接受任何
新音樂方面,都沒有什麼障礙。香港那邊的流行音樂一過來,聽著好聽,聽著比革命樣板戲更讓大家興奮,人們自然也就跟著去唱,跟著喜歡了,不像北京,還要辯論半天,廣東人不管那些,真的直接就做起來了。我記得改革開放剛開始那陣,也的確是有不少東西讓我不太習慣的,這邊也在一些事情上有過爭論,但在流行音樂方面,廣東基本沒猶豫過,發展得很堅決,也很快,所以,到1985年前後,廣東流行音樂也就形成了一個高峰。
廣東這邊的音樂人在研究香港台灣的流行歌曲,而北方的音樂人,像崔健這樣的,直接接觸到甲殼蟲。
記者:1986年時,中國音樂界,南北有三件事情值得一提。第一件比較大,可以寫入
音樂史了:崔健站到了工體,向全世界吼出了他的《一無所有》;同樣在這一年,百名歌星集體演唱了《
讓世界充滿愛》,這也讓大家發現了流行音樂人合力的前景。另外一件聽起來比較小,但與您有點關係,而且也很有意義:太平洋公司推出了實驗性的專集《為我們驕傲》,其中就收有您的七首原創歌曲。
李海鷹:《為我們驕傲》的推出,其實還是和政府有關。1985年,廣州舉辦了一屆“紅棉杯”新歌新風新人大獎賽,推出了“十大歌星”、“十大金曲”———這種做法也是學香港的,但在內地,還是第一次,這也開創了內地音樂的排行榜先例。這事出來的時候,北京之類的城市,唱流行歌的人該被怎么定義,什麼樣的是娛樂明星什麼樣的是表演藝術家,還在討論之中呢。當時北方跟娛樂最搭邊的,應該就算是
春節聯歡晚會了。但這並不代表著北方音樂人就沒開始作為。在那段時間,廣東這邊的音樂人在研究香港台灣的流行歌曲,而北方的音樂人因為語言障礙加地域流傳,他們沒機會聽到這些。但北京有很多駐華使領館啊,一改革開放,外國人的東西也來了。北京音樂人,像崔健這樣的,可能聽不了鄧麗君,但他們可以直接接觸到甲殼蟲。
事實上,流行音樂這幾十年來,全世界的重心依然在歐美。所以長期就是這樣的現象,港台學日韓,日韓學歐美,根子還在西方。至於中國南方北方,其實差異並不大。我那時候就在研究
麥可·傑克遜,其實跟北方音樂人,也沒什麼區別,大家都是在學習,都是在模仿。所以,崔健在1986年的出現,也只能說明,中國北方的流行音樂,已經開始有了原創,有了自己的風格。但他們這種原創,和我們一樣是吸收外面的流行元素。只不過廣東音樂人過了一手而已。但像電燈,像汽車,我們也都是過了一手學來的,大家不照樣都在用著,也沒什麼特別不好。
而廣東這邊,因為流行歌曲的起步就是從唱片公司做起的,而不是從音樂人手中起步的,這就使得它的商業味道比較重,當時唱片公司對原創歌曲沒信心,自然原創出現的也就比較少。另外,其實如果說樂隊和現場演出,廣州出現得也很早,70年代末,廣州就有“茶座”駐場樂隊,但他們也是靠翻唱港台、歐美流行歌曲混飯吃。在《為我們驕傲》出現之後,為了支持新人大獎賽及原創作品,廣州文化局規定:歌手們每晚唱港台歌曲不得超過30%。從這之後,我才真正把工作的重心轉移到了原創方面。

《彎彎的月亮》是典型的廣東調,整個被雨水淋出來的感覺。跟整體上高亢、硬氣的“西北風”完全是兩種路子。我更離譜,找來了當時就覺得“聲音很飄”的劉歡來唱軟綿綿的《彎彎的月亮》
記者:但您似乎沒經過多少醞釀,很快您就寫出了《彎彎的月亮》,順帶還捧紅了劉歡。
李海鷹:《彎彎的月亮》實在是個特例。寫流行歌曲,其實很多時候你搞不清楚的,有些地方的經驗可以借鑑,但更多的時候,人們的喜好和心理,你是無從琢磨。所以,並不是經驗豐富就能寫出最流行的歌曲來。
《彎彎的月亮》,其實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創作這首歌的時候,中國還是“西北風”盛行的時候。所有人都覺得,把歌寫成這樣才能好賣,好唱。1989年,音樂電視片《大地情雨》製作組請我給他們配插曲,結果我想了想,當時真是“靈光一閃”,差不多半小時內就把曲子寫好了,取了個名字就叫了“彎彎的月亮”。這首歌是典型的廣東調,整個被雨水淋出來的感覺。跟整體上高亢,硬氣的西北風完全是兩種路子。結果寫完了,錄出來,很多行家都說實在太陰柔了。《
黃土高坡》作曲者
蘇越搖著頭說:“軟綿綿的,兒歌一樣的東西,怎么出得來?”但我更離譜,找來了當時就覺得“聲音很飄”的劉歡來唱,軟綿綿的《彎彎的月亮》,感覺的確讓人耳目一新。更巧的是,這首歌的首播又恰逢
廣州電台推出全國首個流行音樂排行榜,結果導致了歌曲迅速包攬各項冠軍,不但在內地走紅,還反攻到了香港,很多人都記得香港有兩個版本的《彎彎的月亮》。
當時整箇中國盛行:“西北風”,為什麼會有這么一個現象呢?我分析是因為這片土地跟中國太多的事情有關了。所以那時出現了很多描述這片土地的作品,像《黃土地》,《紅高粱》,油畫《父親》等等。
流行音樂與時代從來都是很緊密地結合,所以自然也不能免俗地尋根。當時把陝西民歌的確挖掘了不少,而且挺有意思的,大家也都沒覺得土。因為這類歌曲實際上也的確符合當時的不少年輕人的心態。搖滾,在當時,甚至有很多人看來都是有些另類的東西,但年輕人需要呼喊,需要發泄他們的精力,而西北風這樣的唱法,剛好適合他們,積極,健康向上,充滿陽剛。不過西北風作為一種歌壇的形態,出現一批是不錯的,但最後演變成“非西北風不唱”就有點過了,這點也挺有意思,其實很多東西,流行歌曲也好,經濟方面的也好,甚至影視也好,只要有人開頭做了,大家都一窩蜂地跟過去,這是中國人的一個弱點。
第二個十年
回望之後,不停地轉身
《
亞洲雄風》這些歌曲的流行背後,其實體現著另外一種思潮,就是北京的文化中心意識的體現。
記者:咱們終於說到90年代了。進入上世紀90年代,第一件值得說的事情,自然是1990年的亞運會。那次在北京舉行的亞運會,其實對整箇中國流行樂壇來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為由此就誕生了很多優秀的音樂作品,劉歡、
韋唯等眾多歌手開始大紅大紫。事實上,在那前後流行起來的一些體育歌曲,已經與西北風有著明顯的區別了,但與之後1993年、1994年開始的流行音樂高潮相比,又有一定的區別,您是怎么看待當時這批作品的?
李海鷹:《亞洲雄風》這些歌曲的流行背後,其實體現著另外一種思潮,就是北京的文化中心意識的覺醒。北京作為首都,擁有著被稱為“正統”的文化,這種文化很不容易被同化。而任何流行文化想要進入北京這個圈子,它也必定要有一個被消化然後再拿出的過程。所以,80年代流行音樂在南方,在廣東這邊興起的時候,北京並沒有很迅速地跟上,但它的這種“正統”因素一旦發揮,那么就會形成一種擁有北京特殊氣質的流行元素。所以在90年代初開始,北京就開始爆發了,在那之後第一次流行音樂高峰開始,北京就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流行音樂中心地位,這與首都的這種特殊文化氛圍有很大關係。處在這其中,古典的、現代的、民族的,什麼樣的東西都有它自己的位置。這就跟廣東不同。在廣東,就算流行音樂再差,也能占據音樂的半壁江山。
記者:似乎我們還是得回到您的代表作之一的《彎彎的月亮》,也就是在這一時期,這首歌開始被香港人翻唱了,這在內地流行音樂界的確算個了不起的創舉。

李海鷹:被香港人翻唱的,其實是有兩個版本,一個是
巫啟賢的,另外一個是呂方的。呂方那個版本,其實是華納香港方面購買的著作權。但他們改的時候,把歌詞改成往思鄉的情緒上走,但對我來說,這首歌根本不是想說思鄉。在那首歌寫完幾年之後,我仔細思考後覺得,其實這首歌的主旨,表現的是一種回望,一種從經濟時代向農業時代的回望,一種現代人群向自己舊有的精神家園的回望,這種回望,跟尋根有相似的地方,但又不是尋根。在我看來,我們不能否認人們都有
尋找精神家園的傾向,我也有。我們國家不是宗教國家,我們的傳統文化在這之前被割裂過,所以更有尋找精神家園的理由。但不論是尋找還是回望,在那個時代,都不會明白自己的心究竟該往哪裡擺。就像《一無所有》裡面唱的那樣,“我曾經問個不休”。
記者:90年代中期,中國流行音樂迎來了它真正的黃金時代。從1993年開始,不管是北京、上海、廣州,還是香港、台北,幾大流行音樂中心都有非常有代表性的流行音樂產生,甚至直到今天依然都有人在傳唱,在這其中也包括了不少您的作品,但我注意到,就在1994年時,您居然開始舉行個人作品音樂會了———一般情況下,舉辦個人作品音樂會,都是一位創作者開始有些走下坡路了之後,才進行的回顧和總結。但更奇怪的是,在那之後,您還有更加經典的音樂出現……
李海鷹:每個音樂人的創作,都會有高潮和低谷。在高峰的時候,這個人可能可以寫出一些很有影響力的東西,結果大家就會把他的這些作品當作這個人的標桿———比如我和《彎彎的月亮》,但任何人都不可能永遠保持在同樣的高水平上。我覺得,不管是《彎彎的月亮》還是之後的一些歌,我感觸最深的,就是我並沒有因為一首歌而形成標桿,換句話說,我衝過去了。
1994年舉辦過一屆我的個人作品音樂會,當時幾乎全國的音樂人都在支持我。那次是在北京搞的,當時很多廣東音樂人,都專程飛到北京去,買票進場來支持我,而北京的那些搞流行音樂的,也都在後台出口處站著,對他們來說,這就是一種姿態,一種表態支持的方式。
記者:好像那場演唱會劉詩昆老師也去了吧?這在當時似乎也是流行音樂界的一大創舉,讓一向演奏嚴肅的古典音樂的鋼琴家現場演奏流行音樂,您是怎么做到的?
李海鷹:其實那次音樂會不是劉詩昆老師第一次在現場彈這支曲子。因為我認識他,就是在一場電視台辦的宴會上看到他彈這曲子的。後來我要辦個人音樂會了,突然想起這件事,就給那家電視台打了個電話,他們台長挺支持我,就給了我劉詩昆的電話,打過去,問他是否願意在這個場合彈,他就來了。結果誰也沒想到會有那么轟動。劉老師當時往那裡一坐,一抬手,一開始,然後到了中間的部分,總之一首曲子下來,下面觀眾一共鼓了六次掌———連劉詩昆老師自己都樂了,沒想到會有這么好的效果,搞得他自己也很興奮。
那次個人音樂會,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最值得說的一點,就是它的現場感。那次是一個完整的現場音樂會,真演奏、真唱。這比“真唱運動”早很多。在我看來,音樂的本質就是現場演奏和現場的演唱,就像體育的魅力在於它的不可預知性,在賽前,你只能知道誰是熱門,但你永遠都不會事先知道,
劉翔在比賽前是否會退賽。現場版的音樂最大的魅力也在於此,每個人、每一次的發揮都不相同,你不知道下一秒誰會出現意外。但流行歌壇就是這樣,很多人為了穩定,寧可假唱。
記者:您又舉辦了一次個人音樂會,相比於1994年的那次,您覺得這次又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李海鷹:我覺得,這兩次個人音樂會,都是一種記錄。不光是對我,對很多和我同一個時代成長起來的音樂人來說,都是一個記錄。事實上我們那一代音樂人,不管是寫歌的還是唱歌的,歲數也都不小了,對於我們這些人來說,以後是沒有多少次這樣的機會了。所以,我這兩場個人音樂會,對很多歌手應該也都是一種一輩子的紀念吧。這次音樂會讓我同樣感動的是,在中國這30年來流行音樂界的許多歌手同樣都來了,而且都坐在台下看著,這在流行音樂界,已經很難了。
這次的音樂會,比上一次最大的特色在於:這次居然出動了交響樂團———流行歌曲用交響樂團來伴奏,難道不值得這些音樂人留下記憶么?
第三個十年
尋找文化中一脈相承的東西
記者:在1994-1995年那段整箇中國的流行音樂輝煌期之後,很多音樂人選擇了沉寂,但您似乎既沒有選擇蟄伏等待下一次的高峰到來,同樣也沒選擇繼續創作同類型的歌曲。您的道路有些奇特,因為在1999年的時候,我們又聽到了另外一首您堪稱標桿性的作品:《七子之歌》。聽說這首歌也是您的“靈感”之作?
李海鷹:這首歌的淵源也有些奇特。當時是央視要拍一個紀錄片,叫《澳門歲月》,為澳門回歸做準備的。當時他們邀請我給這個節目做幾首歌,這個歌詞是他們找來的,說是聞一多寫的,關於澳門的一首詩。後來我想看看這詩的前因後果,看看聞一多到底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寫出來的,於是就到外面去買聞一多全集,但從頭翻到尾,也沒有翻出來這首詩在哪裡。後來我就想試一下,因為我的故鄉中山與澳門隔得並不遠,就運用了一些家鄉的歌謠感覺進去。當時根本沒想過什麼
國家任務,但後來這首歌很受歡迎,結果被確定為唯一的主題歌曲,這些其實對我來說並不重要,我感到最欣慰的,是澳門人都很喜歡這首歌。
記者:後來這首歌還跟著嫦娥一號上了天,是不是覺得有點無心插柳的感覺?
李海鷹:那也是他們選的,當時是國防科工委選出來,帶到天上去的,他們通知過我,但也就是通知,我自己並沒有對此進行過任何努力。
記者:從80年代開始到90年代末,其實香港方面一直對內地流行音樂有著很大的影響,在1997年香港回歸時,甚至還出現過四大天王在人民大會堂同台唱歌的壯觀景象。但進入新世紀之後,香港流行音樂對內地的影響看起來正在減弱,甚至香港歌手的專集,也幾乎必備國語版了。
李海鷹:香港流行音樂的問題其實很複雜。整個香港的繁榮,都與大陸息息相關。不管是轉口貿易,還是它的經濟對整個珠三角地區的輻射,都可以算做一體化基礎上的真正共同繁榮。香港的流行文化也是,從無到有,從低到高,從吸收外來元素到自己引領地區流行趨勢。內地之前對香港的趨之若鶩,也跟當年香港向西方、向日韓學習流行一樣。如今香港流行音樂沒有當年在內地那么紅火,很大原因也在於如今內地人的眼界也開闊了,這正是改革開放的最大貢獻之一。在眼界開闊了之後,面對香港的那些流行元素,我們自然不容易像剛開始接觸時那么興奮,畢竟大家的選擇都很多了。
流行文化這種東西不像法典那么至高無上,也沒那么嚴謹,更不需要太過認真地去總結一套理論,進行研究。流行文化就是這樣,該自然沉澱的,就會自然沉澱下來,過了很多年之後,變成經典。像《彎彎的月亮》之類的歌曲就是。這種東西,應該是古今如一的。因為根據歷史學家考證,像《
陽關三疊》這些名家詩詞,其實在古代它就是流行歌曲。有人告訴我,他們考證當年的陽關城,真是在城西就有那么一排酒樓,唐代酒樓就有唱曲兒的,估計在那裡唱的歌,《陽關三疊》自然免不了,那時就是這樣的風俗。
記者:來之前我把您這幾十年來的代表歌曲又翻聽了一遍,感覺您這些年來創作的歌曲,都有點曲風偏軟,這是不是跟您生活在南方有關?因為我們聽香港流行音樂,也很少能聽到那些比較硬朗、比較鏗鏘的歌曲,當然,搖滾除外。
李海鷹:1994年時,曾經召開過南北流行音樂人的一個研討會。但就我個人而言,並不認同這種地域性的劃分。我承認我的歌大多都是走偏輕柔的路子,但我覺得這更多是與作者自身有關,而單純地根據地域劃分南派北派,並不科學。因為流行音樂屬於文化的範疇,中國的文化,又有著悠久的歷史,就算
中央集權開始,也有2000多年了。而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化都是從中央輻射開的。就算你說南方、說廣東,廣東這幾千年來同樣是在中央統治下的,並沒有自己獨立的政治制度,所以,就算劃分也只能是分個人。
不過,如果真要說南派,我覺得廣東最大的好處在於,它雖然一直處於中央的統治範圍之內,但自古以來始終被中央認為是“蠻夷之地”,處於“化外”,中央對它的要求也不高,接受統治就行,所謂的“教化”程度並沒有那么深,對所謂文化正統的觀念也沒有那么深。這樣的先決條件也就決定了廣東在接受新鮮事物方面沒有內地其他原來文化中心圈的那些地方那么多障礙。接受新思想、新思潮比較容易———包括我們自己,誰都不會把廣東當作是中國的中心。所以,你看清朝末年,同盟會辛亥革命也好、
康有為梁啓超的維新也好,都是從廣東起步,因為他們容易接受這些思想。不過,廣東人接受了新思想,要想再進一步地發展,就必須進京,打入文化核心層,讓文化中心的人也接受。所以你看當年康有為要實施自己的主張,就必須進京,革命也必須北伐,打到北京才行。
所以,前段時間廣東提出建設文化大省,我覺得想法很好,我非常支持。因為廣東的文化思想本來就領先,而因為經濟建設領先全國,文化硬體配套建設得也不錯,如今在軟體上也開始下功夫,自然應該有這樣的一個目標。但是,這種建設不能偏,廣交、廣芭這些團隊應該有,但這些得搞出一些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東西。而流行文化在廣東本來就占據了不可忽視的地位,但流行文化的發展則要更多依靠市場,而不是政府主導。就像流行音樂,它和古典音樂,和文革及在那之前的歌頌音樂都不相同的是,流行音樂唯一的評判標準,是公眾是否喜歡,聽起來很民主的樣子,但也很現實。
我做的是音樂,是流行音樂,所以我要在浩瀚的武器庫中尋找,在精神方面去尋找祖宗留下來的東西。
記者:進入新世紀之後,您的創作似乎又開始轉移方向了,以影視作品的音樂居多,為什麼呢?
李海鷹:其實從《七子之歌》以後,我的主要精力就已經投放到影視方面的音樂上了。因為我不是很想做實驗性的音樂,不想做只被專家們認可的東西,我喜歡做讓大眾認可的東西。這也算是我自己的方式吧,因為在我看來,古典和流行,沒界限。不管什麼時候,人們對於比較有特點、有
張力、大型的、精緻的作品,都會有一定的期待,這也是我的目標和方向了。
記者:搞了這么多年的流行音樂創作,也出了如此多的精品,您應該也算得上是廣東流行音樂界的翹楚了。就您看來,您的創作之路對後來的廣東流行音樂界都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是否可以這樣說,因為您的創作風格,導致了整個廣東流行音樂界的風格變成了現在這樣相對集中?
李海鷹:我覺得不能這么說。就我個人而言,我的流行音樂創作,屬於古典音樂+
民族音樂的模式,如果說對我有影響的流行音樂人,我不能不說,當年的鄧麗君的確算一個。但流行文化屬於大眾文化,不能說是由一個人來進行引領或者影響。它是由很多人、很多歌、很多創作人共同製造出來的。而且,廣東的特色就在於,它在這幾十年來,一直在思想方面引領全國風氣之先,這也就決定了廣東的創作人不可能只接受一種單一的模式和風格的薰陶,更無從談起讓某一人統領誰。我唯一認可的,是自己的創作人身份。而創作人的工作,只是去做,文化創作的事是個人的,但不是主觀的。所謂的引領一時風氣之類的,只能是後人來進行總結。
不光是人,我覺得作品也一樣。一部文化作品,該有多大的影響力,就會有多大的影響力,這不是行政上的干預就能起作用的。你看,
曹雪芹就不用去想什麼領導方面的問題,他的作品開始是禁書,但在來看,不照樣是經典?而創作者則不應該在作品一出來就急著去關心它的社會反饋,得沉下心來,製作一些有價值的、有思考的東西,走自己獨特的路,一個創作者得耐得住寂寞。我覺得作為作者,就該寫點自己的東西,你又不是搞行政的,總想那些獎做什麼?

記者:從現在看來,您的這些歌曲,曲風實在多樣,但您給人留下的經典作品,在您說來可都是“靈感之作”,能不能透露一下,這么多年支撐您的“靈感”的源頭是什麼呢?畢竟很多音樂人,在寫完其中一些的優秀歌曲之後,創作能力便開始減弱了。
李海鷹:要說源頭……還得算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但我研究傳統文化,不是上下五千年一起看,我是從古代吸取營養,然後作用於現代。我覺得,1842年之後,也就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就開始變了,到
胡適,“五四”之後又變了。我覺得自從“五四”之後中國就一直沒有好的、可以算得上是流行作品的東西出現。所以我看的一般都是祖宗的文化,看1842年之前的東西。但我研究這些,不是單純地去做研究,或者說將古代的東西保存下來。像我也看戲劇,但並不是想把崑曲保留並發揚光大。我做的是音樂,是流行音樂,所以我要在浩瀚的武器庫中去尋找,在精神方面去尋找祖宗留下來的東西。從元明清的劇本,到古代的倫理、道德,在現代看起來,很多東西依然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基礎,戰亂和動盪環境下產生的東西,不會是這個民族生存的基礎。所以,我之前說《彎彎的月亮》時大家都在尋根,都在回望,我告訴你為什麼,因為我找到了自己的根,那就是我們無比深厚的傳統文化。
而且,如果說吸收,我認為更應該吸收它最根本的東西。在我看來就算是傳統文化,其中太多具體的東西也都有它的高峰和低谷。像唐詩宋詞元雜劇明清小說,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高峰。我們為什麼這么說?因為在這段時間內,有人把它玩到頭了,讓後人只能望其項背,無法超越了。但這些東西里,又有一脈相承的東西,就像《
紅樓夢》里也有詩歌,但我們任何人都不會說,《紅樓夢》里的詩歌超越了所有唐詩。我想,我要吸收的就是這些一脈相承的東西。
 李海鷹
李海鷹 李海鷹
李海鷹 李海鷹
李海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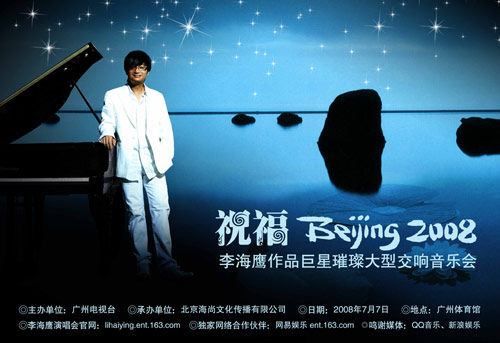 音樂會海報
音樂會海報 李海鷹
李海鷹




 李海鷹
李海鷹 李海鷹
李海鷹 李海鷹
李海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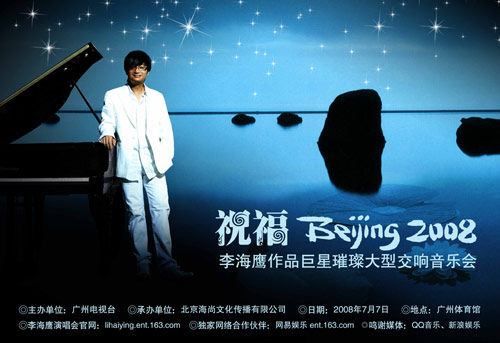 音樂會海報
音樂會海報 李海鷹
李海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