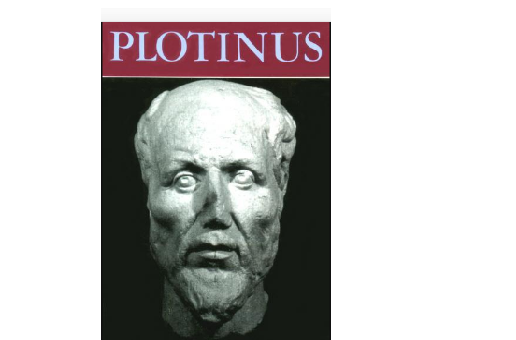簡介
它的特點在於:建構了超自然的世界圖式,更明確地規定了人在其中的位置,把人神關係置於道德修養的核心,強化了
哲學和
宗教的同盟,具有更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新柏拉圖主義的中心有羅馬、亞歷山大城、
敘利亞、
雅典。以雅典為主。重要的人物是
普羅提諾(plotinus)。
起源發展
新柏拉圖主義最早產生於埃及的亞歷山大,那裡幾百年間一直都是
希臘哲學與
東方神秘主義的交會地。該學派的創始人是阿摩尼阿斯·薩卡斯(Ammonius Saccas),不過最重要的人物則是他的學生
普羅提諾(Plotinus, 204/5~270年)生於埃及。普羅提諾早年在亞歷山大學習、研究,直到公元243年到羅馬定居。普羅提諾的作品主要都是他晚年的講課筆記,並流露出一定程度的神秘主義色彩。他將
柏拉圖的
客觀唯心主義哲學、
基督教神學觀念與東方神秘主義等思想熔為一爐,從而為基督教文論的基本取向和
奧古斯丁等人的神學思考鋪平了道路。 與柏拉圖的“理念”相似,普羅提諾也將美的根源歸結到彼岸世界,並對有別於世俗藝術的“美”的追求本身懷有極高的期待。這一方面使西方人藉助藝術尋求超越的衝動得以傳遞,另一方面也必然要求批評去揭示文學背後所隱喻著的永恆真理甚至信仰的啟示。
內容
新柏拉圖主義認為,世界有兩極,一端是被稱為“上帝”的神聖之光,另一端則是完全的黑暗。但新柏拉圖主義也相信,完全的黑暗並不存在,只是缺乏亮光而已。此處,亮光與黑暗對應基督教的善與惡。世間唯一存在的就是上帝,照耀著神聖之光,但就像光線會逐漸變弱,神聖之光也無法普照整個世界。
普羅提諾認為,靈魂受到神聖之光的照耀,物質則位於那光照不到的黑暗世界,而
柏拉圖所提出的自然界的“形式”則微微受到神聖之光的照耀。因此,新柏拉圖主義強調,世間一切事物都有這種神聖之光,但最接近上帝的光芒的,還是人類的靈魂,只有靈魂才能與神秘與偉大合二為一。在一些偶然的時候,人甚至可以體驗到自己就是那神聖的自然之光。
三大本體
普羅提諾論證說太一、理智和靈魂為“三個首要本體”。“本體”,指最高的、能動的原因,現代人也把它譯為“原則“。嚴格地說,本體並不是抽象的原則,而是具體的神。它超越存在和本質,因而可以決定存在和本質。
第一本體
肯定和否定兩重規定性
它有肯定和否定兩重規定性,肯定地說,
太一是神本身,是善本身。太一既是無所不包的統一性,又是單一、唯一的神。它不是萬物的總和,而是先於萬物的源泉。它的善不是倫理之善,而是本體的完善和圓滿,或者說,它是生命之源、力量之源。正因為如此,它不能與任何一個有生命、有力量的東西相等同。否定地說,太一不是一個東西,它無形式、無善、無德性、無意志、無思想、無意識、無運動或行動。
普羅提諾特彆強調太一或善的否定特徵,以此說明它超越了“是”所指示的存在和本質,太一不是一個東西。他說:“正依靠一,所是的東西才是東西。除了一個東西之外,它還能是什麼呢?除去一,它就不再是什麼東西了。……任何東西失去一也就失去了其所是”。這表明,普羅提諾可能意識到柏拉圖和
亞里士多德關於最高原則的分歧,他同意柏拉圖把善作為最高原則,而不同意亞里士多德把“所是的東西”作為最高原則。
不具備多樣性原初的一
太一之所以沒有任何肯定性的特徵的主要理由是,它不具備多樣性,是不可分割的原初的一。另一方面,一切能夠肯定的東西都有它的對立面,都是區分和分割的結果,只能歸屬於“多”,而不是“一”。比如.太一沒有思想、意志和行動,因為在它之外,沒有一個與之對立的思想對象、意志目標和被作用者。太一甚至不能意識到自身,不能在自身內部作出思想者和思想對象的區分,因而不能成為
亞里士多德所謂的“思想的思想”。
不可知性
太一除了可用另外一個名稱,即“善”來指示它之外,不能被說成“是”什麼,“有”什麼。我們只能說它“不是”什麼、“沒有”什麼。太一的否定性質同時也是它的不可知性。
普羅提諾說,
太一不是理智的對象,因為“理智只能認識事物,因而陷人多樣性,失去了一心。再說,理智只能靠概念和範疇去把握對象,而一切概念和範疇都需要區分才能被定義,因此只適用於能被分割的東西,但不適用於不可分割的太一。這裡需要說明,普羅提諾雖然否認太一是可知的,但同時又說,太一能被觀照。觀照不是區別分辨的認知活動,而是熱忱的道德追求。我們將看到,他是用人神相通的宗教神秘主義來解決人如何觀照太一的問題。
普羅提諾雖然沒有用過多的概念來規定太一,但卻用形象來比喻它。太一時常被喻為“太陽”、“源泉”。按照這些比喻,可以想像,太一雖然不運動,但卻能生成其它本體,這一生成過程被稱為“流溢”。這一比喻有兩方面意義。其一,
太一的生成並不是主動的創造,創造是一種外求的活動,但太一卻是完滿自足的,“因為它既不追求任何東西,也不具有任何東西,更不需要任何東西,它是充溢的,流溢出來的東西便生成其他本體。”或者毋寧說,流溢是善的自然流露。
普羅提諾說,物滿自溢,這個道理甚至連無生命的事物也要遵從。無生命的事物尚且儘可能地滋生繁殖,何況那最完善的太一呢?最完滿的原初之善怎么可能封閉在自身之內,好像嫉妒無能似的呢?它是萬物的力量。其二,流溢是無損於自身的生成。正如太陽放射出光芒無損於自身的光輝一樣。希臘哲學從早期的“補償原則”到後期的“
流溢說”,經歷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按照前者,生成是一種缺失,有待生成物的歸復作為補償;按照後者,生成是完善的本性所在,是自滿自足、產生外物而又不需外物的補償。前者反映出早期
自然哲學脫離宗教世界觀的趨向,後者反映出後期哲學歸復宗教世界觀的相反趨向。
第二本體
心靈
“理智”即希臘文的“
奴斯”,或譯為“心靈”。理智是最先從
太一中流出來的本體,被產生的本體不再保持原初的絕對統一性,它包含著一些原初的區分,因而具有肯定性質,可用最一般的範疇表示它。當然,理智仍然享有太一的統一性,因此,被區分出來的多樣性仍然是統一的。如果說太一是絕對的一,理智則是一和多的統一。用
柏拉圖的語言來說就是,單一的理智是
造物主,眾多的理智是理念,理念存寓於造物主或神聖理智之中,每一理念部分有神聖理智而成為造物主藉以創造的原型。這就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的辯證法。
理智
普羅提諾還進一步說明了適用於理智的範疇。它們是:思想和存在、異相同、動和靜。理智相當於
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思想的思想”,它既是思想活動,又是思想對象。思想活動產生於思想對象的存在,被思想的存在反過來賦予思想活動以存在。思想和存在是在理智內部作出的區分,都是理智必不可少的性質。對於思想活動,可進一步區分動和靜的性質,對於思想對象,可進一步區分異和同的性質。思想以其運動產生思想對象,以其靜止保持自身位置不變,猶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不動的推動者”。再者,思想對象各有差異,否則將不能被思想;但又有同一性,既與自身,又與其它對象保持同一,否則將不會成為同一個思想活動的對象。
以上六範疇基本取自
柏拉圖的“
通種論”。
普羅提諾認為、通種只適用於第二本體“理智”,因為它們是區分的產物,不能適用於不能被區分的
太一。通種表示的三組區分是最高的理智區分,是一切可感區分的前提。
第三本體
靈魂從理智中流溢出來。
普羅提諾說,理智的流溢是對
太一的流溢的模仿。作為第三本體的靈魂即
柏拉圖所說的世界靈魂。它是一種能動力量。它的
能動性表現在變動不居,活躍於各個領域,即可以作用於與自己本性相一致的理智和太一,也可以作用於與自己本性不一致的低級對象。或者說,靈魂既是一,又是多,但不像理智那樣,是一和多的統一。當它與理智和太一相通時,它復歸於原初的統一,因而是一;當它被分割在個別事物之中時,作為推動事物變化的內部動力,它是多。
普羅提諾使用哲學與宗教相混雜的表達方式,太一、理智和靈魂是三個本體,但又是同一個最高的神。他和其他希臘人一樣,相信星辰日月都是神,但他在哲學上卻是
一神論者。用單數大寫的神表示三大本體。用哲學的語言說,神即是一,或是絕對、純粹的一(
太一),或是一和多的統一(理智);或既是多,又是一(靈魂)。就是說,三個本體為同一位神。後來的基督教教父將“本體”譯為神的“
位格”,把神作為單一實體,引申出上帝“三位一體”的概念。
在倫理學上,
普羅提諾認為,靈魂趨向自然,同物質相結合是一種墮落。人要克服這種墮落,必須回歸到“太一”。他把回歸“太一”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是淨化靈魂的階段,使靈魂擺脫物慾的束縛,指向純粹的心智。第二個階段是理性沉思,在這個階段上表現為純粹的概念活動。第三個階段是出神或直覺。當人達到出神狀態,就會排斥一切感性因素和理性判斷成分,與神合一。當然,一般人是達不到這種最高境界的,只有道德高潔、智慧超群的人才能享受如此殊榮。他的學生
波菲利告訴我們,在他與老師相處的六年中,普羅提諾曾經有四次達到“出神”狀態,而他本人自然不如老師,在68年中只有一次達到這種境界。
由上述不難看出,在
普羅提諾的哲學中,以
柏拉圖和
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古希臘的理性思辨精神已經不多了,代替它的是神秘主義。所以,新柏拉圖主義的出現標誌著古希臘的理性思辨精神的衰落。它對後來的
基督教神學和中世紀的
經院哲學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可感世界
普羅提諾承認在三大本體之外,還有質料。質料沒有任何規定性,包括形狀的規定性,但質料不是“虛無”,而是“非是者”、非存在。非存在並非一無所有。而是一團漆黑的混沌。排除了事物所有性質之後,事物不成其為事物,剩下的只有質料。正如塗抹一切顏色之後仍有黑色一樣,質料並不是完全虛無的狀態。
質料和
太一是對立的極端,猶如黑暗與光明光明的對立。正因為如此,由太一發端的流溢終止於質料,猶如光線不能穿越無際的黑暗。然而,靈魂以其活躍的能力,卻能與質料相結合,產生出個別的、可感的事物,它們的總和就是可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