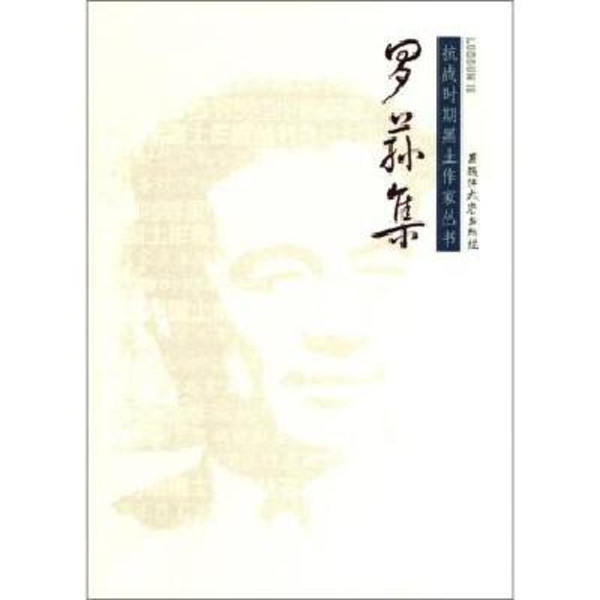《抗戰時期黑土作家叢書》為抗日戰爭時期(東北淪陷以後至抗日戰爭勝利)與黑龍江文學有密切關係的作家作品選集,收錄了金劍嘯、蕭紅、高蘭、蕭軍、塞克、舒群、羅烽、白朗、羅蓀、關沫南等有重要影響的黑土作家的作品。作品反映了抗戰時期黑土作家的生活和文化活動,以及黑土文學的發展脈絡和發展歷程。本叢書的出版,將使廣大讀者尤其是文學研究工作者全面了解抗戰時期黑龍江的文學創作;在黑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們通過閱讀黑土作家的作品,將深刻了解這塊土地曾經孕育出的文學精英,增強文化自信。 本書為該叢書之《羅蓀集》分冊。 《羅蓀集》主要收錄了羅蓀的“寂寞”、“靈魂的閃爍”、“蒼蠅”、“新題目,老文章”、“沉默救國”、“奇文共賞”、“伏惟尚饗”、“探梅和賞櫻”、“告別武漢”等作品。
基本介紹
- 書名:抗戰時期黑土作家叢書:羅蓀集
- 出版社:黑龍江大學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
- 頁數:325頁
- 開本:16
- 定價:48.00
- 作者:羅蓀
- 出版日期:2011年10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81129382X, 9787811293821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內容簡介
羅蓀,文藝評淪家、前《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國現代文學館名譽館長。在60年的文學征途中,歷經自中國新文學運動到改革開放時期的長過程。他所留下的不尋常足跡,值得後人思索。
《羅蓀集》主要收錄了羅蓀的“寂寞”、“靈魂的閃爍”、“蒼蠅”、“新題目,老文章”、“沉默救國”、“奇文共賞”、“伏惟尚饗”、“探梅和賞櫻”、“告別武漢”等作品,從中讀者可以領略她的思想和藝術才華。
《羅蓀集》主要收錄了羅蓀的“寂寞”、“靈魂的閃爍”、“蒼蠅”、“新題目,老文章”、“沉默救國”、“奇文共賞”、“伏惟尚饗”、“探梅和賞櫻”、“告別武漢”等作品,從中讀者可以領略她的思想和藝術才華。
圖書目錄
前言
小說
寂寞
靈魂的閃爍
未發的書簡
——懷友人T君
代表
雜文
蒼蠅
新題目,老文章
論讀書
旅行之類
沉默救國
奇文共賞
伏惟尚饗
“國慶”乎?
“一·二八”四周年
新“欽差大臣”
探梅和賞櫻
“與抗戰無關”
再論“與抗戰無關”
美麥和美機
“太平盛世”
告別武漢
江上
喜劇世界
略論“自大”
談“人格”
第三種人
新踏踏派
反虛偽的精神
魯迅先生——蘇聯文藝的介紹者
頌“勝利”
新春試筆
看“岳飛”有感
“小雨點”
一粒帶著諷刺的子彈
掘發人性
自覺的聲音
關於魯迅的“明天”
最後的旗幟
——回憶
士可“辱”不可“殺”
轟炸書簡
養鼠成患
一面鏡子
“不行”之所在
慶祝一章
——山城雜章
“哭泣文學”種種
“殺人”與“改造人”
時間
——新年雜感
《寂寞》集後記
夢與現實
——讀張恨水的《八十一夢》
苦雨雜記
“作家”、“詩人”、“豬”
箕豆夜錄
預言和泡沫
“錯覺”的悲喜劇
東北人民需要什麼
附錄
好人羅蓀
紀念孔羅蓀誕辰90周年座談會
斯人已去遺風長存
——孔羅蓀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側記
惜別孔羅蓀
記羅蓀
播種的人
《天藍的生活》的歸來
——懷念羅蓀先生
摯友情
——孔羅蓀與戈寶權
復出文壇甦醒時
高山流水
生命之花
——巴金與羅蓀
羅蓀論
羅蓀年譜
小說
寂寞
靈魂的閃爍
未發的書簡
——懷友人T君
代表
雜文
蒼蠅
新題目,老文章
論讀書
旅行之類
沉默救國
奇文共賞
伏惟尚饗
“國慶”乎?
“一·二八”四周年
新“欽差大臣”
探梅和賞櫻
“與抗戰無關”
再論“與抗戰無關”
美麥和美機
“太平盛世”
告別武漢
江上
喜劇世界
略論“自大”
談“人格”
第三種人
新踏踏派
反虛偽的精神
魯迅先生——蘇聯文藝的介紹者
頌“勝利”
新春試筆
看“岳飛”有感
“小雨點”
一粒帶著諷刺的子彈
掘發人性
自覺的聲音
關於魯迅的“明天”
最後的旗幟
——回憶
士可“辱”不可“殺”
轟炸書簡
養鼠成患
一面鏡子
“不行”之所在
慶祝一章
——山城雜章
“哭泣文學”種種
“殺人”與“改造人”
時間
——新年雜感
《寂寞》集後記
夢與現實
——讀張恨水的《八十一夢》
苦雨雜記
“作家”、“詩人”、“豬”
箕豆夜錄
預言和泡沫
“錯覺”的悲喜劇
東北人民需要什麼
附錄
好人羅蓀
紀念孔羅蓀誕辰90周年座談會
斯人已去遺風長存
——孔羅蓀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側記
惜別孔羅蓀
記羅蓀
播種的人
《天藍的生活》的歸來
——懷念羅蓀先生
摯友情
——孔羅蓀與戈寶權
復出文壇甦醒時
高山流水
生命之花
——巴金與羅蓀
羅蓀論
羅蓀年譜
文摘
寂寞
一九三九年的初春,我接到一個朋友從鄂北寄來的信,他的名字叫林濤,武漢淪陷以後,一直沒有聽到關於他的訊息,因為他在武漢淪陷前,正患著相當嚴重的肺結核,而那時候,他又努力支持著病體,參加了保衛大武漢的工作,所以使許多來到重慶的朋友們,都異常的關懷著他的下落。
這封信遞到我手裡的時候,真是說不出的愉快和欣慰,我望著那信面上的字跡,正如同看見了他那頎長而清癯的身影,那蒼白而兩頰上略有一層薄薄的紅雲的臉龐,那一雙富有熱情而深邃的眼睛,那一口爽朗而悅耳的北平話。但是在我拆讀了這封用“血紅”的筆寫的信的時候,我在為一個快要倒下來的戰友而哀傷,為一個慘酷遭遇的弟兄而憤恨。下面便是他病在鄂北樊城的一個淒冷的小客棧里寫來的信:
……我還剛剛要提筆準備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已忍不住辛酸的淚傾瀉下來。好友,請你不要笑,我會變得這么樣的脆弱吧。我連支持起自己的體力的勇氣都沒有了,可是,在這樣的時候,我是怎樣的在想念你們啊!
這裡還是冷酷的冬天啊!我獨自躲在這個荒僻的小城中的一個淒冷的小客棧里,我必須掙扎著我所有的精力,寫這封信給你,以及我的那些幸福的朋友們。因為我現在已完全陷於絕路,我必須向你們伸出求援的手來,我相信你們一定會援助我,即使是我現在已變成一個完全沒有用處的廢物。
我還記得很清楚,在半年前,我們還都在保衛大武漢的激流中,每個人都以自己的熱力來沸騰那一個澎湃的高潮。但是我卻不幸的正在昂揚的時候,病纏住了我,稍微累了一點,便會大量的吐著血。可是一等精神恢復,便不能抑止住自己的熱情工作,工作!它雖然疲倦著我,卻也十分的解救了我。朋友中,你也是其中的一個,曾一再熱情的勸我回到鄉間去休養一個時候,抗戰是長期的,倘沒有一個經得起鍛鍊的體格,是難以支持的。
沒有來得及等我考慮這些問題,而一切不幸都已尾隨著我而來了。
電台要疏散,發給我六十元錢的遣散費,那時候,我正病臥在一個朋友的家裡。我不能立時離開這我所愛的城市,我看見那么多熱情的年青的夥伴,馳騁在祖國的戰場上,激昂的熱流中,我不能離開他們。雖然我也許會成為他們的累贅,可是我還有一點勇氣和毅力來支持自己。
不幸的日子終於到了,就在狂熱的雙十節那一天,我扶在朋友的肩上站在江漢關的石級上,巡視了那么偉大的壯觀的行列,那么熱情而激昂的隊伍,我實在不會相信,我們的心臟,我們的偉大的城會陷落的。
我支持著病體,拒絕了一個朋友的伴送,我寂寞的回到了荊門,鄂中的一個小城。這裡有我的家,一個破落的大戶。當我看見年邁的雙親,用了悲喜交集的情緒迎著我的時候,我的心創痛而拘攣起來。我帶回了什麼給他們呢?
唉,好友,我不想多說這些屬於個人情緒的事吧。雖然你們當會瞭然當日的景況。我在這個小城裡平靜的住了一個月的光景,說是平靜,實際上也只是我個人好似很平靜的住著而已。難民和新的恐怖卻時時襲擊著這個小城。武漢淪陷後,這兒已成了鄂中的重鎮。不幸是孿生的,十一月十三日,這個小城遭遇了空前殘酷的轟炸。我們一家三口在倉皇中逃出城外,等到回來的時候,我的家已經變成一片瓦礫。自然,這並非是加於我個人命運上的例外。而我現在卻變成一個空無所有的了。
終於靠著親友的幫助,我們輾轉在山野之中。我相信你們一定想像得出,我在第一個月中的休養,在第二個月卻取得了雙倍的報復。我幾次想掙紮起我的體力,到鄂東去參加戰爭,但是我在這一次的遭遇中,這個幻夢又被毀滅了。有一天,我忽然得到一份鄂北日報,發現了我的朋友啊!我如同吃下了一服興奮劑,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得到了勇氣,我竟然振作了起來,我可以支持自己的體力,不再終天躺在床上。我必須作一次最後的冒險,我不能坐視著老父老母的凍餒,我還須用出我最後的力量,去追求那一團熱火。
我終於設法去湊了一點點錢,而留在家裡的卻只是大洋兩元。可是我再不能顧慮這些了,我必須拿出最大的勇氣來。我又重新開始了我的征途。
這時候的心境宛如出征的英雄,推開了所有的雜念,忽然好像變成了壯健的戰士了。
一到樊城,就去找我的朋友K君,而這個報館的窘況,卻使我冷了許多,但是朋友們艱苦搏鬥的精神,吃苦耐勞的毅力,十分的感動了我。他們在沙漠中開荒。我雖然體弱,但我還有自信,我仍然應該是他們中間的一個。
他們分配給我的工作是每天從下午四點鐘到夜深兩點鐘的譯電,據K說,這是在他們一夥中間擔任最少的工作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力量竟至於如此的脆弱了,我僅僅的工作了兩個夜晚,就再也不能支持下去了。如果我再工作一天,也許就連生命也都將停止在這裡。我不能打擾他們,因為他們都在艱苦困難中工作,他們都窮得每天僅僅吃兩頓飯。
現在,我病倒在這間淒冷而狹隘的小客棧里,無窮盡的熱望,無窮盡的幻想,和著無窮盡的回憶,折磨著我,鼓舞著我。而我卻沒有一點力量能夠再振一振我那折斷了的翅膀。
好友,我這時候只有向你們伸出求援的手,希望你們的召喚,而不會遺棄這樣一個病弱的戰友吧?!因為,我在呼吸停止之前,我還有一個幻想,我還有一點希望,我還須再振一振我的無力的翅膀,即使飛得低一點,也不妨,總之,我應該飛一飛啊!好友,我深信你們不會吝惜對於我的援助的。
我只要求你們寄給我一點點旅費,我先到宜昌去,我決定要去。之後,我的力量還夠的話,我就會飛到你們的面前來的。
P3-5
一九三九年的初春,我接到一個朋友從鄂北寄來的信,他的名字叫林濤,武漢淪陷以後,一直沒有聽到關於他的訊息,因為他在武漢淪陷前,正患著相當嚴重的肺結核,而那時候,他又努力支持著病體,參加了保衛大武漢的工作,所以使許多來到重慶的朋友們,都異常的關懷著他的下落。
這封信遞到我手裡的時候,真是說不出的愉快和欣慰,我望著那信面上的字跡,正如同看見了他那頎長而清癯的身影,那蒼白而兩頰上略有一層薄薄的紅雲的臉龐,那一雙富有熱情而深邃的眼睛,那一口爽朗而悅耳的北平話。但是在我拆讀了這封用“血紅”的筆寫的信的時候,我在為一個快要倒下來的戰友而哀傷,為一個慘酷遭遇的弟兄而憤恨。下面便是他病在鄂北樊城的一個淒冷的小客棧里寫來的信:
……我還剛剛要提筆準備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已忍不住辛酸的淚傾瀉下來。好友,請你不要笑,我會變得這么樣的脆弱吧。我連支持起自己的體力的勇氣都沒有了,可是,在這樣的時候,我是怎樣的在想念你們啊!
這裡還是冷酷的冬天啊!我獨自躲在這個荒僻的小城中的一個淒冷的小客棧里,我必須掙扎著我所有的精力,寫這封信給你,以及我的那些幸福的朋友們。因為我現在已完全陷於絕路,我必須向你們伸出求援的手來,我相信你們一定會援助我,即使是我現在已變成一個完全沒有用處的廢物。
我還記得很清楚,在半年前,我們還都在保衛大武漢的激流中,每個人都以自己的熱力來沸騰那一個澎湃的高潮。但是我卻不幸的正在昂揚的時候,病纏住了我,稍微累了一點,便會大量的吐著血。可是一等精神恢復,便不能抑止住自己的熱情工作,工作!它雖然疲倦著我,卻也十分的解救了我。朋友中,你也是其中的一個,曾一再熱情的勸我回到鄉間去休養一個時候,抗戰是長期的,倘沒有一個經得起鍛鍊的體格,是難以支持的。
沒有來得及等我考慮這些問題,而一切不幸都已尾隨著我而來了。
電台要疏散,發給我六十元錢的遣散費,那時候,我正病臥在一個朋友的家裡。我不能立時離開這我所愛的城市,我看見那么多熱情的年青的夥伴,馳騁在祖國的戰場上,激昂的熱流中,我不能離開他們。雖然我也許會成為他們的累贅,可是我還有一點勇氣和毅力來支持自己。
不幸的日子終於到了,就在狂熱的雙十節那一天,我扶在朋友的肩上站在江漢關的石級上,巡視了那么偉大的壯觀的行列,那么熱情而激昂的隊伍,我實在不會相信,我們的心臟,我們的偉大的城會陷落的。
我支持著病體,拒絕了一個朋友的伴送,我寂寞的回到了荊門,鄂中的一個小城。這裡有我的家,一個破落的大戶。當我看見年邁的雙親,用了悲喜交集的情緒迎著我的時候,我的心創痛而拘攣起來。我帶回了什麼給他們呢?
唉,好友,我不想多說這些屬於個人情緒的事吧。雖然你們當會瞭然當日的景況。我在這個小城裡平靜的住了一個月的光景,說是平靜,實際上也只是我個人好似很平靜的住著而已。難民和新的恐怖卻時時襲擊著這個小城。武漢淪陷後,這兒已成了鄂中的重鎮。不幸是孿生的,十一月十三日,這個小城遭遇了空前殘酷的轟炸。我們一家三口在倉皇中逃出城外,等到回來的時候,我的家已經變成一片瓦礫。自然,這並非是加於我個人命運上的例外。而我現在卻變成一個空無所有的了。
終於靠著親友的幫助,我們輾轉在山野之中。我相信你們一定想像得出,我在第一個月中的休養,在第二個月卻取得了雙倍的報復。我幾次想掙紮起我的體力,到鄂東去參加戰爭,但是我在這一次的遭遇中,這個幻夢又被毀滅了。有一天,我忽然得到一份鄂北日報,發現了我的朋友啊!我如同吃下了一服興奮劑,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得到了勇氣,我竟然振作了起來,我可以支持自己的體力,不再終天躺在床上。我必須作一次最後的冒險,我不能坐視著老父老母的凍餒,我還須用出我最後的力量,去追求那一團熱火。
我終於設法去湊了一點點錢,而留在家裡的卻只是大洋兩元。可是我再不能顧慮這些了,我必須拿出最大的勇氣來。我又重新開始了我的征途。
這時候的心境宛如出征的英雄,推開了所有的雜念,忽然好像變成了壯健的戰士了。
一到樊城,就去找我的朋友K君,而這個報館的窘況,卻使我冷了許多,但是朋友們艱苦搏鬥的精神,吃苦耐勞的毅力,十分的感動了我。他們在沙漠中開荒。我雖然體弱,但我還有自信,我仍然應該是他們中間的一個。
他們分配給我的工作是每天從下午四點鐘到夜深兩點鐘的譯電,據K說,這是在他們一夥中間擔任最少的工作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力量竟至於如此的脆弱了,我僅僅的工作了兩個夜晚,就再也不能支持下去了。如果我再工作一天,也許就連生命也都將停止在這裡。我不能打擾他們,因為他們都在艱苦困難中工作,他們都窮得每天僅僅吃兩頓飯。
現在,我病倒在這間淒冷而狹隘的小客棧里,無窮盡的熱望,無窮盡的幻想,和著無窮盡的回憶,折磨著我,鼓舞著我。而我卻沒有一點力量能夠再振一振我那折斷了的翅膀。
好友,我這時候只有向你們伸出求援的手,希望你們的召喚,而不會遺棄這樣一個病弱的戰友吧?!因為,我在呼吸停止之前,我還有一個幻想,我還有一點希望,我還須再振一振我的無力的翅膀,即使飛得低一點,也不妨,總之,我應該飛一飛啊!好友,我深信你們不會吝惜對於我的援助的。
我只要求你們寄給我一點點旅費,我先到宜昌去,我決定要去。之後,我的力量還夠的話,我就會飛到你們的面前來的。
P3-5
序言
羅蓀(1912—1996),一位歷近百年人生走過20世紀歷史風雲的人物,雖淡出歷史舞台卻並未終結人們歷史記憶的文化人。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他的一生就與共產黨的文化事業密切相關。他在八年抗戰期間,作為“抗協”常務理事和《文學月報》主編,與一切消極抗戰言論做鬥爭,扶植文學新秀,不僅是一位激情抗戰的文化戰士,而且還是一位新中國文藝播種人。解放後,歷任《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國現代文學館名譽館長等職務。同時筆耕不輟,他又是作家、文藝理論家和編輯家,寫過詩歌、小說、散文和文學評論,身後留下15部文集。當羅蓀先生百年之後,作家端木蕻良寫的一副輓聯是:“做人做事平生嚴謹如一日;為友為文世上坦誠無二言。”“嚴謹”和“坦誠”,幾乎是羅蓀生前朋友們普遍的評價。中國人一向重視蓋棺定論,但能留得生前身後名又能有幾人?而對羅蓀先生高度的讚譽與他的政治生活似乎並無絕對的關係,恰如原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舒乙所言:“好人羅蓀,我們深深懷念您。”
這是一位人品和文品都值得後人懷念的人,他以嚴謹和坦誠的人生態度為朋友為文學事業做了許多好事實事。如果以歷史大事記的方式回顧一下羅蓀的人生經歷,人們知道並肯定他的第一個貢獻是抗戰時期的實績。1938年,他在漢口積極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作為重要骨幹擔任了《抗戰文藝》編委(《抗戰文藝》是抗日戰爭時期出版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刊物,從1938年創刊到1946年閉刊,一共出版了十卷,計73期,羅蓀參加了從第一卷到第五卷的編輯工作)。後來該協會內遷重慶,羅蓀的家就成了編輯部,團結了大批積極抗戰人士。更為重要的是羅蓀還發起了文藝界與梁實秋所謂“文藝與抗戰無關論”的堅決鬥爭,為抗戰文藝作出了重要貢獻。羅蓀第二個貢獻是打倒“四人幫”之後擔任《文藝報》主編之初,竭力為文藝界的撥亂反正鼓與呼,大力提倡突破禁區、解放思想,為所謂文藝“毒草”平反,為藝術家恢復名譽,社會反響巨大,為新時期文藝思想解放開了路。羅蓀笫三個大貢獻是晚年受巴金先生的委託和中國作協的安排,負責籌建中國現代文學館。1982年,古稀之年的羅蓀為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備工作殫精竭慮,奔走呼籲,親自踏察館址,徵集資料,傾注了一位領導者更是一位作家對文學的情感,奉獻了他最後的光與熱。他和巴金先生作為第一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名譽館長當之無愧。
評價羅蓀,譽之為中國文藝發展的建設者和見證人,有史實為證,但這並非是全部。實際上,羅蓀對中國新文學事業有過不小的貢獻,目前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對這位當年的東北作家、激情抗戰的文藝戰士,研究還遠遠不夠,這不能不說是缺憾。從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羅蓀創作了大量與抗戰相關的小說、詩歌、散文與雜文,研究這些作品,對於豐富東北作家群創作面貌,認識作為文藝評論家的羅蓀對抗戰文藝的貢獻都是非常有意義的探討。
羅蓀與現代文學的深刻淵源始於哈爾濱。
1928年,16歲的羅蓀為了減輕家裡負擔,輟學考入哈爾濱郵政局。他始終保持對文學的熱烈嚮往,一邊工作一邊開始用“羅蓀”等多個筆名給《國際協報》和《晨光報》投稿,第一首詩作由《晨光報》副刊《江邊》刊出,第一篇小說《新墳》由《國際協報》副刊《綠野》連載。以後又發表了長篇小說《暗》。同時,他與幾位文學同道組織了“寒光”劇社,表演話劇。後來由他提議創辦了一份《國際協報》的文學副刊《蓓蕾》周刊,並由他擔任編輯,由是表現出羅蓀的文學和組織才能。他創辦的“蓓蕾”文學社團結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學青年,也使羅蓀的文學才華與日進展,他像一隻春燕,在哈爾濱的寒冬利用文學的陽光播撒早春的氣息。直到“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國主義的魔爪伸進哈爾濱,《國際協報》處境艱難,1931年末,《蓓蕾》周刊被迫停刊。據當年共同創辦“蓓蕾社”的台灣著名作家陳紀瀅著文說:由於《國際協報》是當年東北最大的一家報紙,羅蓀作為一名少年文學愛好者,主編該報《蓓蕾》副刊,有聲有色,日漸興旺,它的影響已超越東北範圍,受到平、津、滬等地文壇的重視,並把當時東北地區的作家聚集到了一起,把他們作品介紹到關內,為後來東北作家群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少年羅蓀是拾薪之人,為東北地方文藝的發展作出了他的貢獻。並由此結下了與中國新文學發展的不解之緣。他日後以筆為槍,寫下的大量戰鬥檄文都和在哈爾濱這段時期的創作與編輯生活密切相關,在他的一生中,哈爾濱是一生難解的故鄉情緣,尤其是鐵蹄下東北人民的呼與吸之痛更與他的生命休戚相關。特別是後來全面抗戰爆發後那個激情的文藝評論家,時刻把抗戰作為人生要義。與梁實秋的“文藝與抗戰無關論”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當年居住哈爾濱生成的切實的喪國之痛與強烈的愛國情懷,都成為羅蓀先生積極推動抗戰文學的直接思想動因。
1932年9月,羅蓀與夫人周玉屏以蜜月旅行為由途徑大連到了上海,從此告別了家鄉哈爾濱。人生掀開了新的一頁,也正式開始了一個“左翼”文藝評論家的文學生涯。自此他的生命將與新中國的文藝事業息息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後人往往看見的是一本本文集積累的文學成就,但是作家本人的精神成長軌跡卻隱於文字背後,有待進一步發現開掘,我們今天看到的思想之樹結出的一粒粒飽滿的種子,都是經過人生風雨的洗禮錘鍊後破土而出熠熠發光的。離開哈爾濱後,羅蓀的創作興趣從最初的詩歌、小說轉移到散文和雜文上了,這與他開始受到魯迅先生的影響有直接關係。1934年,羅蓀曾隨叔父孔敏到魯迅家中拜訪過魯迅先生和許廣平,並於1935年5月22日從武漢給魯迅寫信,邀請他為《大光報》副刊《紫線》寫稿,羅蓀時為該副刊編輯。能主動向魯迅先生約稿表現出羅蓀的文學誌向和他對魯迅先生的景仰程度,實際上羅蓀早在哈爾濱時就經常讀魯迅作品及其編的雜誌,汲取精神給養,從一踏上文學之路就奠定了堅實的“為人生”的現實主義精神立場。這也決定了在日後多次複雜的文藝思想爭論中,羅蓀能夠保持鮮明的“左翼”立場和批判激情。羅蓀對魯迅先生的景仰之情還表現在對魯迅精神的深刻理解上,特別是在魯迅先生去世之後,面對許多宿敵對魯迅的謾罵與詆毀,羅蓀撰文挺身捍衛魯迅。他在1940年紀念魯迅誕辰六十周年的文章《自覺的聲音》中寫道:
魯迅先生誕生的六十年,恰恰正是中國在滅亡與新生的路上掙扎與彷徨、鬥爭與妥協的最激烈的戰鬥的時代。他,代表著中國的“自覺的聲音”,在這無聲的古老潭穴里,投下了一顆猛烈的爆炸彈。這聲音並不只是激起一些復歸於平靜的浪花,它不但搗破著舊的巢穴,暴露了鬼魅的行徑,揭發了怯懦、卑劣、無恥、殘酷的劊子手和奴才們的面目,而且用了自己的生命和血來拯救和洗清那些“生長在劊子手主義和奴才主義環境裡的孩子們”。
羅蓀堅定地指出魯迅代表了中國“自覺的聲音”,也正是有這樣的“聲音”的存在與吶喊,才能拯救被劊子手和奴性主義麻痹的國民靈魂。這正是魯迅精神的實質和思想根源。有了這樣明確的警醒的認識,才能真正繼承魯迅的戰鬥精神並身體力行地為繁榮雜文創作作出自己的貢獻。唯其如此,八年抗戰期間,一位奮筆疾書戰鬥的文藝家羅蓀才能給時代留下了鏗鏘有力的回音。他努力讓自己的文字化作“中國的聲音”。
風雲激盪的20世紀30年代,羅蓀同那個時代的許多人一樣,注定在大浪淘沙的歷史轉折中不時調整自己人生的航程。大時代的光與影與個人命運疊合映證。1938年在漢口舉行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成立大會上,活躍著羅蓀身影,曾經有過亡國之痛的他對文協宗旨“民族的命運也將是文藝的命運”、“抗敵救國是我們的旗號”有著深刻的體會,也是他人生鮮明的精神立場和價值所在。此時,如果有阻礙抗戰的言與行,我們相信,羅蓀一定會像魯迅先生痛打落水狗那樣發揚頑強的戰鬥精神,表達一個正直中國人的良知。所以,今天的我們同樣能夠理解羅蓀先生當年與梁實秋“文藝與抗戰無關論”論戰的激情。因為在羅蓀的思想里,真的是認為“民族的命運也將是文藝的命運”,此外,別無選擇。
思想的鬥爭從來都是尖銳的戰爭,帶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但是大敵當前,山河破碎,救亡是當務之急。1938年,這箇中華民族嚴峻沉重的年代,對於黨派、知識分子、個人來說,真正到了歷史抉擇之際,我們今天看到當時國共兩黨聯合抗戰的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了,在“左聯”解散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也成立了。這真是一個同仇敵愾民族生死攸關的歷史大轉折。但是轉折是複雜的,多種黨派、多種勢力、多種主義話語和個人價值偏好使得大時代語境十分嘈雜,表面上合作抗日,但是各種話語對抗交鋒衝突不斷,而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衍生積澱的文藝界的鬥爭,則成為進入全面抗戰後表面統一背後話語紛爭的根苗。各種宗派情緒與消極思想並非“統一戰線”就能統一,而是借用各種歷史時機有所表現。梁實秋的“文藝與抗戰無關論”就是代表。1938年12月1日。《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梁實秋,在當天《中央日報》的《平明》副刊上發表《編者的話》,其中有一段代表性文字:
現在抗戰高於一切,所有人一下筆就離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為不同。與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至於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沒有益處的。
反對“抗戰八股”似乎是占據了話語先機,但真實意圖並非那么簡單。在抗戰形勢最為嚴峻的時刻和抗戰文學遠未深入的情況下,以反對“抗戰八股”為藉口,提出文藝可以“與抗戰無關”的主張,特別是還公然嘲諷堅持抗戰為宗旨的文藝界統一戰線——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冷嘲熱諷地叫囂:“所謂‘文壇’,我根本不知其坐落何處,至於‘文壇’上誰是盟主,誰是大將,我更是茫然。”梁實秋所說“文壇”,指的正是文協。對抗戰文藝統一組織機構和抗戰主張極盡挖苦詆毀之能事,其用心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梁實秋身為國民黨《中央日報》副刊主編,其言論表明了國民黨戰略轉變的動向,這種對尚在普及階段的抗戰文藝的排斥心理實際上體現了取消抗戰文藝的真實動機。
第一個對梁實秋《編者的話》快速做出反應並提出質疑的就是青年評論家羅蓀。東北作家的抗戰激情和他“為人生”的現實主義戰鬥精神,使他能夠及時準確地對“文藝與抗戰無關論”這一消極抗戰的言論作出判斷。他寫出了題為《“與抗戰無關”》和《再論“與抗戰無關”》兩篇雜文,相繼發表在重慶《大公報》上。針對梁實秋的“文藝與抗戰無關論”論調,羅蓀嚴正地指出:
這次戰爭已然成為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戰爭所波及到的地方,已不止限於通都大邑,它已擴大到達於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影響之廣,可以說是史無前例。在這種情況下,想令人緊閉了眼睛,裝作看不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今日的中國,要使一個作家既忠實於真實,又要找尋“與抗戰無關”的材料,依我拙笨的想法也實在並不容易……在今日的中國,想找“與抗戰無關”的材料,不過是某些人們心理上的“避難所”的一種幻覺罷了! 民族危亡,羅蓀以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認識到文藝與抗戰的重大關係。想起東北家鄉人民的水深火熱,侵略者的暴虐行徑,羅蓀義正詞嚴落地有聲地大聲疾呼:“今日的中國是沒有與抗戰無關的地方的!”他認為:“作為時代號角,反映現實的文學藝術,更其不能例外的要為祖國的抗戰服務。然而梁實秋抹殺了今日抗戰的偉大力量的影響,抹殺了今日中國的抗戰這個真實的存在,抹殺了今日全國愛國文藝界在共同努力的一個目標:抗戰的文藝。”羅蓀的文章發表後,引起熱烈回響,一場文藝與抗戰關係以及要不要堅持抗戰的爭論,大範圍擴展開來。著名作家郭沫若、茅盾、周揚、老舍、夏衍、田漢等通過報紙、刊物、專著、演講、座談等形式,紛紛對“文藝與抗戰無關論”提出批評。人們不約而同地嚴詞責問:梁實秋不勸人把抗戰文章寫好,反而勸人寫點不抗戰也好的文章,是所為何來?是不是做了幫凶?其結果,《中央日報》面對群情鼎沸的局面,不得不拋出替罪羊——1939年4月梁實秋被迫辭職離任。然而爭論並未停歇,事關民族大義,文藝與抗戰關係問題的爭論,早已匯入了政治上“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的抗日救國的時代呼聲中,這也是民族的正義之聲。
何為大是大非?羅蓀與同時代人一生中都面臨著是與非的考驗與抉擇,這是一代帶有悲劇意味的知識分子,從“五四”到“抗戰”再到“反右”、“文革”,真是人生百年風雲變幻。作為個人生命史,歷史不可回溯,但人生關鍵抉擇真的就是那么幾步。在與梁實秋的“文藝與抗戰無關論”針鋒相對反擊時,歷史可以證明:羅蓀對了。這不是宗派相爭,更不是宿怨報復,這是民族大義大是大非的問題,這場爭論之所以那么長久,其意義那么深遠,其中就隱含著不辯自明的真理:外虜當前,文藝必須為抗日戰爭這場正義之戰服務。抗日烽火已燃遍祖國大江南北,正義的人們心中響徹的正是羅蓀那句穿越歷史的鏗鏘話語——今日的中國是沒有與抗戰無關的地方的!
以文藝為抗戰服務,是青年羅蓀人生的信仰。八年抗戰期間,他曾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常務理事,出版部副主任和會刊《抗戰文藝》編委,《文學月報》主編,同當時不抵抗主義進行了堅決鬥爭,為文藝更好地為抗戰服務作出了貢獻。這期間羅蓀創作了大量的雜文,發揚魯迅先生的戰鬥精神,同一切消極抗戰言論論戰,其目的是要在血與火的洗禮中煥發中華民族的新精神,把抗戰進行到底。即使是抗戰勝利了,他依然警惕著那些發動內戰分裂東北的陰謀,在《東北人民需要什麼》一文中,大聲呼籲:經過十四年法西斯統治終於獲得勝利的東北人民不再需要武力戰爭,不再需要法西斯統治,更不需要官僚政治以及任何形式的掠奪。而真正需要的是一個偉大的希望——要有一個和平、民主、統一、團結的新東北,要有自由、和平、幸福的生活。可以想像,羅蓀對於東北新生活的構想,是一個堅守人道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對未來烏托邦社會情景的構想,對家鄉的深情,對形勢清醒的認知。這些都表現出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價值立場,這時的羅蓀作為文化戰士,在嚴峻的現實面前表達了思想的力量。
羅蓀還是一位優秀的編輯家,不論是《蓓蕾》,還是《文學月報》等刊物,都辦得有聲有色,特別是《文學月報》連續出版了兩年,計3卷15期,每期發行量都達到萬份,為抗戰時期少有。這一刊物在重慶和大後方曾有廣泛影響被譽為“文藝雜誌的巨星”。這些刊物扶植了新人,推動了文藝發展,在這一點上,羅蓀功不可沒。作家碧野曾在1992年撰文《播種的人》回憶了他與《文學月報》的故事,充滿深情地敘述了他與羅蓀交往的細節,當年真誠友愛的主編羅蓀推薦了《燈籠哨》和《烏蘭不浪的夜祭》,大大鼓舞了青年作家碧野,回憶難忘的往事,他在文章中熱贊羅蓀是中國新文學的播種人。多么恰切的評價,沒有羅蓀這樣辛勤耕耘的優秀編輯家,就沒有中國新文學繁茂的文學之林。
羅蓀,這位東北作家,優秀的評論家和編輯家,其身影已漸漸隱於歷史的地平線之中,但是我們依然從那些鮮活的文字以及朋友們親切的回憶中,看見了這位為新中國文藝播種的人,他是朋友眼裡的好人,更是一位激情的文藝戰士,正直的文人。
斯人已去,遺風永存!
郭力
2011年4月30日
這是一位人品和文品都值得後人懷念的人,他以嚴謹和坦誠的人生態度為朋友為文學事業做了許多好事實事。如果以歷史大事記的方式回顧一下羅蓀的人生經歷,人們知道並肯定他的第一個貢獻是抗戰時期的實績。1938年,他在漢口積極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作為重要骨幹擔任了《抗戰文藝》編委(《抗戰文藝》是抗日戰爭時期出版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刊物,從1938年創刊到1946年閉刊,一共出版了十卷,計73期,羅蓀參加了從第一卷到第五卷的編輯工作)。後來該協會內遷重慶,羅蓀的家就成了編輯部,團結了大批積極抗戰人士。更為重要的是羅蓀還發起了文藝界與梁實秋所謂“文藝與抗戰無關論”的堅決鬥爭,為抗戰文藝作出了重要貢獻。羅蓀第二個貢獻是打倒“四人幫”之後擔任《文藝報》主編之初,竭力為文藝界的撥亂反正鼓與呼,大力提倡突破禁區、解放思想,為所謂文藝“毒草”平反,為藝術家恢復名譽,社會反響巨大,為新時期文藝思想解放開了路。羅蓀笫三個大貢獻是晚年受巴金先生的委託和中國作協的安排,負責籌建中國現代文學館。1982年,古稀之年的羅蓀為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備工作殫精竭慮,奔走呼籲,親自踏察館址,徵集資料,傾注了一位領導者更是一位作家對文學的情感,奉獻了他最後的光與熱。他和巴金先生作為第一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名譽館長當之無愧。
評價羅蓀,譽之為中國文藝發展的建設者和見證人,有史實為證,但這並非是全部。實際上,羅蓀對中國新文學事業有過不小的貢獻,目前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對這位當年的東北作家、激情抗戰的文藝戰士,研究還遠遠不夠,這不能不說是缺憾。從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羅蓀創作了大量與抗戰相關的小說、詩歌、散文與雜文,研究這些作品,對於豐富東北作家群創作面貌,認識作為文藝評論家的羅蓀對抗戰文藝的貢獻都是非常有意義的探討。
羅蓀與現代文學的深刻淵源始於哈爾濱。
1928年,16歲的羅蓀為了減輕家裡負擔,輟學考入哈爾濱郵政局。他始終保持對文學的熱烈嚮往,一邊工作一邊開始用“羅蓀”等多個筆名給《國際協報》和《晨光報》投稿,第一首詩作由《晨光報》副刊《江邊》刊出,第一篇小說《新墳》由《國際協報》副刊《綠野》連載。以後又發表了長篇小說《暗》。同時,他與幾位文學同道組織了“寒光”劇社,表演話劇。後來由他提議創辦了一份《國際協報》的文學副刊《蓓蕾》周刊,並由他擔任編輯,由是表現出羅蓀的文學和組織才能。他創辦的“蓓蕾”文學社團結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學青年,也使羅蓀的文學才華與日進展,他像一隻春燕,在哈爾濱的寒冬利用文學的陽光播撒早春的氣息。直到“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國主義的魔爪伸進哈爾濱,《國際協報》處境艱難,1931年末,《蓓蕾》周刊被迫停刊。據當年共同創辦“蓓蕾社”的台灣著名作家陳紀瀅著文說:由於《國際協報》是當年東北最大的一家報紙,羅蓀作為一名少年文學愛好者,主編該報《蓓蕾》副刊,有聲有色,日漸興旺,它的影響已超越東北範圍,受到平、津、滬等地文壇的重視,並把當時東北地區的作家聚集到了一起,把他們作品介紹到關內,為後來東北作家群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少年羅蓀是拾薪之人,為東北地方文藝的發展作出了他的貢獻。並由此結下了與中國新文學發展的不解之緣。他日後以筆為槍,寫下的大量戰鬥檄文都和在哈爾濱這段時期的創作與編輯生活密切相關,在他的一生中,哈爾濱是一生難解的故鄉情緣,尤其是鐵蹄下東北人民的呼與吸之痛更與他的生命休戚相關。特別是後來全面抗戰爆發後那個激情的文藝評論家,時刻把抗戰作為人生要義。與梁實秋的“文藝與抗戰無關論”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當年居住哈爾濱生成的切實的喪國之痛與強烈的愛國情懷,都成為羅蓀先生積極推動抗戰文學的直接思想動因。
1932年9月,羅蓀與夫人周玉屏以蜜月旅行為由途徑大連到了上海,從此告別了家鄉哈爾濱。人生掀開了新的一頁,也正式開始了一個“左翼”文藝評論家的文學生涯。自此他的生命將與新中國的文藝事業息息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後人往往看見的是一本本文集積累的文學成就,但是作家本人的精神成長軌跡卻隱於文字背後,有待進一步發現開掘,我們今天看到的思想之樹結出的一粒粒飽滿的種子,都是經過人生風雨的洗禮錘鍊後破土而出熠熠發光的。離開哈爾濱後,羅蓀的創作興趣從最初的詩歌、小說轉移到散文和雜文上了,這與他開始受到魯迅先生的影響有直接關係。1934年,羅蓀曾隨叔父孔敏到魯迅家中拜訪過魯迅先生和許廣平,並於1935年5月22日從武漢給魯迅寫信,邀請他為《大光報》副刊《紫線》寫稿,羅蓀時為該副刊編輯。能主動向魯迅先生約稿表現出羅蓀的文學誌向和他對魯迅先生的景仰程度,實際上羅蓀早在哈爾濱時就經常讀魯迅作品及其編的雜誌,汲取精神給養,從一踏上文學之路就奠定了堅實的“為人生”的現實主義精神立場。這也決定了在日後多次複雜的文藝思想爭論中,羅蓀能夠保持鮮明的“左翼”立場和批判激情。羅蓀對魯迅先生的景仰之情還表現在對魯迅精神的深刻理解上,特別是在魯迅先生去世之後,面對許多宿敵對魯迅的謾罵與詆毀,羅蓀撰文挺身捍衛魯迅。他在1940年紀念魯迅誕辰六十周年的文章《自覺的聲音》中寫道:
魯迅先生誕生的六十年,恰恰正是中國在滅亡與新生的路上掙扎與彷徨、鬥爭與妥協的最激烈的戰鬥的時代。他,代表著中國的“自覺的聲音”,在這無聲的古老潭穴里,投下了一顆猛烈的爆炸彈。這聲音並不只是激起一些復歸於平靜的浪花,它不但搗破著舊的巢穴,暴露了鬼魅的行徑,揭發了怯懦、卑劣、無恥、殘酷的劊子手和奴才們的面目,而且用了自己的生命和血來拯救和洗清那些“生長在劊子手主義和奴才主義環境裡的孩子們”。
羅蓀堅定地指出魯迅代表了中國“自覺的聲音”,也正是有這樣的“聲音”的存在與吶喊,才能拯救被劊子手和奴性主義麻痹的國民靈魂。這正是魯迅精神的實質和思想根源。有了這樣明確的警醒的認識,才能真正繼承魯迅的戰鬥精神並身體力行地為繁榮雜文創作作出自己的貢獻。唯其如此,八年抗戰期間,一位奮筆疾書戰鬥的文藝家羅蓀才能給時代留下了鏗鏘有力的回音。他努力讓自己的文字化作“中國的聲音”。
風雲激盪的20世紀30年代,羅蓀同那個時代的許多人一樣,注定在大浪淘沙的歷史轉折中不時調整自己人生的航程。大時代的光與影與個人命運疊合映證。1938年在漢口舉行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成立大會上,活躍著羅蓀身影,曾經有過亡國之痛的他對文協宗旨“民族的命運也將是文藝的命運”、“抗敵救國是我們的旗號”有著深刻的體會,也是他人生鮮明的精神立場和價值所在。此時,如果有阻礙抗戰的言與行,我們相信,羅蓀一定會像魯迅先生痛打落水狗那樣發揚頑強的戰鬥精神,表達一個正直中國人的良知。所以,今天的我們同樣能夠理解羅蓀先生當年與梁實秋“文藝與抗戰無關論”論戰的激情。因為在羅蓀的思想里,真的是認為“民族的命運也將是文藝的命運”,此外,別無選擇。
思想的鬥爭從來都是尖銳的戰爭,帶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但是大敵當前,山河破碎,救亡是當務之急。1938年,這箇中華民族嚴峻沉重的年代,對於黨派、知識分子、個人來說,真正到了歷史抉擇之際,我們今天看到當時國共兩黨聯合抗戰的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了,在“左聯”解散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也成立了。這真是一個同仇敵愾民族生死攸關的歷史大轉折。但是轉折是複雜的,多種黨派、多種勢力、多種主義話語和個人價值偏好使得大時代語境十分嘈雜,表面上合作抗日,但是各種話語對抗交鋒衝突不斷,而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衍生積澱的文藝界的鬥爭,則成為進入全面抗戰後表面統一背後話語紛爭的根苗。各種宗派情緒與消極思想並非“統一戰線”就能統一,而是借用各種歷史時機有所表現。梁實秋的“文藝與抗戰無關論”就是代表。1938年12月1日。《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梁實秋,在當天《中央日報》的《平明》副刊上發表《編者的話》,其中有一段代表性文字:
現在抗戰高於一切,所有人一下筆就離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為不同。與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至於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沒有益處的。
反對“抗戰八股”似乎是占據了話語先機,但真實意圖並非那么簡單。在抗戰形勢最為嚴峻的時刻和抗戰文學遠未深入的情況下,以反對“抗戰八股”為藉口,提出文藝可以“與抗戰無關”的主張,特別是還公然嘲諷堅持抗戰為宗旨的文藝界統一戰線——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冷嘲熱諷地叫囂:“所謂‘文壇’,我根本不知其坐落何處,至於‘文壇’上誰是盟主,誰是大將,我更是茫然。”梁實秋所說“文壇”,指的正是文協。對抗戰文藝統一組織機構和抗戰主張極盡挖苦詆毀之能事,其用心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梁實秋身為國民黨《中央日報》副刊主編,其言論表明了國民黨戰略轉變的動向,這種對尚在普及階段的抗戰文藝的排斥心理實際上體現了取消抗戰文藝的真實動機。
第一個對梁實秋《編者的話》快速做出反應並提出質疑的就是青年評論家羅蓀。東北作家的抗戰激情和他“為人生”的現實主義戰鬥精神,使他能夠及時準確地對“文藝與抗戰無關論”這一消極抗戰的言論作出判斷。他寫出了題為《“與抗戰無關”》和《再論“與抗戰無關”》兩篇雜文,相繼發表在重慶《大公報》上。針對梁實秋的“文藝與抗戰無關論”論調,羅蓀嚴正地指出:
這次戰爭已然成為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戰爭所波及到的地方,已不止限於通都大邑,它已擴大到達於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影響之廣,可以說是史無前例。在這種情況下,想令人緊閉了眼睛,裝作看不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今日的中國,要使一個作家既忠實於真實,又要找尋“與抗戰無關”的材料,依我拙笨的想法也實在並不容易……在今日的中國,想找“與抗戰無關”的材料,不過是某些人們心理上的“避難所”的一種幻覺罷了! 民族危亡,羅蓀以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認識到文藝與抗戰的重大關係。想起東北家鄉人民的水深火熱,侵略者的暴虐行徑,羅蓀義正詞嚴落地有聲地大聲疾呼:“今日的中國是沒有與抗戰無關的地方的!”他認為:“作為時代號角,反映現實的文學藝術,更其不能例外的要為祖國的抗戰服務。然而梁實秋抹殺了今日抗戰的偉大力量的影響,抹殺了今日中國的抗戰這個真實的存在,抹殺了今日全國愛國文藝界在共同努力的一個目標:抗戰的文藝。”羅蓀的文章發表後,引起熱烈回響,一場文藝與抗戰關係以及要不要堅持抗戰的爭論,大範圍擴展開來。著名作家郭沫若、茅盾、周揚、老舍、夏衍、田漢等通過報紙、刊物、專著、演講、座談等形式,紛紛對“文藝與抗戰無關論”提出批評。人們不約而同地嚴詞責問:梁實秋不勸人把抗戰文章寫好,反而勸人寫點不抗戰也好的文章,是所為何來?是不是做了幫凶?其結果,《中央日報》面對群情鼎沸的局面,不得不拋出替罪羊——1939年4月梁實秋被迫辭職離任。然而爭論並未停歇,事關民族大義,文藝與抗戰關係問題的爭論,早已匯入了政治上“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的抗日救國的時代呼聲中,這也是民族的正義之聲。
何為大是大非?羅蓀與同時代人一生中都面臨著是與非的考驗與抉擇,這是一代帶有悲劇意味的知識分子,從“五四”到“抗戰”再到“反右”、“文革”,真是人生百年風雲變幻。作為個人生命史,歷史不可回溯,但人生關鍵抉擇真的就是那么幾步。在與梁實秋的“文藝與抗戰無關論”針鋒相對反擊時,歷史可以證明:羅蓀對了。這不是宗派相爭,更不是宿怨報復,這是民族大義大是大非的問題,這場爭論之所以那么長久,其意義那么深遠,其中就隱含著不辯自明的真理:外虜當前,文藝必須為抗日戰爭這場正義之戰服務。抗日烽火已燃遍祖國大江南北,正義的人們心中響徹的正是羅蓀那句穿越歷史的鏗鏘話語——今日的中國是沒有與抗戰無關的地方的!
以文藝為抗戰服務,是青年羅蓀人生的信仰。八年抗戰期間,他曾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常務理事,出版部副主任和會刊《抗戰文藝》編委,《文學月報》主編,同當時不抵抗主義進行了堅決鬥爭,為文藝更好地為抗戰服務作出了貢獻。這期間羅蓀創作了大量的雜文,發揚魯迅先生的戰鬥精神,同一切消極抗戰言論論戰,其目的是要在血與火的洗禮中煥發中華民族的新精神,把抗戰進行到底。即使是抗戰勝利了,他依然警惕著那些發動內戰分裂東北的陰謀,在《東北人民需要什麼》一文中,大聲呼籲:經過十四年法西斯統治終於獲得勝利的東北人民不再需要武力戰爭,不再需要法西斯統治,更不需要官僚政治以及任何形式的掠奪。而真正需要的是一個偉大的希望——要有一個和平、民主、統一、團結的新東北,要有自由、和平、幸福的生活。可以想像,羅蓀對於東北新生活的構想,是一個堅守人道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對未來烏托邦社會情景的構想,對家鄉的深情,對形勢清醒的認知。這些都表現出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價值立場,這時的羅蓀作為文化戰士,在嚴峻的現實面前表達了思想的力量。
羅蓀還是一位優秀的編輯家,不論是《蓓蕾》,還是《文學月報》等刊物,都辦得有聲有色,特別是《文學月報》連續出版了兩年,計3卷15期,每期發行量都達到萬份,為抗戰時期少有。這一刊物在重慶和大後方曾有廣泛影響被譽為“文藝雜誌的巨星”。這些刊物扶植了新人,推動了文藝發展,在這一點上,羅蓀功不可沒。作家碧野曾在1992年撰文《播種的人》回憶了他與《文學月報》的故事,充滿深情地敘述了他與羅蓀交往的細節,當年真誠友愛的主編羅蓀推薦了《燈籠哨》和《烏蘭不浪的夜祭》,大大鼓舞了青年作家碧野,回憶難忘的往事,他在文章中熱贊羅蓀是中國新文學的播種人。多么恰切的評價,沒有羅蓀這樣辛勤耕耘的優秀編輯家,就沒有中國新文學繁茂的文學之林。
羅蓀,這位東北作家,優秀的評論家和編輯家,其身影已漸漸隱於歷史的地平線之中,但是我們依然從那些鮮活的文字以及朋友們親切的回憶中,看見了這位為新中國文藝播種的人,他是朋友眼裡的好人,更是一位激情的文藝戰士,正直的文人。
斯人已去,遺風永存!
郭力
2011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