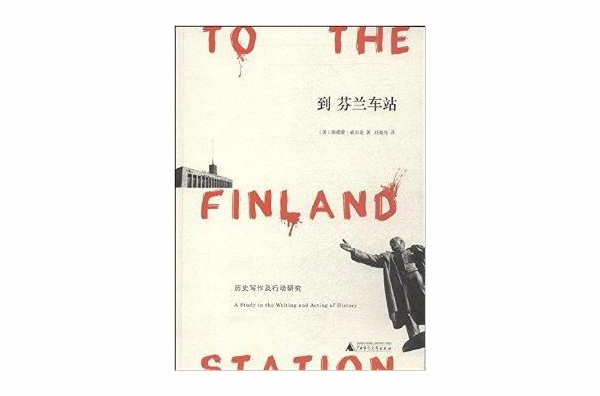《到芬蘭車站:歷史寫作及行動研究》講述了義大利邊城那不勒斯,窮學者維柯,正伏案撰寫一部引發史學新思維的巨著;革命之都巴黎,密謀顛覆拿破崙皇朝的革命家巴貝夫,慷慨陳詞臨刑前的自白;倫敦,流亡者的新故鄉,革命傳單與當票陪伴著馬克思,走完人生最後一程;聖彼得堡紅旗揮舞,列寧與托洛茨基口號高亢,宣告羅曼諾夫王朝的覆亡……跨越兩百年的時空場景,《到芬蘭車站:歷史寫作及行動研究》在威爾遜的筆下一幕幕鋪陳,巨細靡遺。
基本介紹
- 外文名:Finland: A Study in the Writing and Acting of History
- 書名:到芬蘭車站:歷史寫作及行動研究
- 作者:埃德蒙·威爾遜 (Edmund Wilson)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4年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9535460
- 譯者:劉森堯
-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頁數:455頁
- 開本:16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埃德蒙·威爾遜(1895—1972)美國二十世紀廣受尊崇的文學(文化)批評家和社會評論家。曾任《名利場》、《新共和》副主編,並為《紐約客》、《紐約書評》等撰稿。威爾遜是位多產作家,取材廣泛,既有以美學、社會和政治為主題的作品,也有詩歌、劇本、遊記和歷史著作。被譽為“文學界的自由人”,“知識上的紈絝子”, “美國最後一個文學通才”。
劉森堯,台灣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愛爾蘭大學愛爾蘭文學碩士。著有《電影生活》、《導演與電影》,譯有《電影藝術面面觀》、《電影表演與藝術》、《我的最後一口氣:布努艾爾自傳》、《魔燈:伯格曼自傳》、《電影語言:電影符號學導論》、《魏瑪文化》、《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等。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馬歇爾·伯曼
他(威爾遜)是詹森、聖勃夫、別林斯基、馬修·阿諾德傳統的最後一位重要評論家。他的目標和實踐是為了在一個更大的社會框架中考察文學作品——這個框架包含著對作者人格、目標、社會和個人根源,周圍道德、知識和政治環境,以及作者眼界的性質等方面的專注、犀利、直截了當、發人深思的觀點——也是為了將作者、作品及其複雜的背景呈現為一個錯綜的整體。……對他來說,藝術散發著光芒,但不僅是通過它自身的光線。
——以賽亞·伯林
威爾遜拿手的批評性敘事,變化多端的演奏方式,在書中發揮無遺。他複述人物的文章和思想,加以概念辨析和批判,又不時徵引逸聞與趣事,隨處穿插細節和場景,節奏感控制得恰到好處:高潮來了,又掐斷了,織人另一波起伏中。
《到芬蘭車站》的魔力在於,威爾遜並不為他的歷史命題所裹挾而濫情,他與筆下的人物在神光離合之間,時而投合其中,時而間離其外,對人物既同情又了解,從不藏起他批判的鋒芒。雄渾,是的,但是冷峻。
——江弱水
名人推薦
——馬歇爾·伯曼
他(威爾遜)是詹森、聖勃夫、別林斯基、馬修·阿諾德傳統的最後一位重要評論家。他的目標和實踐是為了,在一個更大的社會框架中考察文學作品——這個框架包含著對作者人格、目標、社會和個人根源,周圍道德、知識和政治環境,以及作者眼界的性質等方面的專注、犀利、直截了當、發人深思的觀點——也是為了將作者、作品及其複雜的背景呈現為一個錯綜的整體。……對他來說,藝術散發著光芒,但不僅是通過它自身的光線。
——以賽亞·伯林
威爾遜拿手的批評性敘事,變化多端的演奏方式,在書中發揮無遺。他複述人物的文章和思想,加以概念辨析和批判,又不時徵引逸聞與趣事,隨處穿插細節和場景,節奏感控制得恰到好處:高潮來了,又掐斷了,織入另一波起伏中。
《到芬蘭車站》的魔力在於,威爾遜並不為他的歷史命題所裹挾而濫情,他與筆下的人物在神光離合之間,時而投合其中,時而間離其外,對人物既同情又了解,從不藏起他批判的鋒芒。雄渾,是的,但是冷峻。
——江弱水
圖書目錄
致謝
1971年作者序
第一部
第一章米什萊發現了維柯
第二章米什萊與中世紀
第三章米什萊與大革命
第四章米什萊要活在歷史中
第五章米什萊夾在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
第六章大革命傳統的式微:勒南
第七章大革命傳統的式微:丹納
第八章大革命傳統的式微:法朗士
第二部
第九章社會主義的起源:巴貝夫的答辯書
第十章社會主義的起源:聖西門的階層制度
第十一章社會主義的起源:傅利葉和歐文的理想社區
第十二章社會主義的起源:安凡丹與美國社會主義運動
第十三章馬克思:普羅米修斯與路西法
第十四章馬克思決心要改變世界
第十五章恩格斯:來自曼徹斯特的年輕人
第十六章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合作
第十七章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磨劍
第十八章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創造歷史
第十九章辯證法的神話
第二十章馬克思和恩格斯回去寫歷史
第二十一章歷史行動者:拉薩爾
第二十二章歷史行動者:巴枯寧
第二十三章馬克思:商品的詩人與無產階級的主宰者
第二十四章馬克思死在書桌上
第三部
第二十五章列寧:烏里揚諾夫兄弟們
第二十六章列寧:革命大導師
第二十七章托洛茨基:年輕的鷹
第二十八章托洛茨基要歷史認同
第二十九章列寧向歷史認同
第三十章列寧抵達芬蘭車站
索引
序言
我們經常易於將其他國家的社會動亂加以理想化,英國人像華茲華斯和福克斯等人就曾經把法國大革命加以美化,法國人拉法耶特也曾美化了我們美國的獨立革命。俄國距離西方很遠,許多美國的社會主義和自由派分子即認為俄國的革命將掃除一切舊的壓迫現象,廢棄商業文明,同時將建立一個如托洛茨基所說的,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合乎人性的社會。我們這種想法實在太過於天真,我們沒看出來,新的俄國必然還是包含了許多舊的俄國:檢查制度、秘密警察、顢頇醜陋的官僚嘴臉,以及殘酷專制的極權作風等等。本書主要想探討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如何形成,一個基本的“突破”如何發生,以及現階段人類歷史如何因而產生重大變化。我無意推斷現今的蘇聯政府是否會成為人類史上最專制的政權,以及史達林是否為俄國有史以來最為殘酷無情的沙皇。本書應該可以看成是一些革命家自認為在努力建造一個“更好的世界”的忠實記錄。我在撰寫過程中少不了一些個人的偏見,也許應該趁此加以修正,至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是非功過——不管暗示了什麼——我則不願加以評斷。
曾經有人批評我對法國社會主義傳統語焉不詳,比如有人問我:喬雷斯和左拉在哪裡?我的答覆是:他們沒有討論的必要。至於法朗士,我覺得他沒有得到該有的讚賞,撰寫本書之時,我即已不贊同小皮埃爾和柯納爾神父對他的看法,現在更加不贊同。我最近重讀法朗士的《當代歷史》一書合成一冊的新版本,我覺得比初讀時更加喜歡,書中所描寫的十九世紀法國的政治和社會,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政治和社會的真實寫照,而《饑渴的眾神》這本小說中,透過一位不妥協的政治狂熱分子所發出的警告,正好吻合了俄國革命前大屠殺事件以來的一切現象。總之,我對法國大革命之後的作家並未適當加以對待,但是從他們身上我倒是學到不少東西。
至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我已經沒什麼話可以再補充,一位叫作大衛·麥克雷倫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最近出版了一本他稱之為馬克思的《大綱》的英譯本選集,這本書的原稿有一千頁之多,寫於1857年的十月到1858年的三月之間,至目前為止只出現兩個版本,一個是1939年的俄文本,另一個是1953年的德文本。麥克雷倫先生認為這本書極為重要,可以說是“馬克思的思想重鎮所在”,並且宣稱“任何關於馬克思思想後續發展的研究,如果忽略這本書,必將注定失敗”。其實,這本手稿只是馬克思企圖勾勒出他整個體系的大綱而已,根據麥克雷倫先生的說法,由於這本手稿的出現,許多學者可以更加確定“馬克思是個人文主義者,是個存在主義者,甚至是個‘精神的存在主義者’[真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然而,《大綱》畢竟從未真正出版,可以說是馬克思不願意寫完他的作品的另一典型例子,我認為他提出的問題一向過於龐大,以致根本無法加以解決。(《大綱》主要的重點似乎落在經濟問題上面,馬克思如同往常一直想仿效荷馬史詩的寫法——把自己寫的東西看成是一種原始文化的產物——心理學方面的問題,因而懸而未決。)因此,《資本論》的第一冊,這是馬克思唯一自己生前出版的部分,在今天看來多少像是某種騙局,他在勞動價值上面大作文章,帶動無產階級和資本家進行無情的階級鬥爭,至於中間人所創造的價值則隻字不提,原稿在此即告中斷。然而,《資本論》第一冊書中的煽動性憤怒情緒卻在該書出版之後引發了許多的革命行動。坦白說,如果以馬克思早期未發表的文字為基礎去研究他的思想發展,這更加枯燥乏味而徒勞無功,終究只能淪於學院式獨立研究的考據行為罷了。馬克思期望人們閱讀的那些部分,人們已經讀了,並且還感受到了他隱含其中的那些情感。
也有人批評我在本書中對列寧形象的描繪過於美好,關於這方面的批評,我必須承認有道理。當初撰寫此書時,只能搞到經蘇聯政府批准的材料,那是暗中安排認可的產物,舍此別無渠道。托洛茨基寫過許多關於列寧生平的文字,他也認為蘇聯官方的管制行為甚至都使得列寧家人所編撰的家庭紀事也變得不十分可靠,而托洛茨基在他自己所寫的《我的生活》一書中對列寧的吹捧筆調,如我所說,簡直就像柏拉圖在寫蘇格拉底。直到最近我們才真正有機會看到一些非經蘇聯官方管制的資料、某些當事人所寫的對於列寧的反面印象,如斯特盧威和瓦倫迪諾夫。我們得到的另一個印象是,列寧只對不和他作對的人才會流露關注和溫和的態度,至於對其他人,他的態度則是粗魯而惡劣。斯特盧威和瓦倫迪諾夫這兩個人曾經都是列寧得意的助手,但最後都對他背叛唾棄,我在此引用一段斯特盧威所寫關於列寧的文字(引自理查·派普斯所撰《斯特盧威——左派的自由分子,1870-1905》一書):
我對列寧的印象一開始就不好,這種印象延續了一輩子。但是他令人不愉快的印象並非來自他的唐突態度,而是比一般唐突態度更甚,是一種嘲弄揶揄的態度,一部分是做作出來,另一部分則是與生俱來,發自他最深層自我的一面,他對待敵手一向即持此種態度。他一開始即把我當敵手看待,即使我跟他最親近的時候也是如此,他會如此並非源於理性,而是直覺在作祟,也就是一般獵人所說的“嗅覺”。後來我開始比較接近普列漢諾夫,他和人接觸的方式也是擺出一副唐突而幾近於嘲弄揶揄的姿態,和列寧比較起來,他倒像是個貴族。他們這兩個人對待人的態度,用一句不容易翻譯的法文形容詞講,就是“粗暴跋扈”(cassant),但是在列寧身上,他的那種粗暴跋扈方式,則接近於令人無法忍受的暴民風格,同時也乏味而冷酷。
許多人和我一樣對列寧有相同的印象,我隨便提兩個人,很不相同的兩個人:薇拉·扎蘇利奇和米歇爾·圖乾一巴拉諾夫斯基。薇拉·扎蘇利奇是我這輩子見過最聰明敏銳的女人,她就很討厭列寧,她甚至討厭列寧的長相,他們在政治上的爭執並非只是理論或策略上觀點的歧異,而且主要也是由於各人在氣質上的差距。
多年來我一直和米歇爾·圖乾一巴拉諾夫斯基走得很近,他常常告訴我他對列寧有多么討厭,他對列寧的嫌惡多少出於一種純真的本能,有人認為他的這種傾向顯得愚蠢。他以前和列寧的哥哥亞歷山大很熟,而且也很要好(亞歷山大後來因參與謀刺沙皇而被處決)……他經常以困惑而接近嫌惡的口吻提到兩個兄弟竟然會那么不同,哥哥有一種純潔而堅定的道德感,而且待人溫和而有分寸,即使是對待陌生人或敵人也是如此,弟弟則否,他老是擺出一副唐突而殘酷的姿態。
的確,列寧對待部屬的態度始終充滿冷淡、輕蔑及殘酷,在我看來,列寧身上這些反常的怪異性格正好也是他從事政治活動的本錢,他眼睛所看到的,除了一心一意要完成的目標之外,別無其他,他藉此與其他一些政治圈的朋友形成一個權力的核心,而他唐突和殘酷的本性——從我們開始交往以來,此一本性即顯露無遺——和他對權力的酷愛巧妙而不自覺地緊緊結合在一起。我們實在很難看出,是他對權力的酷愛促使他不斷努力在追尋他的理想目標,還是適巧相反,他透過對理想目標的追求,以便達成掌握權力的熱望。
瓦倫迪諾夫的見證(在他所撰《與列寧的會面》一書中)與上面所述可說大同小異:“沒有人能夠像他那樣,對自己所設定的計畫那么熱心,性格那么堅定,能夠叫別人屈服於他的意志之下,而事實上他這個人給人的第一印象竟是那么唐突粗魯,實在毫無魅力可言。即使像普列漢諾夫或馬爾托夫①或任何其他人都沒有列寧那種本事,可以對他人產生催眠式的影響力,然後加以掌握引導。他們會緊緊跟隨他,好像跟隨一位獨一無二且無可置疑的領導者一般。的確,列寧的出現確是一種少有的現象——特別是在俄國——他那鋼鐵般的意志,驚人的毅力,不可思議的行動能力,所有這些都賦予他一種牢不可破的自信心……”後來瓦倫迪諾夫和列寧鬧翻,他們之間有如下的對話,瓦倫迪諾夫說:“我不會忘記你竟然那么快把我列入你最痛恨的敵人行列,只不過我在哲學領域中和你意見不同而已,你競對我橫加謾罵攻訐。”列寧回答道:“你說得對,在這一點上面你說得很對,所有脫離馬克思主義的人都是我的敵人,我不願和這種人來往,我不要和他們坐在一起………‘列寧不願意和我握手,說完話轉身就走,我從此脫離布爾什維克的組織。”
斯隆也提到他加入共產黨時對列寧的印象:“每次他一走人大廳,整個氣氛就變了,變得很生動有力。他會把一股熱情感染給別人,如同在聖彼得堡時,大家圍在塞迪亞宮,他散發出一股熱烈的光芒,籠罩著大會堂的四周。可是如果和他面對面交談或就近觀察他——看他剪報、聽他下輕蔑的判斷、他分析事情的能力、下決定的果斷聲調——你絕對感受不到任何神秘的氣氛。我記得1921年前往莫斯科時,我偶然聽到他一些簡潔有力的評斷語氣,當時感覺身體好像受到重擊一般。”
吳爾夫有機會讀到高爾基的一些重要文章,終於能夠指出蘇聯官方所刊行的高爾基的《與列寧在一起的日子》一書充滿了謬誤和歪曲,甚至根本就捏造了高爾基和列寧之間的關係。他們兩人之間的基本差異在於列寧只想到階級,而高爾基想到的則是人的問題,他一向把宗教看得很嚴肅——雖然他並不相信基督教——常常談到“尋找上帝”的問題,列寧對這個則表示很生氣:“任何宗教的觀念,任何牽涉到小神祗的觀念,即使只是一點點,都是一種不可寬恕的罪惡。”高爾基自認有責任保護知識分子——藝術家、作家及科學家——就要求列寧給他一個可以為他們做事情的職位,他不斷跟列寧請願,後來列寧變得很不耐煩,就跟他說,這種事情和革命事業相較起來根本就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是微不足道的。不過,列寧倒不像史達林那樣趕盡殺絕,他有仁慈的一面,比如他就開釋了許多“有罪的人士”。二十年代初期,列寧要處決一批社會革命黨人,高爾基出面斡旋,甚至以絕交相要脅,後來列寧讓了步,把這些人暫時關在監獄,但不久史達林繼位之後,還是把這些人“清除”掉了。高爾基曾創辦一份雜誌,叫作《對話》,其目的主要是拉攏蘇聯和外面世界的關係,但這份雜誌卻不準在蘇聯境內發行,而且不刊登俄國人寫的文章。高爾基就跟列寧警告不要太過於專制,因為革命的目的即掃除專制,但列寧對這個話聽不進去。最後,高爾基在不同的時期寫了三個對列寧的印象手記,其中包括了不少批評的語調,最後一個也是最著名的一個即是《與列寧在一起的日子》,但在史達林主政時期,就已被動過了手腳。原來版本的結論是這樣:“一個人所作所為如果是正確而誠實的,那么他最終必將勝利,否則,只有注定失敗一途。”這個結論改為“列寧死了,但是他思想和意志的繼承者還活著,他們將繼續他未完成的工作,這在人類史上將是一樁空前的勝利”。高爾基所有有關猶太人的看法全被蘇聯官方刪除,下面有關列寧的一段談話同樣被刪除:
我常常和列寧談到革命策略和生活方式殘酷的一面。
“你期待怎么樣呢?”他困惑而生氣地反問,“在這種空前的惡劣鬥爭中,你還想談什麼人性嗎?”
“在一場戰鬥中,你如何衡量必要和不必要的攻擊?”在一次熱烈爭論之後他這樣問我。這個問題很簡單,我只能以詩般的曖昧方式回答:“我認為沒有其他的答案。”[這是什麼意思?]……
有一次我問他:“你會為人民感到難過嗎?我自己是會的。”
“我只為聰明的人感到難過,我們之間聰明的人很少。我們這個民族大多數時候聰明又懶散。聰明的俄國人大都是猶太人,或至少有猶太血統。”
從上面這段對話中我們看得出來,列寧對易於妥協和愛爭論的俄國人顯得很不耐煩,因此他會為此而憤怒,我們看不到我在書中所描繪的他仁慈的一面,這並不足為奇。
有兩段個人的插曲我在書中未曾提及(因為我當時並不知道),也許跟革命運動無關,不過似乎可以在此順便一提。我從《艾琳娜.馬克思:一個社會主義悲劇》這本書知道,馬克思和他的管家琳蘅生了一個兒子,這位管家是當初馬克思和燕妮結婚時,燕妮的母親讓她陪嫁過來的嫁妝,她一輩子忠心耿耿陪著馬克思一家人,幾乎不支領什麼酬勞。馬克思和琳蘅生的這個私生子叫亨利。弗雷德里克·德穆特,從母姓,出生於1851年六月,當時正是馬克思一家人落難英國倫敦最為窮困潦倒的時候,一家人擠在蘇荷區一個只有兩個房間的小公寓裡。這位私生子後來好像過繼給一個勞工階級的家庭撫養,從此不知下落,但1880年代卻再度出現,不久就拋下妻子兒女移民澳洲。馬克思的女兒艾琳娜一直以為弗雷德里克是恩格斯的兒子,她對父親的形象一向認定為理想完美,後來知道事實真相時自然十分吃驚,但她與這位同父異母弟弟依然保持非常友善的關係。在這方面列寧的形象似乎比馬克思更為人性一些,他有一位極為親密的女性朋友,甚至可以說他極為愛她。這位女性朋友名叫伊奈莎,母親是蘇格蘭人,父親是一位法國的歌唱家,她從小被祖母帶去俄國,長大後在一個法裔的俄國工業家家中當家庭教師,十八歲時和工業家的兒子結婚。不久之後她成為布爾什維克革命者,成為列寧的忠實信徒,她帶著兩個最小的孩子離開了丈夫,但仍繼續靠丈夫接濟過活,直到她丈夫的財產被布爾什維克革命沒收充公。她成為列寧的得力助手,為他彈奏貝多芬,陪他出席黨會議,她能流利使用五種語言,對列寧的幫助更是不可限量,因為列寧除了母語之外,只懂得一些簡單的德語而已。一位法國的社會主義者說,他有一次看到列寧“在一家咖啡館裡,用兩隻蒙古的小眼睛,不斷瞪著我們這位法國小姑娘,看個不停”。列寧的元配妻子娜傑日達也常常提到這位女孩,甚至一度還想讓賢,自己退出來,讓列寧把這位女孩娶過來。伊奈莎是少數被列寧直稱“你”而不稱“您”的人之一,可見他們之間親密的程度,他們常有書信往來,1917年,列寧從瑞士回彼得格勒時,伴隨他一起回來的夥伴中,她即是其中一員。她曾經入獄三次,有一次甚至還被流放到外省。根據各方面的記載,她確是一個相當迷人的女性,但根據描述,她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是“營養不良、饑寒交迫……因工作過度而不斷面露疲態,顯然疏於自我照顧所致”。1920年她坐著載貨火車前往高加索,不久即染上傷寒死在那裡。在上述引用吳爾夫的那段文章中,他也曾提到伊奈莎這個人,巴拉巴諾娃曾告訴他說,當列寧聽到伊奈莎的死訊時,幾乎當場崩潰,“我從未見過他那樣子,這似乎比死了一位‘好布爾什維克黨員’或一位好朋友還嚴重。他失去了一位最親密的夥伴,他情不自禁”。巴拉巴諾娃和其他一些人都認定伊奈莎和列寧生有一個女兒,這位女兒後來嫁給一個德國共產黨員,這位德國共產黨員最後卻被史達林“清算”掉了,烏里揚諾夫家認領了這位女孩。巴拉巴諾娃曾在社會主義政治研習會中和伊奈莎共事過,她跟吳爾夫說:“我對伊奈莎不太有好感,她喜歡賣弄學問,從她的穿著(永遠一成不變的樸素裝扮)和思想言行等,你可看出來她是個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分子。她精通多種語言,列寧對此則一竅不通。”列寧重感情,有人不計利害關係願意死心塌地為他奉獻一切,他當然感動。
多伊徹所撰《列寧的童年時代》,未完成的列寧傳記的第一部分,書中對列寧的先祖著墨不少。但是關於烏里揚諾夫這個家族的起源,最多也只能追溯到列寧的祖父那一代,再往上就一無所知了。多伊徹推測列寧的上面幾代祖先可能是農奴,混雜有蒙古人、韃靼人或卡爾梅克人的血統,他的祖父來到阿斯特拉罕一帶,這裡是許多農奴的避難所,列寧自己則說:“我對我的祖父一無所知。”他的祖父當時從事裁縫,很貧困,晚年時環境相對好轉,已經列入低階層的資產階級,但由於出身寒微,始終無法獲得真正的公民身份。到了列寧的父親那一代,由於接受較高的教育,並且終生獻身教育界,終於取得榮譽貴族的頭銜,真正躋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行列。但是列寧自己——雖然母親也算系出名門,他自己也一向自視為學者——卻始終是一副粗俗相。
多伊徹另外撰寫了三大冊的托洛茨基的傳記,對托洛茨基的整個政治生涯描寫得可謂巨細靡遺,比我在本書中大而化之的描寫自然要詳盡得多,不過,我認為我所寫的似乎沒有修訂的必要,托洛茨基早年生涯的部分,多伊徹和我所引用的資料來源大致相同:托洛茨基的自傳以及馬克斯·伊斯特曼所撰的《萊昂·托洛茨基:一位年輕人的畫像》。關於處決沙皇家族這件事情,我後來讀了托洛茨基的《一九三五年流亡日記》,則印證了我一向的看法:列寧不知道而且不同意這件事情,這不是真的(這件慘案在蘇聯官方當局一向列為秘密檔案)。這則日記讓我們了解到,托洛茨基和列寧一樣,對這件事情的態度都是冷血無情:
和斯維德洛夫談話時,我隨口順便問:“喔,是的,沙皇在哪裡?”他回答:“全都解決了,沙皇槍決了。”“他的家人呢?”“他的家人一起解決了。”“全部嗎?”我問,露出明顯訝異的樣子。“全部!”斯維德洛夫答道:“有什麼不對嗎?”他在等待我的反應。我問:“誰下的命令?…‘我們在此一起決定的,伊里奇認為我們不要讓白軍有依靠的目標,特別是在目前這種艱難的處境之下……”我不再追問,覺得事情已經告一段落。的確,這個決定非下不可,剛好可以藉此昭告世界,我們要奮不顧身繼續無情戰鬥下去。沙皇家族的處決不僅可以嚇唬敵人,瓦解他們的士氣,同時可更進一步警惕我們自己,要知道此去只有前進,沒有退路,擺在前面的,不是全面勝利就是毀滅。黨中央的高階層智囊團中可能有人不同意此種做法,但工人大眾和士兵則絕不會有任何疑慮,因為他們絕不會了解和接受任何其他的決定。列寧很了解這個,他懂得如何和民眾一起感覺、一起思考,特別是在此一大的政治轉折點之際……
我來到國外時,有機會讀到關於當時如何槍決以及如何焚化屍體等等的描寫報導,我不知道這中間有多少是真實的成分,有多少是杜撰的成分,我只能說我對槍決如何執行實在絲毫不感興趣(沙皇夫婦和他們的兒女先被用槍加以射擊,然後用刺刀加以刺殺,最後把屍體全丟入一個舊的礦坑),坦白說,我不了解這種好奇心。
關於這個新的版本,我改動的地方非常少,只恢復了原來的附錄部分,然後拿掉《一九四。年的總結》一文(在各類平裝版本中以《三十年代末期的馬克思主義》為名),我把此文收入我另一本選集《光明的彼岸》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