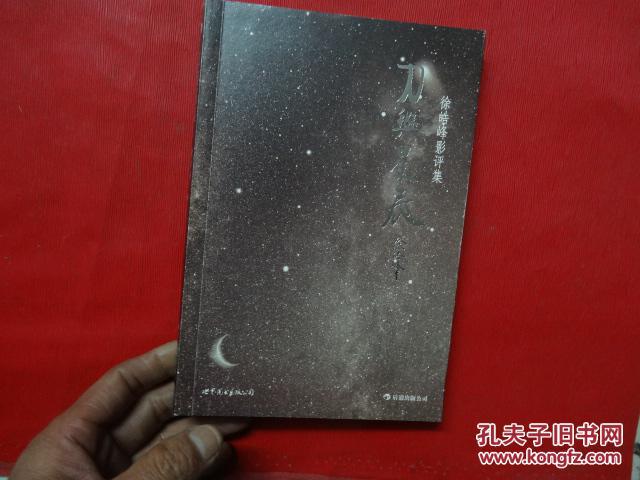《刀與星辰》是世界圖書出版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徐浩峰。本書講述了徐浩峰歷年來的影評合集。
基本介紹
著者簡介,內容簡介,目錄,經典語錄,
著者簡介
徐皓峰,導演,武俠文學作家,被冠以“當前硬派武俠小說第一人”,任教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曾出版紀實文學《逝去的武林》,長篇小說《道士下山》、《大日壇城》等,同時也是王家衛電影《一代宗師》的編劇和武術顧問之一。2011年自編自導並親自擔任武術指導的影片《倭寇的蹤跡》入圍威尼斯電影節、釜山電影節、台灣金馬獎。
內容簡介
目錄
自序 刀與星辰
無道之器——武俠電影與傳統文化
武打片的瓶頸
論金庸作品的惡俗因素
故事的文化依託——評《赤壁》
武打中的世界觀——《投名狀》劇作分析
導演經驗與歷史經驗——恍然《梅蘭芳》
革命情操與時尚神話——評《無極》
藝術的商業偽證——預想《刺秦》
戲劇核心的高貴性——評《三槍拍案驚奇》
大眾娛樂的淫巧奇技——評《十面埋伏》
第五代審美的商業變格——評《英雄》
武打設計的思維方法——評《臥虎藏龍》
一部電影的隱顯技巧——《臥虎藏龍》本事
《座頭市》的中國心——武術觀念在日本劍戟片中的實踐
局面設計與情節——評杜琪峯《放逐》
末世的武道——評黑澤清《神木》
非聖經的敘事——評《建國大業》
網路時代的劍仙片
徐克的分寸感
香港賀歲片民眾心理與後現代文化的雙重範本
文學不能改編處——《色戒》小說與電影
白唐與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白色》
從東西方文化觀《羅生門》與《公民凱恩》
剪輯與敘事
後記 莫聽穿林打葉聲
經典語錄
1.香港有“潑皮賤相的審美”,喜歡混小子,大多數黃飛鴻都是嬉皮笑臉,像六七歲小孩一樣自己嬌慣自己,沉迷在占哥們口頭便宜、占女人手頭便宜的低俗趣味中,猛力扮可愛。
當然他們後來會突然成長,一臉正氣,比武時懂得“手下留情”,被擊倒的對手會感激地喊一聲“黃飛鴻!”——這是一個名號的誕生,一個狠人的確立。不下狠手,就是最高道德了么?
2.武俠片歷史上的大多數影片的性質和現今大片一樣,不是敘事電影,是晚會。晚會沒有價值觀,只有口號,“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和“給您拜年了”性質一樣。一個故事的核心是辨析價值觀,一個晚會的核心是湊場面和湊名角。
3.把別的東西拿來了,就說是對這個東西的創新——這是許多年來我們常犯的錯誤,我們只是圖個新鮮,而博得大名的創造者也只是圖個樂子。我們總是把樂子當成藝術,而在做商業片的時候,又總是把創意當成“不是商業片”,一個人鄭重宣布說“我現在要拍一部商業大片”的時候,往往就是他要拍一部B級片的時候。
4.對於日本的刀劍片,我們往往只做出“注重打鬥前的氛圍渲染”這種外行的分析,而忽略了其觀念。這類影片不是注重打鬥前的氛圍,而是在觀念上對動作有一種珍惜,作一個動作,便是與神與祖師同在。
6.劇作是一個偷換概念的遊戲,能把不合理的變得可以接受,在觀眾眼皮底下玩以假換真的魔術,之所以這個魔術能完成,因為作用在了觀眾的情感上,在客觀知識上不對的,但在觀眾在情感上認同了,這事就成立了。但調情從來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容易的是當嫖客。
中國的商業電影,嫖客心態太重了,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拍商業片以來,至今如此。在消費上占有它,在心理上鄙夷它,這是嫖客對妓女的心態,也是導演們對觀眾的心態。我們是把老百姓當作最粗俗的蠢貨,覺得是幾招就可以擺平的,所以二十年來,我們的商業片都是在向外國偷招,把幾部好萊塢電影中的經典橋段拼湊在一起,覺得就是商業片了,可以取信於投資方,自己也自信了。
7.《赤壁》中的種種怪現象,追根到底,是缺失了精神依託後的焦慮。而日本明治維新後,在積極西化的同時,有著“失根”的焦慮,認為在近代化進程中落後的中國反而保留了古典的所有美好,大正年間出現了“中國情趣”風潮,這類人在谷崎潤一郎的小說《鮫人》中表達的心聲是:“居然沒能生在中國,實在是個無法挽回的不幸。”
當今的我們已經後現代了——我們的依託在哪兒,是朝鮮么?
8.我所受的美育,是要為天下受苦的人代言,在我的青春,對街頭乞丐的興趣,遠遠大於漂亮女生。我們崇拜梵谷,對高更不以為然,因為梵谷苦到割了自己的耳朵,高更雖然窮困之極,但他畢竟在塔希提島上玩土著女人,享受了點生活。
9.凡人神話
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中國》中,有在西四十字路口拍攝的鏡頭,一輛三輪小卡車正經過,車斗中站著個胖乎乎的喜悅青年。這個一閃而過的身影,酷似西四胡同中的某老頭,筆者對他講了此事。他毫不猶豫地說:“那肯定是我。”
他說三十年前的某天,他在郊區農村搞了三麻袋糧食,拉進城中,一路歡天喜地。也許真是他?他在胡同中鄰里關係很差,常有人罵他,但認定自己出現在一部義大利電影中後,他愛占人小便宜的毛病便開始收斂,因為他找到了尊嚴。
對於這個西四老頭,安東尼奧尼的《中國》是他的神話。西方的神話一詞,台灣翻譯成“迷思”,神話是光怪離奇之事,的確令人迷思。但神話不是與我們的生活毫無關係的怪談夢囈,恰恰相反,神話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原始的人類甚至認為,神話是唯一的真實,他們的生活不過是對神話的模擬,或是神話的一層淺淺的投影。
正如西四老頭和電影《中國》的關係,他覺得那部沒看過的電影,比他的生活更真實、重要。這部電影印證了他存在的價值,他甚至顛覆了世界的邏輯,覺得文革的意義就是為了讓他沉浸在搞糧食的興奮中,恰巧與安東尼奧尼在街頭相遇。安東尼奧尼是一個神跡。
10.站到人前有種種方法,最簡單的便是戲劇性,美國的好萊塢在這方面典型地成功。從陳凱歌的《風月》、《霸王別姬》便可以看出他在這方面的努力。也許是不努力,甚或是他對自己這么做感到極不耐煩,因而,這兩部電影重在過程,氣韻豐實,懸疑、多解、蘊情,種種餘味留得很足,但一近高潮,馬上快刀斬亂麻,成了純純然的戲劇衝突,似曾相見,近乎是些俗套,好像種了十年人參,結果長出一根蘿蔔。
11.我們贈送戰爭場面、明星派對、名媛的裸體——都很值錢,而言呢?不要說這電影是大眾娛樂,滿足大眾最庸俗的欲望便稱職了,可惜大眾並沒有你想像的那么庸俗,看我們大眾文學的傳統,三言兩拍充斥著人生警句。嫖一個妓女和看一個故事畢竟不同,人之所以看故事,首先是精神上的不滿足。
故事的本質是反抗生活,活得平庸了,要看西部片,感受到不平等,需要去電影院看一個愛情,活得齷齪,便需要一個王者的故事。
故事是對人生的修正,通過看他人的故事而探究自己,故事的收尾需要講出一個理,此理最好不是語言,是一個人物的反常情緒,或一個視覺意境。但有了這個理,觀眾靈性上才可滿足,否則僅覺看了一場熱鬧,我們抱怨了很久“好看,但沒勁”,勁便是導演的贈言。
12.“睡不服女人(《夜宴》)”、“算不過領導(《黃金甲》)”、“說不過壞人(《英雄》)”、“打不服傻子(《赤壁》)”——這些是大眾的生存常識,但他們並不願意在電影院裡看到,而我們的大片恰恰違反了此點。大眾希望看到略高於常識的智慧,防毒軟體也需要升級的。
13.法國電影的基因是色情,地爾密的一個浴女鏡頭,開啟了法國的靈感。美國電影的基因是暴力,鮑特讓歹徒直對鏡頭,朝觀眾開槍,讓美國導演們都悟了。而中國電影的基因,是“不拿事當事”的自嘲。
基因誕生期的導演演員都表情豐富、眼神靈活,突然間他們就被一幫眼神冷峻、表情嚴肅的人所取代,趙丹辛酸地說:“崔嵬得天獨厚。”和趙丹的機靈鬼形象相比,崔嵬是個五大三粗、說一不二的漢子,高度符合一個共產黨員光明磊落的造型,他導演的片子也如此,但一有機會仍很風趣,將日語胖翻譯拍得可愛無比,把漢奸拍成了加菲貓,甚至小兵張嘎見到漂亮女孩會臉紅,他也拍下來了,那才是多大的孩子呀?
即便為政治服務,中國電影也是不拿事當事,登峰造極的是《地雷戰》。這部紀錄片、教學片、故事片的四不象,玩出了一個“巴巴雷”。在鬼子進村的危險時刻,幾個小孩不埋殺死敵人的地雷,而埋上了一泡屎。粘得日本人滿手屎,中國人就很高興了。在極度緊張、真實的情景下,忽然誕生了一個異想天開的玩笑,真是神來之筆。
此片導演文靜拘謹,但他的內心是一個野人,能擺脫國恨家仇的大眾情緒,把中日戰爭變得好玩好笑。憑著一泡屎,他就是偉大的藝術家。在政治指標極強的時候,也能在瞬間改變整個事件的性質,玩性頗大,和中國導演的自由心靈相比,一般的外國電影就顯得死性。
後來,在創作空間極小的範圍里,導演們送給國人的禮物,是一個個妖艷的女特務、姨太太,在高度純潔的年代,向我們暗示了世界的豐富性。至於國民黨、日本兵,我們很難對他們產生仇恨,他們給了我們一種遊戲快感。
這是一批官氣十足、情趣尚存的導演,但很快這點情趣就蕩然無存了。國人的天性是好玩、不正經,樣板戲是中國最正經的作品,戈達爾見了樣板戲後,說這是世界上最好的電影。我覺得他在胡說八道。
14.他對大眾有時照顧得過多,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台灣的武打片流行李小龍的打法,李翰祥導演的《火燒圓明園》中有一段北京市民反抗八國聯軍的巷斗場面,就也用李小龍式的踢腿,而且有“啪啪”的配音。嚴格說來李小龍的踢腿不是傳統武術,更多是西洋擊劍的步伐與法國式踢腿的結合,這樣的動作出現在一部歷史長片中,就有點超前。
再據服裝考證,那時的北京人是墜襠棉褲,褲襠垂到膝蓋,將腿踢高有點難度。即便不懂武術與服裝,見到一百多年前的北京人個個都跟武打明星般將腿踢得又高又旋,多少有些怪味,如此迎合大眾,破壞了影片的整體感覺。
15.要知“神氣”兩字是習武第一關鍵,而幾乎所有拍太極拳的影視作品,只是拍如何將對手纏住,然後用肩膀或臀拱一下——對於這種公園太極拳,著名搏擊家王薌齋有嚴厲的批評:“如果這種太極拳是張三豐發明的,我會瞧不起張三豐。”可惜被老一輩武術家明確指明是錯誤的東西,卻成為今日電影的時尚,尤其以徐克為代表的新派武俠片則只講究姿態的美觀,離真正的武術相去太遠。
中國是儒家的大本營,卻在腐壞到極點的清末,中國也是一派燦爛的人世。看日本影片中的妓院,總是一片渾渾噩噩,比不了中國的秦淮河,尚有一份風情。侯孝賢《海上花》中的清末妓院,竟有女校的靜氣,史實上妓院也的確被稱為“書齋”。
中國人善於改變事物的性質,在自殺和通姦之外,還有著廣闊的空間,那就是遊戲。《海上花》中沒有情慾床戲,嫖客和妓女只是在酒桌上做遊戲。中國人甚至將吃也做成了遊戲,將菜對應上典故名句,坐在桌前,也像趕廟會猜燈謎一般。中國的遊戲範圍之廣花樣之多,將將抵消儒家的壓力。
中國是把沉重變成遊戲,日本把遊戲也變得沉重。中國的插花、擊劍、弓射、擒拿、圍棋,到了日本都成了需要嚴肅追求的“道”,半分輕鬆不得。雖然技藝得到了巨大提高,但下盤棋,竟拼力到要嘔血而亡,看戲時要有“領掌人”,鼓掌都要專門有一個帶頭人,觀眾不得妄動,這是堵死了生活的餘地,難怪只剩下自殺和通姦。
而中國的武俠,是中國民眾自創的好遊戲。中國的武俠,僅是一種口頭遊戲。考察中國歷史,只有政治在野勢力,如墨子組織、白蓮教、青幫,並無俠客群體,因為沒有任何經濟願意支持一個獨往獨來、不依照團體利益只遵照天理人心的俠客群體。
至於少林寺、武當山等世外體系?中國的寺院有獨立中央財政之外的寺院經濟,一座名寺往往是當地最大的財閥,在徵收地租上並不慈悲,常會引起民變。高僧們也要維護集體利益,並沒有所謂的世外體系。而創立佛教的釋迦牟尼認為結黨必然營私,不讓建立寺院。寺院是中國人的發明,我們喜歡熱鬧。
明清黑社會常會供奉達摩為祖師,自稱為禪宗流緒,筆者懷疑這是寺院蓄養打手的餘緒。當然,公共汽車上至今有給老人讓座的好青年,歷史上不欠心緒來潮的俠客,但過於零星脆弱。
武俠就是願望,民眾口頭創造武俠故事來抒發心中不平,由於講得多了,造成一個俠客遍地的生活幻像,只有最底層的人才信以為真,而對權貴則毫無約束力。君不見,清末時的頂尖高手們多在王府供職,八卦掌和太極拳都是得到了王爺們的支持,方開宗立派。
武俠故事中的天理人心,在現實中蹤跡全無,懲惡揚善只是個無望的假想。因為是公然的謊言,所以難以滿足大眾,於是俠客們的對手,從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變成了內斗,武俠與武俠之間的對壘。
18.我們該如何對待自己的身體?對待自己身體的態度,是有民族性的。
看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二十年金曲回顧,會驚訝地看發現,那些歌星們對自己的身體毫無感覺,毛阿敏以左手持刀、右手拿槍的姿勢唱著“一隻蝴蝶飛進我視窗”,幾乎是樣板戲作派。甚至混血的費翔,肩膀抖得松松垮垮,只是晃晃而已,那是活動活動的體操,而不是表達力度的舞蹈。即便如此麻木,也迷倒了整國人。
19.不想再寫“冬”和“又一春”段落,因為這兩個段落,金基德陷入導演的自我膨脹中,令影片全然崩潰。
“冬”段落,出獄歸來的小和尚已經中年人,由金基德自己扮演。他頭戴毛線帽腿套紅褲子,渾身圓鼓鼓站在岸邊,和冰凍的湖面、破敗的浮廟完全不搭配,穿成這樣的人是沒有權利感慨的,雖然他還是演出了點淒楚的神情——電影的視覺就是如此苛刻。
20.基耶斯洛夫斯基一直聲稱只拍低成本電影,他放棄了高投資,降低了投資方為回收成本、謀求高利潤而對自己的干擾程度,獲得了創作的自由。人生在世,總有為自己求得平等的途徑,只是看你能不能放棄?
22.《羅生門》中的太陽被表現為挑逗、嘲弄、示威的對象。一開始,太陽便是“偷窺”的形象,隨樵夫而移動,沒有西方道德上不動至尊的位置。而強盜與妻子性交時,太陽反覆以略顯詭異的形象出現,它不是旁觀者,而是性交的參與者,它被強暴了。
在妻子的敘述段落,被強盜玷污成為無法抗拒的、接受這一命運的唯一內心支點是“與太陽作對”——這一日本民族意識,所以妻子在交合前,仰頭望日,於是強盜壓在她身上,如壓在太陽上。之後公堂證詞,強盜與武士一致對妻子“做愛時的歡愉”感到驚訝。
《羅生門》公映後,日本出現了無數部“太陽在做愛場面中”的影片,都是賣座片——證明了“文化的差異決定了接受的差異”。
23.《公民凱恩》中的上都是與蒙古帝國首都名稱一致的。在西方人眼中,蒙古上都是個掠奪巨大財富的集中地,凱恩的上都也如此。在解說詞中,在結尾段落收藏展示場面,表明了他的巨大占有欲。《公民凱恩》的廣角鏡頭,並非泛泛地玩“深度空間”、玩人物間的疏離感,而是為了具體地展示凱恩的控制欲、占有欲和自我中心。
廣角鏡頭的特點是縱深中人物行為超速,幾步便可走得很遠。如教師訓練蘇珊時,凱恩偷偷入門,在後景小小一點,但當前景人物發生爭執,凱恩幾步便走到前景,由小猛地變大——這一視覺衝擊力,一下子使他成了畫面中心,場面被他進攻了、控制了、占有了。
一個自我中心越強的人,他的空間占據範圍也越大,普通人對於領袖人物一般是不敢接近的,道理也在這兒。當凱恩與他的監護人發生衝突時,廣角鏡頭下,在縱深處的凱恩身影小小,但高大牆壁下只有他一人,使觀眾產生“他占據了巨大空間”的想法。廣角鏡頭使人物與環境、活物與物質在視覺上產生相互侵占或排斥的感應,從而表現出凱恩的心理優勢。
而當前景人物遮擋,破壞了凱恩輪廓完整時,鏡頭中的凱恩必走幾步避開或另一換一個鏡頭。而當廣角鏡頭強烈表現縱深透視時,如宴會一場,凱恩必站在透視線上,只需一招手,便可觸及最遠處的人。鏡頭中含著攝天花板也是為了擴大凱恩的空間占有率。廣角鏡頭完成了凱恩的性格塑造。
此片中的幾個升降鏡頭,雖然音樂做得緊張,但鏡頭運用仍出入自如,方向性和目的性明確,這反映了西方特有的“空間安全感”。而《羅生門》的曖昧環境,以及不同人物進入樹林、武士在樹林中自殺的鏡頭,表達了東方的“空間恐懼感”。
片頭交待羅生門時,空間便不明確,當結尾嬰兒出現,進一步造成空間的混亂;樵夫進入樹林是一長串失去方向感的鏡頭;強盜在林中奔跑,因並非簡單的過程交待,含有強盜本人的情緒表現,公路和案發地點間的距離變得過於有彈性;而當丈夫自殺前,樹林如人一樣,變得富有思想感情,在這裡運用了俳句擬人化的手法,空間不再作為一個現實空間——處處可見空間恐懼的意識,方向感和目的性喪失,同時將環境人格化。
24. 這點怎么解釋呢?我們先假設多數製片人都是外行,對於外行來說,能打動他們的只有台詞。海明威說過寫小說不難,只要多寫對話,人們就會喜歡。“人們太喜歡對話了”——這是訣竅,也是無奈。
對話是人們最容易理解的東西,而以文字描述畫面,多數人則沒有感覺,克洛德?西蒙的小說被用“印象主義”這個畫派名詞來形容,他詳細地寫出了許多絕妙的畫面,但他的作品被大眾認為讀起來費勁,以致他在得諾貝爾文學獎時說自己是個蹩腳貨。
文學大師的畫面描述都難以贏得大眾,所以一般編劇的畫面描述也很難降服製片人,只好寫出有魅力的廢話和最直白的動作,以便讓製片人理解劇本。編劇生存的第一個技巧,其實是製作贅肉的技巧,正像導演生存的第一技巧是裝出對廉價的價值觀感興趣。
劇本中會有許多的這樣精美的“贅肉”,導演的前期的主要工作就是刪減,如果識別不出,和製片人一樣被這些贅肉感動了,便麻煩了。因為人在讀文字時的心理是尋求意義,而觀影是獲得意境。電影是意境的藝術,而不是意義的藝術。
導演要警惕被製片人盛讚的劇本,編劇製作贅肉的技巧越華麗,給導演帶來的麻煩越大,製片人很多時候都是強烈要求拍贅肉的,因為正是這些贅肉最初感動了他。導演的工作包含著詭詐,你的合作夥伴往往是無法說服的,因為你不能改變他人的審美,那是他自小到大形成的,讓他服從你的審美,只能採取誘騙的方式。
25.許多人只是在青春期時,看到了自己父母的局限,對他人則用“好人”、“壞人”簡單地區分,所以幼稚的好萊塢電影能贏得大多數觀眾,因為大多數人不願費神去理解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