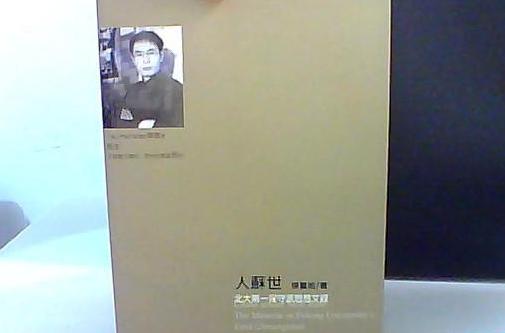《人蘇世-北大第一保守派思想文錄》是2005年風雲時代出版的一本圖書,作者是徐晉如。
基本介紹
- 作者:徐晉如
- ISBN:9789861461328
- 定價:NT$ 320
- 出版社:風雲時代
- 出版時間:20050201
內容介紹,作者介紹,
內容介紹
我的思想沒有迎合任何人。人道主義者被我撕破了偽善的臉皮,民主主義者被我駁得體無完膚,慣於奴役別人的,會從我的文字當中讀出桀驁不馴,革命家則會因我矢志不移地反平等而銜我入骨,而缺乏寬容、反對多元,這將是自由派人士反對我的理由。只有那些真正懂得尊重靈魂和生命意志的人士才可能真心欣賞我的著作,他們都是這個世界的零餘者。
在命運女神的私處
大約在十年前,當時我的家庭經歷了一場巨變,這使我在較長一段時期內把魯迅著作當作心靈惟一的託庇所,於是,我也像少年魯迅一樣,忽然萌生出一種強烈的道德使命感。我覺得自己應該去做一個殉道者,通過切實的行動對於這個世界予以批判。於是在接下來的幾年內,文學成為我的夢想。然而,到1999年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卻感到很茫然。我不善於編故事,也不能寫作輕鬆的文字,對於社會弱勢群體更缺乏同情,企圖通過文字來感染人顯然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妄想。那么,我能做什麼呢?
就在我彷徨無依的時候,上海師大著名學者王昆吾先生表示歡迎我報考他的博士生。我的確曾經很想進入專門的學術機構,清華、北大的諸位師長也多認為我天賦甚佳,可堪造就,於是我就想:那么,我便去投考博士吧。於是就開始複習迎考,於是報名,於是請了我在北大的兩位老師——費振剛先生和程郁綴先生給我寫推薦信。兩位先生為我寫的推薦信我至今珍藏,費先生本來寫的是“我謹推薦”,後來又在“推薦”前面添了“鄭重”二字,他們還有其他學術界的前輩對我的關愛我永生都不會忘記!不巧的是,當年的上海師大忽然嚴格按照制度辦事,本科畢業生工作未滿六年不予報名,這樣,我又只好繼續彷徨。2000年的9月,台灣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先生經盧仁龍先生——我在最困難的時候就曾得到盧先生無私的幫助——之介,答應幫我辦理手續赴台讀博。事情開始倒也順利,然而由於我不隸屬於任何一個學術機構,台灣陸委會就把我的申請駁回了。2001年的下半年,我重又申請了一次,這次台灣方面倒沒有什麼意見,旅台證也下來了,卻遇到別的阻力,終於沒能成行。這樣,進入專門的學術機構的願望又落空了。
進不了專門的學術機構,我並不十分遺憾。子曰:“君子不器。”我在內心深處也並不希望局限在某一種職業,即使這種職業是自己所深深熱愛的。然而不能去台灣感受一下古龍先生曾經生活過的環境,不能親身體驗台灣式的華人文化,倒真令我抱憾。我很奇怪,為什麼這樣一個彈丸之地,竟能誕生出古龍這樣一位不世出的天才,誕生出華人文學當中最具有現代性的那些作品——古龍小說?看來,這個謎只有等我將來有機會再去解了。
彷徨是對於思考著的人相當有益的一種生存狀況。人在彷徨的時候,常常會發現很多在通常狀況下不會發現的東西。我就在這個時候更為深刻地理解著生存的荒謬性、歷史的喜劇性,同時,也就更為深刻地認識了自己。這期間,我曾經遭遇了一次短暫的愛情,而最終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我以前一直生活在大學校園內——前兩年是在清華,後三年是在北大,我絕沒有想到人心原來可以卑劣、下作、無恥到那樣的地步,我這才明白,尼采何以把那些道德主義的庸眾喚作“群畜”,它們那沒有靈魂的生命的確和畜生沒有什麼分別。
我很後悔虛擲了那么多的時光。在長達七年的時間內,我縱情於歌,縱情於酒,最終除了留下那些“歌哭無端字字真”的詩句,什麼也沒有剩下。盧躍剛先生說讀了我的詩很詫訝於中國當代文學竟還有如此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東西,余傑稱我為當代龔自珍,然而,詩畢竟是一種太過個人化的體裁,它甚至不能給同類的人們以更多的慰藉。我從不懷疑自己是在永不停息地追索真理,但是我從來都對所謂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抱以深深的警惕,那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不朽事業我是做不來的,所以我常常覺得自己是一個多餘人。因為這樣的一種心緒,我就總是採取“述而不作”的態度。但在經歷了那場奇恥大辱以後,我忽然覺得自己終於有了寫作的理由。我已意識到,雖然我不可能做一個啟蒙者,卻可能通過寫作,帶給更多的生活在寒夜中的人們以溫暖。這個世間的確有一群人,他們和我一樣,把世界看作意志和表象,把情感當作生命惟一的真實,他們也都和我一樣,心靈永遠掙扎在深邃之淵。要是那些日子不曾虛度,我會有更多的文字貢獻給他們。
我的好友陳朴現已遠赴英倫,臨行前他在給我的信中這樣道:“個性與良知永遠會糾纏著我這樣的人,應該同樣也更加糾纏著你。我感受著你的孤獨,又只能看著你孤獨下去,知道你是根本不需要安慰的,安慰於你是一種恥辱。我尊重你。這世界於你太大了,又太小了。它太大,以至於你茫然四顧,不僅找不到一個同行者,甚至找不到一個忠實的聽眾。它太小,以至於你感覺自己被身邊熙熙的人群擠壓得馬上就要爆發,哪怕這爆發帶來的只能是自我的毀滅。誠如錢理群先生所言知識分子總在堂吉訶德和哈姆萊特間徘徊。我為能夠勇往直前的你祝福。我甘願在默默的沉思與祝福中老去。”他卻不知道,其實我的內心比他還要懦弱,我不但不敢去改造這個世界,甚至也懶得去適應這個世界,我像哈姆萊特一樣,因感受著命運的殘酷而選擇了彷徨。我心裡總有《哈姆萊特》中的一段對白時時浮現,怎么也揮之不去:
HAMLET My excellent good friends!How dost thou,Guidenstern?
Ah,Rosencrantz!Good lads,how do you both?
ROSENCRANTZ As the indifferent children of the earth.
GUILDENSTERN Happy in that we are not over happy.
ON Fortune's cap we are not the very button.
HAMLET Nor the soles of her shoe?
ROSENCRANTZ Neither,my lord.
HAMLET Then you live about her waist,or in the middle of
her favors?
GUILDENSTERN Faith,her privates we.
HAMLET In the secret parts of Fortune?O,most true,she
is a strumpet.
(哈姆萊特 我的好朋友們!你好,吉爾登斯吞!啊,羅森格蘭茲!好孩子們,你們兩人都好?
羅森格蘭茲 不過像一般庸庸碌碌之輩,在這世上虛度時光而已。
吉爾登斯吞 無榮無辱便是我們的幸福;我們高不到命運女神帽子上的鈕扣。
哈姆萊特 也低不到她的鞋底嗎?
羅森格蘭茲 正是,殿下。
哈姆萊特 那么你們是在她的腰上,或是在她的懷抱之中嗎?
吉爾登斯吞 說老實話,我們是在她的私處。
哈姆萊特 在命運身上秘密的那部分嗎?啊,對了;她本來是一個娼妓。[1])
2002年5月23日
-------------------------
注釋:
[1] 採用朱生豪先生譯文。
--------------------------------------------------------------------------------
我是一團倔強的火焰
“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1]加繆這樣說的時候,一定是對這個世界的荒謬有著切膚之痛,一定是在同命運戰鬥的過程里感受著彌綸六合的厭倦與暗淡如星的悲劇快慰感。同加繆的時代相比,我們的周遭充斥著更多的險惡的群畜和平庸的布爾喬亞,無數的賤民把自己打扮成摯愛世界的先知,他們一貫以正義、道德的名義戕滅著人類最優秀的種群,他們的嘴臉無比陰險,而卻無不擺出一副大公無私的樣子。面對如此荒謬的存在,聰慧的、頭腦勝過一般人的智者選擇了冷嘲(如王小波),而生命意志強健的靈魂卻選擇了擔荷。我在2001年冬天完成《美狄亞——論康敏的悲劇意義以及其他》的時候很負責任地宣告:“世界有了徐晉如,才知道什麼是悲劇。”那個時候,我分明感受到了死神的召喚。當時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就是與那些卑賤的群畜玉石俱焚。我每天都在思考哲學的根本問題,即生活是否值得經歷。感謝那些下賤的東西,它們的仇恨重新燃起了我的生命之火。我發現,惟有貴族所獨有的豐富的痛苦才使它們因意識到自己的卑賤而滿懷怨恨,也惟有貴族的偉大的快樂才真正使它們心驚膽戰。
當我終於不再渴望毀滅的時候,電視裡正重播曾經火遍全國的小市民喜劇《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張大民和他的情敵徐萬君會面了,我無比震驚於他那平庸的外表下面所隱藏著的深深怨恨,那是無知對有知、卑賤對高貴的怨恨,張大民的笑容顢頇善良,而他說出的話卻刻毒得讓人不寒而慄。看了這部電視劇,我徹底明白,這個世上再也沒有什麼罪惡比庸眾的猥瑣更讓人感到噁心,而庸眾對高貴和高貴者的仇恨是與生俱來的一種品質,任何企圖與庸眾進行對話的努力都注定是徒勞的。我想起去年九月,一位“王大民”給我寫信,也正是採用了與張大民一樣的話語方式。“王大民”在對它“以181cm的身高,且身材挺拔,毫無彎腰曲背之相,已屬難得,更兼眉清目秀,人見無不讚賞”的相貌作了一番自吹自擂之後,更得意洋洋地誇耀自己“有興趣的時候,只需順路一轉手之間,就有數百元的純利可得,也曾有過日進千元之時”,末了,它以張大民式的詼諧風格總結道:
因此,雖然輸給了我,你也不用覺得有什麼丟人的,這就像伊拉克必會輸給美國一樣,實力懸殊,勢所必然。
“王大民”的信給了我一個契機,它讓我終於能夠滿懷激情地梳理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全部思考,並把它們轉化為文字。徐萬君或者我本人的遭遇不是我們的個別經歷,整個貴族階級所長期面對著的,就是這樣屈辱的現實。面對如此荒謬的存在,我想我必須要捍衛靈魂與知識的尊嚴,於是就有了《90年代哲學筆記——關於如何界定貴族與賤民的學說》。在這篇充滿微言大義的著作當中,我對於知識分子進行了全新的定義,可以說,《90年代哲學筆記》就是知識分子的政治學綱領,它標幟著知識分子終於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走向歷史舞台。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一直排斥知識精英,一直拿“文人無行”的藉口否定知識精英的價值。知識精英本來應該是這個社會惟一的貴族,然而他們卻無時不刻不受到來自群畜和庸眾的攻擊。我所要為之奮鬥的,就是重新確立知識分子的貴族地位。
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知識的尊嚴、知識的貴族性始終遭到質疑,而那些庸眾當中的有知者竟也自甘下賤,否定知識的傲慢,把自己降到群畜的層次。托克維爾這樣感慨道:“永遠值得惋惜的是,人們不是將貴族納入法律的約束下,而是將貴族打翻在地徹底根除。這樣一來,便從國民機體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給自由留下一道永不癒合的創口。多少世紀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階級,長期來發揮著它那無可爭議的偉大品德,從而養成了某種心靈上的驕傲,對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慣於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為社會軀體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僅氣質雄壯,還以身作則來增強其他階級的雄壯氣質。將貴族根除使它的敵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再也不會復生;它可以重獲頭銜和財產,但再也無法恢復前輩的心靈。”[2]這一感慨同樣適用於多災多難的中國。由於在中國古代,貴族的責任與義務是由“士”來擔當的,所以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即是西方意義上的貴族。經歷了一場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巨變之後,今天的知識分子再也不具備傳統社會“士”的地位,他們的心靈如何才能像他們的先輩一樣偉大?在當代中國思想界,除了我的著作,沒有任何一部著作對這個問題作出解答。然而,我之所以能夠發現並解答這個問題,並非因為我有多么聰明,而只是因為我的身上還葆有著未遭戕滅的高貴。
這個集子選錄的文章大部分沒有可能在媒體發表。其實我在寫作每一篇文章的時候都清醒地意識到:總有一天我會被媒體封殺。它們這樣做絕對不會是因為政府的高壓,而是因為它們中的大多數都太卑賤。在一個貴族作為整體的階級已經遭到滅頂之災的社會裡,倖存者都是孤獨者,我們必須面對來自群畜和庸眾的猖狂進攻,我們都必須拿起武器。在那些賤民中的有知者所吹響的號角聲中,群畜早就發起了向我們的進攻,然而,我們當中的每一個都應意識到,它們的內里無比孱弱,它們的心靈充滿自卑。我們當以遭到攻擊而驕傲,因為如果群畜也開始欣賞我們,那隻說明我們也已變得卑賤!
由於某一不可控的因素,本來應該在2002年8月就和讀者見面的這部書現在還在我的電腦中沉睡。不過這倒使我能夠在本書中補入《那些人道主義的雜種們——9·11事件周年感賦》一文。同時,我把原先失載的少作《二十自序:我本零餘》錄為該書第六編開宗明義的文章,這篇文章說明,儘管在七年前我虛歲二十歲的時候思想還沒有像今天一樣成熟,然而我所堅持的價值、所堅守的高貴,從來沒有絲毫更移。我不是在以學理而是在以階級性為出發點進行思考,就憑這一點,也應該把我同中國當代所有的其他思想者區別開來。
在墨漆沉沉的黑夜裡,我將是一團倔強的火焰,悲愴而歡欣地燃燒著。
2002年10月10日
-------------------------
注釋:
[1]《西西弗的神話》,中譯本3頁,廣西師大出版社2002年2月
[2]《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譯本148頁,商務印書館1992年8月
作者介紹
徐晉如,1976年生,蘇北鹽城人,現居北京。高中時讀理科,以第一志願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後轉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就讀直至畢業,但在情感上始終是一個清華人,並且終身感激在清華所受的理工科訓練。居常以讀書思考為最大的樂趣,視學術研究為第二生命。為人最恨鄉愿,性格中暴力傾向明顯,從不掩飾對於卑賤靈魂的刻骨深仇,因此而運交華蓋,命途多舛。但至今不後悔。平生所欽服者有莊周、龔自珍、陳獨秀、郁達夫、古龍諸子,以個人主義為世間第一要義,是尼采反道德論的忠實信徒。著有詩集《胡馬集》、歷史小說集《光榮年代》、學術專著《二十世紀詩詞史》、《經典與偽經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