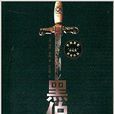在《黑伯爵》一書中,雷斯重現了一位被遺忘已久的歷史英雄。此人一度家喻戶曉,但今天幾乎無人知曉。他跌宕起伏的歷險出現在《三個火槍手》中;他的光榮和最後的悲劇命運激發了《基督山伯爵》的創作靈感。他是著名小說家大仲馬的父親——亞力克斯·仲馬。亞力克斯的母親是黑奴,父親是流亡聖多明克(今海地)的法國貴族。亞力克斯一度淪為奴隸;但他卻設法到達巴黎,成為法國佩劍貴族的一員。他32歲時已獲得一系列不可思議的勝利:論功行賞,他統率五萬大軍。然後,他突襲阿爾卑斯山冰封的絕頂,為法國軍隊打開道路,立下了絕世戰功。他隨後指揮拿破崙的騎兵團,戰績輝煌;被俘後陷身地牢……《黑伯爵》引用了迄今鮮為人知的檔案、書信、戰場報告、亞力克斯的獄中日記,堪稱非小說敘事的開創性傑作。
基本介紹
- 書名:黑伯爵
- 作者:湯姆·雷斯 (Tom Reiss)
- 出版社:西苑出版社
- 頁數:354頁
- 開本:16
- 品牌:西苑出版社
- 外文名:The Black Count
- 譯者:邱世超
- 出版日期:2014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15104263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他是拿破崙的愛將,統帥騎兵團橫掃歐洲,卻不想被拿破崙背叛,身陷囹圄!
他的身影出現在《三個火槍手》和《基督山伯爵》中!
他就是法國小說家大仲馬的父親——亞力克斯·仲馬將軍!
作者簡介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時代》
此書堪稱一份出色的報告,調查縝密而詳盡……作者耗費十年時間和精力完成此書,可見一斑。”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迷人……絕對是一本充滿豐富想像力的傳記。
——《紐約時報·書評》
雷斯詳述了亞力克斯·仲馬被錯誤遺忘的一生……本書堪稱他的不朽之作。
——《華盛頓郵報》
令人印象深刻……雷斯以一種有趣的方式構建了整個故事……很有吸引力。
——《華爾街日報》
獲獎作家所著的偵探作品……出色的研究。
——英國《每日郵報》
勝利了……雷斯筆下成功展現了仲馬將軍的非凡一生:憔悴的騎兵、浮華的功績,以及一位父親的舐犢之愛。
——英國《先驅報》
曾經因為種族原因,亞力克斯·仲馬的非凡人生被湮沒在了歷史長河中,如今在本書的動人故事中得以重現……藉助筆下人物自身的誇張性格以及法國大革命的時代背景,雷斯成功創造出了一個激動人心的故事。
——《出版人周刊》
名人推薦
——傑克·威澤弗德 《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成吉思汗與現代世界演變》作者
圖書目錄
序二 2007年1月25日
第一卷
第一章 糖廠
第二章 《黑人法典》
第三章 諾曼征服
第四章 “法國不應存在奴隸”
第五章 美國人在巴黎
第六章 光明之城的黑伯爵
第七章 王后的龍騎兵
第二卷
第八章 革命之夏
第九章 “浴血重生”
第十章 “黑色之心亦嚮往自由”
第十一章 “仁愛先生”
第十二章 世界大佬之爭
第十三章 革命觸底
第十四章 圍攻
第十五章 黑魔
第三卷
第十六章 遠征隊長
第十七章 “共和理念的譫妄”
第十八章 如夢燃火
第十九章 神聖信仰軍囚犯
第二十章 “女公民仲馬……擔憂丈夫的命運”
第二十一章 地牢
第二十二章 等待與希望
後記 遺忘的雕像
後記
亞力克斯·仲馬將軍的第一篇生平傳記出版於1797年法國在義大利北部大獲全勝之後。 此時正值十年法國大革命的高潮之一,而當時亞力克斯·仲馬將軍被拿破崙稱讚為擊退野蠻人的羅馬英雄。這篇文章對仲馬將軍英勇事跡盡情渲染,與兩年後仲馬將軍的命運一對比,頓時令人唏噓不已。但是這篇文章中另外一點讓我震驚:它公正地記錄了仲馬的種族問題。
亞歷山大·仲馬將軍
有色人種
共和國五年芽月4日
共和國歷史只會向子孫後代紀念偉大行為,地位或軍銜對於個人來說毫無差別。在記錄偉大人物的生平年鑑時,其信實的筆觸應該描寫這個英雄,描寫他的高尚道德及不朽榮譽,而不應考慮他是否出生在歐洲或在非洲炎熱的大地上,抑或他的膚色是古銅色還是更接近黑檀色。黑人用勇氣鑄就的功績與那些出生在舊世界的人的豐功偉績一樣值得尊敬。事實上,誰能夠比這個經歷了所有奴隸制的苦難之後依舊為自由而戰的有色人更有權力獲得公眾的尊敬?他只要記住所經歷過的所有苦難,就可以和最有名的戰士平起平坐了。
這就是亞歷山大·仲馬——1762年出生在聖多明克的混血有色人種——自大革命以來的行事方式。這個年輕人來到法國與祖國的保衛者們並肩戰鬥……展現了無畏的勇氣和超人的智慧,很快就聞名軍中,甚至包括義大利軍隊,並升遷為第二騎兵師的指揮官。將軍身高1.8米,將是你見過的最瀟灑帥氣的人之一;他不僅外貌出眾,而且舉止優雅親切。他的捲髮好似希臘和羅馬人的捲髮。
帶著攻占義大利時所獲的榮譽,亞歷山大·仲馬跟隨不朽的波拿巴轉戰提洛爾。共和國五年芽月4日(1797年3月24日),他奉命率領約20名騎兵前去偵察敵軍動向。仲馬命令一位準將占據山谷後的位置,掩護他的側翼。奧地利人見前方法軍人數很少,便氣勢昂揚地沖了過來;敵軍人數眾多,仲馬所率的騎兵們漸漸不敵。到了布里克森小鎮前面的克勞森爾橋前(原文如此),(法軍)還未來得及擺開迎敵陣勢,就被緊緊地困在一條狹窄的過道里。眼見情勢危急,仲馬將軍獨自拍馬前往橋頭,抵抗敵軍騎兵小隊的進攻長達數分鐘,最終迫使他們撤退。他被20個奧地利人圍住,但他殺死3名,並重傷了8名;他身上卻只受了三處輕微刀傷。敵軍被他的英勇氣勢嚇倒,掉頭四處逃竄。為了增加氣勢,他大喊一聲:“投降吧!法國大軍就在我身後!共和國的將軍永遠都不會落後於他的士兵。”
我找到的另一篇小傳出版在11年後的1808年。當時仲馬已然辭世,拿破崙繼承了皇權。這篇簡短的傳記摘自一本名為《軍隊軼事》的書籍(由一位叫皮埃爾·努加雷的巴黎出版商編寫)。在閱讀時,奇怪的是,我總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開頭也是“亞歷山大·仲馬,1762年出生於聖多明克,來到法國與祖國的保衛者們並肩戰鬥”。
他在法國義大利軍團中表現突出,升遷至第二騎兵師的指揮官。他跟隨不朽的總統帥(波拿巴)轉戰提洛爾;共和國五年芽月4日(1797年3月25日,原文如此,應為24日),他奉命率領約20名騎兵前去偵察敵軍動向。仲馬命令一位準將占據山谷後的位置,掩護他的側翼。奧地利人見前方法軍人數很少,便氣勢昂揚地沖了過來;敵軍人數眾多,仲馬所率的騎兵們漸漸不敵。到了布里克森小鎮前面的克勞森爾橋前(原文如此),(法軍)還未來得及擺開迎敵陣勢,就被緊緊地困在一條狹窄的過道里。眼見情勢危急,仲馬將軍獨自拍馬前往橋頭,抵抗敵軍騎兵小隊的進攻長達數分鐘,最終迫使他們撤退。他被20個奧地利人圍住,但他殺死3名,並重傷了8名;他身上卻只受了三處輕微刀傷。敵軍被他的英勇氣勢嚇倒,掉頭四處逃竄。為了增加氣勢,他大喊一聲:“投降吧!法國大軍就在我身後!共和國的將軍永遠都不會落後於他的士兵。”
這篇小短文我讀了很多遍,終於知道為何如此熟悉:這就是1797年的傳記!只是沒有描寫種族、奴隸制,共和國的價值觀也被抹去了。仲馬將軍的功績以及克勞森橋保衛戰與之前的版本一模一樣,用詞和句序也都沒變。但是讚許仲馬 “經歷了所有奴隸制的苦難後依舊為自由而戰的有色人”卻被刪掉了。
巴黎曾經有一座仲馬將軍的雕塑,出自19世紀晚期雕塑名家阿爾佛雷德·蒙賽爾之手。雕塑坐落在馬爾塞布廣場,這個廣場後來也被稱為三仲馬廣場,因為有仲馬將軍、小說家大仲馬和劇作家小仲馬的雕像。這一構想在19世紀90年代提出,當時整個法國掀起了懷念一個世紀前大革命的浪潮。建造仲馬將軍雕像的經費不是來自政府或任何軍事組織,而是由一小群大仲馬小說的愛好者通過捐贈籌集的款項——大仲馬也曾試圖為父親樹一尊雕像,終未能如願。籌款活動由法國當時最有名的兩位名人牽頭:作家阿納托爾·法朗士和女演員莎拉·伯恩哈特。波恩哈特為此舉行了專場表演。雕刻這尊雕塑花了整整十年,1912年秋天正式將雕塑立於馬爾塞布廣場的右側,後官方手續的繁瑣拖沓又讓這座雕像遮蓋了大半年。
經過兩年的搜尋,我找到了這座雕像現存唯一的一組照片,是由市政雕塑攝像師於1913年拍攝的。仲馬身穿雙排扣的簡式大衣,露出胸部,以一個堅定愛國者的姿態凝視遠方,握著來復槍的方式就像提著一根拐杖。除了五張從不同角度拍攝的照片之外,還有一張照片仲馬將軍的銅像覆蓋著破爛白布,只露出了手臂和來復槍;背景是一位留著翹八字鬍的馬夫駕著一匹馬拉的貨車。看著這些珍貴的照片,我的感覺是雕像確實不錯;它抓住了仲馬直白而敢為的神韻。但是讓我迷惑的是蒙在白布里的那尊雕塑。1913年5月28日《晨報》的一張剪報提供了些許線索,標題是《遺忘的雕塑》:
可憐的將軍!看來他們把他拋棄在這裡。他手握步槍,躺在草地中央,就像被永遠拋棄一樣。另外兩位仲馬——大仲馬和小仲馬的銅像已經立於此很久了。但是他,這位老兵,他們的父親、祖父……卻被遺忘了。我們必須還他以正義,因為廣場空間開闊,我們也從不缺少雕塑,我們應該把老將軍的銅像豎起來……但是豎起雕塑是一回事,為其舉行落成典禮又是另一回事。
據這份報紙報導,上一年雕像就搬到了這裡,不過一直蒙著白布,由於各個官僚機構之間通信緩慢——市長、市議會、內政部、分管藝術的副國務卿、分管藝術的行政委員會、藝術和博物館局、建築與景觀規劃局,最後是雕塑家。從他抱怨落成儀式推遲的投訴信的潦草字跡可見他異常煩悶。官方的落成儀式似乎無限期延遲。5月27日,著名漫畫家波布帶著一群詼諧幽默的人舉行了一次模擬落成儀式,他們拉下了“作為其面紗的骯髒的摩爾斗篷”。波布女士引用了一首詩並說道:“為了紀念將軍,由一個小女孩表達了所有法國年輕人的敬意。不必說,一大批參與的民眾在驚訝中見證了這次可笑的落成儀式。”
第二天,編輯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補充了這一故事:
數月以來,馬爾塞布廣場都有一個稻草人:就是穿著僧人長袍的仲馬將軍……請給出一個理由,為什麼沒有部長主持落成儀式?星期二,一群歡樂的喜劇家決定自行行動……今天早上,仲馬將軍再一次打扮得像聖方濟會托缽僧。
1913年初夏,共和國總統簽署命令批准豎立這一雕像,但是沒有記錄顯示舉行了落成儀式。7月,一位負責景觀規劃的官員抱怨說,蒙在老將軍身上的破爛白布已碎成一片一片的。書面記錄到此為止。
我耗費了很大精力去尋找雕塑的蹤跡,因為1941—1942年納粹毀掉了雕像。 德國占領者熔化了數百尊法國雕塑,他們更關注的是雕像的主題而非雕像的大小:對於他們來說熔化那些為了自由、平等、友愛而戰鬥的混血戰士的雕像是很容易做的決定。
2008年,我坐在三仲馬聯合會創建者安高特先生的小居室里同他一起觀看錄像片。他的居室在奧爾良公爵以前宮殿的對面,那裡曾上演過《亞當與夏娃之夜》,現在是一家養老院。這是一部紀錄片,記錄了一位高大威武、膚色較淺的黑人,穿著18世紀的軍服,正騎著馬穿過維萊科特雷;從背景里的小型汽車和DVD店面來看,這顯然不是18世紀的場景。這位騎士穿過現代小鎮來到墳地,繫上馬,走到仲馬將軍的墳前,表達了自己的敬意。他是來自瓜德羅普島的法國作家兼政治活動家克洛德·利布,他邀請了影片攝製組幫他拍下自己騎馬穿過小鎮的畫面。安高特看過影片的一部分。攝影機關掉後,利布大哭起來,他說這是為了證明他對仲馬將軍的熱愛。
我在巴黎找到了克洛德·利布。他正在遊說薩科齊政府給仲馬將軍頒布一個榮譽軍團勳章並在城市中央樹立新的雕像。其實,利布領導了一個小型的法國政治社團,這個社團正在就法國政府有關加勒比地區奴隸遺產的問題進行遊說。社團成員非常少,但是利布常在媒體上陳述自己的觀點,並發表長篇辯論文章。在他的網站上,他自稱為“多樣化的歷史學家”。他異常活躍。他向我展示了寫給法國總統和巴黎市長的成摞信件,還有自己出版過的書籍和文章。
“為什麼仲馬將軍沒有得到榮譽軍團勳章?”他表示很疑惑。
“大革命時代每位將軍都有一個!為什麼納粹把他的雕像毀壞之後,就再沒有重塑一尊?巴黎的每個街區都有雕像。種族主義、種族主義,完全是種族主義。”
利布堅持不懈的活動顯然產生了作用。我第二次見到他時,他正與巴黎市長在一起,市長同意了他豎立雕像的提議。又過了一段時間,在一個法國電視剪輯中我看到他與市長站在一起,兩人分別掀起一面小三色旗幟,其下分別是一個戴著鐐銬的壯觀的奴隸銅像,兩尊都有4.5米高。在21世紀種族政治盛行的法國,仲馬將軍帶著巨大鐐銬的雕像已經成為紀念法國殖民奴隸制所有受害者的紀念碑。一支軍樂隊為亞力克斯·仲馬奏響了《馬賽曲》,市長和這位活動家都發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講,然後大家各自回家。
法國依舊沒有一尊真正紀念亞力克斯·仲馬將軍的雕像。
序言
堂姐叫道:“你去哪裡?”
“噢,去給爸爸開門,他跟我們告別來啦。”我平靜地答道。
可憐的姑娘從床上跳了起來,一把抓住了我伸向門把手的手,狠命地將我拽回床上。
我使出渾身力氣想要掙脫,卻只能大喊:“再見,爸爸!再見,爸爸!”
第二天清晨,大人喚醒了孩子們,小亞歷山大得知父親已在前晚去世。
“爸爸死了,”我問道,“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再也見不到他了。”
“你為什麼說我再也見不到爸爸了?……為什麼會見不到?”
“因為上帝帶他回去了。”
“永遠嗎?”
“永遠。”
“你說我再也見不到他了?……一次也不行嗎?”
“一次也見不到。”
“上帝住在哪裡?”
“上帝住在天堂。”
我苦思了一會兒。儘管當年只是個懵懂孩童,我還是意識到發生了什麼無法挽回的事。趁著大人們不注意,我從叔叔家溜了出去,跑回了自己家。
家裡的每扇門都敞開著,所有人都面露懼色;瀰漫著死亡的氣息。
沒有人發現我的到來。我找到了家裡存放武器的房間,扛起了那桿槍,那桿父親答應等我長大後就贈予我的槍。
我扛著槍爬上了樓梯。
在二樓樓梯口,我碰到了母親。
她剛從父親房間出來,臉上掛滿淚水。
“你去哪兒?”母親見到我,十分吃驚,以為我還在叔叔家。
“我要去天堂!”我答道。
“什麼,你要去天堂?”
“讓我過去。”
“孩子,你去天堂做什麼?”
“我要去殺了上帝,他殺了爸爸。”
母親一把將我摟進懷裡,緊得讓我透不過氣來。
亞歷山大·仲馬45歲時寫下了上述文字,他認為是時候該回顧此生了。他沒有採用編年體例記錄自己31歲前的點滴,而31歲時他還遠沒有成為家喻戶曉的作家,但是他卻用了200多頁敘述父親仲馬將軍如小說般跌宕起伏的一生——仲馬將軍出生於法國殖民地,在法國大革命中九死一生,以過人的勇武與膽識,成為了拿破崙麾下一名統帥五萬精兵的將軍。這是傳記文學史上的一次大膽嘗試,其中關於他父親的素材來自於母親和父親朋友們的回憶,以及從母親及法國軍務部收集的信件和官方檔案,雖然存在很多空白省略以及情節和對話的再創作,卻實乃誠懇之作。直至敘述完了父親去世時的畫面,大仲馬才開始在自傳中回顧了自己的一生。
一名幼童如何能憶起如此多的細節,也許有人會對此產生懷疑,大仲馬在《基督山伯爵》中塑造的白人奴隸海蒂這一角色恰好可以替他解答。在海蒂四歲時,她的父親遭小說中的主要反派人物之一陷害謀殺,在對伯爵談起自己父親時,她說:“雖然當時我年僅四歲,但當年的事對我萬分重要,一絲一毫都不曾忘記。”
在大仲馬的小說中,記住一個人是最重要的事,而忘記是最惡劣的罪行。《基督山伯爵》的反派人物沒有將主人公愛德蒙·堂泰斯殺害,而是將他關入了地牢,讓世人將其遺忘。大仲馬筆下的主人公不會忘記任何事或任何人,例如堂泰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記憶超群,對所遇之人過目不忘。當他一一報復三個仇家時,卻發現他們早已忘記了他,更別提當年所犯下的罪行。
之所以為亞歷山大·仲馬將軍這位被遺忘的英雄寫傳,是因為兒時拜讀過大仲馬傳記中關於其父親的回憶錄,至今令人難以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