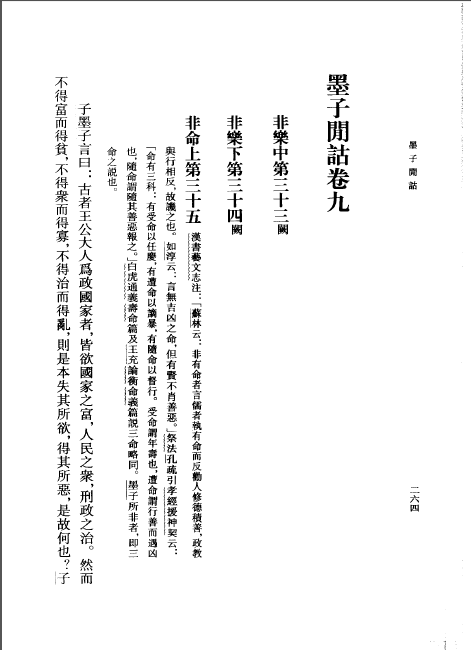非命簡介
《淮南子·泛論訓》: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墨子非命論
上篇
原文
子
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
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眾(2)。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眾則眾,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3)?”以上說王公大人,下以駔百姓之從事(4),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
然則明辨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5),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6)。何謂三表?子
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7),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8),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蓋嘗尚觀於聖王之(9)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蓋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10)、布施百姓者,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
是故子
墨子言曰:吾當未鹽,數天下之良書(11),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12)。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13)?
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誶也(14)。說百姓之誶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乾主,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15),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
昔者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16)。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17),處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鄉者言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乾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
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
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為君則不義,為臣則不忠,為父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則不良,為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之財不足,而饑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塗之辟(18),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19)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20)。”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21):“紂夷處(22),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23),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24),天亦縱棄之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
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是故子
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25),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注釋
(1)本篇的主題為反對命定思想。墨子認為命定論使人不能努力治理國家,從事生產;反而容易放縱自己,走向壞的一面。命定論是那些暴君、壞人為自己辯護的根據。關於檢驗言論,
墨子提出了“三表”法,即通過考察歷史、社會實情,並在實踐中檢驗言論,堅決反對誤國誤民的命定論。
(3)此句中“命”,按劉昶說當為“力”。
(4)駔:同“阻”。
(5)鈞:制陶用的轉輪。
(6)表:此句中用為原則。
(7)原:推斷、考察。
(8)廢:通“發”。
(9)蓋:通“盍”,何不之意。
(10)出:此字恐有誤。
(11)鹽:為“■”之誤,意為“暇”。
(12)五者:疑為“三者”。
(13)錯:為“措”之假借字。
(14)誶:依俞樾說讀為“悴”,憂愁之意。
(15)移:為“利”之誤。
(16)本句“則”當為“利則分”之漏。
(17)罷:通“疲”。
(18)塗:當為“途”。心途,即心計。辟:通“僻”。
(19)《仲虺之告》:《尚書》篇名。
(20)龔:依孫星衍說,當為“用”之音近假借字,因此意。
(21)《泰誓》:《尚書》篇名。
(22)處:當為“虐”。
(24)此句有誤,“排漏”疑作“兵備”。
(25)忠:通“中”。
譯文
墨子說過:“古時候治理國家的王公大人,都想使國家富裕,人民眾多,法律政事有條理;然而求富不得反而貧困,求人口眾多不得反而使人口減少,求治理不得反而得到混亂,則是從根本上失去了所想的,得到了所憎惡的,這是什麼原因呢?
墨子說過:“主張‘有命’的人,雜處於民間太多了。”主張“有命”的人說:“命里富裕則富裕,命里貧困則貧困,命里人口眾多則人口眾多;命里人口少則人口少,命里治理得好則治理得好;命里混亂則混亂;命里長壽則長壽,命里短命則短命,雖然使出很強的力氣,有什麼用呢?”用這話對上遊說王公大人,對下阻礙百姓的生產。所以主張“有命”的人是不仁義的。所以對主張“有命”的人的話,不能不明加辨析。
然而如何去明加辨析這些話呢?
墨子說道:“必須訂立準則。”說話沒有準則,好比在陶輪之上,放立測量時間的儀器,就不可能弄明白是非利害之分了。所以言論有三條標準,哪三條標準呢?墨子說:“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實踐的。”如何考察本原?要向上本原於古時聖王事跡。如何推究呢?要向下考察百姓的日常事實。如
何實踐呢?把它用作刑法政令,從中看看國家百姓人民的利益。這就是言論有三條標準的說法。
然而天下的士人君子,有的認為有命。為什麼不朝上看看聖王的事跡呢?古時候,夏桀亂國,商湯接過國家並治理它;商紂亂國,周武王接過國家並治理它。社會沒有改變,人民沒有變化,桀紂時則天下混亂,湯武時則天下得到治理,它能說是有命嗎?
然而天下的士人君子,有人認為有命。為何不向上看看先代君王的書呢?先代君王的書籍中,用來治理國家、頒布給百姓的,是憲法。先代君王的憲法也曾說過“福不是請求來的,禍是不可避免的;恭敬沒有好處,凶暴沒有壞處”這樣的話嗎?所用來整治軍隊、指揮官兵的,是誓言。先代君王的誓言裡也曾說過“福不是請求來的,禍是不可避免的;恭敬沒有好處,凶暴沒有壞處”這樣的話嗎?
所以
墨子說:我還無暇來統計天下的好書,不可能統計完,大概說來,有這三種。雖然要從中尋找主張“有命”的人的話,必然得不到,不是可以放棄嗎?
要聽用主張“有命”的人的話,這是顛覆天下的道義。顛覆天下道義的人,就是那些確立“有命”的人,是百姓所傷心的。把百姓所傷心的事看作樂事,是毀滅天下的人。然而都想講道義的人在上位,是為什麼呢?答道:講道義的人在上位,天下必定能得到治理。上帝、山川、鬼神就有了主事的人,萬民都能得到他的好處。怎么知道的呢?
墨子說:“古時侯湯封於亳地,斷長接短,有百里之地。湯與百姓相互愛戴,相互謀利益,得利就分享。率領百姓向上尊奉天帝鬼神。所以,天帝鬼神使他富裕,諸侯親附他,百姓親近他,賢士歸附他,沒死之前就已成為天下的君王,治理諸侯。古時候文王封於岐周,斷長接短,有百里之地,與他的百姓相互愛戴、相互謀利益,得利就分享。所以近處的人安心受他管理,遠處的人嚮往他的德行。聽說過文王的人,都趕快投奔他。疲憊無力、四肢不便的人,聚在一起盼望他,說:‘怎樣才能使文王的領地伸到我們這裡,我們也得到好處,豈不是也和文王的國民一樣了嗎?’所以天帝鬼神使他富裕,前文所說:‘講道義的人在上位,我因此認識到這點。”
所以古時候的聖王頒布憲法和律令,設立賞罰制度以鼓勵賢人。因此賢人在家對雙親孝順慈愛,在外能尊敬鄉里的長輩。舉止有節度,出入有規矩,能區別地對待男女。因此使他們治理官府,則沒有盜竊,守城則沒有叛亂。君有難則可以殉職,君逃亡則會護送。這些人都是上司所讚賞,百姓所稱譽的。主張“有命”的人說:“上司所讚賞,是命里本來就該讚賞,並不是因為賢良才讚賞的;上司所懲罰,是命里本來就該懲罰的,不是因為凶暴才懲罰的。”所以在家對雙親不孝順慈愛,在外對鄉里長輩不尊敬。舉止沒有節度,出入沒有規矩,不能區別對待男女。所以治理官府則會盜竊,守城則會叛亂。君有難而不殉職,君逃亡則不會護送。這些人都是上司所懲罰,百姓所毀謗的。主張“有命”的人說:“上司所懲罰是命里本來就該懲罰,不是因為他凶暴才懲罰的;上司所讚賞,是命里本來該讚賞,不是因為賢良才讚賞的。”以這些話來做國君則不義,做臣下則不忠,做父親則不慈愛,做兒子則不孝順,做兄長則不良,做弟弟則不悌。而頑固主張這種觀點,則簡直是壞話的根源,是凶暴人的啟發。
然而怎么知道“命”是凶暴人的啟發呢?對飲食很貪婪,而懶於勞動,因此衣食財物不足,而饑寒凍餓的憂慮就來了。不知道要說:“我疲憊無力,勞動不快疾。”一定要說:“我命里本來就要貧窮。”古時前代的暴君,不能忍住耳目的貪婪,心裡的邪僻,不聽從他的雙親,以至於國家滅亡,社稷絕滅。不知道要說:“我疲憊無力,管理不善。”一定要說:“我命里本來要亡國。”《仲虺之告》中說:“我聽說夏朝的人偽托天命,對下面的人傳播天命說:上帝討伐罪惡,因而消滅了他的軍隊。”這是說湯反對桀主張“有命”。《泰誓》中說:“紂的夷滅之法非常酷虐,不肯侍奉上帝鬼神,毀壞他的先人的神位、
地祇而不祭祀。並說:‘我有天命!’不努力防備,天帝也就拋棄了他而不予保佑。”這是說武王所以反對紂主張“有命”的原因。
要聽用主張“有命”的人的話,則在上位的人不聽獄治國,下面的人不勞作。在上位的人不聽獄治國則法律政事就要混亂,下面的人不勞作則財物日用不足。對上沒有粢、酒來供奉上帝鬼神,對下沒有東西可以安撫天下賢人士子;對外沒有東西可以接待諸侯的賓客;對內則不能給飢者以食,給寒者以衣,撫養老弱。所以“命”,上對天帝不利,中對鬼神不利,下對人不利。而頑固堅持它,則簡直是壞話的根源,凶暴人的啟發。
所以
墨子說:“現在天下的士人君子,內心想使天下富裕而怕它貧困,想使天下得到治理而怕它混亂,主張‘有命’的人的話,不能不反對。這是天下的大害啊!”
中篇
原文
子
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2),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3)。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偽,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4)?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為刑。此言之三法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眾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為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
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憲布令以教誨,明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雲者,亦不然矣。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5)?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6),慎言知行(7),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得其居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驅騁田獵畢弋,內沉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8),身在刑僇之中,不肯曰我罷不肖,我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必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眾愚朴人。
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式是惡,用闕師(9)。”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10),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11),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亦然:“且(12)!政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13)。”在於商、夏之《》、《書》曰:“命者,暴王作之。”
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
墨子非也。
注釋
(1)此篇與《非命上》意同。
(2)由:當作“為”。
(3)於:此處通“烏”,疑問詞。
(4)此句下失“或以命為有”一句。
(5)故:依孫詒讓說作“胡”。對:即懟,憤恨意。
(6)桀:通傑。
(7)知:當作“疾”。
(8)厲:即絕滅後代意。
(9)用:當作“厥”,喪滅意。
(10)居:疑為“虐”。
(11)不:疑作“百”。
(12)且:通“徂”,往、去意。
(13)此句當作:“吉不降自天,自我得之。”
譯文
墨子說:“凡發表談話、寫文章的原則,不可以不先樹立一個標準。如果言論沒有標準,就好象把測時儀器放在轉動的陶輪上。即使工匠很聰明,也不能得到正確的答案。然而現在世上的真假,不能得到辨識,所以言論有三種法則。”哪三種法則呢?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實踐的。怎樣求言論的本原呢?用天帝、鬼神的意志和聖王的事跡來考察它。怎樣推究言論呢?用先王的書來驗證它。怎樣把言語付之實踐呢?用它來作為標準。這就是言論的三條標準。
天下的士人君子,有的認為命是有的,有的認為命是沒有的。我之所以知道命的有或沒有,是根據眾人所見所聞的實情才知道有或沒有。有聽過它,有見過它,才叫“有”,沒聽過,沒見過,就叫“沒有”。然而為什麼不試著用百姓的實際來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來,有曾見過命的形象,聽過命的聲音的人嗎?沒有過的。如果認為百姓愚蠢無能,所見所聞的實情不能當作準則,那么為什麼不試著用諸侯所流傳的話來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來,有曾聽過命的聲音,見過命的形體的人嗎?沒有過的。
那么為什麼不用聖王之事來考察呢?古時聖王,舉拔孝子,鼓勵他事奉雙親;尊重賢良,鼓勵他作善事,頒發憲令以教誨人民,嚴明賞罰以獎善止惡。這樣,則可以治理混亂,使危險轉為安寧。若認為不是這樣,古時侯,桀所搞亂的,湯治理了;紂所搞亂的,武王治理了。這個世界不變,人民不變,君王改變了政令,人民就容易教導了。在武王時就得到治理,在桀、紂時則變得混亂。安寧、危險、治理、混亂,原因在君王所發布的政令,怎能說是“有命”呢?那些說“有命”的,並不是這樣。
說“有命”的人說:“並不是我在後世說這種話的,自古時三代就有這種話流傳了。先生為什麼痛恨它呢?”答道:“說‘有命’的人,不知是三代的善人呢?還是三代的殘暴無能的人?”怎么知道的呢?古時候有功之士和傑出的大夫,說話謹慎,行動敏捷,對上能規勸進諫君長,對下能教導百姓。所以上能得到君長的獎賞,下能得到百姓的讚譽。有功之士和傑出的大夫聲名不會廢止,流傳到今天。天下人都說:“是他們的努力啊!”必定不會說:“我見到了命。”所以古時三代的凶暴君王,不改正他們過多的聲色享受,不謹慎他們內心的邪僻,在外則驅車打獵射鳥,在內則耽於酒和音樂,而不顧國家和百姓的政事,大量從事無用的事,對百姓凶暴,使下位的人不敬重在上位的人。所以國家空虛,人民亡種,自己也受到刑戮的懲罰。不肯說:“我疲懶無能,我沒做好刑法政事。”必然要說:“我命中本來就要滅亡。”即使是古時三代的貧窮人,都是這樣說。對內不能好好地對待雙親,在外不能好好地對待君長。厭惡恭敬勤儉而喜好簡慢輕率,貪於飲食而懶於勞作。衣食財物不足,至使有饑寒凍餒的憂患。必不會說:“我疲懶無能,不能勤快地勞作。”一定說:“我命里本來就窮。”即使是三代虛偽的人,也都這樣說。粉飾“有命”之說,以教唆那些愚笨樸實的人。
聖王擔憂這個問題已經很久了。所以把它寫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在先王的書《仲虺之告》中說:“我聽說夏代的人詐稱天命,宣布天命於世,所以天帝痛恨他,喪失了他的軍隊。”這是說夏朝的君王桀主張“有命”,湯與仲虺共同批駁他。先王的書《太誓》也這樣說,道:“紂很暴虐,不肯
侍奉上帝,拋棄他的先人的神靈而不祭祀。說:‘我有命!’不努力從事政事,天帝也拋棄了他而不去保佑。”這是說紂主張“有命”,武王作《太誓》反駁他。在三代百國書上也有這樣的話,說:“你們不要崇奉天是有命的。”三代百國也都說沒有命。召公的《執令》也是如此:“去吧!要虔敬!不要相信天命。只有我倆而不能相互誡勉嗎?吉利並不是上天降下的,而是我們自己得到的。”在商夏時的詩、書中說:“命是凶暴的君王捏造的。”
天下的士人君子,想要辨明是非利害的原因,對於主張“有命”的人,不能不趕快批駁。主張“有命”的人,是天下的大害,所以
墨子反對他們。
下篇
原文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2),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
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眾之耳目之請(3),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
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
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
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4),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驅騁田獵畢戈,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我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饑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5),此皆疑眾遲朴。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6),民不而葆。既防凶星(7),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增(8),用爽厥師。”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為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9):“惡乎君子(10)!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11)。”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
是故子
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葛緒,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12),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13),下以持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抎其國家(14),傾覆其社稷者,此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注釋
(1)此篇與《非命上》意同。
(2)辯:通“辨”。
(3)請:通“情”。
(4)此句中“不而”當為“而不”。
(5)術:通“述”。
(6)允:誠實。惟:於。
(7)防:此處為“放”。星:當為“心”。
(8)增:此處當為“憎”。
(9)於去發:當為“太子發”。
(10)惡乎:發語詞。
(11)帝:當作“商”。
(12)雖毋:發語詞。蕢:當作“實”。
(13)使:依王念孫說為“從”意。
(14)共:依王念孫說當為“失”。抎:拋棄、墜落。
譯文
墨子說:“凡發表言論,則不能不先立標準再說。如不先立標準就說,就好象把測時儀器放在運轉的陶輪上。我認為雖有早、晚的區分,但必然終究得不到一個確定的時間。所以言論有三條標準。”
什麼是三條標準?答道:有考察的,有本原的,有實踐的。怎么考察呢?考察先代聖王的事跡;怎么推求本原呢?要推求眾人聽見所聞的實情;怎么付諸實踐呢?於治國中當作政令,觀察萬民來評論它。這就是三條標準。
所以古時候三代的聖王禹、湯、文、武,剛主持天下政事時,說:必舉拔孝子而鼓勵侍奉雙親,尊重賢良而教導人們做善事。所以公布政令實施教育,獎賞善良懲罰凶暴。認為這樣,混亂的天下,將可以得到治理;危險的社稷將可得到安寧。如果認為不是這樣,古時桀時的混亂,湯治理了;紂時的混亂,武王治理了。那個時候,世界、人民都沒有改變,君王改變了政務而人民改變了風俗。在桀、紂那裡則天下混亂,在湯武那裡則天下治理。天下得到治理是湯武的功勞;天下的混亂是桀紂的罪過。如以此來看,所謂安、危、治理、混亂,在於君上的施政;那么怎么可以說是有命呢?所以古時禹湯文武剛開始在天下執政時,說:必須使飢餓的人能吃上飯,寒冷的人能穿上衣服,勞作的人能夠休息,混亂的得到治理。這樣他們獲得了天下人的讚譽和好評。怎能認為是命呢?應該認為是他們的努力啊。賢良的人,尊重賢人而喜好治國的啟發方法,所以上面得到王公大人的獎賞,下面得到萬民的稱譽,這就得到天下人的稱譽好評。怎能認為是他們的命呢?也是他們的努力啊!
然而今天主張“有命”的人,不知是根據從前三代的聖人善人呢?還是
從前三代的凶暴無能的人呢?如從他們的言論來看,則必定不是從前三代的聖人善人,一定是凶暴無能的人。
然而今天以為有命的人,從前三代暴君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於那時不改正聲色的欲望,而放縱他的內心的邪僻。在外驅車打獵射鳥,在內耽於酒和音樂,而不顧他的國家百姓的政事;過多地作無用的事,殘暴地對待百姓,於是失去了國家。他們不這樣說:“我疲沓無能,我不努力地聽獄治國。”一定說:“我命里本來就要失國。”即使是三代疲沓無能的百姓,也是這樣。不能好好地對待雙親君長,很嫌惡恭敬儉樸而喜好簡慢粗陋,貪於飲食而懶於勞作,衣食財物不足,所以自身有饑寒凍餒的憂患。他們不這樣說:“我疲沓無能,不能努力地勞作。”也說:“我命里本來就窮。”從前三代的虛偽的人也是這樣。
古時暴君編造這些話,窮人複述這些話。這些都是惑亂百姓、愚弄樸實的人,先代聖王對此感到憂慮,在前世就有了。所以寫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雕在盤盂上,流傳給後世子孫。說:哪些書有這些話?禹時《總德》上有,說:“誠信不到達天帝,就不會保佑下民。既然放縱自己的兇惡的心意,天帝將會懲罰的。不謹慎而喪失了德,天命怎會保佑呢?”《仲虺之告》說:“我聽說夏人假造天命頒布於世,上帝痛恨他,因此使他喪失了軍隊。”他無中生有,所以叫假造;如本來就有而說有,怎么是假造呢?從前桀主張“有命”行事,湯作《仲虺之告》以批駁他。《太誓》中太子發說:“啊呀君子!天有大德,它的所為非常顯明。可以借鑑的不太遠,殷王就是:說人有命,說不必恭敬;說祭祀沒有好處,說凶暴沒有害處。上帝不保佑,九州都亡滅了。上帝不順心,給他降下滅亡的災難。只有我周朝,接受了商的天下。”從前紂主張“有命”而行事,武王作《太誓》太子發反駁他。說,你為什麼不向上考察商、周、虞、夏的史料,從十簡之篇以上都沒有命的記載,將怎么樣呢?
所以墨子說:“現在天下君子寫文章。發表談話,並不是想要使其喉舌勤勞,使其嘴唇利索,內心實在是想為了國家、邑里、萬民的刑法政務。”王公大人之所以要早上朝,晚退朝,聽獄治政,整日分配職事而不敢倦怠,是為什麼呢?答道:他認為努力必能治理,不努力就要混亂;努力必能安寧,不努力就要危險,所以不敢倦怠。卿大夫之所以用盡全身的力氣,竭盡全部智慧,於內治理官府,於外徵收關市、山林、澤梁的稅,以充實官府,而不敢倦怠,是為什麼呢?答道:他以為努力必能高貴,不努力就會低賤;努力必能榮耀,不努力就會屈辱,所以不敢倦怠。農夫之所以早出晚歸,努力從事耕種、植樹、種菜,多聚豆子和粟,而不敢倦怠,為什麼呢?答道:他以為努力必能富裕,不努力就會貧窮;努力必能吃飽,不努力就要飢餓,所以不敢倦怠,婦人之所以早起夜睡,努力紡紗、績麻、織布,多多料理麻、絲、葛、苧麻,而不敢倦怠,為什麼呢?答道:她以為努力必能富裕,不努力就會貧窮;努力必能溫暖,不努力就會寒冷,所以不敢倦怠。王公大人若確信“有命”,並如此去做,則必懶於聽獄治政,卿大夫必懶於治理官府,農夫必懶於耕田、植樹、種菜,婦人必懶於紡紗、績麻、織布。王公大人懶於聽獄治國,卿大夫懶於治理官府,則我認為天下一定會混亂,農夫懶於耕田、植樹、種菜,婦人懶於紡紗、績麻、織布,則我認為天下衣食財物,一定會不足。如果以此來治理天下,向上侍奉天帝、鬼神,天帝、鬼神必不依從;對下以此來養育百姓,百姓沒有得到
利益,必定要離開不能被使用。這樣於內守國則不牢固,出去殺敵則不會勝利。所以從前三代暴君、桀、紂、幽、厲之所以國家滅亡,社稷傾覆的原因,就在這裡啊。
所以
墨子說:天下的士人君子,內心確實希望為天下謀利,為天下除害,面對‘有命’論者的話,不可不努力批駁它。說道:命,是暴君所捏造,窮人所傳播,不是仁人的話。今天行仁義之道的人,將不可不仔細辨別而努力反對它,就是這個啟發啊。
作者簡介
墨子(前468 -前376),名翟(dí),春秋末戰國初期宋國(今河南商丘)人,一說魯國(今山東滕州)人,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社會活動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創立墨家學說,並有《墨子》一書傳世。
《
墨子》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記載墨子言行,闡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稱作墨辯或墨經,著重闡述墨家的認識論和邏輯思想,還包含許多自然科學的內容,反映了後期墨家的思想。在邏輯史上被稱為後期墨家邏輯或墨辯邏輯(古代世界三大邏輯體系之一,另兩個為古希臘的邏輯體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學);其中還包含許多自然科學的內容,特別是天文學、幾何光學和靜力學。
非命背景
中國古代哲學中把天當作神,天能致命於人,決定人類命數。“天命”說早在殷周時期已流行。從古器物發掘中所見到的甲骨卜辭,彝器銘文,“受命於天”刻辭的不只一次出現,說明早在殷周時期,天命觀就已經在人們的頭腦里紮根了。
這用《易經》的話來說,叫做“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對於這裡的命,後人注釋道:“命者,人所稟受,若貴賤天壽之屬也。
在古人的思想觀念中,人們的富貴貧賤、吉凶禍福,以及死生壽夭、窮通得失,乃至科場中舉、貨殖營利,無一不取決於冥冥之中非人類自身所能把握的一種力量,即命運是也。
命運的觀點,在古代源遠流長。由夏經商曆周,至春秋時,孔子弟子子夏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可見孔門弟子是信奉命運的。孔子進一步指出:“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宋國的桓魑有一次想謀害他,孔子聲稱:“天生德於予,桓魑其如予何”(同上)!
總之,在孔子看來,一個人的生死存亡、富貴貧賤完全與高懸於天的命運有關,絕非塵世碌碌眾生的力量所能改變。故孔子又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日》)。
儒家祖師爺孔子是位極度信命的老夫子。按理說,孔子是個知識淵博的大儒,對於人類社會有著深刻的認識,怎么就會信起命來呢?原來,他早年風塵僕僕,奔走列國,到處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很想乾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可是到了後來,當他碰了一鼻子灰以後,才深深地省悟到,命運之神竟是如此這般的厲害,然而這時他已是個五十左右的人了。“五十而知天命”,就是他從不知命到知命這一思想轉化過程的最好說明。與此同時,他不僅“知命”,他和他弟子還不遺餘力大肆宣揚“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君子屬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的思想。這裡他的說教是,一個人的生死貧富,都是命里早就注定了的,作為一個君子來說,非得知命不可,否則就夠不上做“君子修的資格。正因為君子是“知命”的,所以他能安分守己,服從老天爺的安排,但是小人卻不這樣,他們不肯聽從天命,往往冒險強求,希望有幸,意得個好結果。
當然,看問題也不能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孔子袋語》記錄孔子的話說:“古聖人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我孔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這裡,他認為賢和不肖是根據才華來劃分的,乾和不乾是人們自己可以把握的,至於機遇好和不好,是時間的問題(既在對的時間遇到錯的人;或在錯的時間遇到錯的人;或在對的時間遇到對的人;或在錯的時間遇到對的人),而是死還是活,那就只得看老天的旨意了。
作為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
孔子的這種天命思想,又在後來大儒孟子身上得到了新的反映。《孟子·萬章》上篇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意思就是,沒有人叫他乾,而他競幹了,這就是天意,沒有人叫他來,而他競來了,就是命運。同時他還舉例說明,堯、舜的兒子都不肖,是因為舜、禹為相的時間太長.所以堯、舜的兒子不有天下;禹的兒子啟賢能,而禹為相的時間義短,所以啟能得到天下。以上這些,都不是人力所為而自為,不是人力所致而自至。從理來說,這屬於天意,對人來說,這屬於命運。天和命。實在是一致的。在《孟子·盡心上》中,孟子還說:“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說:“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年n會善不吉亞粵健'下 尺甘;首而而芒.幣會十h.坯地環老.非幣等待天命,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後者是說,天底下人的吉凶禍福。無一不是命運,只要順理而行,接著的就是正命。所以懂得命運的人不站立在有傾倒危險的牆壁下面。因此,盡力行道而死的人所受的是天的正命,犯罪而死的人所受的不是天的正命。這裡,孟子雖然認為天命的力量無可抗拒,但是不管怎樣,我還是應該按照我的仁義而行,不能無緣無故地白白送死。無疑,這對孔子的天命觀來說,有著補充的一面。此外,
先秦諸子信命的還很多,而以儒家的勢力為最大。
天命觀經過先秦學者的一陣鼓吹,其時從上到下。從統治者到平民百姓,信命的風氣一時很盛。早在殷商時期,當時的統治者們,就已習慣於在每做一件事之前,總要先占卜一下天意如何,是凶是吉?後來,又由於人與天地相應觀念的影響,更使得人們普遍認為,整個天下的命運和每個個人的命運,都和天時星象有關。《周禮·春官》記載:“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這是說馮相氏和保章氏,是專管歲時星象,並從而窺探命運從而推測人間吉凶禍禍福的一種職官。
命數,這是一個複雜而重要的概念。郭志誠等對數有一段很好的論述:“人為自然界天與地作用的產物,人在天地間生存、運動;宇宙萬物都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人、天、地及
宇宙萬物的運動無一不受著一種數的制約。古人認為,對這種數,人們可以通過卜筮等術數手段,得到神的指點和啟示,感知和認識它。”數是宇宙本質現象在度上的規定,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它是有形的,也是無形的,它是點和線,也是波和場。它是數字的學問,也是哲學的學問。它是清晰的,也是模糊的。
唐代大儒劉禹錫在《天論》中認為數是事物內部的聯繫,凡物必有數,由數可以得理,順乘其勢。他說:“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併,必有數存乎其問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傾。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又云:“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人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可見,數是考察事物的著眼點,通過數的分析,可以知道事物的發展趨勢。
在孔子的學說中,還保存有“天命”的觀點。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中,知道了
樂天知命,才被稱為君子。夫子到五十歲明白這個道理,一切通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