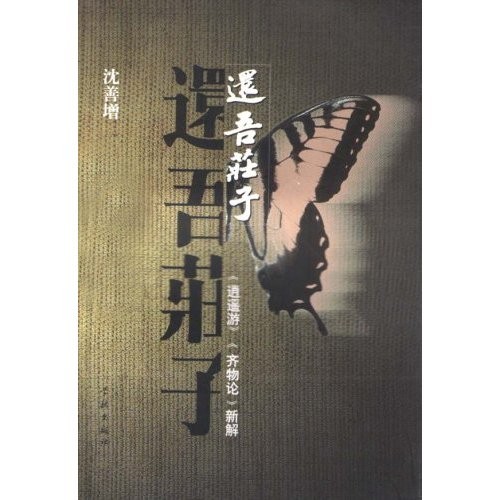《還吾莊子》以現代人的觀點全面闡述了《逍遙遊》和《齊物論》,全書知識豐富,解說詳盡,通俗易懂,不失為一本讓人覺得不得不看之書。
基本介紹
- 書名:還吾莊子
- 作者:沈善增
- ISBN:9787806680087
- 頁數:470
- 定價:28.00
- 出版社:學林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1年6月1日
- 裝幀:平裝
圖書信息,內容簡介,目錄,
圖書信息
書名: 還吾莊子
作者: 沈善增
出版社: 學林出版社
書號: 9787806680087
發行時間: 2001年6月1日
地區: 大陸
語言: 簡體中文
內容簡介
讀中國書不能不讀《莊子》,不能不讀《逐吾莊子》。以前讀一些講解佛經的著述,開篇都是從解題著手,而且,從總到分,洋洋灑灑要講一大篇。一個詞一個詞地落實、引申,一個經題可以做成一篇博士論文,覺得這樣非常煩瑣。因此,我第一稿注《逍遙遊》時,是沒有題解的。但實際注下來,發現直接切入正文,效果也未必佳。古人解經從題目著手,自有他的道理。尤其是我這次移宮換羽,改走一本正經以莊注莊的路子,考慮再三,還是走這條老路,才是終南捷徑。因為從解題進入,至少有三條好處。
首先,可以看到,《莊子》一書,是作者精心寫成,而非由後學輯錄而成。
《莊子》,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共有五十二篇。到晉代的司馬彪注本,計有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合五十二篇。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最早注本——郭象注本,只剩下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合三十三篇。少掉的十九篇,不是郭象沒看到,而是被他認定不是出自莊子之手,有損莊子大家形象而刪去的。在兩晉時代,對五十二篇中哪些是莊子寫的,哪些是後人輯錄的,哪些是不肖之徒假借莊子名義偽托竄入的,各家意見很不一致。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內篇七篇一定出自莊子本人之手,是他老人家一字一句摳出來的,而不是別人根據他的談話記錄整理而成的。形成這條共識的一條充足的理由,就是七篇的題目。七個題目統一都是三個字,而且這三個字明顯是根據整篇的中心思想概括擬就的;不像外篇與雜篇,隨取篇首的二或三字為題。外篇與雜篇的取題法,完全因襲《論語》的作派。《論語》是後人輯錄的,所以各家據之懷疑外篇與雜篇中也有部分甚或全部是後人輯錄的。但不管怎么說,反過來可以證明內篇是莊子親自動手寫的。
然而這點共識,到近代還是有人提出質疑。齊思和在《莊子引得)的“序’中說:“至於內七篇,則從來學者,皆以為莊周所自撰,疑之者尚鮮。成玄英疏序云:‘內篇理深,故於篇外,別立篇名。外篇以去,即取篇首二字為題。故陳景元曰:“內七篇目,漆園所命也。”’今按,內七篇目是否為莊子所自定,固難質言,而其著述體例,與外篇雜篇,截然有別,則極明顯。以梁任公之好辨古書,亦謂:‘內篇為莊子自作,無問題。’然余觀《齊物論》篇稱:‘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施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莊周乃惠施之友,若是篇果莊所自為,安得列惠施於古賢之林耶?又《逍遙遊》、《齊物論》、《德充符》等篇,皆於篇末附記莊周軼事,亦不似莊周所自為者。再以著述之體裁觀之。戰國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章學誠已言之矣。最早之私人著述,若《論語》、《孟子》等書,皆用問答之體。殆出於門人後學所記。後儒往往分為篇章,以便誦習,即以篇首二字名其篇。若夫先立一題,然後執筆著論,如《荀子)、《呂氏春秋》、《韓非子》等書,則戰國末年之事。是則內七篇,殆亦後學所述,未必即出於莊周之手歟?”
之所以把齊思和先生這段話引在這裡,是因為我覺得此中很典型地透露出一種習氣,以疑古為能事。這種動輒把不合己意的篇章語句指為後人偽托竄入,乃至抓住幾條就把整本書定為偽書,我在讀注莊各家乃至先秦諸子的注本時,經常碰到。開始對這樣做學問的先生很有些敬畏感,因為他們說起話來指手畫腳的腔調,實在是權威得很,你不服還真不行。像齊思和先生這么質疑,是算謙虛得不得了的。讀他們這些論斷,常感到非常慶幸,沒有他們火眼金睛指出來,自己被偽“莊子”騙了賣了還不知道,多么危險啊!等到後來我按照他們的指點,感到莊子的話怎么越讀越糊塗,才發覺事情似乎有些不對頭。我好不容易決定不理這些權威人士,從另外的途徑去解《莊子》。待我總算從他們布下的八卦陣中走出來,接近了本來的莊子,我才明白那些權威意見除了別有用心的篡改外,大多是由他們的一孔之見發出的自說自話。
就以齊先生質疑內篇非莊子自作的三條理由來說,都是站不大住腳的。
其一、莊子與惠施是朋友,他怎么會把惠施列到“古賢”中去?
從《莊子》中看,兩人確實是朋友,但《徐無鬼》篇中有莊子過惠子之墓,發出傷心感慨的片段。所以莊子在《齊物論》中把惠施與昭文、師曠並稱為“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完全有這可能,莊周為什麼不可以在惠施死後才開始著書立說呢?而且,惠施死了,莊子失去了探討辯論的對手,才把求道熱忱化作筆底波瀾,也是順理成章的。至於說莊子這段話是“列惠施於古賢之林’,那是齊先生的誤解所致。以我看到的注莊各家,沒有一個弄明白莊子為什麼在這段話里要把昭文、師曠與惠施並舉。齊先生就想當然地把三者的共同點理解為“賢”了,其實與“賢”是不搭界的。到底共同點是什麼,以後注到時再詳說,這裡賣個關子。此外只需說明,“賢”乃妄測,遑論“古賢”,齊先生的質問落了個空。
在莊子時代,陰陽五行學說才初露端倪,還沒有發展為繁複的系統理論,所以,後面的六種意見,因其太系統、太全息、太數理化,顯見不會是莊子所言之“六氣”。從莊子說“六氣”不加任何解說來看,這“六氣”應該是當時流行的一個概念。考察一下,只有司馬彪的說法可能性最大。此說又有《左傳·昭元年》所載醫和之言可作佐證。《莊子》中還有一處提到“六氣”,見於《在宥》篇:“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從這段話中看,“六氣”不是“天氣”與“地氣”,故而李頤、王逸把“天玄”、“地黃”列入“六氣”之中是不對的;但是,前有“天氣”、“地氣”,後有“四時”,可見“六氣”又與氣候有關,所以,“陰,陽,風,雨,晦,明”等可見的天象氣候變化為“六氣’的內容,也是很妥貼的。從這段話可見,古人對天象氣候,有幾種不同的分類法。“天氣”、“地氣”是一種分法,重在空間的廣大、對萬物的涵養。“四時”是一種分法,重在周期性的變化。“六氣”又是一種分類法,重在現象的區別。“天地”強調根本性,“四時”強調周期性,“六氣”強調現象特性。“天地”為體,“四時”為常(也即體的必然表現),“六氣”為用(體的偶然表現,儘管在偶然背後隱藏著必然,偶然性受到必然性的制約,但表現出來,不易看見規律性,像是一種意志行為)。故而,“乘天地之正”後面,不能說“御四時之辯”,而只能說“御六氣之辯’。這兩個分句,照佛家之言來說,“乘天地之正”就是證體,就是禪宗所說“明心見性”,密宗所說“胎藏部”、“蓮花藏”;“御六氣之辯”就是致用,就是顯教而說“普度眾生”,密宗所說“金剛部”、“金剛地’。如果要加個“四時”進去,只能是“通四時之變”。“六氣’中“陰陽”、“晦明’可以互變,“風雨”是相成而不一定能互變,“陰陽”、“風雨’、“晦明”之間則沒有什麼必然聯繫,因此,這個“辯”,只能訓為“別”,釋為“變”是不確切的。
只有“乘天地之正”,才能“御六氣之辯”,前者是必要條件,後者是可能結果。而這兩者,又構成“游天窮”的必要條件。“游無窮”才是莊子追求的目標,才是得道的理想境界。這才是“逍遙”。達到“逍遙’的才可稱為“至人”。至人已證大道,已起大用,已得大自在,像這樣的人,他還會受到什麼條件的限制呢?“彼且惡乎待哉?”
“待”也是莊子的語彙系統中一個重要的概念。《說文》:“待,埃也。”段玉裁註:“今人易其語日:‘等’。”從“等待”這原初義,引申出“依靠,仗恃”之義。因為”等待”必須站在一個地方守候著,這個立足點,也就是立場,由立場引出了憑恃。《商君書·農戰》:“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又由“依仗”之義,引申出“需要、必須”之義。《韓非子·五蠹》:“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莊子就是在“依仗”與“必須”之義上使用“待”的,可意譯為“立場”與“條件”。在譯為“條件”時,應考慮到其中蘊有“立場”的意思,這“條件”是指有關“立場”、“依據”的重大條件。“彼且惡乎待哉?”以佛家用語說,就是:“那人還有什麼相可執著呢?”
為什麼說能“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即可“無待”呢?因為達到這一境界,個體就與本體(道)完全同一了,他的自由度等同於道,是無窮大的。無窮大的個體,也就等於個體的消亡,因此,才可以說是“無我”。而這個“無我(小我)”的”我”,才是真正的“我”。因為“我”的本義是“主宰”,也就是自由意志。只有具有無窮大的自由意志,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這樣的自由意志,沒有一絲一毫不自由之處。
需要指出的是,東方哲學,佛家與道家,從一上來就明確這自由意志不是西方神學所謂的“全知全能”,為所欲為。在《序》中我已引過元圭禪師的“佛有三能三不能”之說。這裡,莊子也確立了“游無窮”的邏輯關係,以“乘天地之正”為前提。因此,如果一定要用“唯物’與“唯心”的二元對立來套,那么,佛家與道家都可以統戰進來壯大“唯物主義”的陣營。因為他們都認為有獨立於主觀意識之外的客觀規律存在,都認為覺悟者就是完全能窮盡、順應、掌握這些規律的人。當然,用“唯物”、“唯心”這樣的理論框架來套佛家與道家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因為東方哲學與西方哲學的立場、觀點、方法都有很大的不同,簡單類比,無助於弄清其本來面目,只有越抹越糊塗。我們還是以了解莊子的原意為目的。
以上說了我對莊子這幾句話的註解,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郭象是怎么注的。
“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游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
目錄
第一章 逍遙遊
題解
鵬飛南徒
堯讓天下於許由
藐姑射之山
樗與狸狌
第二章 齊物論
題解
今者吾喪我
*缺問王倪
瞿鵲子問長梧子
罔兩問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