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1947年農曆十一月初六出生於江蘇省
豐縣趙集村,豐縣趙集村現有趙本夫故居,其兄弟還居住在趙集古村,趙集古村是一座有五百年歷史的古集,是北宋趙抃的後裔。趙集古村至今還保留祖輩傳下來的的古樸傳統,其村民風淳樸,互幫互助,趙集古村這片大地哺育了趙本夫。1961年由本村國小考入豐縣中學,1967年高中畢業後回村務農。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作協專業作家。
1971年3月參加工作,在縣委宣傳部任新聞幹事十年,1980年調入縣廣播站任編輯,1981年發表處女作《賣驢》獲當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3年調縣文化館從事文學創作,1984年三月考入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後改名
魯迅文學院)。1986年畢業後又考入
北京大學作家班,次年轉入
南京大學,1988年大學本科畢業。
1985年調入江蘇作協任專業作家,1986年初當選為江蘇作協副主席,之後又在
豐縣掛職縣長助理並任徐州市文聯主席,1990年被任命為江蘇作協專職副主席。現為
江南詩畫院顧問。

趙本夫先後發表作品二百多萬字,以小說為主。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
刀客和女人》、《
混沌世界》、《
黑螞蟻藍眼睛》、《
天地月亮地》,小說集《
寨堡》、《
空穴》、《
走出藍水河》;短篇小說《鞋匠與市長》。作品被翻譯成英、俄、日、挪威、泰等多種文字,收入國內外四十多種選集。現為江蘇省作協專職副主席,《鐘山》雜誌主編,一級作家,享受國務院津貼的江蘇省優秀中青年專家。
由他的短篇小說《
天下無賊》改編的同名電影獲得巨大反響;他的長篇《刀客與女人》改編成電視劇《
走出藍水河》,已經在各地熱播;趙本夫擔任編劇的二十五集電視劇《
青花》也已經開始在北京等地播出。
人物特點
《
天下無賊》是1999年的作品,
馮小剛,2001年前後從峨影手中購買到了改編權。對於原作和影視之間的差異問題,趙本夫曾經有名言說:"小說是我的,電影是馮小剛的。"言下之意,改編權已經給了人家,怎么改,是對方的事情。趙本夫說:既然同意改編了,就要明白,導演會有自己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詮釋。小說是文字的語言藝術,電影是綜合的藝術,所以導演、演員的表現甚至製片方的投入,都會影響到它最終的面貌。作家應該有思想準備-電影可能拍得很漂亮,也可能會有這樣那樣的缺憾。
 電影《天下無賊》
電影《天下無賊》為人低調的江蘇省作協專職副主席趙本夫最近走進了媒體的視野:他的短篇小說《天下無賊》被馮小剛改編成電影,很快就要開機;根據他的長篇小說《刀客與女人》改編的電視劇《
走出藍水河》去年11月在湖北首播,不久將在北京乃至全國播出。對於《天下無賊》過於理想化的劇情,趙本夫昨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天下無賊》近乎一個美好的童話,是個肥皂泡。
葛優向馮小剛推薦《天下無賊》
馮小剛拿到《天下無賊》電影劇本著作權可謂曲折。趙本夫透露,《
天下無賊》最早是葛優媽媽向葛優推薦,然後葛優推薦給馮小剛的,
電影著作權方面最早是
北京電影製片廠聯繫的,已經達成意向了,但那時馮小剛手中有別的劇本,於是這個事情就擱下了。馮小剛最後是從峨嵋電影製片廠重新拿到《天下無賊》劇本的。趙本夫說,與
北影廠簽訂著作權的事暫緩之後,該廠一位領導調任峨影廠當廠長,項目就轉到了峨影廠並通過峨影廠下面的一個公司和趙本夫簽了
著作權轉讓契約。這時馮小剛又找到趙本夫,得知著作權已經被峨影廠購買了之後只好等著,“峨影廠在改編時碰到一些障礙,做不下去。經過協商,他們同意將著作權轉給馮小剛。”
《天下無賊》改編成電影難在內心戲很多
趙本夫介紹,《
天下無賊》1999年發表在《作家》上,還獲得了第八屆小說“百花獎”。2002年,馮小剛曾經想請趙本夫改編劇本,但當時趙本夫要隨中國作協代表團出訪美國沒有時間。於是,馮小剛自己親自改編,“從一個短篇小說改編成電影,馮小剛的工作量很大。”趙本夫說。馮小剛曾表示,《天下無賊》在關照人物內心上要下更大功夫,希望能讓更多人看了以後不僅僅是一笑而過。趙本夫昨天也說,小說里內心戲比較多,有不少寫內心的細節,這點在電影表現上是難點。
《天下無賊》目前在甘肅夏河選景,這符合趙本夫原來的想像嗎?趙本夫說,小說里的故事情節主要發生在西部和火車上。江蘇土生土長的趙本夫能把西部寫好嗎?趙本夫解釋說:“我去過西部。但文學主要靠想像,靠虛構,那么多生活不可能都經歷過。”《
天下無賊》的男主角已經由最初的周星馳變為葛優,哪一個更加符合趙本夫筆下的人物呢?趙本夫說自己對影視娛樂並不是很熟悉,但認為周星馳比較善於搞笑,而葛優比較有潛質,同時他也表示,“尊重馮小剛的勞動,不會幹涉。”
《天下無賊》是個近乎完美的童話
趙本夫對記者說,自己對《天下無賊》整體比較滿意,“無論結構還是語言都不錯。”趙本夫說。首先是小說的名字起得比較妙、比較打眼;其次是作品的立意比較好,給改編提供的空間比較大。和趙本夫的滿意相比,不少人卻批評《天下無賊》的故事過於理想化。雖然如此,但他認為電影出來之後在這點上不會引起很大的爭議,
“《
天下無賊》探討的是人靈魂的一種進化,呼喚的是一種美好的東西,作品的立意和走向才是值得關注的。”那為什麼要通過賊來呼喚美好的東西?趙本夫告訴記者,主要是想反其道而行之,有點
黑色幽默,“生活太複雜,某一個瞬間就可能讓一個人改變主意。《天下無賊》是一個近乎美好的童話,一個肥皂泡。”
趙本夫的聲音帶了點淡淡的江蘇
豐縣老家的鄉音,不疾不徐,遇到任何提問,都沒有情緒的大起大落。而在溫和之外,趙本夫總算承認,自己的性格其實很強悍,骨子強悍。“真正有修養的人,不是表面上的咋咋呼呼,沒有必要。作家的叛逆,不是一定要和誰過不去。行為裝束上的標新立異,是淺薄的。真正的強悍,不需要表面的張揚,你必須要有自己的堅持,我在生活中很隨和,但在某些觀點上,別人要想改變我,難。”別人無法改變的,首先就是他多年如一日的創作傾向。
趙本夫作品中的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三十年如一日。“對善惡的看待,不應單從法律的角度,還應該對人多一點深層的理解,應該立體地人性化地看待一個人。《
天下無賊》中王薄和王麗兩個賊,其實不是典型意義上專門謀財的賊,他們只是一對叛逆的年輕人,所以他們的身上,有著善良的因子,他們會被傻根這個小伙子的天真和質樸打動,才會千里迢迢護送傻根回家,演出了一幕天下無賊的童話。有讀者覺得兩個賊的轉變太快,其實我們的生活里,並不缺少這樣的例子--可能只是一個人的一句話觸動了你,它讓你的心瞬間感到溫暖,這時候,每個人都有做個好人的意願。”有鑒於此,趙本夫的作品裡,沒有十惡不赦,沒有顛倒糜爛,他的筆調三十年如一日的善良、敦厚、筋道、好看。常常在不知不覺中,感動了一個或者另一個。
 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在阿壩地區採風留影
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在阿壩地區採風留影趙本夫,對時下的評論界倒是有些看法:“新世紀以來,作家們都在各領風騷三五年,有些作品當時很紅,過幾年就不能看了。文學的確在面對外界的各種誘惑和干擾,但最關鍵的問題在於,作家要清醒,清醒你在乾什麼?寫作不是給領導看的,不是趕風潮的,那是你對生活的認識和感知。被更多的人喜歡當然很好,但是外人的評論也不必太在意。我對這些年的評論界,是不滿意的--我們缺少真正的評論家,動輒就是捧場、表揚。作為評論家,應該反問自己,有沒有自己的批評視角、批評體系?如今的很多批評就是書評,一樣的視點,泛泛而談內容、形式和不足。還喜歡歸類,給作家歸類,給作品歸類,歸類雖然很省事,但不準確,對那些並不屬於哪一類的作品,你還要生搬硬套,那能塞進去么?既然是批評家,那么,哪一部作品哪一個作家是你發現的?沒有那樣的發現,怎么能算得上合格的批評家。俄羅斯的大批評家們,就曾經扶植、發現了多少作者啊,沒有這樣的建樹,就不是真正的批評家。”

中國作家應該有這樣的信心--東方人能夠寫得過西方人,有這個實力。在"先鋒"派很紅的時期,許多有名的批評家就私下裡說,很多作品自己也看不懂,但不好意思說看不懂啊,說看不懂似乎意味著你沒水平,沒讀過那么多書。在文學創作領域,技術上形式上雖然也要講究,但更重要的還是精神的高度。"先鋒"派是正楷還沒練好就去狂草了,意識到了,跟在別人後面是沒有希望的,於是又回過頭來了。
不懂電腦——趙本夫是極少數的不懂計算機的作家之一,連簡單的打字都不會,家中老伴、女兒人人一台,連小外孫都會打字,只有趙本夫與之無緣。對此,他有充足理由,“網上雖然很精彩,但我不想受更多的誘惑,人不可能擁有所有的東西。”
 趙本夫
趙本夫夜半遇賊——《
天下無賊》只是個美好的願望和夢想,其實生活中當然有賊,趙本夫自己不但遇到過,還抓過。那是1976年初,唐山大地震,趙本夫在家鄉
豐縣的地震棚里,一天夜裡,有賊闖進來,趙本夫迷迷糊糊之間,慢悠悠地問賊:“你想幹啥?”賊被這樣鎮定的語氣嚇了一跳,倉皇逃跑,趙本夫爬起來拔腿追了出去,後來被夫人生生又拉了回來。
機械文“盲”——趙本夫對所有的機器都持敬而遠之的態度,因為覺得很麻煩,搞不懂。在家踩著椅子換燈泡,夫人每每手持竹竿站在一旁指點他,隨時準備給笨手笨腳的老公一點教訓。
小說作品
長篇小說
小說集
《
寨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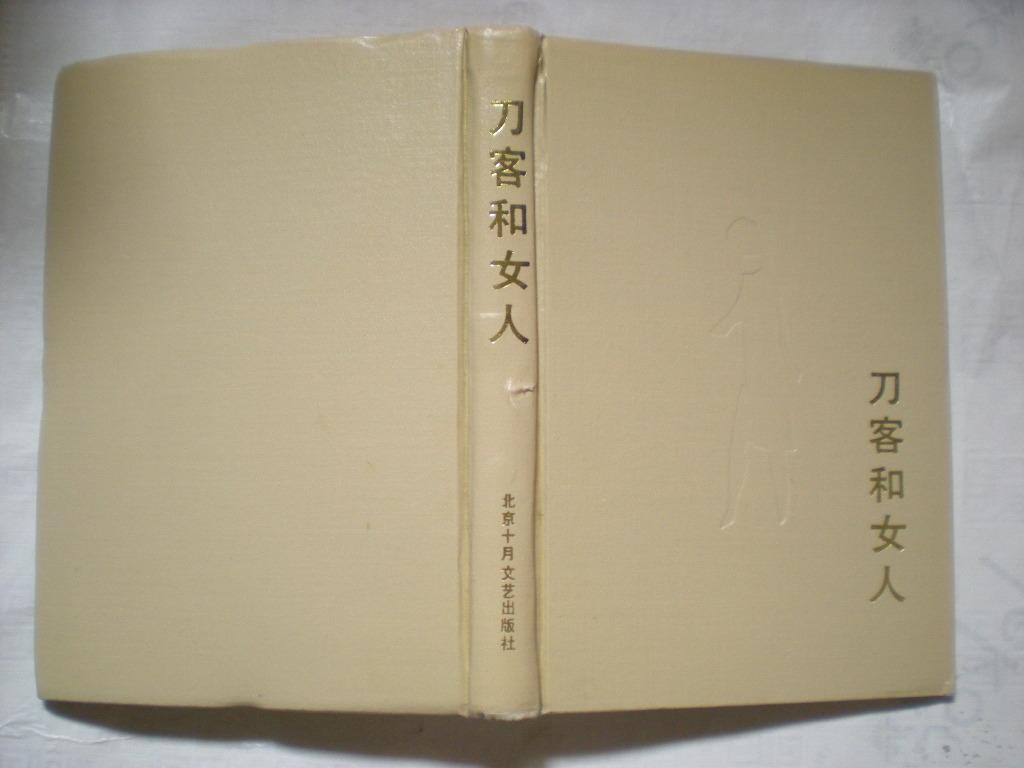 《刀客和女人》
《刀客和女人》短篇小說
《鞋匠與市長》
編劇作品
個人影響
趙本夫懷念
汪曾祺、
艾煊等一批文壇故人的文字,雖然簡短,但字字珠璣,真情四溢,能從中感受到趙本夫深埋心底的蒼涼和寂寞,也許,還有某種不足為外人道的苦澀承擔?趙本夫很坦然地敘述著自己的日常生活,對於文學思維和文學語言的堅持,對於公眾話語的獨立思考。說到自己小說風格的變化,趙本夫說近幾年又寫了兩部長篇小說,《
黑螞蟻藍眼睛》和《
天地月亮地》,是根據自己多年的生活積累和對童年生活的反覆提煉,在諸多自認為非常紮實的中篇小說的基礎之上,反覆醞釀,嘔心瀝血,精心創作的作品,這個系列涉及到人與土地、人與自然的關係這一宏大主題,這一系列最後要寫成四部,他用“地母”系列這一名稱來涵蓋這樣宏大複雜、多元斑斕的長篇組合,他正在撰寫的是第四部,第三部還在醞釀中。趙本夫的寫作還很傳統,仍舊堅持手寫,拒絕電腦,他說,面對稿紙,讓自己有一種親近感和寫作的莊嚴肅穆。創作不是碼字,趙本夫說,作品究竟是不是精品力作,是不是傳世之作,需要讀者的認可和時間的檢驗。大仲馬的東西那么好,影響力那么大,但在當時的法蘭西,卻被認為是不入流的下里巴人。也就是在席哈克當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內,大仲馬才被允許進入法國的
先賢祠,算是被確認為
法國文學的經典。如果我們耐不住寂寞,迫於這樣那樣的壓力,去迎合、緊跟各種風尚,結果時過境遷,短短的幾十年,作品都成了廢紙一堆,這樣的慘痛教訓,我們見到的還少嗎?趙本夫認為,作家要靠作品說話,但也未必是作品越多越好,首先是要保持一個作家應有的清醒頭腦來觀照這個大時代的滄桑巨變。趙本夫說自己的長篇系列不會急急忙忙的出手,慢工才能出細活,從從容容,不必為了什麼獎項。這樣的寫作,純粹,簡單,雖然辛苦,但是沒有額外的心理負擔,這種狀態,很好。
 趙本夫參加訪談
趙本夫參加訪談趙本夫的文學就這樣在不經意中給人以希望和力量。在他的筆下,沒有絕對的壞人,趙本夫總是願意從善良的角度去發掘人性的光輝,但這樣的善意的表達又絕對不是廉價生硬的光明尾巴。記得在一次其他作家的作品研討會上,趙本夫曾經說過,現在是一個多變的迅速轉型的時代,許多事情的發生令人無法用過去現成的理論框架來解釋,作為一個作家,面對這些潮起潮湧,更要有自己的悲憫情懷,他說到了一條
社會新聞:一個女孩子為了給父母治病而在媒體上刊發廣告出賣自己。他說,人間有許多類似的故事,藏在其間的人間冷暖和悲劇意味是值得作家們捕捉的。理解了趙本夫這樣的悲憫視角,就不難解讀他的又一部短篇小說《鞋匠與市長》,看上去是一個很小的切入點,但是卻蘊含著非常宏大的主題,兩個人最終的歸宿和結局又是那樣的意猶未盡,令人無限遐想。
 趙本夫在易卜生紀念館簽名
趙本夫在易卜生紀念館簽名趙本夫也會偶爾拿出一些小散文給讀者帶來次次驚喜。這些小散文,一改時下同類文體的無病呻吟花花草草,也不是故作高深、賣弄典故、兜售常識的所謂文化散文。趙本夫的散文貴在有情,他總是透過自己純樸的近乎白描的語言娓娓道來,讓人感受到文字背後傳遞的撼人心魄的力量!趙本夫生活中是位鐵桿球迷,對足球有很專業的見解,這是圈內人都知道的。但就在雅典奧運會期間,趙本夫卻有一篇獨闢蹊徑寫足球的小散文刊發在解放日報的《
朝花》副刊上,這個散文喚作《母親的奧運》,不到一千字的文字,寫他86歲老母親半夜起床對奧運進展的關心,寫母親對奧運冠軍樸實無華的讚揚,寫母親在奧運期間對全家人的照顧,讀這樣的散文能夠掉眼淚,能夠讓人們在乏味枯燥甚至是無聊的現實紛爭當中體會到一種最為本真的情感,最為無私的聖潔的慈愛,這樣的文字,誰能說還有很多?
趙本夫還身兼大型純文學刊物《鐘山》雜誌的主編,趙本夫雖然不過問具體的編輯業務,但是他卻以自己的敏銳目光和文學理想為這個文學重鎮盡著自己的心力,自己的本分。面對喧囂浮躁的文壇,五花八門的這樣那樣的主張,有形無形、急功近利的算計,經過反覆斟酌,趙本夫為雜誌提出了“原創、拒絕、遠行”的辦刊主張,看似簡單的六個字,每個詞組卻都可以寫出洋洋灑灑的
文學論文,每個詞組都滲透著一種守護文學精神的堅韌和孤絕。趙本夫坦言,這是一種我們對文學理想的期許,更是對自己的一種鞭策,也許永遠達不到這樣的高度,但是我們一直在努力!
作家心聲
土地在中國人心中的情結可能是一種自然本性。當人們把大地變成財富時,各種悲劇就發生了。歷史上的戰爭、殺戮、爭奪……都是想把大地據為己有。而當大地回歸自然,成為萬物的母親時,一切都美好起來。這其實是一個關於人類的話題。動筆之前趙本夫曾經多次回到故鄉感受大地的呼吸,也曾去西部荒野行走,城市與荒野的對比參照,讓一切都清晰起來。城市中的生命力卻很脆弱,充斥著傾軋、爭奪、緊迫感……而西部很貧窮,人們的幸福指數卻較高,生命變得很悠然。究竟哪種生活方式更適合人類呢?
 趙本夫
趙本夫趙本夫說敲響時代警鐘這句話特別對。這部長篇是自己人生所有的積累和思考。文明不可阻擋,文明是在建立一種秩序,隨著文明的發展,秩序越來越密不透風。但任何生命都是生而自由的,這就與秩序形成了矛盾。好比南方的盆景,我承認它是藝術,但從不喜歡它——動不動就修修剪剪,多一點枝節就得給剪掉,它長得該多難受?這是對生命本身的扼殺。對文明應該從另一個角度去想一想,確實到了該警醒的時候了。
趙本夫自小接受傳統教育,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是天然的。一個作家最大的使命就是寫出好作品,沒內容或者玩花樣是不可能的。一個作品,不在於你怎么寫,而是在於你到底寫了什麼。
相關內容
為人低調的江蘇省作協專職副主席趙本夫最近走進了媒體的視野:他的短篇小說《
天下無賊》被
馮小剛改編成電影,很快就要開機;根據他的長篇小說《刀客與女人》改編的電視劇《
走出藍水河》去年11月在湖北首播,不久將在北京乃至全國播出。對於《
天下無賊》過於理想化的劇情,趙本夫昨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天下無賊》近乎一個美好的童話,是個肥皂泡。
葛優向馮小剛推薦《
天下無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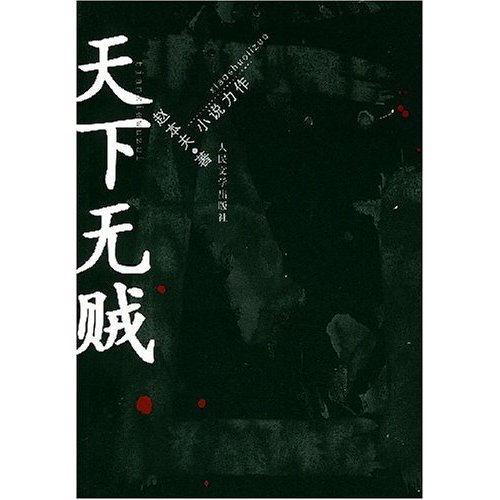 《天下無賊》
《天下無賊》馮小剛拿到《
天下無賊》電影劇本著作權可謂曲折。趙本夫透露,《
天下無賊》最早是葛優媽媽向葛優推薦,然後葛優推薦給馮小剛的,
電影著作權方面最早是
北京電影製片廠聯繫的,已經達成意向了,但那時馮小剛手中有別的劇本,於是這個事情就擱下了。馮小剛最後是從峨嵋電影製片廠重新拿到《
天下無賊》劇本的。趙本夫說,與
北影廠簽訂著作權的事暫緩之後,該廠一位領導調任峨影廠當廠長,項目就轉到了峨影廠並通過峨影廠下面的一個公司和趙本夫簽了
著作權轉讓契約。這時馮小剛又找到趙本夫,得知著作權已經被峨影廠購買了之後只好等著,“峨影廠在改編時碰到一些障礙,做不下去。經過協商,他們同意將著作權轉給
馮小剛。”
趙本夫介紹,《
天下無賊》1999年發表在《作家》上,還獲得了第八屆小說“百花獎”。2002年,馮小剛曾經想請趙本夫改編劇本,但當時趙本夫要隨中國作協代表團出訪美國沒有時間。於是,馮小剛自己親自改編,“從一個短篇小說改編成電影,馮小剛的工作量很大。”趙本夫說。
馮小剛曾表示,《
天下無賊》在關照人物內心上要下更大功夫,希望能讓更多人看了以後不僅僅是一笑而過。趙本夫昨天也說,小說里內心戲比較多,有不少寫內心的細節,這點在電影表現上是難點。
《
天下無賊》目前在甘肅夏河選景,這符合趙本夫原來的想像嗎?趙本夫說,小說里的故事情節主要發生在西部和火車上。江蘇土生土長的趙本夫能把西部寫好嗎?趙本夫解釋說:“我去過西部。但文學主要靠想像,靠虛構,那么多生活不可能都經歷過。”《
天下無賊》的男主角已經由最初的周星馳變為
葛優,哪一個更加符合趙本夫筆下的人物呢?趙本夫說自己對影視娛樂並不是很熟悉,但認為周星馳比較善於搞笑,而葛優比較有潛質,同時他也表示,“尊重
馮小剛的勞動,不會幹涉。”
趙本夫對記者說,自己對《
天下無賊》整體比較滿意,“無論結構還是語言都不錯。”趙本夫說。首先是小說的名字起得比較妙、比較打眼;其次是作品的立意比較好,給改編提供的空間比較大。和趙本夫的滿意相比,不少人卻批評《
天下無賊》的故事過於理想化。雖然如此,但他認為電影出來之後在這點上不會引起很大的爭議,
“《
天下無賊》探討的是人靈魂的一種進化,呼喚的是一種美好的東西,作品的立意和走向才是值得關注的。”那為什麼要通過賊來呼喚美好的東西?趙本夫告訴記者,主要是想反其道而行之,有點
黑色幽默,“生活太複雜,某一個瞬間就可能讓一個人改變主意。《
天下無賊》是一個近乎美好的童話,一個肥皂泡。”
趙本夫的作品改編成影視劇似乎總要經歷些磨難:《
天下無賊》第一次劇本沒有通過;而根據《刀客與女人》改編的電視劇為何要用趙本夫另一部小說的名字《
走出藍水河》呢?原來,一開始用《刀客與女人》申報時沒有通過,於是改名。“小說《刀客與女人》我寫的時候叫《
人間詞話》,出版社出於商業考慮改了書名”。現在電視劇卻幫他了卻了心愿,毛阿敏演唱的片尾曲就叫《人間詞話》。
 趙本夫
趙本夫和《
天下無賊》的理想化相比,電視劇《
走出藍水河》就比較凝重了:寫了從民國初建到“文革”結束這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主要是通過一個土匪的命運寫一種文化心態、人文心態,包括對‘文革’的反思”。雖然電視劇把“文革”部分加以改動,但趙本夫如此評價自己這部1985年寫就的小說,“這部小說我寫了十幾年,改編時並沒有增加內容。不追求時效性的主要目的是想藉此告訴讀者,我的小說賣的不是水而是血。”(劉江華)
日報評論
2008年12月23日。
北京華僑大廈,“《當代》雜誌長篇小說獎”評選活動現場。7位評審當場投票,從全年出版的一千多部長篇小說中遴選出5部“最佳”。結果,趙本夫的《
無土時代》以6票當選,這部作品是他寫了20年的生命之作。
讓人尊敬和喜歡的,是他雖然文名官名都響亮,可他為人行事一向低調,不艷慕榮華富貴,不喜歡誇誇其談,不露面於大庭廣眾……他屬於那種真正的好作家。
他的名字不如“傻根”來得響亮
在當今這個e時代,還真不能否認影視對文學的“提攜”作用,儘管大多數作家對之擺出了一副有點嫉恨又很艷羨的“酸葡萄”身段。 有了電影《
天下無賊》,趙本夫才真正為大眾所知曉。其實他出道甚早,在新時期文學繁榮階段就嶄露頭角,短篇、中篇、長篇小說屢屢發,地方、中央乃至全國小說獎一一得,由此也早就坐上了江蘇省作協專職副主席的交椅,享受著副廳級待遇。不過,老百姓才不管你是處級作家、廳級作家還是部級作家,他們看的是你的作品,品評的是你的人物,所以,“趙本夫”的名字還是不如“傻根”來得響亮。
《天下無賊》本是趙本夫的中篇小說,發表後在文學界得到了一些喝彩,之後也就“輕舟已過萬重山”,直到導演馮小剛將它搬上銀幕,一下子變得大紅大紫。傻根是《天下無賊》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帶著打工掙來的血汗錢回家的農民工,更是一個涉世未深、帶著一副純真無邪眼光看世界的憨厚青年。這樣一個可愛形象經過電影螢幕浪漫主義的放大,得到了廣大觀眾的共鳴。這也正好體現出趙本夫寫作的初衷——調動起廣大人民民眾內心的善良品質,使社會群體精神向著真善美的境界努力行進。
所以,自從電影《
天下無賊》大紅大紫之後,趙本夫嘴裡多了一句話:“小說是我的,電影是馮小剛的。”每當人們向他“歌功頌德”之時,他就認真地來上這么一句。而此時,他對自己說的另外一句話是:“你的任務是寫好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 他的頭腦始終保持著清醒。
他越來越深地把自己藏起來,藏到工人、農民、市民中,藏到避開文壇,過普通老百姓的平常日子,甚至藏到離開城市,回歸鄉土,回到大自然……
於是,就有了他的新書《
無土時代》。趙本夫說,迄今為止,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最鐘愛的一部長篇小說。
他最關注和憂慮的
《無土時代》是趙本夫長篇小說“地母三部曲”的最後一部,也是最難寫的一部。
“地母三部曲”是趙本夫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自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創作,1995年出版了第一部《
黑螞蟻藍眼睛》,1997年出版了第二部《
天地月亮地》。自此之後,這第三部可難倒了他,以至於幾年裡都不敢“輕舉妄動”。
從1997年到2007年,10年間,他多次啟筆,又不滿意而放下。有一次甚至已經寫了20萬字,還是覺得不行,最終把它們全部廢掉了——20萬字呀,那是多么巨大的勞動,天天起五更熬半夜不說,家裡人都跟著懸著心,亦愁,亦憂,亦喜,亦怕(趙本夫自己不用電腦,全憑手寫,然後是夫人替他打字。夫人賢惠,就是為了給他打字才學會電腦的)。20萬字,原子筆磨光了十來桿,手指上磨出了繭子,更何況煎心熬神的心力腦力呢!漫長的10年,3600多個日日夜夜,這部作品成了趙本夫的心病,壓得他喘不過氣來,“我情緒上經常是陰的,感覺很不快樂”。
他用田園牧歌對抗e時代
他從小生活在徐州
豐縣一個有著600年歷史的古村趙集,並在那裡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直到1984年才到南京定居下來。他家祖上是當地的大家族,曾經擁有不少土地,但到上世紀40年代逐漸衰落破敗。趙家的衰落過程有點與眾不同,不是家族子孫不肖揮霍,也不是無能經營,而是家人一次次被綁票,爾後一次次“割地賠款”,單是他父親就被綁過兩次。這些綁架、殺人與自殺的血淋淋事件,在他少年時代一次次遭遇到,並由此構成了他生命底色的灰色調,他覺得自己從來就沒有過童年,內心裡是非常憂鬱的。
儘管已進城多年成了城裡人,他還是留戀農村。他留戀農村那種人與人之間親密無間的關係,不喜歡城裡人老死不相往來的淡漠。他喜歡土地上的無限生機,那混合著牛嘶馬叫和莊稼拔節生長的熱鬧與嘈雜,經常讓他陷入回家的衝動。他也讀了不少書,包括中西方思想家對城市文明以及鄉村簡單生活的思考等等,這些思想火花點燃了他的“原始鄉村記憶與情感”,使他越來越從感性的“鄉村”理想,演繹為自覺守護“鄉村”的意識。
從外表看,趙本夫方臉闊眉,五官非常周正,臉上總是掛著一副厚實、又帶著憂鬱的神情,穩重得像一座北方的大山。平日的他一向節語、戒躁、勤懇、寬厚、忠誠,是一位兄長式的完全可以信賴的朋友。當然,大半生的豐富經歷,也使他積累了成熟的人生經驗,自信地面對世界,所以他走上江蘇省作協的領導崗位也是順理成章、受人擁戴的。然而從另一方面說,他的腦海里又經常涌動著許多不可思議的奇異浪花,有時天真得像個孩子。
趙本夫雖然憂鬱,然而並不悲觀。憂鬱是少年時代的印跡,一個人的少年印跡是永恆的,一生都很難改變;但它不會遮蔽成長以後的成熟,也不應該成為不斷躍上新高度的阻礙。已經人到中年的趙本夫,在說他是個理想主義者的同時,也微笑著展示出自己對世界樂觀的一面,他說,今天是最好的時代,我很慶幸自己趕上了。
他曾走進一個牧民家的帳篷。這是一個四口之家,夫妻倆帶著一兒一女,加上一頭奶牛,四口人輪流放這頭牛。家裡不富裕,用城裡人的標準看相當貧寒,可是對素不相識的客人趙本夫,主人拿出了最好的食物,像親人一樣貼心地招待。
在塔克拉瑪乾大沙漠腹地,他跟著主人走路,行進中吃了一個西瓜。他隨手把西瓜皮扔了,卻被主人撿回,精心地扣著放在地上。主人解釋說,這是沙漠的規矩,留給未來的遇難者,興許就能救一條命。
還有一次在蘭州逛市場,他無意間打碎了一個賣主的如意,老闆氣得大喊大叫。趙本夫心想這下完了,老闆還不得要求賠個天價?沒想到,最後人家僅僅要他賠了10塊錢。
……
趙本夫一次次熱淚盈眶,一次次受到強烈無比的震撼。他看到了如今已很難見到的淳樸,他也最終相信了人與人之間的善良相待真的在現實生活中存在,從而使他對人性之美和世界的明天信心大增。
他還有一句讓人心驚的話:“我的小說賣的不是水而是血。”
這就是趙本夫,我無法全盤總吉他,只好籠而統之冠以“好作家”的稱謂。其實稱謂並不重要,我也不是單想為一個趙本夫“歌功頌德”——我想說的是,這樣的好作家越多,則文壇幸甚,文明幸甚。(摘自2009年2月13日《光明日報》)
 趙本夫:大地才是一切生命的依託
趙本夫:大地才是一切生命的依託 趙本夫代表省作協給南水北調工程的工人贈書
趙本夫代表省作協給南水北調工程的工人贈書 趙本夫
趙本夫 電影《天下無賊》
電影《天下無賊》 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在阿壩地區採風留影
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在阿壩地區採風留影
 趙本夫
趙本夫 《無土時代》
《無土時代》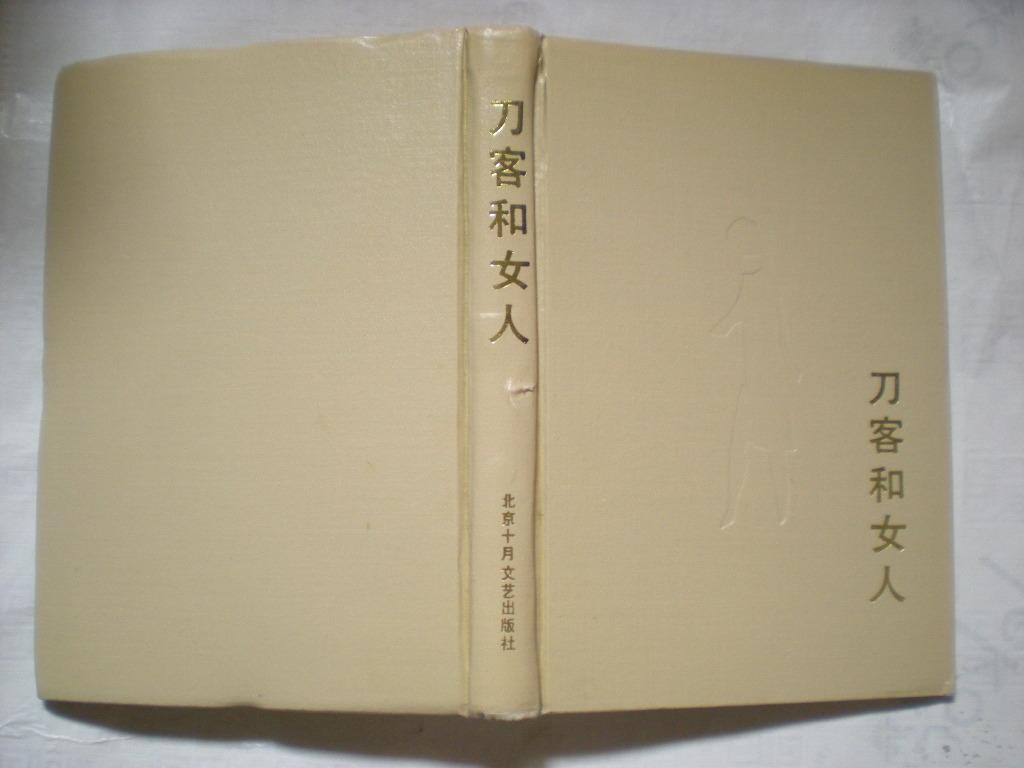 《刀客和女人》
《刀客和女人》 趙本夫參加訪談
趙本夫參加訪談 趙本夫在易卜生紀念館簽名
趙本夫在易卜生紀念館簽名 趙本夫
趙本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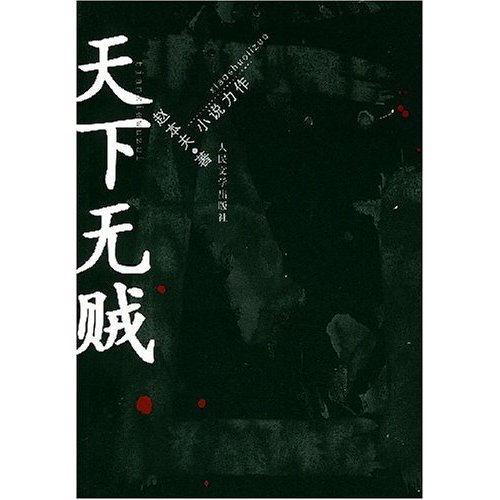 《天下無賊》
《天下無賊》 趙本夫
趙本夫 趙本夫:大地才是一切生命的依託
趙本夫:大地才是一切生命的依託 趙本夫代表省作協給南水北調工程的工人贈書
趙本夫代表省作協給南水北調工程的工人贈書 趙本夫
趙本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