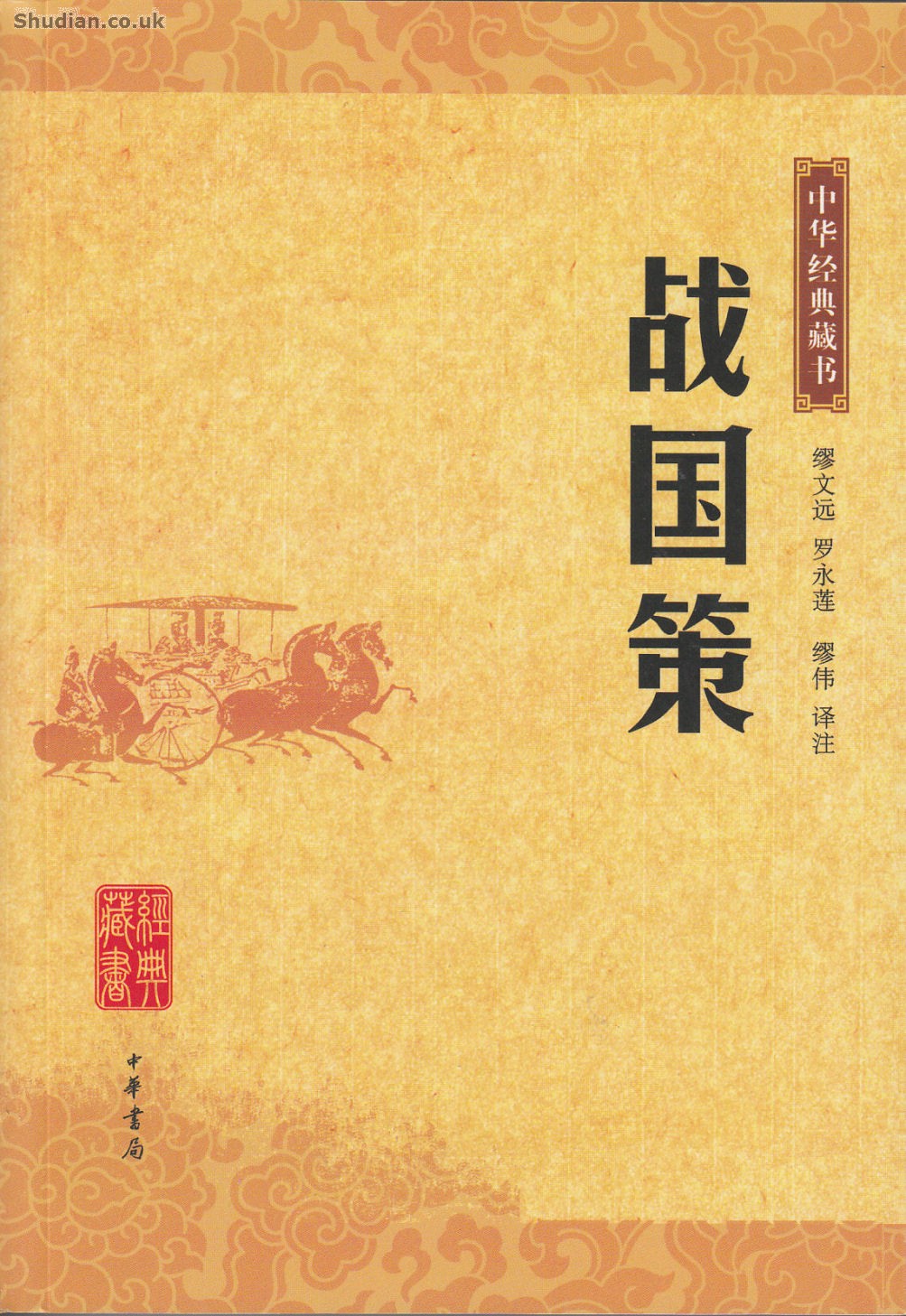作品原文
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
“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不捨人不休傳,衛國城剛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訴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鶩,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余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於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
“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遍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
“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籍與多而兵勁,則事以眾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檳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晉而滅,蔡恃越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
“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麒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眾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懼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眾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
“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視,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均。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蔽,舉沖櫓,家雜總,穿窟穴,眾罷於刀金。而士團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於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
“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窮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而敵國勝,沖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為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
“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沖,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剛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昔者魏王擁士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昧,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從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之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建九?旌,從七星之?。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衛鞅之始與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禽於齊矣;沖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作品譯文
蘇秦遊說齊閔王說:“臣聽說率先挑起戰爭的人必然後患無窮,而不顧招人忌恨,帶頭締結盟約攻打他國的最終陷於孤立。如果後發制人就能有所憑藉,順應時勢即可遠離仇怨。因此聖賢做事,無不借勢而為,順天而動。藉助形勢,有利於展開步驟;倚重天時,則是成功的關鍵。因此,不懂得借勢順天之理,能成就大事的機會實在微乎其微。
譬如說,即使有干將、莫邪一類的寶劍,如果不施以人力,則不能破損毫髮;而再堅硬的箭矢,如果不能藉助弓弩,也不能殺傷遠處的敵人。箭並不是不銳利,劍並不是鈍而無力,那是什麼緣故呢?只是由於少了借力之物。為什麼這樣說呢?過去趙人襲衛,車不停歇,人不喘息,一下子包圍了衛國都城,在剛平(衛地)築土城加以控制。當時衛都八個城門皆被堵塞,兩個城門被摧毀,亡國之禍迫在眉捷。衛國國君在形勢緊急、間不容髮的情況下,光著腳丫逃奔魏國求援。魏武候親自披甲帶劍,為衛國出頭,向趙國挑戰。邯鄲大亂,黃河與太行山之間也不可收拾。衛國乘機重整旗鼓,北向攻趙,奪取了剛平,攻下了趙邑中牟的外城。
衛國並非比趙國強大,只是有了魏國的支持。假如把衛比作箭,魏就好比機弩弓弦,從而藉助魏國而占有河東之地。這時趙國非常恐懼,楚國就救趙而討伐魏國,雙方在州西這個地方大打一仗,楚國穿越魏都大梁城門,駐軍林中而飲馬黃河。趙人得到楚國的援助,也去攻打魏國河北之地,縱火焚燒棘溝而奪取黃城。毀剛平、破中牟、陷黃城、焚棘溝,這並非是趙國、魏國的本意,然而當初他們都那么賣勁的大幹,而最後的結果卻是這樣呢?這是因為衛國和趙國善於利用時機,明白攻占決勝,須依時借勢。如今執國施政的卻不是這樣,自己軍隊弱小卻喜歡挑鬥強敵;國家疲憊偏要觸犯眾怒;敗局一定卻仍然一意孤行;沒有相當實力,卻不能屈志以居下位;自己地狹人少,卻與大國抗衡為敵;事情失敗卻不改詐偽之心。犯下六種錯誤還妄圖建立霸業,其實離霸業是越來越遠了。
臣聽說善於治理國家的君主,應該順應民心,切實估計自己的兵力,然後才能聯結諸侯實現自己的抱負。所以締約時不以自己為主承擔怨怒,作戰時不替他人去抵抗強敵。這樣就能保全自己的兵力以控制全局,而且可以實現拓展疆土的願望。以前,齊王聯結韓、魏兩國討伐秦、楚作戰並非特別賣力,分得土地又不比韓、魏多,可是天下惟獨將戰爭歸咎於齊,為什麼呢?是因為齊國率先倡導討伐秦、楚,觸犯眾怒。再說那時天下正烽煙四起,齊燕爭鬥,又有趙國圖謀中山,秦、楚與韓、魏不斷交鋒,而宋、越專事攻伐。這十個國家,勾心鬥角,相互競爭,然而天下只埋怨齊國,這又是什麼道理呢?因為在締約時齊國喜歡站在領袖的位置,兩軍相交時喜歡攻打強敵的緣故。
再說強國招致禍患,往往是因為一心想凌駕在諸侯之上;而弱國遭受災殃,常常是由於一心想算計別人取得好處。所以,強國不免危殆,小國則不免覆滅。為大國所計,不如後發制人,堅決討伐那些不講道義的國家。後發制人能有所倚仗。盟國多而兵力強,從而形成以人多勢強對付疲弊衰弱的利局,戰爭必能取得勝利。辦事合乎公道,就能取得利益。強國依此而為,名號自然不爭而得,霸業也能袖手而成。
至於小國最好的策略則莫過於謹慎從事,不輕信諸侯。小心謹慎,四鄰之國就沒有藉口尋仇犯境;不輕信,就不會被諸侯出賣,成為利益的犧牲品。在外不被出賣,在內沒有爭鬥,就可遠離禍患,有利於國內實力的積儲和增長。小國若能如此,那么不用祈禱就能享福,無須借貸自能富足。所以說,施行仁政可以稱王,建樹信義可以稱霸,而窮兵黷武只會招致滅亡。為什麼這樣說呢?過去吳王夫差倚仗國大兵強,率領諸侯四方征戰,攻擊楚國,占據越國,並對諸侯們發號施令,儼然君臨天下,最後卻落得身死國亡的下場,為天下所恥笑。為什麼得這樣的結果呢?原因在於夫差平時總是想成為天下之主,倚仗國力強盛率先挑起戰爭。以前萊、莒兩國喜歡施用陰謀,而陳、蔡兩國則專行詐術,結果,莒國因倚仗晉國而滅亡了,蔡國因依仗越國而滅亡了。這些都是在內使用詐術,在外輕信諸侯招來的橫禍。由此看來,國家無論強弱大小,都有各自的禍患,前車之鑑,在歷史上都有印證。
常言道:千里馬一旦衰老,跑不過劣馬;孟賁一旦力乏,打不過女子。劣馬、女子的筋骨勁力,遠遠比不上千里馬和勇士孟賁,但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這是因為後發制人,我方就有所憑藉。如今,天下諸侯相互借重而相互牽制,並且對峙的時日還很長,如果哪個國家能夠按兵不動,後發制人,同時善於轉嫁仇怨,隱去用兵的真實意圖,假正義之名以伐無道,那么兼併諸侯取得天下便能指日可待。掌握諸侯的國情,明了天下的地理形勢,不結盟,不互相扣留人質,關係會更牢固;不急躁冒進,事情會進展的更為順利。一起共事能堅守承諾,一起受害而不相互埋怨,彼此都強大了就越發親近。如何能做到這樣呢?在於形勢令他們憂患相同、利害一致。有什麼事實可作佐證呢?早先,齊、燕兩國在桓曲交戰,燕兵敗北,十萬兵眾匹馬無歸。胡人乘勢襲擊燕國樓煩等地,擄掠牛馬。那胡人與齊國,非親非故,又沒有訂立什麼盟約,卻竭力配合齊國,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他們憂患相同、利害相關呀!以此可見,聯合形勢相同的國家就可以最大程度地獲取利益,後發制人可使諸侯歸附並加以役使。
“所以英明的君主和有遠見卓識的相國,假如致力於王霸之業,就不要把使用武力擺在首位。戰爭既耗損國力,又滋擾民生。國家的元氣遭到損耗,便再也無力號令諸侯。戰爭對國家的損耗是顯而易見的。士人聽說將有戰事,便捐獻財產,以充軍用,而商人就運送酒肉糧食以犒勞戰士,長官讓人拆下車轅當柴燒,殺牛設宴款待軍兵。其實這些都是坑民害國的做法。國人祈禱,君王設祭,大城小縣皆設神廟,凡有市場的城邑無不停業為戰爭服役,其實這是虛耗國家的做法。
決戰之地,屍橫滿地,哀鴻遍野,人們扶著受傷的將士,表面看來將士立功,國家取得了戰爭的勝利,而實際上,資財損耗之多,國人痛哭之慘,足以令國君憂心如焚。陣亡將士的家屬為安葬父兄而傾盡家財,負傷將士也耗盡積儲以求醫問藥,那些僥倖全身而回的軍人,在家中大擺筵席以示慶賀,花費也不在少數。所以戰爭使人民耗費的錢帛,十年耕種所得的收穫也難以抵償。軍隊出戰,矛戟弓弩,車馬刀矢,損失大半,再加上被人盜竊藏匿所造成的損失,也是十年耕種無法抵償的。國家負擔這兩筆費用,已是力竭筋疲,哪裡還能對諸侯施以號令呢?攻城拔地之時,百姓作為後方支援,替士兵縫補破爛的戰衣,運輸攻城的器械,頭上頂著禾草,挖掘地道,為徭役所累。將軍顧不上士兵勞累,日夜督戰,數月能攻下城池就算很快了。將士疲弊,連下三城,相信再沒有餘力戰勝敵人。
因此說,明君賢相圖謀天下,並不把使用武力置諸首位。歷史上是有先例的。過去,智伯攻滅范、中行氏,接著麾兵西向,圍攻晉陽,吞併兩國,又逼得趙襄子走投無路,兵威可謂盛極一時。然而後來智伯卻落得身死國亡的下場,為天下人所恥笑,這是什麼緣故呢?是由於智伯挑起禍端,滅亡之禍威脅到韓、魏二君的緣故。從前,中山國調動全國之兵,迎擊燕、趙兩國,敗趙兵於南方的長子,破燕軍於國境之內,並殺掉其領兵的大將。那中山只是個千乘小國,與兩個萬乘大強國同時為敵,連續取得兩次決定性的大捷,成為用兵的典範。然而這樣善戰之國終不免滅亡,以致國君奔齊為臣,原因何在?是因為它不考慮戰爭的禍患,接連不斷地發生戰爭。由此看來,戰爭的弊端在史書上是很多的。
“如今稱得上善於用兵的人,屢戰屢勝,攻則取,守則固,天下人給予高度頌揚,而舉國上下莫不倚之若長城,其實這並非是國家的好事。臣聽說戰爭取得大捷,士卒傷亡慘重,百姓因防務而疲憊不堪,城郭也會損毀得面目全非。兵死於戰,民疲於內,城郭破敗,國君是不會高興的。以箭靶為喻,它並沒有與人結怨,可是人人都會以強弓硬弩對待它,射中的就高興,沒有射中的則會滿面羞慚,不論老少尊卑,皆以一射為快。原因何在?是人們厭惡讓人看出自己不會射箭。現在有的國家屢戰屢勝不可攻拔,這不僅僅是示人以難,同時還妨害到別國的利益,別國的敵視情緒也就更重了。像這樣既勞累百姓、損耗國家,又成為眾矢之的之事,聖明的國君是不會幹的。
有遠見卓識的明君賢相也不會妄動刀兵,以致於損兵折將,大傷元氣。明君賢相,總是力求不施攻伐而臣服諸侯,以謙恭辭讓獲得更多的財貨土地。因為明君之於戰事,不動刀兵就能戰勝敵國,不用武力就可掠奪到土地,別人尚未察覺而王業就可完成。明君之處事,不費財力,而以長期的策劃取得永久的利益。所以可以這樣說,後發制人可令諸侯歸附並加以驅使。
據臣所知:‘戰爭之道不在軍隊的多少’,即使有百萬敵軍,也能敗之於朝堂之上帷幄之中;即使遭遇闔閭、吳起那樣的將帥,也能通過室內的策劃擒獲他;雖然有千丈的城池,也可以在酒席之間摧毀它;雖然有百尺高的戰車,也可以在坐臥之時摧折它。所以,絲管之聲在朝堂不絕於耳、和著優伶和侏儒歡笑歌舞之時,國土已經擴張,諸侯前來臣服。如此的君王,名號與天地相等不算高貴,政權控制海內也不算巨大。
因此,善於開創王業的君主,在於能使諸侯勞頓而自己閒逸,使天下混亂而本國安寧。安逸與大治在我方,而勞頓與混亂在它國,這就是王霸之道。積蓄國力以待來敵,以消兵禍,那么他的國家沒有隔夜之憂。有什麼事實作佐證呢?過去魏惠王擁有領土上千里,甲士三十六萬,倚仗自己實力強大,攻取邯鄲,西圍定陽,又邀集十二家諸侯朝拜周天子,為圖謀秦國作種種準備。秦孝公聞報,憂心忡忡,寢食難安,食不甘味,動員全國,修繕戰守的器具,境內嚴加防守,同時招募死士,任命將領,以待來敵。
衛鞅向秦孝公獻計說:‘魏王有匡扶周室之功,號令得以施行天下,既能邀集十二家諸侯朝見天子,從者甚眾。以區區一個秦國,恐怕還不能與之爭鋒競勝,大王可否以臣為使去見魏王?臣有把握挫敗魏國。’秦王答應了他的請求,衛鞅往見惠王,大加稱頌:‘我聽說大王勞苦功高而能號令天下。可如今大王率領的十二家諸侯,不是宋、衛,就是鄒、魯、陳、蔡,大王固然可以隨意加以驅使,然而就憑這些力量還不足以稱王天下。大王不如向北聯結燕人,東伐齊國,趙國自會服從;再聯合西方的秦國,南伐楚國,韓國自會望風而服。大王有討伐齊、楚的心愿且行事合於道義,實現王業的日子便不遠了。大王自可順從天下之志,加天子衣冠,再圖齊、楚。’惠王聽了,十分高興,便依天子體制,大建宮室,製作丹衣和九施、七星之旗。對惠王的妄自尊大、越禮不軌,齊、楚兩國君主大為激憤,而各路諸侯也都投到齊國伐楚的旗幟下面。齊人伐魏,殺掉了魏太子申,殲師十萬。惠王震恐,急忙下令收兵,又向東臣服於齊。諸侯們這才停止武力制裁。在那個時候,秦孝公乘機取得魏國的河西地區,而且對惠王毫無感激之情。所以衛鞅當初與孝公商議對策的時候,謀約於座席之上,策劃於酒席之間,定計於高堂之上,而魏國大將龐涓已為齊所擒,刀兵不動已收西河以外的地方。這就是臣所講的‘敗敵於廳堂之上,擒獲敵將於帷幄之中,在酒宴上攻下敵城,在枕席上折斷敵人兵車。’”
作品評析
蘇秦以眾多事例引證了他的政治洞見和哲理,他的主要觀點是:
1、要後發制人、順應時勢。率先挑起戰爭的人和領頭攻打他國的人必然後患無窮、陷於孤立。後發制人會有所憑藉,順應時勢可遠離仇怨。
2、大國應該討伐那些不講道義的國家,以此可名利雙收、完成霸業。小國應該謹慎從事,不輕信他人,逐漸增強實力。
3、不能把使用武力擺在首位,儘量避免戰爭,避免因為炫耀武功而成為眾矢之的。
4、取勝的關鍵是在帷幄之中的策劃和謀略,而非疆場上的廝殺。
這4個觀點蘇秦用了大量事例來論證,一般都是先說出觀點,然後舉出當時已經發生的事件來佐證,在敘述事例過程中也夾雜一些評論,整體上事實和理論相結合,極富有說服力和真理性。
蘇秦對君王的諫言中有破有立,破大於立,破立的中心主旨是一致的,那就是在國家政治軍事鬥爭中儘量要占有道義,儘量要“不戰而屈人之兵”,絕對不能好戰和強出頭。上面這些至理規則同樣適合於和平年代的人際關係中,我們要根據自己的情況,作好自己的發展戰略,對待朋友、競爭者要有智慧、有謀略,要將上述國際關係領域的法則嫻熟地運用在人際關係上,畢竟人與人之間和國家與國家之間在其作為一個利益主體方面,有著很大的可比性。
作品簡介
《戰國策》是
中國古代的一部歷史學名著。它是一部國別體史書(《國語》是第一部)又稱《國策》。是戰國時期遊說之士的著作。主要記載戰國時期
謀臣策士縱橫捭闔(bǎi hé)的鬥爭。全書按
東周、
西周、
秦國、
齊國、
楚國、
趙國、
魏國、
韓國、
燕國、
宋國、
衛國、
中山國依次分國編寫,分為12策,33卷,共497篇,約12萬字。所記載的歷史,上起公元前490年
智伯滅范氏,下至公元前221年高漸離以築擊
秦始皇。是
先秦歷史散文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著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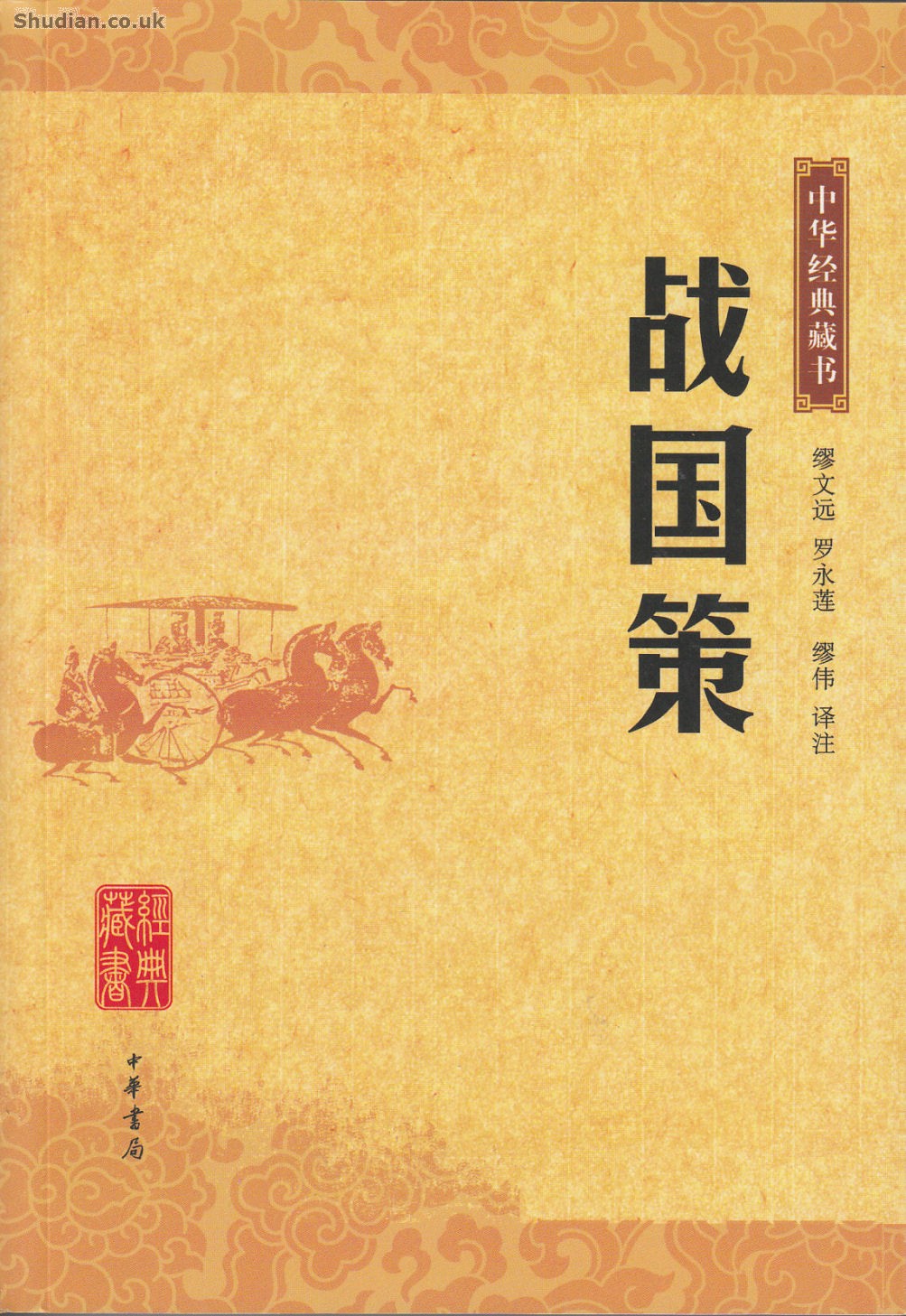 戰國策
戰國策《戰國策》是我國一部優秀
散文集,它文筆恣肆,語言流暢,論事透闢,寫人傳神,還善於運用寓言故事和新奇的比喻來說明抽象的道理,具有濃厚的藝術魅力和文學趣味。《戰國策》對我國兩漢以來史傳文政
論文的發展都產生過積極影響。
編者簡介
劉向(約前77—前6)又名劉更生,字子政。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沛縣(今屬江蘇)人。楚元王劉交四世孫。漢宣帝時,為諫大夫。漢元帝時,任宗正。以反對宦官弘恭、石顯下獄,旋得釋。後又以反對恭、顯下獄,免為庶人。漢成帝即位後,得進用,任光祿大夫,改名為“向”,官至中壘校慰。曾奉命領校秘書,所撰《別錄》,為中國最早的圖書公類目錄。治《春秋彀梁傳》。著《九嘆》等辭賦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說苑》、《列女傳》等書,《五經通義》有清人馬國翰輯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輯為《劉中壘集》。生平事跡見《漢書》卷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