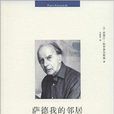本書是一部開創性的研究著作,是西方現代思想學術史上第一部嚴肅思考薩德侯爵其人其作的專著。作者將薩德的思想行為和十八世紀法國的社會背景特別是法國大革命聯繫在一起,探討了薩德的哲學思考與法國唯物主義、無神論、百科全書學派的內在關聯,以及薩德文學作品的特殊風格與哲學內涵。本書初版於1947年,二十年後再版時作者又寫了《惡魔哲學家》一文作為補充。半個多世紀以來,這本書逐漸成為研究18世紀思想史的必引文獻之一,影響並啟發了包括德勒茲、德希達、巴塔耶、布朗肖、拉康在內的眾多法國學者關於薩德及相關論題的研究與思考。
基本介紹
- 書名:薩德我的鄰居
- 作者:皮埃爾·科羅索夫斯基 (Pierre Klossowski)
- 出版社:灕江出版社
- 頁數:157頁
- 開本:32
- 品牌:灕江出版社
- 外文名:Sade Mon Prochain
- 譯者:閆素偉
- 出版日期:2014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0769451, 7540769459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名人推薦,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薩德的作品和行為顯然包含著反社會的毒素,這也是其長期遭禁的原因。但兩次世界大戰讓歐洲知識分子不得不直面西方文化中所包含的惡的因素,甚至是他們自身所包含的惡的因素。薩德在二十世紀特別是戰後受到關注,因為他的唯一使命,似乎就是探索惡的領域;他走得如此之遠,以至於不為任何社會所容。
科羅索夫斯基認為,薩德毫無疑問揭示了很多真實,他幾乎是勇往直前地在邪惡的領地孤身奮戰。為什麼會有薩德這樣的人出現?科羅索夫斯基在這樣的“惡魔哲學家”身上探索到了怎樣的思想秘密?答案都在這本書中。
科羅索夫斯基認為,薩德毫無疑問揭示了很多真實,他幾乎是勇往直前地在邪惡的領地孤身奮戰。為什麼會有薩德這樣的人出現?科羅索夫斯基在這樣的“惡魔哲學家”身上探索到了怎樣的思想秘密?答案都在這本書中。
作者簡介
皮埃爾·科羅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1905-2001),生於巴黎,父母為波蘭裔。科
羅索夫斯基追隨喬治·巴塔耶,與紀德、里爾克為友,還曾出演過羅伯特·布列松的電影。他曾以翻譯為生,將維吉爾、荷爾德林、尼采、卡夫卡、海德格爾、維根斯坦的作品譯為法語,同時他的創作活動也十分活躍,小說、文學評論伴以油畫、素描(其兄弟即為著名畫家Balthus Klossowski)。他的學術和哲學才能體現在本書和《尼采與惡的循環》(Nietzsche ou le cercle vicieux,1991)等著作中,《尼采與惡的循環》被視為海德格爾之後關於尼采的重要論著。
譯者閆素偉,1950年生。巴黎第三大學高等翻譯學院翻譯學博士,北京國際關係學院
法國語言和文學教授。主要譯著有《聖人無意》(弗朗索瓦·於連著,商務印書館,2005年),《十六世紀的無信仰問題》(呂西安·費弗爾著,商務印書館,2012年)等。
羅索夫斯基追隨喬治·巴塔耶,與紀德、里爾克為友,還曾出演過羅伯特·布列松的電影。他曾以翻譯為生,將維吉爾、荷爾德林、尼采、卡夫卡、海德格爾、維根斯坦的作品譯為法語,同時他的創作活動也十分活躍,小說、文學評論伴以油畫、素描(其兄弟即為著名畫家Balthus Klossowski)。他的學術和哲學才能體現在本書和《尼采與惡的循環》(Nietzsche ou le cercle vicieux,1991)等著作中,《尼采與惡的循環》被視為海德格爾之後關於尼采的重要論著。
譯者閆素偉,1950年生。巴黎第三大學高等翻譯學院翻譯學博士,北京國際關係學院
法國語言和文學教授。主要譯著有《聖人無意》(弗朗索瓦·於連著,商務印書館,2005年),《十六世紀的無信仰問題》(呂西安·費弗爾著,商務印書館,2012年)等。
圖書目錄
1惡魔哲學家
39薩德我的鄰居
薩德與革命
薩德體系之概要
在無神論的面具下
135附錄一
150附錄二
薩德生平及作品
薩德是能夠被思考的嗎?
科羅索夫斯基作品目錄
39薩德我的鄰居
薩德與革命
薩德體系之概要
在無神論的面具下
135附錄一
150附錄二
薩德生平及作品
薩德是能夠被思考的嗎?
科羅索夫斯基作品目錄
序言
我要遠離某種思想狀態,這種思想狀態讓我說:薩德我的鄰居。有些人不停地強調薩德的無神論具有的基本特點,以證明某種獲得解放的思想所具有的解放作用;其實我與這些人根本並不相近。無神論宣布說,上帝什麼都不是。所以,如果這種思想是從上帝那裡釋放出來的,那豈不成了從“什麼都不是”當中釋放出來的?那么它的自由會不會也……“什麼都不是”呢?
作者最新的研究《惡魔哲學家》試圖回答的,正是這個問題。在本書再版時,將這篇文章放在前邊,不僅想表明是什麼東西使作者與最初的構想對立,而且如果可能的話,還要填補一項重要的空白。作者雖然堅持最初時講過的一些話,正如在《薩德體系之概要》——本書收錄的研究文章中最早的一篇——中開始闡述的那樣,但是也許當時就應該根據以下情況,對薩德和理性之間的一些關係進行更加嚴格的考察:1.理性的無神論繼承了一神論的規範,維持了心靈的統一結構,以及負有責任的自我的特性和身份。2.如果人的絕對權力是理性無神論的原則和目的,薩德所追求的,則是通過清算理性的規範,將人進行分解。3.除了當時的理性的唯物主義之外,由於沒有形成其他的概念(這一點在《薩德體系之概要》中已經指出),薩德使無神論成了完全畸態怪物的“宗教”。4.這一“宗教”包括有某種苦行,也就是行為的冷漠重複,而這種苦行表明了無神論的不足之處。5.這樣一來,薩德的無神論便重新引入了畸態怪物的神聖特點,也就是不斷重複之行為的神聖特點;所謂神聖,意思是說,其“真實的存在”一向只能通過儀式才能得以實現。6.如此看來,為薩德的畸態怪物規定條件的,解放了薩德的畸態怪物的,不是無神論,而是相反,當薩德企圖將其自身的畸態怪物理性化的時候,畸態怪物迫使薩德將無神論去理性化。
描述薩德的思想是一回事,描述薩德的暴虐(sadisme)則是另一回事。比如,我們必須首先承認雞姦這一最初的既定事實。由此從無果的客體產生無果的享受,是對破壞規範的模擬,闡述薩德的情緒,以證明在理性意義的掩蓋之下,情感上的畸變譴責了作為規範保證者的唯一的上帝,而情感上的畸變又成了理性的畸變。這種譴責按照思想的規律,被納入了同謀的串通之中。思想能夠打破串通的同謀嗎?
但是,作者沒有探索《薩德體系之概要》開啟的道路,反而把話說得十分模糊,同時想按照“絕對的客體決定的絕對欲望”的心理神學的方式(上帝:心靈之根本),通過對薩德的心靈的分析思考,延伸這一最初的研究。然而,在作者看來,作品的最後一部分(《在無神論的面具下》)似乎使問題淹沒在了幾乎帶有華格納風格的浪漫主義當中。因為,在這裡藉口描寫某種薩德在“意識上的不幸”,將暴虐記在了無信仰的賬上。而且這一結論的推論本身也是完全合乎邏輯的:薩德為自己的意識找到的意義是建立在某種禁忌之上的。在指責上帝的同時,意識通過絕對的客體打擊了絕對的欲望,卻沒有觸及絕對欲望的持久性。因為在這裡,欲望是被否認的永恆,薩德的意識在這種永恆當中已經無法辨識自己,而是只能通過無邊的苦惱來感覺到。他把“相信上帝”這一禁忌當成是給自己找到的理性的意義。薩德的自我通過這一禁忌,打破了自己的整體性:由此產生了欲望和意識之間永恆的、相互的冒犯,欲望堅持要與其對象聯繫在一起,所以意識要想維繫在其意義當中,只能作出摧毀的決定,而且是由欲望摧毀意識。在同時發生的不協調的兩件事情當中,在薩德的意識層面上,對欲望的淨化和對欲望對象的摧毀混同為一種要求,而且在這一要求當中,只有當快感產生於受到傷害的欲望,並遮掩了心靈的悲傷時,摧毀才會帶有快感。心靈的悲傷指的是失去了絕對的客體時的悲傷。
也許作者正是想讓薩德從理性評論的狹隘限制當中擺脫出來,所以才闡述了薩德的體驗,作者當時是按照馬西庸的二元論,希望獲得精神的貞潔,所以才認為薩德的行為與卡爾波克拉特的信徒對性慾高潮的崇拜一樣,認為性慾高潮能夠釋放出“天堂之光”。
但是,要想讓這種對異端分子的參照真正具有闡述的意義,作者必須在一切表述當中保持相等的距離,尤其是對正統教條的表述。如果是這樣,那么他表述,或者想像薩德的“意識的不幸”時,就不應該是為了“殷勤地”讚美貞潔,而應該有更多的“教權”的味道,正如他在《對處女的敬意》中所做的那樣;也不應該把“不幸”解釋成在面對處女的反常形象時,出現的男性特徵情結。這種形象切實表示了生育本能之死的意義。但是作者並沒有把這一形象看成是對兩性人神話的規範(一神論的規範),而是看作被掩蓋的在薩德的思想當中具有根本意義的雞姦的動機,這一動機隱藏在可惡的男性特徵的主題之下,希望占有作為上天之貞潔的不可占有的處女,作者並且提出,這是薩德心理的原動力。這是一種浪漫主義,作者承認自己從前沉湎於其中而自樂,但是今天,他必須拋棄這種虔誠的意願。
作者最新的研究《惡魔哲學家》試圖回答的,正是這個問題。在本書再版時,將這篇文章放在前邊,不僅想表明是什麼東西使作者與最初的構想對立,而且如果可能的話,還要填補一項重要的空白。作者雖然堅持最初時講過的一些話,正如在《薩德體系之概要》——本書收錄的研究文章中最早的一篇——中開始闡述的那樣,但是也許當時就應該根據以下情況,對薩德和理性之間的一些關係進行更加嚴格的考察:1.理性的無神論繼承了一神論的規範,維持了心靈的統一結構,以及負有責任的自我的特性和身份。2.如果人的絕對權力是理性無神論的原則和目的,薩德所追求的,則是通過清算理性的規範,將人進行分解。3.除了當時的理性的唯物主義之外,由於沒有形成其他的概念(這一點在《薩德體系之概要》中已經指出),薩德使無神論成了完全畸態怪物的“宗教”。4.這一“宗教”包括有某種苦行,也就是行為的冷漠重複,而這種苦行表明了無神論的不足之處。5.這樣一來,薩德的無神論便重新引入了畸態怪物的神聖特點,也就是不斷重複之行為的神聖特點;所謂神聖,意思是說,其“真實的存在”一向只能通過儀式才能得以實現。6.如此看來,為薩德的畸態怪物規定條件的,解放了薩德的畸態怪物的,不是無神論,而是相反,當薩德企圖將其自身的畸態怪物理性化的時候,畸態怪物迫使薩德將無神論去理性化。
描述薩德的思想是一回事,描述薩德的暴虐(sadisme)則是另一回事。比如,我們必須首先承認雞姦這一最初的既定事實。由此從無果的客體產生無果的享受,是對破壞規範的模擬,闡述薩德的情緒,以證明在理性意義的掩蓋之下,情感上的畸變譴責了作為規範保證者的唯一的上帝,而情感上的畸變又成了理性的畸變。這種譴責按照思想的規律,被納入了同謀的串通之中。思想能夠打破串通的同謀嗎?
但是,作者沒有探索《薩德體系之概要》開啟的道路,反而把話說得十分模糊,同時想按照“絕對的客體決定的絕對欲望”的心理神學的方式(上帝:心靈之根本),通過對薩德的心靈的分析思考,延伸這一最初的研究。然而,在作者看來,作品的最後一部分(《在無神論的面具下》)似乎使問題淹沒在了幾乎帶有華格納風格的浪漫主義當中。因為,在這裡藉口描寫某種薩德在“意識上的不幸”,將暴虐記在了無信仰的賬上。而且這一結論的推論本身也是完全合乎邏輯的:薩德為自己的意識找到的意義是建立在某種禁忌之上的。在指責上帝的同時,意識通過絕對的客體打擊了絕對的欲望,卻沒有觸及絕對欲望的持久性。因為在這裡,欲望是被否認的永恆,薩德的意識在這種永恆當中已經無法辨識自己,而是只能通過無邊的苦惱來感覺到。他把“相信上帝”這一禁忌當成是給自己找到的理性的意義。薩德的自我通過這一禁忌,打破了自己的整體性:由此產生了欲望和意識之間永恆的、相互的冒犯,欲望堅持要與其對象聯繫在一起,所以意識要想維繫在其意義當中,只能作出摧毀的決定,而且是由欲望摧毀意識。在同時發生的不協調的兩件事情當中,在薩德的意識層面上,對欲望的淨化和對欲望對象的摧毀混同為一種要求,而且在這一要求當中,只有當快感產生於受到傷害的欲望,並遮掩了心靈的悲傷時,摧毀才會帶有快感。心靈的悲傷指的是失去了絕對的客體時的悲傷。
也許作者正是想讓薩德從理性評論的狹隘限制當中擺脫出來,所以才闡述了薩德的體驗,作者當時是按照馬西庸的二元論,希望獲得精神的貞潔,所以才認為薩德的行為與卡爾波克拉特的信徒對性慾高潮的崇拜一樣,認為性慾高潮能夠釋放出“天堂之光”。
但是,要想讓這種對異端分子的參照真正具有闡述的意義,作者必須在一切表述當中保持相等的距離,尤其是對正統教條的表述。如果是這樣,那么他表述,或者想像薩德的“意識的不幸”時,就不應該是為了“殷勤地”讚美貞潔,而應該有更多的“教權”的味道,正如他在《對處女的敬意》中所做的那樣;也不應該把“不幸”解釋成在面對處女的反常形象時,出現的男性特徵情結。這種形象切實表示了生育本能之死的意義。但是作者並沒有把這一形象看成是對兩性人神話的規範(一神論的規範),而是看作被掩蓋的在薩德的思想當中具有根本意義的雞姦的動機,這一動機隱藏在可惡的男性特徵的主題之下,希望占有作為上天之貞潔的不可占有的處女,作者並且提出,這是薩德心理的原動力。這是一種浪漫主義,作者承認自己從前沉湎於其中而自樂,但是今天,他必須拋棄這種虔誠的意願。
名人推薦
薩德是能夠被思考的嗎?皮埃爾·科羅索夫斯基是戰後法國第一位著手撕開薩德作品之
黑暗的哲學家,這一任務之艱巨,甚至超過了對康德和黑格爾的解讀。科羅索夫斯基的著作不僅是所有那些關於施虐者的理性以及理性主義的施虐的著述之源,而且被時間證明為我們時代的政治學、社會學和心理分析思想的不曾枯竭的基本源泉。
——Alphonso Lingis
黑暗的哲學家,這一任務之艱巨,甚至超過了對康德和黑格爾的解讀。科羅索夫斯基的著作不僅是所有那些關於施虐者的理性以及理性主義的施虐的著述之源,而且被時間證明為我們時代的政治學、社會學和心理分析思想的不曾枯竭的基本源泉。
——Alphonso Ling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