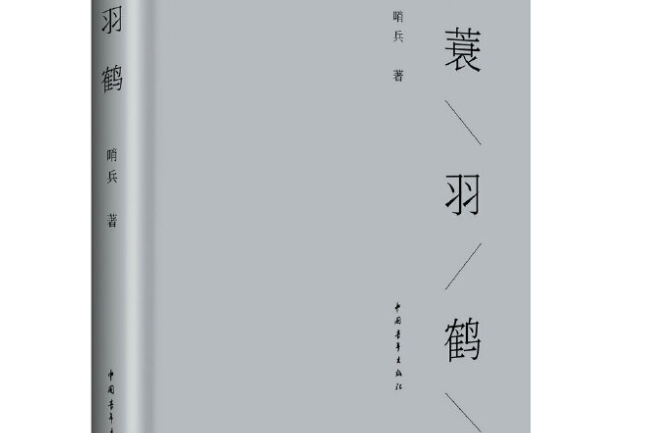內容簡介
《蓑羽鶴》以洪湖作為一個整體的詩性形象,包含著哨兵寫作的兩個位移,一是從作為自然地理的洪湖到作為詩性地理的洪湖的位移,一是由“湖泊寫作”到“自然寫作”的位移。在該書中,洪湖在某種程度上已由一個自然地理符號轉化為一個文化符號,作為一個文化符號的呈現,是和哨兵追求個性化的語言表達方式聯繫在一起的。該書具有地方志的某種烙印,但更傾向於“自然寫作”的開闊之境,對追求地方志的客觀性書寫有所警惕,而是更多地矚目生命神性的至善至美。
作品目錄
作品鑑賞
翻開《蓑羽鶴》,大量洪湖詩撲面而來。洪湖是詩人寫作的題材中心,幾乎統攝所有作品,其他題材可被視為這一中心的衍生和分支。詩人不僅有著偏執題材,也透露出偏執企圖:不滿足對於洪湖烏托邦的單純想像,反覆渲染洪湖意象群,通過詩的巫術,召喚它越過詞語王國的邊界,變成某種客觀實體,構造始於虛構,但讓自我深信不疑的真實,猶如夢的世界中睜開雙眼,一切無從懷疑。他無孔不入地書寫洪湖,詩中洪湖折射出無數角度和細節,栩栩如生。洪湖作為地理空間,遺世而獨立,作為詩人的精神空間,更是獨屬一人的宮殿,詩人懷著強烈的“王”意識,自封為宮殿的孤獨國王:“我從來不相信考古學,只相信歷史/相信清水堡住著古人,在替我除草/剔雜,重修那座塌了的城”(《清水堡》)。哨兵的作品體現出了詩歌藝術的排他性,詩內的世界和詩外的音調召喚理想型讀者,一般讀者很難接近這種中心,甚至背道而馳。
哨兵的洪湖詩可歸為當代景物詩,作為一個主體性異常強大的詩人,他的景物詩從骨子裡背離傳統景物詩的閒適傳統,暗含人與景物的緊張對峙。詩人居於自我詩歌王國的中心,景物被其馴化,歸順自我的磁場,甚至有淪陷的危險,詩人彌散為無處不在的分身和幽靈。他對於景物不僅冒犯,更是征服,哪怕那些極為閒適的詩歌,也難逃干係,暗流洶湧,寧靜的景物作為背景和表象,反而凸顯了這種緊張:“餘生我也想在遇龍河邊造一架/水車,這樣就沒有什麼能變成荒漠/就算住在喀斯特熔岩上,我也會守著屬於/我的絕壁,重新澆灌出麥地”(《灕江水車》)。
哨兵的詩歌並非能整齊劃一地放入某種總結框架,始終存在走音者和叛離者,顯示了寫作的微妙和複雜性:“但那場雨/藏著我對世界的懷疑。有關/雨,我不知道洪湖是喜歡春天的/還是冬天的。但我恨/雨,讓金灣村失去了八位妻子/母親和祖母。但雨/不遂我願,年年都落在洪湖/也落在金灣村,像一代一代的/漁民”(《雨》)。
這類詩中,景物掙脫了詩人的束縛,以高於詩人的形象顯現,變成新的無上隱匿者。詩中意象帶入金灣村歷史,帶入那些歷史賦予的複雜經驗,不僅脫俗絕世,也含有陰暗的死亡之美,掩埋命運的秘密。這一次,洪湖變成了隱匿者,藏匿了自己的來源和權力,也藏匿了每個人的去向和命運,充滿濃郁的神秘美學,也讓人看到底色下的謙卑,這種謙卑的極致,就是個人對於命運的順從。詩人意識到,相對於人類,天地才是大隱與終隱,人與景物的緊張關係崩斷,人被景物完全馴服。
當詩人不僅僅將外界景物視為自我象徵和命運投射時,往往能看到一種舒緩的大美。人的主體性從景物中撤退,弱化對於景物的侵犯,讓它們更多呈現出自身的美來,景物有了充分的獨立性:“該怎么描述那枚殘陽,從合歡樹頂/墜入桃林和灌木叢,又順著緩坡/滾向那群飲水的村牛,在犄角/掛上暮晚。在洪湖入江口/沒有誰能拯救落日/日落江湖,王維留白/僅餘大美,卻無力描述這枚殘陽”(《落日詩》)。
這類詩近似於小品文,給人一種絕望美感,整首詩囊天括地,靜謐中透露出大氣。這類詩在詩人筆下不多見,是逃離詩人個人磁場的倖存者,也是詩人打破封閉姿態的敞開之作,他將鏡頭拉為大全景,讓古典天地觀得以彰顯,化為萬物的寧靜與深邃。類似的還有:“在我看來,女人們下湖/藕,簡直就像天使從另一個世界/回自己。我驚嘆她們的胳膊/腿和腰身,與藕枝/全一致。透過荷盪上變形的光線/過去,我甚至懷疑女媧/造人類,應不是依據神話/是比照洪湖的藕”(《藕》)。
整首詩異常舒緩,作者雖然給人與物打上洪湖印記,但這種美的描述超越了這種特殊性,擴散到對於女性身體之美的讚嘆。藕作為經典意象,高潔脫俗的古典含義與自然界的勞作之美,女性身體之美融為一體。詩人用語言呈現光影之美,一些場景完美得如同印象派的畫作。
哨兵不同於某些詩人,需要藉助詞語和理念的遮掩才能完成作品,他不憚於展示自己的心靈深淵,火山熔岩。很多詩歌如同孤魂呢喃,似乎要獻給世間的同類遊魂。他的寫作經常與人群為敵,在對抗的心態中建構詩中的自我形象:“唯有風夠格論說洪湖,所有談及/藍絲草、紫鴨、黑魚、詩歌/請給我統統閉嘴——你們屬於人/理解不了人外”(《風》)。
這種“人”並非全稱,而是他以外的人類,與其說表達敬畏,不如說反映其詩歌的對立性。在哨兵筆下,空間烏托邦的開放性往往是虛假的,具有深度對立性和強烈排他性,是金剛罩中的桃花源,這種空間結構宣示了詩人對洪湖的絕對占有,也宣告了自我精神的孤立:“我朋友一直都想在聚萍上/或苔蘚處,養出一頭豬/在洪湖,乾一樁不可能完成的事/像某個寫詩多年的傢伙,試圖/用語詞去改變什麼。可惜/我幫不了他。我又不是/很牛的詩人,能讓豬/長出翅膀,像鳥兒一樣飛翔”(《豬》)。
哨兵朝著人群逆向而動,又忍不住對自己和詩歌的命運進行挪揄。某種意義上而言,他恰恰是特別需要理想讀者的詩人,他在詩中穿過那條岔路尋找棲身之所,渴望著體諒與自我的身份確認:“我有家/沒有星月,也能借湖面反光/穿過這條岔路。要是有一條船/趁著夜色轟響十四匹馬力柴油機/朝我奔來,天黑後/就有人原諒我白白浪費/一生的光陰和語詞”(《原諒詩》)。
詩人如同詩歌界的達摩,對抗宏大的召喚,踏上一個人的絕境之旅:“不在城裡/尋歡,我就在清水堡廟/面壁,與洪湖/獨處”(《歉意》)。這種面壁意味著高度自覺的精神修煉,自我悲劇命運的清醒認知和自覺承擔:“是現實。所有的蓮/只願爛在洪湖,化作淤泥”(《蓮》)。詩人的自我形象和蓮的意象高度合一,沉迷於自我精神世界,自絕於人間,寫到山窮水盡,撞到南牆不回頭。但這種心態存在著真實的矛盾性。一方面,他沉湎虛空,打算把牢底坐穿;另一方面,那種巨大的絕望與焦灼感包裹詩人的肉身:“鳥類/從不乞討稻梁,也盡享一生的幸福/水藻漂泊,身負喪家之占/卻比我更為忍受這個世界的悲辛”(《岸:漁民病歷》)。
他意識到詩歌的無能,命運的失控,準備頑抗到底,借出世來承擔命運,但難以排遣愁緒,而入世則讓人更加不堪,一種左右不得的心態躍然紙上。這種糾結的悲劇意識中不斷浮現出死亡意象。在《過洪獅村夜聞喪鼓》中,詩人的感受由彼及“我”,如同失魂的水鬼,為自己敲打起喪鼓。這種以詩為杖,在絕望和虛空中輪迴的代價是巨大的,詩人背對世界又有所不甘,患上了時代所有的病,凸顯出極度孤獨的形象,甚至暴露某種厭世的心理危機:“一個叫四兒的朋友/逆著我走的道,販螃蟹和甲魚/進城,卻在賭場走失/死於厄運……洪湖可以忍受這一切,我不能/我不能忍受野渡/橫舟。對於官墩村/洪湖,還有這個世界/我已失去耐心,我甚至不能忍受月亮”(《洪湖東岸,中秋在官墩碼頭無人擺渡,小賭半日》)。
詩人似乎尚未抵達精神的圓滿,找到屬於生命的終極意義,少有“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那種釋然。他的詩充滿了進行時態的焦灼,其自我放逐不同於“在路上”模式,相對於暗含渴望的孤身前行,這類放逐無限後退,迴避大於渴望:“二十五年來/唯有逆著人類的方向,我才能抵達/要去的地方”(《二十五年後在湖上再次駕船》)。
多次在詩中出現的洪湖小路,不是通往外界,也不是真實通向洪湖,而是更小的容身之所,其縱向形態象徵著時空的縱向延展,通向更為隱秘真實的平行空間。這條甬道暗度精神陳倉,試圖帶領詩人終極逃亡,但指向不明:“請原諒漢語/在洪湖,無力為潛水鴨和漁民/搭起故居。我有家/沒有星月,也能借湖面反光/穿過這條岔路”(《原諒詩》)。
對於這種情緒的表達,哨兵適可而止,並未過度重複,避免了單調的形成。這種單調不是指單獨作品中的單調,而是指作品集中過度重複某種思想情感形成的整體性單調。這類精神危機沒有讓詩人轉向宗教救贖,而是讓作品中出現了神佛類意象。正是因為這類象徵終極救贖的意象,以往的焦躁得到了平復:“換種角度/拿一尊關公的眼光,打量/虛空,卻是一口偃月刀的舊刃/在斷檁和殘廓間,撐著/某些搖搖晃晃的東西”(《搖搖晃晃》)。
《悲哀》《想像》這類詩寫得氣勢恢宏,含有複雜豐厚的經驗,渴望成就偉大的孤獨和痛苦。《想像》在整部詩集中非常搶眼,作者將自己與那條河流融為一體,互相感受著彼此的存在和命運。這條河承載著歷史文化,早就化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徵,在這裡成為詩人命運的象徵,成就了詩人的自我英雄化。
“這條混雜泥土的河流是某個人顫巍巍的手指刻進大/地的契形文字:一。唯一,一生”(《想像》)。這條河流的一,是奔流到海不復歸的一生,也是萬物歸一的一,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一,正如詩人所說,這需要想像。詩人的命運與河流相互呼應,形成了緩緩流動的韻律和空間感,充滿了磅礴氣勢:“我仿佛聽到有人從高山/和雪線下走出來,穿過大漠、峽谷,途經鄉村、城/市,一直返還到了大海。像我路遇的亡命者、流浪漢/酒鬼、賭徒、窮親戚,操著混雜泥土的方言”(《想像》)。
作品影響
榮譽表彰
2018年12月13日,《蓑羽鶴》獲得第七屆湖北文學獎。
2019年11月,《蓑羽鶴》獲得湖北省第十屆“屈原文藝獎”文學獎。
出版信息
作者簡介
哨兵,魯迅文學院第十五屆高研班學員。曾參加第十八屆青春詩會、第六屆青創會。曾獲得《人民文學》新浪潮詩歌獎、《芳草》第二屆漢語詩歌雙年十佳、第四屆《長江文藝》完美(中國)詩歌獎、《中國作家》郭沫若詩歌獎優秀獎等獎項。著有詩集《江湖志》《清水堡》《蓑羽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