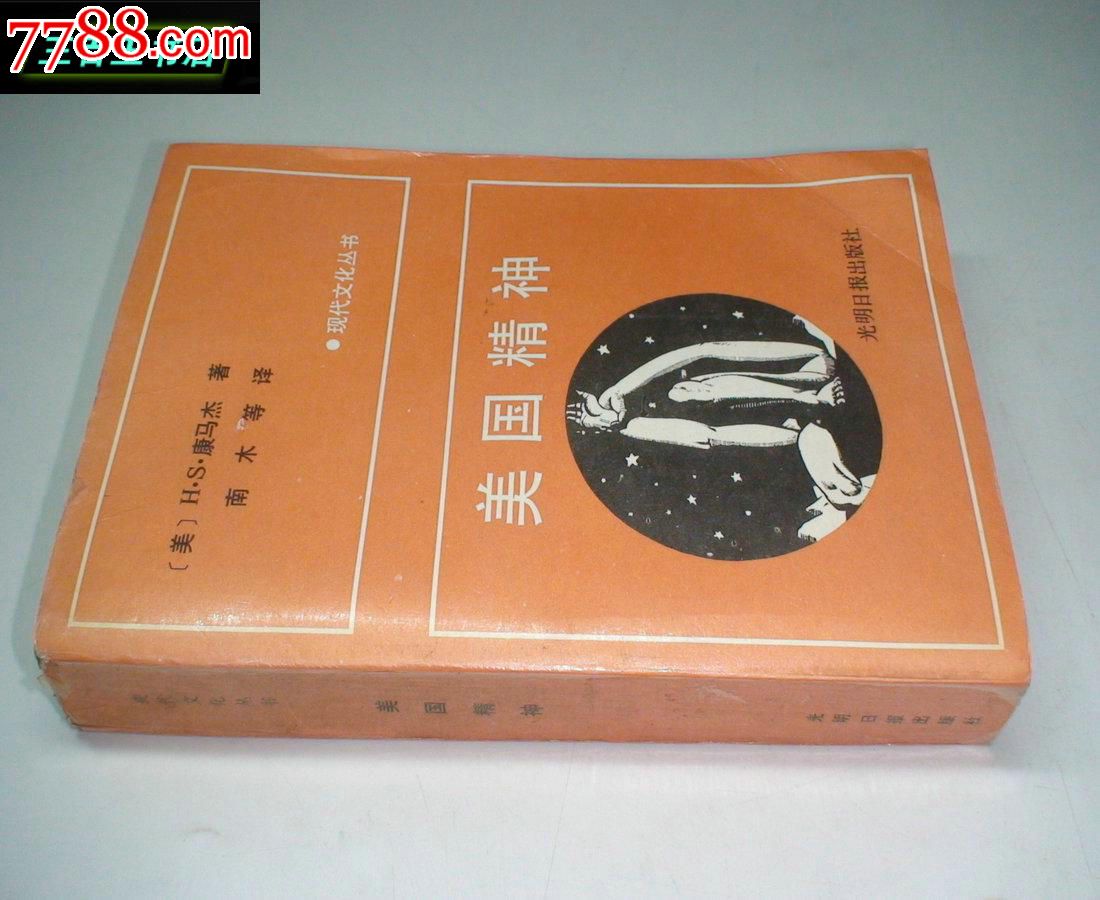創作背景
本書成於上世紀40年代末。彼時,整個世界剛剛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中走出來,反法西斯的世界戰爭的勝利,使世界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戰後的美國趁著西歐各國撫慰戰爭創傷的時機,逐步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寶座。
戰後美國進入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加上
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的促進,美國經濟迅速發展,形成了戰後初期經濟的繁榮。而這種繁榮是由以下幾個因素促成:第一,戰前長期蕭條和戰爭造成的消費需求大量縮減,戰後不論是生產資料或者生活資料都急需補償,推動了生產的持續增長;第二,戰後初期雖處於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的前夕,一些新技術已開始套用於生產和管理,新興的工業部門開始出現。另外,由於戰後
生產自動化水平提高,需要大量投資,增加廠房設備,不僅增加了生產資料的需求,而且促進了擴大再生產的循環過程;第三,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刺激了經濟發展。而杜魯門政府的“公平施政”綱領繼承和捍衛了
羅斯福新政的成果,符合
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
無疑,經濟的發展和政治上的穩定,又一次恢復了美國人的信心,儘管仍有經濟危機的干擾,但美國人已從戰爭的陰影中走出,又恢復其固有的樂觀與信心。
在二戰中發揮的作用與戰後領先世界的優越地位又使美國人自豪不已,他們覺得有理由把美國看作一個偉大的國家,把美國人民看成偉大的人民。
自豪之餘,人們回首走過的二百多年的風風雨雨,不禁對民族的內涵發生了興趣——在美國人的血液中似乎流動著一種共通的,一脈相承的東西,它融合著自信與樂觀,現世而熱情,無疑也曾有過深刻的困惑與迷茫,也正是這種一脈相承的東西促使美國人在一個沒有歷史的新大陸實現他們的“美國夢想”。
《美國精神》一書正是試圖探索“稱之為美國精神的難以捉摸的東西”(康馬傑語,下同),也就是一種獨特的美國思想、性格和行為方式。
《美國精神》一書正是這樣的時代背景的產兒。
內容簡介
《美國精神》是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評論家亨利·斯蒂爾康馬傑教授(1902—)繼《美利堅合眾國的成長》(與塞繆爾·埃利奧特·莫里遜合著,1930)、《美洲:自由人民的歷史》(與阿侖·內它科合著,1942)和《多數人的統治和少數人的權力》(1943)等一系列著述之後推出的又一部傑作。它自1950年由
美國耶魯大學出版付梓問世以來,重版20餘次之多,在東西方學術界享有極高的地位和聲譽。
為了更好地闡述所謂“美國精神”,作者選擇了美國歷史上的一段特定時期(約自19世紀80年代迄至20世紀40年代末為止)作為考察和研究的時限。因為他視90年代為“美國歷史和思想的一道分水嶺”——即由以農業為主的美國開始轉變為以工業為主的城市化的美國;而自那時以後近60年的美國又“具有某種統一性”,可以作為一個整體加以研究,於是展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書便以“19世紀的美國人”開其篇,而以“20世紀的美國人”為結尾,並在論述作為分水嶺的90年代之後,以大量的代表性著述和重大歷史事件為依據,從哲學、文學、新聞學、經濟學、史學、政治學、法學、建築崐學等各個角度,對現代美國思想和文化的演變與發展作了較為全面的剖析和評價,可見,這部書雖然旨在闡釋美國的
國民性或民族特質,實質上卻是對現代美國所作的一次綜合性研究。
(一)哲學
新舊交替的時代給美國人心理帶來巨大衝擊,正是在這種困惑與迷茫的情緒下,他們翻過了這道歷史的分水嶺。而基於這種困惑與迷茫,進化哲學與實用主義應運而生,他們適應了這個變化的時代,為心靈無所傍依的美國人的靈魂提供了堅實的土壤,使他們得以繼續前行。可以說進化哲學與實用主義是這個燥動的時代的哲學,他們塑造現代的美國人的靈魂,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學、歷史還是法律、社會學無不打上這時代哲學的極深烙印。
先以誕生這種時代哲學的背景談起。
19世紀末是近代美國向現代美國轉變的歷史時期,其主要特徵是以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
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在這兩個歷史性轉變帶動,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和思想文化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從而為20世紀現代美國奠定了基礎。
美國內戰的結束標誌著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的來臨。戰後“南部重建”憑藉政治、法律手段鞏固了內戰所帶來的歷史性轉變,基本上消除了種植園
奴隸制度和
奴隸主階級寡頭專政,把南部納入全國統一市場,為
資本主義在全國範圍內的迅速發展準備了必要條件。
隨著重建的展開,美國歷史進入了“
鍍金時代”,這個時代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美國工業迅速發展,走向集中、壟斷,壟斷資本主義在國內市場上逐漸居於優勢,成為美國經濟生活的基礎;第二,聯邦政權不再為兩個利益對立的統治集團所分享,而是為新興的
工業資產階級獨攬;第三,南部走上了緩慢而痛苦的“
普魯士式”發展道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美國閉塞的落後地區。
在19世紀最後的30多年間,美國資本主義不僅在廣度上,而且在深度上都有了迅速的發展。在廣度方面,突出地表現於西部的開拓與移民洪流的湧入;而在深度方面,則是
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壟斷制的建立和發展是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自我揚棄和局部質變。它使生產進一步社會化,橫向和縱向的聯合把社會經濟的各部門結合為一個整體:它使大企業的所有權與管理權日益分離;它使工業資本越來越依賴於
銀行資本,從而形成無所不在的
金融寡頭統治,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適應了這一時期美國生產力和
生產社會化的發展的客觀要求,同時也帶來了更加尖銳的社會矛盾。
在美國資本主義向縱深發展的同時,其城市化也進入鼎盛時期,以工業為基礎的近代工業城市的普遍興起,加速了美國工業化的進程,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已由原來的農業國發展成為主要
資本主義工業國,實現了“新”、“舊”資本主義的交替。
隨著“新”、“舊”資本主義的交替,美社會
階級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原有的資本家、工人、農場主三個大集團的內部分化趨勢日益增強;與“舊”資本主義相一致的舊階層不斷衰落,而隨“新”資本主義產生的新階層卻迅速發展,資產階級內部逐漸分化為壟斷資產階級,舊
中產階級和新中產階級。壟斷就是資產階級同其他階層的矛盾,特別是與保持獨立經營的企業主,即舊中產階級的矛盾加深,而新中產階級則隨著壟斷資本生產關係的確立而發展起來,農場主階級在生產
商業化過程中,除少數上升為大農場主外,大部分因喪失生產資料而滄為農業工人,工人階級的構成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如非熟練工人開始成為產業工人主體,集中在機械化程度較高的
壟斷企業;白領工人階級形成,
工人貴族階層擴大等等。
在向壟斷過渡時期,美國
社會流動的頻繁對
階級結構的變動產生深刻影響,這種社會流動表現為人口在地域間的橫向流動和社會各階層的縱向流動。
西進運動導致人口大量移民西區,從而使
人口重心不斷向西移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迅速發展吸引了大批人口流向城市,向壟斷過渡則加速了社會各階層的上下流動。在19世紀後期,有相當一批富豪出身於社會中下層,後來逐漸發展成為大資本家。中下層之間發展對流也較為普遍,東北壟斷資本向中西部迅速發展,造成了這個地區農場主大批破產,其中一部分為謀生計流向東部或更遠的西部。這就形成了巨大的橫向對流,這種橫向流動與縱向流動相結合,使美國社會
階級結構的變動更具有複雜性和特殊性,而移民洪流則大大加強了原有的
社會流動,促進了美經濟的迅速發展,也引起了美排外情緒的增長。
90年代是美國歷史的分水嶺,在分水嶺的一邊,主要是一個農業的美國,它關心的是國內事務,這個美國在物質和社會方面尚處於發展過程中;在分水嶺的另一邊,是現代的美國,它主要是一個城市化的工業國家,它同世界經濟和政治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同時也為舊世界特有的難題所擾,它在人口、社會組織、經濟和技術諸方面經歷著深刻的變化,而且試圖改變傳統的組織機構和舊觀念,以適應新情況。
而面對新時代的到來,美國人既無經驗也無精神準備,他們盡最大的努力去適應新的經濟和哲學秩序,然而在現代資本主義大潮之中,個人猶如草芥一般渺小,即使拿出他們珍視的樂觀與進取,卻也無從把握個人命運,於是他們的自信終於瓦解,面對世界,他們惶惑了,正如愛德華·A·羅斯指出:“在新形勢下老調重調簡直是白費唇舌。原先建立穩定秩序,指導人們行動並賦予美國制度以生命力的那些哲學思想本身也受到衝擊,在遍及世界的一種新的力量的衝擊下,過去的經濟、社會以及道德觀念統統都在土崩瓦解”。
時代呼喚著新的哲學誕生。進化哲學和實用主義應運而生。
19世紀末,
達爾文的進化論對宗教的影響已趨衰微,可是它對哲學卻產生了革命性影響。進化論闡明:人類不是上帝仁慈意旨的恩賜,而只是
自然淘汰的結果。所謂“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
斯賓塞在《綜合哲學體系》一書中證明:人類的進化過程不僅是生物的而且是社會的和心理的進化過程。進化過程從簡單走向複雜,從野蠻走向文明,從混亂走向秩序,從無政府狀態走向規律。進化論學說證明了宇宙是由規律制約,證明人類的命運是日益進步的。
進入工業社會後,農業社會緩慢節奏下溫情脈脈的人際關係被大機器生產的轟隆聲所淹沒,資本主義競爭以其爾虞我詐的殘酷本性昭然於世,驚惶之中,人們跌入物慾的競爭,在時代大潮中滾來滾去,而對前途及自身的命運毫無自信,而進化學說所揭示的宇宙、自然界及人類不斷進步的光明前景無疑給人們打了一針強心劑,人們有理由展望樂觀的未來。
“優勝劣敗,適者生存”——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在光明的前途之下,又要適應這條冰冷的
自然法則。這無疑是資本主義進入競爭時代的法則,也是為其競爭殘酷性所進行的辯解,故而這對事業已納入順境,其生存已確定不移,會與大自然和諧一致的人來說,是極受歡迎的,可是,它對那些在自然或社會冷酷無情作用中注定成為失敗者的人來說,則是殘酷的。
經過美國歷史學家,哲學家約翰·菲斯克的闡釋,進化論的觀點深入到美國人的心靈深處。“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一樣是不斷進步的”這種觀念適應了這個變動的時代,因此為處於新舊夾縫中的人群緊緊抓住,他們開始相信未來是美好的,即使個人的命運無從掌握,至少能夠掌握努力本身,於是他們鼓起勇氣去接受自然、社會的考驗,努力使自己跟上時代大潮。
如果說約翰·菲斯克闡釋的進化哲學撫慰了初入工業社會孤立無助的人們的靈魂,那么隨著工業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和鞏固,實用主義則欣然與舊傳統決裂,將信仰付諸於行動藉以創造一個嶄新的未來。
威廉·詹姆士通常被公認為是實用主義的奠基人。在詹姆士看來,哲學有一個主要 的實用目的:賦予一個人的生活以意義,而信仰則是行動指南,每個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法找到自己的真理。而凡是行得通的就是正確的,因為它對一個人的生活方式真正有所影響。所謂“
有用即是真理”。在這裡,實用成為價值的唯一標準。每個人無疑成為自我的君主,個人的
能動性因此而得以
張揚。
如果詹姆士就其讚美了人可以選擇自己根本信仰的個人權利這個意義來說可以被認為是空想的實用主義者的話,那么
約翰·杜威就可以代表崇實的實用主義者,他熱心研究個人與自然和社會環境之間互相作用的過程,認為應把科學套用於人生各個方面。
杜威相信人類的進步。既然人是能夠思想的,他就能改變他周圍的社會環境,甚至自己的本性,對人們來說,最為重要的是保證“現有目標”的實現,這些“現有目標”的實現將成為達到其他“現有目標”的手段。他認為:人類在歷史上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機會去明確指導社會變革進程,故而人類應該運用各種科學方法去了解人和社會的性質。“一旦我們了解了人究竟像什麼樣兒,那時我們就能用科學方法去控制環境和個人,使每個人都得到最大的幸福(A·ZJ·賓克萊)。
杜威的整個哲學是他要迎接這一偉大挑戰的嘗試,因此他提議要做的事情是改造哲學,改造道德,改造社會,而最為主要的是改造教育。另外,既然實用是價值的標準,那么道德規則或原理也不是絕對的,而對任何特定思想的檢驗就看這個思想所引起的具體行動如何。
實用主義鼓勵了人們在行動中作出努力並承擔責任,在這種情形下,自我成為拯救世界的戲劇中的主角,在宇宙的舞台上充滿了積極參與的高貴和尊嚴,在奮鬥中,人們自覺掌握了自己的未來,因而恢復了樂觀與自信。可以說,實用主義在新、舊過渡的美國社會生活中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成為一代人的行為準則。
哲學是時代精神的體現。進化哲學和實用主義猶如兩面高揚的旗幟,社會科學的其他各科無不受到其深刻影響。
(二)文學
新的世紀即將到來的惶惑在文學上得以最深的體現,而在進化哲學和實用主義的影響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美國文學家大都成為這兩種思潮的鼓吹者,這一時期的文學有三種傾向性。
1.文學中的宿命論
宿命論源於達爾文的進化學說。新、舊交替的時代充滿了悲觀氣氛,以致藝術家們很容易求助於科學的學說,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學說可以為悲觀主義提供某種最終的正當理由,可以把人類陷入可悲的混亂的責任從社會本身轉嫁給宇宙。而一切罪惡,痛苦和無奈無疑在“適者生存”這一冷漠的宇宙規則下得到了解釋。
對當時經濟與社會罪行的抗議以及乾脆使人們良心擺脫對這些罪行的責任的這種哲學,在
傑克·倫敦和
西奧多·德萊賽的作品中第以鮮明體現。
傑克·倫敦把進化哲學變成日常用語,並以生存競爭原則對其冒險生涯進行解釋,而這解釋進一步演變為對於物質力量極端稱頌,人只不過是動物,生活不過是一場爭吵,大自然則是冷漠無情的,進化哲學在此表現出濃郁的宿命色彩。
而在當時的許多作品中都有這種宿命論的痕跡。譬如:
德萊塞的《
嘉莉妹妹》、《珍妮·格哈特》、《巨人》、《金融家》。
海明威的《
午後之死》、《阿非利加的綠色小山》。史蒂芬·克蘭的《馬吉》。
弗蘭克·諾里斯的《麥克蒂格》和《范多弗和獸性》等等。
美國文學中的非理性崇拜浪潮,基本上是來自歐洲。由於美國文學主要是派生的,所以非理性表現得極為模糊。由於它最不成熟,所以也最為頹廢。其代表人物有舍伍德、安德森、沃爾多、
弗蘭克、伊夫林、斯科特等人。
資本主義後使個人的命運無從把握,進化論給自然界及人類規定了一個冷漠的進化規律,個人命運在生存競爭之中何等微不足道而又無能為力。那么理性又有何意義可言?於是一個詩人和小說家的新流派開始陳述他們
達爾文主義宿命論變體的觀點,而攻擊理性,意念統一性,正常標準,基本規律和
倫理道德或成為這一文學流派的顯著特點。
正如
非理性崇拜的思潮鼻祖弗洛伊德所言:“我們的文明充滿著這樣的苦難和不幸,其本身就應該受到譴責,我們如果將其全部拋棄,回復到原始狀態,我們將更加幸福。”
而作者對這種思潮的傾向性極為明顯,認為這個派別站在偽科學的立場,因而注定要走向自我毀滅,“因為建築在無聊瑣事泥沼上的文學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
在科學對信仰的影響以及經受時代考驗的價值觀念處於解體的情況下,他們同樣困惑不安。然而他們儘管趨於悲觀主義,卻沒有完全絕望,他們關心更多的是個人的精神安寧,而非社會的物質福利;他們同意造反者和改革家們認為美國生活有缺陷的觀點,而更多的是變化本身感到沮喪,他們同意自然主義者和非理性主義者認為生活本身令人悲觀失望的觀點,但他們卻又堅信生活的意義是悲劇性的。世世代代都堅持下來了,難道這個民族卻要對世界分崩離析的勢力屈膝投降嗎?”(
埃倫·格拉斯哥)。
在世事變遷中,
傳統主義者們以傳統為最後的堡壘,獨立於物慾縱橫的世界之中。“他們對工業主義造成的損害感到吃驚,因而渴望回到田園中去:他們厭惡商業文明,以無比欣慰的心情回憶沒有金錢銅臭而命運悲壯的往事,他們對沒有根基、忘記過去而又忽視未來的社會感到沮喪,於是他們便再現了一個根深葉茂,能從過去得到安慰的社會。”
4.反抗的文學
隨著工業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文明的虛偽和醜惡暴露無疑,這是一個“在政治上腐敗,在道德上腐蝕人的經濟制度。”而有良知的作家們都提筆對這一“不人道、不公正的經濟制度”進行抨擊。如威廉·
艾倫·懷特,
溫斯頓·邱吉爾,歐內斯特,普爾及戴維·格雷厄姆,菲利普斯等。
這些作家在作品中揭露了
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性,資產階級
道德觀對人的異化,充滿了對
資本主義文明的懷疑和否定,如
約翰·斯坦貝克在《
憤怒的葡萄》一書中,不僅記述了奧奇一家從灰盆地區逃到黃金的加利福尼亞的故事。還控訴了一種經濟制度:正是這種制度把他們趕跑,把土地從耕種者手裡奪走然後交給銀行,在豐饒的土地上造成饑荒,以法律的名義幹著無法無天的勾當,並嘲弄正義與民主的原則。
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制度的虛偽與腐朽使
托馬斯·沃爾夫在痛苦和彷徨中斷言:“我相信我們在美國這裡迷了路……”
三、歷史學:
貝尼特在《西部的星》一書中自豪地說:“我們乾出的是前無古人的事業。”如此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是在創造歷史的一個民族,必然會意識到自己有義務把它記錄下來,“一個民族確信自己是在披荊斬棘地開闢道路,好讓其他民族跟上來,這個民族必須會明白自己有責任把路線清楚地標出來……”
由此可見,美國人對歷史感興趣不難理解,就他們而言歷史就是“朝著人眼望不到的遠大目標飛速前進”的一個國家的記錄,回憶往昔,可以使他們倍受鼓舞,倍感自豪。
19世紀中葉可以說是美國歷史寫作的黃金時代,而到了19世紀末,史學則呈現一種新的發展趨勢——史學家不再展示歷史現象的輝煌或是陰暗,而從現象背後探索某種決定歷史發展的規律性的東西。正如作者所言:“在這個新的世紀裡,歷史學家對力量的重視大於對人物的關心。他們要科學不要倫理,要真實不要戲劇,要分析不要記述。任何事情都不歸之於上帝,也很少歸之於機遇,而必須承認的
偶然性多半怪罪史學家之無能而不是歷史難以預測。過去的一切似乎都是由於非人力的種種巨大力量相互作用而產生的,這些力量包括經濟的、地理的、社會的、科學的、心理的等等……這表明:是人適應自然和歷史而不是自然和歷史適應人”。自然和歷史在此又冷漠地與人相對立,達爾文的進化哲學在史學上又出現了極為微妙的表現。
(四)社會學: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美國的社會學領域,出現了兩位大師——維廉·格拉哈姆·薩姆納和萊斯特·沃德。二者都是進化哲學的信奉者,但都走向了兩個不同的方向。
薩姆納相信“適者生存”這個道理,而亦肯定進步是必然的,但在進化過程中人類會碰到什麼樣的情況則悉憑自然的安排。他的《社會靜態學》一書認為:理智與意志把人與其他動物區別開來,但對人來說:最高的智慧就是沿著自然劃定的道路前進,而最莊重地運用意志力則在於不去花氣力改變她的規律。薩姆納的這種社會學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消極主義和軟弱無能。
沃德則對消極主義和
絕對主義的社會學體系發起攻擊,他認為:社會學是一門積極的、充滿活力的科學,如果運用得當,它將使人類能控制進化的過程。沃德是給社會學研究帶來足資使用的科學和哲學工具的第一位美國人,也是第一位真正的進化社會學家。他認識到:雖然環境改造生物,人卻能改造環境。而“適者生存”這一概念為沃德所批判,他認為僅適於生存並不是文明所能接受的標準,“
社會進步意味著它每前進一步就要扼制宇宙的過程”(赫克斯利),人類有能力干預自然,而只有經過人類的干預,自然產品才適於人類使用。在這裡,
沃德進一步發展了
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個體的
能動性進一步高揚。為了更好地征服自然,人類只能集體地,有計畫地,有組織地去征服自然,政府的設立成為必要。在經濟方面,“國家干預”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為了促進社會進步,消滅弊端,人類必須採取的步驟有:第一步建立起真正的人民政府。第二步:創立真正的政治學和將立法人員都培訓成為社會科學家。而教育則是社會學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沃德的學說激勵了整整一代學者和改革者,使他們相信:沿著幸福的路線去改造社會是可能的,他也激勵了用他的工具進行研究和用他的武器進行戰鬥的一代新人。
(五)新經濟學:
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使財富和權力日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科學和發明給社會帶來無與倫比的益處,但科學與發明對經濟的直接影響是財富的再分配,整個社會日益分化為兩大對立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經濟領域的新變化要求適合這種形勢變化的新經濟學的誕生。
這是逐步形成了後來成為20世紀正統經濟學說的新經濟思想的三項原理:承認經濟學是一門歸納性的實用科學,評價理論和科學思考的現實意義;承認國家干預經濟過程的必要性。
而經濟關注的整個焦點也發生了轉移,它的主要任務是探索新渠道並要求採用新方法,研究人員的注意力也從對
經濟規律的探求轉向對經濟機構的分析。在這裡,實用主義思潮的影響顯而易見。
索爾斯坦·維布倫是新經濟學家的傑出代表。他的最主要的貢獻是:揭示了工業與手工業的對抗;認為工業的目標是生產商品,商業的目標是賺錢,當二者發生衝突時,生產便讓位給賺錢。
他指出:貨幣經濟本身就是一種弊端,其受益者是一個掠奪成性的階級。
可以說:維布倫的經濟學著作深刻地反映了
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種種劣跡,維布倫稱之為:“
資本主義的破壞”。
(六)新政治學:
隨著社會,經濟和技術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發生的深刻變化,傳統的憲法理論不再適應實際情況,靜態的憲法與動態的政治之間的分叉變得越來越明顯。而根據理論設計的政府與發揮實際作用的政府之間產生斷層,故有識之士呼籲:我們的政治思想“需要注入當代的真知卓見”。
而進化論,實用主義對經濟力量和心理因素的認識則促使政治學開始了從靜態的轉變為動態的,從分析的轉變為起作用的,從抽象的轉變為具體的變革。進化論使憲法不是靜態而是動態的這一論點獲得了科學基礎,證明了憲法的不斷完善的合理性;同時,進化論揭示了國家是歷史的產物,人們開始以新的眼光看待州的權利和國家主義這整個問題;而變革則是正常的,如同自然界不斷發展一樣。國家也有它發展的過程。而實用主義是促成政治學得以稱為一門科學的第二個原因,實用主義的方法產生了甚至比進化論的方法更直接更即時的影響。“這是因為,進化論乃是一種哲學態度,而實用主義則是一種技巧;進化論提供一個出發點,而實用主義則要求分析和解答。”實用主義注意的不是有關政治制度的理論而是政治制度的機構;它不是在道德的範疇而是在行政管理、經濟學和心理學的範疇探索貪污腐化、缺乏效率和政府無能的原因。學者們開始分析政府的實際活動,開始運用資料去探討在政治問題發揮作用的各種因素。
促使對政治的研究適應現代需要的第三個因素則在於對經濟基礎的探討。
經濟是政治的基礎,隨著壟斷的深入,金融巨頭和大工業資產階級對政治的影響日益明顯,這一集團對指定政策亦起了極大作用。而在經濟上,壟斷亦必然導致財富的集中和
貧富分化的加劇,新出現的社會問題亦源於此。新政治學家對此進行了探討,揭示了壟斷的罪惡。
20世紀中葉,美國民主政治的五大領袖:布賴恩、拉福萊特、威爾崐遜、
西奧多·羅斯福和
富蘭克林·羅斯福都是進化論和實用主義的信奉者,同時,他們認識到政治的經濟基礎和
壓力集團對制定政策引起的作用。他們把新政治學的理論運用到實際中去。
(七)法律:
進化論和實用主義哲學同樣在法律的演變中起到重要作用。固定的,機械的法律概念和能動的政治思想發生了衝突,法律結構的重新調整成為必然,這一任務由新法理學家們完成。而羅斯特·龐德為自己規定的任務是要使法律成為實現社會重建的有效工具,他把其法學思想稱為“社會學的法理學。”
社會學的法理學象實用主義一樣,是一種方法——一種考慮法律和套用法律的新方法。這種方法從絕對論轉到相對論,從理論轉到實踐,從被動的——因而是悲觀的——宿命論轉到創造性的——因而是樂觀的——自由天地。它斷言:好的法律就是能充分為社會服務的法律;法律是為實用而制定的,應根據目的而不是根據起源來理解法律;法律的實際作用比抽象的法定內容更為重要。法律要依靠社會而不能脫離社會。法律必須適應社會的需要,並根據滿足這些需要的程度來判斷法律的好壞。它指出法律的生命在於執行和實施;而法律界是繼續不斷的社會產物;法律是可以繼續不斷地改進,最後,法律既關心個人利益也同樣關心集體的社會利益;整個一系列有關社會的利益、需要和需求都合理地屬於法律管轄範疇。
由此可見,實用主義和進化論原則滲入到社會學的法理學中去。法律是進化的,法律也是為現實服務的。人們開始把注意力引向法律的實施而不是法律的制定。
(八)宗教:
認為“普遍接受基督教是他們國家繁榮昌盛的一個主要根源,他們的國家是上帝恩寵的特殊對象”,美國人一直自詡為天之轎子,故而宗教在美國是繁榮昌盛的,而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科學技術浪潮的衝擊以及19世紀末進化論和實用主義對美國人心靈的征服,美國的宗教在繁榮表象之後,神學卻在緩慢地走向破產,教會的物質勢力從來不像現在這樣強大,而精神力量也從不像現在這樣微弱。
隨著教會深入到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同時,其本身也逐漸退出學術思想領域,穩步趨向
世俗化,宗教越來越成為社會活動而不是靈性交流,宗教主要成為奉行某種儀式和做好事的機構。而教會認可對社會承擔責任,又逐漸形成基督教的社會化,有些教會甚至聲稱個人的解救與社會改造不可分開,“企圖在現世建立一個天國,而不願去等待幻想中的太平盛世。”
另外,《美國精神》一書還對新、舊交替時期的美國建築的特點進行了介紹。
“1890年的美國同1860年的美國是完全不同的。我成了十足的陌生人。無論是我,還是任何別的人都無法理解它。”(
亨利·亞當斯)
的確,在這新、舊過渡的時期,人們充分感知個人命運在整個
資本主義社會嚴酷法則面前的軟弱無力與在生存競爭進化原則鼓勵下的心靈的掙扎的痛楚,人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醜惡痛心疾首的同時,不免又對傳統的溫情留戀不已,舊有的價值觀念土崩瓦解,人們又在尋覓和建築新的價值體系……。這一切的一切形成一種世紀末的迷茫。而這種迷茫則在各種
社會思潮以及社會科學各學科的演變中得以充分體現。《美國精神》一書就為我們描繪了人們在這世紀末的迷茫中的徘徊和尋覓。
而歷史是向前發展的。如作者在之中所言:“首先是進化論,然後是科學決定論,深刻地改變了大多數美國人的觀點;即使對那些本人不諳專門的教義以至新觀點的含義的人來說,也是如此。美國人以往通常只接受物質領域裡的變化,也在準備接受思想和道德領域的變化了;他們已不大象往常那樣,對他們支配或控制變化的能力充滿信心了……,20世紀崇拜的是勤奮肯乾而不是聖母瑪利亞,而且,正如他感覺到的那樣,這種崇拜是荒誕無稽的。每一領域都擯棄絕對主義即使在道德上也是如此……實用主義戰勝了與之競爭的種種哲學體系,這倒不是由於實用主義具有優越的邏輯性,而是由於其優越的現實性和實用性,而一個崇拜
個人主義的民眾卻把哲學社會化了,並把社會科學這一術語套用於歷史,經濟和政治。便利的通訊手段,城市化和
人口流動同數以千計的出版,廣播和電影機構結合在義起,使得在性格和習慣方面比19世紀產生大得多的一致性。美國成為世界強國以及二次世界大戰促使美國放棄孤立主義從而使
國際主義得以滲進思想和社會實踐領域,並越來越變得具有世界意義了。文化這個東西不斷趨於民主化,也許可以說是大眾化了。
由是,作者得出結論:“20世紀的美國精神比19世紀中葉以至18世紀中葉更為成熟。”二十世紀的美國人在走出世紀末的迷茫之後也更加成熟。
《美國精神》一書始終關論於“那個我稱之為美國精神的難以捉摸的東西”即“一種獨特的美國思想,性格和行為方式”。為此,作者在哲學、文學、歷史、政治學、法律、經濟學、宗教、建築等各方面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從而抽象出一種本質的、共同的東西以揭示由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這一背景下人們的心理狀態。同時也對這一時期美國的思想、文化演變與發展進行全面剖析與評價,故而成為了解現代美國的一扇視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