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
1866年1月29日在法國
勃艮第地區的克拉姆西出生。從小在諳熟音樂的母親的薰陶下養成了對音樂的愛好。1880年,定居巴黎。15歲時,隨父母遷居巴黎。1886年中學畢業後考入
巴黎高等師範學校,1889年,畢業於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通過會考取得了中學教師終身職位的資格,並開始與他崇拜的
托爾斯泰通信。1889~1891年,在羅馬的法國學校就讀。此後多次去
義大利、
貝魯特、
比利時和荷蘭等地旅遊,收集創作素材。其後入羅馬法國考古學校當研究生。歸國後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和
巴黎大學講授藝術史,並從事文藝創作。
 羅曼·羅蘭
羅曼·羅蘭創作之旅
1897年,羅曼·羅蘭在《巴黎雜誌》上發表第一部作品《
聖路易》及上演他最初創作的兩部悲劇《阿爾特》與《狼》。1899年發表《
理性的勝利》。羅曼·羅蘭早期寫了7個劇本,以歷史上的英雄事件為題材,試圖以“革命戲劇”對抗陳腐的戲劇藝術。20世紀初,他的創作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1901年,《
丹東》首次在《
半月刊》上發表。1902年,發表《
七月十四日》。1903年羅蘭為了讓世人“呼吸英雄的氣息”,替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樹碑立傳,連續寫了幾部名人傳記:《
貝多芬傳》(1903)、《米開朗琪羅傳》(1906)和《
托爾斯泰傳》(1911)共稱《名人傳》。同時發表了他的長篇小說傑作《約翰·克利斯朵夫》。該小說於1913年獲法蘭西學院文學獎金,由此羅曼·羅蘭被認為是法國當代最重要的作家。1904年,《約翰-克里斯多夫》的第一章發表在巴黎《
半月刊》上。1905年《約翰-克里斯多夫》的前三章獲得費米納獎,取名為《
幸福的生活》。1905年,奧朗道夫書店開始出版這部作品,與《半月刊》競爭。1892年,他與巴黎名教授勃萊亞之女克洛蒂爾特結婚,一位千金小姐,又是名交際花,愛上了一個窮書生,這在當時的社交界傳為佳話。1901年,由於一介寒士的羅蘭終究無法滿足闊小姐出身的妻子的心意,兩人便離了婚。離婚以後,他的創作活動改變了方向,傾注全力寫作他的長篇巨著《約翰·克利斯朵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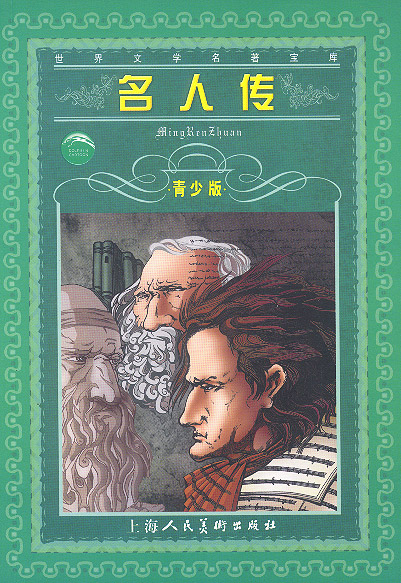 名人傳 羅曼·羅蘭
名人傳 羅曼·羅蘭一戰爆發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羅曼·羅蘭定居在日內瓦,他利用瑞士的中立國環境,寫出了一篇篇反戰文章,他的立場受到了德國作家
托馬斯·曼等人的指責。但他沒有屈服。1914年在《日內瓦日報》上發表《超然於紛爭之上》。1915年他為了表彰“他的文學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繪各種不同類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對真理的熱愛”,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但由於法國政府的反對,結果拖到1916年的11月15日,瑞典文學院才正式通知他這一決定。羅曼·羅蘭將獎金全部贈送給國際紅十字會和法國難民組織。1917年,
俄國十月革命爆發,羅曼·羅蘭與
法朗士,
巴比塞等著名作家一起反對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行動,他公開宣稱:“我不是
布爾什維克,然而我認為布爾什維克的領袖是偉大的
馬克思主義的
雅各賓,他們正在從事宏偉的社會實驗。”
1917年,羅曼·羅蘭放棄國際
紅十字會獎的獎金和其他文學獎金。1918年,發表《阿格里讓特城的恩培多克勒》。1919年發表了寫於1913年的中篇小說《
哥拉·布勒尼翁》,1920年發表了兩部反戰小說《格萊昂波》和《皮埃爾和呂絲》,1922至1933年又發表了另一部代表作《欣悅的靈魂》。這一時期還發表了音樂理論和音樂史的重要著作七卷本《貝多芬的偉大創作時期》(1928-1943),此外還發表過詩歌、
文學評論、日記、回憶錄等各種體裁的作品。1922年~1937年,旅居瑞士的維爾奈夫。1922年,發表《
戰敗者》。1924年,發表《
甘地傳》。1934年,羅曼·羅蘭與一位俄國婦女瑪麗·庫達切娃再婚。1935年6月,羅曼·羅蘭應
高爾基的邀請訪問了蘇聯。並與
史達林見了面。1931年,發表《向過去告別》。1937年9月,羅曼·羅蘭在故鄉克拉木西小鎮附近購買了一座房子,1938年5月底他從瑞士返回故鄉定居。
 1921年
1921年晚年
1940年德軍占領巴黎,羅曼·羅蘭本人被
法西斯嚴密監視起來,1944年8月,
納粹敗退,巴黎解放。他才又見到了光明。1944年12月30日,羅曼·羅蘭去世。享年78歲。1945年1月2日在他的故鄉克拉姆西鎮舉行了宗教葬禮。
主要作品
劇作
從1898年至1903年,他參加了“人民戲劇”運動,前期作品主要有取材於法國大革命的《革命戲劇集》,包括《群狼》(1898)《
丹東》(1900)《七月十四日》(1902)等劇本8部;
 《約翰·克利斯朵夫》
《約翰·克利斯朵夫》傳記
小說
長篇巨著《
約翰·克利斯朵夫》。中篇小說《哥拉·布勒尼翁》(1919),以及一系列反映其反對戰爭、反對一切暴力。害怕團隊精神制度妨害個人“精神獨立”等思想的論文。後期作品有長篇小說《
母與子》(舊譯《欣悅的靈魂》)四部:《阿耐蒂和西勒維》(1922)《夏天》(1924);
其它
《母與子》(1927)《女預言家》(1933)和一系列散文、回憶錄、論文等。特別是1931年,他發表了《向過去告別》。
寫作特點
戲劇
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在巴黎日常生活中占統治地位的,是那種荒淫無恥、庸俗透頂和出賣靈魂的文學。羅蘭果然十分痛恨這種文學,但也無力與它去作有效的鬥爭。他覺得只有拿起自己一支禿筆作為武器,通過革命的歷史題材,去創作一些寓有深意的劇本,在他構想的“人民劇院”上演,才能使意志消沉的法國人民重新振作起來,才能用巨大的道德力量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去激發法蘭西民族的復興,這就是羅蘭創作劇本的宗旨。本著這種宗旨,羅蘭在十年中寫下了十二個劇本。這些劇本當時都沒有出版,只有個別劇本在小劇院上演過。它們失敗了。十年的青春年華盡付東流。原因何在呢?主要原因在於當時統治法國文壇的是一些庸俗低級的作品,觀眾也習慣了這類作品。羅蘭的劇本中不但沒有色情,而且都是一些政治性的、理想主義的、英雄主義的主題。這當然無法滿足頹廢、消沉的法國一代觀眾的要求。
羅蘭在自己的劇本中,究竟宣傳了什麼理想,什麼精神呢?羅蘭所處的時代,歐洲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已經十分尖銳,工人運動已經興起,共產主義的幽靈已經在歐洲上空遊蕩。由於環境和教育的關係,羅蘭沒有接受共產主義世界觀。就這一點說,羅蘭當時是落後於他的時代的。作為脫離現實鬥爭的正直的知識分子,他對真理的探索,必然導致一些超階級的內容。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前,羅蘭一心嚮往的,基本上就是人道主義、和平主義以及自由、公正、良心、意志、.信仰等等這樣一些抽象的概念,所以羅蘭在1898年寫成的《群狼》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祖國還是公正。羅蘭在1899年寫成的《理性的勝利》中,提出了另一個問題:祖國還是自由,民族的利益還是超民族的理性的利益。羅蘭在1902年寫成的《總有一天》中,又提出了一個問題,祖國還是良心,應當服從自己的祖國,還是自己的良心。如此等等。羅蘭認為自己總是站在失敗者一邊。
1898年5月3日,羅蘭的劇本《哀爾特》被搬上一個小劇院的舞台。半個月之後,該劇院又上演了他的另一個劇本《群狼》。但這一插曲沒有挽救羅蘭劇本創作失敗的總的命運。羅蘭後來在《廣場上的集市》中痛快地加以鞭撻的巴黎文藝界,始終對他的劇本冷若冰霜。他不迎合庸俗的市民情趣,去寫作一些時髦的題材,以求得到容易發表的機會。他只寫激動他內心精神世界的作品,說自己要說的話,不為了名利而出賣靈魂。
傳記
羅蘭寫作英雄傳記,為的是鍛造自己,也為了給苦難中的不知名的兄弟們以安慰“偉大的心靈宛如高山風暴衝擊它們,烏雲纏繞它們,可是在那兒,呼吸卻比別處更加強有力。空氣在那兒有一種純淨,能讓心靈去掉污跡”他的《貝多芬傳》前言,猶如一面旗幟,“周圍的空氣令人壓抑舊歐洲在悶熱和污濁的氣氛中窒息了。一種沒有偉大的功利主義壓抑著思想—世界在精明的、待價而沽的自私自利中衰弱下去了。世界簡直透不過氣來讓打開窗戶吧!把自由的空氣放進來吧。讓呼吸英雄們的心靈吧。”
在一個物質生活極度豐富而精神生活相對貧弱的時代,在一個人們躲避崇高、告別崇高而自甘平庸的社會裡,《名人傳》給予人們的也許更多是尷尬,因為這些巨人的生涯就像一面明鏡,使人們的卑劣與渺小纖毫畢現。人們寧願去讚美他們的作品而不願去感受他們人格的偉大。在《米開朗琪羅傳》的結尾,羅曼·羅蘭說,偉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不說普通的人類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們應上去頂禮。在那裡,他們可以變換一下肺中的呼吸,與脈管中的血流。在那裡,他們將感到更迫近永恆。以後,他們再回到人生的廣原,心中充滿了日常戰鬥的勇氣”。這實在是金石之言。
《名人傳》非常好地印證了一句中國人的古訓:古今之成大事業者,非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韌不拔之志。貝多芬的“在傷心隱忍中找棲身”,米開朗琪羅的“愈受苦愈使我喜歡”,
托爾斯泰的“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無不表明偉大的人生就是一場無休無止的戰鬥。時代的千變萬化,充滿機遇,人們渴望成功,但卻不想奮鬥,要的是一夜成名。浮躁和急功近利或許會使人們取得曇花一現的成就,但絕不能躋身不朽者之列。《名人傳》也許會讓人們清醒一些。
即使劇本失敗,羅蘭仍舊繼續創作。不過他改變了創作形式,主要是寫作他的《名人傳》,所謂《名人傳》,直譯就是英雄傳。在羅蘭心目中,什麼人是真正的英雄呢。羅蘭說:“我所說的英雄,不是指那些靠自己的思想和威力而取得勝利的人。我所說的英雄,是指那些具有偉大靈魂的人。”所以羅蘭要歌頌的英雄,不是凱撒,不是拿破崙,而是貝多芬、米蓋朗琪羅、托爾斯泰。那么羅蘭寫《名人傳》的主旨是什麼呢?羅蘭在《貝多芬傳》中說:“周圍的空氣是窒息的。老舊的歐洲在沉重而汗濁的氣氛中呻吟。缺乏宏偉業績的物質主義壓抑著思想,世界在斤斤計較和賣身投靠的利己主義中毀滅。世界已奄奄一息。要打開窗子。要讓新鮮的空氣進來。要呼吸英雄們的精神。”就是說,羅蘭要用英雄們的偉大精神,來改造當時歐洲普遍存在的物質主義的利己打算,用高尚的德操來拯救歐洲的墮落。
小說
羅曼·羅曼所熱衷的是表現自我精神探索的直接經驗。以主人公人生遭際中的靈魂經歷構建情節框架是他小說創作的基本特徵。誠如中國著名學者羅大岡所說,“偉大的心”和“真誠的藝術”是貫穿羅曼·羅蘭創作道路始終的原則精神。儘管《約翰·克利斯朵夫》和《母與子》兩部長篇巨著都展現了當時社會歷史的廣闊畫面,但占著中心位置的都是主人公的情感律動和思想態勢,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存在於主人公的意識裡面並內化成他們精神日臻完善的動力,社會生活背景又總是隨著主人公內心活動的張弛起伏而時顯時隱。是人們慣常把這兩部巨著統稱為“思想小說”。
羅曼·羅蘭的這種創作個性跟巴爾扎克、狄更斯、左拉等人注重表理客觀世界外部形態的權威經驗幾乎背道而馳,跟斯丹達爾、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內傾性的藝術風格也有著明顯區別。他的小說“不以故事為程式而以感情為程式”(《<約翰·克利斯朵夫>定本序言》),講述“一個真摯、漫長、富於悲歡苦樂的生命的內心故事”(《<母與子>初版序》)。心理分析和心態描寫在這裡不再是取決於人物所處的特定環境的第二性內容,而已經是處於首要的主導的位置的直接強烈表現。羅曼·羅蘭的獨到成功使一度風行的偏執於“模仿自然”的現實主義理論陷入了窘迫的困境。曾幾何時,古希臘文論史上的“模仿自然”和“表現心靈”之爭,被人推演成橫亘古今、非此即彼的價值標準,把“模仿自然”尊奉為唯物主義進步思想的基點和現實主義創作的不二法門,把“表現心靈”貶斥為喻心主義反動觀念的標誌和非現實主義的共同要害。這種貌似嚴正的理論,不僅混淆了哲學上的認識論和文學的創作論的兩者界域,而且經不起實踐的檢驗,史有甚者,還會將現實主義窒息於狹窄收耳胡同里。
在正面性格的結構形式上,羅曼·羅蘭的經驗也是彌足珍貴的。“每個人身上都有二十個不同的人”(羅曼·羅蘭《哥拉·布勒尼翁》),羅曼、羅蘭筆下的正面人物都是多重性格的合成體。就數量言,克利斯朵夫身上的缺點幾乎不少於優點,“我毫不隱藏地暴露了他的缺點與德行”。他魯莽、笨拙、輕信和有些自鳴清高,脾氣乖僻易怒,遇事手忙腳亂,思想不夠靈活,生活不拘小節,還跟好些女性有過風流瓜葛。在安乃德身上,存在著十分強烈的女性的本能要求,她情懷熾熱,容易鐘情,先後愛上過好幾個男人;她獻犢情深,為子的成長時喜時憂,對兒子的少年任性不勝痛心,兒子參與冒險行為後她不止一次地從夢中哭醒。
這種從多方面多角度描寫而成的正面性格,不僅豐富生動,而且切合生活的本色形態,“把真實和偉大這兩種特性調和、匯集、結合起來……創造出高於但又和一同生活的人物”(雨果《莎士比亞論》),使正面典型具備了感人至深的藝術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堅持現實主義立場的羅曼·羅蘭跟同時代的現代派作家們在多重性格的表現上存在著根本區別。現代派作家們出自人性不可知論的意念一味地描寫人物的多重性格,從而導致了形象的渙散解體。羅曼.羅蘭則是把握住了形象的正面性格機制中處於主導地位的探索進取精神,任憑人物內心世界的多種因素在性格的運轉過程中發生形形色色的變化,而始終如一的精神力量總是把歷經百轉千回的性格一直推進到崇高境界。這種嚴格遵循現實主義確定性原則的表現,開創了正面典型性格結構的典範。
羅曼·羅蘭獨創性的藝術成就是多方面的,仁述而外,他還首創了長河小說(又稱江河小說)的體裁和音樂小說的形式,引進了史詩、悲劇、抒情詩、哲理小說等多種表述方式。他的富有個性的小說藝術不僅領了風氣之先,成為現實主義發展史上跨越世紀的里程碑,而且對曾經風行一時的現實主義研究方式提出了挑戰。這種方式把現實主義抽象成一些概念系統,並演化出對號入座、固定劃一的評價標準。如果它是科學,羅曼·羅蘭豈不要被排斥於現實主義的範疇之外,這將是何等荒謬!從生活出發而不是從觀念出發是現實主義作家創作的一條重要藝術準則。羅曼·羅蘭把自己的作品“獻給各國受苦、奮鬥、而必勝的自由靈魂”(《<約翰·克利斯朵夫>獻辭》),並且說:“不論克利斯朵夫、哥拉和安乃德有理沒理,反正他們存在。生活本身就是一條不小的理由”(《<母與子>初版序》)。他的藝術構思和典型塑造完全來自對生活的長期觀察和思考、體驗和積累,這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一生為爭取人類自由、民主與光明進行了不屈的鬥爭。他的小說特點,常常被人們歸納為“用音樂寫小說”。
音樂角度
羅曼·羅蘭從創造或創造者的角度來言說音樂的,他真正關心的不是音樂作品的外在形式,不是音樂在聽眾那裡產生的心理效應,而是在音樂家心中促成音樂來臨的創造性力,關心的是音樂從虛無中誕生的過程。羅曼·羅蘭的音樂家傳記和音樂小說比其他音樂小說高明的地方,就在於他從不糾纏於各種浪漫傳奇故事,而是在作品中展示音樂創造的秘密。《約翰·克利斯多夫》說的是發生在音樂家靈魂之中的故事。約翰·克利斯多夫從每一次的經歷中吸取音樂的靈感,從無數的歡樂和痛苦中痛飲音樂的美酒,逐漸地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化為一閡宏偉的交響樂。如同胡塞爾的“先驗自我”直接地通向上帝,約翰·克利斯多夫作為最有人性者和創造的化身也被塑造為塵世的上帝。在約翰·克利斯多夫身上,羅曼·羅蘭完成了對音樂的最高愈義的現象學還原。
當試圖用語言“客觀地”描述音樂時,困難就成倍地增加。這種描述實際上是企圖用語言去轉化、翻譯、解釋音樂。而任何轉化翻譯或解釋都是有限度的。羅曼·羅蘭曾經比較語言和音樂:
貝多芬常常竭力要把自己內,‘深處的感覺,把那種微妙的精神狀態翻譯成音樂,這是不能用文字解釋得清楚的,但它又像文字那樣確定——實際上.更為確定;因為文字是一種抽象的事物,它能總結許多經驗、而且能包含多種不同的意義。比之說話,音樂的表達能力和準確性,比文字要大上成百倍。由此可知,要表現特殊的情感和題材,不僅是音樂的權利,而且是音樂的義務。如果沒有擔當起這個義務,其結果將不成其為音樂——那簡直什麼東西也不是。
按照上面的文字,音樂的世界恰恰存在於抽象的語言文字之外:語言結束之後,音樂方才開始。確實,語言作為經驗的結晶總是擅長言說一般之物,直接的經驗卻總是特殊的、具體的、新鮮的、獨一無二的、不可重複的;而後者正是藝術尤其是音樂的領域。如果一般的、日常的語言能夠表達音樂之所表達,能夠如實對等地翻譯音樂,那么音樂可能就不再存在了。語言必定早已取音樂而代之。因為音樂相對來說只是少數專家精通的工具,而語言人人會說,語言對於廣泛地交流的經驗顯然更加方便。退一步說,即使語言在某種程度上傳達出音樂的表現效果,這種傳達肯定也達不到完美無缺的地步,那么把這拙劣的替代品拿來作甚?不能流動的水只是一潭死水。
現象學是關於本質的學問,通過一般意義的現象學還原之後,就應當對懸置所保留的領域做本質的描述。實際上,這兩個步驟幾乎不存在明顯的分界線。因為“現象”或“音樂”並非一堆變化不定、雜亂無章的感覺複合體或無形式、無結構的質料,感覺質料由於意義的給予而被統一為一個對象。因而羅曼·羅蘭的“感覺”、胡塞爾的“直觀”,本身就是本質性的;在這種感覺和直觀中,對象本身就是被構造或被創造的。感性直觀和本質直觀在這裡是統一的。當然本質還原畢竟屬於更高的層次,它是藉助於所謂“變更”而實現的。打個比方,“變更”的機制好似讓高水平的許多鋼琴家演奏同一樂曲,不同的演奏使不變的本質得到一系列的顯現。通過“想像力的自由變更”,得以把握變中的不變,直觀對象的本質;而通過本質還原,可以發現一個具有結構、層次和意義的現象系列,一個無窮的可能系統。羅蘭甚至也有類似這種本質系統的文學描述:
忽然聲音來了:有些是沉粉的,有些是尖銳的,有些是噹噹的響若,有些是低低的吼著。孩子一個又一個的聽上老豐天,聽它們低下去,沒有了;它們有扣田玲里的鐘聲,奴奴蕩蕩,隨看風吹過來又吹遠去;細聽之下,遠遠的還有的不同的聲音交錯迴旋,仿佛羽蟲飛舜;它們好像在那兒叫你,引你到遙遠的地方……愈趁愈遠,直到那神秘的一角,它們理進去了,沉下去了……這才消滅了!……吸!不!它們還在喃喃細語呢……還在輕輕的拍著翅膀呢……這一切多么奇怪!。
聖·馬丁教堂的大鐘開始奏鳴:先是一個最高的音,孤零零的像一頭哀鳴的鳥向天發問;接著響起第二個音,比前一個低三度,和高青的哀吟結合在一起;然後足及低的一個五度音.仿佛是時前兩個青的薈復。三個音觸成一片。在鐘揍底下,那竟是一個巨大無比的蜂房裡的合唱。空氣和人的心都為之如勸。克利斯多夫屏著氣,心裡想:音樂家的音樂,和這個千千萬萬的生靈一齊叫吼的音樂的海洋相比,真足多么可憐;這足殲獸,是音響的自由世界,決非由人類的聰明分門別奧,貼好標籤,收拾得整整齊齊的世界所能比擬。他在這片無邊無岸的音響中出神了……
當約翰·克利斯多夫洞察這個音響世界後,他就能夠根據這個音響世界在自己的音樂中創造出無限豐富的音響效果。當然羅受·羅蘭在這裡使用了文學手法,根據現象學,這個音響世界的本質系統並不依賴於“教堂鐘聲”之類的經驗事實,它在音樂家作曲的同時就已經無形地、“先天地”存在了。
人物思想
羅曼·羅蘭人道主義的思想基礎首先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
烏托邦思潮,尤其是泛神論者盧梭富於詩意的民主理想,再加上1789年公布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1793年代表小資產者以及勞苦大眾意識的資產階級左翼山嶽黨垮台,右翼政黨吉隆丹掌握政權以後,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實際上成為一紙空文。羅曼·羅蘭不知不覺地反映小資產階級知識者的階級意識,天真地把自由平等博愛的宣言看成永恆不變的真理。自從青年時期以來,他懷著恢復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革命理想,堅持自由平等博愛的方向,希望能把這個口號變為實際行動。他認為這是振奮人心,復興法蘭西民族的關鍵問題。中年以後的羅蘭,基本上仍舊懷著這種理想和熱烈願望,不過不再和青年時代一樣,他想“振興”的不再局限於法蘭西祖國與歐洲,而是全世界,全人類。
 羅曼·羅蘭的簽名
羅曼·羅蘭的簽名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條件下,人道主義有不同的內容與特點。而且,即使在同一歷史時期,同一階級之中,在不同的階層,不同的個人身上,人道主義的表現也不免大同小異,各有千秋。羅曼·羅蘭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他同時期的資產階級官僚、政客、商人、資本家,以及為帝國主義效勞的文人、記者的偽善的人道主義,也有深刻的區別,不可混為一談,雖然從思想體系上說,他們的人道主義都屬於唯心主義,主觀主義的範疇。
羅曼·羅蘭的人道主義還有一個特點:宗教感情。羅曼·羅蘭思想的三個重點,那就是宗教意識、真理的追求和博愛精神,簡單說,就是“神”、“真”、“愛”三個字。這三方面互相聯繫,但也有主次之分。最主要、最根本的因素,他認為是“神”,也就是“上帝”。神的“靈光”無往而不在。宇宙萬物,無非神靈顯現。神的靈光反映在個人良心中,出現一個“愛”字.凡此種種,羅曼·羅蘭皆深信不疑。作為藝術家,羅曼·羅蘭從未單獨提到一個“美”字舀他認為美是真和善的結晶。美是愛的反映;真是神的化身,文學藝術作品都應當以“真”為靈魂,“愛”為血肉,才能夠有動人心魄的精神感召力。藝術不是單純的形式美,不是單純的技巧。在羅曼·羅蘭回憶錄《內心旅程》中有一段話發揮他的唯愛論:“對於天生是音樂家的我來說,畢生的努力在於將生命各種相反的因素,以及他們的規律,組成嘹亮的綜合曲調。有兩條原則:(一)真理……對自己要真誠;除開自己認為真誠的東西之外,不多說一個字,該說的也不少說一個字……(二)愛,人類愛;愛……共同的歡樂,共同的痛苦……同情的規律。我把這股奔騰的流水,合併在同一條河床里:愛與真理的合流。”
羅曼·羅蘭十分強調個人、自由、個人意識。因為他認為個人意識是神靈在個人心中的顯現。個人意識的崇高目標是對“愛”與“真”的無休止的追求。這就是羅蘭的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緊密結合的原由。正和他的人道主義不能和資產階級統治勢力,也就是說上層資產階級偽善陰險的人道主義相提並論一樣,他的個人主義也不能和市儈式的唯利是圖的個人主義相提並論。他的個人主義目的不在於個人享受,不論物質享受或精神享受。他反對文學藝術上的唯美主義,認為那是一種供精神享受的奢侈品。羅曼·羅蘭的個人主義強調依靠個人力量促進人類泛愛的實現,他的個人主義是他的烏托邦式的世界大同思想的組成部分。
資產階級統治集團虛偽地宣傳的“人權”、“人道主義”,事實上早已破產,這是無法否認,不容諱言的。凡爾賽政權對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戰士以及巴黎的廣大革命人民的血腥大屠殺,是資產階級口頭的人道主義徹底破產的鐵證。西方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人民的殘酷壓榨和屠戮,也是西方資產階級統治集團口頭人道主義破產的鐵證。為什麼有些人看到“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破產”這個論斷,表示極大的反感?難道我們必須卑躬屈節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辯護士嗎?但是,把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的虛偽陰險的人道主義和羅曼·羅蘭的書生氣的、天真的泛愛人道主義信念混為一談,確實是不正確的。把羅曼·羅蘭的書生氣的人道主義言論作為西方資產階級上層的策略性的偽善人道主義破產的一個例證,確實是形上學式的引申,是錯誤的論點。糾正這種錯誤的聯繫和引申,但是決不能同意全部推翻西方資產階級作為階級鬥爭的手段之一的虛偽人道主義破產的論斷。因為否定這個論斷等於否定客觀現實,而歷史事實是不容否定,也無法否定的。
總而言之,對於羅曼·羅蘭人道主義的看法可以歸結為下列幾點:(一)從思想體系上說,羅曼·羅蘭的唯心論的、主觀主義的人道主義理想和信念屬於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範疇;(二)根據對具體事實的分析,羅曼·羅蘭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資產階級統治集團口頭的虛偽人道主義有本質的區別,前者的出發點是追求真理和實行泛愛,後者的目的是衛護個人利益和階級利益;(三)羅曼·羅蘭的人道主義對資產階級統治勢力的關係顯然表現為離心力的作用,而不是向心力的傾向:(四)羅曼·羅蘭的人道主義在他個人漫長和艱辛的進步過程中,起了一貫的促進作用,換言之,是他思想不斷進步的積極因素之一。當然,這種人道主義的階級局限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在他思想進步的過程中起了消極的作用,但是他的人道主義的積極面對他思想進步過程所起的積極作用是主要的,決定性的,而他的人道主義所產生的消極作用是次要的,非決定性的。
人物評價
在茨威格心目中,羅曼·羅蘭占據著崇高的地位。《昨日的世界》寫到兩人第一次見面時說:“我在他房間裡感覺到一種人性的、道義上的優勢;一種不帶驕傲情緒的、內心的自由,這種自由對於一個堅強的人來說是不言而喻的。我一眼就看出,他在關鍵性時刻將代表歐洲的良知。”茨威格還評價說:“詩歌、音樂、科學的三位一體與法、德、意文化三位一體的交融在羅蘭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體現”,“成為時代精神的代言人、世界的良心”。
盧那察爾斯基稱讚羅蘭為:“和平主義教皇”。
他獲得了19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的評價為:“文學創作中高度的理想主義以及在描寫各種不同典型時所表現出來的同情心和真實性”。
人物影響
羅曼·羅蘭一生貫穿人道主義思想。前期受託爾斯泰影響較深,主張全人類抽象的“愛”、以“英雄精神”對抗社會淪喪,文化墮落,提倡藝術為普通人服務。
20世紀30年代,羅曼·羅蘭積極投身進步的政治活動,他任國際反法西斯委員會主席,聲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並出席巴黎保衛和平大會,對人類進步事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他旗幟鮮明地反對兩次世界大戰,反對納粹德國迫害季米特洛夫、呼籲蘇聯停止對知識分子的流放、乃至反對國民黨政府對左翼作家的鎮壓等等,在維護正義方面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羅曼·羅蘭的作品也對人起到了指導作用,傅雷的少年經歷及感染浪漫派文學,對他的情緒有極大影響,用他自己後來的話說:“神經亦復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在遊學期間,他先後到過瑞士、比利時、義大利、但“均未能平復狂躁之情緒。”但是,傅雷的這種情緒很快就被羅曼·羅蘭轉移。留法不久,一個偶然的機會,傅雷讀到了羅曼·羅蘭寫的一本小書《貝多芬》,“讀罷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燭照,頓獲新生之力,自此奇蹟般突然振作。此實余性靈生活中之大事。”由此可見,這本小書的產生,是作家受到貝多芬精神影響的結果。羅曼·羅蘭當時的狀況,與此時的傅雷頗為相似,故此,傅雷便如“神光燭照”,感動得“不禁嚎啕大哭”了。
羅曼·羅蘭是王元化所喜愛的作家。王元化青年時代所寫的這兩篇讀《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文章,認識獨到,見解高遠,後收在1952年初版的作者文學評論集《向著真實》一書中。羅曼·羅蘭與《約翰·克利斯朵夫》,確實是王元化的精神寶藏。據王元化的高足胡曉明教授介紹,直到王先生仙逝之前的那一年,還在請人讀這本書。而且還在其夫人去世後,寫過有關這本書最新的心得。日本學人相浦杲先生是深知王元化的,他說王先生對羅蘭的認識一直沒有變。這在王元化,是一種長期的人文生命的堅守。
 羅曼·羅蘭
羅曼·羅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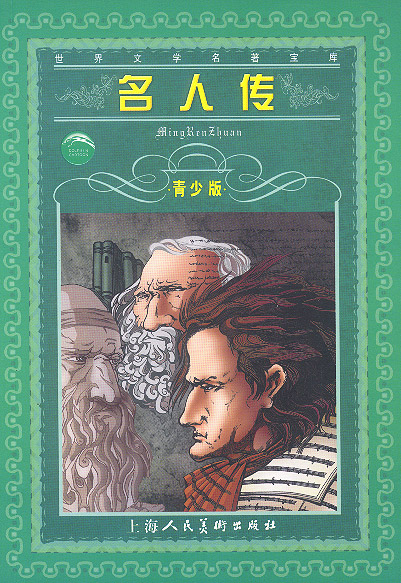 名人傳 羅曼·羅蘭
名人傳 羅曼·羅蘭 1921年
1921年 《約翰·克利斯朵夫》
《約翰·克利斯朵夫》 羅曼·羅蘭的簽名
羅曼·羅蘭的簽名
 名人傳
名人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