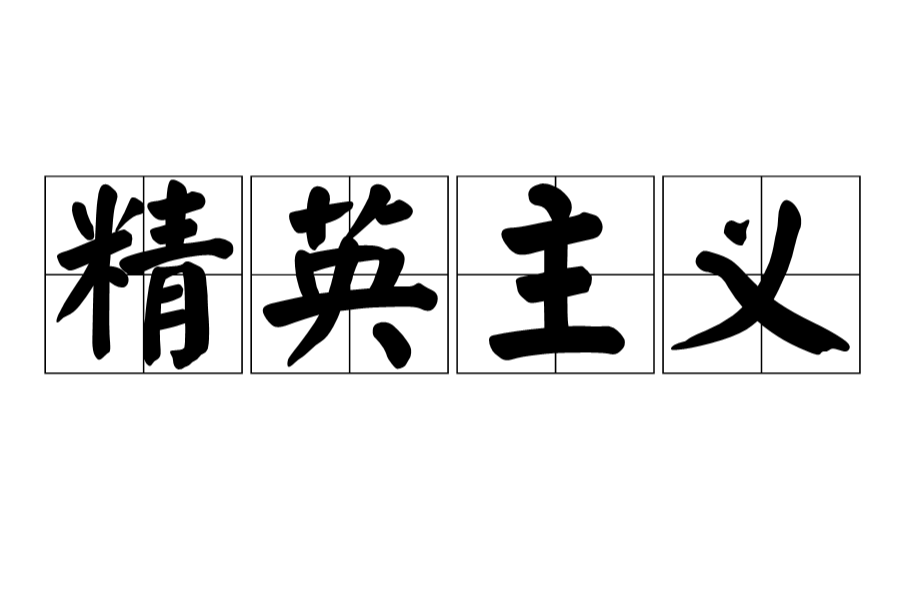發源
儘管人們可以從
柏拉圖、馬基雅弗利等人的著作中找到精英主義的蛛絲馬跡,且蘇格拉底有公開的精英主義傾向(其主張唯有“有理性的有知識的人”才能擔任雅典陪審員)。但是,一般觀點認為系統而有影響的精英主義形成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其發展的頂峰。
早期的精英主義發源於義大利。莫斯卡、
帕累托、米歇爾斯、
奧爾特加、勒龐等人在批判大眾民主的基礎上發展了早期的
精英主義理論,韋伯、熊彼特等人則從民主政治出發,論證了精英民主的政治合理性。當代的精英主義者,如伯納姆、
米爾斯等人則從經濟和制度的角度論證了精英主義。
興起
精英主義的興起反映了西方思想界對大眾民主興起的保守態度,人們試圖以精英主義來對抗大眾民主的潮流。受到來自
多元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潮的批判和挑戰,精英主義在當代日趨衰落。晚近崛起的新精英主義則更多關注利益集團,試圖在精英決策、精英統治的合法性等問題上有所突破。
 精英主義
精英主義人們常常使用“權力精英”、“社會精英”、“寡頭”、“統治階級”等概念來稱呼精英。
帕雷托在區分“精英統治”和“民眾”兩個概念的基礎上從“高度”和“素質”兩個方面來定義精英;
韋伯、
熊彼特等人傾向於將精英視為民主政治的獲勝者;拉斯維爾則試圖以“高度”的概念作為定量地分析精英的標準。但時至今日,即使是精英主義者內部,精英的含義亦並不一致。
早期精英主義
早期的精英主義有一種貴族傾向,把身份、地位、財產作為衡量精英的標準。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精英主義逐漸接受並融合了民主的某些要素,發展成為精英民主。精英主義民主否認古典民主理論中“
人民主權”、“公意”、“共同福利”等價值取向,更傾向於將民主視為一種方法或是一種程式,對民主採取工具主義的態度。這種程式民主的概念直接影響到達爾、亨廷頓等人的民主理論。
精英主義關注社會的權力結構及其特性。早期的精英主義更多地體現為一種
社會理論,它把社會中的人分為精英與大眾兩種類型,並提供了“精英—大眾”的兩分法。
以大眾主義者的角度而言,常認為精英主義者是蔑視大眾的。甚至認為精英主義是一種蔑視、嘲笑,甚至是仇視普通大眾,認為大眾是一個無知、盲動而又自命不凡的群體的
主張,而認為“奴隸”、“野蠻人”、“烏合之眾”、“群畜” 等名詞是精英主義下的產物(這很可能是一種對精英主義的誤會與偏見)。事實上,理想的精英主義其實具有一種高道德的自持,關於知識的追求更是無止境的。真、善、美的全面成長應當是身為精英的使命。然而,精英主義卻常成為既得利益者作為剝削、奴役中、下層階級的藉口,以致使精英主義這個觀念後來卻成為 “剝削者”、“敵視大眾者”的代名詞,但這樣的認知都是具有階級偏見的。
以人類歷史而言,高度文明(civilization)通常為上層精英所開啟。因為上層精英通常不需擔憂生存問題,而有
餘力去發展文化活動以致於高度的文化活動----文明。但這樣的成果當然是精英階層與大眾階層合作的結果。若無大眾階層提供生產服務,精英階層如何能有餘力發展文明。由此可知,精英階層與大眾階層的存在,在人類文明的發展上都是不可缺少的。但這樣的明確二分法卻是無謂的。畢竟,一個人是否為精英(或大眾階層),這種界定並沒有明確的指標,因為真理的追求是無止境的。既為無止境,就沒有絕對的精英。但大眾階層卻是可以明確界定的。若一個人沒有“永恆性的體認(靈性、良知的體認)”、沒有“成長的自覺”、不知行合一的去求知、求真,那這樣的人就很有可能成為“無知者”。然而,缺乏上述體認的人在人類歷史中卻占多數(相對於精英、知識份子而言)。是以,這多數人就可稱為“大眾”。大眾(mass)一詞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開始被強調,這個字被強調是由於相對於資產階級(常是一群“非” 追求真、善、美,而為追求利益的少數壟斷資源的人)的多數人的自覺。他們自覺與“主流文化”(他們認為這是以精英階層的意志所建構的)、“剝削者”、“有錢人”不同,而提出的一種自我文化的強調。
在政治理論上,精英主義反對大眾民主,主張精英治國。精英主義者幾乎普遍對民主政治抱有悲觀主義情緒。在他們眼裡,民主制是騙人的把戲,根本不會成功。由於刻意去迎合大多數人的利益,民主政治常常發展成為所謂的“暴民政治”,只有政治精英才是民主政治的堡壘,佑護民主免於暴民政治。
在政治認知上,精英主義貶低
理性的作用,推崇
政治現實主義。精英主義綜合了社會學、心理學甚至是數學、經濟的方法,主張理論研究的中立、客觀。他們常常以
科學主義自居,主張從現實出發來理解政治社會的結構與發展,對二戰後興起的政治科學有著重要影響。
精英主義的興起從另一個角度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某些缺陷,精英主義傾向於將民主視為程式的作法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民主與自由主義的結合,為當代西方
憲政民主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在現代
政治學理論體系中,精英主義理論的影響已經超出其理論本身,在政治科學領域裡有著重要地位。然而,精英主義蔑視普通大眾,反對民主,宣揚
個人主義的英雄史觀,其理論上的缺陷亦毋庸置疑。
相關文章
概述
精英主義
民粹主義與寡頭主義看似相反而實相生,因此順利的
轉型就當是:不要民粹主義,但不能不顧人民;不要寡頭主義,但不能扼殺精英。“大眾”與“精英”在個人尊嚴與
公民基本權利上應當平等。 近年來國內一些
論著開始重視反對民粹主義的問題 。實際上在“全球化”的市場經濟改革中,民粹主義也成了“全球”性的話題,“社會轉型與民粹主義”的問題日益受到關注。一種有代表性的意見認為:民粹主義作為一種主張“革命”的激進思潮實為害群之馬,應當大力清除之,而代之以權威主義;民粹主義會帶來災難性的“大民主”,遠不如明君加順民的“傳統”制度好。另一種較緩和的意見則認為:民粹主義重視“人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卻流為“拜民主義”的極端,應當以精英主義來糾正它或至少是調和它,實現大眾與精英兼顧、下層與上層妥協的主張。
評述
這些看法的共同點在於:都把民粹主義理解為對“人民利益”、“人民立場”的強調,因而主張精英至上、權貴本位的人傾向於全盤否定它,而主張上下兼顧的人則傾向於否定其極端並調和之。這一共同點恐怕是從“民粹主義”這一名詞給人的印象而來。民粹主 義這一譯名其實有欠準確,它的英、俄原詞都以“人民”為詞根,應譯為“人民主義”或 “平民主義”,從這一字面上看它似乎是很排斥精英傾向與權威傾向的。但考諸史實則大不然。歷史上的
民粹派其實不但不反對權威,而且甚至可以說是極端的權威崇拜者。他們不僅容不得反對派,甚至容不得“旁觀者”。俄國民粹派當年有句名 言:“誰不和我們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誰反對我們,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而對敵人就應該用一切手段加以消滅。”民粹派最著名的領袖特卡喬夫曾說過大意如此的一段話:什麼叫革命?革命就是少數人強迫大多數人接受前者所賜予的幸福。當年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與民粹派的第一場論戰就是圍繞“政治問題”展開的。民粹派反對西方式的民主,認為 西方的“統治機關是選舉的,選出來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們欺壓窮人” 。因此“對人民來說,兩害相權取其輕,
專制的沙皇還比立憲的沙皇好些。”而馬克 思主義者則嚴厲抨擊這種“反對政治自由(據說這只能使政權轉到資產階級手裡)的徹頭 徹尾的民粹派份子的觀點”,並堅持認為議會民主決不“只是資產階級的工具”,它也是無產階級組織的工具。另一方面,民粹主義者也決不反對精英主義,而且甚至還是極端的精英主義者。俄國民粹派當年的“英雄駕馭群氓”的著名理論就是典型,這種理論主張英雄創造歷史、英雄主持正義,而人民則是無關緊要的“背景”和無知或只知“模仿”的群氓。 當然,從民粹派主張中更能找到無數尊崇“人民”、強調“民主”的詞句。那么這些 話與上面所引的那些精英主義、權威主義言論如何統一呢?是否其中有一方為主而另一方為次、一方為真話而另一方只是說說而已?顯然不是,實際上與其說民粹派是平民主義者或精英主義者,不如說他們首先是整體主義者,與其說他們和平民主義或精英主義構成對立,不如說他們首先與各種“個體主義 ”構成對立。而他們的平民傾向與精英傾向,“民主”傾向與專制傾向,正是在這一點上得到統一的。
民粹主義者崇拜“人民”這不假,但他們崇拜的是作為一個抽象整體的“人民”,而對組成“人民”的一個個具體的“人”卻持一種極為蔑視的態度,無論這個“人”是勞動 者即所謂“平民”,還是知識分子即所謂“精英”。民粹主義中最缺乏的就是公民個人尊嚴與個人基本權利的觀念。在民粹派看來,一個個的“人”只是作為整體的“人民”的工 具,前者在後者面前微不足道,只要後者的“利益”需要,就應當毫不猶豫地拿前者作犧 牲,而不必考慮他的意志。俄國民粹派崇尚農奴制時代的傳統農村公社(
米爾),主張“ 在米爾的集體中消解自我”,就是基於這種整體主義觀念。
民粹主義者崇拜“人民”,尤其崇拜當時占俄國人口大多數而且生活在米爾公社中的農民。他們因此常被認為具有重農主義傾向、輕視城市工人等等。然而這種“重農”與崇尚自由經濟的法國重農學派截然相反,民粹派所崇拜的農民只是農村公社精神的化身,而對於現實中個體農民擺脫米爾束縛的要求十分敵視。在民粹派著作中,這些獨立農民被罵為“守財奴”(即кулак,這個詞後來被漢譯為“富農”,其實它最初只是俄語中一個罵人的詞,既無“富”也無“農”的詞義)。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現象:俄國民粹派一方面極言知識分子的虛偽、委瑣於農民樸實、崇高,甚至提出“知識分子應當拜倒在農民腳下”,但另一方面又強調要束縛農民,據說農民一旦“脫離土地,忘記‘務農’,那么俄國人民、人民的世界觀、人民發出的光和熱便不復存在,剩下的只是空虛的靈魂、‘完全的自由自在’、可怕的‘愛上哪兒就上哪兒’”。於是,說出知識分子應當“拜倒在農民腳下”的同一個民粹派思想家在另一個場合又嚴厲地宣稱:“公社最兇惡的敵人就是‘當家的’、‘當家作主’和‘有產有業’的農民”。
 精英主義
精英主義同樣,民粹主義者崇拜“英雄”,但與像卡萊爾、
胡克這類西方市民社會的“英雄” 論者截然不同,他們心目中的“英雄”只是共同體的人格化身、整體意志的代言人。民粹 派一方面要求一個個的農民都要聽命於代農村公社立言的“英雄”,另一方面強調“個人主義”的小知識分子要拜倒在整體“人民”腳下。“平民主義”與“精英主義”、“人民 崇拜”與救世主意識、個人對“大眾”的負罪感與英雄對“群氓”的優越感在他們那裡是完全融合為一體的。顯然,在這種情況下以“精英主義”或權威主義來反對(或平衡)“平民主義”或民主主義,並不能跳出民粹主義的陷阱。這就正如在民主問題上“多數決定”機制的缺陷不能用“少數決定”或個人獨裁來彌補一樣。為避免“多數決定”侵犯“少數”或個人的公 民基本權利而形成多數暴政,必須確立每個公民(無論其屬於多數還是少數,甚或只是獨 立的一個人)都享有基本權利的原則,這些權利既不能被“多數”(甚至是“整體”)剝 奪,當然更不能被少數人剝奪。
通俗地說,民粹主義的特徵是:它認為五個人只要一致決定就能剝奪第六個人的財產 。(或生命,或個人意志)。這種想法的害處是顯而易見的。但為了糾正它決不能倒過來,讓一個人有權決定剝奪那五個人的財產。實際上,這樣的“顛倒”恰恰可以從民粹主義本 身的邏輯中推出來:既然五個人的決定就有權剝奪第六個人,那末作為“五人共同意志” 之化身的這個人便可以剝奪這第六個人,同時也可以以同樣理由剝奪那五個人中的任何一 個,換句話說也就是一個人有權剝奪五個人。顯然,要避免這樣的危險,既不能強調“多 數特權”也不能強調“少數特權”,而只能強調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
在市場經濟改革中,“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實際含義是承認每個公民都有在市 場競爭中追求
個人利益的權利,儘管競爭結果實際上只能有一部分人作為贏家得到了更多 的利益,但只要他們沒有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權利,就不能以“整體”的名義(例如以“共同富裕”的名義)剝奪他們。
然而這決不意味著只給少數人以追求個人利益的特權。“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決 不能理解為只給這部分人(哪怕他們是“精英”)“富起來”的權利或
機會。恰恰相反, “富起來”的權利與機會應當是給予每個公民的,至於他們怎樣利用這種權利與機會並且 取得了怎樣的結果則是另一個問題。農村大包乾是“允許一部分人先富”的實踐,但作為 致富機會的土地並不是只給了“一部分人”,而是基本平均地分給了全體社員,就是這個 道理。
正是在這一點上體現了改革的“人民性”,這個“人民性”是決不能以“精英主義” 來取消或調和的。然而現在的確有一種可慮的觀點,即以反對民粹主義為由損害改革的人 民性,把允許部分人先富變成了只給部分人以致富的機會與權利。這是必須反對的。 改革的確應當破除民粹主義觀念,即破除那種以整體主義侵犯公民個人尊嚴與基本權 利(不僅僅是侵犯“精英”的尊嚴與權利)的想法與行為。這個任務是艱巨的,但這個任 務與破除“寡頭主義”實際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過程。只有制止那種以“第一級火箭” 、“原始積累”之類理由損害改革公正性的寡頭主義傾向,才能有效地排除那種以整體利 益為理由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民粹主義危險。同樣,政治觀念上的“拜民主義”與“拜官 主義”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正如歷史上的民粹派既鼓吹“人民專制”又鼓吹英雄救世 一樣。以“拜官主義”反對“拜民主義”,也正如以寡頭主義反對民粹主義、以不公正的 “競爭”反對“反競爭的公平”一樣,只能造成惡性循環。 如今不少論著強調民粹主義危險主要產生於社會轉型期,這大致不錯。但人們往往忘記指出:不公正的轉型方式是產生這種危險的主要土壤,而寡頭主義則是轉型期不公正的主要表現。俄國民粹主義在19世紀只是一種知識界思潮,使其“到民間去”的種種努力當時均未奏效,而到世紀末它在知識界也已失去影響。正是以“國家是為強者而存在的”這一寡頭主義構想為標幟的
斯托雷平改革,使民粹主義不僅死灰復燃,而且很快發展為一股 社會大潮,最終衝垮了斯托雷平體制,並使自由主義與
社會民主主義都成了這一體制的殉葬品。而伊朗巴列維王朝大搞“
權貴資本主義”的“白色革命”,也激起了以伊斯蘭教為符號的又一次民粹主義狂潮,並使公民權利成了巴列維王朝的陪葬。相反,公正的轉型方式是民粹主義的最佳免疫劑。美國歷史上民粹主義一直不成氣候,這既不是因為美國的“文化”與歐洲有多大不同,也不是因為美國缺少據說是民粹派土 壤的“公社”(美國最早的殖民
拓荒者也多經歷過公社生活,而且從
歐文、卡貝直到今天的
摩門教徒,各種“公社”的實驗在美國從未停止過),而是因為美國沒有歐洲那種封建 等級制遺產,在向
工業社會邁進時少有寡頭主義的扭曲,因此人們更相信公平競爭而不相信民粹主義的“反競爭的平均”。當代的“捷克模式”也是個例子,在東歐諸國中最富於 左派傳統的這個國家對激進轉軌的阻力反面最小,轉軌過程的公正防止了民粹主義情緒的產生是個重要原因。
總結
總之,民粹主義與寡頭主義看似相反而實相生,因此順利的轉型就當是:不要民粹主義,但不能不顧人民;不要寡頭主義,但不能扼殺精英。“大眾”與“精英”在個人尊嚴與公民基本權利上應當平等。至於他們在競爭的社會中形成的差別,則應當在起點平等、規則平等的公正原則下得到承認——當然,在這一原則下上述差別只能是動態的。誰也不能自封天生的或永恆的“精英”,正如誰也不能自封天生的或永恆的“大眾”代言人一樣。
 精英主義
精英主義 精英主義
精英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