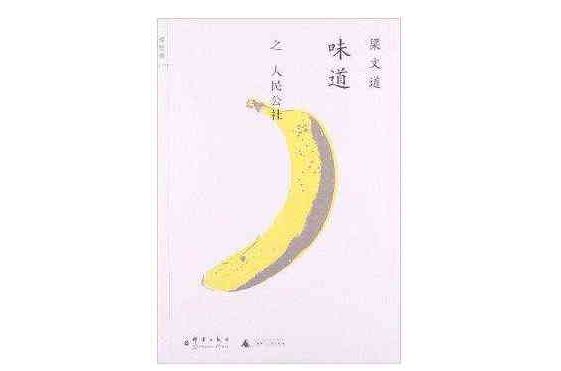《味道·人民公社》為梁文道食評文集《味道》系列之一,主要談論“吃”的社會意涵,挖掘不同場合、不同人群、不同社會、不同時代人們“吃”的不同內容與邏輯,引出“吃”作為不可或缺的社會紐帶的意義,正是“吃”聯結或區隔了不同的個人與群體。
基本介紹
- 書名:理想國·味道:人民公社
-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群言出版社
- 頁數:240頁
- 開本:32
- 作者:梁文道
- 出版日期:2013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802564053, 7802564050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名人推薦,
內容簡介
《味道·人民公社》是梁文道筆下的“飲食社會學”——“吃”是聯結社會的紐帶,是構成“人民公社”的基石
作者簡介
梁文道,1970年生於香港。1988年開始撰寫藝評、文化及時事評論,並曾參與各種類型的文化及社會活動。現為鳳凰衛視評論員,《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等中國內地、香港及馬來西亞十餘份報刊雜誌專欄作家。主要著作有《常識》、《我執》。
圖書目錄
自序 行外人的懺悔
第一輯 吃的邏輯與禁忌
吃飯吃出了一個社會
請客吃飯的邏輯
敬酒要喝
喝還是不喝
吃飯時吃飯 屙屎時屙屎
守規矩
一片考驗良心的火腿
開齋
吃齋
素食
第二輯吃與被吃者
羊怎樣成了羊肉
寵物雞變成了豉油雞
雞肉不等於雞
貓該怎么吃
三花
痛與奢華
飲水思源
一飯之恩
第三輯吃的恐懼與偏見
一代不如一代
自己帶油上餐館
自求多福
真假難辨
“天然”食品
另一種太空競賽
為什麼老麥薯條味道好
麥當勞是香港人的排隊老師
老麥歡迎你回家
豬的氣味
自從家裡多了一位外傭
在鐵路上開餐
Smoking European
第四輯吃的豐裕與貧困
早餐里見世界
如何煮一頓公平晚餐
稻田的故事
嘗一口韓國農民種的米
喝的不是咖啡,是生活
賣咖啡的方法
良心要花錢買嗎?
別小看薯仔
蕎麥復仇記
集中營寄來的食譜
饑荒
再慘也要吃
人不止靠糧食而活
浪費
人車爭食的年代
國宴的藝術
好日子結束了
算賬
革命從慢食開始
新人類的吃
當起義來到廚房
絕食
第一輯 吃的邏輯與禁忌
吃飯吃出了一個社會
請客吃飯的邏輯
敬酒要喝
喝還是不喝
吃飯時吃飯 屙屎時屙屎
守規矩
一片考驗良心的火腿
開齋
吃齋
素食
第二輯吃與被吃者
羊怎樣成了羊肉
寵物雞變成了豉油雞
雞肉不等於雞
貓該怎么吃
三花
痛與奢華
飲水思源
一飯之恩
第三輯吃的恐懼與偏見
一代不如一代
自己帶油上餐館
自求多福
真假難辨
“天然”食品
另一種太空競賽
為什麼老麥薯條味道好
麥當勞是香港人的排隊老師
老麥歡迎你回家
豬的氣味
自從家裡多了一位外傭
在鐵路上開餐
Smoking European
第四輯吃的豐裕與貧困
早餐里見世界
如何煮一頓公平晚餐
稻田的故事
嘗一口韓國農民種的米
喝的不是咖啡,是生活
賣咖啡的方法
良心要花錢買嗎?
別小看薯仔
蕎麥復仇記
集中營寄來的食譜
饑荒
再慘也要吃
人不止靠糧食而活
浪費
人車爭食的年代
國宴的藝術
好日子結束了
算賬
革命從慢食開始
新人類的吃
當起義來到廚房
絕食
序言
行外人的懺悔
從藝術評論到時事評論,再到現在這堆飲食文字,這二十多年以來,仿佛不論我寫些什麼,只要我退一步思考自己正在寫的東西,它們就會把我引回同一個源頭。在我看來,這一切寫作類型似乎都可以溯源到一段時間、一個地點;那便是從啟蒙運動到法國大革命這一百年里的巴黎了。
回想最初,當我還在努力書寫藝術評論的時候,我就時常在想自己正在書寫的這種東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和讀者有什麼關係,它在社會中又據有什麼位置。一邊思考一邊閱讀,很自然地我就找到了狄德羅。這位法國“百科全書派”的思想領袖死在大革命前五年,公認是引爆大革命的思想源流之一。其實這位多才多藝的啟蒙怪傑還是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藝評家,所謂“現代意義”指的並非在他之前沒有人評論藝術。不,當然不是,從柏拉圖以來,西方關於藝術的書寫從來沒有斷過。但狄德羅是第一個會經常為不同畫展撰寫單篇評論的人,而且他在每一篇評論里還要花掉不少篇幅去描寫那些畫作的細節,似乎是要讓那些無法親臨畫展但又對它們很感興趣的讀者也能“看見”他所目睹的作品,這種先描述後評論的體式也成了日後藝評常見的習慣。
我關心的還不是狄德羅的藝評成就,而是使得他得以創造出這種評論類型的條件。首先,自當有經常對公眾開放的畫展,那些藝術品不再只是專供親友觀賞的私藏;而且有展出時限,不會永久存放在一個固定的地方。然後要有一群愛好藝術的觀眾,他們自己未必擁有多了不起的藝術收藏,只是想多開眼界,還想跟上藝壇潮流。再來還必須要有一個成熟的出版機構,以及流通印刷品的健全市場,使得這些評論能夠面世,能夠被人買回家去閱讀。換句話說,狄德羅之所以是最早的藝評人之一,並不在於他有開天闢地的創見,而在於這么多條件乃至於機制的存在。這些條件延續至今,雖有變化,但早在法國大革命前便種下了現代藝術體系的社會環境。從這個角度來講,藝術評論的出現無異於一整套藝術體系之誕生的標誌。
短打型的時事評論就不必多說了,今人對“公共領域”的出現早有了解,都知道大盛於啟蒙時代的這種寫作是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運動的催化劑之一。
現在我想多說一點關於飲食評論的事。無論是一般食經作者和美食家,還是對法國大革命素有研究的中國學者,大概都很少想到看起來完全無關的這兩件事的隱秘聯繫。所以,我想介紹葛立莫·德·拉-黑尼葉(Alexandre Balthazar Laurent Grimod de la Reyni+re),歷史上第一位餐廳評論的作者。他的《老饕年鑑》(Almanach des gourmands)可能是史上第一部餐廳“指南”。他比更多人認識的薩瓦蘭(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味覺生理學》的作者)還要年長,也出道得更早,正好活過了整段革命時期。他的父親是當時法國最有錢的富翁之一,但天生下來就雙手變形的德·拉·黑尼葉很反叛,不願接受家族保守的老觀念。他喜歡誇張的表演,曾經整治過好幾場像劇場演出一樣的宴會,免去侍者,用機器轉盤給客人上菜,乃其時巴黎社交圈裡的名人。但歷史記住了他的理由,則是因為他開創了前所未有的評論類型,也就是我們今天已見怪不怪的餐廳評論。 德·拉·黑尼葉糾集了一幫喜好吃喝的朋友,就像北京一群文人吃客那樣,組成一個“評鑑委員會”,定期聚會,品評大小餐飲供應商的成果。但和北京這些朋友不同,當年那伙巴黎美食家不必依附雜誌,他們乾脆自己出版年鑑。又與今日絕大多數食評不同,他們裁決的不只是食肆,還包括菜販肉商乃至於農場酒莊,有意者可以郵寄樣品,讓這群大老爺在會議中品嘗商量。
中國文人向不避談飲食,今天山東曲阜自誇的“孔府宴”甚至還把它的源頭追溯自夫子那句“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以證文人美食文化之深遠。而且中國大概也是全世界第一個發展出繁盛餐館業的國家,早在宋朝,杭州就出了不少人人嚮往的名店。那時節,一般歐洲人外食的唯一選擇可還是簡陋客棧里的粗湯呢,其高下先後不可以道里計。然而,又的確是德·拉·黑尼葉這夥人以《老饕年鑑》首領今日飲食指南之先河。不知道為什麼,中國古人就是沒想過像他們那樣,以街區為分類,逐一評介各區卓越食肆。如果真要追究,那又是另一個比較歷史的大題目了。
先來看看餐飲這個行業。今日史學界公認西歐餐廳的出現,乃是法國大革命之後的事。從前專為王公貴族做飯的家廚眼看著主人排隊斷頭,頓失依傍,只好跑出來以一技之長在市場上謀生。正好又碰上了新興資產階級有錢有閒,亟欲在生活品味上與舊貴族一競高下,搶奪文化資本領域之內的專制地位。於是一時問,巴黎滿城餐館,尤其不乏裝潢雅致、菜品繁複的高貴名所,正是官學外流,民間享福。且看德·拉·黑尼葉在大革命後幾年的見證:“1789年以前,巴黎餐廳不過百數,現在卻至少多了五六倍新店。”在這種情況底下,消費者要能明辨其中等次,恐非易事。於是一本迷津指南,難免應運而生。
我是個外行,沒有能力在這裡混進宋代有沒有發生過資本主義萌芽的爭論,但不論內行與否,相信都不難看出這是個資本主義的故事。《老饕年鑑》的出版及其大受歡迎,靠的乃是一大群新興消費階層。這些人開始把吃飯理解為一種消費活動,既不只是滿足家常日用層面的生理需要,也不單單是貴族大排筵席式的奢華展覽,而是介乎二者之間,一種同時帶著獵奇嘗鮮的色彩,又可以揉入日常生活之中的特殊行為。這種行為用今天的話講,就叫做“上館子”,看似沒什麼了不起。但請放回當年的背景里看,忽然出了這么一批人,他們可以選擇不在家裡吃飯,出門卻又不是為了到人家裡做客,反而是去一種叫做“餐館”的地方花錢晚飯;這難道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嗎?
一開始,或許只是好奇,想試試所謂的好環境好菜色是怎么回事。後來大家發現,就算是廉價的飯堂,也不失為解決腸胃問題的便利辦法。再隨著工商業的發達,很多人開始把食肆當成午間會議的臨時場地,更多工薪階層則需要它來補氣果腹。於是飲食就和市場上其他一切貨物一樣,真真正正地被納進了現代消費社會的花花世界裡頭。既然消費,便要選擇。一心從事文字創作,有打算以此為業的德·拉·黑尼葉便看準了這個市場上的新需要,操筆下海,乾起了餐館評價的勾當。《老饕年鑑》的目的,就是要告訴大家該當如何選擇。
這是個政治公民與經濟市民同時誕生的年代,在很多人的下意識裡頭,消費非但無罪,甚至還是自由的具體體現。當年的巴黎市民(至少是有資產的巴黎市民)還不像百年後波德萊爾筆下的“漫遊者”那般怪異,毫無目的地在街上信步閒逛;他們比較接近我們現在都會鬧區裡頭的“消費者”,把一張城市的地圖看成是消費活動的潛在對象,每到一塊街區,心裡想的就是這附近有什麼好玩好買好吃。從這個角度來看,整座巴黎便是一座大商場,難怪《老饕年鑑》最受讀者喜愛的部分就是它的分區指南。
相形之下,德-拉-黑尼葉自己最喜歡的諷刺小品則不得不割愛,讓出篇幅給書中那些資料日益豐富的實用指南。於是《老饕年鑑》變了,變得越來越像日後的《米其林指南》,也變得越來越不像文人愛讀的《雅合談吃》那一類趣味散文。《老饕年鑑》連續出了很多年,而且沒有滯銷的跡象,但德·拉·黑尼葉最後還是狠下決心,停止作業。有人認為,那是因為他過不了自己那一關。身為啟蒙之子,身為大革命的過來人,德·拉·黑尼葉本來有很大的抱負,就算當不上第一流的文人思想家,他起碼也要做個優秀的劇作家。豈料命運弄人,喜歡吃喝復又精於此道的他,居然成了個美食家。不只如此,他還發現讀者原來不太欣賞他精心巧構的文字藝術,也不太在乎他自己珍而重之的散文小品,他們只想細讀排在這堆創作之後的餐館指南。這叫他情何以堪?
說起來,德·拉-黑尼葉自己不是預料不到這情況的,早在第一冊的《老饕年鑑》裡頭,他就斷言大革命是個下半身顛覆了上半身的革命,物慾層面的感官享受代替了更高層次的細緻感情,窮無止境的胃口則取締了更上層樓的靈性追求。可是,那又是個《百科全書》之後的時代,文人相信理性非但能夠為世間萬物定下準則的位置,甚至能在這各種事物之中找出它自身依循的原理和準則。所以德·拉·黑尼葉一方面溫和地譏諷大家好吃愛喝的潮流,鄙之為下;另一方面卻又試圖調解矛盾,想要為口腹之慾這種至為本能至為動物的欲望定出它的“理性”和標準。
談到這裡,我們不妨回想—下狄德羅的藝術評論,以及從啟蒙時代一路發展到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所有政論寫作。由此觀之,它們豈不都在制定規則?一幅畫為什麼好?一個政府為什麼壞?討論這類問題全都需要理性和判準。同樣,評價餐館當然也得有它的合理依據,不能主觀隨口地瞎說好吃不好吃。定義“美食”,替“美食”立下原理,這就是德·拉·黑尼葉交給自己的任務了。加上後來的薩瓦蘭,當年就有這么幾個法國人想要把飲食拉上藝術的台面,想要替它創造屬於它的美學。似乎本來再低下不過的肉慾,只要能講出個道理,它的地位便會提高不少似的。所以,德·拉·黑尼葉還不忘反過來教訓食客,指導他們欣賞飲食的“藝術”,告訴他們有品位的進餐態度。例如,“切莫用刀切分麵包。佐餐的麵包該當自己以手掰開,這才是恰當的禮貌”,時至今日,這句話仍被今人視為玉律。換句話說,他想要把惡名昭彰的“饕餮之徒”變成令人艷羨的“美食家”;因為天生下來胃口奇大而來者不拒,並不算是藝術,只有經過教養的有節制有選擇地品嘗才叫做藝術。誠然。德·拉·黑尼葉是西歐第一個把“gourmand”當成正面詞使用的人。在他之前,這原是七宗罪的第一宗罪。
說了這么半天,我好像還沒有進入主題。既是書序,這番歷史回顧和這套集子裡的東西就應該有些關係,但那究竟是種什麼關係呢?坦白講,我也說不大清楚,只能勉強把前面對德·拉·黑尼葉的小小介紹當成是我自己的鏡子,照出自己的思路,也照出自己的困境。
凡乾一事,我總是習慣後退一步,想想自己到底在做什麼,然後再稍稍追溯—下這件事的源流,看看它和周遭環境的關係。於是我寫書評時論,就不免粗糙考據書評與時論的由來;後來在電視台做節目,自然得思考電視與社會的關係。好聽點講,這叫做自覺反省;說難聽點,這是不專心幹活。一個人在騎腳踏車的時候要是太過自覺,心裡老是想著雙腿發力如何帶動齒輪運轉的力學問題,他多半會摔得很慘。同樣,做了十年的電視節目,我至今不肯隨便對著鏡頭說“親愛的觀眾朋友”;因為我老是認為我自己根本不認識那些觀眾,又怎能當他們是親愛的朋友;難怪大家一直嫌我是個不入流的主持人,不夠親切不接地氣(我又忍不住要想:你在螢光屏上看見的“親切”,到底是種怎么樣的“親切”呢?)。就算吃飯,我有時也會想得太多,結果想到最後連飯都沒吃好。以下你可能要看到的這一大堆雜碎,其實就是歷年以來我想得過多吃得過壞的產物。
儘管如此,由於它們都發表在香港飲食雜誌《飲食男女》上頭,沾了不少同文的光,日久我竟然也被人當成了“美食家”,真以為我對這門學問有研究。這可是個天大誤會,其實我不僅不懂吃,還不懂得下廚,完全連入門的門檻邊都摸不著,又怎能攀比如蔡瀾、二毛、沈宏非和陳曉卿等真正行家?就連我這些偶爾被人誤會為“美食文字”或“食經”的爛貨,也都是另一種想得太多的成品。正因為自己寫吃,所以又丟不開老毛病地開始聯想關於飲食書寫的種種,想它在今日獲得崇高地位之奇怪,想讀者和市場對它之渴求的原因,當然更想到了它的前世今生。一邊想,一邊寫,便寫成了這副模樣,很少評論美食,也很少介紹菜譜,甚至也不大願談任何具體菜品,幾乎完全不像合乎常規的飲食書寫。所以至此,除去自己沒貨之外;還有一個理由,那就是我常常懷疑飲食書寫為什麼一定要包含以上幾大要素,飲食書寫之所以成為一種“次文類”的根本條件又是什麼。
今天的氣氛十分古怪,一方面大家不信任專家,喜歡笑罵他們是“磚家”;另一方面大家又愛批評某些人言談跨界,不是專家卻對人家的專業說三道四。究竟我們是真不相信專業門牆的地基,還是打從心底尊重專家的界限呢?在這種狀況底下,包括這堆飲食文字在內,我一切書寫莫不皆屬“偽專家”的妄言,很值得批判。
所以我當然會想起德·拉·黑尼葉以及他所身處的那個世紀,因為那是一個許多規範剛剛成形的年代。在他之前,沒有人知道什麼叫做食評。正是由他開始,才有了這種我們今天熟視無睹的次文類。但和狄德羅的藝評一樣,這不全是一個人的功勞,而是整個經濟環境和歷史脈絡的變動的造就。想起他,想起那百年間出現的無數作者,我不能不思考當書寫藝術不一定是藝評的時候,書寫政治也不一定要合乎某種時評規範的時候。拿我們中國自己的例子來看,問題會變得更加有趣。比方蘇東坡,你說他到底是個美食家、畫家、詩人、旅遊達人,還是個幹部呢?沒錯,他自然是個幹部,是個官員;而那還是個官員也能(甚至也該)舞文弄墨的時代。換到今天,一個官員寫詩寫到拿下魯迅獎,就要人獎俱毀了。我們很容易忘記,這裡頭的要點並不在於幹部能不能也是詩人,而在於他寫得怎么樣(可惜愚見以為,這位奪得魯迅獎的官員也還真寫得不怎么樣)。換了蘇軾活在今天,恐怕也很難免去“偽美食家”、“偽畫家”、“偽詩”及“偽旅遊專家”之譏。
或許我可以體會德·拉·黑尼葉毅然放棄《老饕年鑑》的心情。他立志當個“文人”,大革命前的歐洲文人就該像狄德羅和伏爾泰那樣,自由自在地創作任何體裁的文字,無拘無束地探究任何他感興趣的知識,就算不能學歌德那般探討色彩學的原理,至少也可延續蒙田以來的道路,一切隨筆。然而,當他跟上時代的浪潮,甚至引領潮流,要為美食正名,要替美食定錨之後,他便發現連自己都被定住了。因應市場需要,因應讀者期待,他的寫作不再自由。他不能夠借著吃喝大談革命之後的新形勢,因為人家要看的是一家館子裝潢是否得體,服務是否周到,飯菜是否可口。那是現代餐飲業的萌芽階段,是吃喝逐漸專業的時代,他的寫作既參與了這個時代的創造,也被困在了這個時代裡面。他最後的出路就是出走,離開他手創的事業,離開他心愛的巴黎。
我一邊在乾幾種“專業”的事,一邊又在想像這些專業以外的天空,難免不合時宜,也難免不夠專業。就算“主持人”這個職業身份,我都擔當不起(到了內地,我才知道電視節目主持人也是一種大學裡可以選修的專業)。難怪前陣子有位記者知道我快出新書,就反覆以各種方式問我出書的理由。一開始他問了半天,我都沒搞懂他的意思,後來我才明白那是怕不好意思。他要問的東西很簡單,直白地講就是,一個在電視媒體混飯吃的人,怎么也有膽量跑去學人家出書當作家?
他問得很對,這三卷小書本來就不該出版,出版社兩年前預告,一直被我拖拉至今,即便這篇序言,也是拖到下廠前才勉強趕出,其中一個主要理由就是我真不夠膽。從我做一個普通讀者的角度來說,這套書實在令人遺憾,浪費了無數樹木,浪費了買書的消費者的時間和金錢。我很對不起大家。
從藝術評論到時事評論,再到現在這堆飲食文字,這二十多年以來,仿佛不論我寫些什麼,只要我退一步思考自己正在寫的東西,它們就會把我引回同一個源頭。在我看來,這一切寫作類型似乎都可以溯源到一段時間、一個地點;那便是從啟蒙運動到法國大革命這一百年里的巴黎了。
回想最初,當我還在努力書寫藝術評論的時候,我就時常在想自己正在書寫的這種東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和讀者有什麼關係,它在社會中又據有什麼位置。一邊思考一邊閱讀,很自然地我就找到了狄德羅。這位法國“百科全書派”的思想領袖死在大革命前五年,公認是引爆大革命的思想源流之一。其實這位多才多藝的啟蒙怪傑還是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藝評家,所謂“現代意義”指的並非在他之前沒有人評論藝術。不,當然不是,從柏拉圖以來,西方關於藝術的書寫從來沒有斷過。但狄德羅是第一個會經常為不同畫展撰寫單篇評論的人,而且他在每一篇評論里還要花掉不少篇幅去描寫那些畫作的細節,似乎是要讓那些無法親臨畫展但又對它們很感興趣的讀者也能“看見”他所目睹的作品,這種先描述後評論的體式也成了日後藝評常見的習慣。
我關心的還不是狄德羅的藝評成就,而是使得他得以創造出這種評論類型的條件。首先,自當有經常對公眾開放的畫展,那些藝術品不再只是專供親友觀賞的私藏;而且有展出時限,不會永久存放在一個固定的地方。然後要有一群愛好藝術的觀眾,他們自己未必擁有多了不起的藝術收藏,只是想多開眼界,還想跟上藝壇潮流。再來還必須要有一個成熟的出版機構,以及流通印刷品的健全市場,使得這些評論能夠面世,能夠被人買回家去閱讀。換句話說,狄德羅之所以是最早的藝評人之一,並不在於他有開天闢地的創見,而在於這么多條件乃至於機制的存在。這些條件延續至今,雖有變化,但早在法國大革命前便種下了現代藝術體系的社會環境。從這個角度來講,藝術評論的出現無異於一整套藝術體系之誕生的標誌。
短打型的時事評論就不必多說了,今人對“公共領域”的出現早有了解,都知道大盛於啟蒙時代的這種寫作是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運動的催化劑之一。
現在我想多說一點關於飲食評論的事。無論是一般食經作者和美食家,還是對法國大革命素有研究的中國學者,大概都很少想到看起來完全無關的這兩件事的隱秘聯繫。所以,我想介紹葛立莫·德·拉-黑尼葉(Alexandre Balthazar Laurent Grimod de la Reyni+re),歷史上第一位餐廳評論的作者。他的《老饕年鑑》(Almanach des gourmands)可能是史上第一部餐廳“指南”。他比更多人認識的薩瓦蘭(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味覺生理學》的作者)還要年長,也出道得更早,正好活過了整段革命時期。他的父親是當時法國最有錢的富翁之一,但天生下來就雙手變形的德·拉·黑尼葉很反叛,不願接受家族保守的老觀念。他喜歡誇張的表演,曾經整治過好幾場像劇場演出一樣的宴會,免去侍者,用機器轉盤給客人上菜,乃其時巴黎社交圈裡的名人。但歷史記住了他的理由,則是因為他開創了前所未有的評論類型,也就是我們今天已見怪不怪的餐廳評論。 德·拉·黑尼葉糾集了一幫喜好吃喝的朋友,就像北京一群文人吃客那樣,組成一個“評鑑委員會”,定期聚會,品評大小餐飲供應商的成果。但和北京這些朋友不同,當年那伙巴黎美食家不必依附雜誌,他們乾脆自己出版年鑑。又與今日絕大多數食評不同,他們裁決的不只是食肆,還包括菜販肉商乃至於農場酒莊,有意者可以郵寄樣品,讓這群大老爺在會議中品嘗商量。
中國文人向不避談飲食,今天山東曲阜自誇的“孔府宴”甚至還把它的源頭追溯自夫子那句“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以證文人美食文化之深遠。而且中國大概也是全世界第一個發展出繁盛餐館業的國家,早在宋朝,杭州就出了不少人人嚮往的名店。那時節,一般歐洲人外食的唯一選擇可還是簡陋客棧里的粗湯呢,其高下先後不可以道里計。然而,又的確是德·拉·黑尼葉這夥人以《老饕年鑑》首領今日飲食指南之先河。不知道為什麼,中國古人就是沒想過像他們那樣,以街區為分類,逐一評介各區卓越食肆。如果真要追究,那又是另一個比較歷史的大題目了。
先來看看餐飲這個行業。今日史學界公認西歐餐廳的出現,乃是法國大革命之後的事。從前專為王公貴族做飯的家廚眼看著主人排隊斷頭,頓失依傍,只好跑出來以一技之長在市場上謀生。正好又碰上了新興資產階級有錢有閒,亟欲在生活品味上與舊貴族一競高下,搶奪文化資本領域之內的專制地位。於是一時問,巴黎滿城餐館,尤其不乏裝潢雅致、菜品繁複的高貴名所,正是官學外流,民間享福。且看德·拉·黑尼葉在大革命後幾年的見證:“1789年以前,巴黎餐廳不過百數,現在卻至少多了五六倍新店。”在這種情況底下,消費者要能明辨其中等次,恐非易事。於是一本迷津指南,難免應運而生。
我是個外行,沒有能力在這裡混進宋代有沒有發生過資本主義萌芽的爭論,但不論內行與否,相信都不難看出這是個資本主義的故事。《老饕年鑑》的出版及其大受歡迎,靠的乃是一大群新興消費階層。這些人開始把吃飯理解為一種消費活動,既不只是滿足家常日用層面的生理需要,也不單單是貴族大排筵席式的奢華展覽,而是介乎二者之間,一種同時帶著獵奇嘗鮮的色彩,又可以揉入日常生活之中的特殊行為。這種行為用今天的話講,就叫做“上館子”,看似沒什麼了不起。但請放回當年的背景里看,忽然出了這么一批人,他們可以選擇不在家裡吃飯,出門卻又不是為了到人家裡做客,反而是去一種叫做“餐館”的地方花錢晚飯;這難道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嗎?
一開始,或許只是好奇,想試試所謂的好環境好菜色是怎么回事。後來大家發現,就算是廉價的飯堂,也不失為解決腸胃問題的便利辦法。再隨著工商業的發達,很多人開始把食肆當成午間會議的臨時場地,更多工薪階層則需要它來補氣果腹。於是飲食就和市場上其他一切貨物一樣,真真正正地被納進了現代消費社會的花花世界裡頭。既然消費,便要選擇。一心從事文字創作,有打算以此為業的德·拉·黑尼葉便看準了這個市場上的新需要,操筆下海,乾起了餐館評價的勾當。《老饕年鑑》的目的,就是要告訴大家該當如何選擇。
這是個政治公民與經濟市民同時誕生的年代,在很多人的下意識裡頭,消費非但無罪,甚至還是自由的具體體現。當年的巴黎市民(至少是有資產的巴黎市民)還不像百年後波德萊爾筆下的“漫遊者”那般怪異,毫無目的地在街上信步閒逛;他們比較接近我們現在都會鬧區裡頭的“消費者”,把一張城市的地圖看成是消費活動的潛在對象,每到一塊街區,心裡想的就是這附近有什麼好玩好買好吃。從這個角度來看,整座巴黎便是一座大商場,難怪《老饕年鑑》最受讀者喜愛的部分就是它的分區指南。
相形之下,德-拉-黑尼葉自己最喜歡的諷刺小品則不得不割愛,讓出篇幅給書中那些資料日益豐富的實用指南。於是《老饕年鑑》變了,變得越來越像日後的《米其林指南》,也變得越來越不像文人愛讀的《雅合談吃》那一類趣味散文。《老饕年鑑》連續出了很多年,而且沒有滯銷的跡象,但德·拉·黑尼葉最後還是狠下決心,停止作業。有人認為,那是因為他過不了自己那一關。身為啟蒙之子,身為大革命的過來人,德·拉·黑尼葉本來有很大的抱負,就算當不上第一流的文人思想家,他起碼也要做個優秀的劇作家。豈料命運弄人,喜歡吃喝復又精於此道的他,居然成了個美食家。不只如此,他還發現讀者原來不太欣賞他精心巧構的文字藝術,也不太在乎他自己珍而重之的散文小品,他們只想細讀排在這堆創作之後的餐館指南。這叫他情何以堪?
說起來,德·拉-黑尼葉自己不是預料不到這情況的,早在第一冊的《老饕年鑑》裡頭,他就斷言大革命是個下半身顛覆了上半身的革命,物慾層面的感官享受代替了更高層次的細緻感情,窮無止境的胃口則取締了更上層樓的靈性追求。可是,那又是個《百科全書》之後的時代,文人相信理性非但能夠為世間萬物定下準則的位置,甚至能在這各種事物之中找出它自身依循的原理和準則。所以德·拉·黑尼葉一方面溫和地譏諷大家好吃愛喝的潮流,鄙之為下;另一方面卻又試圖調解矛盾,想要為口腹之慾這種至為本能至為動物的欲望定出它的“理性”和標準。
談到這裡,我們不妨回想—下狄德羅的藝術評論,以及從啟蒙時代一路發展到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所有政論寫作。由此觀之,它們豈不都在制定規則?一幅畫為什麼好?一個政府為什麼壞?討論這類問題全都需要理性和判準。同樣,評價餐館當然也得有它的合理依據,不能主觀隨口地瞎說好吃不好吃。定義“美食”,替“美食”立下原理,這就是德·拉·黑尼葉交給自己的任務了。加上後來的薩瓦蘭,當年就有這么幾個法國人想要把飲食拉上藝術的台面,想要替它創造屬於它的美學。似乎本來再低下不過的肉慾,只要能講出個道理,它的地位便會提高不少似的。所以,德·拉·黑尼葉還不忘反過來教訓食客,指導他們欣賞飲食的“藝術”,告訴他們有品位的進餐態度。例如,“切莫用刀切分麵包。佐餐的麵包該當自己以手掰開,這才是恰當的禮貌”,時至今日,這句話仍被今人視為玉律。換句話說,他想要把惡名昭彰的“饕餮之徒”變成令人艷羨的“美食家”;因為天生下來胃口奇大而來者不拒,並不算是藝術,只有經過教養的有節制有選擇地品嘗才叫做藝術。誠然。德·拉·黑尼葉是西歐第一個把“gourmand”當成正面詞使用的人。在他之前,這原是七宗罪的第一宗罪。
說了這么半天,我好像還沒有進入主題。既是書序,這番歷史回顧和這套集子裡的東西就應該有些關係,但那究竟是種什麼關係呢?坦白講,我也說不大清楚,只能勉強把前面對德·拉·黑尼葉的小小介紹當成是我自己的鏡子,照出自己的思路,也照出自己的困境。
凡乾一事,我總是習慣後退一步,想想自己到底在做什麼,然後再稍稍追溯—下這件事的源流,看看它和周遭環境的關係。於是我寫書評時論,就不免粗糙考據書評與時論的由來;後來在電視台做節目,自然得思考電視與社會的關係。好聽點講,這叫做自覺反省;說難聽點,這是不專心幹活。一個人在騎腳踏車的時候要是太過自覺,心裡老是想著雙腿發力如何帶動齒輪運轉的力學問題,他多半會摔得很慘。同樣,做了十年的電視節目,我至今不肯隨便對著鏡頭說“親愛的觀眾朋友”;因為我老是認為我自己根本不認識那些觀眾,又怎能當他們是親愛的朋友;難怪大家一直嫌我是個不入流的主持人,不夠親切不接地氣(我又忍不住要想:你在螢光屏上看見的“親切”,到底是種怎么樣的“親切”呢?)。就算吃飯,我有時也會想得太多,結果想到最後連飯都沒吃好。以下你可能要看到的這一大堆雜碎,其實就是歷年以來我想得過多吃得過壞的產物。
儘管如此,由於它們都發表在香港飲食雜誌《飲食男女》上頭,沾了不少同文的光,日久我竟然也被人當成了“美食家”,真以為我對這門學問有研究。這可是個天大誤會,其實我不僅不懂吃,還不懂得下廚,完全連入門的門檻邊都摸不著,又怎能攀比如蔡瀾、二毛、沈宏非和陳曉卿等真正行家?就連我這些偶爾被人誤會為“美食文字”或“食經”的爛貨,也都是另一種想得太多的成品。正因為自己寫吃,所以又丟不開老毛病地開始聯想關於飲食書寫的種種,想它在今日獲得崇高地位之奇怪,想讀者和市場對它之渴求的原因,當然更想到了它的前世今生。一邊想,一邊寫,便寫成了這副模樣,很少評論美食,也很少介紹菜譜,甚至也不大願談任何具體菜品,幾乎完全不像合乎常規的飲食書寫。所以至此,除去自己沒貨之外;還有一個理由,那就是我常常懷疑飲食書寫為什麼一定要包含以上幾大要素,飲食書寫之所以成為一種“次文類”的根本條件又是什麼。
今天的氣氛十分古怪,一方面大家不信任專家,喜歡笑罵他們是“磚家”;另一方面大家又愛批評某些人言談跨界,不是專家卻對人家的專業說三道四。究竟我們是真不相信專業門牆的地基,還是打從心底尊重專家的界限呢?在這種狀況底下,包括這堆飲食文字在內,我一切書寫莫不皆屬“偽專家”的妄言,很值得批判。
所以我當然會想起德·拉·黑尼葉以及他所身處的那個世紀,因為那是一個許多規範剛剛成形的年代。在他之前,沒有人知道什麼叫做食評。正是由他開始,才有了這種我們今天熟視無睹的次文類。但和狄德羅的藝評一樣,這不全是一個人的功勞,而是整個經濟環境和歷史脈絡的變動的造就。想起他,想起那百年間出現的無數作者,我不能不思考當書寫藝術不一定是藝評的時候,書寫政治也不一定要合乎某種時評規範的時候。拿我們中國自己的例子來看,問題會變得更加有趣。比方蘇東坡,你說他到底是個美食家、畫家、詩人、旅遊達人,還是個幹部呢?沒錯,他自然是個幹部,是個官員;而那還是個官員也能(甚至也該)舞文弄墨的時代。換到今天,一個官員寫詩寫到拿下魯迅獎,就要人獎俱毀了。我們很容易忘記,這裡頭的要點並不在於幹部能不能也是詩人,而在於他寫得怎么樣(可惜愚見以為,這位奪得魯迅獎的官員也還真寫得不怎么樣)。換了蘇軾活在今天,恐怕也很難免去“偽美食家”、“偽畫家”、“偽詩”及“偽旅遊專家”之譏。
或許我可以體會德·拉·黑尼葉毅然放棄《老饕年鑑》的心情。他立志當個“文人”,大革命前的歐洲文人就該像狄德羅和伏爾泰那樣,自由自在地創作任何體裁的文字,無拘無束地探究任何他感興趣的知識,就算不能學歌德那般探討色彩學的原理,至少也可延續蒙田以來的道路,一切隨筆。然而,當他跟上時代的浪潮,甚至引領潮流,要為美食正名,要替美食定錨之後,他便發現連自己都被定住了。因應市場需要,因應讀者期待,他的寫作不再自由。他不能夠借著吃喝大談革命之後的新形勢,因為人家要看的是一家館子裝潢是否得體,服務是否周到,飯菜是否可口。那是現代餐飲業的萌芽階段,是吃喝逐漸專業的時代,他的寫作既參與了這個時代的創造,也被困在了這個時代裡面。他最後的出路就是出走,離開他手創的事業,離開他心愛的巴黎。
我一邊在乾幾種“專業”的事,一邊又在想像這些專業以外的天空,難免不合時宜,也難免不夠專業。就算“主持人”這個職業身份,我都擔當不起(到了內地,我才知道電視節目主持人也是一種大學裡可以選修的專業)。難怪前陣子有位記者知道我快出新書,就反覆以各種方式問我出書的理由。一開始他問了半天,我都沒搞懂他的意思,後來我才明白那是怕不好意思。他要問的東西很簡單,直白地講就是,一個在電視媒體混飯吃的人,怎么也有膽量跑去學人家出書當作家?
他問得很對,這三卷小書本來就不該出版,出版社兩年前預告,一直被我拖拉至今,即便這篇序言,也是拖到下廠前才勉強趕出,其中一個主要理由就是我真不夠膽。從我做一個普通讀者的角度來說,這套書實在令人遺憾,浪費了無數樹木,浪費了買書的消費者的時間和金錢。我很對不起大家。
名人推薦
我這些偶爾被人誤會為 “美食文字”或“食經”的爛貨,其實是另一種想得太多的成品。正因為自己寫吃,所以又丟不開老毛病地開始聯想關於飲食書寫的種種,想它在今日獲得崇高地位之奇怪,想讀者和市場對它之渴求的原因,當然更想到了它的前世今生。一邊想,一邊寫,便寫成了這副模樣。
——梁文道
——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