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作者
《湘山野錄》的作者
文瑩,字如晦,一說字道溫,北宋時期
錢塘人。生卒年月不詳,大約生活在真宗至神宗這一段時間。據《
文獻通考》引
晁公武《
郡齋讀書志》,說文瑩是吳地僧人,而《
四庫全書總目》的作者認為《通考》有誤,認為文瑩在荊州之
金鑾寺隱居並著成《湘山野錄》一書。
內容
《湘山野錄》寫成於神宗
熙寧年間,主要內容是記載自北宋開國至神宗時期的歷史,內容十分廣泛,涉及朝章國典、宮闈秘事、將相軼聞,下及風俗風情,主要內容仍是朝廷高官顯貴的趣聞軼事。這個
文瑩雖是身居佛寺,卻也是心在朝廷,不甘寂清之人,書中有幾個條目記載他和當朝大臣的一些交往,語氣中也不滿自得之氣。雖是身在佛門,也只不過佛門中的一個
凡夫俗子罷了。
因為是當朝人記載本朝的歷史,所以書中就不免以尊者諱,為賢者諱,而且不僅諱,更有為皇帝臉上貼金之事。如卷上《聞前代興亡以自省戒條》記載仁宗繼位後告訴大臣“除君臣不可聞之事外,自余皆宜明講。”一副虛心納諫的面孔。後來當宮內侍講大臣講解《
禮記·檀公篇》中“君即位而為捭,歲一漆之。”
鄭玄解釋“捭,著身棺也。”但侍講大臣因為是講皇帝即位後就要造棺材,不願明說。待講經完畢,侍講大臣退出後,仁宗獨留尚書
宋祁詢問真相,宋祁只好實話實說。仁宗大笑說:“死生,常理也,何是憚”。其實這是一件小事,也說明不了多少問題,但
文瑩在這裡卻小題大做,把它當作仁宗的一個美德。
卷下《真宗求占城稻種》條記載宋真宗“深念稼穡聞占城稻耐旱,西天綠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貨求其種。占城得種二十石,至今在處播之。西天中印土得綠豆種二石。始植於
後苑,秋成日近臣嘗之,仍賜占稻及西天綠豆御詩。”這裡是讚美宋真宗重視農業,關心農業生產。
《湘山野錄》的主要內容當然是對皇帝歌功頌德、塗脂抹粉。但這位僧人也有口沒遮攔的時候,有時把統治階級內部勾心鬥角的黑暗內幕也一不小心給說了出去,這裡最明顯的例子是關於太祖太宗之交“斧聲燭影”一案的記載。《續湘山野錄》“太宗即位”條是這樣記載的:祖宗潛耀日,嘗與一道士游於
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無,每有乏則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
劇飲爛醉。生善歌《步虛》為戲,能自引其喉於
杳冥間作
清徵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祖宗聞之,曰“金猴虎頭西,真龍得其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語,豈足憑邪?”至
膺圖受禪之曰,及庚申正月初四日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遍訪之,或見於
軒轅道中,或嵩洛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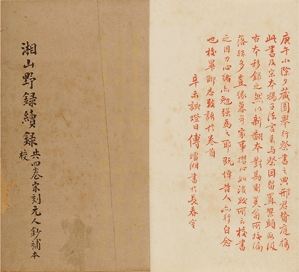 湘山野錄
湘山野錄後十六載
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已祓禊,駕幸西沼,生醉坐於岸木陰下,笑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與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謂曰:“我久欲見汝
決克一事,無他,我壽還得幾多在?”生曰:“但今年十月廿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後苑。苑吏或紀見宿於木末鳥巢中,止數日不見。帝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四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氣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
宮鑰開端門,召開封王(即太祖
趙光義)。延入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
三鼓,殿雪已數寸,帝引拄斧截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
周廬者寂無所聞,帝已崩矣。太宗受遺詔於柩前即位。逮曉登明堂,宣遺詔罷,聲慟,引近臣環玉衣以瞻聖體,玉色溫瑩如出湯沐。
這一段記載的開始,
文瑩是想宣揚太祖帝位得來的神秘性,但一不小心,把太宗繼位的可疑性給暴露出來,頭天晚上很活潑硬朗的皇帝第二天早上突然駕崩,而且身邊只有御弟一人,人們無法不懷疑太宗繼位的合理性,也就給後人留下了“斧聲燭影”的千古之謎,至今仍在困惑著不少的專家、學者。
文瑩在書中還揭露了統治階級內部的勾心鬥角,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冒著
欺君之罪,對有可能威脅到自己前途和命運的人,坑蒙拐騙,威脅利誘,
無所不用其極。在卷上《种放三不便之奏》和《种放為權威所陷》條就揭露了一樁權貴的一個大陰謀。种放是北宋時期著名的
隱士,據說曾師事
陳摶老祖,對北宋的弊端有著自己清醒的認識和獨到的見解。宋真宗在西嶽祭祀回京途中,駐在河中府,當有三千名長安人要求皇帝去長安光臨一下,而且要求十分堅決。真宗不知如何是好,就找种放一起決定是否去長安。种放懇切勸阻,認為有三條理由不能去長安,其一“陛下方以孝治天下,翻事秦、漢,侈心封禪郡岳,而更臨游別郡,久拋宗廟,於孝為闕。”其二“精岳重臣扈從車蹕,京國一空,民心無依,況九廟乎?”其三,“其百司供擬頓仗事繁,晚春蠶麥已登,深費農務。”真宗接受了种放的勸阻,並慨嘆滿朝的文武大臣,並沒有一人勸阻自己。种放說:“這些人都願意隨從護駕,舉行百世盛典,趁機中飽私,撈取名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盤。”當時真宗便想邀請种放一起回朝,种放沒有答應。真宗臨行又告訴种放,有一天會讓他到朝廷去。這一下把好多大官嚇壞了,他們唯恐种放到朝廷後妨礙他們,便設下一個詭計,讓种放的熟人
雷有終告訴种放說:“不久朝廷就會有詔旨下來,但不要輕意答應來朝,應該堅持隱節,過一段時間再另上一奏摺,請求朝覲見,並問候皇帝一路風塵之苦,這才是君臣之間忠厚誠懇心情的表示。”
种放不知是計,便遵囑而行。真宗回到都城後,就與執政大臣商量召見种放的事,大臣詭密地說:“種某人肯定不會來的。請陛下記住我的話,時間長了,他自己又會自動請求朝覲。”真宗下詔之後,結果果然如此,皇帝便十分疑惑。過了半年,河陽知縣
孫爽果然受种放要求,上奏要求入覲。皇帝十分震驚,問執政大臣為什麼能料事如神,執政大臣回答說:“我是太了解种放了,他不是真隱居,而是把山林當作枷鎖一樣;隱居不仕的目的是
沽名釣譽,哪是真隱士。他為什麼這時要求入覲,還不是因宰相
王旦要退休嗎?希望陛下明察。”這位大臣這么一說,真宗對
种放的好感一點兒也沒有了,再也不提讓他入朝覲見,而是讓河陽縣賜給种放一百兩銀子買山隱居。
宗徽宗祟寧二年
(公元1103年),朝廷下詔禁毀元祐黨人的書籍,《湘山野錄》由於某些記載暴露了北宋朝廷的陰暗面,因此也上了禁毀書目。
目錄
生死謎
卷上
杜祁公求免預明堂大享
聞前代與亡之事以自省戒
夏辣作詩舉筆無虛致
种放奏十議書
張詠鎮陳台
張乖崖成都還日
种放三不便之奏
光梵大師通敏有先識
日本國忽梯航稱貢
退傅張士遜?[金明
錢思公鎮洛
太宗喜奕棋
學僧注法音集
杜祁公致仕於南都
擇臣僚伴虜使射弓
說明
卷下
李侍讀魁梧善飲
丁晉公釋褐授饒倅
蔭補子弟有當齊挽之職
張尚書鎮蜀
僧錄贊寧洞古博物
館中詩筆最得唐人風格者
蘇子美贈秘演詩
蘇子美坐自盜律
錢文僖求相骨法
蔡君謨出守福唐
撫人饒餗
李文和公識學優瞻
契嵩師沒於靈?L山
張景尚義氣
成都無名高僧有功
程東美守賓州
蜀盜糠者皆斬
韓熙載事江南三
交賊寇邕
真宗求占城稻種
中貴人盡帶將仕郎
天台教主禮法師
向敏中為東嶽奉冊使
歐公撰石曼卿墓表
版本
相關信息
李建勛游東山原文
李建勛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與賓僚游東山,各事寬履輕衫,攜酒肴,引步於漁溪樵塢間,遇佳處則飲。忽平田間一茅舍,有兒童誦書聲。相君攜策就之,乃一老叟教數村童。叟驚悚離席,改容趨謝,而翔雅有體,氣調瀟灑。丞相愛之,遂觴於其廬,置之客右,叟亦不敢輒談。李以晚渴,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此不宜多食,號為五臟刀斧。"叟竊笑。丞相曰:"先生之哂,必有異聞。"叟謝曰:"小子愚賤,偶失容於鈞重,然實無所聞。"李堅質之,仍脅以巨觥,曰:"無說則沃之。"叟不得已,問說者曰:"敢問’刀斧’之說有稽乎"曰:"舉世盡雲,必有其稽。"叟曰:"見《鶡冠子》。所謂五臟刀斧者,非所食之梨,乃離別之’離’爾。蓋言人之別離,戕伐胸懷,甚若刀斧。"遂就架取一小策,振拂以呈丞相,乃《鶡冠子》也。檢之,如其說,李特加重。
譯文
李建勛在南唐被剝脫宰相之位後,被命令鎮守豫章。有一天,和賓客同僚去東山遊覽,各自都穿著寬鬆的鞋子,輕便的衣衫,帶上酒菜,在山溪叢林船塢之間遊玩,遇見風景優美的地方就坐下飲酒。忽然看見平整的田野間有一座茅屋,裡面傳出來兒童的讀書聲。於是和大家拿出書本一起走近,看見原來是一個老頭在教幾個村裡的孩子。老人家驚恐地離開教席,整了整衣服迎了上來招呼客人,他的氣質瀟灑大方。李建勛很喜歡,就在茅屋裡喝酒,把老頭安排在客人的右邊,老頭也不敢隨便開言。李建勛因為後來有點渴,連著吃了幾個梨子。賓客同僚里有人說:“這個東西不適合多吃,有外號叫做‘五臟刀斧’”。老頭偷偷在笑。李建勛說:“先生的笑,肯定有不同的說法。”老頭道歉說:"小人蠢笨而且低下,偶然在您面前失禮,但是確實沒有什麼意思"。李建勛一定要問個究竟,就用一個盛滿酒的大酒杯來威脅老人家,說“不說就要灌你。”老頭不得已,就問開始說話那人:“敢問‘刀斧’這個說法有典故嗎?”那人回答說:“全世界都這么說,肯定有典故。”老頭說:“出自《鶡冠子》。 所謂五臟刀斧的說法,不是吃的梨,而是離別的“離”啊。這是說人們在離別時,心裡受到刺激,比受刀斧還要疼痛。”於是咋書架上取來一小本書,彈拭掉灰塵上呈給李建勛,正是《鶡冠子》。 大家檢視看,跟他說的一樣。李建勛因此很看重他。
提要
《湘山野錄》三卷、《續錄》一卷,宋僧
文瑩撰。文瑩,字道溫,
錢塘人。《
文獻通考》引晁公武《讀書志》,以為吳僧。今按《讀書志》,實無吳字,《通考》誤也。其書成於
熙寧中,多記北宋雜事。以作於荊州之金鑾寺,故以湘山為名。《讀書志》作四卷,《通考》則《續錄》亦作三卷,皆與今本不同,未詳孰是。厲鶚《宋詩紀事》稱,文瑩及識蘇舜欽,欲挽致於歐陽修,文瑩辭不往。今考《錄》中“歐陽公謫滁州”一條,稱文瑩“頃持蘇子美書,薦謁之,迨還吳蒙,見送”云云,與鶚所言正相反。豈別據他說,未及考此書耶?《續錄》中“太宗即位”一條,李燾引入《長編》,啟千古之論端,程敏政《宋紀受終考》,詆之尤力。然觀其始末,並無指斥逆節之事,特後人誤會其詞,致生疑竇,是非作者本意,未可以為是書病也。吳開《優古堂詩話》,論其以陽郇伯妓人入道詩,誤為陳彭年送申國長公主為尼詩;朱翌《猗覺寮雜記》,論其載“琴曲賀若”一條,誤賀若夷為賀若弼;姚寬《西溪叢語》,論其記宋齊邱事失實。蓋考證偶疏,未為大失。
王士禎《古夫子亭雜錄》,論其載王欽若遇唐裴度事,小說習徑,亦不深求。惟朱弁《曲洧舊聞》曰:宇文大資言,
文瑩嘗游丁晉公門,晉公遇之厚,《野錄》中凡記晉公事,多佐佑之。人無董狐之公,未有不為愛憎所奪者。然後世豈可盡欺哉?是則誠其一瑕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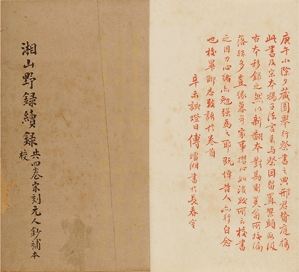 湘山野錄
湘山野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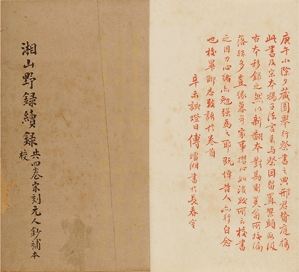 湘山野錄
湘山野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