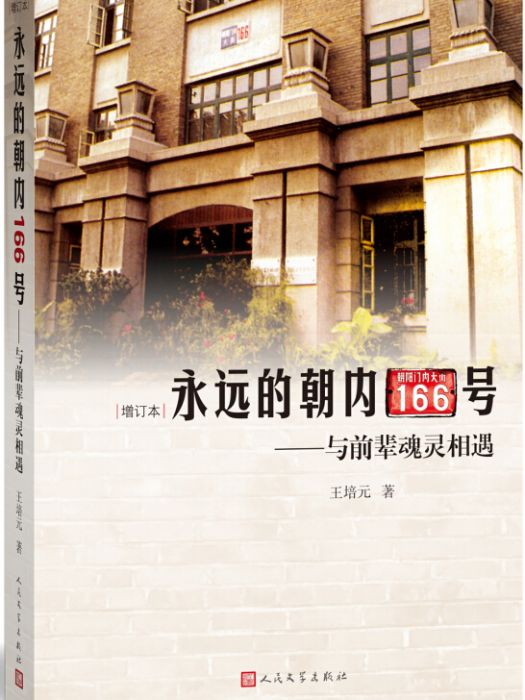《永遠的朝內166號:與前輩魂靈相遇(增訂本)》是2014年11月1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王培元。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永遠的朝內166號:與前輩魂靈相遇(增訂本)
- 作者:王培元
-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 ISBN:9787020105441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
內容簡介
《永遠的朝內166號:與前輩魂靈相遇(增訂本)》是一部以列傳形式書寫的中國現當代知識分子命運史。
馮雪峰、聶紺弩、牛漢、韋君宜、綠原、舒蕪、林辰、蔣路、嚴文井、秦兆陽、孟超、樓適夷、陳邇冬、巴人、汝龍、張友鸞、王仰晨……這些名字不僅深深嵌入了風雲激盪的中國現當代文化和文學的歷史,而且也與北京朝內大街166號——人民文學出版社息息相關。
剛直,狂狷,率真,勇毅,堅韌,倔強,曠達,謙和,篤實,執著……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足以構成一個社會單元,具有獨立的精神文化價值;而當作者面對這紛繁複雜的人生畫面,以熱烈、激憤和悲憫的情感,力圖揭示歷史的同一性時,則顯示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這是人格的力量、悲劇的力量,更是情感和理性的力量。
圖書目錄
緣 起…1
彳亍在空蕩蕩的樓道之中,獨坐於北窗下靜悄悄的辦公室里,有時似乎覺得馮雪峰、聶紺弩、樓適夷、孟超、林辰、韋君宜、嚴文井、秦兆陽、蔣路等前輩的魂靈,就在166號這座幽深寧靜的大樓里逡巡、遊走。他們在看著你,眼神里流露出信任、希望、鼓勵和期許。
馮雪峰:一隻獨棲的受傷的豹子…7
馮雪峰有魯迅說的“浙東人的老脾氣”與“硬氣”,性格倔強執拗、赤誠率真、偏激衝動、焦躁易怒。1937年7月,他與赴南京和國民黨談判的中共代表團負責人博古一見面,就吵翻了……當厄運降臨的時候,他就像一隻受傷的豹子,悄悄地躲進密林深處,默默地舔舐著傷口裡流出的鮮血,孤獨地承受著、忍耐著苦痛和哀傷。即使在那艱厄窘迫的歲月里,馮雪峰仍保持著特立獨行的個性,保持著精神的高潔和靈魂的尊嚴。
聶紺弩:“我將狂笑我將哭”…39
驚世駭俗的聶紺弩,以及由聶紺弩這種人物造成的獨特的精神氛圍、人文環境,或許是那時人文社最具魅力的所在。在我看來,他的率真,他的狂狷,他的豪放,他的憤世嫉俗,他的傲視群倫、鄙夷一切,他的才華絕代、出類拔萃,他的時而“金剛怒目”,時而“菩薩低眉”,是“人文”人物中一道已經遠去、恐怕再也不會重現的絢爛而別致的風景。
林辰:恂恂儒者…69
他不但參與了十卷本和十六卷本《魯迅全集》的編輯出版工作,而且是其中不可替代的核心人物。他把自己一生最寶貴的年華和時光,都默默無聞地奉獻給了關係到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建設百年大計的魯迅著作的編輯出版事業。每次逐條討論《魯迅全集》的注釋文字時,只有得到林先生的首肯,主持人才宣布進入下一條。誰遇到了解決不了的難題,去向林先生請教,馬上就會迎刃而解。
蔣路:編輯行的聖徒…86
蔣路先生最突出、最典型地體現了“人文之魂”,堪稱編輯行的聖徒——他身上有一種內在的非凡的宗教精神,有一種獻身於一項神聖事業而不惜犧牲自己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氣質。正是這種與眾不同的精神氣質,讓我對他肅然起敬。
牛漢:“汗血詩人”…100
在遭遇了戰亂、流亡、飢餓、迫害、囚禁之後,在經歷了種地、建房、養豬、拉車、宰牛的勞改歲月之後,在遭受了苦難的擊打之後,牛漢其人與詩,都日益成熟起來,愈加沉實而美麗。然而,他的心依然年輕,血依然燥熱,骨頭依然堅硬,生命力依然強悍、蠻野、飽滿。
舒蕪:“碧空樓”中有“天問”…122
新中國第一起最大的文字獄,舒蕪就深陷其中。如今,那些噩夢般的往事,那些恩怨情仇,隨著歲月的流逝,似乎如煙塵一般漸漸地消散,並終將湮沒於歷史的深淵。他的書房,先叫“天問樓”,後稱“碧空樓”。他的一本文集,書名是《我思,誰在?》,書前題記云:“我思了,我在么?在的是我還是別人?”這是否透露出了舒蕪的心靈的訊息?
韋君宜:折翅的歌唱…144
韋君宜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界一位罕見的認真、執著、純粹、堅貞、勇毅的知識女性。由於這種品性,她堅定地獻身理想,熱烈地擁抱信仰,奮不顧身地投入革命;一朝幻滅,便格外痛楚;醒覺之後,又分外決絕。她的《思痛錄》,已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中一塊標誌性的界碑、一個不可代替的文化標本。
秦兆陽:何直文章驚海內…172
他是把編輯工作,把主持《人民文學》和《當代》雜誌的工作,當做一項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不可或缺的事業,來對待、來追求的。這是他的一個鮮明特點,也是他那代人的共同點。他一生的榮辱、悲喜與沉浮,簡直折射著一部波詭雲譎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一個文學時代,一個“果戈理到中國也要苦悶的時代”,隨著秦兆陽的辭世,也許永遠地消逝了。
嚴文井:“一切都終歸於沒有”…194
有一次他大聲說:“我算有思想嗎?我真的有自己的思想嗎?沒有,我沒有自己的思想。”只有睿智的人,才敢於這樣自嘲,敢於這樣反思。而在嚴文井的自嘲和反思中,似乎還可以品咂出一絲苦味。他似乎心智澄明,似乎大徹大悟,但又似乎依舊惶惑。他的自嘲與反思里,就有這惶惑在。
綠原:詩之花在煉獄裡怒放…219
綠原以剛毅的理性和堅強的意志,穿透、超越和戰勝了生存的殘酷與現實的荒謬,他的意志力量是常人難以企及的。苦難淬鍊了綠原的詩,鍛打了綠原的詩,成就了綠原的詩,卻無情地徹底毀滅了他的同志和友人——被稱為“未完成的天才”的路翎。
孟超:“悲歌一曲李慧娘”…245
天真而又樂觀的孟超,內心充滿了激情的孟超,寫過詩、寫過小說、寫過雜文的孟超,怎么就突然寫起了崑曲呢?然而,誰能料到,懷著一腔豪邁、壯烈的激情,“試潑丹青塗鬼雄”的孟超,最終竟因這齣“鬼戲”含冤而死呢?卻原來,製造這個冤案的元兇,恰恰就是他的同學、同鄉甚至還是親戚,那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文革”中炙手可熱的大人物——康生。
樓適夷:用自己的頭腦思考…266
晚年,樓適夷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腦子這個器官,是專司發號施令的,要管住自己的腦子,談何容易。”他終於明白,用自己的頭腦來思考,是何等的重要!
巴人:“在我夢底一角上組起花圈……”…284
1970年3月,曾被譽為“活魯迅”的巴人,被遣送回故鄉奉化大堰村。年底,開始神志不清。第二年,精神失常。冬天不穿衣服,蓬頭跣足,在曠野里狂奔。兩年後,口鼻耳流血不止而死。
他走進“無物之陣”…302
面對作協袞袞諸公的毫無情面的批鬥,馮雪峰如同走入了“無物之陣”(魯迅語)。孤立無助,百口莫辯,連為自己“辯誣”的權利亦被剝奪;對於橫加在自己頭上的種種謠諑、攻訐和詆毀,只能被迫地、屈辱地接受下來。最終以羅織鍛鍊的莫須有罪名,戴上了一頂“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荊冠。此後他的命運,也便鑄定了。他步入了近二十年隱忍苟活的漫長苦難人生,直至1976年1月30日飲恨辭世。
聶紺弩的“獨立王國”…321
對所謂“獨立王國”之罪名,他終於不得不違心承認。他越寫檢查和交待,“越覺得自己像個由國民黨或簡直由特務機關派來的”,“越寫越恐怖”,寫來寫去,甚至產生了一種“大虛無”、“大恐怖”。
無限夕陽樓主人陳邇冬…342
陳邇冬是博覽群書、滿腹經綸的大家,又是倜儻不羈、文採風流的人物。他一生,室名先後有好幾個。早年在桂林,叫過“冬眠樓”。五六十年代進京後,室名是“十步廊”,後來又有“它山室”。不過,我喜歡的,則是他晚年的題署——“無限夕陽樓”,意境恢廓深幽,有無限的韻致,讓人生出聯翩不盡的情思。
我所接觸的舒蕪先生…356
即使在衰弱不堪的病中,依然手不釋卷,還在思考、談說周氏兄弟。——這就是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舒蕪先生給我留下的印象。
初冬懷王仰晨先生…365
在這個北京的冷寂的冬晚,想起這些已經逝去但卻難以忘懷的往事,領受過他的教益和恩惠的我,就又不可遏止地懷念起這個具有堅定信念和鮮明是非感,表面看起來很平和,但實際上內心燃燒著熱烈愛憎的、可親可敬可愛的老頭兒來。
傑出的翻譯家汝龍…375
汝龍搞翻譯五十年,譯契訶夫四十年。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具有一股“橫下一條心,默默幹下去”的勁頭和韌性。巴金說,汝龍“讓中國讀者懂得了熱愛那位反對庸俗的俄羅斯作家。他為翻譯事業奉獻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獻了一切,甚至自己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譯家這個稱號”。
主要參考文獻…390
後 記…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