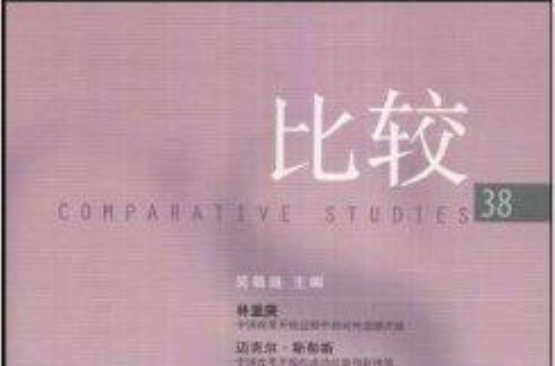《比較38》是為讀者提供的一個有關比較制度的分析的學術性平台。《比較》站在理論前沿,根據中國經濟改革中遇到的重大問題,有選擇地介紹別國的經驗和教訓、轉軌經濟的理論和實踐,以及比較研究領域的發,同進,有針對性地介紹國內外學術理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方案設計、政策建議和評論。
基本介紹
- 書名:比較38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頁數:168頁
- 開本:16
- 品牌: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作者:吳敬璉
- 出版日期:2008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8612973, 7508612973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內容簡介
《比較38》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圖書目錄
第三十八輯
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對外思想開放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和新挑戰
三十年改革及中俄轉軌路徑比較
前沿
機制設計:如何實現社會目標
經濟實驗:實驗經濟學方法評論評述
海外特稿
中美貿易的動態理論:對失衡的解釋
社界
決定各國奧運成功的因素
金融評論
全球化、巨觀經濟運行和貨幣政策
越南的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外部原因的解釋
法和經濟學
捆綁式銷售中的價格折扣:競爭還是壟斷?
改革論壇
外資進和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後評價分析和政策建議
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對外思想開放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和新挑戰
三十年改革及中俄轉軌路徑比較
前沿
機制設計:如何實現社會目標
經濟實驗:實驗經濟學方法評論評述
海外特稿
中美貿易的動態理論:對失衡的解釋
社界
決定各國奧運成功的因素
金融評論
全球化、巨觀經濟運行和貨幣政策
越南的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外部原因的解釋
法和經濟學
捆綁式銷售中的價格折扣:競爭還是壟斷?
改革論壇
外資進和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後評價分析和政策建議
文摘
第三十八輯
中國改革開融過程中的對外思想開放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我知道有許多人都在進行回憶、思考和總結,並在此基礎上寫成相關的文章和書籍。當中國50人論壇的學術委員會委員劉鶴先生提出,希望我為他們即將出版的《中國經濟50人看三十年:回顧與分析》一書作序,我欣然同意。我覺得這是我的榮耀,因為這些作者許多都是在過去30年中結識的朋友,我們擁有過一段共同的經歷,足以讓我花費一番工夫,貢獻自己的點滴之力。
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可以稱之為世界現代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也將被看為世界歷史的轉折點。儘管國內外人士對這段歷史都有著廣泛而濃厚的興趣,但對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卻缺乏詳盡的了解。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說過一句話,後來常被引用。他說:“能解讀中國經濟改革的人應該榮獲諾貝爾獎。”因此,可以說,由制定過改革方案、參與過改革進程的眾多中國經濟學家及決策者們,以自己的視角撰文薈集的這本書,在此刻出版,意義非同尋常。分享這一偉大曆程的經驗及分析這些寶貴的經驗,我以為對經濟學界本身,對世界各轉型國家的經濟決策者,乃至世界上還正在為快速促進本國經濟進步而奮鬥著的很多國家領導人和經濟學家們來說,都受益無窮。
我作為國際組織的一員,並以其有利的身份參與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特別是參與了這一過程中的前十年,這對我來說是一份難得的殊榮。
我的參與始於1979年7月的一個夏日,儘管到後來我才意識到那一天的重要性。
那一年,我攜家人來京旅遊,住在北京飯店。那是我第一次帶兩個孩子回福建老家,很興奮。當時,外國人來華並非易事,像我們這樣的華僑也不例外。當時我在世界銀行東亞處工作,南、北越統一後不久,世界銀行便開始了越南業務。當時的越南仍很封閉,抵達河內最便利的航線就是經北京轉機。當時的中國尚未恢復世界銀行席位,與世界銀行沒有業務關係。我必須以主管越南業務官員的身份,到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申請特批過境中國(北京)的簽證。1977-1979年間,我本人曾在赴河內途中幾次過境北京。
即便這是短暫過境中國的機會,我們這些海外經濟工作者也很嚮往。當時,外面的世界並不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我們都極想了解這個國家到底是個什麼樣。
在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曹桂生公使的幫助下,我的家人獲準與我同行。我們在北京僅停留3天。第二天,我們意外地接到中國銀行的邀請,在前門烤鴨店設宴招待我們。到了烤鴨店,我才知曉,原來,宴請的主人是中國銀行研究部主任林基鑫——恢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席位可行性調研團的團長。在座的調研團其他成員還有:王連生(當時在財政部地方財政司工作,是中國隨後派往世界銀行的首位執董);戴乾定(當時在中國銀行研究部工作,後任中國銀行倫敦分行行長及中國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董);張曉康(當時在外交部國際機構司工作,現任中國駐新加坡大使)。作為調研的內容,他們當時已經訪問了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了解這兩個國家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打交道的經驗。
從席間的討論中我發現,調研團成員最關心的是如何從世界銀行集團的“國際開發協會(IDA)”獲得軟貸款的問題(那時,軟貸款是免息的,償還期為50年),討論主要集中在申請軟貸款的條件上。我告訴他們,任何一個國家申請世界銀行貸款,無論是硬貸款(按照市場利率),還是軟貸款,關鍵步驟是世界銀行要派員對那個國家進行一次經濟考察。申請軟貸款的資格取決於經濟考察的結果。為此,那天晚上我們主要討論了準備世界銀行經濟考察的程式。
1980年初,林基鑫的調研團向中央提交了題為“恢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合法席位的程式和安排的報告”。報告經國務院批准後,中國銀行隨即邀請世界銀行集團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行長訪華,磋商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世界銀行席位的相關事宜。
· 麥克納馬拉率領的世界銀行代表團於1980年4月抵京。單獨會見麥克納馬拉行長時,鄧小平強有力地說:“中國下決心要實現現代化、發展經濟。有世界銀行的幫助,中國實現這些目標可能會更快、更有效率些;沒有世界銀行的幫助,我們照樣要做,只是花的時間可能會長些。”在雙方的積極配合下,談判很順利。一個月後,世界銀行董事會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世界銀行席位。麥克納馬拉行長從中國回去不久,我即被任命為負責中國業務的首席經濟學家,分管經濟調研及與中國政策對話的工作。1985年,我被派往北京,建立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並任首席代表。我的這一任命直至1990年。
就在前門烤鴨店那次意想不到的晚宴之後不到一年時間,我便身臨其境,不僅可以就勢觀察中國剛剛開始的改革開放過程,而且從一定程度上親歷其中。根據我當時的工作身份,參與中國改革開放過程的一個主要領域自然是對外經濟思想的開放過程。因參與這個過程的許多前輩已故去,反映這方面的文章不像講述改革過程的文章那么多,我願藉此作序的機會與大家分享我所了解的相關情況。中國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演化,有幾個階段,我將分幾個主題來講述:首先是如何引進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思想,隨後是如何引進我稱之的主流現代經濟學思想。這裡只講述中國領導人及經濟工作者如何接觸外國經濟思想,以及如何與外國經濟學家和外國改革實踐者們接觸,主要談我親身經歷的事件,不涵蓋中國內部發生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辯論與紛爭,那些內容在從計畫到市場演變過程中遠比這裡所談的內容重要。
認識思想引進的重要性
重要成就通常始於新思想和創新想法。20世紀70年代改革開放啟動時,中國正走出幾十年游離於世界之外的極度知識封閉境況,儘管許多中國經濟學家是那么努力、富有勇氣和能力,但沒有幾個領域像經濟學那么嚴重地與外界隔絕。
中國領導人早就認識到學習外國思想及先進經驗的重要性。早在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報告中的“第十大關係”中就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然而,事與願違。在隨後的20年間,傳統的蘇維埃中央計畫體制原封不動地被照搬到與蘇聯情況千差萬別的中國經濟中來。學習西方國家經濟思想和經驗幾乎被看成是一種政治罪過。
中國下定決心啟動改革開放最重要的發端之一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中國高層領導發現世界他國的經濟進步是那么迅猛,相比之下中國是那么落後。僅在1978年,前後共12位副總理及副委員長以上的中央領導人,先後20次訪問了50多個國家。鄧小平先後4次出訪,到過8個國家。“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後。什麼叫現代化?五十年代一個樣,六十年代不一樣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樣了。”鄧小平說。
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的講話主題再次重現學習外國經濟和技術的必要性。“我們要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來建設自己的國家,同時也要虛心學習外國一切先進的東西,學習和借鑑外國的管理經驗和先進技術”;“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永遠陷於落後不行”。按照鄧小平的指示,引進外國思想和學習外國經驗,早年在協助中國領導人和經濟工作者們確定改革目標和改革步驟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引進蘇東改革理論和經驗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領導人和很多經濟工作者對於經濟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已經認識得很清楚,但對於改革目標和步驟卻還很陌生。從思想理論到中央計畫體制,蘇東國家的情況與中國較相近,加上中國的經濟工作者們自20世紀50年代後期就對蘇東國家的改革方案有所了解。其實,中國改革的先驅孫冶方和顧準的改革思想與東歐早期的改革思想理論幾乎是一致的。所以,開放改革思想從學習蘇東的改革理論開始是很自然的。這一舉動由中國社科院牽頭,特別是經濟研究所,所里的很多主要經濟理論工作者都曾在蘇聯留學。
1979年到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與蘇東國家經濟交流活動頻繁,其中包括孫冶方1978年訪問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劉國光和柳隨年1982年訪問前蘇聯,廖季立1983年訪問匈牙利。1979年,蘇東經濟學家頻繁受邀訪華,首位來訪者是南斯拉夫經濟學家馬克西莫維奇(Maksimovich)。其中影響力最大的訪問活動莫過於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Wlodzimierz Bins)和捷克經濟學家奧塔·錫克(Ota Sik),他們於1979年12月及1981年6月的應邀來華講學。
布魯斯是與奧斯卡·蘭格(Oskar Lange)及米哈爾·卡萊斯基(Michal Kalecki)齊名國際的波蘭經濟學家。他對波蘭經濟改革思想的最大影響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他與蘭格和卡萊斯基一起供職于波蘭經濟委員會,任副主席,為波蘭政府經濟改革特別是“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提供建議。後來,部分由於波蘭政府領導人哥穆爾卡(Wladyrslaw Gomulka)對改革失去了興趣,加上布魯斯有猶太血統的原因,他丟了官位,在波蘭的影響日漸消隱。1972年,布魯斯流亡英國,到牛津大學任教。
1979年,時任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的董輔初赴牛津大學訪問時結識了布魯斯,遂邀請布魯斯年底赴華講學。布魯斯在經濟研究所的四樓會議室連續講課兩天,會議室里擠滿了聽眾。聽眾中有來自社科院的學者,也有來自國務院決策部門的官員。講課報告以簡報形式送到中央領導人手中,反響積極。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內,布魯斯得到主管經濟學的副院長於光遠和主管外事的副院長宦鄉的熱情接待;在中央,布魯斯得到薄一波副總理的接見。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由副總理出面接見一位流亡英國坦率直言的波蘭人,意義非同尋常。在華講課期間,布魯斯由趙人偉全程陪同。
繼布魯斯成功訪華後,劉國光(經濟所副所長,後任經濟所所長、社科院副院長)遂邀奧塔·錫克於1981年5月來華講學。錫克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改革經濟學家和政治人物,主要因“新經濟模式”而聞名,該模式被解釋為“在蘇維埃計畫體制框架下減少中央指令,擴大市場經濟的作用”,一種被看做是介乎於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錫克的經濟理論在1965年及1968年4月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採納。“布拉格之春”期間,錫克被任命為捷克斯洛伐克副總理兼經濟部部長。1968年8月華沙公約組織的部隊入侵布拉格,錫克正在國外訪問,因無法回國而流亡瑞士,直至1989年捷克天鵝絨革命政權更迭。
錫克在北京的講學同樣很成功,吸引了研究機構及政府部門眾多經濟工作者,還安排了他與國內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廖季立和馬洪等座談。大概因為在指導經濟改革計畫方面經驗豐富,與布魯斯比起來,錫克更加受到中國政府領導人的重視。負責全程陪同錫克的吳敬璉跟劉國光商議,以後還是應當多請一些東歐的經濟學家,來華介紹蘇東改革經驗。
那時,中國已經恢復世界銀行席位,我正在北京討論世界銀行第一次經濟考察報告草稿(詳見後文)。吳敬璉和劉國光來找我,提議請世界銀行出面,邀請一些既懂改革理論又有實際改革經驗的東歐經濟學家來華,組織一次學習蘇東經濟改革經驗的會議。我當即應允協助。這就是1982年7月在浙江莫乾山一個避暑山莊裡召開的“莫乾山會議”。
我們邀請的東歐專家組由布魯斯帶隊,包括:波蘭國家物價委員會前主任斯特魯明斯基(Julius Struminsky)、捷克斯洛伐克前副總理奧塔·錫克的工作搭檔考斯塔(Jiri Kosta)、匈牙利改革經濟學家肯德(Peter Kende)。此外,我們還邀請了蘇東經濟改革專家、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格蘭尼克(DavidGranick)教授。中方參會者由薛暮橋、廖季立和劉卓甫帶隊,以他們三人名義起草的大會討論報告會後提交到了國務院領導人手中。
即便是後話,也很難評價與這些蘇東改革經濟學家的交流對中國領導人及經濟工作者們的影響有多大,對中國整體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更難以估量。但是,據我個人當時的體會,回想當時中國經濟工作者們的情況,及後來對近30年的觀察,我覺得對以下三方面影響意義深遠。
首先,東歐改革經濟學家引進了使用現代經濟學來分析蘇維埃計畫體制弊病的方法。東歐經濟學家們不像中國經濟學家們那樣脫離國外的經濟理論。如奧斯卡·蘭格和米哈爾·卡萊斯基其實是在西方接受的教育。那段期間應邀來華的東歐經濟學家都身居國外。布魯斯在英國牛津大學,錫克在瑞士聖加侖大學,參加莫乾山會議的其他東歐專家分別居住並工作在德國、法國和奧地利。因此,他們可以在中國用現代經濟理論的概念和技術來分析中國的經濟情況。這就把對經濟問題的解釋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例如,1979年來華講學時,布魯斯就介紹了買方市場和賣方市場的概念,並提出買方市場在改革轉軌期間的重要性。這一概念和理論一直被中國經濟工作者們沿用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
東歐專家們用現代經濟分析的方法來剖析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制,使這個方法達到一個新高度的是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Jfinos Komai)。1985年,科爾奈首次受世界銀行之邀來華參加“巴山輪會議”(詳見後文),用諸如“投資飢餓症、短缺經濟、軟預算約束”等概念進一步闡明並加深了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弊端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東歐改革經濟學家向他們的中國同行論證了中央計畫體制紊亂的內在根由是體制問題。中國的決策者和經濟工作者們原本以為很多經濟上的問題是政策失誤,究其根源,其實是中央計畫經濟體制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問題,只有通過一套根本的經濟體制改革措施才能加以解決。
其次,詳盡了解東歐的改革經驗加劇了中國經濟工作者們對於在中國使用東歐經濟改革模式的悲觀心理。雖然可以洞察中央計畫經濟的弊端,但專家們提供的解決方案——無論是布魯斯的“有管理的市場模式”還是錫克的“新經濟模式”,都暴露了重大的瑕疵。“莫乾山會議”討論了蘇東改革的新辦法。但中國的改革前輩們敏銳地質疑了借用高科技,特別是靠高速計算機來解決經濟體制問題的可行性。薛暮橋、廖季立及中國領導人尤其質疑錫克等東歐改革經濟學家關於價格改革先調後放的提議,特別是價格調整依據的是計算機精確計算出的數據。即便用高速計算機和使用多部門的投入產出表,也不可能同時計算出經濟中數以萬計的價格呀?
再次,當東歐這些專家們開始搞清楚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之後,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東歐的改革經驗不大適用於中國。中國經濟體制實行基本消費品嚴格配給制、人才流動很受限制、經濟生活全面由國家掌控,這是一種極端的“指令性經濟”。在東歐,市場機制較發達,企業和家庭消費層次有更大的自主權,具有較成熟的信息和管理系統。即便這樣,所有的改革嘗試仍以失敗告終。中國向他們學什麼?除非另謀改革出路。
當東歐專家更多地了解了中國的實際情況之後,也欣然接受了中國需另謀改革出路的說法。一件事足以說明這個問題。“莫乾山會議”上,我們討論了中國改革是採用“一攬子”的方法還是分步進行的方法。與會所有東歐專家強烈建議“一攬子”的方法。會後,東歐專家們到中國幾個城市進行考察。考察途中,他們回話,說他們改變主意了。鑒於中國各地情況千差萬別,經濟落後,貧困現象嚴重,綜合改革中需要的人才、資金和物資儲備薄弱,考慮中國仍是個低收入的開發中國家,沒有犯錯誤的餘地,建議採用謹慎的漸進改革方法。鑒於上述情況,他們認為,中國改革要有總體規劃,要有明確的改革目標,然後可一步一步地進行。因此,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與會的東歐專家、世界銀行專家(伍德和我本人)以及中國專家之間獲得了共識。
中國改革開融過程中的對外思想開放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我知道有許多人都在進行回憶、思考和總結,並在此基礎上寫成相關的文章和書籍。當中國50人論壇的學術委員會委員劉鶴先生提出,希望我為他們即將出版的《中國經濟50人看三十年:回顧與分析》一書作序,我欣然同意。我覺得這是我的榮耀,因為這些作者許多都是在過去30年中結識的朋友,我們擁有過一段共同的經歷,足以讓我花費一番工夫,貢獻自己的點滴之力。
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可以稱之為世界現代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也將被看為世界歷史的轉折點。儘管國內外人士對這段歷史都有著廣泛而濃厚的興趣,但對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卻缺乏詳盡的了解。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說過一句話,後來常被引用。他說:“能解讀中國經濟改革的人應該榮獲諾貝爾獎。”因此,可以說,由制定過改革方案、參與過改革進程的眾多中國經濟學家及決策者們,以自己的視角撰文薈集的這本書,在此刻出版,意義非同尋常。分享這一偉大曆程的經驗及分析這些寶貴的經驗,我以為對經濟學界本身,對世界各轉型國家的經濟決策者,乃至世界上還正在為快速促進本國經濟進步而奮鬥著的很多國家領導人和經濟學家們來說,都受益無窮。
我作為國際組織的一員,並以其有利的身份參與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特別是參與了這一過程中的前十年,這對我來說是一份難得的殊榮。
我的參與始於1979年7月的一個夏日,儘管到後來我才意識到那一天的重要性。
那一年,我攜家人來京旅遊,住在北京飯店。那是我第一次帶兩個孩子回福建老家,很興奮。當時,外國人來華並非易事,像我們這樣的華僑也不例外。當時我在世界銀行東亞處工作,南、北越統一後不久,世界銀行便開始了越南業務。當時的越南仍很封閉,抵達河內最便利的航線就是經北京轉機。當時的中國尚未恢復世界銀行席位,與世界銀行沒有業務關係。我必須以主管越南業務官員的身份,到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申請特批過境中國(北京)的簽證。1977-1979年間,我本人曾在赴河內途中幾次過境北京。
即便這是短暫過境中國的機會,我們這些海外經濟工作者也很嚮往。當時,外面的世界並不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我們都極想了解這個國家到底是個什麼樣。
在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曹桂生公使的幫助下,我的家人獲準與我同行。我們在北京僅停留3天。第二天,我們意外地接到中國銀行的邀請,在前門烤鴨店設宴招待我們。到了烤鴨店,我才知曉,原來,宴請的主人是中國銀行研究部主任林基鑫——恢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席位可行性調研團的團長。在座的調研團其他成員還有:王連生(當時在財政部地方財政司工作,是中國隨後派往世界銀行的首位執董);戴乾定(當時在中國銀行研究部工作,後任中國銀行倫敦分行行長及中國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董);張曉康(當時在外交部國際機構司工作,現任中國駐新加坡大使)。作為調研的內容,他們當時已經訪問了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了解這兩個國家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打交道的經驗。
從席間的討論中我發現,調研團成員最關心的是如何從世界銀行集團的“國際開發協會(IDA)”獲得軟貸款的問題(那時,軟貸款是免息的,償還期為50年),討論主要集中在申請軟貸款的條件上。我告訴他們,任何一個國家申請世界銀行貸款,無論是硬貸款(按照市場利率),還是軟貸款,關鍵步驟是世界銀行要派員對那個國家進行一次經濟考察。申請軟貸款的資格取決於經濟考察的結果。為此,那天晚上我們主要討論了準備世界銀行經濟考察的程式。
1980年初,林基鑫的調研團向中央提交了題為“恢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合法席位的程式和安排的報告”。報告經國務院批准後,中國銀行隨即邀請世界銀行集團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行長訪華,磋商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世界銀行席位的相關事宜。
· 麥克納馬拉率領的世界銀行代表團於1980年4月抵京。單獨會見麥克納馬拉行長時,鄧小平強有力地說:“中國下決心要實現現代化、發展經濟。有世界銀行的幫助,中國實現這些目標可能會更快、更有效率些;沒有世界銀行的幫助,我們照樣要做,只是花的時間可能會長些。”在雙方的積極配合下,談判很順利。一個月後,世界銀行董事會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世界銀行席位。麥克納馬拉行長從中國回去不久,我即被任命為負責中國業務的首席經濟學家,分管經濟調研及與中國政策對話的工作。1985年,我被派往北京,建立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並任首席代表。我的這一任命直至1990年。
就在前門烤鴨店那次意想不到的晚宴之後不到一年時間,我便身臨其境,不僅可以就勢觀察中國剛剛開始的改革開放過程,而且從一定程度上親歷其中。根據我當時的工作身份,參與中國改革開放過程的一個主要領域自然是對外經濟思想的開放過程。因參與這個過程的許多前輩已故去,反映這方面的文章不像講述改革過程的文章那么多,我願藉此作序的機會與大家分享我所了解的相關情況。中國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演化,有幾個階段,我將分幾個主題來講述:首先是如何引進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思想,隨後是如何引進我稱之的主流現代經濟學思想。這裡只講述中國領導人及經濟工作者如何接觸外國經濟思想,以及如何與外國經濟學家和外國改革實踐者們接觸,主要談我親身經歷的事件,不涵蓋中國內部發生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辯論與紛爭,那些內容在從計畫到市場演變過程中遠比這裡所談的內容重要。
認識思想引進的重要性
重要成就通常始於新思想和創新想法。20世紀70年代改革開放啟動時,中國正走出幾十年游離於世界之外的極度知識封閉境況,儘管許多中國經濟學家是那么努力、富有勇氣和能力,但沒有幾個領域像經濟學那么嚴重地與外界隔絕。
中國領導人早就認識到學習外國思想及先進經驗的重要性。早在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報告中的“第十大關係”中就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然而,事與願違。在隨後的20年間,傳統的蘇維埃中央計畫體制原封不動地被照搬到與蘇聯情況千差萬別的中國經濟中來。學習西方國家經濟思想和經驗幾乎被看成是一種政治罪過。
中國下定決心啟動改革開放最重要的發端之一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中國高層領導發現世界他國的經濟進步是那么迅猛,相比之下中國是那么落後。僅在1978年,前後共12位副總理及副委員長以上的中央領導人,先後20次訪問了50多個國家。鄧小平先後4次出訪,到過8個國家。“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後。什麼叫現代化?五十年代一個樣,六十年代不一樣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樣了。”鄧小平說。
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的講話主題再次重現學習外國經濟和技術的必要性。“我們要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來建設自己的國家,同時也要虛心學習外國一切先進的東西,學習和借鑑外國的管理經驗和先進技術”;“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永遠陷於落後不行”。按照鄧小平的指示,引進外國思想和學習外國經驗,早年在協助中國領導人和經濟工作者們確定改革目標和改革步驟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引進蘇東改革理論和經驗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領導人和很多經濟工作者對於經濟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已經認識得很清楚,但對於改革目標和步驟卻還很陌生。從思想理論到中央計畫體制,蘇東國家的情況與中國較相近,加上中國的經濟工作者們自20世紀50年代後期就對蘇東國家的改革方案有所了解。其實,中國改革的先驅孫冶方和顧準的改革思想與東歐早期的改革思想理論幾乎是一致的。所以,開放改革思想從學習蘇東的改革理論開始是很自然的。這一舉動由中國社科院牽頭,特別是經濟研究所,所里的很多主要經濟理論工作者都曾在蘇聯留學。
1979年到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與蘇東國家經濟交流活動頻繁,其中包括孫冶方1978年訪問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劉國光和柳隨年1982年訪問前蘇聯,廖季立1983年訪問匈牙利。1979年,蘇東經濟學家頻繁受邀訪華,首位來訪者是南斯拉夫經濟學家馬克西莫維奇(Maksimovich)。其中影響力最大的訪問活動莫過於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Wlodzimierz Bins)和捷克經濟學家奧塔·錫克(Ota Sik),他們於1979年12月及1981年6月的應邀來華講學。
布魯斯是與奧斯卡·蘭格(Oskar Lange)及米哈爾·卡萊斯基(Michal Kalecki)齊名國際的波蘭經濟學家。他對波蘭經濟改革思想的最大影響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他與蘭格和卡萊斯基一起供職于波蘭經濟委員會,任副主席,為波蘭政府經濟改革特別是“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提供建議。後來,部分由於波蘭政府領導人哥穆爾卡(Wladyrslaw Gomulka)對改革失去了興趣,加上布魯斯有猶太血統的原因,他丟了官位,在波蘭的影響日漸消隱。1972年,布魯斯流亡英國,到牛津大學任教。
1979年,時任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的董輔初赴牛津大學訪問時結識了布魯斯,遂邀請布魯斯年底赴華講學。布魯斯在經濟研究所的四樓會議室連續講課兩天,會議室里擠滿了聽眾。聽眾中有來自社科院的學者,也有來自國務院決策部門的官員。講課報告以簡報形式送到中央領導人手中,反響積極。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內,布魯斯得到主管經濟學的副院長於光遠和主管外事的副院長宦鄉的熱情接待;在中央,布魯斯得到薄一波副總理的接見。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由副總理出面接見一位流亡英國坦率直言的波蘭人,意義非同尋常。在華講課期間,布魯斯由趙人偉全程陪同。
繼布魯斯成功訪華後,劉國光(經濟所副所長,後任經濟所所長、社科院副院長)遂邀奧塔·錫克於1981年5月來華講學。錫克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改革經濟學家和政治人物,主要因“新經濟模式”而聞名,該模式被解釋為“在蘇維埃計畫體制框架下減少中央指令,擴大市場經濟的作用”,一種被看做是介乎於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錫克的經濟理論在1965年及1968年4月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採納。“布拉格之春”期間,錫克被任命為捷克斯洛伐克副總理兼經濟部部長。1968年8月華沙公約組織的部隊入侵布拉格,錫克正在國外訪問,因無法回國而流亡瑞士,直至1989年捷克天鵝絨革命政權更迭。
錫克在北京的講學同樣很成功,吸引了研究機構及政府部門眾多經濟工作者,還安排了他與國內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廖季立和馬洪等座談。大概因為在指導經濟改革計畫方面經驗豐富,與布魯斯比起來,錫克更加受到中國政府領導人的重視。負責全程陪同錫克的吳敬璉跟劉國光商議,以後還是應當多請一些東歐的經濟學家,來華介紹蘇東改革經驗。
那時,中國已經恢復世界銀行席位,我正在北京討論世界銀行第一次經濟考察報告草稿(詳見後文)。吳敬璉和劉國光來找我,提議請世界銀行出面,邀請一些既懂改革理論又有實際改革經驗的東歐經濟學家來華,組織一次學習蘇東經濟改革經驗的會議。我當即應允協助。這就是1982年7月在浙江莫乾山一個避暑山莊裡召開的“莫乾山會議”。
我們邀請的東歐專家組由布魯斯帶隊,包括:波蘭國家物價委員會前主任斯特魯明斯基(Julius Struminsky)、捷克斯洛伐克前副總理奧塔·錫克的工作搭檔考斯塔(Jiri Kosta)、匈牙利改革經濟學家肯德(Peter Kende)。此外,我們還邀請了蘇東經濟改革專家、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格蘭尼克(DavidGranick)教授。中方參會者由薛暮橋、廖季立和劉卓甫帶隊,以他們三人名義起草的大會討論報告會後提交到了國務院領導人手中。
即便是後話,也很難評價與這些蘇東改革經濟學家的交流對中國領導人及經濟工作者們的影響有多大,對中國整體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更難以估量。但是,據我個人當時的體會,回想當時中國經濟工作者們的情況,及後來對近30年的觀察,我覺得對以下三方面影響意義深遠。
首先,東歐改革經濟學家引進了使用現代經濟學來分析蘇維埃計畫體制弊病的方法。東歐經濟學家們不像中國經濟學家們那樣脫離國外的經濟理論。如奧斯卡·蘭格和米哈爾·卡萊斯基其實是在西方接受的教育。那段期間應邀來華的東歐經濟學家都身居國外。布魯斯在英國牛津大學,錫克在瑞士聖加侖大學,參加莫乾山會議的其他東歐專家分別居住並工作在德國、法國和奧地利。因此,他們可以在中國用現代經濟理論的概念和技術來分析中國的經濟情況。這就把對經濟問題的解釋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例如,1979年來華講學時,布魯斯就介紹了買方市場和賣方市場的概念,並提出買方市場在改革轉軌期間的重要性。這一概念和理論一直被中國經濟工作者們沿用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
東歐專家們用現代經濟分析的方法來剖析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制,使這個方法達到一個新高度的是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Jfinos Komai)。1985年,科爾奈首次受世界銀行之邀來華參加“巴山輪會議”(詳見後文),用諸如“投資飢餓症、短缺經濟、軟預算約束”等概念進一步闡明並加深了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弊端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東歐改革經濟學家向他們的中國同行論證了中央計畫體制紊亂的內在根由是體制問題。中國的決策者和經濟工作者們原本以為很多經濟上的問題是政策失誤,究其根源,其實是中央計畫經濟體制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問題,只有通過一套根本的經濟體制改革措施才能加以解決。
其次,詳盡了解東歐的改革經驗加劇了中國經濟工作者們對於在中國使用東歐經濟改革模式的悲觀心理。雖然可以洞察中央計畫經濟的弊端,但專家們提供的解決方案——無論是布魯斯的“有管理的市場模式”還是錫克的“新經濟模式”,都暴露了重大的瑕疵。“莫乾山會議”討論了蘇東改革的新辦法。但中國的改革前輩們敏銳地質疑了借用高科技,特別是靠高速計算機來解決經濟體制問題的可行性。薛暮橋、廖季立及中國領導人尤其質疑錫克等東歐改革經濟學家關於價格改革先調後放的提議,特別是價格調整依據的是計算機精確計算出的數據。即便用高速計算機和使用多部門的投入產出表,也不可能同時計算出經濟中數以萬計的價格呀?
再次,當東歐這些專家們開始搞清楚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之後,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東歐的改革經驗不大適用於中國。中國經濟體制實行基本消費品嚴格配給制、人才流動很受限制、經濟生活全面由國家掌控,這是一種極端的“指令性經濟”。在東歐,市場機制較發達,企業和家庭消費層次有更大的自主權,具有較成熟的信息和管理系統。即便這樣,所有的改革嘗試仍以失敗告終。中國向他們學什麼?除非另謀改革出路。
當東歐專家更多地了解了中國的實際情況之後,也欣然接受了中國需另謀改革出路的說法。一件事足以說明這個問題。“莫乾山會議”上,我們討論了中國改革是採用“一攬子”的方法還是分步進行的方法。與會所有東歐專家強烈建議“一攬子”的方法。會後,東歐專家們到中國幾個城市進行考察。考察途中,他們回話,說他們改變主意了。鑒於中國各地情況千差萬別,經濟落後,貧困現象嚴重,綜合改革中需要的人才、資金和物資儲備薄弱,考慮中國仍是個低收入的開發中國家,沒有犯錯誤的餘地,建議採用謹慎的漸進改革方法。鑒於上述情況,他們認為,中國改革要有總體規劃,要有明確的改革目標,然後可一步一步地進行。因此,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與會的東歐專家、世界銀行專家(伍德和我本人)以及中國專家之間獲得了共識。
序言
從1978年至今,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30個年頭。改革開放所要達到的目標,按照中共十七大的概括乃是"從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現在,這個歷史轉折還沒有完全實現。為了完滿地實現這個轉折,我們應當認真總結30年的經驗教訓,讓歷史照亮我們未來的道路。在這個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日子裡,主編吳敬璉如是說。本輯《比較》收錄了三篇回顧、總結和比較的文章,正是為了以歷史展望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