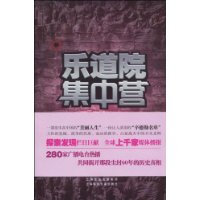簡介
鴉片戰爭肇始,隨著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封建專制的中華帝國國門大開,西方教會和文化勢力由沿海向內陸逐步滲透。1883年美國
傳教士狄樂播及其夫人阿撒拉來濰縣傳教,並在當地教友的協助 下,在老濰縣東關處買地建立“樂道院”,用以傳教、辦學和開辦診所。
庚子賠款後,樂道院所獲資金較多,得到了較大規模的發展,占地200多畝,一度成為昌濰一帶的教會、教育和醫療衛生中心。西方教士、教師、醫務人員麇集在此活動,其場所很是顯要,院內的鐘樓為濰縣城東部的標誌性建築物。
1937年7月7日瀘溝橋事變後,日軍於當年底占領膠東半島,在煙臺、青島等地活動的外國僑民開始前來
濰縣樂道院避難。因為當時美國等對日本持中立態度,所以日軍對樂道院基本不加干涉,院內的傳教、教學和醫務活動尚能正常開展。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美英正式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英等和日本成為敵對國。這時在美國夏威夷等地的日本僑民採取種種措施竊取美軍情報,為日本軍國主義服務,引起了美國對日本僑民的憤慨,因此美國政府將僑居舊金山等地的6萬多日本人集中到洛杉磯附近指定的地區,並不準 與外界聯繫。日本為報復美國,將中國淪陷區內美國、英國和其他反法西斯國家的人士強行收管。因濰縣靠近膠濟鐵路,交通比較方便,又加之
濰縣樂道院場地較大,因此被日軍強霸,他們趕走教師學生和醫護人員,將此辦成了監獄式的集中營,長江以北的美英等僑民陸續被擄來關押,大多被關押3年之久,其中包括327名兒童。成年人中有不少知名人士,有曾任蔣介石顧問的美國人雷振遠、華北神學院院長赫士、燕京大學校務長司徒雷登、齊魯大學教務長德位思等;還有曾獲奧運會400米冠軍的世界著名運動員英國人
埃里克·利迪爾(利迪 爾當時為英語教師,對教學工作有很強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在集中營內非常惡劣的條件下,仍盡其所能為裡面的孩子們授課。英國人以他 為原型拍攝的電影《火焰戰車》被評為奧斯卡金像獎。因饑寒交迫和操勞過度,利迪爾在抗戰勝利前不久在集中營內去世。1991年他的難友為紀念他,在香港發起成立了“利迪爾基金會”。因為他是蘇格蘭人,又曾在英格蘭求學,因此基金會專門分別從蘇格蘭和英格蘭采來花崗岩製成碑座和碑身,運到現濰坊二中安放);另有多名大學教授、醫生等高級知識分子。
集中營的人物
清潔工張興泰
日軍對被關押者的食物等生活用品供應極差,並嚴密封鎖裡面的訊息使外面難以得知,因此這些美英等僑民生活非常困難。
這時,一個平日默默無聞、名叫
張興泰的中國清潔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張是附近的農民,受僱在集中營向外運輸糞便,能夠較自由進出。一天,美國人德位思交給張興泰一封信,請他秘密帶出並送到原樂道院內所設廣文中學校長黃樂德牧師手中。信中說明了集中營內啼飢號寒的慘狀,請求黃想法援助。黃樂德
費心勞力募得包括當地百姓捐助的30萬偽元(據稱折合美元10萬出頭),通過瑞士(中立國)駐華使館同日軍交涉,將款項及購得衣食藥品等輾轉送進集中營。這些物品為緩解集中營內的窘境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後來好多前來濰坊二中憑弔重遊的僑民都稱讚這位普通中國農民的膽識和正義感。
大使恆安石
恆安石先生1981年至1986年曾任美國駐中國
大使,當年作為美籍僑民被關押在集中營內。那時日軍白天強行監督僑民勞動,晚上嚴加看管,僑民要想越獄十分困難。但1944年的一天,恆安石及英國人狄蘭神秘地逃出了集中營。這也是集中營內發生的惟一一次出逃成功的事件。
恆安石和狄蘭身體都較壯,精通
漢語,而且早就做好了出逃準備。此前,他們即通過清潔工張興泰托人同抗日力量取得聯繫,6月9日晚上他們發現日軍巡查崗哨有機可乘,便在難友的幫助下,瞬間逃出,出來後馬上被在外邊接應的游擊隊保護起來,並送到平度縣孫正村十五縱隊總部。恆安石和狄蘭在此受到了很好的禮遇。援華美軍後來為表謝意,曾給十五縱不少援助。
僑民得到解救
1945年8月15日,日軍宣布投降,但他們暫時並沒有放鬆對集中營的管制。關押在集中營內的僑民則通過種種渠道已經了解到
法西斯即將垮台這一訊息。
兩天后,一個看似平常的日子。突然,集中營內的僑民聽見自天空傳來一陣不同尋常的轟鳴聲,仰天望去,只見一架巨型轟炸機正在 集中營上空盤旋,隨著飛機的下降,機身上的美國標誌已看得十分清晰。集中營內的僑民一起歡呼起來。飛機上的美軍看清後,毅然實施了空降突擊,7名全副武裝的美國空降兵跳傘成功,落在集中營北則的玉米地里。他們著地後馬上向集中營撲去,自感末路已至的日偽軍看守全都嚇傻了眼,一動都不敢動。集中營內的囚徒們則狂喊著蜂擁推倒大門沖了出去,頓時兩股力量匯成一股,人們跳著、叫著、哭著、笑著,不分國籍、不分男女老幼地擁抱在一起。稍事平靜後,集中營內的樂隊奏起了中、美、英、蘇四國國歌選段,氣氛莊嚴肅穆。
之後,日偽投降,僑民有組織地陸續回國。
修建背景
樂道院處濰縣城(它與坊子合稱濰坊市)東南約一英里,原為李家莊農田,經代表人李芳齡售給美國長老會的代表
狄樂播(Rev. Robert M. Mateer, M.D., 1853-1921),時在1881年即光緒七年。
這是英法聯軍破北京燒圓明園,北京條約訂立二十年以後,中國民眾排外情緒仍舊激昂的時期。尤其是這個濰縣古城自隋唐以來文風特盛,科舉時期,人才輩出。光緒末年還出過兩名狀元,其一是慈禧最稱心的王壽彭,此公到了晚年在北洋軍閥時期曾任山東省教育廳長。要者,濰縣區的農產豐富,人力操作的織布工業是全國最密集之區,出品是棉布和繭綢俗稱
山東綢(shantungPongee),其他手工業如漂染加工,木雕器物,仿古銅器,直到今日,本地的風箏製造馳名世界。因此,自古迄今它是個工業城,其民眾不但自尊心重,排外情緒也比較激烈,在1881年的前後,倘有西方人進城不是被辱罵便是被欺侮。
在此情況下,狄樂播在此建造
教堂,醫院和學校,取名樂道院,必築圍牆以保全全,然它不足以擋住十五年以後
義和團策動下的民眾暴動,時在1900年。
根據美國長老會向清廷報失的資料已經說明:樂道院占地長約二百碼,寬一百五十碼,面積六點二英畝,等於二點五公畝,損失樓房四十二座,平房一百三十六間,可見初建時已具規模。
義和團在山東的又一名稱是大刀會。1900年山東巡撫是滿人毓賢,他鼓勵大刀會的活動,卒釀成教案,德國遂強租青島。義和團源出白蓮教,它盛於江淮間。在嘉慶時(1796-1820)初期的口號是“反清復明”,活動廣及華中與華北五省,百年後改了口號,為“扶清滅洋”,很受慈禧的嘉許。
毓賢被調山西,袁世凱繼任山東巡撫。袁世凱在發跡以前曾在登州(今蓬萊)的宋慶將軍下任一軍頭職位,和當年
登州文會館(先國小,中學後設大學)的館長狄考文(Calvin Mateer D.D., L.L.D., 1836-1908)交好。狄考文是樂道院的創辦人狄樂播的長兄。袁世凱上任後,查明山東民情,深恐政令不能下達,遂通知在山東省的各國領事,著他們將僑民撤退至通商口岸以保全全。濰縣區的外僑先去投靠在坊子開煤礦的德國警備區,山東西南部及河北省東部的外僑集中壽光縣的羊角溝,途中受到袁世凱派兵的護送,等候煙臺方面雇商輪來接迎。登州的外僑經袁世凱折衝樽俎,由北洋海軍統領薩鎮冰親率座艦海坼前來送他們到朝鮮。當年,平壤是美國長老會發展工作的中心。袁世凱的護僑政策致山東的外僑無一傷亡,此事激怒了北京的慈禧,大罵那個山東“洋巡撫”,正欲予以治罪,八國聯軍已兵臨城下。
重建
1902年,美國長老會得到清廷部分賠償,加上新收進的捐款,將樂道院重建。此時,德國築膠濟鐵路即將完成,濰縣恰在青島和濟南的中間,長老會遂決定將登州文會館的大學部遷到濰縣樂道院。結果,1904年文會館遷來此地與青州的廣德書院合併,各取一字,定名廣文學堂。
廣文學堂的中國教員名單缺如,美國藉教員前後可數十六名全為專業,其中還有濰縣的傳教士兼職的多位。其中有一位對樂道院重建及齊魯大學初創工程多次前赴美國募款最多(約三十萬美元)勞苦功高的是
路思義牧師(Henry Winters Luce, 1868-1941)。
變遷
廣文大學自從遷
濟南成立齊魯大學以後,樂道院仍是長老會的中心,包括醫院,醫院人員及傳教士的宿舍,校舍和學生宿舍則成為廣文中學的新校園。
珍珠港事變後它被封閉,成為集中營的所在。
日本的軍事當局將盟邦在華北,內蒙及偽滿州國地區的人民全部集中,拘於樂道院,將華中的拘於上海
閘北集中營,另有一集中營設在香港赤柱,是華南方面的集中營。
1945年八月十七日黎明前,一架B17型轟炸機自昆明起飛在西安上汽油,當日下午飛臨樂道院上空,七名跳傘的軍官安全著陸,守衛的日本士兵悄然放下了武器,集中營的俘虜遂得到解放。軍官之中有一名是中國人,譯音王成漢。
滿目瘡痍的樂道院重由長老會收回,處於內戰下,濰縣和其附近成為孤島,故難有什麼作為和重修的功果。等到內戰告終,進入1950年代,中國對美國人來說乃是大幕深垂。此後,樂道院這個名稱便逐漸消失人間。濰坊市政府在2006年八月十七日召開集中營解放六十周年紀念大會。出席參加的代表有:北京政府,美國駐北京的大使館,山東省政府。還有世界各地代表二十三人,全是當年被拘於樂道院的盟國年紀很小的學生“俘虜”,今日已成為老人。與會的民眾約為五千人,極盡地方一時之盛。
相關書籍
己丑之秋,正是豐收季節。如果把
濰坊文壇比作碩果纍纍的田野,那么,
馬道遠長篇小說《樂道院集中營》的出版,無疑為這田野增添了一道獨具特色的靚麗風景。
《樂道院集中營》雖非戰爭題材,但終歸是
歷史小說;而要將眾多的角色還諸歷史,使今天的讀者能觸摸到昨天的真景物,品嘗到昨天的真滋味,那也殊非易事。在這裡,作者的“修養”,即學識、知識面、文化水平、文學功力等等,就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據我所知,馬道遠是濰坊年輕人當中少有的文學迷、讀書迷,他讀書之多及知識面之廣,常令我輩年長者汗顏;設若馬道遠僅僅是一位熟悉當代農村生活的農民作家(我們濰坊這類作家並不少),那要他惟妙惟肖地塑造出《樂道院集中營》里的盟國僑民基督教徒,並且生動逼真地描繪出六十年前老濰縣人的生活畫卷,那顯然是不可思議的。
再進一步說,說到文學作品的“主題”即所謂“靈魂”的問題。按說在我們濰坊,樂道院集中營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此題材並非馬道遠一人獨占,過去也有不少人頗懷興趣甚至已動筆寫作;然而據我了解,大家關注的往往僅僅是“題材”即“樂道院”事件本身,思考的也僅僅是“侵略與反侵略、壓迫與反壓迫”這一一般層面上的問題(這問題錯倒沒錯,只是不夠,獨立思考的作家還應該再挖掘一下),而很少有人將思考的鋒芒觸及“宗教與人性”、“人的異化”、“人格的分裂”等等的層次。難得的是馬道遠這樣做了,所以他的作品內涵就顯得格外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