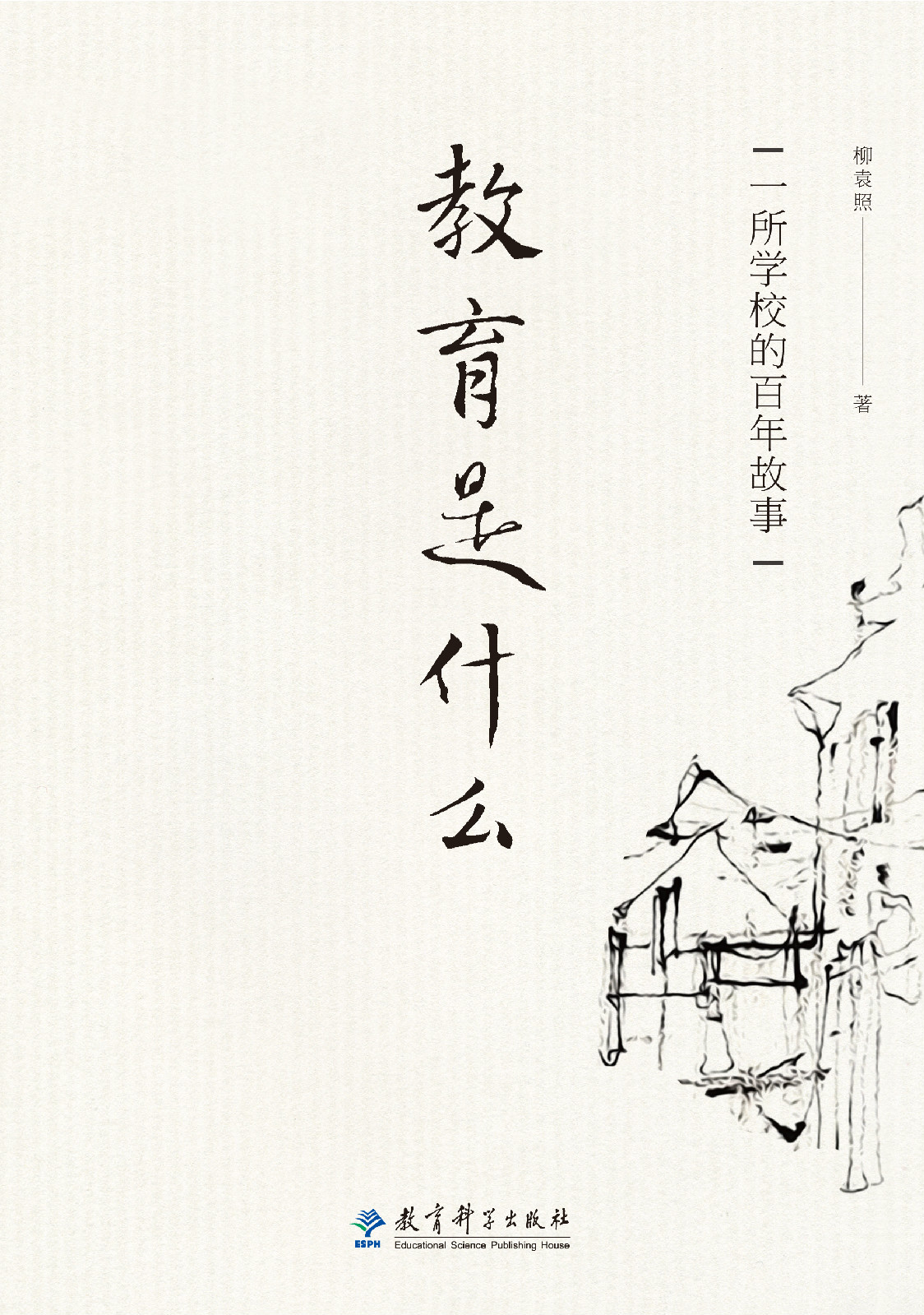作者簡介
柳袁照,語文特級教師,江蘇省
蘇州第十中學校長,教育部中學校長培訓中心兼職教授、蘇州大學碩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有《我在“最中國”的學校》《柳袁照詩選》《清泉石上》《我在這個園子裡·遇見你》《流連》等教育專著、詩集十餘部。

目錄
輯一 斯人
三先生王季玉
蔡元培的振華情緣
曾在西花園演講的胡適
兼職教師蘇雪林
老校長楊絳
“麥子女聖”沈驪英
費孝通與恩師沈驪英
“月季夫人”蔣恩鈿
“中國的居里夫人”何澤慧
李政道回母校
院士貝時璋與“中國的貞德”陸璀
校友葉梅娟、張羽的故
那些“準校友”的故事
夏鄭安老師走了
桂秉權老師與《此情未已》
亦師亦兄徐玉卿老師
寂寞的葬禮
布衣秦兆基老師
我的第一個語文老師
錢振邦老師搬家了
輯二 斯事
瑞雲峰的千年往事
舊雨來,今雨亦來
蘇州織造署的往昔與現在
穹窿山的記憶
行走在春天
諦聽天籟
真水無香
從母校帶走一生的財富
12月31日的迎新聯歡會
校園是什麼
愛的磁場
渾然天成的文化精魂
愛意在校園瀰漫
我與七班的故事
書寫我們自己的歷史
我在“最中國”的學校
在這個園子裡,遇見你
序言
教育是什麼?這個最簡單、最普通的問題,還需要問嗎?尤其是我們的校長、教師,每天都在學校里做著教育的事情。但有時,最簡單、最以為人人都知道答案的問題,是最講不清楚的。我們不用教科書上的語言,是否能憑自己的感悟,個性化地表述出教育是什麼嗎?至少我不能。這幾年,我天天想著這個問題。今天,看到校園草叢裡的一簇小花,我似有所悟,教育不就是這簇小花嗎?雖不起眼,也要盛開,盛開得自自然然。我一直推崇泰戈爾對教育的詩意的詮釋。他說,教育應當向人類傳送生命的氣息。這簇小花,雖然弱小,但渾身煥發出蓬勃的生命活力。教育不也如此嗎?無論是高貴,還是低賤,只要是生命都要讓它綻放。
尊重生命,以生命呵護生命。我們要尊重每一個孩子,他們都是完美的、獨特的“這一個”。教育就是要呵護他們,尊重他們,包括為他們的成長創設條件,捍衛他們成長過程中的尊嚴。這簇小花,引發我對教育本質的思考。今天的價值取向,在日常的學校生活中,是不是被扭曲了?我與我們的先輩一樣,也是主張崇尚自然的。我去年出了一本書,取名為《清泉石上》,意在表明教育要如“清泉石上”一樣,自自然然。唐朝詩人王維有兩句詩“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我以為教育就是要追求這樣的境界。
每一所學校都應該是教育的神聖、神奇之地,對每一個孩子都應當充滿愛,充滿關懷,把他們當成天才來珍愛,當成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上蒼之恩賜來培育。很榮幸,我所在的學校,就是這樣的一所學校。當年叫蘇州振華女校,今天叫蘇州十中的這所學校,已經走過了108年的歷程,歷史的氣息、文化的氣息與教育交織在一起。古樹名木與小花小草交相輝映,自然之狀態與百年人文傳統,如樹林成蔭,大氣古樸。40年前我曾在這裡讀書,感受這裡的一切,12年前我擔任了這所學校的校長,繼續感受這裡的一切。浸潤與體驗,使我真正認識與體會了什麼是教育,什麼是真教育、大美的教育。那就是,合乎道德的大善的教育。
我虔誠地對待這所學校,閱讀校園,閱讀校史,其實,是閱讀這個校園裡的每一個人,歷史的、現實的每一個人。他們是這所學校的主人,是在這個校園(能讓內心柔軟的地方)成長起來的生命,或大樹,或小花小草,都是鮮活的、能讓我感動的生命。師生們都以自己獨特的生命成長狀態,闡釋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平等的。我寫他們,記錄他們,闡述我對他們的理解,試圖揭示他們對我的影響。正因為他們幫助我成長,我的生命才變得更有價值。
三年前的新春第一天,我在學校值班。新春的第一朵花盛開在校園裡,老樹上的舊枝也綻出了新芽。我內心充盈,對這個校園充滿著愛和感恩,滿眼是美景,如蘇州園林般的畫景,需要對每個與這個園子有關的人交流、傾訴,隨即我寫了一首小詩,“在這個園子裡,遇見你,是個幸福的開始”。我對每一朵花、每一棵草、每一塊石頭致意。這是我對這個園子最幸福、最美好、最直率的表白。“你”是誰?是老師,是學子,是曾走進又走出的每一位校友,是每一個與這個校園有關的人。“你”是誰?為何我們不能再拓寬一些視野,不能把它看成是教育,看成是日常的、完整的、幸福的校園生活?
我在這裡,一年一年走過,當時只是感覺漫長,而今走過,再回首似乎僅是一瞬間。斯園、斯人、斯事,對我來說,都是生命中的珍藏;舊時光、新時光,對我來說,都是美好難忘的時光;瑞雲峰、老桂花樹,對我來說,都是教育的記憶。我把本書中的每一個文字,都看成是生命——屬於我的,更是屬於這個校園每一株草木的蓬勃生命。
柳袁照
(2014年5月22日)
文摘
老校長楊絳
近十年之中,我幾次北上,前去拜訪我們的老校友
楊絳先生。每次去看望她,我們聊得最多的話題,就是當年她讀書時的“振華”。振華女校,剛開始只有國小,後來又辦中學,再辦師範。楊絳在那兒學習了六年(1922~1928)。她對那裡有著太多的記憶,早年曾寫過一篇短篇小說《事業》,幾乎就是以在振華讀書的經歷為素材寫的。
我第一次見到楊絳先生是在2005年12月。那是陽光明媚的一天,我與北京振華校友會的幾位老校友一起去看望她。這些老人都是在各行各業很有建樹的人了,可是在楊絳先生面前,她們表現得依然像是小妹妹,小心翼翼地敲門,小心翼翼地說話。楊絳先生那年94歲,身體硬朗,典型的江南女子的氣質與風度,開門、讓座、端茶,溫文爾雅,吳儂軟語。
楊絳先生家的書房裡有幾張沙發、一張寫字檯、幾個書櫥。這裡曾是錢鐘書先生的書房,錢先生去世後,楊絳先生就在這裡讀書、寫作,也在此接待親朋好友。那天,她執意讓我們坐在沙發上,自己則坐在兩張沙發中間臨時放置的一張木凳上。她就像一個慈祥的祖母或外婆一樣,慢慢地與我們說往事,說她的王校長季玉先生,說她念念不忘的振華。
楊絳先生說:“振華有一股味兒,那股味兒影響了我一生。”她回憶說——
我在振華時,學校還不在今天的織造署舊址,而是在嚴衙前那個老振華校舍,一個大的、私人的宅子。外面是門房,進來是轎廳、大廳,後頭幾間是住房。樓上和樓下用木板與洋鐵皮搭成很簡陋的六間教室。現在,我閉著眼睛也能想得出來,哪兒是校長辦公室,哪兒是教員辦公室。後面樓下的大廳就是大課堂,早上的朝會都在那裡舉辦。教室四面漏氣兒,很“蹩腳”。英文是請外國先生來教的,其中有一個老師長得很美,在隔壁教室上課,我們經常湊到板壁上的窟窿眼去偷看。化學實驗室就在我們隔壁。有一次,學生做硫化氫實驗,氣味很濃,我們懷疑是誰“泄了氣”,還冤枉了一胖一瘦兩個姐妹。結果下課後,大家才知道,那是化學實驗室里躥出來的臭味兒。
校長季玉先生特別認真,又特別隨和。我與她在一起很多年。每天早上第一課(朝會)就是訓話。她總說:“伲(蘇州話,即‘我們’)振華,實事求是。”她說話有點兒捲舌頭,我們學不像,就問她:“你幹嗎要捲舌頭呀?”她說,小時候父母在外做官王季玉先生的父親王頌蔚,曾在清廷軍機處做章京,是蔡元培的座師。,保姆是外省人,所以帶得她們說話也有點兒捲舌頭。大事小事,她都要講“實事求是”。她告訴我們,從家裡帶來了菜,不要一個人單吃、不給別人吃,大家要過好集體生活。那時教師都與學生在一桌吃飯,季玉校長也與我們一起吃。所以,我們的一伙食一直都很好(其他學校都是校長單獨先吃,然後教師們吃,最後才是學生吃)。我們夾菜都用公筷,大家先把菜夾在自己的碟子裡,然後才吃。吃完飯,要把筷子擱在碗上,坐著,等大家都吃完了才一起離開。這是規矩。
2006年是蘇州十中百年誕辰,我們請楊絳先生為學校題詞。她揮毫寫下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然後又寫了一行小字“季玉先生訓話”,落款寫著“楊絳敬錄”。她小心翼翼地端詳著題詞,一再說“寫得不好”。已經95歲高齡的楊絳先生,仍然寫出如此筆力遒勁的字,這讓我們很是欣喜。回來後,我們精選了金山石,把題詞鐫刻其上,恭立於學校西花園中。這是楊絳先生對母校的紀念,其間凝聚著她對季玉先生的深厚情感。她說——
季玉先生上課時特別凶,可是等到晚上,就完全與學生打成一片了。校舍是老房子,有一條很長的弄堂。晚上,弄堂里只有一盞燈,點在大課堂的門口。季玉先生站在燈下,我們學生也都站在燈下,我們說的話她都聽。有一次,我對季玉先生說:“您叫我一聲阿姨吧,因為今天太先生(即振華的創始人、王季玉校長的母親王謝長達女士)和我說話時,稱我為‘季康妹’楊絳先生原名楊季康。。”季玉先生與我們親密無間,沒大沒小。有時,我們有點兒什麼不情願的,就當面跟她嘀咕,彼此沒有隔閡。我們可以跟她吵,跟她犟,跟她“胡來”,什麼都可以。可見,我們的感情是頂頂好的,大家都很愛她。那時候,我們振華的老師都是東吳大學的老師(兼職),水平特別高,許多老師都是名人,振華的學生成績也都特別好。我們用的教科書都是英文的,課堂上也都說英文。
這次拜訪楊絳先生,給我們帶來很多啟示。後來學校改造時,我們把有代表性的歷史、文化經過物化後,都安置在校園中。比如,學校建造了“季康亭”,亭子後面連著一條蜿蜒的長廊,長廊與西花廳相連,亭廊里有許多石刻,鐫刻著楊絳先生讀書時許多老師的畫像與生平簡介,王騫、葉楚傖、顏文梁都在其中。小小的振華學校,竟然能夠延請到這些大師,可想楊絳先生在此受到的是何樣的教育。在楊絳先生的回憶中——
當年振華有許多“會”(類似今天的學生社團),比如,“英文會”兩周活動一次,活動時不許說中文,只許說英文。還有“演講會”,所有學生都得上台演講。我剛到振華那年才十一二歲,聽說要登台演講,可真嚇死我了。於是我就到圖書館找了一篇東西背下來。“演講會”在大禮堂舉辦,我站到台上,看見下面全是人,感覺好緊張啊,結果背到一半就背不出來了,嚇得直哭,沒辦法,就想走下台,可是迷迷糊糊,竟然直接從台中央跳了下去,逃了。評判的時候,老師說我上半截講得還可以,竟然給了我鼓勵。我感到很不可思議。不過後來經過鍛鍊,我當上了學校“演講會”的會長和“英文會”的會長。振華的許多學生,畢業後都報考金陵大學,我也去考了,還考了第一名。金陵大學校長吳貽芳到我們學校來,季玉先生叫我坐在她旁邊,動員我上金陵大學,可是我放棄了,報考了東吳大學,最終又去了清華大學。
振華的課程比其他學校的都要多,都要豐富,對學生的要求也高。我們考試時分數也總是比其他學校的學生高。我們每周六都要“會考”,中學部和國小部的所有學生都要參加,什麼課程都考。考常識時,我常常能拿第一名,可要是考時事,我就不行了。考試時,學生答不出來,也得坐在那兒,到時間才能離開考場。
振華的辦學條件一般,但學生的生活與其他學校完全不同。我們的生活很艱苦,但學生很自治,樣樣都靠自己。其他學校教室的地板大都是廣漆的,拖地的有“娘姨”;而我們學校沒有,早上起來,學生的頭一件事就是做值日。地板都是爛的,有的爛成了窟窿,頭髮都被纏在掃把上,很難掃。桌子也是自己擦,衣裳也是自己洗。我們都是用井水,由學生自己打水。每一間舍房都有房長,大家輪值,自己的事情自己管。
當時經常打仗,有一次得到訊息後,我們出去躲避,每人穿了件大棉襖,帶個小包,裡面裝著一塊洗臉布和一支牙刷。大家排著隊,黑地里跑到景海女子中學。那裡的學生每人讓出半個床,與我們合睡。大家穿著衣服,脫了鞋,倒頭就睡。第二天早上起來,沒吃早飯,也沒洗臉漱口,就又排著隊,回到自己學校。當時正值大考,大家照舊考試,一點兒也不鬆懈。
振華十分重視學生的戶外活動,季玉先生常趕我們出去。可是振華的校舍很小,活動場地不大,只有一個操場,也就一個籃球場那樣大,緊貼著牆根,地上鋪的全是泥沙。於是,學校每周組織我們去南園。南園在城南,當時是一片田園,我們去那裡散步、跑步,偶爾還去菱塘里采菱。學校還經常組織我們去東吳大學參加大學生的活動,活動各式各樣,有的幽默、風趣,有時也會“捉弄人”。有一次,台上有人大叫,讓大家掏錢、扔錢,說誰掏得多、扔得多,就會生個大胖兒子。季玉先生耳背,聽不清楚,也沒弄明白,就學別人的樣子,也在那兒掏錢、扔錢,大家忍不住開懷大笑。我是一個淘氣、愛玩的人,可成績還不錯,季玉先生就讓我跳一級,但要求課程不能少,初三與高一的課都要聽,因此在同一年裡,我學了兩個年級的數學,而且居然都跟上了。這下,我再也沒工夫淘氣了。
楊絳先生與費孝通先生是振華的同班同學,費孝通是當時班裡唯一的男生,說起當年的事情,楊絳先生告訴我們——
有人說我們是同桌,其實不是。他是好學生,我是“壞”學生。上體操課時,我們要排隊,我長得矮小,排在最後邊,他就再排在我後面。體操課要學跳交際舞、民間舞,兩個人一組,手鉤著手。我發育得晚,啥也不懂,費孝通懂事早,不跟我跳,只站在我旁邊。我們跳不起來,我就生氣,跟他吵架。我說,你比我高,你應該排到前面去。他說,前面是女生,我不能去。我說,我們都是女生,你為什麼來這兒上學?我在沙坑裡畫他的樣子,畫一個醜化的臉,張著嘴巴,哇哇叫。後來費孝通的夫人只要見了我,就會提起這件事。她對費孝通說,你的女同學可真兇啊!
在講述這件往事時,楊絳先生一臉的笑容,耄耋老人,童心依舊。
楊絳是振華的學生,後來又回到振華當校長。那是1937年,蘇州淪陷,振華被迫搬遷到上海法租界。提到這件事,楊絳先生問我們這算不算她做過校長?問得很是真誠。我們說,這是歷史,當然算,不僅算,還應大書一筆。楊絳先生說——
那個校長是季玉先生“逼”我當的。她哭著對我說:“我把自己都‘嫁’給了振華,可是日本人來了,不能再在蘇州辦學了,只能去上海,你不幫我誰幫我呢?”我被感動得心軟了,就對季玉先生說:“我幫你!”她很高興,馬上請孟憲承先生(後來成為華東師範大學第一任校長)到教育局去立案。我那年26歲,樣子看起來很年輕。可是當校長要老成一點才好,於是我拚命裝老,把頭髮捲起來,像個傳道婆婆,可怎么裝也裝不像,很可憐的。我什麼事情也不會做,但什麼事情都必須做,包括去找校舍。我與季玉先生天天出去跑,六個班級,至少需要六間房,我們看中了的大房子還租不起。我記得當時季玉先生交給我一個存摺,裡面是她省吃儉用攢下來的美金,她讓我帶著,這就是我們全部的辦學經費啊!可那時物價飛漲,這3000塊錢就像泡了湯一樣,不值錢。那段時間季玉先生吃的是什麼?她用糠蝦蘸蘸醬油下飯;牛奶餿了,她也捨不得倒掉,說那不等於優酪乳嗎?於是就吃“優酪乳”。季玉先生有一句話:“居無求安,食無求飽,先人之憂,後人之樂。”這是她自己的寫照啊!我曾經給她買了一件羊毛衫,她死也不肯收。我說:“學生孝敬您,您為什麼不能收?”她回答:“我從來不收人家的禮物。”我給她織了一雙襪子,她是大的小腳,我是按照她的尺寸織的,她卻說:“我不穿的。”於是,我對季玉先生髮脾氣,當著她的面把襪子都拆掉了。
季玉先生在這方面是非常偉大的,對我的影響很大。她還交給我一枚振華的校印。除了管學校,我還教高三的英文,爸爸說我這是“狗耕田”。
回憶起這些,楊絳先生飽含深情。那天,楊絳先生知道我們要去,一大早便坐在桌前,默憶當年的校歌,然後,恭恭敬敬地把它抄錄在紙上。我們坐下後,她唱給我們聽:“三吳女校多復多,學術相觀摩。吾校繼起,德智體三育是務。況古今中外,學業日新月異。願及時奮勉精進,壯志莫蹉跎!”開始她只是小聲地哼,慢慢地便唱出了聲。楊絳先生說自己耳朵背了,那些音也就掌握不準了。她還記得當年自己唱校歌時穿的是深棕色的校服、黑鞋子、白襪子。
80多年前的往事,老人家竟然還記得那么清晰。蘇州十中西北角有個小丘,樹木蔥鬱,最高處有一小亭,說到它時,楊絳先生興致很濃。當時,她在老宅子裡讀書,畢業前,學校搬遷到清朝織造署遺址。她也參加了搬遷勞動,這個小亭子是她和同學們一起搬磚頭建起來的,是他們那一屆學生留給母校的畢業紀念物。在我們的拜訪即將結束時,楊絳先生深情地說:“請把我對母校的想念帶回去!”
距離2005年的那次拜訪已經九年了,但當時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這些天,我一直在想:楊絳先生一再說的“振華的那股味兒”到底是什麼?也許就是她那天與我們敘述的那樁樁往事中所蘊含的種種意味吧?!“那股味兒”代代相傳,綿延百年,將永遠氤氳在美麗的校園中。
(2014年7月7日)
兼職教師蘇雪林
胡適的弟子
蘇雪林曾經在振華女校教書,那是1930年代的事情。十多年前,蘇雪林從台灣致函蘇州十中:“60年前,我是在振華學校兼過幾小時的功課,教的是什麼今已不憶,那時校長是王季玉先生,留學美國,一生以辦學為職志,振華就是她獨立經營的,管理嚴格,功課認真,造就人才蔚然稱盛。”我們查閱歷史檔案,當年蘇雪林在振華女校,擔任學生社團“國文研究會”新文學組指導教師。她與楊蔭榆在振華共事過。一個曾經是北京女師大的校長,一個曾經是北京女師大的學生,命運讓她們曾一起在西花園棲息。
蘇雪林是一位有個性且有爭議的中國現代著名女作家。她執筆時間之長,在中國新文學史上也是少有的。她的作品幾乎涉及所有題材,天地萬物囊括其中。她活到102歲,一生無子嗣,婚姻也頗為不幸,在振華教書期間,住在天賜莊附近。她為1930年5月的《振華女校校刊》作序。序中說:“振華者,余向向學校之一也。創辦以來於今十餘載,校長王季玉先生苦心擘畫,不遺餘力,校務蒸蒸日上,聲譽卓著。其管理嚴密,教授認真。師生朝夕所孳孳者惟研究學問而已,砥礪品行而已,於時下之惡習,一無所染。學成而升學者十九錄取,其出而任事者亦大得社會歡迎。”蘇雪林對振華女校評價極高,一生都是如此。
楊蔭榆去世的第二年,蘇雪林得悉訊息後,寫就了著名的《悼女教育家楊蔭榆先生》一文,在對好友楊蔭榆的懷念中,仍不忘說“七月間我回蘇州度夏,會見了我最為欽佩的女教育家王季玉先生”。蘇雪林對振華校長王季玉評價極高,一生也都是如此。
蘇雪林曾與魯迅論爭。她從對魯迅欽佩,走向反對。一個重要的緣由就是北京女師大風潮,蘇雪林與魯迅對楊蔭榆女士的看法截然相悖。1938年7月蘇雪林回到蘇州:“我特赴楊宅拜訪蔭榆先生。正值暑假期內,學生留校者不過寥寥數人,一切規模果然簡陋。談起女師大那場風潮,她原原本本地告訴了我。”
蘇雪林1949年去了台灣。
蘇雪林對老師有一顆敬仰、感恩之心,這一美德,無論如何都是我們應該繼承的。蘇雪林對她的老師胡適,真的是情有獨鐘,“由欽敬而至於崇拜”,拿她自己的話來說“老而彌篤,痴心一片”。
1959年,胡適在台灣師範大學畢業生典禮上做演講。當時蘇雪林適巧在台灣師範大學任教,她也在場,坐在前排。胡適先生講為人師之道,講著講著,忽有感慨。他說,為人師不易,他自己教書30年,不知自己究竟給了學生多少好處,聽人稱自己為老師,總會慚愧。胡適隨即舉例說,如他在北京女師大教書,出過幾個人才,女作家蘇雪林,至今還“老師”、“老師”地稱呼自己,真叫人難以承擔。這個細節,是蘇雪林自己在《適之先生和我的關係》一文中披露的,可以想像,當時,坐在台下的蘇雪林心裡是怎樣的高興。
隨著年事漸高,蘇雪林對胡適的師生情誼有增無減,她把胡適稱為“現代聖人”。在胡適面前,總有某種近賢近聖的感覺。她自述,孔子、朱熹、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哲人學者俱往矣,都不可見,而她現在竟能和與那些古人同樣偉大的人共坐一堂,親炙他的言論風采,而感幸運不已。
由於歷史的原因,蘇雪林一度不為人所知。
蘇雪林的作品《溪水》,現在已編入滬教版七年級下冊語文新教材。
在學校西花園的長廊里,繼楊蔭榆、胡適之後,我們也為蘇雪林鐫刻了一塊石碑,上面寫著:“蘇雪林(1897—1999),振華女校教員,作家、詩人和學者,被譽為20世紀30年代‘女性作家中最優秀的散文作者’。1930年到1934年,在振華擔任學生社團‘國文研究會’新文學組指導教師。1995年10月7日,先生從台灣致函學校,稱振華‘管理嚴格,功課認真,造就人才,蔚然稱盛’。”
(2009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