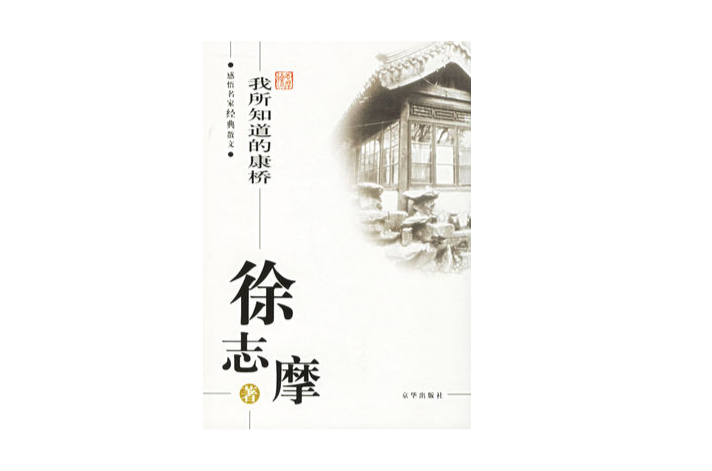本書收選了徐志摩最經典的散文39篇。為了幫助青少年讀者更準確地理解現代文學經典名著,編選者對原著中生僻的字和詞做了必要的注釋,並在每篇散文後附有簡短的解讀評點。相信讀者朋友翻開本書的同時,一定會體驗到高效通暢的閱讀快感。
基本介紹
- 書名:我所知道的康橋:徐志摩散文經典
- 出版社:二十一世紀出版社
- 頁數:354頁
- 開本:16
- 品牌:天下書盟
- 作者:徐志摩
- 出版日期:2014年10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9190877
內容簡介
有人說:“散文可以比較直接而真切地反映一個作家的人生感受與思想歷程。”這句話對於有著“民國四大才子”美譽的徐志摩而言,更是恰如其分。徐志摩的散文沒有那些營造氛圍和矯揉造作的痕跡,讀來好似與最親密的朋友對話——他坦陳自己的心跡給你看,對他的情感和經歷讓你感同身受。這份隨性和灑脫,這種親熱和真誠使人在閱讀中得到最大的被尊重和被信任的幸福感。可以說,他那些從心窩裡流淌出來的文字,成就了文學史上的一個經典。
媒體推薦
圖書目錄
9/印度洋上的秋思
17/翡冷翠山居閒話
22/巴黎的鱗爪
37/我所知道的康橋
49/天目山中筆記
56/“濃得化不開”(星加坡)
63/“濃得化不開”之二(香港)
69/“死城”(北京的一晚)
78/北戴河海濱的幻想
82/一封信(給抱怨生活乾燥的朋友)
86/“迎上前去”
92/自剖
99/再剖
104/求醫
110/想飛
116/曼殊斐兒
132/泰戈爾
140/濟慈的夜鶯歌
151/丹農雪烏
166/羅曼羅蘭
174/謁見哈代的一個下午
182/白郎寧夫人的情詩
205/一個行乞的詩人
218/“就使打破了頭,也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
221/羅素又來說話了
231/落葉
245/論自殺
255/守舊與“玩”舊
262/吸菸與文化(牛津)
267/盧梭與幼稚教育
276/“話”
287/海灘上種花
294/關於女子(蘇州女中講稿)
308/秋
318/我的祖母之死
331/我的彼得
336/吊劉叔和
341/傷雙栝老人
345/家德
351/徐志摩年表(1897—1931)
序言
野馬上的唱詩者
作為新月詩派的靈魂,志摩以詩著稱,藉詩傳世,而其散文亦屬佳品,搖曳多態,光華灼灼,豐麗馥郁,頗為可觀。諸多文段不啻詩歌,美得出塵,自天上來,仿若玉露瓊漿,我們且擎起杯盞:初巡口腹歡愉,再巡靈魂微醺,三巡身心偕忘。梁實秋先生說:“我一向愛志摩的散文。我和葉公超一樣,以為志摩的散文在他的詩歌以上。志摩的可愛處,在他的散文里表現最清楚最活動。”楊振聲先生亦稱:“至於他那‘跑野馬’的散文,我老早就認為比他的詩還好。那用字,有多生動活潑!那顏色,真是‘濃得化不開’!那聯想的富麗,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態度與口吻,夠多輕清,多頑皮,多伶俐!而那氣力也真足,文章里永看不出倦怠,老那樣像夏雲的層涌,春泉的潺湲!他的文章的確有他獨到的風格,在散文里不能不讓他占一席之地。比之於詩,正因為散文沒有形式的追求於束縛,所以更容易表現他不羈的天才吧?”此論既肯定了志摩的散文,且對其藝術特徵的概括恰切而生動。
志摩1922年於文壇初試啼聲,至1931年殞落塵寰,前後不過十載,而創作頗豐,留下四部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四部散文集:《落葉》、《巴黎的鱗爪》、《自剖》、《秋》,一部小說集《輪盤》,一部戲劇《卞崑岡》,以及諸多譯作、集外詩文。以詩名世的志摩,不論作散文抑或寫小說,無不賦之以“濃得化不開”的詩情。盛瓶雖異,而馨香恆在,穠麗無改,千姿一貫,總教人忘不了是為志摩的篇章。他自稱:“我是一隻沒籠頭的野馬,我從來不曾站定過。”彼時及後世的論者便愛以“跑野馬”形容其自由無羈的文風。我們不妨視之為野馬上的唱詩者。知堂先生的澀味與沖和氣象是學不來的,而志摩的詩情與野馬風氣怕也難以仿擬。前者煉的是心境與造詣,後者仗的是天賦與個性。這恐都歸於造化的吧。
如上所述,志摩的散文頗具“野馬風”,行文如脫韁野馬,騰躍恣縱,奔跳自如,靈動無拘,行止由意,往復隨心,寫得洒然、翩然、飄然,一任思緒飛動、聯想迭生、意象沛發。此正是志摩個性之瀟灑、創造之活躍與想像之豐沛的體現。且以《印度洋上的秋思》為例,文章里時而是恆河邊情醉的男女,時而是紗帳中甜睡的嬰兒,時而是河石上獨傷的詩人,時而是柴屋裡悲泣的少婦,時而是抽菸的礦工,時而是凝定的潭水,時而又迴轉於志摩的船上,並藉以引發又一輪遐思,繁縟絡繹,綿綿未斷,目不暇給。其野馬風氣,可見一斑。然而這匹“野馬”並非無蹤可尋、散漫無度、亂縱失序,文章里雖是畫面繁複、聯想紛呈,但其間卻有聯絡,即一輪清明的秋月。而縈繞秋月者,是志摩的一脈綿綿愁思。
志摩到底是詩人,作文如唱詩,取其兩長,異彩各彰,既得了散文形式之自由,也未嘗阻遏詩情之涌流;既有散文的平易、曉暢、連貫與完整,亦不乏詩歌的意境、意象、音韻與跳躍。簡而言之,志摩的散文是“詩化散文”,頗具形式感,尤為風格化。舉其要者,即修辭之繁與音樂之美。志摩的文章,網羅艷華之象,出入虛實之間,讀之不能不能感受到他修辭的縟麗。其譬喻豐富,意象層出,聯想環生,排比成勢,處處珠璣,在在有情。同時,志摩善於協調長短句式,以成節奏的起伏緩急、音韻的悠揚鏗鏘,求的是音樂之美。試舉一段,描寫雲雀,文出《想飛》:
你能不能把一種急震的樂音想像成一陣光明的細雨,從藍天裡衝著這平鋪著青綠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點都是跳舞的小腳,安琪兒的。雲雀們也吃過了飯,離開了它們卑微的地巢飛往高處做工去。上帝給它們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著,這兒一隻,那邊又起了兩!一起就衝著天頂飛,小翅膀活動的多快活,圓圓的,不躊躇的飛,——它們就認識青天。一起就開口唱,小嗓子活動的多快活,一顆顆小精圓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們讚美的是青天。瞧著,這飛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頂著無底的天頂細細的搖,——這全看不見了,影子都沒了!但這光明的細雨還是不住的下著……
前兩個句子之精彩,令人拍案叫絕。層層比喻,相互套嵌,連綴成片,繁密無間,由近而遠,打通感官,恣縱想像,又恰切得當,不能不服膺志摩的詩才。所謂“妙喻”,須既“奇”且“通”。初讀,耳目一新,頗感陌生;再思,情理俱通,甚覺恰切。這兩句話有著水晶般藝術品質,讀之仿佛看到水晶結生水晶,生髮不已,彼此輝映,無限純粹。後面關於雲雀的飛動與啼囀的敘寫,多出之以靈動的短句,既活現雲雀的情態,且富於音樂性,節奏輕快活潑,宛如雲雀之樂音。徐文之詩化,由此可見。志摩的文章富於變化,此處恐難詳盡,只得見諸具體篇章的賞析了。
被低估的現代性批判者
志摩的思想、主張和關切,在散文里表達得最為清楚。而每篇內容到底不同,或雲遊異國,或深自省察,或審視社會,或悼念逝者,所感各異,所思有別,此處取其犖犖大端者,或謂一以貫之者,亦是最富啟示者。同時,筆者擬為志摩的思想略作重估,稍作辯護,旨在反思當下。對於讀者而言,或可視之為閱讀的意義所在。
20世紀90年代以降,大眾媒體所書寫的志摩形象,大抵是一位風度翩翩的貴族公子哥,是情聖、情痴的代表,故其所演繹的故事無出於才子佳人、風月韻事的範圍。比之於上世紀50—70年代對志摩的政治大批判和全盤否定,大眾文化雖是給他“黃袍加身”,但同樣是“不及其餘”式的理解,是一種遮蔽、誤解與低估。至若今日學界,其對志摩思想的梳理及概括,大體全面,相對客觀。但在價值、意義的評估上,其或不置一詞,或罔顧其最深刻的洞見。而這殊非意外,是今人對現代性的迷信使之然。志摩彼時不合時宜,今日亦然,一如他的自嘲:“我的信仰,我也不怕陶先生(陶孟和——編者注)與讀者們笑話,我自認永遠在虛無縹緲間。”倘若沒有對人性、生命、人生與世界更為廣闊的理解,是難以理解一位詩人之意義的,因為他所呼喚的正是這份“廣闊”,而非一點羅曼蒂克的幻想。
胡適先生對志摩有一段評語,已成後世不易之論,即“他的人生觀里真是有一種‘單純的信仰’,這裡面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里,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一生的歷史,只是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歷史。”此言大體不錯,而容易引入誤解之處,即許多人將志摩的“單純信仰”狹隘地理解為是他個人的實現,而無視他對社會的關切。除卻上述“愛、自由、美”的單純信仰,志摩也是一個情感的信仰者、生命的信仰者、自然的信仰者。而這些亦可統一於他的單純信仰。這份信仰,絕非囿於他個人之美好生活的意義,更是他對生活共同體的關切,是對整個現代生活的重新構想。在精美的語言器皿里,志摩投入了對現代生命深情眷注的目光,盛放了對社會的憂思與性靈的補劑。人,尤其置身於現代處境者,應當如何生活?這是他所追問、所關懷、所思考並不斷作答的根本問題。或許他的思考不成系統,或許他的觀察亦有偏頗,或許他的回答無甚創見,但並非不深刻,並非沒有啟示,並非大流之論。我們該摒除既往對他的固定印象與圖式,重新傾聽他的聲音。
志摩對現代文明的批判是激烈的,其觀點今天讀來仍不失振聾發聵之效,且愈發見其深刻性。他自然不是守舊派,卻也不迷信現代。他曾說:“歸根的說,現有的工業主義、機械主義、競爭制度,與這些現象所造成的迷信心理與習慣,都是我們理想社會的仇敵,合理的人生的障礙。現在,就中國說,唯一的希望,就在領袖社會的人,早早的覺悟,利用他們表率的地位,排斥外來的引誘,轉變自殺的方向,否則前途只是黑暗與陷阱”(《羅素又來說話了》)。他還說:“在我們一班信仰(你可以說迷信)精神生命的痴人,在我們還有寸土可守的日子,決不能讓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性靈的表現,更不能容忍某時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現代是科學)的黑影完全淹沒了宇宙間不變的價值”(《論自殺》)。在志摩看來,“現代的文明只是駭人的浪費,貪淫與殘暴,自私與自大,相猜與相忌,颺風似的傾覆了人道的平衡,產生了巨大的毀滅”(《泰戈爾》)。他認為,科學破除宗教迷信,而自身成為現代迷信;而現代文明本身,也是一種野蠻,如他說:“那時候的人(對現代文明沾染較淺的人——編者注),我猜想,也一定比較的不野蠻,近人情,愛自然,所以白天裡聽得著滿天的雲雀,夜裡聽得著夜鶯的妙樂”(《濟慈的夜鶯歌》)。而這正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現代的看法:“人類沒有進入真正的人性,反而深深地陷入野蠻狀態。”他們在《啟蒙辯證法》一書中認為,啟蒙使人類依靠理性與科學而從神話世界中解放出來,而其自身成為新的神話,帶來了新的蒙昧。“一個被徹底啟蒙的世界卻籠罩在一片因勝利而招致的災難之中。”可以說,志摩的觀點對於彼時和今日狂熱追求現代性的中國而言,都顯得不合時宜。然而我們只消看一看現代性所帶來的危機,如最為直觀的生態危機,便會覺得他的話也並非是無的放矢。
對現代性做出批判,或許如今看來不算新鮮,諸多知識分子致力於此業。而志摩的啟示性何在呢?難道僅僅是因為他把這些觀點表達得娓娓動聽嗎?筆者以為,志摩的洞見與啟示在於:現代文明的病因在人自身,在人心。他說:“如其一時期的問題,可以綜合成一個,現代的問題,就只是‘怎樣做一個人?’”難道生態危機不是緣於人類的貪婪嗎?所以他始終呼喚著心靈的真純,表彰著偉大的人格,如《泰戈爾》、《羅曼羅蘭》等篇章。他的文字是人性高貴的表達,是赤子之心的躍動,是告訴我們學會面向偉大,將心靈敞向豐饒。我們大概習慣了“欲望敘事”所表達的當代人性,習慣了由資本邏輯所界定的“現實”,也見慣了媒體所追捧的商業成功者。而志摩告訴我們,不必理會美國十大富豪,該去傾聽托爾斯泰與甘地的真諦。
志摩對現代性的批判,是一種審美的批判,道德的批判,倫理的批判。“精神的生命”,是他的出發點和歸宿地。張汝倫先生在《如果泰戈爾今天來華》一文中指出:
對西方種種制度(machinery)的迷信,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社會科學在中國思想文化界占有壓倒的優勢就是一個明證。人們不但不反對現代的物質主義,更不反對這種物質主義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現,這就是社會科學帝國主義。人們總是停留在物質制度層面談問題,幾乎沒有人再關心人的精神了,更沒有人會從人的精神和靈魂出發來談問題,十幾年前人們對人文精神討論的反應,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這一點。人們認為當務之急是制度,而不是人心,人心早已不在我們的思想家考慮的範圍之內……我們不能不承認今天世界上的種種問題歸根結底是人的問題,世界的危機歸根結底是人的危機。近代以來,人們陷入的最深的迷信是制度迷信,以為有某種制度可以包治百病,不但能使民富國強,也能使魔鬼變成善人。這種迷信是啟蒙對工具理性迷信的一個變種。
面對現代的問題,與泰戈爾的著眼點庶幾近之,徐志摩正是從人心、精神和靈魂的角度來談,從人自身來談,所以他才說:“我們自身就是我們運命的原因”(《落葉》)。學人李慧超指出:“我們不僅缺乏對自我的思考,也缺乏這種思考的意識,所以無論是什麼時候,我們都會習慣性的找‘自我’以外的原因,比如制度。”我們在探索制度的同時,或許也該思志摩所思、問志摩所問:怎樣做一個人?這或是問題的肯綮所在,也是最可珍貴的啟示。
志摩對現代世界的期望,是一個有情的世界。他希望以“感情”來重構現代人之間的關係。他者對於我而言,並非一個契約主體,且彼此關係並非被現代權利觀念和資本邏輯所宰攝。在志摩看來,“真的感情,真的人情,是難能可貴的,那是社會組織的基本成分”(《落葉》)。人在社會中是孤立的個體,而感情則如同線索和經緯,將人與人聯繫在一起,形成和諧的整體與統一的力量。他認為,社會的危機是感情的危機。現代社會的根本病症不在於政治經濟制度,而是真的感情的喪失,是人心的墮落。
大抵或有人譏嘲志摩天真、虛妄,將其想法歸於一個詩人的浪漫幻想。首先,這類人貌似精明而成熟,實則視野狹隘而淺近,目光為現代性原則所蔽,缺乏對生命、生活的廣闊理解,失去對個人存在和人類歷史的新的想像。我們為什麼單單迷信制度,而不著眼於感情?我們為什麼獨獨信賴物質,而不尊重精神?我們應該有不同的思考,不同的構想,不同的追求,為了一個不同於今日的美好而良善的未來。“人類對世界、對自己可以有一個更為自由和廣闊的理解。只有這種理解,才能把人類從現代性中拯救出來”(張汝倫語)。
此外,筆者不認為志摩的思想是完全脫離傳統和本土的,並非某些論者所言:“當徐志摩全身心地融入到劍橋式的西方文化體系中去時,他卻沒有很好地把它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首先,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中國人“從中國就家庭關係推廣發揮,而以倫理組織社會,消融了個體與團體兩端”(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人與人之間所重者,是情與義。“在中國社會處處見相與之情者,而西洋社會卻處處見出人與人相對之勢。”(同上)志摩提出“感情”是社會組織的基本成分,期望以修復感情來修復現代社會,正合貴人情、重鄉情的傳統國情。而他所謂“感情”,是“友愛與同情”,融入了“平等”的現代精神。其次,志摩貴自然,強調在自然中求得性靈自由、身心和諧,這固然可說是受英國湖畔詩人的自然主義的影響,卻也未始不見莊周的影子。
人云志摩西化尤甚,是個人主義者,亦言之有據。然而,我們莫忽視志摩身上的古典氣質或“反現代”特徵。在諸多篇章里,志摩未嘗言理性與權利,說的是性靈與感情;所重並非科學,熱愛的是自然;矚目的不是獨立個體,關注的是人倫關係。這也是確鑿有據的,見諸《落葉》、《秋》、《羅素又來說話了》、《泰戈爾》等文。倘若我們的世界精神頹敗、感情貧乏、性靈窒礙、自然毀壞,那么權利、民主、科學等又有何存在的意義呢?
胡適說:“他(徐志摩——編者注)的失敗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的失敗。他的追求,使我們慚愧,因為我們的信心太小了,從不敢夢想他的夢想。”或許徐志摩正如堂·吉訶德,屢屢碰壁,總在失敗,時被譏訕,更被風車打翻在地。然而這位愁容騎士到底走了多遠,經歷了怎樣的豐富,見到了怎樣的世界,實現了怎樣的奇蹟,是他的鄉人們永遠不知道的。口言歷史、現代、人類等,太過宏大,且從自身說起:對人生自由而廣闊的理解,對生命的另一重想像,對心靈圖景的拓展,對人性高貴的嚮往,對美的深切感受,或可成為我們閱讀志摩的起點和終點。志摩的文字,是我們心靈的詩意的棲居之所。
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