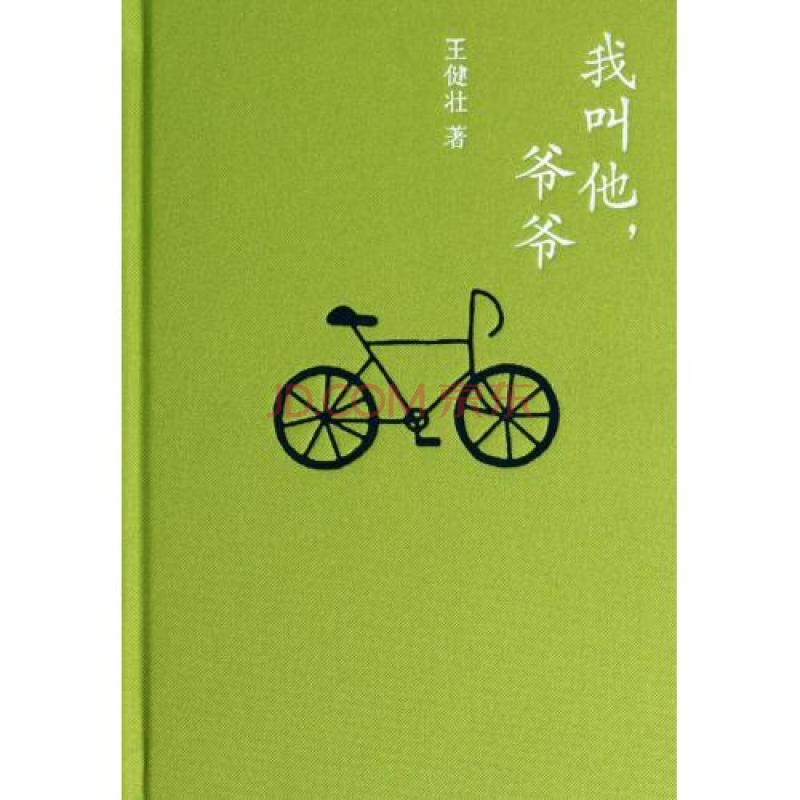者、專欄主任、採訪主任,《時報雜誌》社長兼總編輯,《時報新聞周刊》總編輯,《新新聞》總編輯與社長,《中國時報》總編輯與社長,博理基金會執行長。出版《我不愛凱撒》、《看花猶是去年人》、《我叫他,爺爺》等書。現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基本介紹
- 書名:我叫他,爺爺
-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頁數:296頁
- 開本:32
- 作者:王健壯
- 出版日期:2014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9548804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王健壯,當前台灣重量級的新聞人與時事評論家。長年在報紙專欄撰寫時事評議,見證幾十年來的媒體發展,自稱老派記者,相信自由價值。健談、敢言、評議、論理,媒體人與評論家所需要的客觀與文辭精準,使他的文字比普通文人多一分清晰從容的縱深感。
★這本回憶父親的專欄集結,展現了王健壯冷靜理性以外的一面。五十篇故事,忠厚、純真,穿梭時空,尋尋覓覓,最終所得,仍只是一幅殘缺未全的尋父圖,以及,一部人子懺悔錄。
★本書榮獲2013台北書展大獎,龍應台、楊照、馬家輝 許知遠等名家傾情推薦。
★這本回憶父親的專欄集結,展現了王健壯冷靜理性以外的一面。五十篇故事,忠厚、純真,穿梭時空,尋尋覓覓,最終所得,仍只是一幅殘缺未全的尋父圖,以及,一部人子懺悔錄。
★本書榮獲2013台北書展大獎,龍應台、楊照、馬家輝 許知遠等名家傾情推薦。
作者簡介
者、專欄主任、採訪主任,《時報雜誌》社長兼總編輯,《時報新聞周刊》總編輯,《新新聞》總編輯與社長,《中國時報》總編輯與社長,博理基金會執行長。
出版《我不愛凱撒》、《看花猶是去年人》、《我叫他,爺爺》等書。現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出版《我不愛凱撒》、《看花猶是去年人》、《我叫他,爺爺》等書。現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記者下筆快速,但不一定邏輯鋒利。編輯思慮多面,但不見得洞燭幽微。文人容易意氣飛揚,但風雨襲擊時並非每個都能屹立不移。政論家善於針砭時弊,但論及歷史的縱深、思想的重量或者家國情懷的承擔,不見得個個都有。王健壯是記者,是編輯,是文人,是政論家,但是他同時如白荷出水,高高地在風中招搖一種稀有的價值標準。——龍應台
用剛毅之筆寫出溫柔之愛,當評論家決心溫柔起來,可以是,非常地,溫柔。——馬家輝
政論家善於針砭時弊,但論及歷史的縱深、思想的重量或者家國情懷的承擔,不見得個個都有。王健壯是記者,是編輯,是文人,是政論家,但是他同時如白荷出水,高高地在風中招搖一種稀有的價值標準。——楊照
比起他在報紙上那些過分端莊、鏗鏘的政治、社會評論,這些個人回憶無疑更富魅力,它們也完美地解釋了高雄眷村的小孩緣何變成了今天的王健壯。作為大時代的個人,如何被時代所塑造,又如何改變時代。——許知遠
用剛毅之筆寫出溫柔之愛,當評論家決心溫柔起來,可以是,非常地,溫柔。——馬家輝
政論家善於針砭時弊,但論及歷史的縱深、思想的重量或者家國情懷的承擔,不見得個個都有。王健壯是記者,是編輯,是文人,是政論家,但是他同時如白荷出水,高高地在風中招搖一種稀有的價值標準。——楊照
比起他在報紙上那些過分端莊、鏗鏘的政治、社會評論,這些個人回憶無疑更富魅力,它們也完美地解釋了高雄眷村的小孩緣何變成了今天的王健壯。作為大時代的個人,如何被時代所塑造,又如何改變時代。——許知遠
名人推薦
記者下筆快速,但不一定邏輯鋒利。編輯思慮多面,但不見得洞燭幽微。文人容易意氣飛揚,但風雨襲擊時並非每個都能屹立不移。政論家善於針砭時弊,但論及歷史的縱深、思想的重量或者家國情懷的承擔,不見得個個都有。王健壯是記者,是編輯,是文人,是政論家,但是他同時如白荷出水,高高地在風中招搖一種稀有的價值標準。
——龍應台
用剛毅之筆寫出溫柔之愛,當評論家決心溫柔起來,可以是,非常地,溫柔。
——馬家輝
政論家善於針砭時弊,但論及歷史的縱深、思想的重量或者家國情懷的承擔,不見得個個都有。王健壯是記者,是編輯,是文人,是政論家,但是他同時如白荷出水,高高地在風中招搖一種稀有的價值標準。
——楊照
比起他在報紙上那些過分端莊、鏗鏘的政治、社會評論,這些個人回憶無疑更富魅力,它們也完美地解釋了高雄眷村的小孩緣何變成了今天的王健壯。作為大時代的個人,如何被時代所塑造,又如何改變時代。
——許知遠
——龍應台
用剛毅之筆寫出溫柔之愛,當評論家決心溫柔起來,可以是,非常地,溫柔。
——馬家輝
政論家善於針砭時弊,但論及歷史的縱深、思想的重量或者家國情懷的承擔,不見得個個都有。王健壯是記者,是編輯,是文人,是政論家,但是他同時如白荷出水,高高地在風中招搖一種稀有的價值標準。
——楊照
比起他在報紙上那些過分端莊、鏗鏘的政治、社會評論,這些個人回憶無疑更富魅力,它們也完美地解釋了高雄眷村的小孩緣何變成了今天的王健壯。作為大時代的個人,如何被時代所塑造,又如何改變時代。
——許知遠
圖書目錄
序一:《中時》的味道/許知遠
序二:那一段我們在眷村的青春歲月/張力
自序:尋父圖
【輯一】 以父之名
證書
離家
照片
那把寶劍
黃豆芽
油行
雨衣
坡地上
爺爺
雨中山櫻
旅行
沉默
那碗面
等待公車
南下列車
那兩句話
最後的夏天
永和那個家
陌生的父親
初一旗津
最後的眼神
【輯二】 新天堂樂園
黃浦江上
劉莊女兒
夫天下事
姐夫
風雨當年
匱乏年代
我們倆
芭蕉花
鐵凳子
籠中鳥
菩提樹下
城門洞
城牆上
新天堂樂園
那三年
【輯三】 記憶捕手
獎狀
青春年代
水草田
記憶捕手
海明威與蚊子
遺珠
四把火
小秘密
狗不理坡
火成岩
四〇七宿舍
日記夢
剪貼簿
窮故事
送你到彼岸
附錄 天寧寺聞禮懺聲
序二:那一段我們在眷村的青春歲月/張力
自序:尋父圖
【輯一】 以父之名
證書
離家
照片
那把寶劍
黃豆芽
油行
雨衣
坡地上
爺爺
雨中山櫻
旅行
沉默
那碗面
等待公車
南下列車
那兩句話
最後的夏天
永和那個家
陌生的父親
初一旗津
最後的眼神
【輯二】 新天堂樂園
黃浦江上
劉莊女兒
夫天下事
姐夫
風雨當年
匱乏年代
我們倆
芭蕉花
鐵凳子
籠中鳥
菩提樹下
城門洞
城牆上
新天堂樂園
那三年
【輯三】 記憶捕手
獎狀
青春年代
水草田
記憶捕手
海明威與蚊子
遺珠
四把火
小秘密
狗不理坡
火成岩
四〇七宿舍
日記夢
剪貼簿
窮故事
送你到彼岸
附錄 天寧寺聞禮懺聲
文摘
序一:《中時》的味道/許知遠
“千金劍,萬言策,兩蹉跎。醉中呵壁自語,醒後一滂沱。不恨年華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強半為銷磨。願替眾生病,稽首禮維摩。”
我常想起王健壯坐在余紀忠紀念室的沙發上,對著余抄寫這幅字的情景。詞句出自梁啓超的《水調歌頭·甲午》,時年剛過二十歲的心,因甲午之敗而生出強烈的感慨。
梁啓超的情懷影響了幾代中國知識人,激勵他們締造一個現代中國。余紀忠也是其中之一。在隨國民黨政權流亡台北後,他創辦的《中國時報》要繼承的仍是梁的文人辦報的理想,在知識與政治、輿論與權力、個人抱負與家國情懷間尋找某種平衡。
梁啓超也影響了王健壯。一九七七年,在他主編的第三期《仙人掌》雜誌上,他就以梁啓超為封面人物。這與之前的兩期封面人物傅斯年、蔡元培再恰當不過地表現了這個剛剛從台大畢業的青年人對未來的期待——他要用知識與思想來塑造社會。
六十七歲的余紀忠發現了二十四歲的王健壯,並慷慨(或許過分慷慨)給予後者一個機會——擔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主編。考慮到當時“人間副刊”的影響力,這實在是個驚人的決定。在一個政治仍為禁忌的年代,思想、文學常成為另一個突破口,變成集體思潮與情緒的平台,“人間副刊”正是當時台灣社會思想與文化的中心。除了分享偶像梁啓超的個人情懷,王健壯也必定體驗到了少年得志之感。
接下來的三十年中,王健壯的個人命運與《中國時報》乃至台灣新聞業緊密相關。除去梁啓超的情懷與傳統,他也是美國新聞標準的擁躉,一心要把《紐約時報》、《時代》的方式引入華語世界。
他是幸運的。他這一代新聞人親歷,也推動台灣從政治高壓走向自由民主的歷程,這其中,戲劇性的、如火山噴發的變化,為新聞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他與朋友在一九八七年創辦《新新聞》雜誌,試圖創造一種新的報導風格與視角,來描繪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新景象。
他也是不幸的。像很多傑出的台灣知識人一樣,他那梁啓超式的遼闊情懷無處施展。他成熟的過程,也是個台灣逐漸縮小的過程。這個島嶼曾經以整箇中國為志業,承接三皇五帝到老蔣,但在獲得自由的同時,它也在切割自己與那個廣闊傳統的關係。像很多轉型國家與地區一樣,突然到來的自由沒有激起整個社會更深邃的思考能力,反而迅速地瑣碎化。知識與思想的抱負陷入娛樂、淺薄的泥淖。
大約三年前,我在普陀山上的一次會議中認識了王健壯。那次會議由一位有政治情結的香港商人召集,想要討論中國的未來,他也很相信台灣的轉型能提供某種參照。
會議以消防原因被迫取消,讓人想起一九七〇年代的台灣。在酒桌上,我很被王健壯的風度所折服。他似乎有一種我只在書本上看到民國報人的味道,性情、瀟灑、酒量驚人,對後輩有一種特別的慷慨——或許這也是從余先生處所學。
在之後,我們成了朋友。每逢去台北,都不免在小巷的酒館裡推杯、暢談。儘管年齡與成長環境都不同,我們卻像是精神的同代人。除去都對中國知識人的傳統深感興趣外,我們也都是在美國新聞業的影響下成長的,說起《紐約時報》那些傑出的記者時,都有一種特別的興奮。他也講起台灣的轉型過程,他對於政治人物的看法,當然還有《中國時報》的記憶。不過,他始終有一種內斂,不管他顯得多么性情與瀟灑,你也總覺得他和你保持某種距離,不願與你分享他更深的感受與思想。
當他懷舊時,也難免陷入一種灰心與無力。這份曾塑造台灣命運的報紙如今被一個賣米果的商人把持著。余紀忠英俊、端莊的胸像雕塑仍在,但報業大廈的入口早已矗立著巨大的“旺旺”的滑稽塑像,像是一種粗鄙力量對舊傳統的公然挑戰。王健壯曾試圖重塑《中國時報》的氣質,也曾費力在新老闆與舊傳統之間充當調停人,但都陷入一種無力回天之感。這也真是反諷一刻,他們在強烈的中國情懷中成長,如今“中國的影響”真的來了,他們的情懷卻被迫收藏起來。在萬華的那家叫熱海的簡陋餐廳里,我參加了好幾次老時報人的周一聚會,感受到那股日漸濃烈的落沒感。在這個時刻,梁啓超的感慨一定特別的撫慰人心吧。
還是在台北的計程車,我初次讀到這本《我叫他,爺爺》,立刻就被文字的節奏與濃重的個人情緒所吸引。比起他在報紙上那些過分端莊、鏗鏘的政治、社會評論,這些個人回憶無疑更富魅力,它們也完美地解釋了高雄眷村的小孩緣何變成了今天的王健壯。作為大時代的個人,如何被時代所塑造,又如何改變時代?
有時在台北的暗夜分手時,我看著他的黑衣背影逐漸消失時,總不免想起這句:不恨年華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強半為銷磨……
自 序 尋父圖
今年生日收到一件禮物,幾位好友送我一小塊金箔牌匾,上書“看花猶是還歷人”一行字,把陳寅恪的那句詩“看花猶是去年人”改了兩個字;但“還歷”卻讓我觸目驚心。
我從來不曾想到自己也會在天干地支幾番變化之後,走到了還歷之年,變成花甲老翁。六十歲的彼得·潘還能當自由自在飛翔的小飛俠嗎?還能大戰凶暴可怕的虎克船長嗎?想到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就令人沮喪泄氣到了無言以對的程度。彼得·潘可以打敗虎克船長,可他卻是時間老人的手下敗將。
幾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寫過這樣幾段話:
“時間可不可怕?那要看你是用什麼身份去問這個問題。
“就以我自己為例吧。如果我用個人的身份,一個早已年過半百的老翁身份,我當然會告訴你,時間不但可怕,而且是太可怕了。鏡子裡的我,以及我從年輕時就愛的、熟悉的那些人,怎么一個個都被時間摧殘得那么老?那么病?幾個月前才把酒言歡的那個人,怎么會突然變成訃聞里的一個名字?”
這幾段話寫於六年前,回頭逐句再讀,“不獨悲今昔亦悲”,那些我愛過熟悉過的人,六年後老得更多也病得更多,變成訃聞上名字的當然又多了好幾個人。還歷過後那幾天,我日思夜想縈繞不去的儘是那些人那些面孔那些名字。
我做過三十多年新聞記者,看盡不知多少滄桑沉浮悲歡,理應不是也不該是個濫情之人,但對我愛過熟悉過的那些人事時地物,我卻常常連故作太上忘情狀都矯容。那年我在副刊寫了一年專欄,寫我父親,寫眷村我的“永無島”,寫童年記憶,寫文學少年夢,字字句句都沉重如鉛,每篇文章都幽暗陰鬱逼人,寫得我自己常常喘不過氣,讀我文章的人想必更不好受;把自己的悲愁像病菌一樣散播傳染,真是罪不可赦。
但那並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本意只想寫幾篇關於我父親的故事,想念他也紀念他,替他平凡平淡的一生留下一些我能記得的文字記錄,留與世人看。但我手中那支鉛筆卻常常不聽我大腦的指揮,每當我落筆稿紙那一剎那,它就帶著我一行一句一回首,回首重履往昔時空的每個角落,而且此處停格,彼處放大,也都完全由它決定,多少前塵舊夢就像重播的黑白默片一樣,一幕幕掠過來又一幕幕飄過去,讓我簡直難逃於天地之間。
就因為這樣一路筆走人隨,我原想寫幾篇我記得的我父親的故事,結果卻愈寫愈發覺我不記得的其實比記得的更多,寫到後來竟然像在描繪更像在拼貼一幅尋父圖。人子尋父,這是多大的諷刺,多深的愧疚,我也是在那個過程中才悚然警覺:這么多年來不是他從我身邊走失,走失的那個人其實是我,我現在唯一能做的只是在文字的牽引下,一步一步一寸一寸地嘗試再走回他的身邊。
但曾經走失就再也走不回去。我雖然從他出生的江邊小鎮開始,一路尋跡求索,想像他從地主之子到倉皇渡海來台的那三十六年,回憶他跟我父子共處的那四十四年,但想像是模糊的,記憶是斷裂的,那幅尋父圖即使拼到最後,仍然缺這差那不成其形。
就像我曾經寫過的那句話:“我是從他當爺爺這個角色,才些許看到他宛如父親的一面。”他有六個子女,三女三男,一家八口人每天擠在狹窄的眷村房舍里,但因他少言寡笑,六個子女都與他不親,也難怪我母親在好多年後看到他跟他孫子溫馨相處的畫面時,會忍不住抱怨說:“這個老頭子真是偏心,從來不疼自己的小孩,卻偏愛這個孫子。”
德兒出生那年,我奉命調跑台灣省議會新聞,每天人在霧峰,妻子也在學校教書,照顧德兒的諸般瑣事,便由爺爺一手包辦;社區裡的人常常看到一個老人推著嬰兒車在黃昏時散步的畫面。德兒上幼稚園後,我已調回台北租居永和,左鄰右舍也常常看到一個老人牽著穿制服的孫子的手,嬉笑低語走在小巷彎弄間。“帶孫子上學啊!”“放學了啊!”就是他與路上幾個熟識店家老闆每天碰面的例行問候語。德兒至今不愛吃魚,怕刺,因為爺爺常年餵他吃魚時早把魚刺處理掉了;他至今愛吃蘋果,也是因為爺爺當年每天都幫他削切蘋果;他愛隨手關燈,那也是爺爺的習慣。我在我兒子身上偶爾不經意看到我父親的身影時,常常會心中一驚:那不是隔代遺傳;他是爺爺,卻宛如父親,是我在眷村十八年跟他朝夕相處卻不曾認識並感受到的那個父親;我跟我父親是透過德兒這個媒介,才稍稍彌補了我們彼此之間曾經欠缺的那段父子情。
他跟我在台北同住的那十八年,每一刻其實我都清楚知道,當我喊他“爺爺”時,比我叫他“老爸”時,我跟他之間的距離要更近也更親。當然,在他離開我十二年後,我終於鼓足勇氣提筆寫他故事的那整整一年,我才從一小塊一小塊的記憶拼圖中,逐漸地拼貼出他的圖像;五十篇故事其實敘述刻畫的是一幅尋父圖,穿梭時空,尋尋覓覓,但結果那幅圖像仍然殘缺未完成,只能算是一本人子懺悔錄吧!
這本書獻給我的母親,到現在她還是一個人比花嬌的老太太;也感謝我兒子,他在鍵盤上一字一句一篇敲打他爺爺的故事時,一定比我更懷念那個呵護他牽著他手走過不知多少巷弄的老人,那個我們都叫他“爺爺”的老人。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寫於父後十五年
“千金劍,萬言策,兩蹉跎。醉中呵壁自語,醒後一滂沱。不恨年華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強半為銷磨。願替眾生病,稽首禮維摩。”
我常想起王健壯坐在余紀忠紀念室的沙發上,對著余抄寫這幅字的情景。詞句出自梁啓超的《水調歌頭·甲午》,時年剛過二十歲的心,因甲午之敗而生出強烈的感慨。
梁啓超的情懷影響了幾代中國知識人,激勵他們締造一個現代中國。余紀忠也是其中之一。在隨國民黨政權流亡台北後,他創辦的《中國時報》要繼承的仍是梁的文人辦報的理想,在知識與政治、輿論與權力、個人抱負與家國情懷間尋找某種平衡。
梁啓超也影響了王健壯。一九七七年,在他主編的第三期《仙人掌》雜誌上,他就以梁啓超為封面人物。這與之前的兩期封面人物傅斯年、蔡元培再恰當不過地表現了這個剛剛從台大畢業的青年人對未來的期待——他要用知識與思想來塑造社會。
六十七歲的余紀忠發現了二十四歲的王健壯,並慷慨(或許過分慷慨)給予後者一個機會——擔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主編。考慮到當時“人間副刊”的影響力,這實在是個驚人的決定。在一個政治仍為禁忌的年代,思想、文學常成為另一個突破口,變成集體思潮與情緒的平台,“人間副刊”正是當時台灣社會思想與文化的中心。除了分享偶像梁啓超的個人情懷,王健壯也必定體驗到了少年得志之感。
接下來的三十年中,王健壯的個人命運與《中國時報》乃至台灣新聞業緊密相關。除去梁啓超的情懷與傳統,他也是美國新聞標準的擁躉,一心要把《紐約時報》、《時代》的方式引入華語世界。
他是幸運的。他這一代新聞人親歷,也推動台灣從政治高壓走向自由民主的歷程,這其中,戲劇性的、如火山噴發的變化,為新聞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他與朋友在一九八七年創辦《新新聞》雜誌,試圖創造一種新的報導風格與視角,來描繪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新景象。
他也是不幸的。像很多傑出的台灣知識人一樣,他那梁啓超式的遼闊情懷無處施展。他成熟的過程,也是個台灣逐漸縮小的過程。這個島嶼曾經以整箇中國為志業,承接三皇五帝到老蔣,但在獲得自由的同時,它也在切割自己與那個廣闊傳統的關係。像很多轉型國家與地區一樣,突然到來的自由沒有激起整個社會更深邃的思考能力,反而迅速地瑣碎化。知識與思想的抱負陷入娛樂、淺薄的泥淖。
大約三年前,我在普陀山上的一次會議中認識了王健壯。那次會議由一位有政治情結的香港商人召集,想要討論中國的未來,他也很相信台灣的轉型能提供某種參照。
會議以消防原因被迫取消,讓人想起一九七〇年代的台灣。在酒桌上,我很被王健壯的風度所折服。他似乎有一種我只在書本上看到民國報人的味道,性情、瀟灑、酒量驚人,對後輩有一種特別的慷慨——或許這也是從余先生處所學。
在之後,我們成了朋友。每逢去台北,都不免在小巷的酒館裡推杯、暢談。儘管年齡與成長環境都不同,我們卻像是精神的同代人。除去都對中國知識人的傳統深感興趣外,我們也都是在美國新聞業的影響下成長的,說起《紐約時報》那些傑出的記者時,都有一種特別的興奮。他也講起台灣的轉型過程,他對於政治人物的看法,當然還有《中國時報》的記憶。不過,他始終有一種內斂,不管他顯得多么性情與瀟灑,你也總覺得他和你保持某種距離,不願與你分享他更深的感受與思想。
當他懷舊時,也難免陷入一種灰心與無力。這份曾塑造台灣命運的報紙如今被一個賣米果的商人把持著。余紀忠英俊、端莊的胸像雕塑仍在,但報業大廈的入口早已矗立著巨大的“旺旺”的滑稽塑像,像是一種粗鄙力量對舊傳統的公然挑戰。王健壯曾試圖重塑《中國時報》的氣質,也曾費力在新老闆與舊傳統之間充當調停人,但都陷入一種無力回天之感。這也真是反諷一刻,他們在強烈的中國情懷中成長,如今“中國的影響”真的來了,他們的情懷卻被迫收藏起來。在萬華的那家叫熱海的簡陋餐廳里,我參加了好幾次老時報人的周一聚會,感受到那股日漸濃烈的落沒感。在這個時刻,梁啓超的感慨一定特別的撫慰人心吧。
還是在台北的計程車,我初次讀到這本《我叫他,爺爺》,立刻就被文字的節奏與濃重的個人情緒所吸引。比起他在報紙上那些過分端莊、鏗鏘的政治、社會評論,這些個人回憶無疑更富魅力,它們也完美地解釋了高雄眷村的小孩緣何變成了今天的王健壯。作為大時代的個人,如何被時代所塑造,又如何改變時代?
有時在台北的暗夜分手時,我看著他的黑衣背影逐漸消失時,總不免想起這句:不恨年華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強半為銷磨……
自 序 尋父圖
今年生日收到一件禮物,幾位好友送我一小塊金箔牌匾,上書“看花猶是還歷人”一行字,把陳寅恪的那句詩“看花猶是去年人”改了兩個字;但“還歷”卻讓我觸目驚心。
我從來不曾想到自己也會在天干地支幾番變化之後,走到了還歷之年,變成花甲老翁。六十歲的彼得·潘還能當自由自在飛翔的小飛俠嗎?還能大戰凶暴可怕的虎克船長嗎?想到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就令人沮喪泄氣到了無言以對的程度。彼得·潘可以打敗虎克船長,可他卻是時間老人的手下敗將。
幾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寫過這樣幾段話:
“時間可不可怕?那要看你是用什麼身份去問這個問題。
“就以我自己為例吧。如果我用個人的身份,一個早已年過半百的老翁身份,我當然會告訴你,時間不但可怕,而且是太可怕了。鏡子裡的我,以及我從年輕時就愛的、熟悉的那些人,怎么一個個都被時間摧殘得那么老?那么病?幾個月前才把酒言歡的那個人,怎么會突然變成訃聞里的一個名字?”
這幾段話寫於六年前,回頭逐句再讀,“不獨悲今昔亦悲”,那些我愛過熟悉過的人,六年後老得更多也病得更多,變成訃聞上名字的當然又多了好幾個人。還歷過後那幾天,我日思夜想縈繞不去的儘是那些人那些面孔那些名字。
我做過三十多年新聞記者,看盡不知多少滄桑沉浮悲歡,理應不是也不該是個濫情之人,但對我愛過熟悉過的那些人事時地物,我卻常常連故作太上忘情狀都矯容。那年我在副刊寫了一年專欄,寫我父親,寫眷村我的“永無島”,寫童年記憶,寫文學少年夢,字字句句都沉重如鉛,每篇文章都幽暗陰鬱逼人,寫得我自己常常喘不過氣,讀我文章的人想必更不好受;把自己的悲愁像病菌一樣散播傳染,真是罪不可赦。
但那並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本意只想寫幾篇關於我父親的故事,想念他也紀念他,替他平凡平淡的一生留下一些我能記得的文字記錄,留與世人看。但我手中那支鉛筆卻常常不聽我大腦的指揮,每當我落筆稿紙那一剎那,它就帶著我一行一句一回首,回首重履往昔時空的每個角落,而且此處停格,彼處放大,也都完全由它決定,多少前塵舊夢就像重播的黑白默片一樣,一幕幕掠過來又一幕幕飄過去,讓我簡直難逃於天地之間。
就因為這樣一路筆走人隨,我原想寫幾篇我記得的我父親的故事,結果卻愈寫愈發覺我不記得的其實比記得的更多,寫到後來竟然像在描繪更像在拼貼一幅尋父圖。人子尋父,這是多大的諷刺,多深的愧疚,我也是在那個過程中才悚然警覺:這么多年來不是他從我身邊走失,走失的那個人其實是我,我現在唯一能做的只是在文字的牽引下,一步一步一寸一寸地嘗試再走回他的身邊。
但曾經走失就再也走不回去。我雖然從他出生的江邊小鎮開始,一路尋跡求索,想像他從地主之子到倉皇渡海來台的那三十六年,回憶他跟我父子共處的那四十四年,但想像是模糊的,記憶是斷裂的,那幅尋父圖即使拼到最後,仍然缺這差那不成其形。
就像我曾經寫過的那句話:“我是從他當爺爺這個角色,才些許看到他宛如父親的一面。”他有六個子女,三女三男,一家八口人每天擠在狹窄的眷村房舍里,但因他少言寡笑,六個子女都與他不親,也難怪我母親在好多年後看到他跟他孫子溫馨相處的畫面時,會忍不住抱怨說:“這個老頭子真是偏心,從來不疼自己的小孩,卻偏愛這個孫子。”
德兒出生那年,我奉命調跑台灣省議會新聞,每天人在霧峰,妻子也在學校教書,照顧德兒的諸般瑣事,便由爺爺一手包辦;社區裡的人常常看到一個老人推著嬰兒車在黃昏時散步的畫面。德兒上幼稚園後,我已調回台北租居永和,左鄰右舍也常常看到一個老人牽著穿制服的孫子的手,嬉笑低語走在小巷彎弄間。“帶孫子上學啊!”“放學了啊!”就是他與路上幾個熟識店家老闆每天碰面的例行問候語。德兒至今不愛吃魚,怕刺,因為爺爺常年餵他吃魚時早把魚刺處理掉了;他至今愛吃蘋果,也是因為爺爺當年每天都幫他削切蘋果;他愛隨手關燈,那也是爺爺的習慣。我在我兒子身上偶爾不經意看到我父親的身影時,常常會心中一驚:那不是隔代遺傳;他是爺爺,卻宛如父親,是我在眷村十八年跟他朝夕相處卻不曾認識並感受到的那個父親;我跟我父親是透過德兒這個媒介,才稍稍彌補了我們彼此之間曾經欠缺的那段父子情。
他跟我在台北同住的那十八年,每一刻其實我都清楚知道,當我喊他“爺爺”時,比我叫他“老爸”時,我跟他之間的距離要更近也更親。當然,在他離開我十二年後,我終於鼓足勇氣提筆寫他故事的那整整一年,我才從一小塊一小塊的記憶拼圖中,逐漸地拼貼出他的圖像;五十篇故事其實敘述刻畫的是一幅尋父圖,穿梭時空,尋尋覓覓,但結果那幅圖像仍然殘缺未完成,只能算是一本人子懺悔錄吧!
這本書獻給我的母親,到現在她還是一個人比花嬌的老太太;也感謝我兒子,他在鍵盤上一字一句一篇敲打他爺爺的故事時,一定比我更懷念那個呵護他牽著他手走過不知多少巷弄的老人,那個我們都叫他“爺爺”的老人。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寫於父後十五年
序言
序一
《中時》的味道
許知遠
“千金劍,萬言策,兩蹉跎。醉中呵壁自語,醒後一滂沱。不恨年華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強半為銷磨。願替眾生病,稽首禮維摩。”
我常想起王健壯坐在余紀忠紀念室的沙發上,對著余抄寫這幅字的情景。詞句出自梁啓超的《水調歌頭·甲午》,時年剛過二十歲的心,因甲午之敗而生出強烈的感慨。
梁啓超的情懷影響了幾代中國知識人,激勵他們締造一個現代中國。余紀忠也是其中之一。在隨國民黨政權流亡台北後,他創辦的《中國時報》要繼承的仍是梁的文人辦報的理想,在知識與政治、輿論與權力、個人抱負與家國情懷間尋找某種平衡。
梁啓超也影響了王健壯。一九七七年,在他主編的第三期《仙人掌》雜誌上,他就以梁啓超為封面人物。這與之前的兩期封面人物傅斯年、蔡元培再恰當不過地表現了這個剛剛從台大畢業的青年人對未來的期待——他要用知識與思想來塑造社會。
六十七歲的余紀忠發現了二十四歲的王健壯,並慷慨(或許過分慷慨)給予後者一個機會——擔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主編。考慮到當時“人間副刊”的影響力,這實在是個驚人的決定。在一個政治仍為禁忌的年代,思想、文學常成為另一個突破口,變成集體思潮與情緒的平台,“人間副刊”正是當時台灣社會思想與文化的中心。除了分享偶像梁啓超的個人情懷,王健壯也必定體驗到了少年得志之感。
接下來的三十年中,王健壯的個人命運與《中國時報》乃至台灣新聞業緊密相關。除去梁啓超的情懷與傳統,他也是美國新聞標準的擁躉,一心要把《紐約時報》、《時代》的方式引入華語世界。
他是幸運的。他這一代新聞人親歷,也推動台灣從政治高壓走向自由民主的歷程,這其中,戲劇性的、如火山噴發的變化,為新聞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他與朋友在一九八七年創辦《新新聞》雜誌,試圖創造一種新的報導風格與視角,來描繪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新景象。
他也是不幸的。像很多傑出的台灣知識人一樣,他那梁啓超式的遼闊情懷無處施展。他成熟的過程,也是個台灣逐漸縮小的過程。這個島嶼曾經以整箇中國為志業,承接三皇五帝到老蔣,但在獲得自由的同時,它也在切割自己與那個廣闊傳統的關係。像很多轉型國家與地區一樣,突然到來的自由沒有激起整個社會更深邃的思考能力,反而迅速地瑣碎化。知識與思想的抱負陷入娛樂、淺薄的泥淖。
大約三年前,我在普陀山上的一次會議中認識了王健壯。那次會議由一位有政治情結的香港商人召集,想要討論中國的未來,他也很相信台灣的轉型能提供某種參照。 會議以消防原因被迫取消,讓人想起一九七。年代的台灣。在酒桌上,我很被王健壯的風度所折服。他似乎有一種我只在書本上看到民國報人的味道,性情、瀟灑、酒量驚人,對後輩有一種特別的慷慨——或許這也是從余先生處所學。
在之後,我們成了朋友。每逢去台北,都不免在小巷的酒館裡推杯、暢談。儘管年齡與成長環境都不同,我們卻像是精神的同代人。除去都對中國知識人的傳統深感興趣外,我們也都是在美國新聞業的影響下成長的,說起《紐約時報》那些傑出的記者時,都有一種特別的興奮。他也講起台灣的轉型過程,他對於政治人物的看法,當然還有《中國時報》的記憶。不過,他始終有一種內斂,不管他顯得多么性情與瀟灑,你也總覺得他和你保持某種距離,不願與你分享他更深的感受與思想。
當他懷舊時,也難免陷入一種灰心與無力。這份曾塑造台灣命運的報紙如今被一個賣米果的商人把持著。余紀忠英俊、端莊的胸像雕塑仍在,但報業大廈的入口早已矗立著巨大的“旺旺”的滑稽塑像,像是一種粗鄙力量對舊傳統的公然挑戰。王健壯曾試圖重塑《中國時報》的氣質,也曾費力在新老闆與舊傳統之間充當調停人,但都陷入一種無力回天之感。這也真是反諷一刻,他們在強烈的中國情懷中成長,如今‘‘中國的影響”真的來了,他們的情懷卻被迫收藏起來。在萬華的那家叫熱海的簡陋餐廳里,我參加了好幾次老時報人的周一聚會,感受到那股日漸濃烈的落沒感。在這個時刻,梁啓超的感慨一定特別的撫慰人心吧。
還是在台北的計程車,我初次讀到這本《我叫他,爺爺》,立刻就被文字的節奏與濃重的個人情緒所吸引。比起他在報紙上那些過分端莊、鏗鏘的政治、社會評論,這些個人回憶無疑更富魅力,它們也完美地解釋了高雄眷村的小孩緣何變成了今天的王健壯。作為大時代的個人,如何被時代所塑造,又如何改變時代?
有時在台北的暗夜分手時,我看著他的黑衣背影逐漸消失時,總不免想起這句:不恨年華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強半為銷磨……
《中時》的味道
許知遠
“千金劍,萬言策,兩蹉跎。醉中呵壁自語,醒後一滂沱。不恨年華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強半為銷磨。願替眾生病,稽首禮維摩。”
我常想起王健壯坐在余紀忠紀念室的沙發上,對著余抄寫這幅字的情景。詞句出自梁啓超的《水調歌頭·甲午》,時年剛過二十歲的心,因甲午之敗而生出強烈的感慨。
梁啓超的情懷影響了幾代中國知識人,激勵他們締造一個現代中國。余紀忠也是其中之一。在隨國民黨政權流亡台北後,他創辦的《中國時報》要繼承的仍是梁的文人辦報的理想,在知識與政治、輿論與權力、個人抱負與家國情懷間尋找某種平衡。
梁啓超也影響了王健壯。一九七七年,在他主編的第三期《仙人掌》雜誌上,他就以梁啓超為封面人物。這與之前的兩期封面人物傅斯年、蔡元培再恰當不過地表現了這個剛剛從台大畢業的青年人對未來的期待——他要用知識與思想來塑造社會。
六十七歲的余紀忠發現了二十四歲的王健壯,並慷慨(或許過分慷慨)給予後者一個機會——擔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主編。考慮到當時“人間副刊”的影響力,這實在是個驚人的決定。在一個政治仍為禁忌的年代,思想、文學常成為另一個突破口,變成集體思潮與情緒的平台,“人間副刊”正是當時台灣社會思想與文化的中心。除了分享偶像梁啓超的個人情懷,王健壯也必定體驗到了少年得志之感。
接下來的三十年中,王健壯的個人命運與《中國時報》乃至台灣新聞業緊密相關。除去梁啓超的情懷與傳統,他也是美國新聞標準的擁躉,一心要把《紐約時報》、《時代》的方式引入華語世界。
他是幸運的。他這一代新聞人親歷,也推動台灣從政治高壓走向自由民主的歷程,這其中,戲劇性的、如火山噴發的變化,為新聞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他與朋友在一九八七年創辦《新新聞》雜誌,試圖創造一種新的報導風格與視角,來描繪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新景象。
他也是不幸的。像很多傑出的台灣知識人一樣,他那梁啓超式的遼闊情懷無處施展。他成熟的過程,也是個台灣逐漸縮小的過程。這個島嶼曾經以整箇中國為志業,承接三皇五帝到老蔣,但在獲得自由的同時,它也在切割自己與那個廣闊傳統的關係。像很多轉型國家與地區一樣,突然到來的自由沒有激起整個社會更深邃的思考能力,反而迅速地瑣碎化。知識與思想的抱負陷入娛樂、淺薄的泥淖。
大約三年前,我在普陀山上的一次會議中認識了王健壯。那次會議由一位有政治情結的香港商人召集,想要討論中國的未來,他也很相信台灣的轉型能提供某種參照。 會議以消防原因被迫取消,讓人想起一九七。年代的台灣。在酒桌上,我很被王健壯的風度所折服。他似乎有一種我只在書本上看到民國報人的味道,性情、瀟灑、酒量驚人,對後輩有一種特別的慷慨——或許這也是從余先生處所學。
在之後,我們成了朋友。每逢去台北,都不免在小巷的酒館裡推杯、暢談。儘管年齡與成長環境都不同,我們卻像是精神的同代人。除去都對中國知識人的傳統深感興趣外,我們也都是在美國新聞業的影響下成長的,說起《紐約時報》那些傑出的記者時,都有一種特別的興奮。他也講起台灣的轉型過程,他對於政治人物的看法,當然還有《中國時報》的記憶。不過,他始終有一種內斂,不管他顯得多么性情與瀟灑,你也總覺得他和你保持某種距離,不願與你分享他更深的感受與思想。
當他懷舊時,也難免陷入一種灰心與無力。這份曾塑造台灣命運的報紙如今被一個賣米果的商人把持著。余紀忠英俊、端莊的胸像雕塑仍在,但報業大廈的入口早已矗立著巨大的“旺旺”的滑稽塑像,像是一種粗鄙力量對舊傳統的公然挑戰。王健壯曾試圖重塑《中國時報》的氣質,也曾費力在新老闆與舊傳統之間充當調停人,但都陷入一種無力回天之感。這也真是反諷一刻,他們在強烈的中國情懷中成長,如今‘‘中國的影響”真的來了,他們的情懷卻被迫收藏起來。在萬華的那家叫熱海的簡陋餐廳里,我參加了好幾次老時報人的周一聚會,感受到那股日漸濃烈的落沒感。在這個時刻,梁啓超的感慨一定特別的撫慰人心吧。
還是在台北的計程車,我初次讀到這本《我叫他,爺爺》,立刻就被文字的節奏與濃重的個人情緒所吸引。比起他在報紙上那些過分端莊、鏗鏘的政治、社會評論,這些個人回憶無疑更富魅力,它們也完美地解釋了高雄眷村的小孩緣何變成了今天的王健壯。作為大時代的個人,如何被時代所塑造,又如何改變時代?
有時在台北的暗夜分手時,我看著他的黑衣背影逐漸消失時,總不免想起這句:不恨年華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強半為銷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