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02年10月7日,生於台北縣
板橋鎮,原名張清榮。1914年,板橋公學校畢業。
 評價張我軍的作品-《近觀張我軍》
評價張我軍的作品-《近觀張我軍》1916年,經林木土介紹,入新高銀行當工友。
1918年,升任新高銀行雇員。
1921年,由新高銀行調往廈門分行。
1922年,因父親去世,回台奔喪。
1923年,新高應行結束營業,初冬由廈門搭船到上海尋找新的工作。
1924年,加入“上海台灣青年會”,一月十二日,出席該會召開的“上海台灣人大會”。後由上海轉赴北京。
1924年3月25日,在北京寫下第一首新詩《沉寂》。
1924年4月21日,短評《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發表於《台灣民報》二卷七號。
1924年5月11日,新詩《對月狂歌》發表於《台灣民報》二卷八號。
1924年7月11日,新詩《無情的雨》發表於《台灣民報》二卷十三號。
1924年8月16日,新詩《游中央公園雜誌》(共六首)發表於《北京晨報》副刊
1924年10月14日,新詩《煩悶》發表於《北京晨報》副刊。
1924年10月下旬,回到台灣,擔任《台灣民報》編輯。
1924年11月21日,短評《糟糕的台灣文學界》發表於,《台灣民報》二卷二十四號
1924年12月1日,短評《駁稻江建醮與政府和三新聞的態度》於《台灣民報》二卷二十五號。
1924年12月11日,短評《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歡送韋博士》發表於《台灣民報》二卷二十六號。
1924年12月28日,詩集《亂都之戀》自費在台北出版印行。
1925年,加入
蔣渭水、楊朝華、翁澤生、鄭石蛋等人發起的“台北青年體育會”與“台北青年讀書會”。
1925年1月1日,短評《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櫼中的破舊殿堂》發表於《台灣民報》三卷一號。
1925年1月11日,短論《絕無僅有的擊缽吟的意義》發表於《台灣民報》三卷二號。
1925年1月21日,短評《揭破悶葫蘆》、《田川先生與台灣議會》發表於《台灣民報》三卷三號。
1925年2月1日,短論《聘金廢止的根本解決辦法》發表於《台灣民報》三卷四號。
1925年2月21日,短評《復鄭軍我書》、短論《文學革命運動以來》發表於《台灣民報》三卷六號。
1925年3月1號,短論《詩體的解放》、雜感《研究新文學應該讀什麼書》、新詩《煩悶》發表於《台灣民報》三卷七號。
1925年4月1號,短論《生命在,什麼事都做不成?》發表於《台灣民報》三卷十號。
1925年4月21日,雜感《隨感錄》發表於《台灣民報》三卷十二號。
1925年6月,後記《“親愛的姊妹們押分歧努力”後記》發表於《台灣民報》第六十七號。
1925年7月19日,新詩《弱者的悲鳴》發表於《台灣民報》第六十一號。
1925年8月26日,短論《新文學運動的意義》發表於《台灣民報》第六十一號。
1925年9月1日,與羅文淑(後改名心鄉)在台北江山樓結婚,證婚人林獻堂、介紹人王敏川。
1925年10月18日,短論《至上最高道德——戀愛》發表於《台灣民報》第七十五號。
1925年10月25日,短論《中國國語文做法導言》發表於《台灣民報》第七十六號。
1925年11月至1926年1月,論文《文藝上的諸主意》發表於《台灣民報》第七十七、七十八、八十一、八十三、八十七、八十九號。
1926年12月13日,雜感《看了警察展覽會之後》發表於《台灣民報》第八十三號。1926年12月27日,序文《“亂都之戀”的序文》發表於《台灣民報》第八十五號。
 張我軍的二子張光直(青年時代帥照)
張我軍的二子張光直(青年時代帥照)1926年1月,短論《危哉台灣的前途》發表於《台灣民報》第九十至九十六號。
1926年6月,張我軍夫婦再度前往北京,準備求學深造。
1926年7月25日,雜感《“弱小民族的悲哀”的譯者附記》發表於《台灣民報》第105—115號
1926年8月11日,拜訪魯迅寓所,贈送四本剛出版的《台灣民報》(第113—116號)
1926年9月,考入北京私立中國大學國學系,就讀一年。
1926年9月19日,小說《買彩票》發表於《台灣民報》第123—125號。
1927年3月,與蘇維霖、洪炎秋、宋斐如、吳敦禮等人共同創辦《少年台灣》
19275月1日,小說《白太太的哀史》發表於《台灣民報》第150—55號。
192710月,以日該國學院大學高等師範科畢業之學歷,插班轉入北師大國文系三年級肄業。
1929年4月7日,小說《誘惑》發表於《台灣民報》第255—258號。
1930年,自北師大畢業,與何秉彝、葉鳳梧、俞安斌等人籌組文學社團“星星社”,後易名“新野社”。
1930年9月15日,《新野月刊》創刊,僅一期。
1931年,被北師大延攬為日文講師,後又在北平、中國兩大學兼教日文。
1932年,《日本語法十二講》、《日語基礎漢本》由北京人文書店出版。
1934年,《高級日文進修叢書》、《現代日本語法大全》由北京人文書店出版。
1935年,《日語基礎讀本自修教授參考書》、《高級日文星期講座》由北京人文書店出版。
1936年11月上旬,擔任北平社會局秘書。
1936年,《日文自修講座》由北京人文書店出版。
1939年,《日語模範讀本》由北京人文書店出版。
1939年9月,散文《秋在古都》、雜文《關於“中國文藝”的出現及其它》、《京劇偶談》、《代皰者語及編後記》、《評菊池寬的“日本文學案內”》,發表於《中國文藝》創刊號至一卷三期。
1940年,短評《須多發表與民眾生活有密切關係的作品》發表於《中國文藝》一卷五期。
1940年,雜文《病房雜技》發表於《中國文藝》二卷一期至三期。
1942年,由北平前往東京參加由“日本文學報國會”主辦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1942年,短論《日本文學介紹與翻譯》發表於《中國文學》創刊號。
1942年,《關於島崎藤村》發表於《日本研究》一卷二期。
1943年8月25日,自北平參加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1943年,短論《日本文化的再認識》發表於《日本研究》二卷二期。
1943年,《武者小路寶篤印象記》發表於《雜文》一卷二期。
1943年,《關於德田秋聲》發表於《藝文》三卷一期。
1945年8月,旅平台灣同胞組織“北平台灣同鄉會”,張我軍擔任一個服務隊隊長,協助台胞返鄉。
1946年夏秋間,攜眷返台
1946年7月1日,擔任“台灣省教育會”編纂組主任。
1948年春,回台北擔任“台灣省茶業商業同業公會”秘書,主編《台灣茶業》季刊,雜感《採茶風景偶寫》即發表於該刊第一期。
1949年8月,擔任“台灣省合作金庫”業務部專員。
1949年12月,調研究室專員,主編《合作界》季刊,雜感《山歌十首》、《在台島西北角看採茶比賽後記》、《埔里之行》發表於該刊第二、三期。
1952年,雜感《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禮雜筆》發表於《合作界》第三號。
1955年11月3日,因肝癌逝世於寓所,享年五十三歲。
1925年考入北平中國大學文學系,次年轉入
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曾任北京師大、
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等院校教師。台灣光復後返台灣,先後任茶葉公會秘書、金庫研究室主任。1925年,他的新詩集《亂都之戀》在台灣出版,是台灣第一部新詩集。1926年始陸續發表小說《買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誘惑》。作品有力地揭露與批判了黑暗時代,不僅開創了台灣新詩創作的現實主義傳統,也拓寬了早期台灣小說創作視野與領域。張我軍是台灣文學發難期的總先鋒,被喻為“台灣的
胡適”。
張我軍1902年生於台灣台北
板橋鎮(現板橋巿)一個佃戶家庭,祖籍福建
漳州南靖。少時家貧,1916年學習製鞋,1918年任新高銀行工友、雇員,1920年隨前清秀才趙一山讀書學漢詩。1921年,他前往中國廈門鼓浪嶼新高銀行謀職,因此接觸中國白話文文學,他一方面赴廈門同文書院接受中國新式教育,接觸中國白話文文學,同時也跟著一位當地的老秀才接續古典文學的學習;在泰賢次的考察中,張我軍正是在此時將原名張清榮改為張我軍,而“我軍”正是這位老秀才的筆名,張我軍經由老秀才的推薦,在文社當文書,專事記錄文社同人吟唱的詩文、互相品評的文字,對於古典文學的學習精進更易,在1920年代發表的二首古典詩《寄懷台灣議會請願諸公》、《詠時事》(均刊在《台灣》雜誌),都是這個時期的作品。1923年7月,新高銀行結束營業,被遣散,年末自廈門乘船至上海,參加台灣留學生反日組織“上海台灣青年會”。1924年1月赴北京求學,1924年3月寫第1首新詩《沉寂》送給未來夫人羅心鄉,1925年1月1日擔任《台灣民報》編輯,加入蔣渭水、翁澤生成立的“台北青年體育會”與“台北青年讀書會”,1926年6月偕夫人自台灣到北京,9月考入北京私立中國大學國文系。1927年10月,他以自學資歷,插班轉入國立北京師範大學(北師大)國學系;被推為“北京台灣青年會”主席,與
洪炎秋、蘇維霖等創辦《少年台灣》,出刊9期。1928年參加北師大國文系文學團體“新野社”,1929年留校任日文講師,且於
北京大學兼課。
1927年,張我軍與北京大學台灣學生
宋斐如(原名宋文瑞)創辦《少年台灣》雜誌,由宋文瑞主編,張我軍執筆,共出刊819期,並於同年插班轉入國立
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1927年於北平
察院胡同自宅開設日文補習班,並先後在北平師範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北京大學法學院以及中國大學任教,任職日文講師。1935年任北平市社會局秘書,為北平市長泰德純辦理對日交涉事宜。
張我軍在北京時受到
周作人許多指導和提攜,周作人親自給他的日本文學譯作寫序(序文收進周的文集)。1937年相繼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王克敏傀儡政權統轄的
北京大學文學院日本文學系,北京大學工學院、外國語學院文學系擔任教授,並於1942及1943年以中國華北作家代表身分往東京參加第一、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戰後曾被質疑為漢奸。他後來申辯,他是台灣人,所以是日該國民,這不能叫漢奸,最終被國民黨政府免以追究問罪。1946年初應邀到北平與上海與人合作經商,6月返台並任職於台灣省教育編纂匯會教育組主任,1948年主編《台灣茶葉》季刊,1949年應謝東閔之邀任台灣省合作金庫業務部專員,後任合作金庫研究室主任並編撰《日華字典》,1950年主編《合作界》季刊。但因赴台後懷才不遇,鬱鬱寡歡,整天以酒澆愁,加上菸癮極大,結果患上肝癌,1955年因罹患肝癌退休,同年11月3日病逝於台北市。
張我軍自1955年逝世後,其文學貢獻20年來在
台灣島上竟毫無聲息,被人冷落。直到上世紀70年代,台灣的一些文化工作者,為倡導鄉土文學,反駁台灣當局推行文化專制,抹殺台灣本土文學早已存在的事實,張我軍和其他一些台灣老作家的作品,才像“出土文物”似的重返人間。
1997年,台北縣政府“為鄉里人傑塑像”,在其母校板橋國小立張我軍石像,表彰他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貢獻。
2006年5月4日,台灣國民黨黨史館舉行“五四新文化運動紀念活動”,在黨部大廳展出“五四名人書札”,並在風水牆懸掛五四名人
胡適、張我軍的巨幅照片。
五四運動爆發時,張我軍在廈門
鼓浪嶼高新銀行工作,由於受到祖國新文學、新思潮影響,眼界頓時大開。1922年到北平求學,他認識了同班同學羅心鄉,並與之相戀,但遭到封建家庭的阻撓。經過北平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後的張我軍,為此痛感摧毀舊制度、舊思想、舊文化的必要。1924年10月,他回到台灣任《
台灣民報》漢文編輯。他以筆為武器,開始了對舊文學、舊道德的討伐。由此引發了一場新舊文學的論戰,為新文學的誕生和發展掃除了障礙,因而獲得了文壇“清道夫”的美稱。他陸續在《台灣民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抨擊當時依附於殖民當局,維護封建傳統,專寫古體漢詩,酬唱成風的舊文學界。他揭開舊文學的面罩,層層剝批舊詩界帶來的種種危害和弊端,認為最嚴重的毒害是讓青年養成了“偷懶好名的惡習”,因此他向青年發出警告:“諸君若長此以往,後來觸於突發的事,或是激於義氣,想出來協力改造社會也就無從改造了。”顯然,張我軍對新文學的鼎力提倡,是基於對台灣社會命運的深刻關注。當然,這種對舊文學全盤否定的做法未免失之偏頗。但矯枉有時必須過正,張我軍以摧枯拉朽之勢加速了基本上淪為殖民者強權附庸的舊文學的滅亡,從而為新文學的登場鋪平了道路。
在批判、摧毀舊文學的過程中,張我軍也著手新的文學理論的建設。在《文學革命運動以來》、《詩體的解放》、《新文學運動的意義》、《文藝上的諸主義》等文章中,他對新文學運動的一系列問題如:台灣新文學的屬性,文學的內容與形式,語言建設,東西文化的關係等作了比較深入和細緻的闡述。他的主張緊密地結合台灣文壇的實際,著力解決具體問題,從而使新文學理論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推動了台灣新文學創作的發生與發展。
台灣第一位白話詩人張我軍1924年3月25日於第一首新詩《沉寂》寫到:“在這十丈風塵的京華,當這大好的春光里,一個T島的青年,在戀他的故鄉!在想他的愛人!他的故鄉在千里之外,他常在更深夜靜之後,對著月亮兒興嘆!他的愛人又不知在哪裡,他常在寂寞無聊之時,詛咒那司愛的神!”
對張我軍來說,“亂都”是日軍鐵蹄下的北京城,而詩人心中戀人的所在地,是遙遠的故鄉台灣島。
文學運動
“五四”運動以後,台灣文藝界受祖國大陸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面貌為之一新。20年代,以張我軍、
賴和為代表的一批知名作家,大力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他們結成團體,用白話文創作了許多新文學作品,產生了很大影響。台灣新文學發難期的張我軍,在北京求學,身受五四運動的洗禮,於1924年9月寄回《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發表在《台灣民報》2卷7期上。呼籲台灣青年以“團結、毅力、犧牲”為武器改造台灣的舊文化。同年11月,張我軍又在《台灣民報》2卷24期發表《糟糕的台灣文學界》,介紹師姐文學的發展趨勢,呼籲台灣把“陳腐頹喪的文學界洗刷一新”;針對台灣文界的擊缽吟,抨擊舊詩人如守墓之犬,在那時守著幾百年以前的古典主義之墓。張我軍對舊文壇的尖銳抨擊,擊中了舊文學的要害,也打響了新舊文學論戰的第一槍,一場新舊文學論戰不可避免的到來了。
張我軍就學和教書的北京師範大學
面對舊詩人連雅堂對新文學的發難,張我軍連發三篇文章:《為台灣文學界一哭》、《請合理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絕無僅有的擊缽吟的意義》,嬉笑怒罵,如匕首投槍,將台灣舊文學陣營攪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他以決絕的姿態表示,為要“從根本上掃除清掃”“台灣的文學”,他願“站在文學道上當個
清道夫”。
在新舊文學論戰中,再次掀起了介紹中國新文學的熱潮。張我軍在《台灣民報》第3卷6期上發表了《文學革命運動以來》一文,介紹五四新文學革命,並將胡適《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一節全文轉載。張我軍將內地的優秀作品、理論介紹到台灣。他對台灣的新文學作了定向和定位。他較為準確的闡釋了台灣新文學與祖國內地文學之間的血緣關係:“台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的什麼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隨之影響、變遷,這是必然的道理”。
張我軍始終反對運用方言於白話文寫作,曾指出:“我們日常所用的話,十分差不多占九分沒有相當的文字。那是因為我們的話是土話,是沒有文字的下級話,是大多數占了不合理的話啦。所以沒有文學的價值,已是無可疑的了。”事實證明:張我軍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一位關鍵性人物.他將"五四"文學火種引入台灣,與日本奴役下的台灣舊文壇激烈交戰;他最早明確指出台灣新文學與祖國大陸新文學的支流與主流關係,並且從文化歸屬與統一的角度提出台灣語言建設的主張.無論在理論倡導還是創作實踐方面,他都是一位當之無愧的先驅者。作家
龍瑛宗讚譽張我軍為“高舉五四火把回台的先覺者”。
亂都之戀
1925年12月張我軍自費在台北出版《戀都之戀》,1987年6月瀋陽遼寧大學出版部重刊,是張我軍的處女作,也是台灣新文學史的第一部新詩集,作者標為“抒情詩集”。書寬9.5公分,長17公分,計56頁(1987年重刊本增加3個附錄,增為80頁),除詩集序文1首外,收12篇55首新詩(〈沉寂〉1首、〈對月狂歌〉1首、〈無情的雨〉10首、〈游中央公園雜詩〉6首、〈煩悶〉4首、〈秋風又起了〉6首、〈前途〉1首、〈我願〉3首、〈危難的前途〉1首、〈亂都之戀〉15首、〈哥德又來勾引我苦惱〉6首、〈春意〉1首),其中33首寫於北京,15首寫於回台的海上途程中,7首寫於台北,部份曾發表於北京的《晨報副刊》、台北的《人人》雜誌、《台灣民報》上,定價金30錢。除詩序作於1925年12月,其他55篇的創作時間為1924年3月迄1925年3月。詩作記錄張我軍戀情的心路歷程,以當時軍閥混戰、人心惶惶的北京“亂都”為背景,抒發熱戀、相思、惜別、懷念和結合種種情思,表現對純潔愛情的執著、對人生的熱愛、對黑暗現實的憎恨、對美好未來的憧憬。步趨中國五四運動以後的自然風格,感情細膩真摯,語言鮮明活潑,格調清新流暢,白描多於隱喻與暗示,表現出新文學草創期的單純、素樸風格,不過詩作多數是散文句子的分行,詩的想像較為貧弱,表達的直露也使詩作缺乏耐讀性。
 張我軍的老師周作人
張我軍的老師周作人張我軍於詩集《亂都之戀》中所行吟的故事,就是作者來到北平求學時發生的。剛到北平時,張我軍寄居在後孫公園的泉郡會館,上課就在廠甸的高等師範所辦的升學補習班。當年補習班的夜班部是男女共學,班上有兩朵班花,一位17歲的少女叫羅文淑,肄業於北京尚義女子師範學校,為提高學業才到這所補習班補習功課,結果被少年英俊的張我軍一追就追上了。開頭的那首詩,就是詩人偷偷寫給心上人羅文淑的。不過,那時候雖說風氣剛開,但中國畢竟還是一個保守封閉的社會,男女戀愛,不僅要避人耳目,更要向家長隱瞞,所以這一對青年男女的私約,對羅家沒透半點口風。後來張我軍手邊的錢花完了,在北平無法生存,就暫時回到台北,在日本統治下的獨家漢文報紙《台灣民報》當編輯。張我軍連著給羅文淑去了好幾封信,但都石沉大海,杳無音信,原來女方的家長察覺此事,將男方的情書悉數沒收,女方也不知道張我軍的聯繫地址,弄得只有男女雙方關山阻隔,夢縈魂牽。此時,有一個高等師範四年級學生莊某,對羅文淑心儀已久,見張我軍返台遲遲未歸,就通過媒妁向羅家求婚,除去說了不少張我軍的壞話外,還說自己是大富商的弟弟,可以養活羅文淑的寡母幼弟。羅母正愁“女大不中留”,看到莊某即將畢業,家境也不錯,於是就應允了這樁婚事。羅文淑雖說心中早有他人,但拘於舊禮教約束,也不敢公開表示反對,只能暗暗著急。緊急關頭,張我軍的摯友洪炎秋得聞此事,立即給張我軍發去一封急電。張我軍接到電報後,當即趕來北平,託付另一個女友將羅文淑約出家門,倆人決定離家私奔,共奔台灣,來爭取自己的幸福。自此,羅文淑為自己心愛的人改名為羅心香。
1986年,已經是耄耋老人的羅心香在美國紐約寓所回憶這段戀情時,依舊是那樣甜蜜繾綣,令人回味:“一天我開箱找衣服,突然從箱子上掉下一封信和一張照片,信上只是寫了一首莫名其妙的白話詩。有—天,這個寫詩的青年主動來找我攀談,才知道他叫張我軍。他說自己不是來這裡補習功課,而是來學北京話的。就這樣,我們彼此相識了。我在一個姊姊的陪同下,每星期到他住的泉郡會館去一次,說些話,借幾本雜誌回來看。當時社會上青年男女還不能公開交往,我們只能保持這樣的接觸,他要求同我通信,我告訴他我家是封建舊家庭,不允許同男孩子來往。他說可以用女人的名字寫信,於是就用‘娥君’的名字,每周給我來一兩封信。還經常約我去公園,來去都各走各的路,躲躲藏藏地到沒人的地方才說話。這樣來往了大半年,他忽然不辭而別,接到信後才知道他回台灣了。就在這時家人要包辦我的婚事。正當愁雲密布之時,有人把這訊息電告我軍,他立即從台灣趕回北京,約我見面說,事至如此,只有一起去台灣避難,否則前途將遭厄運。就在這種情況下,我只穿了一身學生服,沒有攜帶任何證件,同我軍一同坐火車到上海,再乘船到廈門鼓浪嶼,然後寫信給家人。他們接到信後,立即寄錢和衣物給我,並要我們儘快正式結婚。得到這個訊息,我們非常高興,遂一同乘船去台灣,在台北江山樓擺了兩桌酒席,舉行了婚禮。”1925年12月28日,張我軍把自己與妻子的這段曲折的矢志不渝的戀愛經歷寫成新詩集《亂都之戀》,自費出版,成為台灣島的第一部白話新詩集。這本詩集出版之際,正是日本殖民主義在台灣實行嚴厲的思想鉗制、推行“皇民化”文化、禁止漢語傳習的時期。《亂都之戀》出版後,台灣不少讀書人才知道世間除了文言的舊體詩外,還有白話的新詩體,於是紛紛起而仿效,給寶島的白話文運動以及詩體的解放,帶來了一陣清新的漣漪。張我軍還甘冒大不韙,毅然宣稱:“台灣文學乃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指出台灣文學與大陸文學密不可分的血緣關係。因此,張我軍被人譽為是“代表了台灣作家不畏強權的道德良心。”
 張我軍任教的北京大學
張我軍任教的北京大學寫作風格
張我軍文學的主要成就在於評論戰及新詩創作和小說創作。
他關於新文學理論的批判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第一,對舊文學的批判。第二,關於文學的內容與形式。第三,對待台灣文學與祖國大陸新文學的關係上。第四,關於東西方文化的關係。第五,關於“國語”與“方言”的關係。
張我軍的詩作曾結集出版,名為《亂都之戀》,這是台灣新文學史上的第一部新詩集。至於張我軍的小說,雖是其文學創作的副產品,但在台灣新文學的草創期中,實具有不可忽視的代表意義。其小說語言,不用台灣語文,完全以中國白話文來創作,以後並影響了鄭登山,廖漢臣及
朱點人等人,與賴和、郭秋生的台灣語文流派不同,也與楊雲萍諸人帶有日本風味的白話文流派截然有別,是草創期中小說語言的“三大派別”之一。
人物軼事
介紹魯訊
張我軍,在上世紀20年代中期,不但寫下了表現自己在北平與大陸姑娘相戀的愛情經驗的詩歌集《亂都之戀》,在台灣報刊撰文介紹了
魯迅、
郭沫若、
冰心等的作品,掀起台灣新文學的第一個浪潮。他還在北平拜訪過魯迅,並且向魯迅表示中國人似乎都忘記台灣了,誰也不大提起它。這段話顯然刺痛了魯迅,令他難以忘懷:“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但口上卻道:不,那倒不至於的,只因為該國太破爛,內憂外患,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1927年夏天,魯迅在《寫在“勞動問題”之前》中記載了張我軍的來訪和上述對話,還特意指出,“但正在困苦中的台灣的青年,卻並不將中國的事情暫且放下。他們常希望中國革命的成功,贊助中國的改革,總想盡此力,於中國的現在和將來有所裨益”。
日語教育
張我軍主編的《日文與日語》雜誌作為“民國以來國人創辦的第一份有影響的日語研究期刊”,對日語語言文學學科而言,具有重大的學科史意義;張氏日語系列教材大大推進了日語在中國各階層普及;作為一位師者,他不僅以有中國特色的日語教學法培養了一批精英之才,更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為將日語教育引入正軌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研究者、編者、著者、師者"四重身份的重合、互動使張我軍成為中國日語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教育家。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之一
黃現璠就讀北師大時(1926-1935),曾師從張我軍習日文,結為師友。1934年黃現璠的日文譯著《元代農民之生活——附奴隸考》出版前的原稿校定,便是他請師友張我軍最終審定的。
 1920年代在北京求學的張我軍(中坐者)
1920年代在北京求學的張我軍(中坐者)交友
1937年“
七七事變”之後,大批
台灣人來到北平,在淪陷區艱難生活,並有自己的社區。他們想為故鄉而戰,卻不能承認故鄉。張我軍除去任北京大學工學院日本文學系教授外,不擔任任何偽官職。他在北平的台灣人圈子裡很活躍,與
連震東、
洪炎秋、
蘇薌雨,被合稱為“台灣四人幫”或“台灣四劍客”。在中國抗戰時期的淪陷區北平,有被稱為“台灣三劍客”的作家,他們分別是
張深切、張我軍和洪炎秋。其中張我軍偶有涉筆,少有創作,被人稱為是“抵抗意識”最強的一位作家。當年一個日本學者曾在《非常時期的日本文壇史》中記載一個場景,最能說明問題:“一行人當中,只有張我軍一個人扭過臉去,不向皇宮鞠躬哈腰,給我的印象很深。此人日本語講得非常漂亮,也曾擔任過翻譯,但是像一個不好對付的人。”
“七七事變”後為時局所迫,張我軍也不得不和日偽方面的人物甚至是頭面人物發生一些往來,但是他把這類活動鎖定在教育、文學、日文翻譯等方面,而儘量避開政治。即使在某些情況下,參加了政治色彩十分濃厚的活動,他也儘量保持清醒的頭腦,沒有迷失大方向。就是與自己的恩師周作人他也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劃清了界限。周作人與張我軍可謂“交情頗深”,早在張我軍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時,兩人就有了接觸,作為老師的周作人還介紹張我軍發表日文翻譯的作品,並且為張我軍翻譯的夏目漱石的《文學論》作序,後來師生二人也一直有來往。張我軍對
周作人一直十分尊重,對於周作人的學問一直十分佩服。在談到翻譯問題的時候對周作人十分推崇,建議想要練習日語翻譯技巧的人可以拿日文原文和周作人的譯文對照著看,因為周作人的譯文是很好的範本,對於提高翻譯技巧會有很大好處;在學生向他請教誰的譯文最可靠時,他也只推薦了周作人一個人的。當自己的生活遇到困難時,他也曾去找周作人想辦法,周作人也“以個人資格”介紹他翻譯日文名著《黎明之前》,幫助他解決困難。但是即便如此,他還是借發表《〈黎明之前〉尚在黎明之前》一文與周作人劃清了界限,他說自己“所求的是周老師,並不是周督辦”,“而老人指周作人。也似乎深知我不是找他要官做的……”,婉轉巧妙地分清了公與私、學問與政治的界限。張我軍與在京的台灣鄉親們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他不僅在返回北京初期號召重組了北京台灣青年會,而且和許多台灣鄉親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據張我軍的好友蘇薌雨先生回憶,當時連震東從日本慶應大學畢業,到北京遊歷,住在洪炎秋的家裡,他們四個人每周必定要聚在一起,去洗澡、吃小館、暢談,十分快活。後來,游彌堅先生也來到北京住了幾個月,他們五個人總是在一起玩,張我軍當時手頭寬裕,在該付錢的時候總是搶著付,非常慷慨。不僅如此,張我軍的家人與蘇薌雨、洪炎秋的家人也往來十分密切。當時蘇薌雨和洪炎秋都先後成家,洪炎秋的母親也來到了北京,這三家人經常輪流做東,不斷在一起聚會,十分親熱。1934年,蘇薌雨把妻子送回娘家,自己去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留學,時間長達數年。在這期間,張我軍不論自己境況如何,總是每月按時資助蘇薌雨一部分學資,從來沒有間斷過。對於這樣深厚的朋友情義,蘇薌雨先生“終生不忘”!1941年才與張我軍相識的蘇子蘅先生也對張我軍對鄉親朋友的熱情留有深刻的印象。當時蘇子蘅一家初來北京,人生地不熟,張我軍及其家人對他們給予了熱情的幫助與照料。在張我軍的介紹下,
蘇子蘅先後在北京大學理學院、工學院和
北京師範大學找到工作,得以在北京定居。當時,住在北京的台灣鄉親們每逢節日習慣於互相宴請,每逢這時張我軍的家裡總是賓客盈門,足見他交遊之廣。
 張我軍的學友葉蒼岑
張我軍的學友葉蒼岑張我軍不僅和台灣的鄉親有著密切的往來,而且也有眾多的大陸朋友。他們之間也都有著密切的關係。據張我軍的大學同學葉蒼芩老先生回憶,雖然他比張我軍低兩屆,但是在1926年到1937年這十多年間,他們三天兩頭見面,一起到琉璃廠去“淘”古書,有錢的時候就買回來,沒錢的時候就在那裡翻看,十分快活。1931年張我軍的次子出生時,葉蒼芩還為他起了名字,叫做“光直”,足見二人之間的親密關係。不僅如此,張我軍還和葉蒼芩等大陸同學共十二人組織了文學團體,一起從事文學活動。同學們對他的組織能力和才華都十分欣賞。
照顧林海音
張我軍與著名女作家
林海音一家的交往頗深。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她的父親林煥文先生是台灣苗栗客家人,原籍廣東省蕉嶺,從林海音的祖父林台算起,移居台灣已經有七代了,被稱為“西河堂林家”。林煥文是個愛國的知識分子,1895年日本侵略者割占台灣時他年僅七歲,親眼目睹了台灣人民同仇敵愾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心中埋下了仇日和愛國的種子。青年時期的林煥文在老家台灣苗栗縣頭份鄉教書。1917年帶著已懷孕的妻子愛珍到日本去謀生。夫婦二人在日本的商業中心大阪定居下來,開設了一家賣網球拍和縫衣針的商店。這樣的生活維持了三年。林海音就是在他們到達大阪的第二年的農曆三月十八出生的。可是教師出身的林煥文不善經商,在這三年里他不僅沒有賺到錢,就連從台灣帶去的老本也差不多要賠光了。於是,他準備到祖國大陸去,由於他當時對大陸情況不是十分明了,便將妻子和女兒先送回台灣,只身前往北京去探明情況。到
北京之後,他確信這裡是一個適宜的安身立命之所,於是,1923年3月將妻子愛珍和年僅五歲的林海音接到北京。一家人在北京團聚之後,臨時住在珠市口的謙安客棧。不久,林煥文通過考試被錄取到收入豐厚、工作穩定的北京郵政總局工作。他們一家也從客棧搬到了租賃的房子裡居住。此後,林煥文的兩個弟弟也從台灣遷到北京居住和生活。他們一家與當時在北京的台灣鄉親保持了密切的交往,其中與張我軍一家的關係更是十分親近。張我軍和林煥文不僅是意氣相投的朋友,還有點親戚關係。林煥文的妻子愛珍是張我軍的故鄉台北板橋人,她是一個樂天知命、不識字的舊式婦女,十五歲就與林煥文先生結婚,生有五女一子。據說幼時曾經許配給張家,男方病故,才嫁給林家。因為有這么一層關係,張我軍的孩子們都稱她為姑媽,林海音和自己的弟妹們則稱張我軍為表舅。兩家人往來很是頻繁,甚至林海音留在台灣的二妹林秀英也是由張我軍的母親帶到北京來的。林煥文一家和許多台灣同胞一樣十分講究民族氣節。當時,在北京的台灣同胞在名義上是日本僑民,但是他們卻把自己的籍貫寫成自己在大陸的祖籍。林海音該上國小了,林煥文沒有把女兒送進北京的日本僑校。他認為,自己本來就是一個中國人,不是所謂的日本僑民,中國人的孩子就應該進中國人的學校讀書,學習中華民族的文化知識。於是他把林海音送到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國小讀書,林海音在那裡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小北京”。1931年林家發生重大變故。林煥文最小的弟弟林炳文暗中做地下抗日工作已經有好幾年了,這次,為了支援朝鮮人民的抗日活動,他以自己在北京郵局工作為掩護,把一批抗日經費送往朝鮮,不幸在走到大連的時候被日本人發現逮捕入獄,在監獄中被折磨致死。林煥文從北平趕到大連去收屍,受到了嚴重刺激,又傷心又生氣,回來不久就染上重病,吐血不止,病逝在北平,年僅四十四歲。當時作為長女的林海音只有十四歲,下面還有五個年幼的弟妹,一家人生活十分艱難。由此,他們對日本人更加仇恨。林海音曾經寫信給在台灣的祖父林台先生,在信中寫道:“自從叔叔在大連被日本人害死在監獄之後,我永遠不能忘記,痛恨著害死親愛的叔叔的那個國家。還有爸爸的病,也是自從到大連收拾叔叔的遺體回來以後,才厲害起來的。爸爸曾經給您寫過一封很長很長的信,報告叔叔的事。我記得他寫了好多個夜晚,還大口吐著血。而且爸爸也曾經對我說過,當祖父年輕的時候,日本人剛來到台灣,祖父也曾經對日本人反抗過呢?所以,我是不願意回去讀那種學校的,更不願意弟弟妹妹從無知的幼年就受那種教育的(日本在台灣辦的學校)。”古繼堂:《林海音——台灣女性文學開山人》,《新文學史料》2002年第2期第7頁。張我軍一家對林家既同情又敬重,從各方面給予了林海音一家很大的幫助,張我軍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林家的父兄的角色。林煥文去世以後,林海音一面盡力維持家人生活,一面到福州人辦的明春中學讀書,畢業後,便考取了張我軍的學生成舍我在北京創辦的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後來分配到當時的《世界日報》當編輯,與同事
夏承楹相戀並結婚。夏承楹出生於北京一個大家族裡,他家是京城舊官宦人家,他的父親
夏仁虎,是前清的舉人,後來曾經擔任中華民國的國會議員、財政部次長以及國務院秘書長,於20年代末退隱在家。夏仁虎有八個子女,夏承楹排行第六。1939年,林海音和夏承楹在北平協和醫院禮堂舉行了隆重的婚禮。婚禮的證婚人是舊文學家趙椿年,男方的介紹人是王光美的父親王槐青,女方介紹人就是張我軍。不僅如此,張我軍還充當林家的操辦婚事的主事人,為林海音的婚禮奔忙。張我軍的長子張光正手裡仍然保存著林海音贈送的當年的結婚照:新郎夏承楹著燕尾服,新娘林海音披白色婚紗,左右有伴郎伴娘。男主婚人著長袍馬褂,女主婚人著晚清婦女大禮服,作為介紹人的張我軍著西裝站在後排。此後張我軍還一直給予他們以無私的幫助,兩家人保持了終生的友誼,他們的後人也多有來往。
 在張我軍關心下成長的名作家林海音
在張我軍關心下成長的名作家林海音主要作品
《張我軍詩文集》
1975年8月,林海音邀請張我軍次子張光直主編《張我軍詩文集》,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1989年,《張我軍詩文集》增訂並改名《張我軍文集》;1985年張我軍長子張光正於北京編選《張我軍選集》,並由時事出版社出版;1993年,台北縣立文化中心特約秦賢次編《張我軍先生文集》多冊,收於《台北縣作家作品集》。
《張我軍全集》
集結張我軍許多作品的《張我軍全集》,內容包含詩、小說、散文與評論,由張光正主編的2002年繁體本,全書552頁,約四十萬字,繁體本補遺〈為台灣人提出一個抗議〉、信件11封。正文分6部份,第一為“台灣新文學運動”,有〈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糟糕的台灣文學界〉、〈請合力折[1]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等14篇[1];第二為“論著”,有〈駁稻江建醮與政府和三新聞的態度〉、〈孫中山先生弔詞〉、〈《少年台灣》的使命〉等26篇;第三為“文學創作”,詩歌有新詩14篇57首、古典詩4首、小說有〈買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誘惑〉、〈元旦的一場小風波〉4篇(第4篇實為散文,被歸入小說類),散文有〈南遊印象記〉、〈採茶風景偶寫〉等10篇;第四部份為“序文與編語”,有〈《宗教的革命甘地》引言〉、〈《中國文藝》一卷三期編後記〉、〈《在廣東發動的台灣革命運動史略》序〉等35篇;第五為“日文與日語”,有〈《日文與日語》的使命〉、〈日本羅馬字的問題〉等18篇;第六為“書信”2封。
舊體詩作
僕僕燕塵里,韶光逝流水。
逢君如隔世,攜手共登樓。痛飲千杯酒,難消士載愁。
他日歸去後,極目故園秋。
人物子女
張我軍育有4子:張光正、張光直、張光誠、張光朴。大兒張光正參加中國共產革命沒有回台灣,其他3個兒子在台灣讀完書都留學美國,次子
張光直(1931-2001)為世界知名考古學家,生前曾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榮膺美國國家科學院和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後二者皆為百年來華人之首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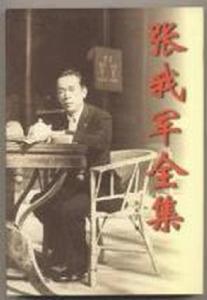 張我軍全集
張我軍全集評價作品
*張光正編:《近觀張我軍》 ,台海出版社,2002年2月。
*田建民著:《張我軍評傳》(台灣作家研究叢書之一),作家出版社,2006年7月。
 評價張我軍的作品-《近觀張我軍》
評價張我軍的作品-《近觀張我軍》 張我軍的二子張光直(青年時代帥照)
張我軍的二子張光直(青年時代帥照) 張我軍的老師周作人
張我軍的老師周作人 張我軍任教的北京大學
張我軍任教的北京大學 1920年代在北京求學的張我軍(中坐者)
1920年代在北京求學的張我軍(中坐者) 張我軍的學友葉蒼岑
張我軍的學友葉蒼岑 在張我軍關心下成長的名作家林海音
在張我軍關心下成長的名作家林海音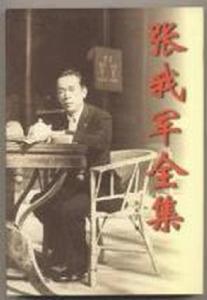 張我軍全集
張我軍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