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形成
少年漂泊
哈特·克萊思的詩與“那深深的驚奇,我們的故土”是那樣地協調,因此,雖然他的作品在美國以外廣為傳誦,但他的風格仍明顯地保留著個人和民族的特色。他在
超驗主義的傳統中發展,但無法過一種遁世的生活。他的母親是一個篤信基督教的科學家,對他的早年生活有很大影響。她引導他相信
個人主義精神應該高於居次要地位的物質世界,並企圖通過幻想獲得一種基本現實。他在精神上做了努力,但在形體上他仍被禁錮在這居於第二位的世界上。他沒有華爾頓湖[1];因此陷入了一個殘酷的心理矛盾之中,他所受的正規教育很有限,十七歲時就踏入了到處都是失業的社會。他的父母分居很早。他自己是個同性戀者,而且嗜酒成性。他時而樂觀,時而感到極度絕望,這種自相矛盾的情況直到他三十三歲自殺之前(1932)仍沒有得到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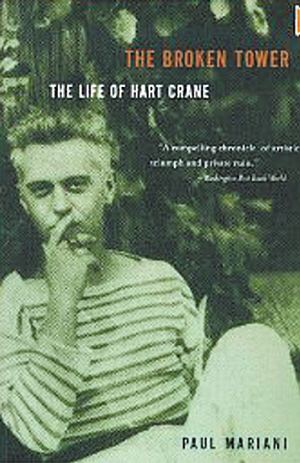 哈特·克萊恩傳記
哈特·克萊恩傳記他的書信雖然很少涉及國家大事,但主要談的是文學方面的事。正是這種強烈、不懈的思想追求,才使他的詩充滿了許多(有時是相互衝突的)隱喻。在另一個絕望到來之前,他似乎不顧一切地追求著生命和詩。
哈特·克萊思出生在俄亥俄州的蓋雷次維勒,是家中的獨生子。他的父母很富有,但在他十歲的時候便離異了。童年時代他很喜歡幻想,而且喜歡打扮得衣冠楚楚。他一生都未忘記他在《貴格山》一詩中稱之為“對離異雙親的詛咒”。十七歲那年他離開了俄亥俄州克列佛蘭的學校。
克萊思在校期間就已開始寫詩。在他保存下來的最早的詩作中,隱喻和意象很多。這既是他較成熟作品的力量之所在,也是其晦澀難懂的原因。
克萊思乾過幾年雜活,曾在紐約做過店員,做過廣告撰稿員等等。這些不稱心的工作他幹得都不久。在此期間,他曾獨自或偕同母親到歐洲,
古巴等地旅行。1919年,環境迫使他接受了父親在
阿克倫的一家商店給他的一份工作。他與父親根本合不來,所以這個工作也沒有乾多久。
定居紐約
1920年他終於定居紐約,想在銀行家奧托·卡恩的贊助下,努力靠寫詩為生。1923年他完成了第一部重要的長詩《獻給浮士德和海倫的婚禮》,後來收入他的第一部詩集《白色建築》(1926)中。為了使他能夠寫出《大橋》一詩,卡恩曾借錢給他。克萊思到
古巴附近的松樹島住了幾個星期,寫出了一些很優美的抒情詩。這些詩成為《大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兩個絕望的年頭中,他一個字都沒寫,接著又到
舊金山和法國度過了一個歉收的季節。1929年秋返回美國後,他全憑著個人的意志而不是靈感,完成了《大橋》。1931年他獲得了
古根海姆研究基金,赴墨西哥準備寫一部有關蒙太祖馬[2]的史詩,但這時他幾乎江郎才盡,精神面臨著全面崩潰。他寫了幾首短詩,組成了《西鎖島:一束島》和《斷塔》:
帶鈴的繩索在黎明拽來了上帝
把我放開仿佛我丟落了一個
末日的喪鐘——踟躕在大教堂中的甬道上
從深淵到耶穌受難像, 從地獄走出的腳步
越走越冰涼。
儘管他1932年頭一次與一個女人正式結婚,但他的失敗感已不可挽回。1932年4月27日,在墨西哥回美國的途中,他從奧里扎巴號客輪上投水自盡了。
從他的早期詩歌中可以看出,他對莎士比亞,
韋伯以及馬洛的語言都非常熟悉。這對他後期優秀的隱喻風格影響很大。法國詩人于勒·拉弗格以及他使用的諷喻語氣對他也很有吸引力。他翻譯了拉弗格的《怨歌集》。這位
象徵派大師對他的影響在《卓別林》和《黑手鼓》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他在《卓別林》中寫道:
我們進行了適中的調整,
對這種隨意的安慰感到滿意
就象風兒緩緩地
在很寬敞的口袋裡沉積。
然而他堅持的道路是樂觀的,他用
詹姆士一世時期的豐富語言肯定了
艾略特在《荒原》中對生活所作的全部否定。1923年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我把艾略特作為一個向著完全不同方向前進的出發點。就他的情況來說,他的
悲觀主義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但是我要儘可能地運用我能從他那裡學到的知識與技巧,制定一個更為樂觀或者(假如我必須在一個懷疑的時代這樣說的話)更令人陶醉的目標。”
克萊思的心理嚮導,但還是風格嚮導,是惠特曼。
重新舉起步伐,向前進不停留
不很快,也不突然——不,決不要從你乎中
擻開我的手
惠特曼——
就這樣——
梅爾維爾給他的啟發是對大海和大海形象的大量象徵性使用。在《白色建築》的《航海》組詩中他把這個形象用得很有力:
——然而永恆這偉大的瞬間,
那無邊的洪水, 隨風激盪,
象錦緞一樣席捲……
在《浮士德和海倫的聯姻》中,他採用有意識的樂觀主義方法去實現他超越物質世界的宏偉目標。全詩的三個部分用現代語言描繪浮土德“我自身的象徵,富有詩意或想像力的永恆人物”始終忠實于海倫“這美的化身”。這首詩似乎在極不利的條件下,在顯著的樂觀主義氣氛中,達到了高潮:
格外地讚頌這些年頭,它們
易揮發的流血的手,伸展並且反覆敲打著商度
想像力跨越過絕望,
超越了交易、詞語和祈禱。
語言、結構和形象都晦澀難懂。克萊思在《總目標和總理論》這篇論文中,試圖解釋這種語言結構和形象。他的企圖是要在古典經驗和“我們當今這個沸騰、混亂的世界中的不同現實之間搭起一座橋樑,因此我發現‘海倫’乘坐著街車,人們向她求婚和引誘她的酒神節歡宴被轉移到一座有爵士樂隊伴奏的大都市屋頂花園裡。我認為特洛伊陷落的‘淨化’可以同最近這次世界大戰中的‘淨化’相提並論。”他為語言和暗喻的晦澀辯護,說這首詩的結構“建立在暗喻邏輯”的有機原理上。言下之意是說,暗喻的力量勝於邏輯思維,因為它比邏輯思維更直接。它給予我們某種體驗,而不是一種思想。暗喻有著自身的邏輯,與思維邏輯截然不同。為此,他引用了這首詩中的一個例子,解釋說“一架飛機的速度與高度”用“迅速移動”的意念來暗示要好得多,因為它也暗示出了飛機和飛行速度與靜止隆起的地球之間的反襯。”他在論文的結尾說:“語言建立起高塔與橋樑,但本身卻始終照例地流動變化著。”他的這些解釋有啟發性,但沒有解決形象擁塞這一基本問題,而且克萊思沒有提及
聽覺諧振(aural resonance)的問題。聽覺諧振雖然不重視解釋,但貫穿著全詩,給了這首詩那怕是最難懂的地方一種整體連貫感,暗示著令人陶醉的目標。
《白色建築》中的《航海》是由六首詩組成的組詩,它將得出一個超驗的結論——“這個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象這樣。”最後一段是歌頌——出神入化必須不受時間與現實世界的限制,但它應該是玄學的,在想像的世界中被變形:
這有形的詞,是它抓住
沉靜下來的柳樹,固定在其中。
這是不露聲色的回答
其口音只有從告別話中才能聽出。
《橋》
《大橋》對克萊思的重要性在他的信中講得很清楚。他從歷史和文化的範圍里與《
埃涅阿斯紀》[3]作比較,“它至少是一首有史詩主題的交響曲”,“其結構與《荒原》同樣複雜。”有些批評家認為這是一首工程浩大但沒有意義的浪漫故事。不過克萊思最終的詩人地位顯然必須根據這一首詩來作判斷。的確,克萊思自己也希望這樣做。
 哈特·克萊恩詩集封面
哈特·克萊恩詩集封面這首詩的部分結尾是事先就寫好的。克萊思對這首詩的構思早已成竹在胸。他把這首詩當作“美國”的一個“神秘的綜合體”。“歷史與事實、地點等等,一切都必須轉化成幾乎可以單獨起主題作用的抽象形式。”布魯克林大橋成為希望和未來,美國走向“阿特蘭提斯[4]”的象徵。這個旅程重新喚起
美國歷史傳說中的人物與地點。
哥倫布、玻卡洪達斯[5]、瑞普、凡·溫克爾、
惠特曼、
梅爾維爾、愛倫·坡和其他人物都在詩中出現。“隧道”一段表現的是在到達明亮的阿特蘭提斯之前的幻滅感和那種傳說中史詩式的下地獄,“——一首歌,一座火之橋!它是中國嗎……?在《序詩:致布魯克林大橋》這首詩中,克萊思實踐了他在《現代詩歌》一文中提出的原則:‘除非機器人詩,就象樹木那樣自然地入詩,否則詩歌就完全失去了當代的功用。”第一段《歡迎瑪麗亞》緊接在試圖將機器引入詩的《序詩》之後。在這一段中,可以看到哥倫布受到將東方與西方結合為一體的理想的鼓舞,從西路到達了中國:“那裡是黎明——/呵,我們的印度王國就沐浴在陽光下,/然而全都失去了,快讓這平底舟靠岸!”此刻必須發現新的陸地,現代化的大橋必須通向那想像力未曾探索到的世界,那“仍有一個超越欲望的海岸!”
第二段《玻哈坦的女兒》是
阿美利加的象徵性“身體”。在這一段中,純潔的玻卡洪達斯露面了,下屬的五個分段都描寫的是從紐約沒落的
物質主義走向理想化的西方。在這個過程中,主人公玻卡洪達斯的情人融為一體。通過他在火刑柱上的犧牲,他獲得了新生,以進行精神上的旅行:“包裹在那堆火中,我看見更多的守護人醒來/——忽隱忽現,疾跑上山稜象一股潮流。”
第三段《短袍》講到十九世紀開往中國的那種
快速帆船:“劈波斬浪,船底開出綠色的草地/鎖在風的機靈里,它們都向東方行駛。”第四段主要是寫飛行員是水手的接班人:“穿過明亮的晴空、展開著,未曾睡眠/翅膀剪裁著光明最後的邊緣。”
第五段中有以女人,即“美國的身體”為主題的《三首歌》。第六段《貴格山》用的是自傳性的材料,哀嘆
新英格蘭精神的沒落:“這裡曾是‘希望之鄉’。”
在《隧洞》中,向地獄的沉降象徵性地描繪為向
紐約地下鐵道的沉降。“誰的頭顱在鼓起的鐵條上搖擺?誰的身體沿著老鐵軌冒煙?”
受折磨的靈魂也同樣因為是紐約的市民而受到詛咒,天天經受著常規的侮辱。這一段的結尾模仿了艾略特:
我們極度痛苦的吻,你聚集,
呵,火之子
聚集——
這首詩向外部摸索前進,走到了露天中,而且在最後一段《阿特蘭提斯》中,大橋完工了:
呵,你鋼化了的認識,它的跨越
在它繩索可及的範圍內
成雙成對地在單個的蝶蛹中歌唱……
由於《橋》力圖達到史詩效果,所以它一直是英文中最難懂的一首詩。雖然它有缺陷,特別是經過一段難產期後,哈特克萊思努力寫成的某些段落,如《印地安納》、《
哈特拉斯角》和《貴格山》,
理想主義和
樂觀主義的狂喜往往很有力,儘管有時很牽強。在美國詩歌中很難找出與之匹敵的對手。這是一部有缺陷的傑作。史詩和浪漫的衝動似乎有分歧。這首詩的長度只彳卜一千行,缺陷是嚴重的:晦澀、矯揉造作,也許在不自然的樂觀主義中有某種程度的不誠實。但是一經朗讀,這首詩在節奏上便有那種理想式的雄心勃勃的張力,還有對這一嘗試的價值的堅定信念。
 布魯克林橋
布魯克林橋——一首歌,一座火之橋:是中國嗎,此時憐憫沉浸著青草,長虹套住了
那條蛇, 雄鷹在葉子間………?
應答輪唱的低語在天空中搖曳。
克萊思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中幾乎再沒有寫出什麼詩來,《大橋》把他的精力消耗殆盡了。不過《破裂的塔》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
我傾吐了我的話語。然而它是否同義語
記載著那個空中法庭的君主
其股為大地鍍上銅色,在傷痕里寫下
適澈的聖諭,曾發誓給於希望一一卻變成了絕望?
相關評論
哈特·克萊恩是一位有難度的大詩人,但是他非常優秀,甚至偉大。然而,詩歌不一定要看上去就很有難度,霍斯曼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其他一些詩人也是如此。還有一些詩人初看很簡單,實際上並非如此。惠特曼宣稱自己的詩平易近人,但他最好的詩卻很微妙、難以捉摸、神秘莫測,要求讀者提升自己對比喻的細節的感知水平。偉大的詩篇可以有幾種迥然不同的難度。持續有力的用典,在
約翰·彌爾頓和
托馬斯·格雷的博學的詩里,需要讀者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認知的原創性,作為
莎士比亞和
艾米莉·狄金森的特殊標誌,需要讀者享有極高的智識上的敏捷。個人的神話建構,在威廉·布萊克和葉芝那裡,初看起來是晦澀的,但他們的神話的連貫性會讓讀者熟悉起來。然而克萊恩是他這一代中的異數,他這一代詩人為詩人批評家伊·溫特斯(Yvor Winters)、艾·泰特(Allen Tate)、理·布萊克默(Richard P. Blackmur),馬·考利(Malcolm Cowley)所環繞。與他們中的每一位討論完克蘭,我發現自己總是陷於悲哀,因為他們對其成就富於感情的誤讀。在他這一代中他與肯·伯克(Kenneth Burke)的關係最深切,伯克對我評述過,很大程度上是在詩人死後他對克萊恩的作品才達到了充分同情共感的理解。艾略特、龐德的時代對克萊恩不是一個仁慈的環境,一個高浪漫派詩人處身高現代主義和艾略特派新批評中,後者判定要與任何一種浪漫主義情感相“分離”。而克萊恩,有將思想、情緒、感覺熔並的一體化情感,這經艾略特的檢測被分為了數個心理要素之後,被認為是危險的。事實上,這一批評視域在成為艾略特的之前是沃·佩特(Walter Pater)的。——哈羅德·布魯姆(美國當代著名文學批評家,耶魯學派代表批評家)
 哈羅德·布魯姆
哈羅德·布魯姆作品欣賞
祖母的情書
今夜無星
除了那些記憶中的
然而供回憶的空間多么廣大
在柔雨鬆軟的環抱中
甚至有足夠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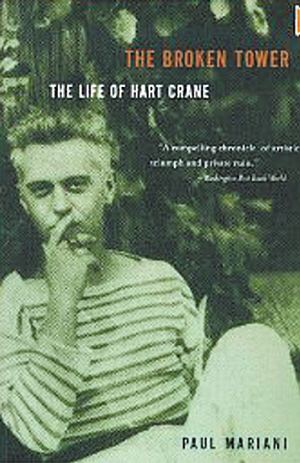 哈特·克萊恩傳記
哈特·克萊恩傳記 哈特·克萊恩詩集封面
哈特·克萊恩詩集封面 布魯克林橋
布魯克林橋 哈羅德·布魯姆
哈羅德·布魯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