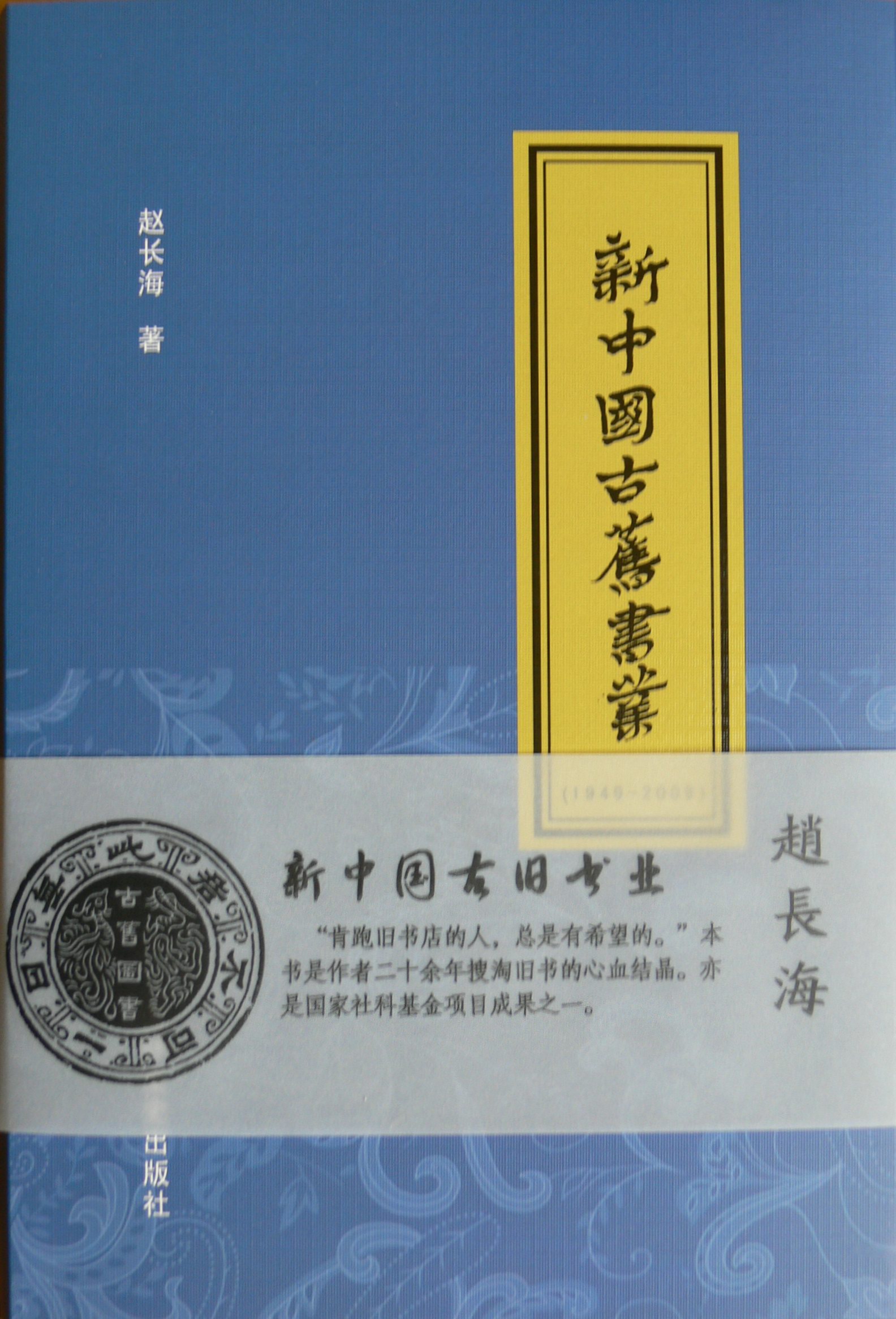舊書
而“舊書”一詞,無論是書面還是口語,雖則出現頻度很高,但準確的定義卻一直是含糊不清的。舊書當然是相對於新書而言的,但多長時間內的書才算是新書,過去多久的書方可稱舊書吶?何況新舊的概念從來都是相對的,且隨著時間的演變,新舊的範疇和外延也是變化不定的。比如當今信息化時代,知識更新周期很快,而古代由於交通及通訊的不發達,一本刻印多年的書,對許多人來說仍然是新鮮的。
台灣舊書業研究者李志銘對新與舊的辯證關係如此描述:“‘新’與‘舊’是‘時間’語彙,也是‘空間’語彙,彼此之間相互定義。從資訊吸收的觀點來說,‘新’與‘舊’並非專指‘時間價值’,同時也意味著每個人對於不同事務的‘熟悉程度’。一本絕版書出版年代久遠,只要是你未曾聽聞過,其實都算是‘新書’。相反地,一本在傳媒廣告上頻頻出現的當月出版書籍,卻有可能使得這本書早已成為顧客印象中熟悉已久的‘舊書’”
對於許多愛書人和藏書者來講,舊書更以其知識的含量和個人情感色彩而定。似乎“舊書”不僅在於時間的過去及圖書表面的破舊,而在於“相比之下,舊書便比新書多了點什麼”。江蘇作家、藏書家薛冰先生曾經以人作喻,深刻地探究過古舊書的底蘊:“舊書都是從新書而來的。正如每一位老人都曾年輕過,每一本舊書也都曾有過簇新時的挺括與帥氣……苛刻地說,一本書,如果已經到了韶華褪盡、蔫頭蔫腦,甚至創傷累累、肢殘體缺的程度,還能引起人們強烈的閱讀興趣,它才可以被稱為舊書。相比之下,舊書便比新書多了點什麼。”接下來薛冰先生用人之壽命來做更具體的譬喻,“一本書能‘活’到幾十歲、幾百歲、上千歲,成為名副其實的舊書以至於古書,甚至化身千萬,不斷再生,自然不會沒有原因……古舊書,該是經受住了歷史與時間檢驗的書。”
薛冰先生無疑是把經過時間大河洗滌沖盪,仍能活躍在讀者心頭的少數讀物,作為真正的舊書。台灣舊書業研究者李志銘與此有相同的見解,認為“新書是被文化工業所‘生產’,而‘舊書’則是使用流通過程中被消化。舊書之‘舊’字表明一本書久經歲月後所承載的文化價值。諸如某位名人寫下的眉批、作者贈書的題詞、甚至是某種形式遺留的痕跡等,讓原本單純的物品增添了生命主體所疊加的文化價值。‘舊書’因而進入社會文化的意義系統,甚至具備了某種‘手工藝品特質’”。
薛冰及劉志銘先生對舊書的見解很易為讀書界所認同,但這顯系讀書人對舊書情有獨鐘,帶有極大感情色彩的發揮,如果把此定義用到出版科學上,那么出版界舊書業界是很難完全認同的,在實踐上也是很難操作的。
正因“舊書”的範疇很難準確的統一界定,故連《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中國出版百科全書》等眾多辭書,對人們耳熟能詳的“舊書”,也沒有解釋的辭條。唯在早期《圖書館學辭典》(商務印書館1958年9月初版)中有“舊書”辭條,其定義為:原系與較新出版的書籍比較而言,唯並無絕對時限。凡已經他人過手閱讀的書刊,一般均稱之為“舊書”,但亦有出版入館後,並無人閱讀,擱置經久,習慣上亦稱之為“舊書”。此條對於“舊書”的定義簡潔明了,主要有兩方面的意義,即二手書和出版社或圖書館擱置較久的圖書。 著名藏書家黃裳先生對於“舊書”的概念,則較為寬泛,在其1980年逛琉璃廠時即曾說到:“舊書的來源是日漸稀少了,舊書的定義也一直在不停地變化,在王漁洋、李南澗的時代,宋元本是舊書……不過今天也還是有今天的舊書的,只要是新華書店不予經營或無力經營的就都是,看來那天地也實在廣闊得很“而那時經營新書的主要是新華書店,私營書店尚不發達,故黃裳的意思實在很明白,即新書店不予經營或無力經營的,都應是“舊書”的範疇。
南京大學古舊書業研究專家徐雁教授,在其《中國文獻資源與知識傳播綱要》一文中對古舊書業定義為:“古舊書業是指向藏書者和讀者回收其售出的古書和舊書,以便再次投放市場銷售的圖書發行業。”在《中國古舊書業:源遠流長與存亡絕續》的論文中再次明確指出:“古舊書業是指從書籍的持有者手中,回收其售出的古書和舊書,並再次將之投向市場向讀者銷售的一個行業。一般說來,它與新書出版發行業一起,共同組成一個國家乃至一個地區的完整的圖書市場。”
徐雁先生曾多次著文談到舊書,而其主要的觀點即:經過流通再回收的書方可稱之曰“舊書”。
在台灣,據舊書業研究者李志銘介紹,“90年代以後,出版業與書店日漸商業化、連鎖化。書籍文化工業大量生產的結果,使得許多新書在上架過後沒有多久,旋即退回出版社,成為所謂‘回頭書’、‘風漬書’。這類根本沒賣出去過的‘新的舊書’,不但對新書市場造成衝擊,也直接影響了傳統舊書業。於是舊書標準到此又經歷了一個巨變,界定更為廣泛。如今,凡是只要排除在新書店架上以外的書,幾乎都可算作‘舊書’的一份子。”
國外對圖書慣用的界定,則一般用珍本書(antiquarian)或稀見書(rare boook)、二手書(used book)。等來界定,沒有“舊書”這種模糊不清的概念。
舊書店
至於對於“舊書店”的界定,《圖書館學辭典》(商務印書館1958年9月初版)定義為:“販賣舊書的書店,在我國北京琉璃廠及上海河南路一帶最為有名。以北京舊書業歷史最為悠久,從業人往往熟知各種版本,不僅努力於古典文化遺產的蒐集與整理,即對於革命文獻、近代史料,亦因各地讀者及圖書館之需要,曾進行調查研究,對以往著名期刊如《新青年》、《嚮導》、《東方雜誌》、《小說月報》等出版時代、卷期、流傳情況能如數家珍;對古典舊書尤多熟習。”
由此看來,此處的“舊書店”即現今常說的“古舊書店”。但因為《圖書館學辭典》發行量甚少,影響面不大,對“舊書”的界定仍較模糊,沒有一個具體的衡量年限,故對於許多文化行政管理者來說,連什麼叫“舊書店”,似乎也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
古舊書業
古舊書業,在解放前及解放初很長一段時間,統稱之曰“舊書業”,如民國日本學者島田瀚之《古文舊書考》,謝興堯於四十年代之《書林逸話》,其所稱“舊書”即主要指“古書”。到了1956年,因公私合營改造的需要,方統稱之曰“古舊書業”。1956年2月9日,北京市“私改”辦公室向國務院副總理陳雲匯報北京私營圖書發行業社會主義改造工作。陳雲對古舊書業的改造很重視,他指出:對古舊書業的改造要慎重些,不要看得簡單化,不要希望一下子把問題徹底解決,要很好使用那些懂行的專家,不要輕易大變,喪失他們應有的積極性。資本主義大戶可以合營,小戶還是讓他們搞一個時期看看。陳雲指示,對於當時全國古舊書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具有重大的積極作用和指導意義。扭轉了許多省市對古舊書業粗暴的做法。此後的2月21日,國務院向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發出了《對私營古舊書業改造必須慎重進行》的電示通知。此可謂“古舊書業”一詞在中國官方檔案中最早的出處。
隨後,在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的《關於私營出版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一些情況和問題》中,就開始使用“古舊書店”、“古舊書業”等詞,如其中講到此時期全國古舊書業公私合營情況時說到:“對古舊書業,大部分城市都和新書業一同實行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個別採取了直接過渡為國營的辦法。對私營古舊書業批准合營之後,有的已清產估價,瀋陽、南京等城市則還調整了古舊書的銷售點。”
當然,當時所提之“古舊書業”還主要是“古書業”,如1956年9月6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安排和改造古書業》的社論,及《光明日報》10月25日社論《古舊圖書不應再任令損毀》,均以“古書業”為主要對象。
1958年,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先生,在《古舊書籍發行工作的意義、方針、任務、政策》一文中,針對當年我國為實行對私圖書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現實必要,而將被“改造”的古書店和舊書店混稱為“古舊書店”。以利於政府有關部門對之進行行業管理。因此,“古舊書業”這一說法自1956年以來流行開來並沿用至今。
2000年第11屆全國書市期間,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古舊書工作委員會召開年會,在題為《把握形勢變化,積極調整古舊書業的發展方向》的報告中指出,古舊書的經營規模和網點布局很不平衡;線裝古書保有量呈下降趨勢,以往那種複本少而品種繁多的舊書經營模式難以見到;經營方式和服務形式同普通書店相比特色模糊,甚至在軟性服務方面還落後於其他書店。由於各地古舊書店、古籍書店以及相關部門在對古舊書業務進行範圍界定時,採取的標準掌握情況不一,導致在實際工作之中出現一些困難。為此,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古舊書工作委員會古委會對古舊圖書的界定範圍作了以下規定:1. 凡是在1911年以前出版的中外書刊、資料、圖片、碑帖、書畫等文字、圖形的載體均為古書;2. 凡是在1949年10月1日以前中外書刊、資料、圖片、碑帖、書畫等文字、圖形的載體均為解放前舊書;3. 1949年以後出版的中外書刊、資料、圖片、碑帖、書畫等文字、圖形的載體經過流通並回收再發行的書刊資料、影印古籍、古籍整理校勘的文化學術圖書也為古舊書範圍。
綜上所述,古舊書業是以微不足道的經濟面目出現,以古舊圖書為主要經營對象的文化事業。雖然它和圖書發行業及信息業有著天然的聯繫,具有圖書館和檔案館的部分功能,但其既非純功利性的圖書檔案事業,也不是純粹的圖書發行業,更非純粹以贏利為主要目的商品經營。古舊書業可說是一個文化中介的混合體。
國內研究古舊書業的學者主要有:
一、南京大學著名教授徐雁,著有《中國舊書業百年》,科學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一百餘萬字,印量3000冊。
二、鄭州大學圖書館研究館員趙長海,著有《新中國古舊書業(1949-2009)》,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字數55萬字,印量1000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