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江蘇無錫人。齋號小端居室,
文學碩士。2002~2006年就讀於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學書法篆刻專業,2013年攻讀該院書法專業碩士研究生。師從
金丹教授。在校期間書法作品曾獲大學生藝術節優秀獎,2005年作品被南京藝術學院收藏,2006年作品入選西泠印社首屆楹聯展,2010年作品入展江蘇省六屆青年書法篆刻展,2013年作品入展江蘇省七屆青年書法篆刻展。現為南京顏真卿書畫院畫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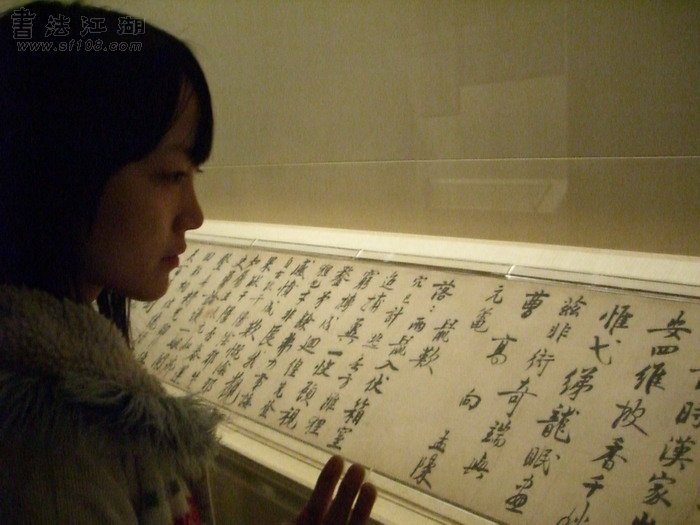 上博“晉唐宋元”國寶展
上博“晉唐宋元”國寶展個人作品
文/倪艷/2006
本文刊登於 《書法導報》2010年4月28日第17期二十三版
【內容提要】 晚清書壇,帖派急劇衰微,碑派一統天下,成為書壇主流,繼阮元“二論”、包世臣《藝舟雙楫》之後,康有為在《書鏡》中,對碑學提出了一套更為完整的理論,將清代碑學推向高潮,在這種形勢下,孕育出一批崇尚碑學的書家,如:沈曾植、
曾熙、鄭孝胥、
李瑞清等,本文以
李瑞清為例,探討其身為晚清碑學末流的負面影響,我們不能否認清代碑學的發生有其合理的成分,但發展至晚清,其背後的負面影響也是真實存在的,因此,對晚清碑學的重審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一、清代碑學的時代背景
清乾嘉時期,由於經學的廣泛普及,成為清代學術的主題,訓詁考據成為研究學問的主要途徑。乾嘉學派的確立,為金石學和考據學提供了土壤,在整個學術界思想轉變的同時,書壇也受到影響,產生了根本性變化,最終導致了碑學理論的確立和碑派書風的形成。
清初書壇,遺民傅山在其所著《霜紅龕集》中提出“四寧四毋”,打破帖學傳統意識,在理論上賦予了書法新的美學觀,可視其為清代碑學的先行者;從實踐上開師碑風氣之先的則是以隸書名世的鄭簠,他以漢碑為師,曾傾家蕩產,各地訪碑,鄭簠碑學實踐的成功給當時乃至後世的書法審美注入了新的血液。而較早提出“不學二王”的則是揚州八怪之一的金農,其在《魯中雜詩》中云:“恥向
書家作奴婢,華山片石是吾師”,以此實踐他的“同能不如獨詣,眾毀不如獨賞”的藝術主張,最早公開離經叛道,明確表明了自己師碑的立場。因此,金農成為書法史上由帖學過渡至碑學的關鍵性人物。阮元在前碑派實踐的基礎上,大力推崇北碑,以《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兩篇文章為師法北碑提供了理由,從此揭開了清代碑學的序幕,成為碑學正式形成的標誌。此後,包世臣在其所著的《藝舟雙楫》中,進一步揚碑抑帖,將碑學思想推向另一個高度。到了清代晚期,康有為更是把他的碑學理論反映在《書鏡》中,提出了一套更為完整而又偏激的理論,並從美學角度審視北碑,提出“十美”,給了其美學上的支撐。當然,《書鏡》的誕生與康有為的政治思想有很大的關係,這裡就不深入展開了。清代碑學便是在這種前提下發展起來的,而到了
李瑞清,將表現金石氣發揮到了極致,便開始漸露衰勢,形成碑學末流。在這種意義上,
李瑞清是否違背了碑學的初衷,將碑派帶入了死胡同,這些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李瑞清(1867—1920),近代著名的書法家、教育家、美術家。字仲麟,號梅庵,又號梅痴、
清道人。清同治六年七月初九出生,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人。
李瑞清誕生於一個三代為官的書香門第,從小愛好書法、繪畫、金石文字。光緒十九年 (1893年) 鄉試中舉人,光緒二十年甲午進士,乙未年入選翰林院庶吉士,光緒三十一年 (1905年) 以候補道分發江蘇,三署江寧提學使,併兼任兩江優級師範學堂監督。
李瑞清的書法融南、北碑帖,博綜漢魏六朝,他上追周秦,尤工篆隸,其書法理論造詣極深,被人稱為近代書學之宗師,聲名遠揚。
李瑞清遺著有《圍城記》,經門人整理其遺稿,又出版了《清道人遺卷》,總計四卷,第一卷為文,第二卷為詩,第三卷為題跋,第四卷為書論 (1939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 。
李瑞清自幼臨習書法,家中所藏金石拓片影響著其書學觀,他青年時代學習北碑,書各體皆備,曾說:
余書幼學鼎彝,學散氏盤最久,後學齊之屬,遍臨諸銅器。弱冠學漢分,所廿六始用力今隸、六朝諸碑糜不備究,爾後始稍稍學唐以來書,然從碑入簡札沉遁不入格,始參以帖學,然帖非宋拓初本無從得其筆法,故不如碑之易得也……余每臨帖以碑筆求之,輒十得八九,若但拘守匯帖,無異向木佛求舍利子,必無之事,不可不知。
可見其鑽研六書,從大篆開始,於《散氏盤》、《齊侯》諸銅器銘文進行過認真刻苦的臨習。尤其是對《散氏盤》學習的時間最長。當時學術界盛行考據訓詁,書壇則是碑派的天下,
李瑞清的書學思想是順應潮流的,明顯受到阮元、包世臣的影響。作為一代金石大師,
李瑞清於魏碑的成就顯得更為突出,世人也認為他“得名則在北碑”。
李瑞清對北碑觀察細緻入微,臨摹心手相應而達到“追其碑之風範”的程度。我們看
李瑞清《寄禪禪師冷看塔銘》酷似北魏《嵩高靈廟碑》,而《尉太夫人墓碑》又是從《鄭文公碑》而來。正如曾農髯所說,
李瑞清“學無不肖,且無不工”。
“求分於石,求篆於金”,是作為其書學理論的主要觀點之一,他在《跋自書篆》中說:
自來學篆書者,皆縶於石耳。《石鼓》既不可學,《泰山》、《琅琊》才數十字,又不脫楚氣,《嶧山》徐模也,勻淨如運算元,成何如書乎?道人志欲左右齊、楚,神遊三代,探險辟荒,未知何日登彼岸也!
篆書是其書法的根基,最好習《散氏盤》,甚至常用《散氏盤》的筆法臨習《鄭文公碑》。其楷書則以取法北碑為主,而對於雲峰山
鄭道昭諸刻石及《中嶽嵩高靈廟碑》、《張黑女墓誌》、《張猛龍碑》等石刻所下工夫最大,也對北碑有深切的體會,他在臨《張黑女墓誌》後跋云:“《黑女志》遒厚精古,北碑中之全神味勝者,由《曹全碑》一派出也。《敬使君》與此同宗,但綿邈不逮爾。”他在臨《鄭文公碑》後跋云:“直《散氏盤》耳,近代學者多鼓努為力,鋒芒外曜,安有淡雅雍容,不激不厲之妙耶?故不通篆隸,而高談北碑者妄也。”他寫北碑的突出特點便是採用篆書用筆,以行筆過程中的搖動、顫抖動作來表現碑刻拓本的峭拔、鈍厚、遲澀之趣,這種技巧的套用在當時被一些臨習大篆和北碑者所採用,並被廣泛認可,然其弊病也被近代學者所提出,崇尚碑學的
祝嘉先生在其《書學史》中肯定了其為一代大家,但“嫌其痕跡太露,筆筆相同,為李書之疵病。然波折由停頓而生,尚未至於醜怪,今則學之者,專學其蜿蜒之形,而忘其停頓之勢,棄本求末,自鳴得意,余不知其可也”。筆者認為這對李氏的評價較為中肯。碑派書家以蒼茫、生澀來表現金石氣,到了
李瑞清則以顫抖作為對金石氣的追求,並成為一種程式化的表現,這未免顯得過於做作和誇張。
李瑞清並非生來就有刻意抖動形成鋸齒狀的毛病,這也許與其晚年頻繁的商業應酬有關,也許與其想開闢新的書風,從而光耀“李派書法”有關,他也並不是目無二王一路的書法,曾臨摹過大量的帖派經典,並自撰題跋,如:右軍《別疏帖》、大令《送梨帖》、《郗鑒帖》、《淳化"張芝帖》、《淳化"大令書》、
歐陽詢《張翰帖》、褚摹《蘭亭序》、顏魯公《告身》、《陰寒》諸帖、楊凝式《韭花帖》等,從題跋來看,其猶喜黃山谷和趙子昂,在臨山谷《題幾》、《書闥》、《發願文》三帖後跋云:“魯直此書,無一筆不自空中蕩漾而又沉著痛快,可以上悟漢、晉,下開元、明”,給予了高度評價,臨子昂《與勉甫札》、《淨土詞》二帖後跋:“晉唐而後,此為大宗”,由此可見,李氏對於帖學經典也曾下過不少功夫。應該說,他的帖學功底對他的碑派書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他的學生馬宗霍在《霋岳樓筆談》中評其“自負在大篆,而得名在北碑”,所評甚確,他的書法面貌是以北碑面貌出現的。
李瑞清與
曾熙同是
張大千的老師,兩人並稱民國書壇巨宗,且都好懸腕作抖筆狀,而作書從來不懸腕的錢名山(
謝稚柳之師)則不以兩人書法為然,認為李、曾二人以顫筆為勢,只不過是驚駭世俗而已,並不能稱作
書家,可見當時就有人對其提出批評。1996年,
陳振濂在《現代中國書法史》中較多地關注了
李瑞清的“顫筆書法”,在文中這樣談到:“從我們的立場上說,只能以他在近代史上最負盛名的書風(也許並不是最成功的)作為主要評判對象——我們評價的是他的歷史作用而不僅僅是他個人的高度。”他以其獨特的思維方式,較早地對李氏顫筆書法形成的原因作了討論,闡述了李氏和
吳俊卿、沈曾植等人的關係,並認為“李瑞清能從北碑中抽取出一個很合乎邏輯但卻實在不算高明的鋸齒形線條作為基本語彙,至少也表明他在對北碑書法進行詮釋方面具有某種特殊的啟發價值,這是一種可以生髮的價值,特別是在與吳昌碩、沈曾植、康有為等成功者相比時更是如此。”由此可見,李氏唯一的價值在於他的探索精神,雖然探索並未成功,但至少能給後人一些啟發。
三、碑學末流的負面影響
帖派在清代前、中期沒有較大的發展,這就給碑派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先決條件,所以康有為說“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碑派的價值在於豐富人們的審美,拓寬人們的視野,為書法的發展走出了一條前人並未走過的路,但當人們拚命將注意力集中於北碑,把北朝無名氏刻工的字奉為經典,這便有悖於書法藝術的客觀規律了,帖派在千年書法史上一直都是獨領風騷,人們也一直將
二王奉若神明,也許帖派的衰微真與刻帖的泛濫有著某種必然的因果關係,但刻帖不管如何嚴重得失真,畢竟還是書法經典的翻刻,而北碑所謂的“金石氣”是因千年的風霜侵蝕而顯現,難以與二王相提並論。
所謂碑學末流,就是指清代碑學的餘緒。
李瑞清的書學思想是順應他所處時代的,因為這是一個碑學盛行的時代。他企圖以碑入帖,自出新意,融諸體於一身,但到最後卻並沒有把晚清碑派引入光明大道,反而誤導了學書者。
李瑞清以其出眾的學識和書法才能,理應有一個很大的成就,但他以其程式化、規律化的“鋸齒形”為藝術語言,誇張顫抖、一意賣弄、矯枉過正、棄本逐末、走向極端,這種顫抖的語言極為簡單化,有規律的顫動,並機械地排列,缺少豐富的變化,他的這種奇特的創作引來商賈們讚嘆的同時,卻遭來同行們的不予認可。雖然他的探索為後世很多書家所詬病,但在他以後以顫抖表現金石氣的觀念也影響了不少人。這也違背了碑學的初衷,他在刻意表現金石氣的同時,愈來愈明顯地扭動筆桿,重複這種簡單的動作,導致晚清碑學從多元走向單一,人們的審美也在進一步發生變化,以致於書壇越來越走向窮途末路,晚清碑學末流的弊端也由此顯現出來。
晚清碑學末流除
李瑞清外,和他同時的還有他的朋友
曾熙、鄭孝胥、沈曾植等人。
曾熙(1861—1930),字嗣元、號季子,湖南衡陽人,其在書法上取法廣泛,商周金文、漢代隸書、南北朝碑刻等都有所臨習,於《張黑女墓誌》用功最深,他的北碑式作品大都平庸,行筆過程中也曾加入細微的搖動波折,用筆遲澀,同樣的程式化與
李瑞清如出一轍。其晚年與
李瑞清一同在上海以賣字為生。他們的學生
張大千的楷書作品也一度以顫抖作為對金石氣的追求,可見他們的影響還是很深的。
鄭孝胥(1860—1938),字太夷,號蘇戡,海藏,閩侯(今福建福州)人。鄭氏平生對何紹基的書法佩服有加,曾有詩云:“目中有蝯叟,他書不能觀”,並對北碑用功頗勤,從《始平公造像》、《楊大眼造像》等石刻中汲取營養,其過於誇張和強調用筆的頓挫未免顯得單一,字形變化也不夠豐富。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號巽齋、乙庵等,浙江嘉興人。沈氏初以晉唐法帖為宗,任官後,受朋友影響,養成收藏金石碑版的習慣,書法實踐也從帖轉向碑,他折服於包世臣的“安吳筆法”,並在包氏基礎上進一步發揮與強化,執筆作書時而盤旋飛舞,時而翻折跳蕩。據其弟子
王蘧常回憶,沈氏作書下筆力量很重,有時甚至筆管倒臥於紙上,生澀而有頓挫的用筆並未給其帶來古樸的效果,反而給人以做作之感。
清代碑學從金農的“不學
二王”,阮元的公開號召,到包世臣、康有為的借題發揮,將宋、元、明帖學全盤否定,清代碑學的負面效應也因此而顯現出來,人們專注於北碑風格特徵的同時,也將它的缺點和弊端不斷放大。從
李瑞清等人的作品可以明顯感受到,他們對碑派書法審美原則的把握和發揮已達到不遺餘力,乃至誇大的地步,真正實現了“以醜為美”,在實踐上拋棄
二王,在理論上離經叛道,導致書法審美觀念上的誤區,康有為在晚年已注意到這個問題,企圖“碑帖融合”,在這種背景與局勢下,李瑞清等晚清碑學末流更加誇張的表現只能給書法帶來負面影響,導致整個書法傳統出現斷層。如今,碑學理論和碑派書法勢力的強大,也使其顯示出更大的包容性和泛化趨勢。隨著甲骨、簡牘的大量出土和敦煌寫經的發現,碑派的取法對象也在不斷豐富,碑帖融合的創作模式也在不斷拓展,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書壇百花齊放的局面將會帶給當代書法欣欣向榮的希望。
參考文獻
[1] 李瑞清,碑帖跋語,中國教育報,2001年6月5日第8版
[3] 劉恆,中國書法史,清代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
陳振濂,現代中國書法史,河南美術出版社,1996年版
[5]
金丹,經學與阮元書學思想的淵源,書法研究,2003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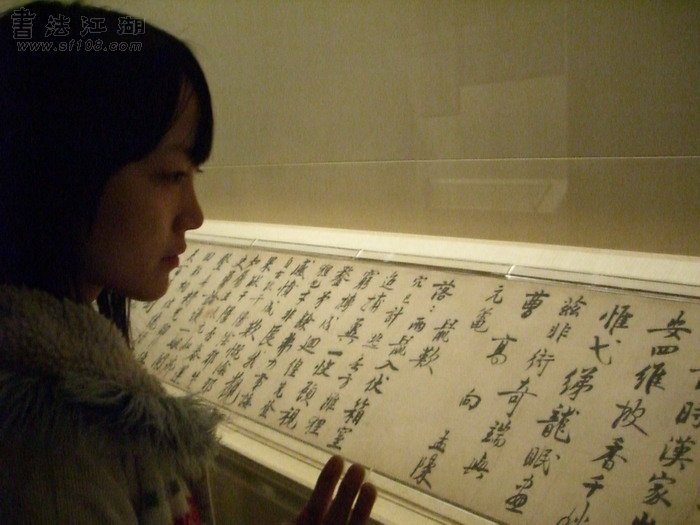 上博“晉唐宋元”國寶展
上博“晉唐宋元”國寶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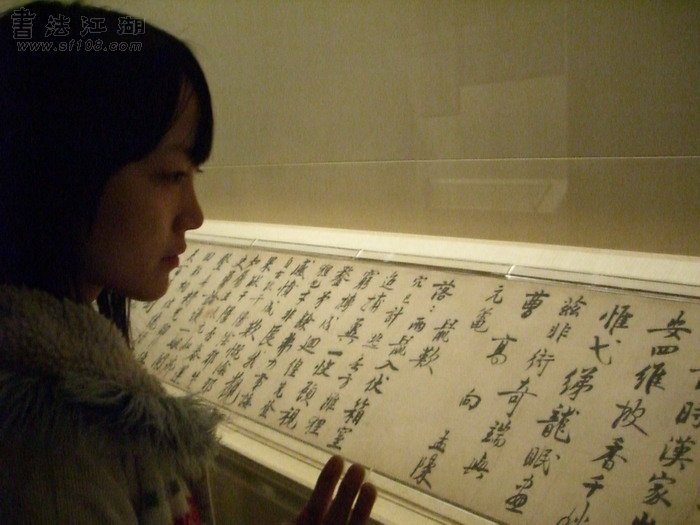 上博“晉唐宋元”國寶展
上博“晉唐宋元”國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