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是1981年廣西師範學院教材科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黃現璠。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
- 作者:黃現璠
- 出版時間:1981年10月(上編)、12月(中、下編)
- 出版社:廣西師範學院教材科油印
- 頁數:367 頁
- 類別:歷史,人文科學
- 開本:787×1092 1/16
- 裝幀:平裝
內容簡介,創作背景,問題提起,問題發展,成書背景,成書過程,推出過程,指導原理,內容提要,中國先秦社會,古西亞,古印度,古希臘羅馬,新穎史觀,撰著意圖,圖書特點,論述風格,意義,社會影響,內容摘介,注釋,
內容簡介
《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一書為著名歷史學家黃現璠教授在其相繼發表的《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1979年)、《試論奴隸社會並非階級社會首先必經的歷史階段兼論商朝不是奴隸社會》(1980年)等長篇論文基礎上大幅補充完善的成果,於1981年10-12月由廣西師範學院的油印公開推出。它是20世紀中國古史分期討論中主張“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第一本專著,凝結著作者學術生涯中經歷的苦難血淚,堪為“無奴學派”創始人黃現璠的“新史學”在改革開放新時代下的重放光彩。
創作背景
問題提起
中國歷史有無奴隸社會的問題,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在中國學者當中引起了爭論。最早認為中國歷史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的學者有可能是陶希聖,但是不久他又改變了自己的主張,認為中國歷史經歷過奴隸社會。而針對郭沫若先生同時期主張中國歷史經歷過奴隸社會的史觀,陳邦國、李季、劉興唐、李立中、王瑛、王斐蓀、陳獨秀等學者相繼撰文反駁,否定中國歷史存在奴隸社會。 由於論戰雙方沒有一位史學專業者,加之傳統正宗史學家對於中國歷史有無奴隸社會以及古史分期問題一直不感興趣,皆未參與。這種論戰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而逐漸歸於沉寂,爭論的結果,中國古代史上有無奴隸社會的問題並未得出任何明確結論。[1]
問題發展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隨著馬列主義歷史唯物論普行於世,郭沫若當年提出中國歷史經歷過奴隸社會的“有奴論”成為了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政治信條”。正如李學功指出:“從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討論來看,絕大多數學者都對‘中國歷史上經歷了一個奴隸社會發展階段’堅信不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相信這一點,即中國不能沒有奴隸社會,已成為幾代中國學人堅定不移的信念,一種難以解開的情結……”。[2]加之,以郭沫若為首的“三論五說”的五大家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長期主導著主流史學思潮,他們又與上層意識形態關係密切,馬克思主義五個階段論於是成為了當時中國史分期的最基本方法。黃現璠於1957年6月出版的中華民族史上第一本簡略通史《廣西僮族簡史》中說:“唐以前和唐末宋初,僮族的社會是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抑是氏族部落社會,值得提出研究。依漢族社會發展史,由氏族部落社會,經奴隸社會,進到封建社會。但社會性質的決定,應該根據社會生產力、經濟、政治等發展的實際情況而定,不能公式化機械的硬套。唐以前和唐末宋初,認為僮族社會是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文獻上都沒有記載,惟有氏族部落社會尚可由各方面材料加以推斷。”[3]可說黃現璠是新中國成立後最初挺身而出反對“有奴論”的第一位學者。這種反對之聲事實上早在此前的“大鳴大放”期間已初露端倪。1957年春的“大鳴大放”期間,黃現璠以全國人大代表和中央民委委員身份在廣西各縣視察工作和作報告時便談到了諸如此類的主張,公開反對將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以及史學界流行的公式化生搬硬套作風,反對“大民族主義中心觀”,明確提出了僮族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階段的“社會發展跳躍論”。[4]同年7月,史學家雷海宗發表《世界史分期與上古史中的一些問題》一文,文中主張:“馬克思稱鐵器時代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階段。我們認為馬克思的判斷,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也沒有理由予以懷疑,新資料的積累只足以更加強馬克思的判斷,唯一的問題是名稱的問題。我們今天知道這是普遍全世界的一個大時代,並非亞洲所獨有。仍用馬克思的原名而予以新的解釋,也無不可。但如可能,最好是另定新名。無論如何,早期奴隸社會一類的名稱是難予考慮的。一個名詞必須有確定的含意,此時若稱奴隸社會(儘管是“早期”),奴隸社會一詞定又必須重訂,更不必說所謂奴隸社會問題本身尚有問題了。”[5]雖然雷海宗於文中並沒有直接談及中國歷史有無奴隸社會問題,沒有明確否定中國奴隸社會存在論,但對“奴隸社會”一詞以及用“奴隸社會”名詞來代替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提出了置疑。同年10月,李鴻哲接著發表了《“奴隸社會”是否社會發展必經階段?》一文,公開置疑主流史學定為一尊的“有奴論”,最後得出結論:“奴隸社會說在理論上站不住腳,不符合歷史事實,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多年來為人所信從,實在是一種教條主義的偏向。但這一種教條卻不是從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得來的,它是由郭沫若先生、斯特魯威院士等提倡起來的。由於這一種教條的存在,蘇聯和我國史學家們曾花費很多力氣在古代各國歷史上找尋奴隸。假若奴隸社會說本身根本不能成立,那么這些工作和爭論皆非徒勞無功!”[6]這些文章發表後,史學界尚未來得及回應,黃現璠、雷海宗、李鴻哲三人相繼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黃現璠因“地方民族主義者”和“史觀反動”等多項“罪名”,被錯劃為歷史學界“頭號大右派”。從此之後,“費孝通、黃現璠、吳澤霖、林里夫等右派分子的反動理論再也沒有市場了。”[7]雷海宗因“宣揚馬克思主義停滯論”、“史觀反動”等多項罪名,被錯劃為史學界“名右派”,含冤於1962年病死;李鴻哲同樣以所謂“反馬克思主義”等罪名被錯劃為“右派”。[8]勇於衝鋒陷陣踏“雷區”的黃現璠、雷海宗、李鴻哲,不是被“炸得”傷痕累累,就是被炸得面目全非,重傷者最終家破人亡。

本書內容摘要
成書背景
李洪岩研究員曾明確指出:20世紀30年代中國有無奴隸社會的“論爭的價值和意義,本來應該在於加深人們對中國歷史特點和社會結構的認識,但不幸的是,由於政治性的原因,它卻成為了意識形態交鋒的一個戰場。這種學術與政治夾雜在一起互動為用、相互論證的局面,雖然使得論爭無法在純然學術的語境中進行,但在當時卻是無法避免的。然而更加可嘆的是,在幾十年的時間段里,奴隸制問題不但沒有轉入正常討論的軌道,反而成了雷區和禁區。學者們惟一所能做的,就是論證奴隸制的普遍性。”[9]這是新中國成立近30年中史學界存在的普遍現象,但是尚有個別例外,例如黃現璠先生於1962年春剛被“摘脫右派分子帽子”不久,再次勇敢地挺身而出,連續推出《儂智高起兵反宋是正義的戰爭》、《土司制度在桂西》兩篇長論文,他於文中從少數民族史出發,徹底否定了中國“奴隸社會存在論”。黃現璠於前文中認為:“相買為奴,時代甚古,蓄奴之多,甚至萬人數千不等。我們能說戰國時呂不韋、繆毒所處之秦是奴隸社會嗎?又能說明代的吳中(江蘇)也是奴隸社會嗎?”[10]接著他於後文中主張:“領主制封建社會之構成,有些在奴隸社會崩潰之後,有些在氏族部落社會的基礎上,這要看具體的各個社會歷史發展情況而定,不能一般的公式化硬套。馬克思的經典著作,對此記載很多,即在《資本主義生產前各形態》一書已一再提及。所以,學術主張,理應百家爭鳴,不能隨便戴上違反馬列主義或不符合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高帽。看過馬克思著作的,首先應該認同這一點,始好討論問題。桂西土州縣在儂智高起義前,不是奴隸社會,而是氏族部落聯盟社會。”[11]文中明確反對將科學化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公式化,公開反對史學界一些“風派”人士肆意給人戴上“反馬列主義”、“反社會主義”和“資產階級史學”高帽的“一言堂”作風,強烈呼籲“學術主張,理應百家爭鳴”,堅信不移地主張壯族歷史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始終不渝地倡導“奴隸社會跨越論”。“眾所周知,60年代,正是我國民族學界‘禁區’森嚴壁壘,‘框框’層出不窮,民族學研究稍有越‘雷池’一步就‘帽子’橫飛,所謂‘研究社會科學危險,研究民族學就更危險’盛行於世的時期。我(指黃現璠——筆者按)不怕又戴上‘政治帽子’而敢於‘闖禁區’、‘跳火坑’的膽識,絕非源於對自己曾被劃為右派的‘結果不滿’,而是完全出於自己終身信仰的‘治學貴疑辨誤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以及對於學術界一些‘鄉曲之士’觀點的深感不滿。”[12]
1957年《廣西僮族簡史》出版後,由於黃現璠於書中提出壯族“無奴隸社會論”,結果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而上述兩篇長論文發表後結果如何?按黃現璠回憶文章所言:“事實上發表這兩篇論文時我曾考慮再三,主要擔心再受政治迫害而禍及家人。不料,政治迫害沒有降臨頭上,只是‘文革’批鬥中多了一項莫須有罪名而已。當時的紅衛兵小將在一些人的指使下猛批我‘學術上反攻倒算和死不悔改’,從而對我拳打腳踢,四次遭人毒打,兩次被人一腳踢昏,批鬥、遊街、掛牌戴高帽示眾、掃廁所掃大街的屈辱經歷自然再所難免。當時我已高齡近70,僅憑一股死不甘心的頑強毅力和自少喜歡從事運動的良好體質撿得一條性命。”正如美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傑弗里·G·巴羅以及加利福尼亞大學史學教授喬治·V·H·莫斯利相繼指出:“傳統觀點認為:一切社會的發展都不可抗拒地從氏族社會到奴隸社會,然後從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按照這種看法,壯族在宋以前屬於奴隸社會,因此,他們不可能有國家……壯族學者黃現璠曾被公認為壯族史學老前輩,他令人信服地提出自己的觀點:傳統理論不適合解釋壯族社會。”[13]“為這個觀點他屢遭抨擊。”[14]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博導教授冢田誠之同樣指出“黃氏(指黃現璠——筆者按)認為壯族社會的發展階段系從氏族社會直接進入初期封建社會,轉折起點始於唐宋時代,從而掀起了圍繞古代壯族社會性質的論爭。他主張原始氏族部落未經過奴隸社會而直接進入了封建社會。”[15]反右運動中,黃現璠教授之所以遭到持續不斷的猛烈批判,皆與他的這些民族史觀關係密切。祝中熹教授亦說“長期以來,五種生產方式的理論,被認為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定則,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因此,解放後的中國,懷疑奴隸社會的普遍性,往往要以犧牲自己的政治生命作代價。”[16]祝先生所言最後幾句用在黃現璠身上再恰當貼切不過。由黃現璠史學體現的追求真理執著精神孕育而出的《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一書,凝結著作者學術生涯中經歷的苦難血淚,這是顯而易見的。
成書過程
1954年9月,黃現璠到北京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時,“帶著疑問拜訪了郭沫若先生,試圖進行探討,見面後郭氏對他說:‘璠弟,我送您一本新版自著《奴隸制時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第1版),回去仔細讀讀,我的主張過去無人駁倒,今後更是無人能駁倒。’黃老回桂後不看則罷,仔細讀來更是疑問重重,閱後第一想法即是重操舊業,精研馬列,進行挑戰。繼而托思於文,邊學邊寫”,[17]1955年10月3日完成論文初稿,題名為《我國古史分期應該重新估定》;二稿論文改定於1974年5月8日,題名為《我國歷史分期必須重新估定》;三稿論文改定於1976年3月2日,題名為《我國古代史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四稿論文改定於1977年12月6日,題名為《中國古代史沒有奴隸社會初探》;五稿論文改定於1978年11月30日,題名為《我國古史分期應該重新估定——古代沒有奴隸社會》,1979年論文發表時是第六稿,題名為《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18]每稿都有修改、題名不一,內容變動程度不同。黃現璠在這些論文的基礎上,大幅補充完善,撰成《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一書。
推出過程
1978年11月,黃現璠的舊友費孝通教授和同鄉吳西將軍應邀來廣西出席“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20周年大慶”時,兩人專程到桂林分別至黃現璠自宅探望,黃現璠將《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長篇論文交與他們,托他們回京後能推薦給京城的學術期刊發表。同時,他還寄給了舊識、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劉瀾濤,劉瀾濤熱心地推薦給北京多家學術期刊。結果無一家學術雜誌敢於刊登,甚至連黃現璠所在學院的學術刊物主編讀後亦直言“寫的很好但不敢發表”。1979年4月,黃現璠應邀參加由國家民委和中國社科院民研所聯合在雲南昆明舉辦的“全國民族工作規劃會議”,他將文稿列印200份帶去會上廣為散發,期望到會的眾多學術期刊代表能夠重視和予以發表,結果失望而歸。[19]至到同年6月,經本學院副院長覃宏裕力排眾議甘願承擔責任力薦給該院學術刊物後始得以揭刊連載。論文發表時黃現璠的右派冤案尚未徹底平反昭雪(同年8月始平反昭雪)。為此,論文發表後馬上召來了一些“偽學者”的惡毒攻擊,甚至個別人還寫信給自治區黨委和中央統戰部,反映黃老的所謂“20餘年來一貫頑固不化死不悔改”的政治動態,甚至偽造“民眾意見,建議不要給黃現璠的右派問題平反。”黃現璠當時聽後憤而說道:“當今之世,學術上的‘凡是派’尚受政治上的‘凡是派’影響,所謂‘雙百方針’,不過是一句口頭禪。發現問題不予指出,人云亦云,眾口一詞一調,以他人之見為己之見,什麼都“自古以來”,張口“五種生產方式論”,閉口“五種社會形態說”;動筆“馬列導師語”,落筆“政治領袖說”,作為學者,哪您還研究什麼?”同時又說:“自馬克思主義傳到我國,對於它的不同理解自然應運而生。一些中國歷史學者,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早期傳播者當作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中國代言人’,將他們的言論當作‘聖旨’,視為‘祖師爺遺教’,甘當學術界的‘凡是派’,甘當教條主義史學的‘奴隸’,這是中國封建專制時代傳統奴性思維的遺毒在當代史學界的典型反映。因而這些人認為中國歷史經歷過奴隸社會,自然不足為奇。”[20]由此可見,作者當時發表這樣的學術論文十分艱難,需要相當的勇氣,今天史學界對這些學術問題能夠暢所欲言的良好形勢,正是黃現璠等學界真壯士不顧政治風險勇於開拓而逐步打造出來的。黃現璠當時已年高81歲,自然不再怕死。有鑒於這樣的學術論文發表四處碰壁,為了避免給期刊和出版社增添政治風險和帶來麻煩,黃現璠甘願自己承擔風險,將在此前撰寫和發表的一系列相關論文基礎上補充完成《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一書,上編完成於1981年9月,同年10月委託所在工作單位廣西師範學院油印成書後公開推出,同年12月又推出中、下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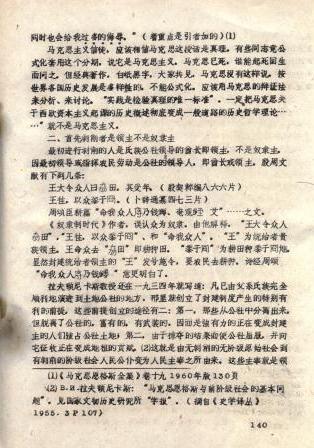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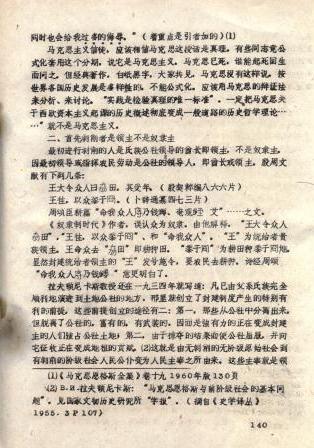
本書內容摘要
指導原理
作者坦陳本書以歷史辯證唯物史觀為導向,書中借用了馬克思有關歐洲古代社會形態論述的一些術語和概念來分析中國先秦社會形態。但是,作者並不認為馬克思有關歐洲古代社會形態的一些觀點和主張完全適用於解釋中國先秦社會形態,反對將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歷史觀念全盤機械化地照搬套用於中國先秦社會研究,明確主張作為歐洲人的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古代史的了解和認識存在局限,他們對20世紀初期考古出土並有助於說明中國先秦社會形態的甲骨文、金文的史料一無所知一竅不通,因而作者並不認為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歷史原理具有世界普遍適用性及其普遍法則的價值。作者完全否定將史達林誤讀馬克思主義原理而自我造出的“五種社會形態”套用於中國古代社會的教條主義,強烈反對將馬克思主義學說當作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而使其教條化、庸俗化並進而發展成背離歷史辨證唯物主義原理的假馬克思主義化。作者於書中反覆強調在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研究中客觀地運用馬克思歷史辨證唯物主義原理的重要性。
內容提要
全書共分三篇17章,構思於20世紀50年代,完成於1981年12月。作者於書稿中運用中國傳統訓詁學和西方歷史語義學的方法,立足於文獻、古文字研究和考古學成果,深入系統地考證了中外“奴”詞及其由它衍生而來的相關詞組“奴隸”、“奴婢”、“奴僕”、“農奴”等世界性術語古來的不同詞義及其所包含的歷史、社會、經濟和文化內涵,同時解析了由這些術語演變而來的“奴婢制”、“農奴制”與“奴隸制”的區別以及它們在近代後如何嬗變為社會形態史的中心概念並滲透於中國現代古史研究的背景原因和過程,嘗試解明世界文明古國大多未經歷過奴隸社會的實態,旨在恢復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中被“階級鬥爭史學”摧殘得面目全非的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的本來歷史面目。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歷史啟迪意義, 適合國內外的中國歷史研究者、學習者閱讀和使用。
具體而言,本書論述內容大致分為如下幾個方面:
中國先秦社會
作為本書的重點,作者於書中反覆強調中外“奴”之組詞繁多,尤以古漢文為甚,作者在“奴隸定義”一節中指出:所謂“奴”,按《辭海》解釋即指喪失自由,受人役使的人。就其屬性而言,奴有公奴(國奴)與私奴之別;就其性別而言,奴有男奴與女奴之異;就其時間而言,奴有短期奴、長期奴、無期奴(世襲奴、世代奴)之差;就其時代而言,奴有原始奴、古代奴、古典奴、中世奴、近代奴之分;就其內容而言,奴包括奴婢、奴僕、奴才、奴隸、奴客、農奴、礦奴、劍奴、典奴、家奴、田奴、牧奴、黑奴、亡國奴……等。至於中國古文獻記載的古代社會中的象奴、奚奴、乾奴、徒奴、頑奴、騷奴、鬼奴、獠奴、戶奴、賤奴、鮫奴、崑崙奴、蠻奴、矮奴、儜奴、瘖奴、傒奴、俠奴、官奴、豪奴、桀奴、騶奴、髡奴、騷達奴、鈐奴、忤奴、從奴、傭奴、人奴、閹奴、大奴、小奴、譂奴、禿奴、顇奴、番奴、耕奴、胡奴、倭奴、騎奴、鉗奴、柔奴、僮奴、髯奴、卒奴、仙奴、傖奴、嬖奴、丁奴、監奴、囚奴、黃頭奴、家生奴、郗家奴、玉川奴、常住奴、小奚奴、潑奴胎、奴胎、奴兵……等對人的貶稱或蔑稱,更是不勝枚舉,不一而足。顯而易見,我們不能將這些“奴”皆以“奴隸”代之或一概稱之,“奴隸”只屬“奴”中之一種,將其作為“奴”之代稱或總稱,當屬無視學理的淺薄之士的淺慮淺見淺識,真學士對此向來不以為然而不會為其所惑。
作者運用大量甲骨文、金文和古文獻史料對“奴”詞及其相關詞組“奴婢”、“奴僕”、“農奴”、“奴隸”進行了逐一深入辨析,特別對甲骨文中“奴”字的本義和引申義進行了詳細分析和論證,斷言中國古文字中最早出現的甲骨文“奴”字的本義和引申義與“奴隸”之義無關。作者同時對主張奴隸社會存在論的眾多學者們將“人”、“民”、“眾”、“眾人”張冠李戴胡解為“奴隸”的教條主義異端邪說進行了入理至深的論辨和批判。作者通過對古文字之“奴”、“隸”、“仆”、“孚”、“人”、“眾”、“民”、“工”、“農”、“兵”、“庶”、“鬲”、“臣”、“宰”以及相關詞組“奴婢”、“奴僕”、“農奴”、“奴隸”、“奴婢制”、“奴隸制”、“農奴制”、“生產工具”、“土地私有制”、“殉葬”、“奴隸數量”、“家庭奴隸”、“戰爭俘虜”、“奉公制”、“上貢制”、“貢助徹”、“父權家長制”、“奴隸社會”的剖析以及對先秦三代社會形態的具體分析,最終得出結論: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
作者認為: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中國史學界不存在真正的馬列主義史學家,因為大家都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研究問題,沒有任何人發展了馬克思的歷史辯證唯物主義。作者進而認為:眾多主張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的學者們似乎表面上習慣於對馬列主義學說“引經據典”,事實上他們大肆宣揚的是“史達林式”的偽馬克思學說。因為他們很少涉及馬克思主義對“奴隸”的定義,從不對“奴”之種類加以任何明確的分類和定義,只是拿著一個空洞無物甚至連科學概念都談不上的“奴隸”名詞往先秦史上肆意亂套,從而以三人成虎式的“層累疊加法”偽造出一個“奴隸社會”邪說,以達到“三人成虎事多有,眾口鑠金君自寬”的政治效應,以為自己的偽馬克思學說坐實史事支撐而妖言惑眾欺世盜名。作者認為:以這種入主出奴思維和偽馬克思學說為基展開的長達幾十年的以往“中國古史分期討論”,儘管在局部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它們從中宣揚以階級鬥爭理論為綱的邪教謬論所造成的教育和學術危害遠遠大於那點局部成果。這種偽造歷史的階級鬥爭邪教“史學”,完全背離了嚴謹的歷史科學,背離了科學化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因而以往“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研究成果總體上大多可以歸為唯心主義史學或階級鬥爭邪教偽說。作者宣稱,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只有歷史辨證唯物主義可取,其具有科學性,其他方面已經過時,而中國的假馬列主義史學及其成果大多是偽說和偽史,應該扔進歷史的垃圾熔爐,來一次“焚書坑奴”,以免偽史學危害後學。
古西亞
作者通過對古西亞的圖符文字、楔形文字中有關“奴”詞的精細考證以及對古代法典相關條文逐一分析,得出了古代蘇美爾、巴比倫、亞述社會中的“奴”大多屬“奴婢”和“農奴”而非“奴隸”的結論。作者認為,新中國成立後至改革開放前之所以在中國史學界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幾乎眾口一詞認為古代蘇美爾、巴比倫、亞述社會為奴隸社會的錯誤主張,完全源於全盤吸收蘇聯學者的觀點以及對楔形文字的牽強附會誤譯所致。作者在肯定林志純(筆名日知)、童書業、周一良、吳於廑、劉乃和等學者有關世界古代史研究所取得的豐碩成果的基礎上,同時指出了他們對楔形文字中一些有關“奴”詞和法典條文的誤譯誤解,例如作者在書中上編“蘇美爾‘奴’”一章中明確指出:
流行於世一版再版的《世界通史資料選輯》(上古部分)一書關於《利皮特·伊蘇塔爾法典》第十五條是這樣翻譯的:“倘米克圖為國王所贈賜, 則不得奪取之。”譯者在“米克圖”後加註解說:“米克圖, 為一種依附之人, 在公元前三千年代之公文書中常可見到, 而在二千年代初之公文書中, 則以此法典第十五條及十六條所提及者為其罕有之記載。顯然的, 國王可以將此等人賜與私人, 到了這時, 米克圖便不能離開自己的主人。而成為事實上之奴隸。”〔原文注42〕編者並未列出楔形文字原文,而這條蘇美爾語楔形文字原文的拉丁化寫法是這樣的:“tukum-bi mi-iq-tum nig-ba-lugal-kam nu-ub-da-an-kar-re”。所謂“米克圖”,即為文中的“mi-iq-tum”(即miqtum或 miqtam),英文譯為“servant”(僕人, 傭人,雇員, 公務人員)。即便作“僕人”解,也不致於列為“奴隸”之列,因為這類“僕人或傭人”擁有人身自由,同法典第十六條已說得很明白:“倘若米克圖自己來到自由民之處, 則此自由民不應將彼強留, 而應聽彼去所欲往之處。”(tukum-bi mi-iq-tum ni-te-a-ni-ta lu-uun-ši-gin-lu-bi nu-un-tag-tag ki-ša-ga-na-še ḫa-ba-gin)〔原文注43〕所謂“米克圖便不能離開自己的主人”之言實不知從何說起。擁有人身自由者也叫奴隸,普天之下還有“人”嗎?
作者於書中在這方面的舉證論辨之處甚多,不一而足。作者認為,以往中國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和翻譯中很少根據第一手楔形文字資料,大多根據俄文,加上為滿足時代的意識形態所需,因而對楔形文字中的“奴”詞以及古西亞法典條文中的誤譯誤解誤導不乏其數。作者認為,《漢謨拉比法典》中沒有“債奴”一詞,可是卻被一些中國學者譯成了“債奴”,進而理解為“債務奴隸”,再斷章取義或捕風捉影地偽造出一個所謂的“債務奴隸制”,以便將古巴比倫的社會性質定性為“奴隸社會”。這是中國主張奴隸社會存在論的學者們為滿足時代的意識形態慣用的手法,應該予以揭示和批判。作者關此經過數萬字的詳細論證後得出結論:楔形文字中的“奴”詞大多指“奴婢”、“奴僕”,而非“奴隸”。古西亞諸法典中明確指涉“奴”義的詞語皆義指“奴婢”、“奴僕”而非“奴隸”。作者認為,古西亞社會存在的少量外族戰奴、宮奴形同畜產,幾乎沒有資格被記入“法典條文”,能被記入“法典條文”受到諸多制限和作為弱勢階層受到法律一定保護的只有作為王宮貴族重要私人財產的“奴婢”或“奴僕”。因而作者最後主張,古代西亞沒有奴隸社會,中國當代所有主張古西亞社會經歷過奴隸社會階段的學說,都是將馬克思主義學說教條化地套用於古西亞社會以及脫離楔形文字原文而對相關“奴”詞肆意曲解的誤識,不足為憑為據為信。作者還通過對蘇美爾社會階層的具體分析以及將其與中國夏代社會階層的比較研究,認為興起於50時代的西方酋邦理論並不適用於解釋中國先秦社會,這是因為夏代“氏國”與蘇美爾“城邦國家”具有政體或國體上的本質區別。
古印度
作者運用印度、英美、日本學者對古印度的研究成果,通過對古印度象形文字的簡明介紹,斷言迄今為止考古發現的古印度象形文字中無“奴”字,並結合考古出土文物從一側面旁證了古印度沒有奴隸社會。同時,作者通過對《摩奴法典》中有關的“首陀羅”條文進行了逐一分析和長篇大論的論證,並對“首陀羅與希洛人”進行了比較研究,對梵文“dāsa”一詞進行了詳考,作者認同季羨林先生主張的四個種姓“同色論”,但反對以其為代表的古印度存在奴隸社會論。作者最後得出結論,首陀羅絕非奴隸,古印度社會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中國當代所有主張古印度社會經歷過奴隸社會階段的學說,都是對馬克思主義有關印度論述的曲解以及對首陀羅族裔認識的無知和社會地位的誤識,不足為憑為據為信。
古希臘羅馬
作者通過對“線形文字B”和荷馬史詩等史料的分析,大致論證了古希臘邁錫尼社會的等級。同時運用大量的外文文獻,對中國學界熱心爭論的“希洛人”是農奴抑或是“奴隸”的問題進行了希臘文詞源的詳考,對希臘文“Eίλώς”(隸屬民)一詞的“本義”和“引申義”進行了詳細分析,列舉了中外學者對“希洛人”的不同解釋。作者在肯定林志純、劉乃和等學者關於古斯巴達社會和希臘古典時代的研究學術成果基礎上,同時通過細緻分析指出了其在“希洛人”定性上將“ Eίλώς”與“Eλoς”混為一談的先入為主之見和誤識,並對郭沫若先生關於“希洛人”論述所犯的常識性錯誤予以了指出。作者還考證了希臘文“μοθων”、或“μοθακες”的詞義以及對斯巴達社會、雅典社會的階層進行了分析,最後得出結論:“希洛人”是農奴,絕非奴隸;古代斯巴達沒有奴隸社會,古雅典只有“受奴役債務者”,沒有“債務奴隸”和“債務奴隸制”。作者主張,古希臘羅馬早期沒有奴隸社會,後期少數幾個城邦中存在的大量俘奴、劍奴所呈現出的“奴隸制社會”性質,是否能代表當時數百個古希臘羅馬城邦的社會性質,尚有待深入研究討論的必要。作者認為,20世紀後大量考古新成果的問世,從多方面證明了19世紀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歐洲古代社會的認識存在局限,應該予以重新評價。
新穎史觀
作者於書中對“奴婢”、“農奴”、“奴隸”加以了具體定義和概念區別,同時將古代社會的“奴役制”區別為“奴婢制”、“農奴制”、“奴隸制”,並對“家庭奴隸制”進行了深入探討。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可以說是古代社會奴隸制問題的延伸,而且是以往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陣營的學者們長期熱心探討的重大理論問題之一。作者於書中主張:亞細亞生產方式是一個社會經濟範疇的名詞,不是歷史時代排列固定的先後的用語,不能將其等同於原始社會或奴隸制社會形態。在世界各國學者關此問題的大量論爭中,作者最早提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經濟範疇說”,並為此作了長篇大論,堪為史觀新穎又獨樹一幟。作者在對先秦三代社會形態展開分析後明確主張:中國古代史的發展演變軌跡應該是從堯舜時代的“族國”→夏禹時代的“氏國”→殷商時代的“城國”→周代的“王國”→秦代的“帝國”這樣一個演進過程;與此相適應的經濟制度為“奉公制”→“上貢制”→“貢役制”→“貢賦制”→“賦稅制”;與此相適應的社會組織形式為“氏族公社”→“部落公社”→“地域公社”→“農村公社”;與此相適應的社會形態為“原始社會”→“上貢社會”→“領主封建社會(雛型)”→“領主封建社會(典型)→“地主封建社會”。作者認為,所謂“農村公社”、“領主封建社會”,都是馬克思學說的術語和概念,只有運用這些概念與主張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的學者們展開論辨,方能揭示出其偽說和誤識。作者同時認為,倘若不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抽象概念和社會形態論而根據中國古代的客觀實態,那么,中國古代的國家應是“族國”→“氏國”→“城國”→“王國”→“帝國”這樣一種演變之跡,其中的“氏國”→“城國”→“王國”皆具有部落聯盟制國家的特質,而與此相適應的社會應稱為“氏族社會”→“封建社會”。作者對此進行了詳論,闡明了其區別所在。這是作者早年(1950年)在“中國殷代社會史”一書中已經提出的史觀,在本書中又進行了完善,對中國古代國家形態作出了科學的分析論證和總結。堪為史觀新穎又史無前例,作者完全否定了一些學者以考古學界的“古國”概念來概括中國古代國家形態的認識,認為這是思慮極淺的陋見,這種淺見似與用“奴隸”來統稱各種“奴”的術語不明概念不分的淺見如出一轍。作者認為,西方古代城邦國家的概念和模糊不清的族邦國家概念不適合套用於中國先秦史;古代社會所體現出的宗法社會特徵依然屬於封建社會的範疇之一,並不適合作為一個時代的社會總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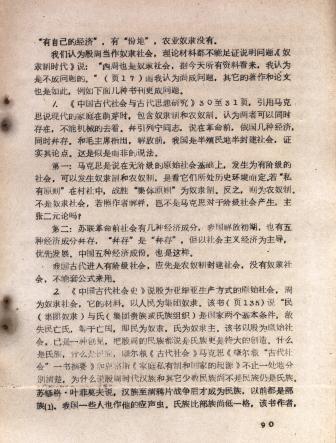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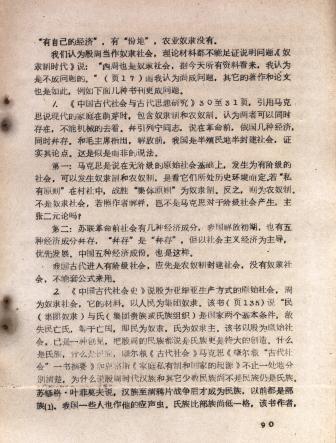
本書內容摘要
作者在對眾多甲骨文、金文的文字考證中體現出諸多新穎史觀和獨到見解,不一而足。作者充分肯定了郭沫若先生於古文字研究上的高深功力和取得的大成就,同時,又完全否定了郭沫若先生以一些甲骨文、金文為據來解釋先秦社會形態時所呈現的治史輕率態度和常識性錯誤。作者認為,在改革開放前30年的主張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的學者們當中,許多人是古文字學家,或考古學家,或文學家,或哲學家,並非現代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學家,不少人缺乏歷史科學的基本素養和客觀求是精神,少數人完全就是“主流史學”(官方意識形態史學)的應聲蟲,假馬列主義史學的“奴僕”,他們偽造古史30年的危害是巨大的。為此,應該實施“史學改革”。這是作者在梁啓超史學當年提出“史學革命”口號的基礎上發出的順應改革開放時代潮流的呼籲,其意義和影響至大至深已為作者開拓的“無奴學派”(簡稱無奴派)群賢學士取得的重大成果所證明。
撰著意圖
作者聲稱,本書撰著的動機並非僅僅限於對中外“奴”詞及其詞組“奴婢”、“農奴”、“奴隸”、“奴婢制”、“農奴制”、“奴隸制”、“奴隸社會”的咬文嚼字之辨以及真理與謬誤之爭,滿足於恢復古史本來面目和消除以往長期流行於世的“階級鬥爭史學”的危害,而是意欲弘揚嚴謹的歷史科學,以科學化的歷史學與邪教的政治史學進行分庭抗禮,展開人性與奴性的角力較量,以取得作者首倡的“史學改革”的實踐成果。為此,作者於書中再次向1979年出席長春史學盛會的80多名史學家發出了時代挑戰。至於作者的深層意圖,書中已經一語道破,即“為了弄清這些外來詞語或術語,搞清西方學者筆下的外文‘奴’詞到底是何義,余認為大有必要對世界古代文明國家的一些外文‘奴’詞和相關的術語以及社會等級作一番具體的解析,以為余自認為自己提出的‘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這一史觀‘具有世界普遍性特徵’建立一個有力的史料可靠依據和佐證。”可見作者野心勃勃,意欲構築和弘揚中國人自己開創的具有“世界普遍性法則或原理”的史觀。這與作者意欲構建“中國生活學”所倡導的洋為中用又竭力反對崇洋媚外的史學思想同符合契,又與作者於本書中多次強調“洋馬放洋屁並非都是香屁”的主張具有一致性。
圖書特點
體例新穎
作者從“考”甲骨文“奴”字入手,引出與此相關的世界性詞語“奴婢”、“奴僕”、“奴隸”等術語、概念、制度和社會形態之“論”。這種論述體例或著述形式,具有獨具一格的開拓創新形式。
甲骨文字考證廣泛
本書在吸取甲骨文專家的研究成果基礎上,不僅精剖微考了眾多與“奴”字相關的甲骨文字,而且深入細考辨析了先秦史上社會身份階層中被一些學者長期張冠李戴為“奴隸”的“臣””、“眾”、“眾人”、“庶人”、“民”、“鬲”、“隸”等大量甲骨文字,對其進行了自成一家之言的解析,對以郭沫若先生為代表的眾多“有奴論”學者的觀點或主張進行了全面反駁,其批判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對甲骨文字相關“奴”詞的廣徵博引,具有非同一般之特點。
外文“奴”詞及其相關術語的解析蝕精入微
作者從考證蘇美爾的圖符文字、楔形文字,巴比倫楔形文字,印度古文字;希臘古典文字;羅馬拉丁文字中有關“奴”詞及其“奴隸”、“奴婢”、“奴僕”、“農奴”相關詞組和術語的語義入手,進而導出世界一些文明古國經歷的“奴婢制”、“農奴制”或“奴隸制”及其社會形態的異同之論。如此基於巨觀視野的論述,呈現出在世界學術界迄今為止有關“奴隸社會論”的漢牛充棟論著中難得一見的特點。
論理邏輯性強
作者著力於“奴”詞及其“奴隸”、“奴婢”、“奴僕”、“農奴”等詞義“考”之明晰精確,重視這些術語或概念“論”之邏輯分析合理,嘗試將歷史語義學、文化語義學之“論”導入詞義之“考”,以多重研究法來全面解明“奴”詞及其“奴隸”、“奴婢”、“奴僕”、“農奴”等詞義和概念的歷史變化以及它們具有的文化與社會內涵和外延。從考察“奴”詞及其“奴隸”、“奴婢”、“奴僕”、“農奴”等相關詞組和術語的歷時性演繹,探討近代以來中外“奴隸”概念對接過程中“奴隸”、“奴隸制”和“奴隸社會”被泛化以致被“濫用”的原因,堪為本書論證獨到之處且呈現出論理邏輯性強的特點。
史料豐富
本書不僅使用了大量中文文獻和考古學成果,還使用了大量外文史料。運用史料之豐富可說難以找到與之匹敵的同類作品。
研究時間極長
作者對中國是否存在奴隸社會問題的思考始於20世紀30年代。從此斷斷續續研究此問題長達近40年,呈現慢工出精作的較高學術價值的特點。
綜合研究方法融會貫通
作者於論證說理中運用中國傳統訓詁學和西方歷史語義學、歷史考古學、歷史考證學、歷史人類學和歷史比較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對相關問題展開了符合客觀事實的入精剖微分析和論證,呈現出綜合研究方法融會貫通的特點。
論述風格
作者於書中宣稱:由於本稿以《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之“否定式”題名展開論述,以否定和對比研究形式來論證余之持論,論述過程中自然難免點名道姓否定了我國一些主張奴隸社會存在論者的觀點,行文過程中難免一些措詞用語實非中聽之言。觀點相異,孰是孰非,自有公論。而余糾正指誤或否定之筆意,旨在對事不對人,於此特予說明。“黃現璠史學”所體現出的這種直言不諱秉筆直書的論述風格在本書有著充分的展現,它與以往的“宗派史學”(占據話語特權的所謂主流史學中的三論五說堪為典型代表)、人云亦云的“風派史學”以及你吹我捧的“教條史學”顯然有別。從本書的論述風格中可以一目了然,世間學者言及的“黃現璠史學”,本質上表現出“黃現璠批判史學”的特質,這源於中國清代學者崔述和“東京文獻學派”的雙重影響。
意義
如果說建國初期黃現璠先生於1957年首先挺身而出否定“奴隸社會存在論”以及主張“奴隸社會跳躍論”或“奴隸社會跨越論”召來了“身敗名裂”和蒙冤受屈22年的厄運,那么,在鄧小平英明領導的改革開放新時代,黃現璠先生相繼發表和公表的“無奴論”一系列論作以及由此發展的“奴隸社會跳躍論”或“奴隸社會跨越論”史觀,不僅為接下來逐步形成和壯大發展的“無奴派”確立了一個歷史起點,為歷史研究的“中國中心觀”確立指明了方向,同時還為“黃現璠史學”自我確立的歷史地位建立了一種前途光明的未來信仰。黃現璠於《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無奴論”主張及其史觀問世所具有的重要意義,集中表現在五個“破除”和三個“建立”:
一,破除教條主義的局限;
二,破除“規律至上論”的主觀論;
三,破除學術研究“公式化”的格局;
四,在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的古史研究中破除“唯我獨革”、“唯我獨尊”的“一言堂”定式;
五,破除中國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長期存在的“西方中心觀”或“歐洲中心觀”。
由此破舊立新,在這五個“破除”的基礎上建立了三個嶄新的學術思維體系:
一,跳出教條主義思維的陷阱,創建中國古代史新體系思維;
二,走出“西方中心觀”思維誤區;樹立學術研究“中國中心觀”;
三,擺脫“五種形態論”束縛,構建“社會形態發展跳躍論”或“跨越論”體系。
社會影響
儘管這些論著發表和公表後黃現璠遭受了一些人“非公開化”的口頭冷嘲熱諷和惡毒謾罵,但卻得到了史學界眾多有識之士大義凜然的“公開化”支持和回響,造成了較大的影響。正如莫金山教授指出:“1979年,黃現璠教授發表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廣西師範學院學報》1979年第2、3期)。文中指出:‘我堅決主張我國歷史上沒有奴隸社會,漢族沒有,少數民族絕大多數也沒有。希臘羅馬奴隸制社會仍是人類歷史發展中的特例,不是通例。’文章發表後,得到張廣志、胡鐘達等人的支持。據筆者粗略統計,目前史學界發表此類文章已近百篇,各種跡象表明,‘中國未經歷奴隸社會’的擁護者日益增多。”[21]西安理工大學人文學院王長坤、魯寬民、尹潔等教授於合撰的《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研究綜述》一文中明確指出:“粉碎‘四人幫’後,特別是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史學領域的研究氣氛非常活躍,中國古史分期的研究也出現了新的勢頭……‘中國未經奴隸社會論’又再度悄然興起。1979年,黃現璠教授發表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文中指出:‘我堅決主張我國歷史上沒有奴隸社會,漢族沒有,少數民族絕大多數也沒有。’‘歐洲的希臘、羅馬由氏族制社會變為奴隸制社會,就不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世界通例,而是歷史特例。’文章發表後,得到張廣志、胡鐘達、沈長雲等人的支持。而且擁護者越來越多,近年來發表的此類文章已近百篇……目前這一派(即無奴學派)正像趙光賢教授在《文史知識》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樣:現在又重新被人們所重視,擁護者好像越來越多,有一種漫燃的現象。相反‘中國奴隸社會論’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戰。”[22]而青海師範大學原校長張廣志教授的話語最能說明他治學嚴謹的態度,他先後說“事實上,從時間先後講,帶頭第一個衝破這個禁區的是當時已年屆81歲高齡的黃現璠老先生,他的文章題為《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刊登在《廣西師範學院學報》1979年第2、3期上。隨後進入這個禁區的才是張廣志。”[23]“新時期主張中國無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說的學者有黃現璠、張廣志、胡鐘達、沈長雲、晁福林等。”[24]復旦大學陳淳教授繼而指出:“1979年黃現璠首先發表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論文,接著張廣志也於1980年發表了《略論奴隸制的歷史地位》一文。到了1982年,越來越多的人趨向於奴隸社會並非人類歷史發展必經階段的看法,殷商並非奴隸社會幾成歷史學界的共識。”[25]這些有識之士的主張充分反映出黃現璠先生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主張中國無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說的第一人,這不僅表現在時間上,而且還反映在思維觀念的大膽突破以及學術觀點的推陳出新和影響廣泛等空間上。由此逐步在中國史學界形成了一個具有典型“問題性”學派特徵的“無奴學派”(簡稱無奴派),湧現出大量“無奴論”學術成果。
內容摘介
我國由原始社會進入階級社會,開始於殷代,是大家公認的。殷代為奴隸社會,也是眾僉議同,成為定論,甚至成為禁區……我認為上述定論,大有問題,值得商討。
黨中央……號召全國人民思想再解放一點。我不揣淺陋,把憋在心中三、四十年的意見,編寫成此文,以請教同好專家。一得之愚,是否有當,聊表野人獻曝之意。接下來的長篇大論,亦算是余兩年前(1979年)向出席長春全國史學盛會並共同默認中國歷史存在奴隸社會的史學界80餘位代表發出挑戰的繼續,於此懇望史學界各位前輩和同仁積極應戰。
作者在長篇大論考證了甲骨文“眾”字之後說:……郭沫若先生利用甲骨文、金文和古文獻並結合考古史料來研究殷代的社會,富有創新性,具有“郭式二重證據法”的特點,學術上並不遜色於“王(國維)式二重證據法”。只不過郭先生的政治意識太強,對“奴隸”先入為主之見根深蒂固。為了滿足自己構建先秦“奴隸社會”的主觀願望,他不惜從“太陽下耕作的農民”中挖掘“奴隸的痕跡”,其文字遊戲是這樣開場的,即先將在“太陽下耕作的農民”形容為“農民在日下從事苦役”。苦役往往與奴隸同日而語,如此一來,“奴隸的痕跡”呼之欲出,繼而補充點郭式文學筆墨和其他牽強附會的史據,再蓋上一頂自以為正統的“馬克思史學”大帽,先秦農民便等同於奴隸了。這種三段式邏輯在以郭沫若先生為代表的主張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的學者們中普遍可見。事實上,郭先生已經正確地認識到“殷末周初稱從事耕種的農夫為‘眾’或‘眾人’,”但他為了滿足“五種社會形態說”,非要從農夫中去找“奴隸的痕跡”,無異於無中生有削足適履多此一舉。試問:同在太陽下耕作的農民,古代與現代的區別無非就是古代農民生產工具相對落後些,至於在苛捐雜稅上,先秦農民比民國時期的農民可要輕鬆得多。何以從古代農民中可以引出“奴隸的痕跡”從而導出“奴隸社會”之說,而民國社會就無人認為是奴隸社會呢?古代與現代的農民是同質的,同質的東西是可以通過比較研究學加以比較研究的,古代與現代的農民在“性質”上沒有任何區別,主張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的學者們硬要從政治上以階級鬥爭理論加以其階級屬性的區別,以致於在史壇上熱衷於“中國古史分期討論”幾十年,至今依然無結論。這種連基本詞語、術語或概念都不分又不講求學理學據的泛奴隸化爭論,只是一味迎合政治需要,即便再討論500年,結論依然會遙遙無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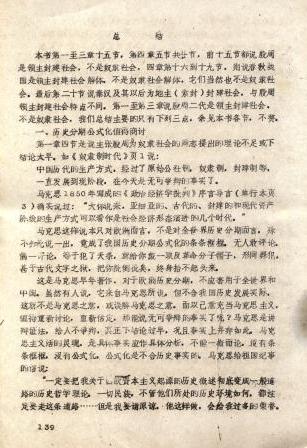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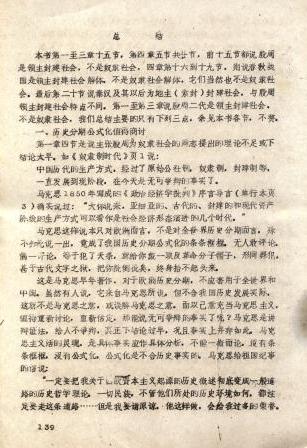
本書內容摘要
作者在長篇大論考證了金文“民”字形字義和《盤庚》篇所言“民”之後說:……周代銘文中的惠於萬“民”和人“民”,皆指周族百姓,似乎具有《尚書·泰誓中》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名譽和《尚書·盤庚》所言“恭承民命”的地位,這類“民”與郭沫若先生筆下的盲眼奴隸之“民”有著天壤之別,實不知郭先生依據為何又以何據從金文“民”字形義中想像而看出了“奴征”?即便老朽政治上如何眼拙或文盲無知,尚未致於到古文字學上左眼視力已近半盲而看不清金文“民”字的地步。假如郭先生解金文“民”之說成立,商王盤庚豈不是在“恭承瞎奴之命”,周康王治下的“萬民”豈不都成了“萬名瞎奴”,全國周民一遍“瞎奴”,這與史料記載的事實相距甚遠,則與“郭式空想臆斷治史法”的認識十分接近。以史為據,郭氏解“民”為“盲眼奴隸”之說,從史料記載上難覓蛛絲馬跡,實可謂無中生有荒誕不經,可以休矣。古人造象形字(卜辭、金文),其字形義不可能以社會最低層之“奴隸”形象為據,大多以自然、習俗、實物之象為據,這似乎是世界古代象形文字之一般造字通例,亦為世界文明古國之象形字皆無“奴隸”兩字之緣由之一。
注釋
1
張廣志:《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
2
李學功:《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8年第1期。
3
黃現璠:《廣西僮族簡史》第22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
4
《廣西日報》1957年8月~11月刊載的“批判極右分子黃現璠”等大量系列文章。
5
雷海宗:《世界史分期與上古史中的一些問題》,《世界歷史》1957年第1期。
6
李鴻哲:《“奴隸社會”是否社會發展必經階段?》,《文史哲》1957年第10期。
7
謝扶民:《兩年來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的基本總結》,《民族研究》1958第1期。
8
胡仲達:《揭露和批判雷海宗的反動史觀》,《光明日報》,1957年9月12日;柳春藩:《揭穿李鴻哲反馬克思主義的惡毒手法》,《史學集刊》1957年第2期。
9
李洪岩:《20世紀30年代關於奴隸社會的論爭》,《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2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10
黃現璠:《儂智高起兵反宋是正義的戰爭》,《廣西日報》,1962年4月2日。
11
黃現璠:《土司制度在桂西》,《僮瑤族史科學討論會論文集第一集》,1962。
12
黃現璠遺稿:《民族調查與研究40年的回顧與思考》(下),《廣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
13
傑弗里·G·巴羅撰,覃曉航(摘譯):《中越邊境上的宋代壯族》,《世界民族》1990年第1期。
14
喬治·V·H·莫斯利:《中國南方邊境的鞏固》第88頁,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3年。
15
冢田誠之,甘文杰(譯):《新中國成立前後有關壯族論著的比較研究》,《廣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16
祝中熹:《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一點淺見》,《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
17
陳吉生:《試論壯族著名史學家黃現璠對20世紀中國新史學實踐與建設的貢獻》,《廣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18
1980年1月28日,北京《歷史研究》編輯部曾來電催促黃老儘快寄去該文,黃現璠因該文主要內容已於前年公表,婉言謝絕。見黃現璠:《我國古史分期應該重新估定——古代沒有奴隸社會》前言,1980年11月30日。
19
黃現璠:《同我國歷史學者商榷一個問題——我國有沒有奴隸社會》,廣西師範學院油印,1980年8月10日。
20
同上。
21
莫金山:《中國奴隸制問題討論的世紀末回眸》,《學術研究》1996年第7期。
22
王長坤、魯寬民、尹潔:《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研究綜述》,《唐都學刊》2005年第3期。
23
張廣志:《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第240頁,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
24
張廣志:《中國古史分期討論七十年》(上),《文史知識》2005年第10期。
25
陳淳:《社會進化模式與中國早期國家的社會性質》,《復旦學報》200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