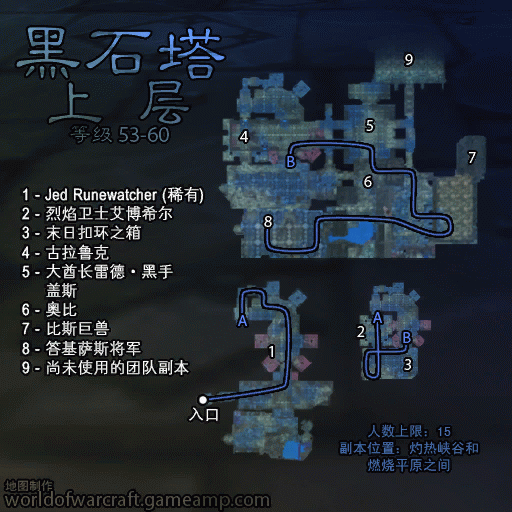黑石塔之戰是遊戲《魔獸世界》的一個重要戰役和世界事件。是獸人部落和人類聯盟之間的一次轉折性的戰役。
基本介紹
- 名稱:黑石塔之戰
- 性質:重要戰役和世界事件
- 意義:轉折性的戰役
- 屬於:《魔獸世界》
內容介紹,後記,
內容介紹
在第二次獸人戰爭的最後幾天,當獸人部落對人類聯盟的勝利近在咫尺的時候,艾澤拉斯的兩個最強大的獸人之間爆發了一次可怕的分裂。當奧格瑞姆·毀滅之錘為進攻洛丹倫的首都——這將是一次可能粉碎掉人類聯盟最後的殘餘力量的進攻——作最後的準備時,古爾丹和他的追隨者擅離職守出海而去。獸人部落因為古爾丹的背叛而損失了將近一半駐軍,暴怒的毀滅之錘不得不後撤,因此錯過了戰勝人類聯盟的最佳機會。
極度渴望力量的古爾丹痴迷於獲得神格,他拚命派出搜尋隊去尋找被埋葬在海底的薩格拉斯之墓,他相信在那裡隱藏著終極力量的秘密。古爾丹已經將他的獸人同胞全部出賣給燃燒軍團作為奴隸,他壓根沒有想過所謂對毀滅之錘盡職的問題。在暴掠氏族和暮錘氏族的支持下,古爾丹成功地在海底找到了薩格拉斯之墓。但是當他打開這遠古地牢的大門時,古爾丹發現等待他的只有無數瘋狂的惡魔。
為了懲罰那些臨陣叛逃的獸人,毀滅之錘命令他的部隊去追殺古爾丹並押回叛變的獸人。古爾丹為他的魯莽付出了代價,他被自己釋放的瘋狂惡魔撕成了碎片。在他們的領導者死後,叛變的氏族很快就被毀滅之錘憤怒的軍團擊潰。雖然叛變被鎮壓了,但獸人部落已無法彌補這次內亂所帶來的損失。古爾丹的背叛給聯盟帶來的不僅是希望,還有重新集結的時間以及發動反擊的機會。
洛薩爵士看到獸人部落內部產生了分裂,就不失時機地集合了他最後的部隊,將獸人逼回了已被毀滅的艾澤拉斯的腹地。在那裡,人類聯盟包圍了獸人在黑石塔的據點。
安度因·洛薩爵士緊緊盯著鋪在木桌上的作戰指揮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習慣性地敲擊著桌面。地圖上近乎零亂地畫滿了黑線和紅線,紅線的層層進逼和黑線的步步後退告訴洛薩爵士,這一場曠日持久的收復失地的戰爭,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了。在過去的幾個月里,由安度因·洛薩爵士、光明使者烏瑟爾和海軍上將戴林·普洛德摩爾率領的聯盟軍隊一路南下,經過浴血奮戰,終於將由強大的酋長奧格瑞姆·毀滅之錘領導的嗜血獸人部隊,從飽受滄桑歷盡折磨的洛丹倫大陸上趕了出去。現在,獸人部隊已經被聯軍逼回到了已被毀滅的艾澤拉斯,對於豪情滿懷的洛薩來說,勝利,只剩下一步。
然而征程中的最後一步卻往往是最難走的一步。洛薩的目光落在了地圖邊緣的一塊黑色的區域上,所有的黑線與紅線都在那裡止住了腳步,開始了糾結。區域中心的一個黑點更像是一塊巨大的石塊,壓在爵士的心頭——那是毀滅之錘與他那些無畏的戰士們在洛丹倫最後的據點,同時也是他們最強大的支柱——位於黑石塔的火山城堡。雖然洛丹倫聯軍已經將城堡團團圍住,但是險峻的地勢以及厚重的城牆再加上勇猛的守軍,讓曾經節節勝利的聯軍無計可施。隨著糧草輜重的日漸減少傷兵亡卒的日益增多,火山城堡的城門卻未曾破開哪怕是一指寬的距離,軍中——尤其是幾個年齡較大的高階貴族騎士,已經流露出了明顯的厭戰情緒。一想到那幾雙躲躲閃閃的眼神和時常在下面竊竊私語的嘴唇,洛薩將手攥成拳頭,狠狠地砸在了木桌上,似乎是希望火山城堡的城門能夠像自己拳頭下的木桌那樣輕易便出現裂痕。然而,這並不能給遠處的城堡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傷害,洛薩也很清楚這一點。於是他嘆一口氣,將被自己拳頭震倒的蠟燭重新扶了起來。幸好,指揮圖只被燒去了一個小角。
洛薩扯了扯自己已經開始花白的鬍子,圍著桌子又晃了幾圈,決定把這個惱人的問題放到晚上再去考慮。現在正是陽光明媚的中午,為什麼要把自己委屈在昏黑的營帳里搞得昏頭漲腦呢。想到這一點,向來樂天的老爵士便舒展了眉頭,挑開營帳的帘子走了出去。忽然而至的陽光讓洛薩感到一陣目眩,他索性閉上眼睛仰起頭,讓午日陽光的溫暖盡情揮灑在自己臉上。站在門口守衛的士兵看見洛薩舒服的表情,笑著說:“今天是好天氣呢,長官。”
洛薩手搭涼棚望向遠處,一塊陰影隨即落入了他的眼帘——黑石塔。就算是如此明媚的陽光也洗不去圍繞在黑石塔周圍的黑暗與陰冷。望著自己前進路上的最後一塊障礙,老爵士剛剛舒展開的眉頭又皺了起來,如果不能儘早將這個城堡攻打下來,那么洛丹倫聯軍幾個月的努力就會功虧一簣。勇猛的毀滅之錘又將率領著自己嗜血的部下,將戰火繼續燃燒在洛丹倫大陸。
一聲嘹亮的軍號聲打斷了洛薩的思考。遠方,一支騎兵部隊開始了對火山城堡那厚重的大門再一次的衝鋒,長劍和盔甲在陽光的照耀下發出耀眼的光芒;相應的,城堡內也響起了沉重的鼓聲和獸人部落蒼涼的戰歌。
“今天的第二次衝鋒?”洛薩問身邊的守衛。“是第二次衝鋒,長官。”守衛回答。“是圖拉揚在指揮吧。”洛薩又問了一個早已知道答案的問題。 “是圖拉揚在指揮,長官。”
“喔……”洛薩強迫自己將心頭的不安壓了下去——他實在是擔心再失去自己部下,自己的孩子們了——哪怕只是一個。然而這在戰爭中又是多么不現實的願望,只有他最信任也是最欣賞的部下圖拉揚——雖然他還只是一個低階的騎士,才能幫助他把這種不安消除一些。
隨著騎士們靠近城堡的大門,廝殺聲沖天而起。
今天是個好天氣。然而對於交戰的雙方來說,天氣的好壞,沒有任何的意義。
“雙方面都住口!圖拉揚,退後!”安度因·洛薩爵士分開圍觀的騎士們,站在劍拔弩張的兩方——剛從戰場上下來的圖拉揚和幾名高階貴族騎士面前。雖然沒有攻破火山城堡的城門,但是對於圖拉揚在戰場上的勇猛表現,整個聯盟軍是有目共睹的。本來洛薩想好好的表揚和激勵他一下,也順便提高一下他在軍中的威望度。沒想到這個急性子的年輕人,剛剛從戰場上撤下來,盔甲還沒有脫,就和軍中的幾名高階騎士吵了起來,這不由得讓洛薩感到一陣陣火大。但是一看到年輕的騎士浸滿了鮮血和汗水的臉龐以及創痕累累的盔甲,老爵士便一下子心軟了下來。但他還是威嚴地喝道:“站到我身後去!”
幾名貴族看到洛薩的到來,一邊放開了已經抓住劍柄的手,一邊氣哼哼地向洛薩說道:“你可來了,爵士。現在你手下的這些年輕人,可真不知道如何尊重上級了,慣著部下也不能讓他們忘記了什麼是長幼尊卑啊,你說是不是,爵士?”說完,幾道輕蔑的目光還繞過洛薩的肩膀,落在身後氣得只喘粗氣的圖拉揚臉上。
洛薩勉強從臉上擠出一絲笑容出來:“眾位都是高階的騎士,犯不上和一個小孩子生氣。關於他,我回去會好好教訓他的。”說完,洛薩測過臉對身後的圖拉揚喊道:“還不向幾位大人道歉?”
“可是……”年輕人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可是什麼可是!跟我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洛薩向幾名貴族行了一個騎士禮,轉身離開了,他似乎已經忘記了“道歉”這件事情。
圖拉揚愣愣地呆了一下,急忙跟著老爵士離開了。既然老爵士忘記,他更樂得不去見那幾張貴族的死面孔。
營帳後面的小樹林裡,洛薩和圖拉揚一前一後緩步走著,陽光透過樹葉之間的空隙投射下來,在地面上形成一塊塊斑駁。
“您為什麼要我和那些膽小鬼道歉?”圖拉揚終於得到了發泄的機會,憋在胸口的怨氣一古腦地爆發出來,“如果不是他們不及時的增派援兵,我也許就能把火山城堡的大門給撞開了!我的長劍與大門只有三個獸人戰士的距離!”
“住口!”洛薩爵士的怒火也一下子勃發出來,轉過身怒視著圖拉揚,“你以為事情都像你想像中的那么簡單么!”
年輕的戰士被洛薩突然爆發的怒火一下子嚇到了,他無法對自己最尊敬的上司做出任何反駁的舉動,所以他只有選擇低下頭。
洛薩注視著那亂蓬蓬濕漉的長髮,還有那寬厚的肩膀,一腔怒火都化成了對孩子的愛憐。他舉起手,狠狠敲了一下圖拉揚的腦殼:“傻小子,你什麼時候才能不讓我操心啊……”
圖拉揚疼得咧了咧嘴,不過隨即開心的笑了起來,他知道,洛薩爵士已經不再生他的氣了。他抬起頭,向洛薩做了個鬼臉:“您不能輕點啊,我這可是剛從戰場上下來。”
洛薩對這個部下無計可施,他微笑著搖了搖頭,又念叨了一句:“傻小子……”
兩個人又恢復了一前一後散步的狀態,沉默了一會,不甘心的圖拉揚再次在後面低聲叨咕:“要不是……哼……我早就……”
洛薩停住了腳步,閉上眼仰起頭,讓剛才那場攻城戰在腦海中重新過了一遍,然後轉過頭緩緩地問圖拉揚:“圖拉揚,我最信任的戰士,你告訴我,平心而論,在今天那種形勢下,我再給你增派三百名騎士,不,四百名!你能夠敲開火山城堡的大門么?”
圖拉揚看著老爵士的眼睛,發現爵士並沒有和他開玩笑的意思。他皺起眉頭思索了一會,然後正正經經地回答:“第一,我們沒有那么多的增援部隊,如果從光明使者他們那裡借,就會讓整個包圍的形勢有所混亂,讓毀滅之錘有機可乘。第二,就算是給我那么多的增援……”年輕的戰士遲疑了一下,“也很難……成功。”
洛薩爵士再一次地笑了,他不但喜歡圖拉揚的熱血,勇敢,更喜歡的他這種坦誠。更何況,年輕的戰士只要在頭腦冷靜的情況下,分析起戰局來不必任何一個人差。他拍拍年輕戰士的肩頭:“所以說,你們不用太苛求那些貴族。他們也付出了很多呀,土地、金子、糧食……我們的給養都是要靠這些貴族啊……”
“土地、金子、糧食……”圖拉揚低聲重複著,攥緊了自己的拳頭。小臂上剛剛有些收口的一處傷口再次迸裂開來,鮮紅的血爬過戰士的手背,滴在草地上。“而我們付出的是什麼?是鮮血,還有……生命……”
洛薩爵士長嘆一聲,無可奈何地避開了這個令他無比傷感的話題:“我們不談這個了,接著陪老傢伙在這個還有陽光的樹林裡多走走吧。”
“是的,長官。”圖拉揚悄悄擦去了手背上的血跡。
兩個人又走了一會,陽光的溫暖和樹林中瀰漫著的芳香讓他們心情都略微好了一些。洛薩撿起一根枯樹枝隨意地比劃著名,忽然間問了一句:“圖拉揚?”
正被兩隻打架的甲蟲分了心神的圖拉揚猛地回過神來,往前踏了一步:“什麼?長官。”
洛薩將手中的樹枝挽出了幾個劍花,很隨意地問道:“你和毀滅之錘是交過手的,而我也沒少教導你的劍術。憑你感覺,我和他交手,誰的勝算更大一些?”
“當然是您!”圖拉揚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那個野蠻的獸人酋長怎么能和您,整個洛丹倫最偉大的戰士相提並論!”但是望著洛薩逐漸嚴厲起來的眼神,年輕戰士的聲音也越來越低,“其實……我和毀滅之錘交手的那一次,他在撤退而我在追擊,也就過了三招。平心而論……不過……”
“不過怎樣?”洛薩追問。
“就我的感覺,要是你們真的交起手來的話……”圖拉揚吐一口氣,說出了自己不願意接受的現實,“應該是勢均力敵。”
“你的感覺和我一樣,”洛薩緩緩說道,“不管怎么說,毀滅之錘也是一個偉大的戰士,否則他也不會將戰火燃燒了幾乎整個洛丹倫大陸……”
“偉大的戰士……未必吧,”圖拉揚不服氣地撇嘴,“一個獸人而已。不過……那時候,我接了他一錘,從長劍柄上傳過來的巨大的壓迫力,和您在戰鬥時發出的魄力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當然,我們都是戰士,”洛薩將目光投射到遠方,喃喃地道:“拋開戰爭的對立面關係,拋開信仰、種族這些東西不談,我和毀滅之錘,我們的內心,我們的魂魄,都是相同的——都是渴望勝利渴望戰鬥的戰士的魂魄……”
“戰士的魂魄……”圖拉揚低聲重複著,“相同的……”
“是的,相同的!”洛薩也重複了一遍,忽然感覺腦海中有一個模糊的想法正在逐漸成型,但是這個想法是什麼卻完全不知道,只是隱約感覺這個想法對於自己來說是如此至關重要。他越想越想不清楚,於是開始一邊繞著圖拉揚急急走著,一邊用手中的枯樹枝不停地敲著自己的頭,好像這樣就能把那個由一團混沌包圍著的答案敲出來一般。圖拉揚被上司完全搞糊塗了,頭隨著洛薩轉著,擔心地小聲問:“長官?”
洛薩隨手敲了圖拉揚腦袋一下,皺著眉頭道:“別亂出聲,沒看見我正在思考問題么!”他又轉了幾圈,忽然停下來,將枯樹枝全部折成一截一截,但是還沒有任何的光亮出現在他混沌的腦海中。他狠狠地砸了身邊的一顆大樹一拳,阻力和疼痛讓他渾身一震,圍繞在真正答案周圍的混沌與迷茫竟也隨之解開了。豁然開朗的洛薩爵士開心地大笑,竟然拉著圖拉楊的雙手跳了起來——困擾著他很長時間的難題終於得到了解答。可憐的圖拉楊被爵士拖著雙手跳來跳去,完全不知道在自己這個長官在乾什麼,慶幸的是洛薩跳了一會變恢復了平靜。
“多謝你,你讓我找到了答案。”洛薩看著自己的戰士,喜悅不可抑制地從眼神中潑灑出來。
“謝我?什麼答案?”圖拉楊仍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我尋找已久的答案。”洛薩沒有正面回答圖拉楊的問題,忽然表情變得一本正經,“聖騎士圖拉楊,傳我的命令!”
“是,長官!”圖拉楊馬上立正站好,他知道洛薩將會有重要的命令讓他來傳達。
“從明天開始,所有對火山城堡採取的攻擊行動全部停止,所有的部隊原地待命!”洛薩一字一頓地說道。
“停止攻城?”圖拉揚懷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聽錯了命令。
“是的,全部停止。”洛薩看著圖拉揚,讓他看到自己眼中的堅定。
隨後洛薩將手搭上自己心愛孩子的肩頭,緩緩地說道:“相信我,我的孩子。我已經找到了……解決這場戰爭的鑰匙。”
洛丹倫聯軍與獸人軍隊的對峙,已經進入了第三天。雖然糧草的嚴重不足已經迫使洛薩將軍中的口糧配備一減再減,雖然幾個高階騎士又開始對洛薩的按兵不動牢騷滿腹,但是洛薩還是心定氣閒地每天待在自己的營帳中,雖然總是全副武裝,但除了將自己的長劍和盾牌擦得鋥亮,其餘連火山城堡看都不看一眼。雖然對自己的長官還是充滿信心,但是年輕的圖拉揚終於還是坐不住了。他決定去問個明白。
剛走到洛薩爵士營帳的門口,幾個高階騎士氣沖沖地走了出來,斜睨了圖拉洋一眼,接著大踏步地走掉了。圖拉揚不屑地望著他們的背影,揭開營帳的帘子走了進去。營帳的中央,洛薩爵士若無其事地仍然在擦拭著自己的盾牌。
“他們又來乾什麼?”圖拉揚問道。
“他們?”洛薩向盾牌上呵了一口氣,然後拿起手中的鹿皮起勁地擦著,“他們來問什麼時候發起總攻,還說這么待一天就讓他們損失很多的金子。”
“現在想起來要出擊了?”圖拉揚哼了一聲,“當初想什麼來著。”
洛薩爵士笑了一下,不置可否。
“是啊,我也正想問,”圖拉揚忽然記起了自己來的目的,將身子向前湊上去,“長官,我們時候總攻?”
“總攻?我什麼時候說要總攻了?”洛薩做出一副無辜的表情看著年輕的戰士。
“什麼?您不是說……找到了……解決戰爭的鑰匙么?”圖拉揚急得話都說不利索了。
“傻小子,你以為解決這場戰爭的鑰匙,就是總攻么?”洛薩敲了一下圖拉揚的頭,這是他最喜歡對這個部下做出的動作。
“那是什麼啊?”圖拉揚頹然退了回去,頭腦也隨著這一擊變得糊塗起來。
“唉,要是不合你說明白,看來你天天都要來煩我,索性和你說明白。”洛薩拍了拍身邊的椅子,示意圖拉揚坐到自己的身邊。“這是那天你給我的啟發。我只是在想,如果換一個角度,我現在被困在火山城堡裡面,而圍困我的獸人軍隊,一直不停地發動猛烈攻勢的部隊,忽然間一連幾天一點動靜都沒有,我該怎么樣去考慮這件事?”
圖拉揚仔細思索了一陣,然後回答:“如果是我的話,我會認為獸人部隊有恃無恐,忽然間多了大量的後備軍和糧草,不急於拿下這場戰爭。對方不急的話,我就會著急,急於尋找解決這個膠著狀態的辦法。”
“就是這樣!”洛薩高興的說,“而且,根據我們與獸人這么長期的交手情況來看,雖然他們大肆侵略的目的我們還不清楚,但是我們能夠知道他們絕對不是樂於偏安於一禺的種族,苟存在一座城堡中,絕對不是他們想看到的。他們一定不會讓這種局面長時間地保持下去。要知道,獸人是不屬於我們這塊大陸的產物,在這種不利的情況,他們一定會樂於回到自己的根據地,積蓄力量,以圖再次來戰。就想你說的那樣,我們不急了,他們反而會急。那段時間獸人部隊瘋狂的防禦,只不過是對於我們的進攻做出的本能反應。反過來如果我們採取防守,他們就會考慮如何進攻了。”
“是啊是啊!”圖拉揚面露喜色,“當他們突擊的時候,我就可以設下埋伏將他們一網打盡了。不過……”他搔了搔腦袋,“這是我給您的提示?”
“不,你給我的提示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洛薩爵士的表情忽然變得嚴肅起來,他站起身慢慢走著,“戰魂。”
“戰魂?”圖拉揚沒有明白。
“是的,戰魂,戰士的魂魄。”洛薩緩緩說著,“這是我體內的戰魂給我的答案,毀滅之錘的戰魂也一定給了他相同的答案。他迫切地想與我一戰,證明誰才是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戰士,就如同我想與他戰鬥一樣。渴求勝利,證明自己的強大,這就是戰魂的指引。更關鍵的是,我和他都十分清楚,我與他這一戰是不可避免的,我勝,則獸人軍隊會一敗塗地;我敗,則使人類軍隊無法繼續前進。對於不想將戰爭長期化下去的毀滅之錘,必定會來和我做這場決鬥的。知道我那天和你說,解開這場戰爭的鑰匙什麼么?那就是我和毀滅之錘的生命啊。”
圖拉揚完全感受到了洛薩爵士語調中的悲壯蒼涼,他低下頭,喃喃地說:“您不會失敗的……”
“當然!”洛薩爵士恢復了自己平常樂天的語氣,“我只是想儘快地結束這場該死的戰爭,回到我的城堡,每天下午可以躺在我那小花園的樹蔭下,喝一杯淡淡的麥酒,然後想著烤得松松嫩嫩的小羊肉做成的晚飯,再加上洗得很乾淨的葡萄……”
“是啊是啊!”圖拉揚笑了笑,看著面前的老爵士。不知道為什麼,一股無盡的悲哀和蒼涼從他的心底湧上來,瀰漫了他的雙眼。圖拉揚驚恐萬分地迫使自己將這種不詳的感覺壓制下去,他使勁攥緊了自己的雙拳。
洛薩爵士似乎發覺到了年輕戰士的異常,“怎么?”他看了看自己的部下。
“沒什麼沒什麼,”圖拉揚極力讓自己保持正常的神態,“到時候我還要去你的城堡去喝光你酒窖中藏的好酒呢。”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有這種不好的感覺,。
洛薩皺了皺眉,剛想追問下去,一聲嘹亮的軍號聲將他的注意力吸引過去。一名騎士來不及通報便沖了進來:“毀滅之錘放棄火山城堡,發動全軍突襲!”
“果然來了!”洛薩爵士興奮地摩拳擦掌,“傳我的命令!所有聖騎士上馬,跟在我的後面,一個也不許掉隊!馬上出發!”他拿起盾牌,手指向桌上的地圖的一點:“我們在燃燒平原等著他們!”
馬嘶聲,口令聲,鐵器的碰撞聲,瞬時間充滿了整個軍營。圖拉揚跟在洛薩的身後,不經意地掃了一眼桌上的地圖。地圖上燃燒平原那一塊區域,不知道什麼時候被蠟油弄污了,黯紅,像乾涸的血痕。
燃燒平原。如血的夕陽將面對面站著的兩名戰士的影子拖得很長,總有一種蒼涼的味道。這是整個大陸最偉大的兩名戰士,命運促使他們站在這裡,展開一場關乎於人類與獸人生死存亡的戰鬥。他們兩個將會把鮮血拋灑在這片草原上,為了自己,更是為了自己的部下、自己的同胞、自己的種族。在他們各自身後很遠的地方,是他們各自的屬下,神情嚴肅,一動不動,他們也都知道不能打擾這場戰鬥。
人類領袖觀察著獸人酋長,獸人酋長也在觀察著人類領袖。安度因·洛薩爵士一手握長劍,一手執塔盾,眼神如大海般深邃悠遠;奧格瑞姆·毀滅之錘酋長雙手握著巨大的戰錘,力量隨著肌肉的躍動流淌在暗綠色的皮膚下。
“你我這一戰,是不可避免的,是遠古之神安排你我在此一戰。”洛薩緩緩開口說道。
毀滅之錘點點頭:“我不崇拜你們人類的神,我只知道,為了我,為了我的部落,我的氏族,我都要讓你喪生於我的戰錘之下!”
洛薩將長劍與塔盾互擊,發出清脆的聲音:“我的長劍和盾牌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毀滅之錘不屑地笑笑:“你們人類只會躲在盾牌的保護之下,從來不敢光明正大地戰鬥!”
洛薩爵士沒有受獸人挑逗的影響,他緊緊盯著對方的雙眼:“你我這一戰,已經沒有任何人能夠阻止,也不需要任何人來打擾!”
毀滅之錘回視著對方,沒有再說話,只是緩緩地點了點頭。
洛薩將長劍平執於胸,向對方致意。毀滅之錘將戰錘高舉過頂,發出嘹亮的戰呼。隨後,兩人各自退後一步,盯著對方的身形再也沒有絲毫的放鬆。兩人之間的空氣仿佛凝固了一般,兩人都在將自己的氣勢、姿勢調整到最好,同時也在等待對方出現哪怕是一點的疏忽。終於,在夕陽落下最後一點餘輝的時候,兩個人同時發出驚天的吶喊,頃刻間,神兵與神兵碰撞出的火花直衝雲霄。
這一場震古爍今,關於到整個大陸命運,在大陸兩名最偉大戰士之間展開的戰鬥,終於開始了。
毀滅之錘的判斷失誤讓他在一開始的時候便落入了下風,他原以為對方的塔盾完全是為了防守而存在的,沒想到洛薩展開的進攻居然有百分之七十是由盾牌發動的。而且外表看起來不是很壯碩的洛薩,一衝上來發動的卻是如此剛烈威猛的招式,這也讓獸人戰士有些措手不及。碩大的盾牌發動的揮舞,撞擊讓始料不及的毀滅之錘忙於應付,完全處在了守勢。即使是這樣,盾牌周圍銳利的刃口也讓他的身上多了幾條不深的血痕,有好幾次毀滅之錘完全是靠著戰鬥的本能才躲過洛薩猛烈迅捷的攻擊。不利的局面讓肌肉在獸人酋長的雙頰上蹦起,在洛薩又一次將沉重的盾牌向他揮過來的時候,他沒有像以前那樣選擇用戰錘去搪架,而是迅速退了兩步,隨即把戰錘在胸前一揮,企圖給追上來的洛薩迎頭一擊。洛薩在對方開始後退的時候便意識到這是個陷阱,他靈巧的側身滑過獸人,長劍的光芒從盾牌的空隙中閃出,掃向獸人的腰側。這一次又迫使毀滅之錘再次彎腰後躍,同時立起戰錘,擋住了長劍再一次的攻勢。洛薩爵士的攻擊如影相隨,盾牌和長劍的聯合攻擊向暴風一般卷向毀滅之錘,連續的撞擊戰錘,試圖在對手的防禦中撕開一個缺口,讓手中的長劍有機會痛飲敵人的鮮血。然而毀滅之錘的防禦是近乎完美的,每一個動作都恰到好處,揮舞得密不透風的戰錘讓對方每一次的進攻都無功而返。而長時間的猛攻讓洛薩體力上出現的小小的漏洞,也讓毀滅之錘抓住機會慢慢從完全的守勢扳回成攻勢。戰鬥的雙方知道,這場戰鬥已經不再是戰技的挑戰,而是意志、體力的挑戰。
一輪清冷的圓月升上了天空,天已經完全黑了,戰鬥卻仍然在繼續。
高昂的鬥志和無比的責任感讓兩名戰士展開忘我的攻擊,讓他們的動作無比迅捷,精神已經完全超越了肉體而存在。攻勢持續不斷,嘹亮的戰呼與兵刃的嘶鳴讓觀戰的人類、獸人士兵們感受到了無比的壓力。不知道有多少次,他們都認為洛薩的長劍會突入毀滅之錘的防守,刺入毀滅之錘的咽喉;或是毀滅之錘的戰錘從天而降,砸中洛薩爵士的胸膛。但是這場戰鬥卻沒有停止,每一次完美的進攻卻都無功而返,而每次防禦都在哪怕是最後的一個瞬間奏效。兩名戰士喘息著、怒吼著,力圖讓自己的意志壓倒對方的意志,視圖讓自己的兵刃撕開對方的肌膚,都在等待著對方哪怕是一點點的破綻。
忽然之間,一片厚重的烏雲擋住了清冷的圓月,仿佛上天也不忍看見這兩名最偉大戰士的廝殺。隨著一聲轟雷,豆子般大小的雨點在頃刻之間拋灑了下來,整個戰場也隨之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人類騎士和獸人部隊都保持著隊形沒有動,他們焦急地用耳朵去辨聽兩名戰士的戰果,卻沒有人有一點動作的衝動。因為他們知道,無論發生了什麼情況,這場偉大的戰鬥,只屬於他們兩個自己。然而他們只能聽到忽而一片沉寂,忽而兵器又猛烈地撞擊了一陣,卻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狀況。忽然洛薩發出了幾聲低吼,毀滅之錘隨之發出一聲痛苦的吶喊,隨即又恢復了沉寂。周圍的幾千名士兵不知道這幾聲呼喊意味著什麼,他們的眼前一片漆黑,他們的面孔被雨點打得生痛。
雨來得快,去的也快。很快,烏雲散盡,圓月又將清冷的光芒撒在了燃燒平原上。當戰士們的眼睛看到在戰場上的情況時,人類騎士們發出了震天的歡呼,而獸人部落中卻唱起了蒼涼的戰歌——戰場中央,毀滅之錘躺到在地,憤怒地喘息著,他頸間逼著一把精亮的長劍,洛薩的劍。
“殺了我!我幾千的部下將會隨著我的魂魄與你們奮勇作戰!”毀滅之錘怒視著洛薩。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洛薩竟然將長劍緩緩地收了回去。“你想乾什麼?是想羞辱戰敗者么?”毀滅之錘發出憤怒的嘶喊。
洛薩面無表情,似乎在傾聽著獸人戰士們悠遠蒼涼的歌聲,沉默了一會,他望向地上的毀滅之錘,緩緩說道:“你沒有戰敗。在這場突如其來的泥濘中,我的戰士長靴要比你的鹿皮靴占了很大的便宜。我想要的是一場公平的決鬥,我的魂魄不會接受這樣結果的勝利。”
毀滅之錘翻身站起來,再次握緊手中的戰錘,高喊道:“人類!你那虛偽的慈悲會讓你嘗到苦頭的!”
長劍盾牌,與巨大的戰錘,再次攪到了一起。
這場戰鬥,已經持續了整個夜晚,東方已經微微泛出紅色。洛薩爵士與毀滅之錘的體力早已在數不清的攻擊與防禦中消耗殆盡,每一個動作都給他們的肌肉帶來無比的撕裂感,平時得心應手的兵器也變得無比的沉重,似乎喘息都變得如此的困難,只是堅強的意志和戰士的本能促使他們做出一個個動作。洛薩用盾牌擋住戰錘的又一次揮舞,從手上傳過來的震動讓他知道對方的力量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然而自己卻無法讓手中的長劍刺到自己想要攻擊的角度。忽然,他的胸膛如暴裂開一樣,在那一瞬,他的腦中變得無比清明,一首神聖的戰歌在其間反覆詠唱,一個低沉、威嚴的聲音在對他訴說著什麼。洛薩的眼前一陣發花,嘴裡面一陣發乾,他閉上眼微微一笑,他知道,他的神,為他指引了方向。胸口突然傳來的撞擊讓他感覺到一陣無比的輕鬆,他再也忍不住喉頭的甘甜感覺,一口鮮血噴出來,吐在了緊握的盾牌上。他睜開眼睛,看見了毀滅之錘無比詫異的表情,獸人酋長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隨意的一擊,竟然宣告了這場戰鬥的結束。
洛薩再也握不住手中的長劍與盾牌,他仰天倒了下去。巨大壓力的突然消散,以及突然到來的毫無防備的勝利,讓體力早已透支的毀滅之錘踉蹌了幾步,終於也跪倒在了洛薩的身邊,他目不轉睛地看著自己值得尊敬的對手,卻發現人類戰士的臉上沒有失敗和受傷的痛苦,取而代之的是滿足的喜悅。
毀滅之錘猛喘了幾口粗氣,讓近乎於乾枯的肺部呼吸新鮮的空氣,他看著對手的臉,慢慢的說道:“我勝的很僥倖,我不知道為什麼你……”
洛薩爵士微笑著搖了搖頭,打斷了獸人酋長的話:“勝利就是勝利,我們的戰鬥沒有僥倖。”
“可是……”獸人酋長沒有感到絲毫勝利的喜悅。
“這是……我的神……給我指引的方向,”巨大的疼痛和逐漸模糊的意識讓洛薩的言語變得支離破碎,“在聽到你的戰士們為你詠唱戰歌的時候,我的神告訴我,我的鮮血……將會填平人類軍中的溝壑,我的生命……將引領人類的勝利……”
獸人酋長的眉頭緊緊皺了起來,他在思索著對手話語中的意義。
“當然,你的勝利……是實實在在的……”洛薩爵士的鼻翼猛烈地翕張著,“能夠與你戰鬥,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驕傲的事情……”
“我也是一樣。”獸人酋長的心中泛起了對這個對手無限的尊敬,在這一刻,他們拋棄了種族、信仰的桎梏,他們用戰士的魂魄在直接對話。
洛薩爵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眼神中忽然泛起異樣的光彩,言語也變得清晰、流利,他用近乎威嚴的口氣對毀滅之錘命令:“扶我起來!給我我的長劍和盾牌!我不能讓我的魂魄躺著升上天空!”
尊貴的獸人酋長默默地執行了老爵士的命令,他扶起洛薩,將他的長劍與盾牌放到他的手中。洛薩將長劍緊緊擁在胸前,用巨大的盾牌費力地穩住身形,面朝著東方。
毀滅之錘將手中的戰錘高舉過頂,發出了雄渾的吶喊。這不是表達勝利的喜悅,而是為一個戰士魂魄的遠去致意。
洛薩依著自己的盾牌,感覺到力量正一點點的離自己而去。他努力地掙開眼睛,想起自己可愛的部下們,想起自己幽靜的花園,想起清涼的麥酒……一個神聖的聲音喊了一聲他的名字。
在朝陽從東方升起的第一縷晨暉映入老爵士眼帘的時候,這個人類軍隊的領袖,洛丹倫大陸最偉大的戰士,呼出了胸膛中最後一口氣。
洛薩死了。
軍中臨時搭建起來的聖堂,幾名高階騎士低吟著聖歌,在他們中間,是年老爵士被擦拭得乾乾淨淨的屍體。盔甲上的銹跡和凹痕都被很小心休整好,他的盾牌與長劍依然守護在他的身邊。盾牌上的血跡沒有被擦掉,那是洛薩爵士的鮮血,每一隻觸到這塊血跡的手指都會不由自主顫抖。在洛薩的腳邊,是他最喜愛的部下,年輕的聖騎士圖拉揚。
年輕的戰士雙目赤紅,頭髮蓬亂,雙手緊握,以至於指甲深深地嵌入了手掌之中,刺出了血。他站起身,聲音如同聖堂中的空氣一般冰冷:“你們沒有資格對這位戰士吟唱高貴的戰歌,至少現在沒有。”
幾名貴族停止了詠唱,面色陰沉,用憤怒的目光注視著年輕的戰士。
“你們這些人,已經被利益熏昏了頭腦,已經忘記了你們加入聖騎士團的宗旨。你們只會為了一些蠅頭小利而爭吵不休,只會讓驕傲、野心、貪婪弄污了你們身上神聖的徽章。如果你們真的忘記了當初的誓言,如果你們真的忘記了騎士受勛前夜的沉思和禱告,如果你們真的忘記了長劍撫在自己肩膀上那一刻的榮耀,你們就因該好好看看躺在你們身邊的人!他才是一名真正的騎士,一名真正的戰士!你們那些貪婪、那些利慾,在他無私的犧牲面前,又是多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他為了整個洛丹倫而戰鬥,他為了我們而死!在他高貴的靈魂面前,由你們嘴裡面唱出的聖歌簡直就是一種褻瀆!”
貴族們低下頭,因為憤怒和羞愧而面無血色。年輕的戰士因為激動和悲傷幾乎不能成言,當他看到洛薩爵士近乎於聖潔的面容時,勇氣與力量再一次從身體的深處湧出來。他大踏步上前,將洛薩爵士沾滿了鮮血的盾牌抓在手中,緊擁在胸前,用盡全身力氣吶喊著:“我會繼承這面榮耀的盾牌!我會高舉著它去燃燒平原,來到獸人戰士面前,告訴他們真正的騎士精神永遠不滅!我會高舉著它去憂傷沼澤,來到毀滅之錘的面前,告訴他人類戰士是多么的堅強和不屈!我會高舉著它走遍洛丹倫大陸的每一個角落,來到每一個人面前,告訴他們這裡棲息這一個多么高貴的靈魂!”
圖拉揚仰望天空,將盾牌高舉過頂,大聲吶喊:“遠古之神!”他清澈的聲音像是號角般喚醒了每個人,“我呼喚你!請守候這個高貴騎士的魂魄!請賜予我們這塊保受摧殘的大陸像他聖潔魂魄般的氣息吧!”
聲音在聖堂上方久久地環繞,圖拉揚俯下身,吻了吻洛薩爵士冰冷的手指。終於,年輕的戰士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像個孩子一般,捂住雙眼啜泣了起來。
後記
圖拉揚在洛薩爵士的葬禮之後將悲傷的兄弟們組織起來,發動了一次成功的反擊。洛丹倫和艾澤拉斯大陸上裝備最簡陋的部隊在憤怒的驅使下摧毀了毀滅之錘的獸人部隊。剩餘的獸人別無選擇,只能逃向他們最後的根據地——黑暗之門。圖拉楊和他的戰士們追擊潰逃的獸人部隊,一直追過了充滿腐爛氣息的憂傷沼澤,直到黑暗之門的所在地。在那裡,在巨大的黑暗之門腳下,四分五裂的獸人部落和強大的聯盟軍隊進行了這場戰爭中最血腥也是最後的一場戰鬥。在兵力對比懸殊的情況下,被他們的嗜血本性逼瘋的獸人根本無力阻擋暴怒的聯盟軍隊。毀滅之錘被俘虜,並被押送回洛丹倫大陸。在那裡,他那四分五裂的氏族被收容所的高牆囚禁了起來。